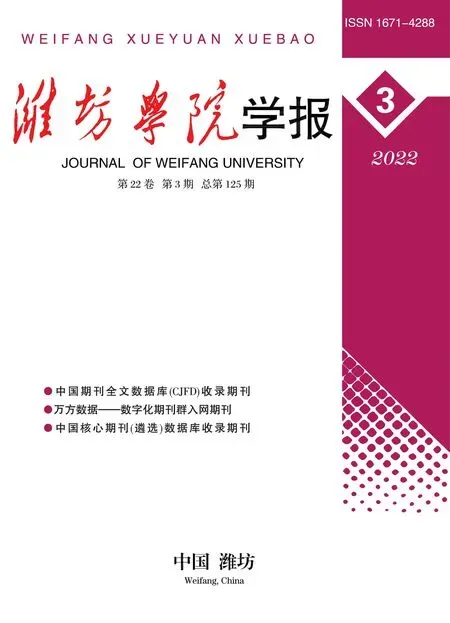浅论宋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特征
2023-01-06赵瑞军
赵瑞军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的发展中,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1]在宋代,儒学汲取了诸家学说和思想,从汉唐训诂笺注发展到重义理、经致用的新儒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社会学诸层面,对中国哲学、史学、伦理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儒家慈善为道德基础的慈善活动,也随之儒学在全社会的普及与发展,走向了一个新阶段、新高峰。《宋史·食货志》曰:“宋之为治,一本仁厚,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2]宋代官方慈善机构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活跃,慈善活动主体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慈善内容涉及到社会救济的各方面,慈善事业发展呈现出繁盛景象,特征明显。
一、儒家思想引导
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德”的培养。儒家的“德”包括“内德”和“外德”。“内德”强调“德”内育,是培养慈善意识的内在自觉性;“外德”强调“德”的外用,是开展慈善活动的外在方式。儒家学派也一直把慈善活动内在和外在的伦理道德,加以推崇。《礼记·王制》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3]《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儒家学派不仅强调培养个体的伦理道德,而且还强调培养政治上的伦理性,主张以德治国,通过政治方式,在全天下实施德治。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即民为国家存亡之根本,“君为轻”即民为君民关系之主要力量。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4]孟子通过总结朝代更迭的历史经验,得出民心向背乃国家存亡之根本,得天下必须得民心的论断。战国后期的荀子则更形象地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5]的观点。儒家“仁爱”思想不仅强调对亲人的爱,也强调政府对百姓的爱,把爱民视作一种政治伦理,要求统治者实施“仁政”。慈善活动作为“仁政”的重要内容,就成为了统治者应当坚守的义务与责任,具有了伦理化和政治化的特征。宋代是先秦以后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在宋代,儒家道统独尊地位得以确认,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仁政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儒家慈善思想得到普及,社会各阶层的慈善意识得以增强。《宋史》载:“宋之为治,一本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2]宋代“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统治者也常以“本朝立国以仁”自视。宋徽宗曾下诏:“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6],把慈善活动当作仁政的重要内容。
二、统治者倡导
宋代是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重要时期,在朝廷及地方、官方及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全社会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慈善体系,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在我国古代慈善史上具承前启后的地位。受儒家价值观、宗法制等因素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为封闭型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生活。这种个体分散式经营、封闭性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对小农经济带来破坏,使百姓四处流亡逃生,在社会上产生大量流民。流民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小则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大则发生暴乱,影响朝代更替。因此,完善的社会慈善体系,会帮助受到灾害的弱势群体度过难关,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君主统治。《唐会要》载唐玄宗时宋璟奏称:“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着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昔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7]宋璟认为子路出私财救济贫民,此为“人臣私惠”,容易坐大势力,不利于君主统治。然而,宋代君主几乎没有受此观点影响。宋代君主不仅对官办慈善机构、地方慈善组织给与了提倡与支持,对于官员及士大夫们的个人慈善活动也予以提倡支持,这就在全社会形成了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这主要是因为宋代自然灾害繁多,土地集中,城市贫民不断增多,这极易形成大量难民、流民,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这三个时期,社会矛盾相当尖锐,为有效控制社会,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君主统治,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借助慈善事业来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稳定统治秩序,并将其作为实施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学者统计,北宋各类自然灾害发生lll3 次,南宋发生825 次,合计1928 次。其中,明确记载死亡人数逾万人者,或有骨肉相食、积尸满野相类记载的特大灾情23 次;死亡逾千人者,或毁坏农田数万顷,或受灾面积“数百里”“赤地千里”,或流民数万,或灾害发生后官府有较大赈灾措施的大灾情48 次;死亡人数逾百人,或灾情发生在两路以上者,或损田数百顷,或毁坏民居、仓库、官署等千区以上,或雹如卵,数县乃至一二十州县受灾,或六级以上、七级以下强烈地震灾害的严重灾情249 次。[8]除灾害外,宋代土地兼并也非常严重,“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9]同时,“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负担沉重,由此导致的城市贫民和游民数量增加,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时期更是发展到高峰。”[10]宋代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土地兼并非常严重,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稳固封建统治,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大力倡导慈善救济,创建了各类慈善机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士大夫推动
受儒家思想及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影响,北宋的士大夫阶层亦积极倡导或参与慈善事业。北宋大儒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1]张载继承发展了孟子“尽性知性知天”思想,认为充分发挥人自身的“德性之知”,就能体悟“天地之性”,把握“天理”,达到“天人合一”,而“大其心”的最高境界就是“民胞物与”。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12]他认为,天地是所有人的父母,所有人都禀赋了天地属性,都是同胞,都是一家人,人人都应相互爱护;而那些鳏寡孤独、老幼病残,身体有残疾、处境困难之人,更应当同情并予以爱护扶助。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主张把儒家伦理学说转变成人们生活中的准则,主张超越一切等级、宗法及有形隔阂,胸怀兄弟姐妹之谊,同情劳苦大众的博爱思想。作为宋代理学奠基者及新儒学的开创者,程颢对慈善思想的阐述,与张载“大心”、“民胞物与”的思想基本相同。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13]“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3]程颢强调要把天地万物都看做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要去关心、爱护它,只有具有浑然与物同体的情怀,才能达到“仁”的境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慈善思想亦有阐述。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14]他还从体用、性情等角度对仁与爱进行了区分,认为:“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15]“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15]张载、二程、朱熹等都是宋代大儒,在政界和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儒家“仁爱”及慈善的阐释,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参与慈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儒家思想将慈善作为一种受内在道德力驱使的自律要求,行善与否成为个人的品性或道德操行的外在体现,成为个人无他律的主动性社会行为。宋代的士大夫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纷纷以儒家乐善好施之义相激,积极从事慈善事业。从而在宋代众多的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既是慈善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慈善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积极践行儒家“道统”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及政治功能,在其推崇参与下,宋代慈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不管是组织化程度还是规模化提升,都远远超越以往历代。
四、社会跟进
在儒家慈善思想的引导和刺激下,宋代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人士,碍于政策、舆论等多方面压力,普遍开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行为,使宋代的慈善事业呈现出通俗化、生活化、普及化特征。在民间,以血缘、地缘、业缘、友缘为中心的各种民间慈善组织纷纷设置,使宋代的慈善活动在社会中广泛开展,融入到了大众日常生活中,成为整个社会的通俗化活动。如曹尧咨“计所有之田,岁收亩六升以入之,遇年岁则发以遇年饥则发以粜。量必宽、价必平,于是一方之人赖以全活者甚众。”黄虎“恤乡邻如家人:里之孤贫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饥岁,以赈以贷。泥涂断港,必梵必梁。故邑无流殍,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处乡也。”[16以业缘为中心所引起的慈善活动,主要是指基于对慈善事业同感而产生的行业性群体慈善机构。如,车若水《脚气集》载:“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17]在两宋时期,这种基层的社会慈善形式比较常见。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临安商人“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18]以学缘关系为中心所以引起的慈善活动,主要是指由于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近距离人际关系之间的相互资助。如,吴遵路与范仲淹友善,吴死后,家无长物,仲淹“分俸周其家。”章庭与黄庭坚友善,黄家有急难,“明扬未尝不竭蹙而趋事。”[16]
总结
在宋代,伴随着儒学的勃兴发展,儒家思想得以广泛普及,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统治者创建各种慈善机构,倡导慈善,为社会风尚起到引领作用;宋代儒风浓郁,士大夫以追求利济品格为己任,倡率救济,为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儒家思想及统治阶层的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使宋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