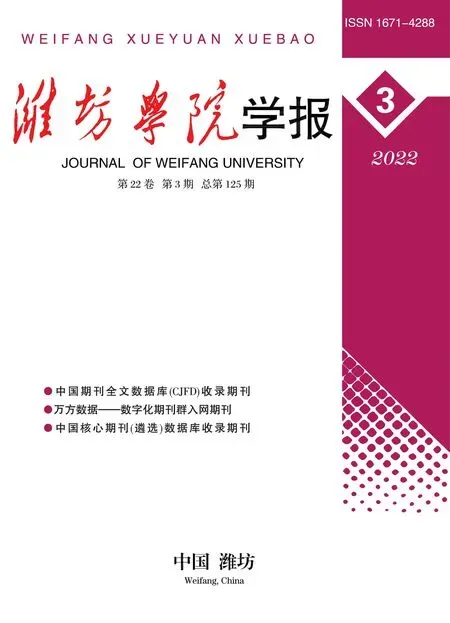陈维崧“性情论”诗学思想探论
2023-01-06郭超
郭 超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作为清初著名文学家,陈维崧各体文学兼备。他的词名甚著,为清初阳羡词派的宗主。他的骈文成就突出,被冠以清初“四六”之首。而他的诗歌创作亦颇有成,现存《湖海楼诗集》,内容博赡,风格多样。对于他的诗,前人已多有正面评价,但对其诗论,论述却不多。从现有文献资料看,陈维崧虽然没有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但在他为友人所作的一些诗文序中却零碎地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显现出独到的理论价值。本文拟对其比较突出的诗歌性情论作一简要论述。
一言为心声,性情之际微矣
历代文论中,“性情”论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最早可追溯到《诗大序》的“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诗作者采用“主文而谲谏”的表达形式,使之带上了鲜明的伦理政教色彩。经过六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发展,“性情”论逐渐转向重视个体的情感表达与个性凸显。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情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368所谓“文质附乎性情”,文采可以美化语言,但精巧华丽之美则本源于作者的性情。
作者主观性情之用,与文学创作风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专论作者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指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1]333,意思是说:气质充实情志,情志确定语言,写作精美的文章,皆与作者的性情相关。直至明清,文人学者亦反复强调文艺作品须表现作者的真实性情。正如陈子龙所言“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独至”之情才为真情,强调个体情感的真实性。“贵意者率直而抒写,则近于鄙朴;工词者黾勉而雕绘,则苦于繁缛”[2],则都是离情的表现,“均不可用”。
陈维崧诗论的基点也在人之性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人们宣泄内心思想情志的有形媒介。陈维崧在《孙豹人诗集序》中指出:“夫声音之际,抑扬抗坠之间,其关人性术者岂微妙哉”[3]10,认识到包括诗歌在内的有声表达方式,都关系到人的性情的表现。反之,人的性情的不同,造就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有声表达方式的不同,进而决定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陈维崧在守正溯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性情于诗文创作之原初影响。他在《董文友文集序》云:
夫言者,心之声也。其心慷慨者,其言必磊落而英多;其心窾爱者,其言必和平而忠厚。偏狭之人其言狷,詄荡之人其言靡,诞逸之人其言乐,沉郁之人其言哀。要而论之,性情之际微矣。[3]42
这是汉代扬雄《法言·问神》篇中“言为心声”说的引申。《文心雕龙·体性》和《中说·事君》曾从不同方向分举个案有所阐发。陈维崧的贡献在于举六种心性类型为例,就“性情影响文学风格”的问题作出一般性界说。关于创作主体的个性因素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最早是魏晋时期曹丕提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是指人先天的禀赋、气质、个性。而陈维崧所讲“慷慨”、“窾爱”、“偏狭”、“詄荡”、“诞逸”、“沉郁”等,都已不同于先天禀赋的“气”,是经过后天培养形成的人的性情特点。所谓“性情之际微矣”,主体性情的差异,又导致主体创作面貌的差异,从而形成多种文学风格共存的面貌。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如其人”的风格成说。“文如其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可以追溯至“心画心声”的说法,扬雄在《法言·问神》篇中云: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发成言,画纸成书。书有文质,言有史野,二者之来皆由于心。[4]
“察言观书”便可判别君子、小人。进一步,书言成文,画心为书,皆可由文字反观其人。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着精彩的述说,他认为:
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5]418
‘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处世上、居聚中也。罗马Seneca 尝云:‘如此生涯,即亦如此文词’,则庶几‘文如其人’之旨矣。[5]422-423
钱先生在辨析了扬雄有关“心画心声”说后,指引我们从“文本诸人”与“文如其人”两方面去理解“文”的面貌与“人”的施为之间的关系,而从天生秉性的决定作用出发,“文如其人”实为确论。
由此,文学创作中应当重视人的主观性情即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清初乐府诗创作为例,清初人对古乐府多持有批判态度,如侯方域曾云:
今人往往好为乐府。仆谓如《郊庙》、《铙歌》诸题,皆古人身在其间,铺张赓歌,今无其事而辄摹拟之,即工亦优孟衣冠而已。[6]
陈维崧的看法与此不同,他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云:
至于拟古乐府,当日贵池吴次尾师谓予以不宜多作;近则梁园侯朝宗亦以沿习为讥。然仆以为才情之士,不妨模范,用见倩眄耳。[3]91
陈维崧认为“才情”之人可以创作拟古乐府。这是他大异于时人的鲜明主张。他特别指出这种创作活动是“模范”,而不是“模拟”,正在于强调作者“才情”的主观效用。陈维崧在另一篇文章《杜辍耕哭弟诗序》中,曾描述自己阅读乐府诗的情感体会:“尝读乐府《上留田行》,见其缠绵愷恻,懇挚沉吟,未尝不临文浩叹,莫能去怀。及观陈思王《怨歌行》,寄兴《金縢》,寓言管蔡,又何其动人至是也。甚矣,友于同气之际深矣哉!”[3]35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情感碰撞,使得陈维崧对乐府诗的创作别有见地,并由此提出了“别裁伪体,直举天怀”[3]400的创作准则。杜甫曾言“别裁伪体亲风雅”[8],是讲对待前人的诗歌要采取比较鉴别的态度,再决定取舍之用。“天怀”是出自天性的心怀,强调本真,不假修饰,直接内心。乐府创作不应该专拟古人,一味拟窃,而应该取舍有度,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性情出发。对此,陈维崧提出的具体做法是:“纬昔事以今情,传新声于古意,绝无依傍,略少抚摹。”[3]400,古乐府创作虽是拟古,但经此努力,便能于拟古中见出创新,从而达到表达作者真情实意的目的了。陈维崧自己的乐府诗创作正是此理念的体现。陈维崧早期学诗于陈子龙,他在《许漱石诗集序》中云:“忆余十四五时,学诗于云间陈黄门先生,于诗之情与声,十审其六七矣。”[3]18《行路难》中自述:“昔年十四五,染翰为乐府。颇著行路辞,聊以告辛苦。”[3]36可见,陈维崧十四五岁就已从事乐府诗创作,现存《湖海楼诗稿》中共193 首。在师从陈子龙的复古道路上,陈维崧经历了一个由模拟写作到探索创新,直至抒写心声的渐进过程,表现出了活泼的生气,恰如明末顾景星《汤次曾乐府和序》中所云:“辞生于情,声生于辞……乐府之诗,心可得知,口弗能授,博习既久,油然乃生。”[9]总之,陈维崧倡导的“今情”“新声”无一不是作者发挥真性情的努力所在,是其承继“言为心声”传统命意之下的新的发展,更是打破明季拟窃风气的有力明证。
二、作诗有性情,有境遇
诗歌中的情感的表达一方面出自诗人抒发主观情志的需要,一方面又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其表现方式又随着主体外在境遇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511,明清交替的动荡环境促使文人注目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现实是一个战乱频仍、灾祸迭起的社会,文人往往都有相当艰辛和动荡的经历。
易代之际,因家国之难而产生的愤激之情非常普遍。如黄宗羲《诗历题辞》中云:“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10]身为明臣子弟,陈维崧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必然受到当时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特别是陈子龙等人牺牲后,陈维崧“狂态殊沾沾”,“自除博士籍,不受文章箝”[3]1673,俨然是一幅浪荡公子哥的形象了。但是陈维崧并没有长期地徒然地停留在逆境之中,而是对文学创作与时局之间的关系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作诗有性情,有境遇”的创作二元论主张,《和松庵稿序》云:
作诗有性情,有境遇。境遇者,人所不能意计者也;性情者,天之莫可限量者也,人为之也。……夫宋子之诗,宋子之性情为之也。……其恻恻焉不自得也,悲天命而闵人穷也,宋子之志也。吾固曰性情为之也。[3]37-38
宋荦在黄州腾达的生平境遇与其所作诗文的风格面貌是不相符合的,因为,“宋子之诗,宋子之性情为之也”,诗文中流露出的凄怆之情皆是宋荦有意为之,实是强调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境遇”是客观外在,“性情”是主观内在。“人的能动性足以泯灭‘经’、‘史’、‘诗’、‘词’之间由于艺术的或社会的功能造成的价值高低大小的差异;作家的艺术个性则是一切艺术风格都可取得共存的先决前提。”[11]同样,诗歌的创作不能以外在境遇就简单地确定它的呈现面貌,内心深处真而厚的情感应凭借着诗人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文艺才能而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维崧自身便是极好的例子。以家国之变为界限,陈维崧的诗歌呈现出前后不同的风貌。而无论是青年时代的雄丽宕逸还是年长之后的慷慨沉郁,皆是其“性情”之显。姜宸英在《湖海楼诗集序》云:
其年起,谓予曰:‘余所裒辑,自十六七岁时更今,几二十余年,然后得诗凡若干首。’然则其年之性情见于此矣。予特取其命诗之意所谓‘湖海楼’者思之,知其意不在诗,将无大拯横流、宏济时艰者其人耶?……及天下太平,干戈不用,……然陈子则年始强立,精力方锐,使其目击太平,以咏歌一代之盛,吾知又将变其慷慨激昂者,比之朱弦疏越,以奏清庙而肃鬼神。世常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其非今之谓哉![3]1825
结合自身的经历,陈维崧更强调个人境遇与性情的辩证关系,他在《和松庵稿序》中云:“余之境遇穷矣,流离困顿,濒于危殆者数矣。然而丝奋肉飞,辄不自禁,犹能铺扬盛丽,形容声色,以奉卜夜之欢,终不自知其惫也。”[3]38“以余之境遇,犹能为和乐之言”[3]38,足见陈维崧坚强的意志力和生活中以苦为乐的旷达胸怀。
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性情”“境遇”二元相关命意下,陈维崧还首次提出“年境”这一概念。其《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云:
凡诗之有编年也,讵不尚哉!夫人之年境不同时,而遭遇亦不一辙。论世者考其年境,以悉其遭遇,而因以见其人之生平,则百不一失。卫叔宝正始名士,渡江以后辄复百端交集。……子瞻动遭口语,黄州儋耳诗歌,笔势冠绝平生。俯仰年境,正复关人笔墨事。[3]7
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其经历亦有不同,所以,要熟知一个人,就不能脱离其所生长(经历)的特定的时代环境。陈维崧通过列举卫玠、谢朓、杜甫、苏轼的真实遭遇来说明,“论世者考其年境,以悉其遭遇,而因以见其人之生平,则百不一失”。所谓“俯仰年境,正复关人笔墨事”,“笔墨事”正是文字之显。言为心声,发而为文,掇笔为诗,那么透过诗文,就可以从中了解作者的生平遭遇及情感态度等等。“故先生之人,益如卫虎、谢公;而读先生之诗,亦如读浣花、坡公二集”[3]7,这成为陈维崧评阅王士禄《十笏草堂辛甲集》的思理脉络所在。不仅如此,陈维崧更是联系自身,表白心迹:
睠言节物,岂独先生。即以余之不肖,自坠地来,亦四更辛甲矣。中间自少而壮,屈指畴昔,感慨为多。怀岁月以悲来,怅流光之不再,知不独先生《辛甲集》为然也。[3]8
所谓“怀岁月以悲来,怅流光之不再”,从自己的身世经历出发,进一步强调境遇遭际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涵咏乎性情,裨系乎治术
晚明诗坛的凋敝气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存在。顺治九年(1652),侯方域在写给陈维崧的书信中曾述及。《陈其年诗序》云:
子知明诗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乎?当其盛也,北地信阳为之宗;而郎耶历下之辈,相与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则公安竟陵无所逃罪。吴趋诸君,即数十年来更变迭出,而犹存乎蓬艾之间。[12]
“北地”指李梦阳,“信阳”指何景明,二人是明前七子之代表;“郎耶”指王世贞,“历下”指李攀龙,二人是明后七子之代表。“公安竟陵”指袁宗道兄弟及钟惺、谭元春。侯方域批评,明季以前后七子为主要倡导者的复古诗风在后起之辈的手中变了味道,表达了对袁、钟、谭等人的责备之意。
针对当时的浮华不实之风,钱谦益曾提出“诗有本”的美学思想。诗应以真诚、悲愤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性情抒发为本,“本”即真性情。如此,才能言诗。诗歌有无之标准则在于是否具备“本”,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中云: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13]767
在此基础上,钱氏严肃地批评了当下诗坛“无诗”以致于走向末路的必然:
今之为诗,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而举世咸以此相夸相命,岂不末哉![13]767
陈维崧对于明末清初诗坛流于浮华、不重真情的判断与此一致。他认识到,在振兴复古诗学的道路上,应摒弃“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的行为,真正做到“为情而造文”。首先他发声的标杆便是“兴会”的提出,其《上龚芝麓先生书》云:
辞赋一道,古诗之流,远溯汉魏,近迄开天,尚矣。然八风既殊,五音迭异。江表轻浮,贻讥吴语;伧楚沉雄,亦类老革。夫“青青河畔草”,并非造设;“明月照高楼”,了无拟议。刘越石绕指之语,曹颜远合离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竞病;斛律北将,制曲牛羊。意者,干之以风骨,不如标之以兴会也。[3]88
这是陈维崧思考并首次提出关于诗赋创作的重要理论命题,涉及“风骨”、“兴会”两个重要的文论概念。究竟是以突出鲜明个性的风格或风度追求诗意,还是以灵感来临时的兴趣或情致引发诗意呢?陈维崧显然是偏向于后者的。情之所至,便会引发创作灵感,文字的真切,情感的真挚,是自然流露而非矫揉造作。这种“真情说”是青年陈维崧对明末流弊的一种思考与反驳,且一直贯穿于其后文学创作的首位。
顺治十七年(1660)南京乡试之际,陈维崧站在时风批评的高度,对明清之际的诗风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剖析,《许九日诗集序》中云:
夫诗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惟极盛所以为极衰也。数十年来,陈黄门虎踞于前,吴祭酒鹰扬于后,诗学复兴,天下駸駸盛言诗矣。然上者饰冠剑,美车骑,遨游王侯间;次者单门穷巷之子,窃声誉,博酒食,沈约、江淹,割裂几尽。甚者铜丁花合,刺刺不休焉。求其涵咏乎性情,裨系乎治术,缠绵婉笃,鼓动飞潜,何未之概见也![3]20
这段痛切针砭可以看做陈维崧对当代诗坛的总结式批评。从批评当代诗歌的不良风气入手,以“遨游王侯”之人、“单门穷巷之子”以及“刺刺不休”之人作为典型代表,提出批评,具有现实的针对性。陈维崧指出,明末诗学重新兴盛的局面,得力于先辈陈子龙、吴伟业等人的努力,如沈德潜言:“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芜,上窥正始,可云枇杷晚翠。”[14]而此时的明末诗坛面貌已然混杂不一,诗学在后代士人手中变了味道。关于当时风气,《尺牍新钞》二集《藏弆集》载邓汉仪《与孙豹人》云:
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流于肤廓,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习为轻靡,无一字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壘;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钟谭之嫡派真传也。[15]
邓氏道出其时诗坛风气日下之情状。士人虽以陈、吴两人为新学榜样,但流于表面,徒具形式,终究还是“钟谭之嫡派真传”,令人痛心。
诚如陈维崧所言,“求其涵咏乎性情,裨系乎治术,缠绵婉笃,鼓动飞潜,何未之概见也”。他从诗歌本体功能论出发,从个体与国家的角度进行诗意的评判:“涵咏乎性情”是就个体而言,诗歌应当是作者主观情志的产物;“裨系乎治术”是就国家而言,诗歌应该提供引导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与此相应,陈维崧心目中的理想型典范便是以神韵诗风著称康熙诗坛的王士禛。他在后来的《王阮亭诗集序》中云:“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3]9王士禛以其中正和平的性情、温柔敦厚的诗教,应和了朝廷“宣志达情”、“范于和平”[7]124的文治理想,受到一众文人学士与朝廷的一致激赏,确为康熙诗坛的领袖。陈维崧的此番评议正是后期紧跟时风导向做出的准确判断,也显示出他自身诗学观念上的价值取向。后来他在为冒襄子冒丹书讲论诗学时有一段话:“夫诗者,先王所以剖治忽、鉴兴废、厚风俗、鸣郁结而养性情也。故情欲其正,气欲其达,声欲其含蓄而不滥,温栗而不杂。”[3]1639强调的正是诗歌对于国家政教统治的功用所在。至此,陈维崧以“性情”为核心的诗学观念由注重个体真性的发挥上升到“治术”之政治高度,具有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