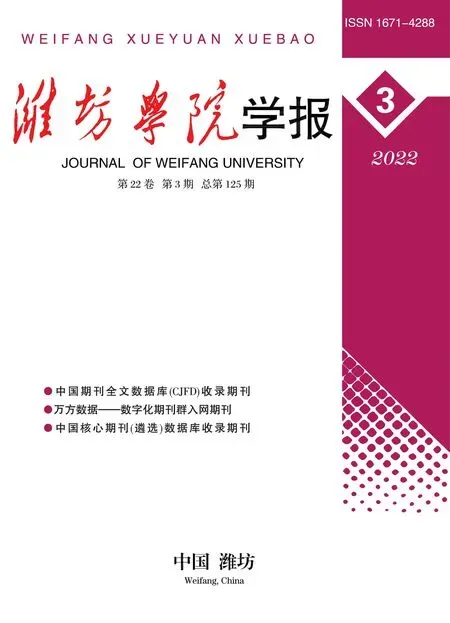《晏子春秋》词语考辨四则
2023-01-06谢祥娟
谢祥娟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晏子春秋》(以下简称《晏子》)是一部记述春秋末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著作,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语言等都有重要意义。《晏子》全书风格相近、文字统一,体例无异,语词朴实浅近,故事性很强。因此,《晏子》历来都为汉语史学界所重,被视为战国中后期重要的代表性语言材料。
研究任何一部古书,都首先要对它作正确的解读。一部古书,它到底体现了怎样的思想、应该将其归入儒家墨家还是法家名家,惟一正确的解决路径就是先去弄懂这部书的语言,看看古人在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不是主观地推测古人在书中应该说些什么[1]P518—519。《晏子》中的不少文句,前人在注解时多有分歧,究竟孰是孰非,哪一种更符合《晏子》原意呢?这往往需要从词汇、语法等方面对这些文句作细致深入的分析。笔者近来在阅读《晏子》时检核到多个前人训解有疑义的地方,本文试就其中四处加以考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说。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将封晏子,晏子辞不受。(内篇杂下第六,页216-217)①引文据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下文简称“卢《注》”):“中食:中等膳食。”陈涛《晏子春秋译注》②陈涛《晏子春秋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下文简称“陈《注》”):“中食:中等食物。”邬霄鸣《晏子春秋选译注》③邬霄鸣:《晏子春秋选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下文简称邬《注》):“中食:中等水平的膳食。”而王连生、薛安勤《晏子春秋译注》④王连生等:《晏子春秋译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下文简称“王《注》”)、石磊《晏子春秋译注》⑤石磊:《晏子春秋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下文简称“石《注》”)以及孙彦林、周民、苗若素《晏子春秋译注》⑥孙彦林等:《晏子春秋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下文简称“孙《注》”)都释为“午饭、午餐”。赵执锋《<晏子春秋>译注商补》⑦赵执锋:《〈晏子春秋〉译注商补》,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下文简称“赵《商补》”)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不对,他释“中食”为“进食之中”。书证是:一、《国语·晋语九》:“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惧其不足,故叹。中食而自咎也,曰:‘岂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叹。”二、曹魏钟会《生母张夫人传》:“(孙氏)愈更嫉妒,乃置药食中,夫人中食,觉而吐之。”——翻检《汉语大词典》,不难看出,这两个例子,赵先生当系直接转引自《汉语大词典》“中食”条。据该条,“中食”另有“佛教徒于中午进斋食”和“普通饭食”两个义项,分别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和《宋史·孝义传·郭琮》例。
显然,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中”是一个表“中等”的区别词还是一个表“中午”的名词,或者如赵《商补》所言表“动作或状态的持续”,“食”是名词性的“食物”义还是动词性的“进食”义。
首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把王《注》、石《注》和孙《注》“中饭、中餐”的训释排除掉。因为,直到中古时期“中”才具有“中午”义。汉译佛经文献中有所谓“过中不食”(过了中午就不再吃饭了)的说法,如三国吴康僧会(?—280)编译《六度集经》中的例子:
妻睹道士,勃然作色,讹留设食,虚谈过中,道士退矣。还山睹乌,呼名曰:“钵”。乌问曰:“自何来耶?”曰:“猎者所来。”乌曰:“已食乎?”曰:“彼设未办,而日过中,时不应食,故吾退耳。”
其中,“中”就是“中午”的意思。在同期的中土文献中却几乎见不到“中”作“中午”用的例证,看来这个义项的出现,当是跟佛经翻译有密切的关系(译经师汉语水平不高、佛经四言体为主的形式特点等)。《汉语大词典》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例子显然书证较晚。准此,这里训“中食”为“午饭、午餐”,显然是疏于从汉语词义发展的历史角度作深入探究。
“中”的“中等”义的确很早就已产生,它是由“中”的本义“里面、中间、中央”近引申而来的。例如,《书·禹贡》:“厥赋惟上上,厥田惟中中。”《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庄子·徐无鬼》:“尝语君,吾相狗也……中之质,若视日。”成玄英疏:“意气高远,望如视日,体质如斯,中品狗也。”查《晏子》全书除本例之外的37 例,“中”无一例为“中等”义。因此循此书条例,此句“中”训“中等”的可能性也较小。
据吕思勉先生研究[2],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饮食的确是分等级的。等级的分化实取决于:1)是否食肉;2)食肉之中所食肉获取的难易。首先,只有贵者乃得食肉。所以,《左传·庄公十年》云:“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杜注:“肉食,在位者。”孔疏:“昭四年《传》说颁冰之法云:肉食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则大夫以上,乃得食肉。”杨伯峻先生注云:“肉食盖当时习语,大夫以上之人,每日必食肉也。《孟子·梁惠王》论庶人,云‘七十者可以食肉’,是一般人民非至七十难食肉。《襄》二十八年《传》载子稚、子尾之食,云‘公膳日双鸡’;《昭》四年《传》载颁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则大夫例得食肉。《哀》十三年《传》亦云‘肉食者无墨’。”[3]另外,同是食肉,尊者食难得之肉,贱者食易得之肉。《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由此可知,诸如鱼飧之类“不可胜食”的肉实为贱者所食。准此,春秋战国之时显贵者方能食肉、而肉之获取难易也是分别等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就我们查核《礼记》《左传》《国语》《论语》《管子》等有关文献,未发现对“何者为上等膳食、何者为中等膳食、何者为下等膳食”的明确记载。本例中言“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晏子摄一国相位,毕竟总有肉可食,“肉不足”是单言肉量不大,但量不大却未必代表所食不精美、不上等。
我们赞成赵氏《商补》“进食之中”的看法。下面试加补证。
先秦文献中,在由“中”作为词素组词(或者作为词组成短语)时,“中”在结构上多放在其他词素(或词)的前面,这似乎是它区别于“上、下、前、后”等方位词的一个特性。这种组合在《诗经》中特为多见,且多为“中+N”结构,N 通常是地理/方所名词。例如:
中心:《诗·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中田:《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埸有瓜。”郑笺:“中田,田中也。”
中谷:《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也。”
中沚:《诗·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毛传:“中沚,沚中也。”
中林:《诗·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施于中林。”毛传:“中林,林中。”马瑞辰通释:“《尔雅》:‘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中林犹言中野。”
中河:《诗·鄘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毛传:“中河,河中。”《吕氏春秋·必己》:“中河,孟贲瞋目而视船人,发植、目裂、鬓指,舟中之人尽扬播入于河。”《鹖冠子·学问》:“中河失船,一壶千金。”壶,指瓠类,系之可以不沉。
其他先秦文献及后世袭用例也不胜枚举。如:
中囿:《石鼓文·壬鼓》:“寓逢中囿,孔庶麀鹿。”
中野:《易·系辞下》:“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史记·淮阴侯列传》:“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胜数。”三国魏曹植《送应氏》诗之一:“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中水:《国语》“鸣鼓中水而须”。
中洲:《楚辞·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王逸注:“中洲,洲中也。”
中流:《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
中操:《文选·汉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李善注:“中操,操之中也。”
中室:《汉书·王莽传下》:“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颜师古注:“中室,室中也。”
中林:《晋书·愍帝纪赞》:“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王维《郑霍二山人诗》:“岂乏中林士,无人荐至尊。”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
中丘:刘宋卞伯玉《荠赋》:“有萋萋之绿荠,方滋繁于中丘。”明叶向高《万宝告成赋》:“遵原隰兮夷犹,溯帝泽兮中丘。”
中池:南朝梁沈约《咏芙蓉》:“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
中座:唐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十韵》:“沱水流中座岷山到北堂。”
中除: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中除不洒扫,积雨霉苔生。”
也用于表时间范畴,例如,“仲冬”在古代典籍中也写作“中冬”,所谓“中冬”,就是指冬天三月之中间一月,也即第二个月。另外,“中年”“中伏”“中旬”等并资隅反。
当然,上述这些“中+N”结构中的“中”还都是典型的表方位的名词,意思是“中间、当中”。同时,在先秦文献中以及后世文献中,可见“中+N/V”结构、表示V 这一动作或与N 有关的动作(状态)、事件进行到中间或正在进行。例证如下:
中饮:《国语·晋语二》:“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徐幹〉》:“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张铣注:“中饮谓半酣也。”
中坐:宴会中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坐,酒酣将出。”
中曲:乐曲演奏到中段。《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汉蔡邕《女训》:“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若顾望视他,则曲终而后止;亦无中曲而息也。”
中畋:在狩猎之中。汉张衡《东京赋》:“中畋四牡,既佶且闲。”张铣注:“言四马至于中畋皆翘健惯习也。”
中驾:车驾前进中。汉秦嘉《留郡赠妇》诗之二:“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踟蹰。”南朝梁吴均《初至寿春作》诗:“中驾每倾轮,当骞复摧翼。”
中酒:饮酒半酣时。《汉书·樊哙传》:“项羽既饗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颜师古注:“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文选·左思〈吴都赋〉》:“鄱阳暴谑,中酒而作。”吕向注:“中酒,为半酣也。”宋梅尧臣《和子华陪宴》:“中酒作暴谑,心亲语多剧。”
中饭:用饭之中。《三国志·魏志·王修传》“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欣于所受,俯惭不报,未尝不长夜起坐,中饭释餐。”
中筵:宴饮之中。晋潘岳《笙赋》:“尔乃促中筵,携友生。”唐王勃《秋日饯别序》:“响词辩于中筵,但觉清风满室。”唐李洞《和知己赴任华州》诗:“一道帆飞直,中筵岳影斜。”
中讲:讲述之中。宋苏轼《仇池笔记·记异》:“有道士讲经茅山,听者数百人,中讲,有自外入者,长大肥黑。”
这些例子中,“中”已经由纯粹表方位向表时间、过程义引申。当然,在“中+V”结构中,“中”也有方位名词的用例,如:
中立:立于中间,不偏不倚。《国语·晋语二》:“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韦昭注:“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
总之,古汉语中“中食”表“进食之中”是可能的,文献中不乏这种结构形式,本句似应在“中食”前断开,作“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中”上古时既没有“中午”义,“中食”也就不会是“中饭、中膳”;据《晏子》语例,“中”也不作“中等”讲,“中食”不是“中等的饭食”,这也有历史学相关研究可资证明。
二、景公出游于寒涂,睹死胔,默然不问。(内篇谏上第一,页33)
卢《注》:“寒涂,寒冷的路上。”陈《注》、王《注》辞稍异而义全同。石《注》以为“寒涂”是一地名,不详其址。赵《商补》从之,并称“从语法上分析,‘于’字作为介词,在此用作引出动作的处所,故可理解‘寒涂’为一处所”。
石《注》以“寒涂”为地名,接近原义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些。赵《商补》从之,是。但是该论证仍未触及问题根本。因为如若释“寒涂”为“寒冷的路途”一样可以由“于”介引。遍检《晏子》全书,凡言“出游于/游于”,之后所接者,前贤皆以为具体地名。例如: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于齐国曰……(内篇谏上第一,页31)公阜,卢《注》曰:“齐国地名。”陈《注》:“齐地名。”
景公游于麦丘,问其封人曰:“年几何矣?”(同上,页23)麦丘,卢《注》:“齐地名。”陈《注》:“齐城邑名。”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同上,页30)牛山,陈《注》:“山名,在山东临淄南。”
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 养之!”(内篇杂上第五,页166)寿宫,卢《注》:“又名‘胡宫’,齐的行宫。”陈《注》:“又名‘胡宫’,齐宫室名。”
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同上,页180)纪,卢《注》:“古国名。”陈《注》:“古国名,春秋时为齐所灭,故城在今山东省寿光县南。”
景公游于菑,闻晏子死……(外篇第八,页288)菑,卢《注》:“菑川。”陈《注》:“地名,其说不一,当即临淄。”
同样,本书中同“游于”结构相同的诸如“畋于”“观于”等后,所接的也多是表具体地名的专有名词: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内篇谏上第一,页40)署梁,卢《注》:“齐国地名。”陈《注》:“齐地名。”
景公畋于梧丘,夜犹早,公姑坐睡,而瞢有五丈夫北面韦庐,称无罪焉。(内篇杂下第六,页197)卢《注》:“当道的高地。”陈《注》:“道路上的土丘叫梧丘。”(按,二氏注皆当本于《尔雅·释丘》“泽中有丘,都丘。当途,梧丘”。宋邢昺疏:“梧,遇也。当道有丘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此或为例外,但想必“梧丘”也定为当时一专指名词。或与“寒涂”相类。)
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内篇谏上第一,页28)淄,卢《注》:“淄水。”陈《注》:“淄上,淄水岸上。”
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内篇问下第四,页123)转附、朝舞,卢《注》:“均山名。”陈《注》:“不详,可能都是山名。”
当然,由于年代悬隔、文献不足等原因,“寒涂”究竟是一个地名还是义指“寒冷的道路”,我们还不敢断言已经作出了确凿无疑的解释。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根据《晏子》语言条例,我们还是倾向于它是一个指称地方的专名。如果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本句所在的整篇文章,后面的内容显然都丝毫未与“寒”字有呼应或联系,试想,如果“寒涂”确是指“寒冷的道路”,《晏子》的撰著者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突出这个“寒”字呢?
三、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嘳(喟)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内篇杂上第五,页157)
嘳然,即喟然,叹息、感叹的样子。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①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下文简称“吴《集释》”):“孙星衍云:‘嘳’,一本作‘喟’,《说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字林》:‘嘳,息怜也。’则虞案:吴怀保本作‘喟’。”卢《注》、陈《注》等皆无异辞。赵《商补》以为“喟然”当训“迅疾貌”。此训或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为“喟然”立义项二,其一为“感叹、叹息貌”,其一即为“迅疾貌”,书证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例。蒋绍愚先生曾言:“在读古书的时候,看到古人对某个字有一个训释,或词典中的某字有一个意义,就不问条件,把这个训释或意义用到某一个句子里的某一个字上,这是读古书的大忌。因为这个字的这个意义能处在什么组合关系中,一般是有条件的,离开了这个条件,这个字就不可能是这个意义。”[4]蒋先生虽然是就“字”而论,毋庸置疑,诸如“喟然”之类的“词”当然也需一体对待。其实,古文献中“喟然而叹”俯拾即是,“喟然”不必非作他解。即《晏子》中“喟然叹/喟然而叹”亦有近20 例,弃“叹息貌”而训“迅疾貌”实无必要。《晏子》中状态形容词词尾“然”可以依附在动词、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或名词之后,标示动词、性质形容词、名词等向状态形容词的词性转变。“~+然”在句中主要充当状语、补语,偶尔也作谓语、宾语,有的已经凝结得很紧密,只能作单纯词看了。下面略举数例[5]:
公忿然作色不说。(内篇谏上第十八)
景公出游于寒涂,睹死胔,默然不问。(内篇谏上第十九)
公汗出惕然。(内篇杂上第九)
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内篇谏上第二)
例证多不胜举。上举诸例中“忿然、默然、惕然、蹴然”分别修饰或补充说明“作色不说、不问、汗出、改容”,尤其是前两例,“作色不说”和“不问”语义上甚至就等于“忿然”和“默然”,二者一前一后复现,有加重语气、渲染放大形状的作用,事实上,使用二者之一即可以令语义完足,去掉任何一个都不影响基本语义的表达。“喟然而叹”亦当作如是观。
数,卢《注》、陈《注》、孙《注》等都释为“几次三番、频频地、连续地、连续多次”,石《注》、赵《商补》训“快”。石、赵得之。此例中“数”当音shuò,疾、速。《礼记·曾子问》:“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郑玄注:“‘数’读为‘速’。”赵《商补》虽然认为“数”训“疾、速”,又称前文“喟然”当训“忽然”,正是由于前有晏子“喟然(忽然)”之举,才有后文晏子御者“何叹笑相从数(疾、速)也”之问。这里的“喟然”训为“叹息貌”信而有征,前面已作证明。即便“喟然”在此确训“忽然”,它所修饰的也仅仅是“叹”,下文一“终”字,表明晏子“笑”是在其叹息之“终”才发生的动作。“数”训“疾、速”,在此实际上是在说晏子由“叹息、感慨”到“笑”这两种判然分别的情绪体验之间的转变之“疾、速”。至于释“数”为“屡次”,从上下文看,晏子并无时叹时笑、沉默之后继而复又叹笑相继的行为。所以,这种解释也是没有根据的。
四、晏子对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内篇谏下第二,页57)
卢《注》释“与”作“同类”,虽可勉强说通,但仍觉于义欠妥。因为,词语训释的问题不在于说得通说不通,而在于是否切合语言事实。陈《注》“与(yù),参与,此指居其间”近是。“与”有“参与其间、在其中”义,古书中所见甚夥。《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又《僖公三十二年》:“蹇叔之子与师。”《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这三例中“与”义同于本例。
任,吴《集释》从苏舆“任,任以事也”的解释;邬《注》、孙《注》、王《注》、石《注》释为“信任”;卢《注》、陈《注》皆释为“委以重任”,赵《商补》从之,并进一步从文意上分析称,如训“委以重任”,既已含“用”义,此处不当再言“用而不任”,否则将造成语义重复。
窃以为吴氏引苏注得之。“任”有“信任”义,较早的例子或许只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王甚任之”比较可靠。《汉语大词典》所举《战国策·魏策》二中的例子:“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王闻之而弗任也,史举不辞而去。”鲍彪注:“任,犹信也。举既非之,而数见之,故王疑之。”细味文意,“任”训“任以事”可能更符合语言事实。《王力古汉语字典》在释义上是本义借义并举、常义僻义兼收的,“任”字下却未列“信任”义项,可以想见,在王力先生等字典编撰者眼中,“任”是否真有“信任”义是很值得怀疑的——要说他们没有读到《史记·屈原列传》,从未留意到这个例子,恐怕不太可能。王力先生曾说过,“如果某词只在某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的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末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不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连在同一部书里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1]P520—521。王先生在此强调在训释词语时必须特别重视语言的社会性,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阅读、注解古书时所最易忽略的问题。
让我们再看“用”。检核《晏子》全书可以发现,“用”有一个十分常见的义项,即用来表示“某人的言语或计策被采用/采用某人的言语、计策”——显然,这跟所谓“任用”或“委以重任”义分属不同的语义场。例如:
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内篇谏上第一)
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景公不用,终伐宋。(同上)
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拒而不受者哉!(内篇谏下第二)
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穷处。(内篇问上第三)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同上)
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内篇问下第四)
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内篇杂上第五)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同上)
言不用者,不受其禄,不治其事者,不与其难,吾于庄公行之矣。(外篇第七)
诸如此类并资隅反。准此,“用而不任”不妨释为“用其言而不委以事务”,苏舆注、吴《集释》释“任”为“任以事也”可谓得其正诂。
本文对数例前贤校注《晏子》中有歧解者作了尝试性分析。应该申明的是,对其中某些例子,我们也仅仅是给出了一个有倾向性的意见,为我们所赞同者也未必即为正诂,而只是代表我们的一种见解罢了。作为经由两千多年流传的上古典籍,由于时过境迁,所载历史故实容有未明;历代刊刻抄写,文献的文字句段或致舛乱——这都为我们今天准确解读《晏子》(任一部古书大都如此)带来不小的麻烦。面对理解分歧的地方,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回到语言研究的路上来,都应该从语言文字方面作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抉剔正误,作出取舍,即便不能还原文本原意,也还可以大致判定何种解释更可能切合作者的著文初衷,而这恰是从事其他任何研究都首先要作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