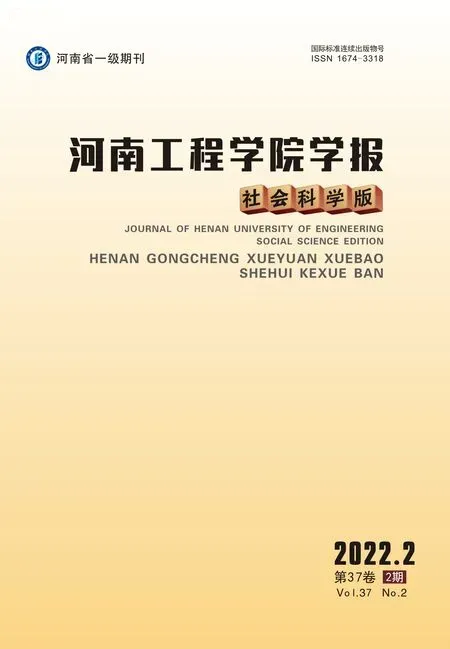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阁楼上的佛》的解读
2023-01-06郑子琨
郑子琨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阁楼上的佛》(TheBuddhaintheAttic)是日裔美国第三代女作家朱丽·大塚(Julie Otsuka)创作的第二部小说,荣获2012年美国福克纳小说奖(Faulkner Award)。小说讲述了20世纪初一群从日本远渡到美国旧金山的“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s)的生存故事。“照片新娘”是对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女性的特殊称呼。19世纪末期,一群日本青年到美国西海岸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当时复杂紧张的国际局势和美国政府的对外移民政策导致这群日本人不被允许与当地人通婚,于是他们以邮寄照片的形式在日本物色新娘,后来这群从日本远渡到美国旧金山的女子就被称为“照片新娘”。
小说自获奖以来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台湾学者林则良成为小说汉译版的第一人,任爱红[1]为其撰写书评,介绍了大塚和她的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小说中的新娘是一群不被理解的人,不仅被白人歧视,而且被丈夫管制,还被后代误解。她们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挤压,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本研究借用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和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探讨新娘们如何把握自己有限的话语权传达个人和群体的声音,透露出新娘作为受害者群体被掩盖在表层文本之下真实的心声,暗含对男性霸权社会的无声谴责和对种族主义的思考。
一、表层文本的三重叙述声音
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女性作家作品中有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2]。《阁楼上的佛》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为主要叙述者,从日本新娘的视角讲述故事,利用集体型叙述声音构建女性群体的叙事权威,最后一章转换视角,由白人承担叙述任务,日本移民变为他者,丰富对“照片新娘”的解读。此外,小说中出现了诸如作者说明之类的文本外的声音,而斜体的多次使用为个人声音的叙述提供了便利。三种叙述声音相互交错,共同完成叙述任务。
(一)文外之音:作者型叙述声音
兰瑟指出,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且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2]17-18。这里的叙述者视角等同于全知全能的作者。谭菲认为:“叙述者的声音完全来自作者本人,叙述对象被类比想象为读者大众。”[3]
小说以第一人称复数为主要叙述方式,作者型叙述声音能够对集体型叙述声音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新娘们坐船前往美国,幻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她们认为,嫁给美国的陌生人也比待在日本农村老死要好得多,因为“在美国女人们不用在农田干活,这里有足够的水稻和柴火供人们使用。无论你去哪儿男人们会先打开门并摘下他们的帽子说道:‘女士优先’和‘您先请’”[4]4。作者型叙述声音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承认了新娘对美国美好生活的设想。但是,男人们绅士行为的对象是美国女性,这群外来的日本女人被当作任人宰割的羔羊,只能言听计从:“有时候,当我们弯腰耕地的时候老板会从后面接近我们耳语几句,即使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也能猜中他的意思。”[4]23彼时的美好幻想与此时的残酷现实形成对比,讽刺新娘们的天真与无知,也衬托出美国人两面性的做派,达到双重讽刺效果。
作者型叙述声音通常以第三人称出现,在小说中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与文本中的故事内容相互呼应,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但是数量过多会使得作者权威失之偏颇,因而小说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并不多,而是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为主,目的在于构建女性角色的叙述话语。
(二)斜体形式: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指出:“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2]20
小说中出现的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中在新娘群体身上,通过第一人称单数或者赋予个体人物名字,再将个人的叙述以斜体的形式来表达,用这种个人叙述方式来弥补集体型叙述声音将人物单一化的缺陷。在介绍新娘们各自的背景时,英文采用斜体的文体形式进行叙述。斜体一般具有引用的功能,表示“引用的词、标题、外来语、书名或报刊名等,但有时作者也会使用斜体取得不同的文学效果”[5]91。例如,在文体学研究中,关于“语相分析可以讨论的方面有标点符号、大小写、斜体及空间排列等”[5]98。其中,斜体属于偏离常规的语相变异,这种变异与正体形成对比,意在突出,而且“在任何变异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作者或说话人的意图”[6]。《阁楼上的佛》中的斜体属于一种语相变异,它将原本的正体形式倾斜一个角度来引起读者的注意,目的在于同其他常规语言加以区别,传达个体的叙述声音。斜体形式与文本内容结合下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应和了集体型叙述声音,与以第一人称复数为主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一起,共同叙说日本新娘此次的美国之旅。
(三)以“我们”之名:集体型叙述声音
兰瑟认为,集体型叙述声音是“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2]23。兰瑟指出:“与作者型叙述和个人型叙述不同,集体型叙述看来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2]23
小说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为主。新娘们来到美国后成为受白人社会歧视和压迫的边缘群体,她们选择用集体形式发声,个体身份被消解,集体身份凸显。小说一开始就以“我们”作为叙述主体:“船上的我们大多数都是处女。我们有长长的黑发和扁平的双脚,我们并不是很高。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小只吃米粥,有点弓形腿,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有十四岁,还属于很年幼的小女孩。”[4]1作者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介绍了日本新娘的群体状况,这样叙述的好处就是将看似一盘散沙的成员联合起来,建构了统一的声音,借此可以把日本女性移民这样的少数族群的社会身份写入杂乱而又带有一统假象的白人主导文化中[2]298。集体型叙述方式不仅可以为书写日本新娘的不同个人经历提供叙述空间,而且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也遵循日本一贯以来的文化传统。同坐一条船的新娘们既是一个统一的日本移民群体,又是代表女性在男权社会展示自我的初次尝试,尤其是到达美国后,她们首先产生的是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肯定:“我们拥有中国人所有的优点——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有耐心,我们十分礼貌——却没有他们身上的恶习——我们不赌博也不抽鸦片,我们不会滋事,我们从不吐痰。我们比菲律宾人手脚更利索,没有印度人那么自大。”[4]20在见到和她们同样移民到美国的其他种族后,作为大和民族的新娘们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她们试图通过和他国移民比较来增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但是,“当两种不同文化交织在一起时一定会引起冲突”[7]。当日本女性代表的弱势文化与美国白人主导的强势文化发生碰撞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摧毁。随着新娘们不断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生活,她们逐渐被白人文化所同化,尤其是她们的后代完全遗忘了日本传统文化,而她们的叙述声音由最初对自我的肯定转变为对自我的怀疑,直到最后卷入历史的旋涡之中消失殆尽。
集体型叙述方式给新娘们创造了言说自我的机会,让她们把握一定的话语权向外界传达女性的声音。任爱红指出,小说作者大塚“曾表示起初她也试图采用一个新娘的视角,但后来发现这种叙述视角的局限性太大,她太想把成千上万个移民美国的‘照片新娘’未被言说的故事都写出来,而单个新娘的视角容量有限,不足以表现这一群体的多样性”[1]。第一人称复数的集体叙述形式为叙说新娘群体的故事提供了叙述手段,而个人型叙述声音弥补了集体型叙述声音统一化、常规化的缺陷,丰富了日本新娘的受害者群像,从个体视角来看,个人不同的经历和想法的加入避免了集体型叙述的单调,增强了其叙述的可信度。
二、隐藏文本:新娘们的难言之隐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讲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发生的事。”[8]这就意味着文学文本中存在两种事件: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却未发生的,从叙事学角度讲是已叙述的事件和未叙述的事件[9]。沃霍尔[10]将普林斯的未叙述事件概念进行细分,归为不必叙述者、不可叙述者、不应叙述者和不愿叙述者。小说的表层文本塑造了受害者群像,实际上在文本空白处暗藏新娘们的难言之隐,保留她们无声的抗议和沉默的谴责。
(一)不必叙述之事件:对男性霸权的讽刺
沃霍尔对不必叙述者的定义是“因属‘常识’而不必表达之事件,即不值得叙述之事件。这些事件或因是‘明摆着的’而不够‘可叙述性的门槛’,或因太微不足道、太平庸而不必表达出来”[10]。新娘们一开始就被当作隐形人,叙述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解释,好像事实应当如此。一方面,因为小说面对的主要读者是美国人,在他们看来日本女性踏入美国社会,理应顺从他们,对他们表示恭敬。在这群信佛的日本人看来,她们恭顺、礼貌、隐忍,面对与她们文化相左的他族,选择隐身保护自己无可厚非。因此,双方都默认这样的做法。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加强了对白人男性霸权主义的讽刺,美国文化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人神往。
(二)不应叙述之事件:受害者群像的新娘
不应叙述之事件即不应该被讲述出来的事件。沃霍尔认为,它是“因社会常规不允许而不应被叙述事件”,这种事件“往往违反社会常规或禁忌,因而不被讲述”[10]。最常见的不应叙述之事件是关于性或血腥暴力的描写,即使到了21世纪,人们仍旧对此避讳不已,尽可能避免提及,但是小说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描述新娘们的初夜,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发生在新娘们身上的悲剧。丈夫们首先从破坏女性身体开始,继而说服她们服从自己,奴役其精神世界,最终这群新娘无法离开自己的丈夫,只能依靠他们生存下去。而丈夫们每晚喝酒至深夜才归家,甚至有的丈夫承认自己在外另寻新欢。这种出轨的情况属于不应叙述之事件,在道德层面上任何时代都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将它作为隐藏文本,而处于表层文本的新娘们在叙述时带有指责男人的轻浮和不忠的意味,加上隐藏的出轨事件,突出新娘们的受害者形象。
(三)不愿叙述之事件:对白人社会的无声谴责
沃霍尔指出,与不应叙述者不同,不愿叙述者通常遵守社会常规,但不愿意被讲述,“不讲述并不是因为事件不重要, 或不可言表, 或讲的事件属于禁忌, 而是因为这在小说中是叙述者不愿讲述之事:讲了就是不行”[10]。新娘们给远在日本的母亲寄的信属于不愿叙述之事件。她们在信中这样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我们不再干农活了,我丈夫在一个上流家庭找到了工作,我们都搬到了城里漂亮的房子中。我长胖了。我变得丰满起来。我长高了半英寸。我现在穿内衣了。我穿着束腰衣和长筒袜。”[4]31中国有句俗话“报喜不报忧”,表面上看新娘们好像摆脱了繁重的农活,在富裕家庭中找了份工作,生活条件看似好了起来,然而她们在信中只字不提自己当保姆或做仆人的事。兰瑟在分析书信体故事《艾特金森的匣子》时曾提到作品中出现的“双声话语”,即女主人公表面上是在说“没有主体意识的妇女语言”[11],实际上是在表达她对婚姻本身“愤怒、力量、决然态度的语言行动”[11]。双声话语在女性作品中经常用来表示不宜对社会公开的内容,通常表现为表面文本和隐含文本。表面文本是社会主流所认可的叙述声音,隐含文本体现的是女性私下叙述的心灵之音,新娘们不愿叙述的隐含文本正是做白人的仆人这件事。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仆被看作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低等的工作。因此,她们为了让母亲放心,不愿意对母亲提起自己当保姆的事。另外,这也折射出物欲对人性的影响和考验。在掩盖自己女仆身份的同时,新娘们隐晦地谴责了美国物质社会对人性的束缚及从精神上奴化外来移民的行径。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热门的经典叙事学因不重视对历史语境的考察而饱受诟病,女性主义批评因过于注重文本中故事情节的性别差异而招致非议,于是二者相互吸纳补充,发展成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不同的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突出对作品中性别叙事的研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强调叙事文本生产与阐释的社会历史语境”[12]。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女性主义叙事学为解析女性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叙事视角和叙述方法提供了途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13]曾呼吁妇女要写作,她认为妇女要写她自己,这是夺取讲话的机会。拥有日裔美籍身份的大塚没有一味地选择跟随美国主流文化,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几十年前的日本,揭开祖辈们难以诉说的创伤记忆,以写作的方式再现了被忽略的“照片新娘”的悲惨历史。身为一名女性作家,大塚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传达个体和群体的话语,既把个体的声音融入集体的诉求之中,又为日本新娘构建了一定的话语权威。另外,利用未叙述事件的叙事策略可以揭示表层文本之下隐藏的真实,达到为“照片新娘”这个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发声的真正目的,呼吁人们关注这群无辜的日本移民。
小说利用叙事人称的转换实现了与不同受述者的对话。日本新娘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不仅在言说自己的苦难,而且在控诉男权社会,同时也会引起现实读者的深思。作为吸引型的叙述者,日本新娘的叙述声音“代替作者试图培养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受难者的同情”[14]。因为小说主要面向的是美国读者,所以更容易唤起人们对那个时期日本移民悲惨遭遇的认同与反思。多重叙事手法拉近了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距离,白人男性读者也会因书中日本女性的形象符合常识而表示赞同,同时又会反思自身,这部女性叙事作品在读者群体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叙事空间。
四、结语
《阁楼上的佛》以多重叙事手法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中饱受折磨与无奈的“照片新娘”无声的内心。放眼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超前积累,“照片新娘”的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她们作为“邮购新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被交易。女性等同于财产的认知没有改变,她们依然被当作物品供男性挑选,不少妇女面对家暴和强奸时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奋起反抗。文学作品是一种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媒介,作为受害者的妇女要摒弃不必要的羞耻之心,主动写作,勇于夺取属于自己的话语权,逐渐转变父系社会对女性形成的固态思维,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