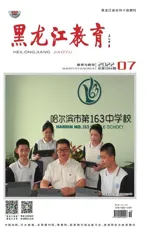高中语文教学:从阅读、理解到审美的跃升
2023-01-06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中学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中学 赵 锋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高中语文课本,不难发现,那一篇篇美若晨曦、朗朗上口的课文,既是语文知识的传播对象和传播载体,更是文学史上的臻品佳作。然而,在应试教育和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这些课文的文学性质和审美功能被冷落。缺乏对课文文学功能的正确认知,导致教师课上不再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不再注重引导学生对审美经验的体悟,习惯于偏重对知识点、文章结构或者主题意义的阐释与讲解。这样的方式使学生很难从中体验到文学之美、情感之真和心灵之净,只会匆匆浏览文字内容,囫囵吞枣般地死记硬背那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如果说,九年级以下的学生还无法真正领悟到文学之美的话,那么从高中阶段开始,探索课文跃升讲授的方式,尝试传输给高中生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就成为一种可行性的探索和文学活动交互理解、对象化接受的必然。
一、阅读:浅层学习的开端
从理论层面上看,阅读是读者对一个文本类型中不同本文的“接触”,并且这个“接触”是带有一定陌生性和主动性的行为,过程中必然带有新鲜感、摸索性和未知化的特征。从实践层面看,阅读是高中生按照课本或者课程标准要求,对具体作品进行浏览和探索的学习行为,是对作品进行无目的性观照后的“主观会见”。“会见”前,只是文字的累积与堆砌。“会见”后,有了学生的阅读行为介入,本文的价值才得以实现。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这里至少悄然阐释了三个问题:一是高中语文课本的具体课文,它是客观存在的多义的客体;二是不同时代的或者同时代的不同的读者(学生),阅读后会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三是读者(学生)的阅读行为会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或者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导致课文具有了当下性和时代特征。
读懂了姚斯暗含的思想,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鼓励学生加强对课文的预习阅读和自我学习。虽然它只是一个浅层的开端,但却是向着“走近”课文迈出的第一步。没有这一小步,就不会有“走进”的一大步。在这个阶段里,不同的学生对同一篇作品的理解定然是千差万别的。作为教师,应当正确看待这样的局面和差别的客观性,不要急于统一学生的思想与认识。因为学生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对课文的看法各有角度,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阅读基础、受教育状况、性格气质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甚至从目前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阶段来看待和阅读。这些内容构成了每个学生的“期待视野”,奠定了阅读的程度、角度和方向,或者说初步左右着他们对课文这个文学作品的接触度和喜好度。比如在讲授《咬文嚼字》一文之前,笔者首先布置学生认真阅读课文三遍,并让大家用简单的一两句话记录下每次阅读的体会与感受。课堂上,我挑选几名学生发言,谈谈三遍阅读的差异。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遍很多学生看不下去,认为此文缺乏故事性,而且不吸引人,内容枯燥且索然无味;第二遍感觉朱光潜先生这篇课文似乎与作文的修改有关,无非从《水浒传》《屈原》以及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作品里找几个例子,让大家学会遣词造句,似乎与当下的要求少有关联;第三遍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发现如果仔细推敲课文里举的例子,以及作者提供的理由和解释,的确“僧敲月下门”比“僧推月下门”更有意境,更有韵味,更有画面感和生活气息,贺铸的“一川烟草”、李白的“杨柳万条烟”等对“烟”的使用更有作者的主观情感渗透其中,实现了情与景的交融、人与世的互通。从中,学生深刻体验到了阅读并非一目十行的浏览,重复的阅读并非机械式的重复阅读,第一次感悟到看起来一个字、一个词的修改、添加或删除,既是文字运用能力的提升,更体现出文字与思想感情的紧密联系,表面上看文字的改动微乎其微,与文章大意并无抵牾,可是仔细揣摩却是思想在深化浓郁、情感在堆积升华,因为语言必须跟着思想感情走,并需要无限接近作者希望表达的思想情感。唯有如此,读者才能真正走近课文作品,才能真正明白语言艺术中文学大师咬文嚼字的追求和精神尊崇。
二、理解:中层学习的“进入”
相较于阅读而言,理解是高一层次的学习。这也是为什么语文考试把对某篇指定文章的考查,定名为“阅读理解”而不是“理解阅读”的原因。看似简单的顺序颠倒,实则传达出二者层次的区别,直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理解”比“阅读”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与阅读强调对作品的“走近”不同,理解更强调“走进”。它不是囫囵吞枣般地整篇翻看,而是要从作品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活过往和段落辞章中领悟文章的主旨与情绪,了解作者的思想与意趣,并结合自己的文化修养、生活经验,在想象、联想和思想观照的基础上,与作者、作品、社会和时代形成认识的互动与调试,继而让作品产生新的意义,对当下读者有所启发、有所触动、催人奋进。由此,读者就从一个被动接受的客体转换成带有主动性、创造性的主体,对一篇文章的理解过程就不仅仅是“消费”“共鸣”,而是进入了“交互”和“再创造”的价值层面。
譬如,在教学《雷雨》的课堂上,笔者首先介绍了该话剧创作的时代背景,曹禺当时的经历和基本创作思路,然后让学生预习阅读剧本内容,了解周朴园、周萍、鲁侍萍、繁漪、四凤、周冲等人物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的矛盾纠葛。有了对基本内容的接受,我又采用分组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学生走入剧本深处,走入作者曹禺的内部心境,通过适当的解释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了在那样一个以封建家长制和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为核心的落伍的悲剧的旧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对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的质疑和恐惧,领会到身处旧社会,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被命运捉弄的悲惨结局。正是《雷雨》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尽情撕毁和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强烈控诉,让学生油然而生地认同了当代社会的幸福和谐,知道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对人性之美的赞许和传承。这样的“再创造”正是高中语文课本“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初衷,也是教育工作者引领下一代向善向真向美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比如《我与地坛》,看似一篇写景叙事抒情的文章,却在娓娓道来的故事片段背后,蕴藏了作者对母爱的崇敬留恋、对生活的热切渴望、对生命的再认识。由于学生对作者史铁生的现实境遇所知甚少,对他的人生经历缺乏了解,所以笔者就从地坛四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与寂静之下孕育鲜活生命之间的对比、从作者因为身体原因找不到出路与小说发表后小有名气之间的对比、从我对母亲的不理解与母亲去世后留给他的坚强意志以及不张扬的爱之间的对比这三个方面入手,引导他们在文章中找出关键句和感情点,进而理解了文后之情、情后之理,懂得了要善待生命、坚守意志、热爱生活、不要放弃,切实把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入社会和世界,让生活更加厚重、扎实、精彩和坚韧。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理解”本身绝非单向地进入本文的过程,而是一个伴随着建设性、创造性和探索性的价值增幅的过程。一方面,作为读者的学生通过作品知晓了特定的时代历史、特定的社会状况,体验或者在联想中复现了作品呈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关系,增加了对历史长河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客观印象;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延展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激活了自身的想象力、判断力和感悟能力,通过对课文作品的解码、编码和重新复刻,提高了文学艺术素养,弘扬了积极向上的生命意识,并通过对比理解和价值判断,深化了对新时代的社会认可、文化接受与生命维护,生成并巩固了对当下生活的信心和进取之心。
三、审美:深层学习的“跃升”
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具备一定文学影响力和审美特质的相对优秀的名篇佳作。它们用文字反映世界,却并不是复制世界的一分一毫,与现实世界完全等同、毫无二致。因为如果仅仅是对客观世界或某个个体的纤细临摹,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没有作者创造性的东西渗透其中,这样的作品就不具备典型性和审美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言:“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掉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2]。高中语文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带着学生一起初步探究审美的世界,让他们不仅知道作品“好看”,还要知道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更要知道从中寻找出作品传递给读者的观照世界、观照人生的新角度、新方式,挖掘出潜藏在作品和万千文字之间的超越一般存在的独立价值。
虽然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积累他们的审美经验并非易事,但结合教学实践,开展对作品的深层学习,让他们从对艺术作品的接受中体验审美的愉悦、产生心灵的净化、实现思想的升华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边城》一文的学习中,学生大多数看到了爱情,对女主人公翠翠的悲惨故事抱以同情,少部分人体验到了作者沈从文对湘西风土人情和下层人物描写的清新淡雅。然而更深一层的内涵鲜有人知。于是,笔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翠翠是个什么样的人?代表了什么?二是为什么天真纯洁的翠翠逃不脱命运的捉弄?三是这个命运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带着问题,师生一起在对作品条分缕析式的精研中,学生明白了翠翠是作者关于美的理想的化身,翠翠的悲怆命运就是作者借对美的揉碎撕毁,表达对湘西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愚昧、落后的批判,对人性人伦扭曲的无言控诉,用梦境般的美的文学创造,“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3]。翠翠的悲剧让很多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反思: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正确看待亲情、爱情和友情?如何防止文化劣根性的卷土重来?如何实现文化和伦理的和谐平衡?如何认识人性和文化的共生关系?一系列的追问,让笔者看到了学习的升华,触摸到了独立审美的萌动。
事实上,学生对《边城》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与作者、与作品直接“对话”的过程,既有心灵的交互,也有灵魂的问答,还有一种萨特所谓的“盟誓”关系贯穿其中。学生在对作品的接受中,一方面发现了作者创造的新世界,在想象、联想和天马行空的意境空间里自由组合或重构文学图景,打破了现实中日常的经验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在对作品中的新世界进行体验的同时,独立地做出自身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世界、探索世界、融入世界的新经验新方式,使得自己“从日常生活的麻痹猥琐和习惯偏见中解放出来”[4],既改变了原有的心灵世界,净化了思想空间,也拓宽了个体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看待历史的视野视域,还能够超越现实世界增强对包括自身存在价值在内的社会关系进行领悟、反思和批判的力度。
高中语文的学习本质就是文学接受活动。区别于一般成人读者侧重审美和批评的动机,这种文学接受的动机更加单纯和集中,明显偏向于受教和求知的需求。但是将“文学作品由第一本文转化为第二本文”[5]这一点,是两者共性的存在。对于高中生而言,由于受社会阅历、教育水平和年龄特点的综合影响,这个转化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一般相对比较慢,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和教育,逐渐推开“阅读”这个“大门”,进入“理解”这个“前厅”,最终深入“审美”这个“大堂”,完成对文学作品的总体把握、心神净化和审美领悟,最终增强增高审美的享受度和愉悦度。对于教师来说,要从育人的高度来看待教书的重要作用和职业意义,不能仅停留在阅读理解的层面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不能只盯着分数这个教学的基本面和功利值,多给学生一些教学指引,多给学生一些学习提升机会,让他们在课本学习的基础上与作品、作家产生共鸣,与社会、世界交汇融通,用优秀的作品调节精神、调适情绪、摒弃杂念、健全人格,继而洞悉人生真谛,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丰满健康向上的精神境界。这既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我们理应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