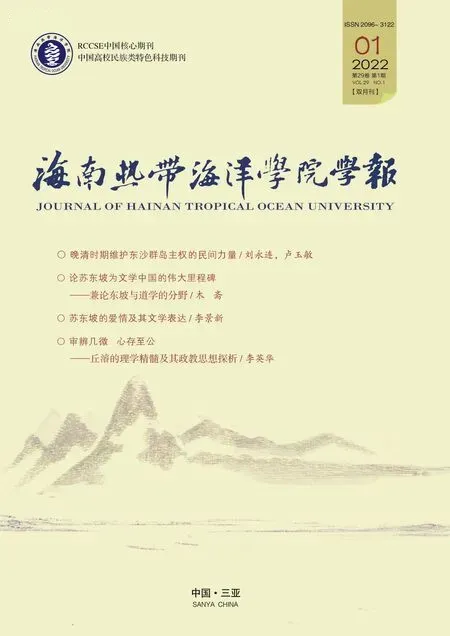论苏东坡为文学中国的伟大里程碑
——兼论东坡与道学的分野
2023-01-05木斋
木 斋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
一、 “文学中国”说
对于东坡,我曾经先后通过三个视角研究,分别是野性、仕隐情结和审美人生。野性视角揭示了东坡一生有别于官场人生、仕宦人生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是东坡伟大创造力的源泉;仕隐情结视角揭示东坡一生心隐于野的精神追求;审美人生视角则是前两者的整合,并进一步升华为古代士人如何对待生命的哲学思想。
反思华夏民族文化的演变历史,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从经学到道学的演变,即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发端,到孔子对儒家思想的奠基,从而形成以“六经”作为基本经典的儒家思想,到两宋时代程朱理学,经学演变为理学道学;二是同样从周公礼乐制度发轫,形成《诗经》作为发端的诗学,到建安时代,诗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逐渐成为士人的本质文化精神。
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演变历程之中,到底谁能代表华夏民族的民族品格?此前,我们一直认为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华夏民族的象征和代表,但这一认知,是基于西周到清末的王朝政治的伦理道德而来,同时,也基于儒家哲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而来。问题是,华夏民族自从西周《诗经》文化以来,就是一个文学中国的国度,而非是一个理学道学的国度,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及其审美人生方式,才是华夏民族真正的代表。正如我们可以称希腊而为哲学希腊,尽管希腊也有从《荷马史诗》开始的文学,但哲学是古希腊的本质。中国,虽然同样有以儒道释三家作为主体的哲学,并构成狭义的中国哲学史,甚至进一步扩展而为中国思想史,但狭义的哲学和思想,并非华夏文化的本质特征。
哲学——由哲学家们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学说,不论在其产生的时代是如何的伟大,对后世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这种由某些圣人思考出来的学说并不能够成为永恒的伟大思想,也不能成为民族永远遵奉的道德规范,因为圣人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受到某种时代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科技文明等诸多方面的制约。这一些当时伟大的圣人及其思想,由于被后人,特别是被统治者所信奉尊崇乃至神话,无一不构建成为“设定的哲学”[1],成为新时代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孔孟儒家学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僵死的经术之学,简称为“经学”。
相反,文学作为审美的表现载体,却伴随着历史文化的演变,拥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相对于灰色的理论和道学,文学是生生不息的艺术实践。不同的时代,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家。在文学中国演变链条中的每一位创造者,拥有着无限丰富的思想和无穷尽的影响力。文学中国展示的源流历史,是对狭义的哲学和思想史的不断修正和补充,是更为本质的、准确的华夏文化哲学和思想的表达。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各自有其伟大之处,但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与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思想相互吻合,发展为扼杀思想的思想,扼杀哲学的哲学。在由士人转型为诗人,进而士大夫群体觉醒的历史进程中,优秀的文学汲取的是儒释道三家哲学中的优秀的思想,并不断修正和发展,突破原本的教义,也同时不断突破在哲学家和思想家内部形成的如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等思想牢笼。
华夏文化的感性的、具象的、审美的民族文化特征,正是产生文学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大背景,同时,文学而非哲学和思辨反过来也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凝定和强化。文学中国之论不仅仅是华夏民族之急需,而且应该成为指引人类未来走向的世界哲学。
如果将文学中国从先秦到唐宋再到明清选择一位代表性人物,笔者认为非苏东坡莫属。从屈原、陶渊明到李、杜,为何要以苏轼作为代表人物?其中除了苏轼的成就更为全面,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之外,更为主要的,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前面的伟大诗人,都还仅仅是某一种哲学思想的阐述者,而苏东坡的审美人生方式,则是以自身的思想熔炉融汇儒道释诸家学说,为后来者提供了战胜人生苦难的哲学思想。
二、 苏东坡与道学的分野
文学不涉及世界的未来,只关注审美的当下,通过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方式指引人类的未来。苏东坡作为文学中国里程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苏东坡出生的时代,正是经学道学从衰微而再次兴起的时代,也同样是文学中国经唐入宋方兴未艾,逐渐走向高峰的时代。东坡原本是可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走道学之路,则为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之路;走文学之路,则为文学东坡之路。北宋的四大理学名家,其中只有周敦颐与东坡似尚未有过人生交集的记载,倒是王安石受到周敦颐的影响颇深。北宋第二位道学宗师张载,年长东坡17岁,同为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考的进士,但我们并未见两者亲密过从的记载。张载长期侨寓并讲学于凤翔眉县横渠镇,因此,世称“横渠先生”。苏轼仕宦生涯的起点恰是在嘉祐六年(1061)做凤翔签判,并有《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书院壁》[2]129一诗,但却对张载不闻不问不写,这与王安石对周敦颐的崇拜形成鲜明对比。
张载当时的名气就已经很大,他提出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可从其中管窥其宏大无私的政治价值指向”[4],说起来好像是神乎其神,气魄很大;实际上,其创立的所谓“绝学”,也不过是孔孟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境界。
天地本无心,一切均在自然无为的自然本体按照规律运转,如同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5],人只是居于其一,因此,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人在天地自然之间是渺小的,是需要遵奉自然规律的。周敦颐《太极图说》,提出人与太极同为“二五之精,妙合而凝”[6]。人是万物之灵,这样就成为张载“为天地立心”的理论来源。
不论是周敦颐的“人仪”之说,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之说,就哲学思想的演变而言,都是对孔孟学说的发展,提升了人与宇宙关系,都是一种进步;但道学以及作为道学理论源头的孔孟学说,都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
孔子学说来自周公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本身,其乐的体性在于人和,由乐而乐诗、乐舞,由此成为后来的文学中国、学术中国之滥觞。此为其精华,但其本质在于为其宗室长治久安服务,由此乃有三纲五常。后来的道学,论其哲学思想,固然不乏精彩和进步,但一遇到纲常人伦教化,就会显露其黑暗糟粕。因此,“为天地立心”,不解决由什么来代表心,则必定会将孔孟儒家哲学替代原本之自然自在之规律,必定走向与天奋斗、人定胜天之途,必定走向以君主代表天地之心的思想专制道路。
“为生民立命”,生民原本有命,有其自身独立之生命,道学家偏偏要为生民立命,则反而南辕北辙,不能尊重个体生命之价值。在宋则为王安石变法,看似强国,实则贫民;在明清则为理学,桎梏千夫,愚昧万众。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的是韩愈道统中的往圣,即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在儒家道统形成之中的九位圣贤。其实,此九位圣贤中的前六位,皆为后人对往圣的虚拟创造,其中只有文王可视为周公之前的滥觞,其余皆与儒家思想的形成关系不大,所以,九位道统圣贤,周公、孔子即可代表。孟子之后,儒家思想分流而为墨家、道家、法家等三教九流,看似与儒家相异,实则可以视为一种大儒家系统,与儒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形成对立互补的关系。
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遂蜕变而为僵死的经学。建安之后,曹魏集团以文学制约经学,中国遂走向文学之路。文学之士日益取代经学之士,文学中国渐次演变而为华夏民族文化之本质特征。所以,六朝唐宋,华夏民族最为繁盛的极盛时代,往圣道学家基本都是缺席的,即便是科举考试,也以诗赋取士。换言之,孔孟程朱等圣贤缺席的时代,是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当然,文学(特别是诗学)以及由此扩展到书法、音乐等艺术,也需要儒家基本经义作为敲门砖,成为士人之所以为士人的主要标志。
韩愈正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大声疾呼拯救道统的衰微,希望自己成为继孔孟之后的道统传承的圣人界碑。然而,不论韩愈怎么努力,怎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7]509,其结果并不能成为孔孟之后继而为伟大道学家,而只能成为中唐文学大师。
其中的缘故,并非韩愈的儒家思想不足以为圣贤,而是这个时代,不需要孔孟之学。这是一个文学中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如同海日之生残夜,江春之入旧年的诗学时代,是一个不需要陈腐学说束缚的时代,是一个不需要“道济天下之溺”的时代。唯一的效果,确实是“文起八代之衰”了,但其之所兴起,却并非文以载道的儒家教条,而是从内里生发的深邃情感和无限宽广的生命激情。这原本就是文学自身向时代提出的要求。后来的文学史大力鼓吹中唐时代的新乐府,大力倡导文以载道、文学为政治服务,其实只是后人对当时这种不成功的实践的拔高解读而已。
既然如此,为何到了两宋时代道学会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度到了两宋时代臻于成熟,培育了科举制度下士大夫文学集团,当然也就培育了一批士大夫道学人物。以周张二程为代表,朱熹汇集此四子的语录而为《近思录》,接续《中庸》《大学》,建构起圣学之阶梯。这也就是张载的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之意。
这种建立在阐发光大孔孟学说的绝学,是否实现了“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开启的,是“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8],二世三世传之无穷的礼制主义坐天下的理念。任何创新的思想都被视为是异端左道的思想专制,是为了宗法继承的血缘纯正,而不断演化甚至异化的对男女恋情思想禁锢、精神枷锁的漫漫长夜,是将由李后主个人的变态演变为两宋明清女性普遍缠足金莲的变态时代,是将唐宋科举产生的生机勃勃的文人群体,阉割为明清八股科举人生下的陈腐道学集团。
万历皇帝20多年不理政,才出现和似乎容忍了李贽开启的人学时代,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牡丹亭》代表的异端文学作品,发散出漫漫理学暗夜时代中人性的光辉。
李贽51岁的时候,在南京任刑部郎中,在其《圣教小引》中道: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年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9]
他在姚安太守的任上,将当地的丰德寺禅堂改建为三台书院,为讲学之所。当时的另一位官员骆问礼由南京兵部郎中出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兼洱海分巡道,九月抵达姚安,对李贽讲学不以为然道:“孔孟程朱不恒于世,窃恐异端之徒得以自恣,而儒道日湮矣。”[10]
这还仅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压迫,那个时候的贞女烈女传记或是《夜航船》一类的小品文,以明代的素材托古,还反映了女性为圣教殉身的社会现实。东坡时代,程朱理学尚在初起阶段,但其要求思想的统一,却是一致的。王安石与二程关系不好,二程也并不同意变法,但在思想专制、文化统一方面,其内里却是一脉承传的。
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7]1427
宇宙与人类世界,其本身就是由差异构成,这个时间,失去了差异,不允许差异存在,就会成为一片“弥望皆黄茅白苇”的“惟荒瘠斥卤之地”,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由此再看张载的“四为”之说,既然孔子已经是只能令后人膜拜的圣人、无法逾越的万世师表,后来的读书人只要仰山铸铜即可,读书人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作,也就等于没有了独立的生命。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明清之后,唯有突破了儒家学说的李贽等“异端”,才放出了思想的光辉。李贽之所承接的两宋文化,正是从东坡而来。李贽《寄京友书》:“《坡仙集》我有批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11]可见李贽对东坡情感之深切。
东坡为何要走文学中国之路,而非追随张载、王安石、二程等人走道学之路,出凡入圣,成为早于朱子的苏子?其中的因素甚多,至少需要写一部大书,或许才能阐释其中之一二。先择其要,文学中国自从建安时代发轫以来,已经形成为一个连绵不断、自我生成而自律、自我排除糟粕的生命本体。就像是一个体制完整的生命体,有着自我辨识的功能。在11世纪前20年出生的以欧阳修、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一代士大夫,是道学家群体,也是北宋士大夫文学集团觉醒的一代。苏东坡承接这一文学集团的精神而成为接棒的领军人物。
欧阳修(1007—1072),年长周敦颐10岁,长张载13岁,长王安石14岁,长东坡20岁。欧阳修以“人情论”作为批判道学家们的武器,在《又答宋咸书》中说:“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12]1015。《纵囚论》中说:“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12]288或说,欧阳修“人情论”,听起来似乎也不是什么高论,都贴近日常生活而没有道学家们的大道理。试思张载的“四为”,不论是哪一句,都是何等大气魄,可谓是纵横捭阖,吐纳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这正是道学中国与文学中国之不同,也正是东坡思想之于程朱理学之所异!
三苏父子,正从这人情之“情”字而来,试看苏洵《辨奸论》揭露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13]234
苏洵此文是否为真,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以笔者所见,此文为苏洵文笔无疑,毫无争论之意义。“夫面垢不忘洗,……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段落,排比而下,三次出现人情之“情”字。不论是什么哲学,不论是什么高大上的口号,总离不开人情物理,总要能符合人类的生命规律才是好的哲学,好的思想。从某一种僵化的理论无限拔高的哲学,是无法吻合于“人情”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标准的!
东坡之所以不为道学而为文学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东坡的“野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东坡不可能走道学之路,成为儒家理学的卫道士,而必然会走张扬个性,放浪纵恣的诗人之路、文学之路,并成为文学中国演变进程中的伟大里程碑。
在东坡的时代,既然儒家道统内不允许有丝毫的颠覆,那就在文学的国度里驰骋。在道学的时代天地里,知雄守雌,无为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正像是在他生命最后一个时刻的遗言:“着力即差!”[14]是的,在漫长的道学理学时代,一切对儒家思想的超越,都如同在中世纪的西方对上帝的亵渎,与其动辄得咎,着力即差,那就还不如在文学的国度里,展现审美人生的光辉,从而成为指引人类走出迷雾的神奇光束。
写到这里,不妨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做一个思考:笔者的“文学中国”说以及连带而生的苏东坡作为文学中国的里程碑这一观点,是否合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是否合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实际情况?
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可能会反对,他们会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哲学灵魂,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基本都在儒家的思想范畴之内,孔子是儒家思想的缔造者,其作为华夏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不可动摇的。诚然,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哲学、官方哲学,其地位无以复加,任何朝代的文学家,无一不受其雨露滋润,即便是野性如同苏轼,异端如同李贽,也无不从儒家的学习开始,儒家思想确实是融入血液,成为其生命的根基。但需要区别的是他们仅仅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并未成为纯粹意义上的道学人物。与此相反,他们用其人生的实践,展示出来的是超越儒家思想的另一种生命的灿烂。在东坡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开始成型的时代。苏轼作为一代伟人,如果对儒家理学认可,则理应与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携手并肩,而事实恰恰相反,苏轼正是二程的死敌。苏轼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势必要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派系——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
苏轼与程颐的矛盾,不仅仅是由于苏轼在群僚面前,开了程颐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庄重的场合开大臣的玩笑,也是苏轼的“野性”表现吧!很多书籍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如《宋史全文》卷十三载: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欲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15]
《孙公谈圃》则载云:
司马温公之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16]
司马光死后,朝廷赐以“明堂大享”的殊荣。群臣在祝贺后,由苏轼率领准备再去祭奠司马光。程颐搬出《论语》圣人语录,说孔子说“哭”了就不能“歌”,苏轼就直接地开了他的玩笑,说他是“枉死市”(白白斩死于市)、“燠糟鄙俚”(系汴京城外地名,比喻乡野的意思)的叔孙通,弄得程颐当众出丑。
这一事件似乎很偶然,其实,这个偶然是在必然之中。苏轼追求的是随心所欲的个性自由,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程颐理学的虚伪。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他曾说:“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7]913《程子微言》亦载:“朱公掞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何时打破这敬字?’”[17]414试思醉饮黄泥坂的苏东坡与这些“端笏正立”的道学御史为伍,真无异于花果山来的孙行者入玉帝灵霄殿朝班。一个是“严颜不可犯”的道学面孔,一个是不失赤子之心的狂人。因此二程洛党攻击苏轼不忠不敬,也就不足为奇了:“左司谏朱光庭公掞,即奏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谓仁祖神考,不足师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18]而苏轼则感到不能忍受这种封建桎梏,他由自己的痛苦感受推及统治方法,说:“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7]1015
苏轼还不可能认识到程颐及其徒孙朱熹所形成的程朱理学同样是封建社会后期加强皇权专制统治的产物,而皇权也需要程朱理学的支撑。这是苏轼政治悲剧的另一原因。这一点,也同样将东坡向“野性”推进了。元祐八年(1093)的仕宦生涯,让苏东坡更进一步体味到时代的黑暗,体味到个性被束缚、人性被扭曲的痛苦。于是,大量追恋黄州、杭州野性生活及思归之作出现了。
其实,这也不是二程的问题,周公的礼乐制度和孔子的儒学理论,其本身就规定了何时可以哭以及怎么哭。人之喜怒哀乐皆为人之本性,如果规定你何时哭,哭几声,您哭得出来吗?还有人的真性情吗?当下很多人,一说起振兴民族传统文化,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弟子规》之类,甚至培训女性的三从四德。如果我们真的回归这样的文化传统,华夏民族还有救吗?救救孩子!我们要学就学苏东坡吧!
三、 审美人生的生命哲学
苏东坡的文学中国里程碑地位,可否取代孔子的儒家哲学的奠基?我的“文学中国”思想的雏形发端于阅读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的巨大影响力,其实不在哲学,而在其文学的感悟与诗性的表达。
枯燥抽象的哲学,对于华夏民族文化在漫长岁月所形成的具象的、审美的、诗性的民族品格而言,往往是说教的、道德的、守旧的、灰色的、缺乏生命力的僵尸。苏东坡自身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同样很难比出自自身生命的诗词文赋更有哲学的魅力。
无论是“野性”还是“仕隐情结”,其实,都还仅仅是苏轼人格的一个侧面而已,欲解读苏轼之人生本质,还需从华夏文化士大夫人格的演进上寻求,需从士大夫人生的终极问题进行拷问。
美学家宗白华[19]曾有六境界说: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艺术境界。功利是人类的最为原始的阶段,而审美则是人类的终极境界。苏轼的人生,像芸芸众生一样,有着“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19],也有“穷研物理”[19]的学术境界和“返本归真,冥合天人”[19]的宗教境界,但我认为苏轼更为本质的是典型的艺术境界,可以用“审美人生”来概括。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19]的艺术境界。相对于苏轼的宇宙人生来说,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苏辙说其兄在晚年流放海南时“日啖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20],可以作为笔者此观点的形象说法。也就是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富贵,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这种情形,也如黄庭坚所说:“东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其商略终古,盖流俗不得而言。”[21]这种孤高,是俗人难以理解的由此反观东坡的野性、仕隐人生,皆可以被涵纳在审美人生的范畴之内,皆为审美人生的一种具体的生命方式。苏轼的哲学思想,往往都是融入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或者是日常生活之中。譬如以东坡对风雨的感受而言,早在杭州通判任上,有感于王安石变法的来势汹汹,他写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就巧妙地以望湖楼前的风雨暗示了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斗争,以及自己一生可能的遭遇: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2]339
这是一幅绝美的泼墨山水画?不!它更像是具有动感画面的蒙太奇。诗人使用迅疾而来、飘忽而去的三个意象——如同翻墨的黑云、跳珠的白雨、卷地而来的风,通过巧妙的剪接,拍摄成了色彩斑斓、寓意深刻的画面。这是一首哲理诗吗?全诗四句并没谈什么哲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描写了自然界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象。但是诗人为什么要摄取这样的3个意象组成画面呢?为什么要用雨后平静的水面去反衬雨前来势凶猛、不可一世的“黑云”“白雨”呢?诗人为什么要揭示自然界这种变化无常而又有常的规律呢?
此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的杭州通判任上,正是变法的风雷震撼着夜空之时。苏轼在写作此诗的前一年,曾经两次上书给神宗,提出了与王安石不同的政治见解。王安石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穷治,卒无所得”[22],“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22]。对整个政治局势,苏轼感到“眼看时事力难任”[2]314,对于个人遭遇,则感慨“敢向清时怨不容”[2]331。东坡通过此诗表达了无论是政治的暴风雨,还是个人的坎坷,都必然是暂时的,必然要回复到澄清的本原上,表达了“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2]253的人生哲理。
元丰五年(1082)三月,写作《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3]356
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已然两年,从“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2]1095的痛苦心境中也已逐渐解脱了,他要买田以终老于黄州:“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24]。这年三月七日,苏轼到黄州30里外的沙湖去买田,归来途中遇雨,时雨具已先被拿走,同行之人举步艰难,十分狼狈,而苏东坡却坦然信步、吟啸徐行,并作了这首词。
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把山水草木看作是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认为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有彼此契合的关系。苏东坡此作颇有象征主义的味道。该诗表面上是写诗人在这次雨中、雨后的感受,实际上却处处是人生态度哲理性的象征。从词序所述情况来看,东坡此次所遇之雨来势不小,然而,词人一起首就以十分藐视的笔调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场席天卷地的风雨,被词人“穿林打叶”四字轻轻带过,更兼以“莫听”“何妨”分别引领,更给人以悠然信步、意态潇洒之感。这是在沙湖道中的漫步,也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的漫游。
这种象征意味在以下几句中,进一步得到深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手拄竹杖,脚穿草鞋,这自然是沙湖道中遇雨的苏轼形象,同时也是惨遭诗案厄运流放黄州一隅的词人自画像。胸怀坦荡、任天而动的苏东坡并不以时运为悲,他认为,“竹杖芒鞋”比达官贵人的骏马还要轻快自如。“谁怕”二字,既是对眼前风雨的藐视,又是对人生厄运的断喝!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更为精彩,一下子就把眼前之实境描写放扩为整体人生态度,包蕴着不惧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原则,而又如此生动形象,富于诗意。
上片的实境着重写雨中,下片则写雨后并设想厄运之后再回首反思时的心态。“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伴着雨丝吹醒了诗人的醉意,他感到了几分冷意。突然雨后天晴了,迎面而来的是落日山前、一夕晚照。自然界的风雨阴晴进一步启示了他:任何风雨都必将有其止息之时,那时再回首展望,曾咄咄逼人的风雨云烟,早已化为乌有。与早年所写的“黑云翻墨”机锋相似,只不过“也无风雨也无晴”,较之望湖楼前的黑云白雨是更高一个层次的认识。前者是承认其“有”而相信其必将云散,后者则进入视而不见,不觉其有的禅宗式的顿悟。
晚年苏轼从海南北归,所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使用了与此诗相似的意象,但由于在前后文中伴有哲理性的议论,使读者更容易发现作者的用意: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月明星散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2]2366-2367
前四句的景色描写,绝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而是深含作者情感和哲学思想的意境。这一景色,不仅仅是诗人渡海的具体环境,也是时代的象征,或说是诗人由具体环境而感受到的对时代的理解。“欲三更”正是对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社会后期的概括,但是,诗人仍是达观的。诗人从自然界的变化感悟到人生“苦雨终风”必将过去。这一点正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这种旷达思想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认识,全诗八句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对于孔孟以来的儒家哲学,苏东坡采用仰望星空的方式,用诗词文赋的形式来融汇阐发儒释道诸多哲学思想,这种诗意栖居的人生哲学(1)李景新有《事业成功的诗意栖居者——苏东坡人生风范漫谈》一文,可参考。该文首发于“全国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并在《新海岸》2009年第2期发表。,更为具有普世价值,更能代表华夏的民族精神。
四、 由人情而为日常
如果说,以诗词文赋阐述哲理,还不能说是东坡的首创,而将诗文写作融入日常生活,则东坡可视为界碑。
我们只消回顾一下东坡之前的文学演变:庄、屈的《逍遥游》《离骚》,自然是不可确切考察其与作者生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在先秦两汉那个时代,文学仅仅是经学的附庸,个人的生命价值淹没在礼乐制度和经学的光环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作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就更是不值得写入竹册帛卷。到了盛唐三大诗人,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我们又能知道这是哪一年的天气,哪一年的晚秋?李白的《蜀道难》,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李白天宝初年到长安得到贺知章的赞赏,而推知其大抵的写作时间在此之前,但《蜀道难》又与李白的日常生活有何关系?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皇帝二载秋,八月闰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北征》)可谓是开北宋士大夫日常文学写作之先河,但还仅仅是儒家思想下的“诗史”,而非东坡式的日常生活式的写作方式。即便是到了北宋,东坡之前的欧阳修仍旧未能完成将文学写作日常生活化这一转型。
将文学写作完全日常生活化,东坡可谓是开天辟地者。这也就是东坡之所以最接地气,最有人气,最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日常生活化,不仅仅是在诗词的题目上、词序上标注与自身日常生活的关系,而且体现在写作题材的日常生活化。日常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唱和、品茗煮茶、赏玩金铭、采菊登高、踏雪赏梅等,构成了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就成为东坡以来士人的主要写作题材。随之而来,伴随的是遣词用语的口语化(如可以将“牛屎”“苍蝇”等所谓不雅语汇入诗)、思想情趣的通俗化以及写作形式的非古典化(譬如苏轼对近体诗格律的散文化)等。
当然,这种接地气的写作方式改革,是伴随着士大夫整体文化的变革而进行的。譬如对归隐生活和高风绝尘的士人风度的追求,引发宋代士大夫人生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官场为俗而山野为雅,仕进为俗而归隐为雅,富丽为俗而平淡而雅,功名为俗而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为雅。这样,东坡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就是在北宋整体雅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出来的另一种通俗文化,也就势必表现出艺术手法和语言方式的变革,如使事用典、改造意象,使之翻新出奇,摇曳生姿。
如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这是一首论茶品茗之作。此题材易写得平淡无奇,至多是以茶喻人。而苏轼却以人写茶,以人的典故写茶:“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2]530用直言忠谏、被汉武帝评为“戆”的汲黯,和“奸犯上意,自刭北阙下”[2]530的宽饶来比喻建溪茶的“苦硬”;用“虽有学问,细行谨防,终非骨鲠之臣”[2]531的张禹来比喻“荣茶”的“无赖空有名”。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知道,建溪茶和荣茶又分别象征着当时的两种人物——直言忠谏之臣和妥协求全之辈。以人比茶,又以茶喻人,翻转了两个层次,却不露用事之痕。故纪晓岚评:“将人比物,脱尽用事之痕,开后人多少法门。”[25]416使事用典,不仅使诗歌增加了含蓄美、凝练美,使之富于趣味和知识,发展了诗歌表达的艺术方式,而且,化用前人诗句,也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2641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是东坡之所以而为东坡的三个重要的写作基地和其伟大思想的摇篮。如东坡在海南创作出的《汲江煎茶》表现其诗文写作已经完全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他审美寄托的一种生命形式: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2]2362
翁方纲对此诗评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25]1859。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是个爱茶之人,他认为第二句“自临钓石取深清”写得精彩至极:“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25]1857-1858指出第二句的精彩,也就顺理成章点出第一句“活水还须活火烹”的立意,说明了为什么要深夜到江边去取水。
接下的三四两句“大瓢贮月,小杓分江”,杨万里说:“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25]1858苏东坡被贬到海南瘴疠之地,居然雅兴不减,自己在春夜去取水,而且要到江边去取最清澈的江水。取水用的是大瓢,不说“贮水归春瓮”,而说“贮月归春瓮”,描写月色明媚,映照在水瓮之中,好像把月亮贮入瓮中,更显得江水的清澈。
担水回来烹茶,用小杓把瓮中的水,分到茶瓶里面,写的不是“小杓分水”,而是“小杓分江”,把春江夜景的意象灌入了茶瓶,遣词用字潇洒自如,正好与“大瓢贮月”对仗工整,显示清夜之中饮茶的诗情画意,让杨万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这首诗的妙处,杨万里还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此诗的五六句,用的是倒装语法,“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25]1858。所以,苏东坡写烹茶的过程,把煎茶的色彩与声响都描绘了出来,却用倒装语法,扭转原来平铺直叙的“煎处已翻茶雨脚,泻时忽作松风声”,突出“茶雨”与“松风”。
结尾两句,杨万里也有说法:“‘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坐)听荒城长短更’,更翻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25]1858苏东坡夜里空腹喝茶,说是喝到第三碗就支持不住了,心底大概想的是自己的文章,远远超过卢仝,却沦落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夜听荒城敲响断断续续的更声。
一首叙述喝茶的诗,如平静流动的江水,夜色澄静,万籁无声,突然进入了峡谷险滩,每一个字都跳跃起来,奇峰突起,就如东坡的词句所言“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23]398。从取水的宁静到烹茶的跃动,一首诗不但从平面变为立体,而且跳跃起来,的确是字字皆奇。
五、 苏东坡的道学研究
前文重在从文学中国的视角来论述苏东坡与北宋道学家之间的分野,这并不等于抹杀三苏父子对道学的研究以及苏东坡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概言之,东坡的哲学研究,相比较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的道学,可以称之为实践哲学、审美哲学、学者哲学、创新哲学、探索哲学。既然是学者哲学,就是自出己意的创新哲学,而非以孔孟之说为准则。此五者的具体内容,需要笔者另文单论。本文先略说几点。
东坡有经解著作三部:《易传》《书传》《论语说》。其中《易传》为三苏合力之作,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到黄州之后不久大致草成,一直到谪居海南最终定稿。其书以“推阐理事”“多切人事”[26]见长。
苏轼的道学研究,原本在两宋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对立,时人称之为蜀学。南宋陈善云:“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27]此处的文章三变,主要指的是阐述道学的学术思想的三次变化,也就是以新学、蜀学、洛学构成北宋时代的三次演变,可知,苏轼不仅研究哲学,而且是两宋时代重要的道学家。
但这与本文所论的东坡与北宋五子道学——程朱理学的分野并不矛盾,而且是文学中国里程碑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换言之,道学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之中,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哲学本体,已经经过自身的排他律,将苏轼的蜀学连同其对立的王安石新学一同排斥出局,而成为一统天下的程朱理学。从表面来看,这是由于二程的弟子众多,尤其程学后裔之中出现了朱熹这样学问渊博的大家,程学遂为博兴,北宋的道学史演变为北宋五子的天下;其实,这些还都属于表层现象。苏轼的道学研究,原本就是其文学中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审美的哲学、学术的哲学、诗人的哲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性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反道学的哲学,是真道学的哲学。就道学史演变而言,直到南宋秦桧之后,不仅苏学才成为当时的显学,连程学也“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18];即便是朱熹之学说,在其生前也被禁为伪学,一直到13世纪中叶之后,程朱理学才被采用为官方学说,后世遂以朱子为道学的集大成者。这个结果乃为道学演变的必然抉择。道学其本身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哲学、帝王的集权统一哲学,必然选择与文学中国的哲学分道扬镳。
北宋道学的时代背景,如同王水照、朱刚先生[28]所论,与士的独立精神的崛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哲学和儒学,其承接中唐古文运动而来,集中体现了宋型文化的本质精神——理性精神。道,则是这个时代最高的哲学概念,就传承而言,是在唐代基本确立的儒家经典的注疏基础之上,汲取先秦诸子、魏晋玄学、道教哲学、佛教哲学,承接韩愈的道统之道的观念,从而建立起来的儒家哲学本体论;就其发展创造而言,则需要根据北宋新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发展创新。可是,道学家并不这样认为,张载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29]程颐则云:“德性之知,不假见闻。”[17]317他们认为人的德性,人的内省式的修身养性,主客一体、天人合一,并不来自自身的社会实践,而只要通过学习儒家经典,穷尽天人之理,即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这样,就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探索性。苏东坡的哲学,相对于道学家而言,其重要的区别点正在于此。就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东坡之哲学,颇类似于实践哲学,不以孔孟之学为判别是非第一性的标准;而程朱理学,则是对孔孟陈说在宋明新时代的极端化、教条化、标准化,进而成为后来明清时代禁锢思想的金科玉律。
孔子之于前代儒家文化,其伟大贡献也不仅仅是守成,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和创新,这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伟大之处。到秦汉集权专制,汉武独尊儒术,孔子学说不断被神圣化,从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帝王愚民统治的工具。所谓程朱理学,就其本质而言,则为这种工具的意识形态帮凶。而三苏之道学,乃为对这种道学之纠偏。
三苏父子都是具有创新性格,富有创新思想的人。苏洵一向是被认为是青少年时代不读书的问题青年,但其实不然。苏洵曾自述:“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13]108是的,有宋时代,这样政治清明奋发有为的时代,哪一个读书人没有一番“奋力”之志呢?但苏洵的本性并不喜欢当时科举考试所必须学习的句读、属对、声律,自命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13]159。苏洵根据个人的性情作出取舍,从弃学游荡到以后“吾自视今犹可学”[30]的重新觉醒,再到大究六经百家之言,却又终究不肯“区区附合于有司之尺度”[13]95,最终放弃科举考试的人生路途。纵观其平生经历,确实是个性的人生,也是有自己见解的人生。“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13]92,走的是体制之外的人生道路,故其学术亦能超越于体制主流学者的思想和论调。
东坡之道学研究,确实是从苏洵演变发展并发扬蹈厉,走向了与程朱理学更为异端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的学者的哲学、创造性的哲学。朱熹对苏轼逐条加以批判,如对苏轼“情以为利,性以为贞”等的批判:“苏氏之说亦误矣”“苏氏又引《文言》‘利贞性情’之文附会其说,皆非经之本旨”[31]。
正如东坡《易传》,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31]苏轼仅此一句就与北宋五子的道学划分出来了楚河汉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探索宇宙万物的道学原理,这才是真道学。东坡的道学研究,其精华正在此处。朱熹批判之“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32]。朱批尖刻处,正为苏文之创新处、之自出己意处、之真道学处、之乖违程朱理学假道学处。至于其审美哲学、实践哲学、学术哲学等内涵,篇幅所限,容当另文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