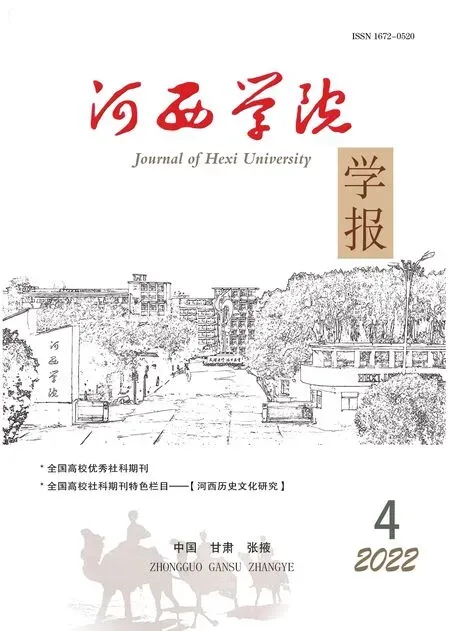历史传统与现代诗情交织的西部书写
——胡杨新边塞诗解读
2023-01-05黄静姝
黄 静 姝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引言
上世纪80 年代,“新边塞诗”在当代诗坛兴起,许多诗人坚守西部热土,仰望历史星空,书写西部地域风物,观照历史传统文化,极力呈现西部世界特有的地域风貌和风俗人情,构建特色鲜明、个性独具的诗歌世界,呈现出重振西部诗歌的文化旨归和价值取向,为诗坛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让西部诗歌成为当代文学场域的独特现象。2007年第二十三届“青春诗会”,诗人胡杨以一组《嘉峪关下》精彩亮相,展示出诗人独特的诗歌创作视阈和审美价值诉求。在此之前,胡杨曾创作出组诗《敦煌》《长城地带》等一批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业已引起诗坛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他赓续新边塞诗的优秀诗学基因,自觉坚守西部深厚的文化传统,徜徉在丝绸之路的古今通道,以本土意味极强的审美取向和坚实的写作态势构建自己的诗歌世界,使“西部”的概念鲜明地进入了当代诗学的“自然”审美范畴,成为当下新边塞诗创作中个性鲜明、成就斐然的诗人。
胡杨新边塞诗创作以自己熟悉的自然物景和社会生活为基点,将“嘉峪关”和“敦煌”作为书写的核心文化场域,描摹西部世界特色独具的风物景观,展现河西走廊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渗透着一种基于文化意识的思索和探寻,呈示出诗人个性独具的诗学建构和美学追求,激昂而不失平静,粗狂又不乏细腻,恢弘亦显亲和,壮阔兼具自然,自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蕴。诗人穿行在西部广袤大地,植根于西部深厚文化,以现实的态度观察世界,以理想的情怀感悟生命,深入挖掘普通事物之中蕴含的亲和自然之诗意,再将理想情怀、精神信念和社会使命意识作为表达之内核,对地域风物进行必要的人文感知和文化应和,用一种穿越古今的深邃洞察力对西部世界进行多样性解构,以一种精神之企盼关涉面对现实与普通生命的诗歌理性,昭示出特有的文化意识和深沉的人文情怀,演绎出丰厚的历史感怀和敏锐的现实透视,为诗歌注入一种流动的生命气息和厚重的文化气韵,透露出一种激发思考并撞击心灵的审美韵致。
从目前实际来看,学界对诗人胡杨及其创作研究尚不够深入、不成体系,对其新边塞诗的作品鉴赏还不够充分、推介不足,没能将其置于地域文学的场域从文化的视阈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是学界对河西走廊诗人认识不够、对河西走廊新边塞诗审美价值发现不足的典型表现。本文从文化视阈采用知人论世的诗歌分析方法,深入分析胡杨的新边塞诗歌文本,探析蕴涵其中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诗情交错共存的诗美特质,为胡杨新边塞诗创作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并且填补学界对西部地域文学研究的欠缺。
一、地域物态的诗意呈现
纵观胡杨新边塞诗创作,诗人沿着诗歌地理书写的创作之路,通过对河西走廊特有环境的透视,给予普通自然景物更深的思想内核和文化气韵,凸显出诗人反映现实的创作视界和姿态。胡杨以自己坚实的诗歌创作实践,显现出诗人对新边塞诗个性独具的体认与表达,拓宽了西部诗歌的表达界域和精神意蕴。胡杨新边塞诗呈现出的是河西走廊客观物景和人文风情,留给读者的是一种特异的感觉:西部特有的自然物景纷至沓来,从容又紧张;丰富深厚的历史记忆错综交织,平淡且浓烈;而贯穿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作者追寻和守护文化根脉的强烈情愫。
胡杨诗歌创作赓续古典诗歌优秀传统,采用意象表达的传统手法描摹地域物态,选取普遍性意象植入自己独特情感,通过视点平移和空间转合营构诗境,在联想与想象中转换思维和发现诗意,赋能意象更大的语义阐释的可能性,将“想表达的”和“能表达的”都恰切地外显出来,展示诗人由内向外拓展诗学界域的意识自觉。诗人通过富有古典意蕴和现代诗情的意象,不仅彰显出新边塞诗特有的意境和诗性,更透露出渗透其间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情怀,完成了诗性话语与智性言说的完美融合,在“现实——文本——作者——读者”之间建立起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意义链。
其一,选取自然意象摹写西部的景观与特征。纵观胡杨新边塞诗中的自然意象,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山脉、河流、戈壁、沙漠、峡谷、泉水、盐池、沙壕、疏勒河、马鬃山、当金山、骆驼、燕子、野鸭、玉米、麦子、油菜花、棉花、向日葵、苜蓿、黑枸杞、胡杨、红柳、沙枣、芦苇、桑树、榆、杏、桃、梨、葡萄……西部大自然常见的物景,都化为他写作的资源,成为他书写的对象。诗人没有受古代边塞诗特定意象的局限,而是努力攫取西部世界尽有的自然景致,着力构筑诗歌世界极具地域特色的意象群落,构成了诗歌世界全景式的地域物态,呈现出鲜明的西部景观与特征。如《嘉峪关门》:“从此门出去/流沙埋掉了脚后跟//从此门出去/燕子被风打了个趔趄//从此门出去/骆驼踩住一条树枝//如果有一场雨漂洗千年的尘埃/如果尘埃落定于/遗失的种子//那么,肯定会有一簇绿叶迅速窜出/那么,这个夏天/就会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送别远去的亲人//”。诗歌从微观视角入手,借助“流沙”“燕子”“骆驼”等具体意象渲染嘉峪关的荒凉景象,小中见大,把作者诗情与历史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表达出自然而真切的诗情,蕴含着厚重又充盈的意蕴。
其二,摄取人文意象表达西部的文化与底蕴。胡杨的新边塞诗创作,既注重对现实与历史中人文意象的诗学重构,又着力挖掘日常经验背后的文化意味;既注重西部地理人文意象的当下解读,又尽力探寻蕴含其中的汉唐遗韵。在胡杨笔下,那些或熟知或陌生的地名,都成为诗人寄托情思的特定意象和文化符号:嘉峪关、阳关、玉门关、敦煌故城、敦煌峡谷、锁阳城、骆驼城、居延海、魏晋墓穴、烽火台、安远寨、八字墩、马圈滩、野麻湾、吐火罗泉、石板井、罗布泊、渥洼池……这些闪耀着灵性之光的诗意具象,被赋予了某种与心灵紧密相连的精神韵味,透射出诗人对西部文化的关注和挚爱,满蕴着地域特色和精神内涵,充满着文化底蕴和高古气韵。其组诗《长城地带》可视为代表,诗人从全新的视角发挥想象,从沉积的戈壁品读出扑向村庄的激情,从“蘑菇台”察觉到雨水的奔跑,从“马峪口”山峡倾听到喷涌而出的马的叫声;在诗歌世界,马鬃山幻化为“集体沉默的马”,故乡浓缩为“一只攥在手上的荷包”……凡此种种,特定意象定格诗意情韵,显示出诗人由外向内发掘意象之文化意蕴的意识自觉。
作为丝路风情和走廊文化的歌者,胡杨将“西部”作为自己坚守的精神领地,以审美主体努力发见西部自然风物的深厚底蕴和诗意内核,再通过联想和想象营构出丰赡的诗歌意境,完成对自我心灵版图的刻绘和诗美世界的重塑。在诗歌《想起匈奴》中,诗人这样写道:“想起匈奴/我走在大街上/我们的城市/曾经是匈奴的营盘/成群的马/大片的草/和泉水/灌入响亮的牛角号”。诗人由现代人的生活把我们带进历史:匈奴、营盘、马、草、泉水以及牛角号这些写意元素,折射出作者历史观照下的诗意追寻,赋予诗歌边塞韵味和文化意蕴;作品呈现的是诗人游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诗情,读者欣赏到的却是苍凉浑厚的诗美世界。又如《侧面》:“一匹马的悲伤,一头骆驼的荒凉/是阿尔金//一眼泉水的孤独/一只鸟怎么也飞不出的湖泊/是阿尔金//一个人带上马的悲伤/骆驼的荒凉/还有那一眼泉清凉中的孤独/还要那鸟翼上/薄薄的霜//阿尔金就更远了/远在人心灵的/高处”。诗歌所描画的阿尔金悲伤、荒凉、孤独,是一座“远在人心灵的高处”可仰望却难企及的理想与希望的精神栖息之地,通过马、骆驼、鸟与泉水的困境完成了诗意的有效表达,展示出诗人灵魂深处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
河西走廊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版图,以广袤的戈壁、辽阔的草原和高峻的雪山为地理特征,河西走廊多样的地貌特征为诗人的想象提供了舞台,这条狭长通道里充满多元色彩的文化也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丰富启示。这里埋藏着褪色的丝绸和锈蚀的剑戟,这里飘荡着战马的嘶鸣和牧人的叫喊,这里蕴藏着百代歌哭与千年恩怨,这里也流动着诗的情韵和美的神采。诗人穿行于现实与历史的时空通道,既注重对现实与历史的描摹和寻绎,又着力挖掘日常经验背后的文化基因;既注重西部地理的人文解读,又醉心于汉唐文化传统的诗性表达;既努力触摸西部人们的生存状态,又着力营构雄阔苍凉、意蕴丰赡的诗境。敦煌月色、阳关城郭、戈壁大雪、草原奔马……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质和文化底蕴的审美主体,是胡杨诗歌创作坚守的诗学场域和精神空间。胡杨诗歌书写西部的苍茫与厚重,描绘西部世界特有的地理物态和人文生态,营造出雄浑壮丽、古朴苍凉、高远辽阔的诗歌意境,成为新边塞诗的标向与远方。
二、历史传统与现代诗情的诗性表达
作为土生土长的诗人,胡杨自觉观照西部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任思绪穿越岁月的铅幕,让自己的诗情沿着丝路古道漫延,执着地寻觅诗意的栖地。他凝视嘉峪关的城墙,他仰望敦煌故城的月色,他倾听玉门关的烈风,他遥想昔日戍边将士以及牵着骆驼西去的行旅者消失在茫茫沙漠……诗人行吟在雄阔粗犷的河西走廊,畅想西部的荣光历史与辉煌现实,以自然外部向诗歌内部演进的书写方式,完成了日常现实与传统文化的艺术重构,体现出历史记忆与当代经验交织融合的诗学特质。
诗人胡杨坚守新边塞诗个性化书写方向,自觉传承沉淀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文化,通过坚实的诗歌创作实践,构筑出独特而有魅力的诗歌世界。正如他在诗集《敦煌》扉页上所说的:“河西走廊,古老东方的传说与神秘,一个行走的写作者有了回忆和展望的无限可能,这个行走者是有福的。”[1]诗人在其创作谈《我的绿洲生活》中也曾说:“从野风猎猎的玉门关外到阴湿寒冷的乌鞘岭下,戈壁、沙漠、草原、山地、绿洲、城堡、古文化遗迹,一一揽入我行走的褡裢,走到哪儿,风餐露宿到哪儿。”[2]胡杨以建构边塞诗的诗美特质为审美追求,虔诚地行走于敦煌、嘉峪关两地,执着追寻传统诗学之根脉,沿着新边塞诗创作之路径,以表达当代人的现代情感为终极目标,对西部深厚的边塞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自觉传承。正如他在散文集《东方走廊》自序《我的河西》中所言:“以古人的方式,以苦行僧般的实践,我能够说出我的河西这几个字,这在别人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我,却是一生的追求。”[3]纵观胡杨新边塞诗,诗歌意象富有边塞特色和古典意蕴,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情韵,呈示出其新边塞诗独有的诗学特质。如《在嘉峪关下》:“从一个垛口看过去/从一排垛口看过去//大雪中晃动的天空/大雪中飘舞的大地//少了一匹马/少了一群羊//一座庞大的城/空落落的/孤零零的”。在诗人眼中,“嘉峪关”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以及纷纷扬扬的飞雪之中变成一座“空落落、孤零零的城”,昔日边塞惯见的“马”和“羊群”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边塞”与“历史”自然融合成耐人寻味的诗句,填满了读者想象的时间和空间。如诗歌《玉门关听风》,通过“风”“戈壁”“古城墙”“雪”“火光”“烤火的人”等形象,由实入虚,从现实延宕到历史深处,重构地理生态和风俗人情的文化意蕴,彰显新边塞诗的诗学特质和美学气韵。从诗歌书写视角考察胡杨新边塞诗创作,没有演绎风云诡谲的历史场景,没有描摹奇幻瑰丽的异域风情,也没有抒写慷慨悲壮的凭吊情怀,而是通过长城、烽燧、敦煌、嘉峪关、阳关、玉门关等蕴含历史文化基因的意象,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手法寻绎诗意。比如在《敦煌之西》中,诗人如斯写:“可汉武帝没这么想,唐太宗没这么想/他们都把自己的触角伸到这里/汉武帝的触角是那些长城,唐太宗的触角是那些端庄菩萨/和壁上华丽的衣袂//敦煌之西,玄奘悄悄溜过去了/像一块石头,被风吹着滚过去/没有了棱角/他的棱角都留在史书里了”。历史遗韵依然存在,现代诗情亦清晰可见;透过这样的诗句,读者感受到诗人对河西大地以及边塞文化的热切歌赞,品察出知识分子灵魂深处传承地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胡杨新边塞诗创作中,“敦煌”“嘉峪关”是诗人诗情迸发的摇篮和诗意滋生的沃土,是诗人无法割舍的精神皈依之所和心灵栖息之地,也是乡土情结的依附和诗歌抒写母题。他赞美敦煌的峡谷:“一种微笑,就有一千种/一万种祝福/人类的峡谷/挤满了幸福的来世”(《敦煌峡谷》);他歌咏新台店草湖:“月光,星光,铺洒于水面/包裹新店台/小小的湖啊/是一座村庄的衣服”(《新台店草湖》);他驻足绿洲上的田园:“绿色的潮汐/把安宁的梦想/隐藏在每一片树叶之下”(《安远寨》);他凭吊大漠中的遗迹:“汉代的御酒倒下几坛子/把美好的传说酿醇/不信醉不倒几个人”(《拜谒汉代胜迹酒泉》),这些篇什无不凝聚着诗人对故乡的赞美之情,体现出追寻诗意生活的美好愿景。张清华教授说:“这就使他的抒情跃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表达,而找到了赖以依托的根基和背景。”[4]诗人自己也说:“故土,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永恒的怀念与讲述。”胡杨以诗歌为载体,将故乡(主体)与“我”(客体)自然契合、相互交合,完成了二元统一的诗学建构,诠释对故乡历史与现实的神往和挚爱,彰显一种独有的理想情怀和精神信念。比如他的诗作《敦煌之西》《放马敦煌》《塞上——献给敦煌》(长诗)《嘉峪关外》《嘉峪关下》《嘉峪关》(长诗)《西域之门——阳光、玉门关的往事》等,诗人置身于特定地域历史和文化精神背景下,感知故乡的悠久历史与荣光现实,诗句已远远超越一般描述本身的能指,成为诗意与情韵表达的源泉与媒介,满蕴着诗人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体现出诗人对汉唐遗韵的敏锐感知与深切体悟,展示出诗人追寻诗意栖居的美学理念。如《烽火台下》:“阳光下,烽火台像是在打盹/牧人在背阴的一面/偷听它的鼾声//广阔的戈壁/羊群散布在远处/像是牧人手中的风筝”。诗人审视现实物景,追寻历史遗风,在描摹故乡自然风光中表达自我体验与精神信念,彰显出诗人对故乡现实的自我审视和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表达,衍射出富有生命情怀的诗歌愿景。
徐兆寿教授在评胡杨《绿洲扎撒》一文中谈道:“西部需要重新发现,是因为在我看来,西部之天地蕴藏着一种亘古的大气,从文化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魂;从地理上说,是宇宙天地间之神妙。此种精魂,此种神妙,是不可言说之言说,是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所不能有的……如果西部诗能在此发掘,必有新气象,大气象。”[5]作为西部本土诗人,胡杨对自然风光的醉心描摹、对自我情愫的强烈抒写、对西部历史的永恒守望以及对文化精神的执着开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个性化的诗歌写作态势,体现出诗人寻绎西部文化与精神的诗意建构理念。更深层次来看,胡杨诗歌对西部文化与精神的追寻,实质是对现代人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的多元阐释。诗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将诗性情怀融入久远而厚重的历史遗迹,展示出类似后现代世界中人们的精神困境和对理想世界的深切渴望。品读胡杨的诗,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诗人的影子,巡行在猎猎西风中:在遗世孑立的嘉峪关下,他凝望大漠,打量时光的踪迹;在朔风四起的阳关内外,他行吟古道中,聆听尘封的绝响;在雄阔粗犷的敦煌以西,他梦回汉唐,畅想历史的走向。“敦煌之西,我骑一匹毛色肮脏的骆驼/一颠一簸揣测古代的商人怎样忍受煎熬”(《敦煌之西》)诗人在西部旷野踽踽而行,发掘人类精神文化高地——敦煌、长城及存现的和消失的西部文明,厚描现实,审视历史,解构文化,摹画着一种饱含理想精神的诗学图景。
三、诗学内涵与审美意蕴的交互重构
胡杨的诗歌扎根于西部语境,以地域化书写为底色,将日常的人事物景纳入诗歌创作视阈,冷静的、理性的、个性化的歌咏和表达,彰显出恢弘壮阔的诗美特质,带给读者别致的审美体验。胡杨诗歌创作具有自觉回归传统诗法的审美追求,至始至终保持着两种特有的姿态:仰望和俯视。他深情地仰望历史,仰望历史之魂;他虔诚地俯视大地,俯视热土之美。胡杨的新边塞诗既继承了古代边塞诗的慷慨悲壮、古朴苍凉、雄浑阔大的传统,又汲取了当代新边塞诗立足现实、融合历史、抒写个性的特点,以独特的个体感悟和诗学实践,以西部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为言说立足点,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对新边塞诗之诗学内涵与审美意蕴的交互重构。
胡杨新边塞诗的地域化和个性化色彩很浓,在诗人笔下,既有现实中的自然物象,亦有记忆中的历史遗迹,有对地域风物和人文景观的纵情歌唱,也有对历史遗迹和文化根脉的深沉感喟,蕴含着一种言说不尽的人文情怀和现代诗情,体现出诗人的写作观和审美观。在诗歌书写中,诗人自觉运用现代诗歌的表达技巧,无论是诗意场景的发见,还是自我感悟的言说,注重对意象意蕴从精神意义层面深入开掘,展示出西部世界的苍凉与厚重,拓展了诗歌创作的视野和空间,让诗歌文本囊括了更加丰富的文化、精神和人性的内蕴。“石缝中的一棵草/摇摇晃晃/它几经跋涉/止步于紧闭的铁锁/细弱的根须/抱住/渐渐渗入的夕阳”(《嘉峪关外》)诗人把“生长在石缝中的草”作为独特的抒写对象,借助“生长在石缝中的草”拥抱“渐渐渗入的夕阳”这一奇特意象,赋予诗歌特定的现实意义:对摆脱现实束缚的崇高理想精神的追寻,对探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力量的歌颂。“夕阳的余光,篝火的灰烬/我们剩余的时光,我们更多的时光/会有更多的牛、羊、马和骆驼出生/它们一直陪伴着这座山,陪伴着/苍天之父汗腾格里、大地母亲于都斤额客/牧人之星玛勒奇奥登”(《祁连山:裕固牧人》)诗中“夕阳”与“篝火”“剩余的”和“更多的”时光以及“苍天之父、大地母亲、牧人之星”相互映照,呈现出具有生命神性的西部世界。从胡杨新边塞诗整体来看,没有故作高深的思想注解和精神喻意,而是在近乎原生态场景的表述中,寄托诗人真实心绪和本我状态,呈现出一种完全回归自然境界的人生境界和艺术特质。
毋庸置疑,胡杨新边塞诗创作立足于现实环境及其诗歌表达的特殊语境,用心感悟西部的自然与风俗,诗性呈现西部的现实与历史,有着深度的自我情感体验,诗歌呈示出感性与理性复合、“有我”与“无我”兼容的内蕴,读者看到的不仅是诗歌艺术世界,也是现实与心灵的世界,诗与现实的关系彰显出审美的弹性与张力。“一千个孩子是我的兄弟/它们是佛祖、菩萨、金刚/一千个孩子是我的姐妹/它们是飞天、丝绸、花朵”(《栽树人》)诗歌把现实与世相进行恰切融合,在自然与灵魂相互触摸之后,诗人认为“这些栽树的人是兄弟姐妹”,是“佛祖、菩萨、金刚、飞天、丝绸、花朵”,形象表达出读者对生命中的某种本原向度的深思:爱与美的力量与意义。“见底的湖,长满了蒿草的湖,自己悄悄藏下了/陈年的盐巴,自己在秋天/从红柳的发捎上走出来/”(《八户》)诗歌于一种随意的描述中接近了诗歌创作的终极真理:在日常生活和普通景物中觅见诗意,在诗意的生活中创造美丽的日常生活。“长城下的一队骆驼,风里,雨里/它们望着前方,像一座座蠕动的城堡”(《长城下的一队骆驼》)诗人将“长城”下的“骆驼”置于风雨之中,把它形象地比作蠕动的“城堡”,西部的特色是如此得鲜明,诗人的观察是何等得细致,诗人的描摹是多么得形象,底蕴厚重而富有历史沧桑感。“哈日嘎纳花静静地开放/祁连山低头抚慰她/但她也在风暴中孤独地颤抖/她的叹息/被牧人长长地一声吆喝/盖住了/像寒冷的孩子披了一件长裙”(《祁连山下》)诗人敏锐地捕捉西部世界中最普通的物象,极大地发挥想象和联想,挖掘现存实境中最隐秘的诗意内涵,形成诗歌高蹈的美学精神与气格。
胡杨新边塞诗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向度,就是诗人坚守于传统诗学的沃土,对诗歌的表达技法进行个性化的探索与创新。他的新边塞诗是一种诗性话语与智性言说的完美融合,是一种自然描摹与生命体悟的有机统一,彰显出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诗学特质:
其一,简单语汇表达真实情感和深厚底蕴。胡杨的新边塞诗,没有刻意选取的辞藻,只有真情的流露表达和诗意的形象呈现;诗歌的语言不是强制的嵌入与堆砌,而是写景状物、抒情言志的自然生成,实现了真实情感与深厚底蕴的诗意化构建。“天气晴好/风在草丛/鸟在水边//植物们各自归位/似乎无须多言”(《小山包上》)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信手拈来的词汇,轻描淡写且不露声色,简单通俗又清新自然,却恰如其分地绘刻出一个田园般的世界,寄托了诗人的旨意和情趣。又如“那一缕炊烟高过树梢/连绵的沙丘/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远了”(《敦煌沙漠上》)诗人用朴素的语言去锤炼诗意,描画理想精神图景,诗意盎然,韵味无穷。概而言之,胡杨用简单语汇或描写、或叙事,自然的表达游走于大漠戈壁、长城烽燧之间的真实感悟,遥望西部苍茫大地,寻觅历史深厚底蕴,借助诗歌的力量揭秘西部世界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之间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依存的存在状态。
其二,巧比善喻呈现诗歌更大的现实性语境。诗人继承和弘扬古典诗歌中比拟的传统技法,对诗歌表述对象进行形象生动的描摹,通过暗喻与意象组成的诗歌语言,最大可能地发挥出诗歌表现美、创造美的作用。“我真正听懂了一棵树,它哗啦啦地拍打秋天的天空/阳关因它而年轻,也因它而古老/就像一盏钟表,储藏了无穷无尽的时间”(《阳关下的一棵树》)在诗人笔下,阳关下的这棵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在倾听瑟瑟西风,它在拍打寥廓天空,它走过了四季枯荣,也见证西部的繁荣与荒凉,极大地呈现出西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我看见的一朵雪莲/奇迹的灯/一场大雪中诞生的乳房/像是久久期盼中珍藏的书”(《一朵雪莲》)在诗人眼中,“雪莲”已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然物象,已经幻化为“灯”“乳房”“珍藏的书”出现在作者的眼前,也深深地留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从胡杨诗歌写作的现实来看,诗人对比拟手法运用是恰当的、充分的,多向度表现空与有、虚与实的微妙关系,使得诗歌脱离概念化、伪描述化等痕迹的干扰,让客观存在合理转化成艺术真实,使读者能够透过诗歌文本产生更多的联想并心有所感,诗歌呈现出更大的现实性语境。
其三,独具特色的形式建构彰显诗歌丰富诗意。胡杨新边塞诗形式的创新主要有三种基本体式:一是诗行内部“意断而形连”。如《河流的尽处》:“内陆河是绿洲的年轮/风吹起的浪花/被阳光照亮/……//一河汪洋/落霞与水鸟共舞/遍地的庄稼翘首应和,美极了……我们还可以看见那,沸腾的河水/撕扯天边的云彩/绿洲的年轮/开始新一轮的突围”。诗歌通过诗句、章节之间的恰切断连,体现出胡杨诗歌气脉贯通的诗学特质。二是诗行内部用逗号间隔。王力先生曾在其《现代诗律学》中提到了一个“诗逗”的概念,说:“所谓‘诗逗’,有时是用逗号的,有时不用逗号,但因意义上的关系,到那里也可以略顿一顿。”[6]如“无垠的戈壁/草都没有,怎么会有一棵树/人们看见它敦实的样子/人们看见它,忠诚的守卫/就找到了自己最后一个春天”(《一棵树》)在诗句的呈现方式上,恰当地选用逗号形成诗句内部的隔离,自然而巧妙对诗意进行必要的分隔,显示出胡杨对现代诗歌表达技法的重新架构。三是通过提行与分节扩张诗意。关于诗歌的行列建设,胡杨根据诗意表达的需要,恰当地进行行列排布,突出或者强调诗句中的某个成份,使得语词的意义得到急剧的扩张,诗意表达也更加蕴藉而深远。如“那些沉默的骨头,那些在风中/呜呜作响的骨头/今夜,想起了自己从前的形成//可以是一杯浊酒,可以是偷偷擦拭掉的泪/可以强忍住握紧一粒种子/让它回到春天”(《星野》)诗歌把“那些在风中呜呜作响的骨头”自然分行,“骨头”的“所指”与“能指”就更加突出,诗句也诗味十足,诗意更深。
结语
胡杨说过,“诗意的生活,并不等同于贫瘠,如果贫瘠的生活都能有诗意的支撑,那么,在我们通往富裕的道路上,我们怎么能够丢掉滋养我们生活的诗意呢?我想,我们的诗人有重新找回诗意的责任,让更多的人诗意的栖居,诗意的生活。”[7]诗人胡杨坚持历史传统与现代诗情的西部书写,扎根在广袤西部,穿行于悠悠丝路,凝视巍峨雄关,远眺敦煌云烟,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不懈追寻诗意的生活,执着创造生活的诗意,以特有的写作姿态,坚实的创作实践,开辟了西部诗歌的抒情空间和美学意境;无论是诗歌情感经验的认知还是主体意识的建构,挖掘出的是现实生活的深度,体现出的是诗歌艺术的高度,呈现的是诗歌的西部特质和边塞风格,彰显的是诗人的诗歌情怀和人文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