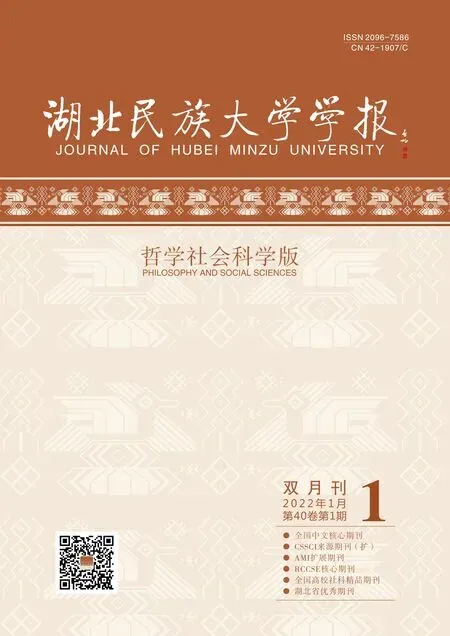南朝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2023-01-05崔明德
崔明德 王 硕
如何处理与诸“蛮”的关系,既决定着南朝各政权能否稳定,也影响着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并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有着密切联系。目前,学界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且对当时推行的民族政策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参见王延武:《两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吴永章:《南朝对“蛮”的统治与“扶纳”政策》,《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方高峰、张晓连:《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民族敕封政策》,《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彭丰文:《南朝岭南民族政策新探》,《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但对起着指导作用的民族关系思想重视不够,尚无专文加以探讨。本文拟对南朝各政权各类人物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作一系统梳理和探讨,以期全面认识南朝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
一、刘宋时期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南朝境内各族,人数众多,名称繁杂,主要有蛮、僚、俚、爨四大族系(2)参见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翁独建:《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说分蛮、僚、俚、傒四大族系,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其中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3)萧子显:《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07页。,大致分布于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部分地区。
秦汉以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统治区域,以何种方式治理诸“蛮”,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等重点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思想认识是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对南方诸“蛮”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西汉司马相如曾建议汉武帝,要集中精力开拓“南夷”,凿山通道、设置郡县,使南方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遐迩一体”(4)班固:《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86页。。东汉边吏郑纯、冯颢、朱辅、王追等人以“化行夷貊”(5)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2851页。“威怀远夷”(6)《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4-2855页。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多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东汉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
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范晔对诸“蛮”的认识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作为官方核心价值观的传递者,范晔对南方诸族及民族关系的看法,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大力支持积极开边政策,认为需要通过武力手段“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二是重视教化的作用,希望以此招徕远人,使文化习俗各异的各族群众“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物产丰盈,有中原王朝稀缺的“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玮宝”;四是南方少数民族“凶勇狡算,薄于羌狄”,力量较弱,容易管理。
总的来看,范晔的这些认识与先秦时期夷夏观念中“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思想观点高度吻合,基本上延续了秦汉时期“遐迩一体”“威怀远夷”等民族关系思想,既主张以武力威慑各族,也注重“柔服之道”(7)《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60页。,强调用德政教化的力量,使拥有奇珍异宝的远方各族真心佩服,自愿来贡,从而达到一种比较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状态。这种认识,是刘宋乃至整个南朝时期对付诸“蛮”的思想根基,在中央决策层面形成了安抚与武力相结合的处理方式。
就安抚而言,刘宋在诸“蛮”地区设立左郡左县(8)据学者考证,刘宋时,诸“蛮”地区有左郡7,左县40。参见方高峰:《试论左郡左县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借其力量进行统治。如宋文帝曾封爨龙颜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9)参见《新纂云南通志(五)》卷84《金石考四·爨龙颜碑》,刘景毛、王珏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宋孝武帝曾封合浦俚帅陈檀为龙骧将军,后又“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10)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9页。。宋明帝时,封蛮帅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11)《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8页。。另据《南齐书·蛮传》记载,“宋世封西阳蛮梅虫生为高山侯,田治生为威山侯,梅加羊为扞山侯”(12)《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7页。。
就武力而言,刘宋广设军府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蛮、宁蛮校尉管理雍州蛮、安蛮校尉管理豫州蛮等,同时派大军武力征伐。如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一次性调集江、荆、雍、豫四州大军讨伐豫州蛮,再如大明四年(460年)宋孝武帝派遣沈庆之讨伐西阳蛮,“大克获而反”(13)《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8页。。
刘宋地方各级官吏在处理与诸“蛮”关系时,则大多采取武力讨伐的方式。这一时期,只有极少数大臣主动安抚诸“蛮”(14)《宋书》中明确记载使用安抚手段处理诸“蛮”关系的,比较典型的有雍州刺史刘道产与朱修之。参见《宋书》卷65《刘道产传》,第1719页;《宋书》卷76《朱修之传》,第1970页。,绝大多数地方官员以讨“蛮”为要务,而且大都不择手段,肆意掠夺。如刘裕麾下大将王镇恶在讨伐司马休之途中,竟然“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15)《宋书》卷45《王镇恶传》,第1368页。,差点贻误战机。沈亮任雍州刺史时,“边蛮畏服,皆纳赋调”,对于不纳征调者,沈亮“悉诛之”(16)《宋书》卷100《自序》,第2451页。。宁蛮校尉、荆州刺史张邵辖区内“丹、淅二川蛮屡为寇”,张邵引诱蛮帅“因大会诛之,悉掩其徒党”,因“失信群蛮”,各地蛮人“所在并起,水陆断绝”(17)《宋书》卷46《张邵传》,第1395页。。天门溇中令宗矫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18)《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6页。。孝武帝时期的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垣护之征伐西阳蛮,“所莅多聚敛,贿货充积”(19)《宋书》卷50《垣护之传》,第1451-1452页。。都益、宁二州刺史萧惠开上任后,明确告诉同僚自己的政治愿景是“收牂牁、越巂以为内地,绥讨蛮、濮,辟地征租”(20)《宋书》卷87《萧惠开传》,第2201页。。益州刺史垣闳到任后,“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闳被赕刺史”(21)李延寿:《南史》卷25《垣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8页。。沈庆之一生多次伐“蛮”,前后长达十八年之久,仅元嘉二十六年(449年)伐南新郡蛮,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22)《宋书》卷77《沈庆之传》,第1998页。。刘宋末,荆州刺史沈攸之“为政刻暴”,曾“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酉溪蛮酋帅田头拟怒杀沈攸之使者,沈攸之趁机勒索,“责赕千万”,田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23)《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405页。。
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从社会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主要有南朝初年国用不足、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寒门出身官员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点:一是相较于武力讨伐,安抚性手段实施起来门槛较高,需要执政者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能够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极容易被一些注重现实利益的政治家、军事家所忽视;二是出于对诸“蛮”力量弱小、物产丰盈等认识,容易引诱出边吏的贪婪本性,使其直接忽略安抚的力量,选择武力讨“蛮”;三是由于刘宋多次北伐失败,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迫于现实压力,刘宋诸帝普遍将诸“蛮”生活地区视作后方资源储备基地,放任地方官员随意搜刮,进一步助长了劫掠诸“蛮”的不良风气。如竟陵人张兴世“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甚奇之”,宋文帝不但没有责怪,反而“称其胆力”(24)《宋书》卷50《张兴世传》,第1452页。。再如大明五年(461年)宋孝武帝下诏称:“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25)《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7页。,鼓励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用兵。
综上可见,虽然刘宋王朝希望采用“讨”与“抚”双管齐下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但由于思想认识过于功利,忽略了“抚”的作用,导致讨“蛮”成为当时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思想潮流推动下,传统意义上的积极开边政策异化为粗暴的掠夺政策,从而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反抗斗争。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龙山雉水蛮寇抄涅阳县”“滍水诸蛮因险为寇”“西阳蛮杀南川令刘台,并其家口”。再如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桂阳蛮反,杀荔令晏珍之,临贺蛮反,杀关建令邢伯儿”。刘宋末,“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26)参见《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7、2398页;《南史》卷79《夷貊传下》,第1981、1982页。。
二、南齐时期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萧齐代宋后,“连年虏动,军国虚乏”(27)朱铭盤撰:《南朝齐会要·食货·垦田屯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1页。,国力相对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南齐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方针趋于稳健,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及治理方式整体走向柔和。
萧道成称帝后,“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社会经济上,多次宣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28)《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9页。,临终前更是嘱托辅政大臣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29)《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页。所谓“柔远能迩”,出自《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与《诗经·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指的是统治者要怀柔远方,优抚近地,安抚笼络远近之人使其归附。齐武帝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永明七年(489年)下诏称:“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迩,兆民所以允殖。”(30)《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页。永明十一年(493年)策问选才时,齐武帝又将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为:“朕思念旧民,永言攸济,故选将开边,劳来安集,加以纳款通和,布德修礼。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31)严可均:《全齐文》卷12《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永泰元年(498年),北魏进犯雍州各地,齐明帝下诏称:“兴师扰众,非政所先,用戢远图,权缓北略,冀戎夷知义,怀我好音。”(32)《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91页。虽然齐明帝的这番话是对北魏的处理态度,但也基本代表了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即不主动出击,希望少数民族在礼义感召下,主动与南齐交好。
总的来说,南齐最高统治者虽有武力开边的想法,但远不如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等人强烈,他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普遍趋于温和,民族政策的柔和性随之增强。地方官员在处理具体民族关系事务时,自然也会尽其所能地将“柔远能迩,缉和内外”等思想予以贯彻实施,继而形成重视抚“蛮”的浓厚思想氛围。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促使南齐处理与诸“蛮”关系的方式出现了较大变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讨伐动因改变。《南齐书》中用兵诸“蛮”的记载共十二次,分别为:建元二年(480年),司州蛮联合北魏进攻南齐平昌戍,戍主苟元宾出兵将其击破,同年,豫章王萧嶷遣中兵参军刘伾绪讨伐北上黄蛮文勉德,又率兵助阵武陵内使王文和进攻酉溪蛮田思飘(33)《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8页。;永明元年(483年),巴东太守王图南遣司马刘僧寿讨伐巴建蛮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34)《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8页。,同年,益州刺史陈显达因“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派人去征收赋税,僚帅又抗命不从,于是他“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35)《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页。;永明二年(484年),辅国将军曹虎伐江州蛮(36)《南齐书》卷30《曹虎传》,第561页。;永明四年(486年),湘州蛮起兵,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齐武帝萧赜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代其为刺史,“以方略讨平之”(37)《南齐书》卷24《柳世隆传》,第452页。;永明五年(487年),太子右率戴僧静等人攻破太阳蛮酋桓诞(38)《南齐书》卷30《戴僧静传》,第556页。;永明九年(491年),安隆内史王僧旭发兵丁村蛮(39)《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9页。;建武二年(495年),梁州刺史萧懿“遣军主韩嵩等征獠”(40)《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5页。;建武三年(496年),北魏遣西阳蛮田益宗进攻南齐司州龙城戍,“为戍主朱僧起所破”(41)《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9页。。这其中,只有陈显达讨伐“大度村獠”的明确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其余出兵主要是因南方各族“不肯宾服”(42)《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2页。,或是在北魏的扶持下侵扰边境。可见,虽然诸“蛮”起兵时,南齐会毫不留情出兵讨伐,但其讨“蛮”的主要动因是维护政权稳定,劫掠物资的因素大大减少。
第二,重视“抚”的作用。刘宋时期设立的左郡左县,南齐大都予以保留(43)南齐时,有左郡33,左县111。参见方高峰:《试论左郡左县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册封诸“蛮”酋豪,借其力量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也基本被继承下来。如萧齐代宋后,“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建议收回前代赐给诸“蛮”首领的政治封号,但多数官员主张“宜存名以训殊俗”,认为应留其爵位以安抚他们,齐高帝下诏“特留”,并加封蛮酋田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44)《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7页。。另外,相较于刘宋时期不太注重安抚诸“蛮”,南齐时出现了一大批以安抚手段处理民族关系的地方官员。如僧惠照任巴州刺史期间,“绥怀蛮蜒”(45)《南齐书》卷54《高逸·明僧绍附明惠照传》,第928页。。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认为,对岭南各地诸族应“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46)《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第526页。。南郡内史王奂到任后,上表称其政治理想是“使边民乐业,有司修务,本府旧州,日就殷阜”(47)《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8页。。始兴内史范云上任时,当地“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他“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48)姚思廉:《梁书》卷13《范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0页。。
第三,手段灵活、成效显著。南齐许多大臣既深谙“以夷治夷”之道,也比较重视诸“蛮”群众的心理情绪和现实需求,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民族纠纷,化解了民族矛盾。例如,荆州刺史沈攸之处“蛮”失当,田头拟“发气死”后,其弟娄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豫章王萧嶷主政荆州后,立即诛杀娄侯而扶立田都,使“蛮众乃安”。另外,考虑到荆州各地“邻接蛮、蜑”,萧嶷又下令属官“皆缓服”(49)《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408页。,即穿上宽袍大袖的官服而不穿戎装,让少数民族从心底放下戒备,免其萌生反叛之心。再如孙谦出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前,齐明帝考虑当地多民族杂处,情况比较复杂,下令招募士兵千人随其赴任,孙谦则认为,“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坚决不受。抵达驻地后,孙谦“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竞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州郡以往掠夺的少数民族人口“皆放还家”,以至“郡境翕然,威信大著”(50)《梁书》卷53《良吏·孙谦传》,第772页。。武陵内史刘悛“善于流俗”,率领当地各族群众兴修水利工程,年过百岁的蛮王田僮亲自前来拜见,在他离任时,“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51)《南齐书》卷37《刘悛传》,第650页。。
三、南梁时期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随着南北朝对峙格局的形成,北魏逐渐意识到诸“蛮”在南北交锋中的重要价值,想方设法进行拉拢。如北魏泰常八年(423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款”(52)李延寿:《北史》卷95《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49页。,太武帝拓跋焘封梅安之子梅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兴光(454—455年)中,蛮王文武龙率众降魏,文成帝拓跋濬“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53)魏收:《魏书》卷101《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6页。。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诸“蛮”地近北魏政治中心,战略地位增强,北魏招揽诸“蛮”的意愿更加迫切,方法也更加多样。如孝文帝既大力封赏诸“蛮”首领,也对普通蛮民多加照顾,曾下诏称:“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54)《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第175页。由于北魏诸帝的拉拢,加之刘宋以来的讨“蛮”政策遭到诸“蛮”憎恨,南朝境内诸“蛮”接连投奔北魏,据《魏书·蛮传》记载,自延兴二年(472年)到正光年间(520—525年),至少有十三次诸“蛮”奔魏事件,人口总数约有80余万人。(55)参见《魏书》卷101《蛮传》,第2246-2248页;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北魏与诸“蛮”联合,给南朝造成了巨大压力。如光城蛮田益宗“世为四山蛮帅”,齐末奔魏,被孝文帝封为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景明(500—503年)初,田益宗击败南梁军队,斩杀千余人,后又主动上书请求南伐,希望乘萧梁“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之机,快速出击,“廓彼蛮疆”。田益宗计划“季冬进师,迄于春末,弗过十旬,克之必矣”(56)《魏书》卷61《田益宗传》,第1371页。!北魏遣镇南将军元英领兵南下,配合田益宗攻下南梁淮南重镇义阳。
面对这种被动局面,南梁执政者一面高举“大一统”旗帜,一面反思总结前代民族政策,形成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新认识,适时调整了治“蛮”策略,形成了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的治理方式。
梁武帝是南北朝时期渴望南北统一的标志性人物,他具有强烈的“大一统”心理情结,时时刻刻都想恢复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在即位诏书中,梁武帝就明确宣称要使“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57)《梁书》卷2《武帝纪中》,第34页。;天监四年(505年)命临川王萧宏大举伐魏,表示要“总一车书,混同禹迹”(58)严可均:《全梁文》卷2《北伐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页。;天监七年(508年)表达了“声训所渐,戎夏同风”(59)《梁书》卷2《武帝纪中》,第46页。的愿望;大同二年(536年),梁武帝对未能达到大一统目标表示遗憾,称“朕以寡德……不能使重门不闭,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车书未一”(60)《梁书》卷3《武帝下》,第80页。。晚年的梁武帝甚至连做梦都是“中原平,举朝称庆”(61)《梁书》卷38《朱异传》,第539页。。受此认识影响,南梁政治家、军事家基本也以实现一统为最高政治目标,将收服诸“蛮”视作统一天下大业中的重要一环。故此,萧梁上下在处理与诸“蛮”关系时,往往会以兵威使不服从者转为臣服,为北上收复中原创造条件,也会强调施行德政,注重恩情笼络,在树立正统权威的过程中使少数民族真心归附。
南梁时期,沈约和萧子显对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最具代表性。沈约字休文,出身吴兴沈氏,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时任散骑常侍、吏部尚书等职,深受梁武帝信赖,著有《宋书》一百卷。在《宋书·夷蛮传》中,沈约表达了他对诸“蛮”的认识:“四夷孔炽,患深自古,蛮、僰殊杂,种众特繁,依深傍岨,充积畿甸,咫尺华氓,易兴狡毒,略财据土,岁月滋深。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62)《宋书》卷97《夷蛮传》,“史臣曰”,第2399页。萧子显字景阳,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萧齐时获封宁都县侯,入梁后凭借出色才能,得到梁武帝礼遇和重用,任太子中舍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等职,撰成《南齐书》六十卷。在《南齐书·蛮东南夷传》中,萧子显表达了他对南方民族关系的认识:“书称蛮夷猾夏,盖总而为言矣。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充斥之事差微,声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怀远,其在此乎?”(63)《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史臣曰”,第1018页。
沈约和萧子显关于南方民族关系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也各具特色。沈约的思想观点带有强烈的历史反思意味,他比较关注南朝境内少数民族的现实境遇,认为对诸“蛮”的讨灭政策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很不仁义,充满报复性,缺乏恻隐之心。萧子显着重强调“德以怀远”的思想价值,认为这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正确道路。可见,随着多民族交往程度的加深,到南朝中期,社会上已明显产生了同情诸“蛮”的舆论氛围,主张通过恩德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史学家能够将这种价值观念表现在历史文本书写中,政治家们毫无疑问也会深受影响,推动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等治理方式的落地。
南梁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的治“蛮”方式,主要包括四项措施。
一是“以德怀之”。唐朝史学家姚思廉在《梁书·诸夷传》中将梁武帝处理民族关系以及外交关系的思路概括为“以德怀之”,称“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64)《梁书》卷54《诸夷传》,“史臣曰”,第818页。。梁武帝的这一思想落实在处理与北魏关系上,主要是善待北魏降将、遣使通和等(65)参见崔明德、胡慧琳:《梁武帝民族关系思想探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落实在处理与诸“蛮”关系上,主要是大力封赏诸“蛮”首领,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宋齐之际,诸“蛮”酋豪一般获封杂号将军,也有领太守等官职,但一般要加“试守”二字,如永明六年(488年),齐武帝曾以郢州蛮田驷路为试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驴王为试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66)《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传》,第1008-1009页。南梁着力提升其政治待遇,“蛮”酋入政时不仅取消“试守”等名称,甚至能担任州郡刺史等高级官职。如天监十三年(514年),司州反叛的蛮人田鲁生及其弟田鲁贤、田超秀南归,梁武帝封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田鲁贤为北豫州刺史,田超秀为定州刺史,命令他们“为北境捍蔽”(67)《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第344页。。为了招揽田益宗,梁武帝还开出了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价码。(68)《魏书》卷61《田益宗传》,第1372页。
二是“抚喻怀纳”。“抚喻”即安抚劝导,“怀纳”即怀柔招纳,这主要是针对南归者的处置办法。如田鲁生等人南下后,内部发生矛盾,田鲁生、田超秀互相诋毁,再起反叛之心。在此情形下,时任郢州刺史的萧秀“抚喻怀纳,各得其用”,稳定住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满足了各自的利益要求,使“当时赖之”(69)《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第344页。。对于那些受北魏欺压而被迫投梁的诸“蛮”群众,萧梁一些大臣更是多加招抚,尽力收纳。如天监八年(509年)三月,北魏荆州刺史元志率兵七万“寇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渡汉水来降”,南梁雍州刺史吴平侯萧昺准备“纳之”,但许多人认为诸“蛮”是萧梁祸患,建议顺势将他们全部诛杀。萧昺坚决反对,认为“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吾得蛮以为屏蔽,不亦善乎”(7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7《梁纪三》,“武帝天监八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592页。,遂打开城门接受诸“蛮”投奔。
三是“破掠诸蛮”。为避免诸“蛮”与北魏进一步合作,彻底解决“蛮虏协谋,志扰边服”(71)《南齐书》卷4《郁林王》,第70页。的问题,萧梁也曾采取武力措施,对附魏诸“蛮”展开全面打击。天监九年(510年),梁武帝“遣兵讨江沔,破掠诸蛮”,同年,雍州刺史萧藻遣蔡令孙等人“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72)《魏书》卷101《蛮传》,第2247页。。但是,南梁全面讨“蛮”政策受阻于北魏的抚“蛮”政策,诸“蛮”首领在北魏撑持下坚决抗争,萧梁出兵大多无果而终。如桓诞子桓叔兴被北魏宣武帝封为南荆州刺史,“萧衍每有寇抄,叔兴必摧破之”(73)《魏书》卷101《蛮传》,第2247页。。
四是“推心抚慰”。萧梁一些地方官员,由于长时间与诸“蛮”接触,对“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74)魏徵:《隋书》卷31《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88页。等特质比较清楚,深知武力讨伐并非解决民族问题的长久之计,他们以“抚慰”等手段处理民族关系,期望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诸“蛮”反叛问题。如东莞莒人臧严,因文采“博洽”得到梁武帝重用,先后在义阳、武宁等地任职,这些地方“皆蛮左”,以往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唯独臧严上任时不置兵马,只带门生数人“单车入境”,得到诸“蛮”信任,于是“群蛮悦服,遂绝寇盗”。再如湘州刺史张缵就任途中,上书表达了“六夷膜拜、八蛮同轨”(75)《梁书》卷34《张缵传》,第496页。的美好愿望,到任后他“停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积极推行抚慰政策,使得“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的莫徭蛮“因此向化”(76)《南史》卷56《张弘策传附张缵传》,第1387页。。彭城人徐文盛,大同(535—546年)末任持节、督宁州刺史,辖地“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徐文盛到任后,“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77)《梁书》卷46《徐文盛传》,第640页。。
综合来看,由于北魏后期欺压诸“蛮”以及南梁极力拉拢,诸“蛮”接连叛魏南下,成为南梁北伐的重要助力。天监十三年(514年),田鲁生等人最先叛魏,“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诸戍”(78)《资治通鉴》卷147《梁纪三》,“武帝天监十三年二月丁亥”条,第4608页。。正光二年(521年),田叔兴“南叛”,使北魏“南荆荒毁”(79)《魏书》卷62《李彪传》,第1399页。。孝昌(525—527年)初,“萧衍遣将曹敬宗寇荆州,山蛮应之,大路断绝。……荆州危急,朝廷忧之”(80)《魏书》卷71《裴叔业附裴衍传》,第1575页。。南梁围攻广陵,“樊城诸蛮并为前驱”(81)《魏书》卷101《蛮传》,第2248页。。北方六镇起义时,诸“蛮”也多有响应,当时荆州、郢州蛮“大扰动,断三鵶路,杀都督,寇盗至于襄城、汝水”,迫使北魏孝明帝下诏称:“朕将亲御六师,扫荡逋秽,今先讨荆蛮,疆理南服”(82)《资治通鉴》卷150《梁纪六》,“武帝普通六年冬十月”条,第4707页。,从而分散了北魏的平叛精力,加速了北魏的瓦解进程。因此,南梁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的治“蛮”策略,大体上获得了成功。
但对于居住在江淮各地的蛮人,南梁比较注重施加恩惠,以避免骑墙状况出现,对于那些远离南北斗争中心的岭南及西南各地俚、僚诸族,南梁统治者因不甚担忧其大规模投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就缺乏危机意识与恩德观念,甚至重走刘宋旧路,不但武力镇压,而且恣意掠夺,暴露了南梁统治者的短视以及民族政策的压迫本质。例如,因“湘、衡界五十余洞不宾”,梁武帝命衡州刺史韦粲出兵讨伐,“悉皆平殄”(83)《南史》卷66《欧阳頠传》,第1614页。。鄱阳王萧范为益州刺史时,“山谷夷獠不宾附者,并遣瑱征之”(84)《陈书》卷9《侯瑱传》,第153页。。武陵王萧纪在蜀期间,“开建宁、越嶲,贡献方物,十倍前人”,梁武帝“嘉其绩,加开府仪同三司”(85)《南史》卷53《梁武帝诸子·武陵王萧纪传》,第1328页。。吴平候萧劢任淮南太守时“以善政称”,任豫章内史时,当地“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但升任广州刺史后,他立即讨伐俚人,并将俘虏“生口”和所获“宝物”送交朝廷,梁武帝十分欣喜,感叹说:“朝廷便是更有广州。”(86)《南史》卷51《梁宗室上·吴平侯景附劢传》,第1262页。再如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奇“在益部累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87)《南史》卷46《张奇传》,第1162页。,当时南梁“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88)《魏书》卷101《獠传》,第2249页。。
四、南陈时期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南梁末年,梁武帝处置东魏降臣侯景失当,爆发了侯景之乱,使南朝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侯景之乱既改变了南朝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南朝的社会结构,南方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进而影响了南陈时期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方式。
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认为“其故即在所谓村屯岩穴之酋豪乃乘机此役复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酋豪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士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谿俚诸族”(89)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页。。据陈先生考证,梁末陈初的侯安都、候瑱、欧阳頠、欧阳纥、黄法氍、徐世谱、熊昙朗、周迪、留异、陈羽、陈宝应等人皆出身少数民族庶族豪绅。朱大渭先生据此进一步指出,建立南陈的武帝陈霸先以及陈拟、陈慧纪、周敷、余孝顷、陆德和等人“也有出身于少数民族酋帅之可能”(90)参见朱大渭:《梁末陈初少数民族酋帅和庶民阶层的兴起》,《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2-362页。。
关于陈霸先等人是否为少数民族,或需要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平定侯景之乱过程中,南方各地少数民族酋帅纷纷崛起,他们中一部分人成为平乱主力,并在南陈建政后成为朝廷支撑性力量,当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91)《陈书》卷20《华皎传》,第271页。。另一部分“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召”,经历侯景之乱的南陈“边鄙日蹙”“衰微已甚”(92)《南史》卷79《夷貊下》,“论曰”,第1987页。,缺乏讨“蛮”实力,只好最大限度维持现状,“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93)《陈书》卷13《周敷传》,第201页。。另外,南方各民族合力保家卫国以及共同建立新政权的特殊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民族冲突,促进了民族交融。在此历史背景下,陈霸先在称帝诏书中就明确表示不强力打压那些“擅强幽险”的“山谷之酋”,而是“皆从肆赦”,赦免他们的罪责,并派遣使者“具宣往旨”,希望各地酋豪“念思善政”(94)《陈书》卷2《高祖纪下》,第33页。。陈文帝陈蒨在位期间也以“惠养中国,绥宁外荒”(95)《陈书》卷4《废帝纪》,第69页。为要务,陈宣帝陈顼更是形成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96)《陈书》卷5《宣帝纪》,第86页。的思想认识,将境内各族视作陈朝子民,不刻意渲染夷夏之别,更看重夷夏一家。
受此认识影响,南陈时期除了个别大臣出于经济目的而“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丝毫不以赏赐。征求役使,无有纪极”(97)《陈书》卷36《始兴王叔陵传》,第494页。“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98)《陈书》卷20《华皎传》,第271页。外,多数地方官员不愿用兵诸“蛮”,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主要是以“抚御”为核心。如陈武帝即位后,酋帅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等人“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奉命前去招抚,“晓以逆顺,所在渠帅并率部众开壁款附”(99)《陈书》卷21《萧乾传》,第278页。。陈文帝时任荆州刺史的陆子隆,针对荆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现实情况,采取“绥集夷夏”的办法,深受各族群众好评,纷纷“诣都上表,请立碑颂美功绩”(100)《陈书》卷22《陆子隆传》,第294页。。阮卓任鄱阳王中卫府录事时,面对“交阯夷獠往往相聚为寇抄”的局面,积极前往“招慰”(101)《陈书》卷34《文学·阮卓传》,第472页。。陈宣帝时任广州刺史的马靖“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但“朝野颇生异议”(102)《陈书》卷21《萧允传附萧引传》,第290页。。另任广州刺史的沈恪,在“州罹兵荒,所在残毁”的恶劣形势下,对各族“绥怀安缉,被以恩惠”,于是“岭表赖之”(103)《陈书》卷12《沈恪传》,第194页。。太建八年(576年),沈君高继任广州刺史,当地“俚、獠世相攻伐”,沈君高“推心抚御”(104)《陈书》卷23《沈君理附沈君高传》,第301页。,使岭南地区得以安定。
五、余论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会根据国力强弱情况、民族关系现状等客观条件,在总结前代民族政策得失的基础上,形成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理清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采取具体细致的治理方式。宋齐梁陈四朝对诸“蛮”的认识各有特色,治理方式也有差异,具有阶段性变化及地域性区别等特点。刘宋重讨伐、南齐重稳定、南梁重恩抚,南陈重和谐,这是政治、地缘、经济、民族关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整体来看,南朝对诸“蛮”的认识与治理方式,总体趋势是从粗暴走向柔和,从盲目走向理性,从浓厚的功利性走向追求政治上的高度一统,武力讨伐的因素在减少,人文关怀的因素在增加。
这种趋势,既是这一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民族隔阂减少以及国家一体化程度加强的反映,同时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南朝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境界逐步提升,治理诸“蛮”的方式逐步理性,使得南方诸族的反抗情绪逐渐降低,互相认同、相互合作的观念逐渐上升,这有助于维护南朝各政权的稳定,有助于推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关于这一点,在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冼氏身上有着充分体现。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自幼贤明,“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后嫁南梁高凉太守冯宝。侯景之乱时,冼夫人深明大义,率军配合陈霸先北上平叛,并劝丈夫冯宝“厚资给之”(105)《北史》卷91《谯国夫人传》,第3005页。。太建元年(569年),广州刺史欧阳纥企图招揽岭南诸族反叛朝廷,冼夫人“发兵拒境”(106)《北史》卷91《谯国夫人传》,第3006页。,将其击溃。隋灭陈后,冼夫人更是展现出强大的民族一统意识,统率岭南各族主动归附,避免了大规模战争,为隋唐大一统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南朝时期关于“柔远能迩”“以德怀之”“抚喻怀纳”“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等思想观点的产生与实践,是隋文帝“以德训人”(107)《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第1843页。、唐高祖“胡越一家”(108)刘昫:《旧唐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页。、唐太宗“爱之如一”(109)《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第6247页。、唐玄宗“德以怀远”(110)董诰等:《全唐文》卷39《册十姓突骑施移拔可汗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4页。等思想认识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些凝聚着政治智慧与理论精华的思想观点,为隋唐盛世时高度和谐的民族关系局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