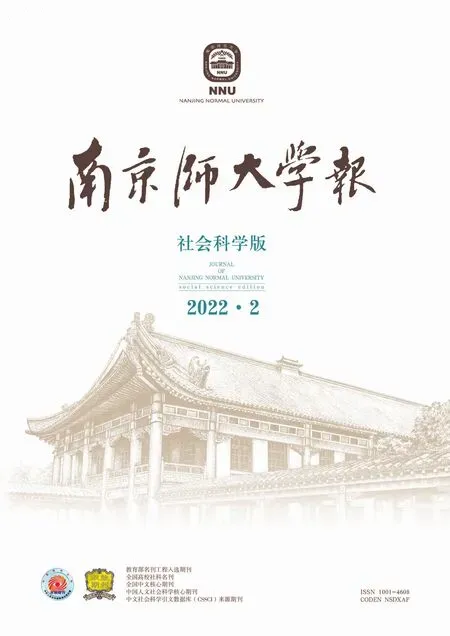实践理性的本体与价值:儒家诚德的现代义理
2023-01-05张方玉
张方玉
现代生活中的诚德,人们通常使用诚信、诚实、真诚等语词来表达,所谓持续推进诚信建设、倡导讲诚实守信用,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发掘传统道德资源和完善现代伦理学体系的意义上,仅仅使用诚信或诚实来诠释诚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自《中庸》聚焦诚德集中论述以来,“诚”已经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后来更是受到宋儒的高度重视,“诚”的学说获得进一步的阐发。近年来,学界对于“诚”的研究,有的侧重传统心性论探讨心灵修养与境界,有的侧重哲学本体论探讨人文精神与宗教性,有的侧重历史文献学探讨概念演进与逻辑,还有的侧重于阐释与弘扬“诚”的时代价值,可谓成果丰硕。问题在于,这些研究似乎仍然未能在现代德性论或者说广义德性论的维度上充分展开,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多数论文与著作所采用的表述依然是——儒家“诚”论、“诚”的学说、“诚”的范畴、“诚”的意义等,而并没有直接使用明确的概念——“诚德”。
一、 诚德:何种意义上的德性
伦理学的德性通常是指人类的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灵魂的三种状态——感情、能力与品质,德性便是其中之一;继而他排除了感情与能力,说明德性在类别上乃是品质;更进一步,他提出人的德性是使人状态好、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应当说,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德性的具体内涵的确是有所差别的,这里所谓“使人状态好、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具有典范的意义,然而就感情、能力和品质的关系而言,广义的德性论也可以将道德感情、道德能力置于道德品质之中。于是,在人类品质的意义上,德性还可以指向一种个人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品质,或者指向一种使人实现世俗成功的品质,或者指向一种使人达成美好生活的品质……理想主义的美德伦理学还将这种品质指向一种“内在于实践的利益”或“内在的价值”,倘若缺乏这种品质,那么“内在于实践的利益”或“内在的价值”的获得就受到严重的妨碍。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德性可以理解为道德的品性、善的品质。
儒家经典《中庸》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表述,一些学人看到这句话,便称中国古代思想早有“德性”范畴。必须辨明,《中庸》所谓的“德性”二字,并非今天伦理学所谓的德性概念。“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的“德性”乃是指“德”与“性”,两字在合成的结构中是平等的、并列的,与后面的“问-学”“广-大”“高-明”“精-微”是完全一致的语法。现代所谓德性一词则是偏正型结构,前面的“德”修饰限定后面的“性”,是指“德之性”。由此可知,《中庸》的“尊德性”虽然是二字联用,所表达的却是“德”与“性”这两个单字的意思,而不是现代汉语中德性的意义。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倘若以现代德性伦理学的眼光视之,中国古代的德性理论是否“先天不足”呢?事实上,中国古代对于德性条目的阐述是相当丰富与深刻的,不但没有因为缺失现代意义的德性概念而显得“先天不足”,反而不断地呈现出德性条目与体系的华丽盛景。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已经有明确的“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而在《洪范》篇中,又有明确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具有——齐,圣,广,渊,明,允,笃,诚——这样八种美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具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这样八种美德,十六种美德就这样一下子呈现出来。在《论语》中,仁、智、勇可谓童叟皆知,此外还有温、良、恭、俭、让,以及恭、宽、信、敏、惠;《孟子》“五伦”相应地呈现亲、义、别、序、信……仅此而言,儒家德性理论已经形成了人类伦理思想的高峰。
以上扼要列举了儒家德性的一些基本条目,从中不难发现儒家德性范畴不仅条目繁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体系性;既有纲领式的德性,比如仁、智、勇,也有具体而微的德行,比如温、良、恭、俭、让。在这众多的德性条目中,倘若让人们辨别出所谓重要的、核心的、关键的德目,人们大约很容易青睐“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而诚德,似乎早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为在《左传》的记载中,诚德和齐、圣、广、渊、明、允、笃并列,只是其中之一;“诚”在《论语》中鲜有提及,偶尔出现也只是语气助词“确实”的意义;而在后来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诚德又未能位列其中。不少学者认为,诚的本义是信,诚与信可以互释,《说文解字》里明确地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于是,诚与信相联,“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诚信被视为很重要的德性,成为儒家传统美德。(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那么,儒家的诚德果真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诚信吗?进一步而言,问题可以这样提出:诚实、诚信是否可以诠释儒家诚德的完整内涵?儒家之诚德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德性?
现代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中,诚信、诚实是高频出现的德性语词。江畅教授的《德性论》将德性划分出四种基本类型:“利己的”德性、“利他的”德性、“利群的”德性和“利境的”德性,每种基本类型又细分出十个主要德目,综合起来就成了四十个现代德性条目。(3)江畅:《德性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9—87页。在这些基本的德目中,我们发现至少有四个条目与诚德直接相关,分别是诚实、守信、务实、忠诚,其中诚实、守信这两条被放置在利他德性中,务实、忠诚这两条被放置在利群德性中。可以看出,诚实、守信、务实、忠诚这四条颇具代表性,大体表明了现代社会对于“诚”的理解。然而,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儒家诚德原本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完整把握儒家“诚”的哲学或许并非易事,但对儒家的诚德进行初步了解也并非难事,儒家经典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有所体悟: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
《中庸》与《孟子》均以“诚”为“天之道”,“诚之”与“思诚”则为“人之道”,于是诚德立刻便具备形而上的本体论基础,进而可以“参赞天地”。这一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语境中的诚实、守信、务实、忠诚的意义。再看“反身而诚”与“养心莫善于诚”,儒家诚德所蕴含的修养论、境界论对于今天喧嚣的社会生活当是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至于宋代儒家大力弘扬诚德,诚德的地位持续提升,成为诸德性之本,成为诸德行之源。
考虑到儒家诚德这样丰富的内涵,于是有学者提出:在本体论言,“诚”既是“天道”,又是人的心性本体;在心性论言,“诚”既是主体的心灵境界,又是主体的道德意志;在德性论言,“诚”是至高的德性,是德性的心灵根基,是为善的持续动力和心理依托。(4)鲁芳:《道德的心灵之根——儒家“诚”论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呈现儒家诚德的深刻内涵是颇有价值的,因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诚德的多重样貌,而问题在于:这里所谓本体论、心性论、德性论的区分实际上造成了儒家诚德作为整体的一种撕裂。探讨儒家诚德是何种意义上的德性这一问题,首先应当明确是在现代德性伦理学的语境中展开的,在此语境之中,所谓本体论层面和心性论层面的考察完全可以置于广义德性论的场域内进行有效的开展。
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诚德的探讨就具备了如此前提性的定位:儒家的诚德乃是一种包含诚实、诚信等意思在内,并且具有更加深刻内涵的德性,是涵盖了形而上之诚德(至诚无息)和形而下之诚德(诚实诚信)的整体德性,因而是儒家德性体系中一种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意义的德性。
二、 至诚无息:根源与本体
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道德现象,把握道德本质,揭示道德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现代视域中儒家伦理学的探讨,显然不能仅仅在道德一般本质的层面上进行,比如人们较为熟悉的社会意识、行为规范、个体修养、内心信念,等等。所谓儒家德性论乃是要在道德哲学的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刻的阐释,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实践精神,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式,是人类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的实践活动。由此,道德之实践理性的意义理应是伦理学关注的重要对象。“一门理想的伦理学要到彻底理解了它所研究的现象时才算完成。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普遍性的知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要实现这个理想,伦理学必须成为哲学的,它必须就是哲学。”(5)[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我们发现,儒家的诚德在事实上已经展开为两个层面的本体论:道德本体论(人道)和宇宙本体论(天道),可以认为,儒家诚德内在地提供了一种东方哲学的道德根源论和宇宙本体论证明,实践理性的根源与本体得以确立。
按照西方哲学的路子,儒家文化曾被视为一种常识性的道德,孔子开创的伦理思想,甚至被认为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因而缺乏所谓思辨的哲学。这样的理解,大约只是把儒家思想局限在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中,大约只是看到“仁智勇”或者“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之道,大约只是看到克己复礼、孝悌为本的行为准则。由此推论,儒家的诚德为西方学者所忽视,恐怕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倘若“至诚无息”“至诚之道”或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进入其研究视域,中西哲学之间一场道德形上学或者实践哲学之间的对话想必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情形。
诚德是儒家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德性,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诚”可谓核心范畴之一。《中庸》明确“诚者,天之道”,又讲“诚之者,人之道”,这就在实际上确立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基础。诚德贯通天道与人道,兼具人类道德和宇宙本体的双重内涵;既是具体的德性条目,又意味着一种具体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理性的根源与本体,儒家之诚德集中且体系化地展现为“至诚无息”的论述: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中庸》)
与《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论述相互映照、相得益彰,“至诚”同样展现出儒家天人相通的思想模式。以今天的语言和视角来阐释,儒家有关诚德的思想实际包含着一个相当系统的宇宙本体论——结构与功能:“至诚无息”与“天行健”是就天道的层面而言的,于是在人就落实为自强不息,这是“天-人”结构;“高明”与“博厚”展现出一种空间性,“悠久无疆”则展现出一种时间性,合在一起就成为“时-空”结构;再进一步,“博厚载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就将这种“天-人”结构与“时-空”结构统一起来,呈现出“结构-功能”的系统,这种结构的功能就清楚地呈现为“载物”“覆物”“成物”。倘若将这种功能延至人类,那么便是“成人”与“成圣”。“至诚无息”所描述的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实际就构成了人道之诚德的根源与本体,结合《易传·文言》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来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诚德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
在“道德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论证上,《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与“至诚之道”的逻辑思路是简捷有效的,这就是由天道贯通人道。相比之下,康德的实践哲学则复杂得多,《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以存在者的自由作为道德的基础,同时又将存在者的道德视为自由主体的基础,于是陷入一种循环论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善良意志符合自由的特征,就是以善良为自身目的的意志,善良意志就是道德自律——自己立法、自己守法。“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唯有在这个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实践法则符合一致。”(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35页。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的自律准则应当始终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这被称为“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是自我的主观判断,同时必须符合理性的普遍要求。这样,“善良意志-道德自律-绝对命令”在逻辑上就构成了由“每一个存在者的意志”上升到“普遍规律的意志”的思想路径,无疑地,这与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口号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在实践理性上的根本性分歧:康德的实践理性是由个体到普遍,由存在者的善良意志形成普遍的绝对命令,是一种“人-天”致思;而儒家的德性则是由普遍到个体,由普遍的天道落实为具体的人道,是一种“天-人”致思。康德哲学留给世人“天上闪闪的星斗”和“内心的道德律”,也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景仰和敬畏,然而必须明白,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律”并非由“天上闪闪的星斗”所赋予,这与儒家“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是根本不同的。
应当说,儒家诚德与康德哲学在道德本体论上的分歧是明显可见的。我们看到,近年来在解读《中庸》之诚时,出现了一种“上下通达”式的研究框架,似乎具有融合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情形。在《中庸的思想》一书中,陈赟认为通常的理解——“诚”是天的存在方式,“诚之”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流俗”的理解:将人道视为天道下贯、落实到人的结果,又将诚的本原、本性分配给先行于人道的天道,于是人道的“诚之”就被视为对天道之诚的摹仿。“天道之诚在最为本质的意义上乃是对人敞开的,自在的世界并没有诚或不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诚者天之道’所表述的,乃是对人而言的天道(在人之天道),而不是脱离了人的存在而言的天道之本然(在天之天道)。”(7)陈赟:《中庸的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0页。在陈赟看来,倘若没有人的参与,天道展现的自在世界无所谓“诚”的本性;因为人的自身活动、因为人的活动踪迹和烙印,所以才有天道之诚。我们不难发现,陈赟的观点明显具有康德哲学的印记——人为自然界立法,想要推崇的就是人本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以人类意识为中心的认识论,来展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儒家之诚,可谓现代哲学的一种尝试,但似乎并不符合儒家诚德的“天-人”结构。实际上,《中庸》正是直接从天道之诚的先验性、普遍性出发的,并由此贯通人道之诚,从而确立实践理性的根源与本体。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诚德才不仅具有道德根源论意义,而且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
就实践理性的本体论意义而言,围绕诚德的争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上文所述的争论存在于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天道与人道(天-人)关系问题,这是侧重于宇宙本体论层面的争议。围绕诚德的另一争论来自于儒家伦理思想内部,其中心论题是诚德与仁德(诚-仁)关系问题,这是侧重于道德本体论层面的争辩。
“诚”与儒家诸德性的关系上,极为简明扼要、言简意赅的论述当是周敦颐的名句:“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8)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页。短短九个字,儒家诚德的地位即刻显现。所谓五常之本,即为仁义礼智信之本,周敦颐认为“诚”是天之所赋予、是事物所受之理。倘若无“诚”,那么五常之德就是“皆无其实”,因此诚德是圣人之本。应当说,这一论断与《中庸》所谓“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是一致的,影响力也很大,后世学者一般深以为然。朱熹所谓“诚者,天理之本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也是对此论断的接续与发扬。在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看来,“仁是诚的真实内容”,可是他又说“诚是仁的全体呈现”,“诚的作用,即是仁的作用”。(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31—134页。这种表述貌似梳理了诚与仁的关系,实际上却使二者关系显得有点混乱,完全不像周敦颐“五常之本”那样简洁明了。而在《仁学本体论》中,陈来先生又明确提出:“儒学即是仁学,故儒学的本体论亦即为仁学的本体论,仁学本体论即是仁的本体论,仁的本体论即是仁学的本体论。”(10)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9页。陈来先生的重要依据是宋儒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共生共在、互相关联而成为一体,所以“仁”可以视为绝对的形而上的本体。这样,在现代哲学的视域中,“诚本体”与“仁本体”的论辩就难以避免。
可以看到,所谓“诚本体”与“仁本体”的论辩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伦理学的范畴,仅就现代德性论而言,在“诚德”与“仁德”之间作一个分辨,明确何者更加具有形而上之本体意义,应是分内之事。综合考察《中庸》之“诚”与《论语》之“仁”,不难发现,“至诚无息”的形上学本体论意义显得更为丰满,可以将“至诚无息”视作儒家实践理性的根源与本体。
三、 诚者自成:意义与价值
实践理性的意义与价值,这是道德哲学摆脱抽象化、空洞化所依赖的基本议题。采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道德何为”或“道德何用”的话题,这也是对于“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深刻发问。需要指出的是,一旦道德哲学的问题放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生活语言所造成的歧义似乎就不可避免。比如,我们说“实践理性的意义与价值”,这是较为清楚的表达;而当我们论及“道德价值”时,往往就会落入讨论某种行为、某些事件或某类现象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于是“道德价值”的讨论就变成了“道德评价”,而实际上原本所要进行的乃是整体性和根本性的追问。再比如,生活中提及“道德价值”时,人们又常常将它混同于“道德功能”,于是罗列出道德所具有的认识功能、调节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等。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道德价值,就可能使伦理学趋同于社会调节与控制理论,就此而言,伦理学的直接效力似乎要比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逊色得多。于是,许多现代伦理学者开始不再宣扬“道德永远符合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而是更加理性地提出:“坚守道德原则,使得人们尽可能生活得和平、幸福、充满创造性和富有意义。”(11)[美]雅克·蒂洛等:《伦理学与生活》(第9版),程立显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27页。无疑地,这种观点推进了人们对于道德价值的理解。
将道德限定于人与人存在利益关系的场合,实际上只是将道德视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充其量仅仅是道德的工具价值、手段价值。而社会关系所调节的,大多数只是一种“外在利益”。在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看来,“外在利益”具有明确的社会竞争特征,可以视为竞争的对象,而这样的社会竞争中必然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人类真正的美德并不在于获得这样的“外在利益”,因为美德的获得能够有益于整个参与社会实践的共同体。在这样的意义上,麦金太尔提出:“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拥有美德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12)[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受到此种所谓“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启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实践理性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将道德视为“社会关系调节器”只是道德的工具价值、手段价值,只是那些“外在利益”的调整,那么道德的目的价值、内在价值是何种形态?我们发现,古典美德伦理学实际上已有很好的呈现。比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善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至善是完满的善”,“幸福就是美好的生活和善良的行为”,“善与幸福具有自足性,仅仅依靠自身就可以完满”。与此相对照,儒家经典《中庸》关于此种“内在价值”与“自足性”的论述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诚者自成”“至诚如神”不仅深刻展现道德的“内在价值”,而且直接将这种“内在价值”推至“与天地参”的高妙境界。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
如前所述,儒家诚德包含宇宙本体论和道德本体论的双重意蕴,所谓“诚者自成”和“道自道”不仅展现出万事万物生成运行的过程,而且很好地说明了“诚”的功能与价值——“天下至诚,能尽其性”:不但可以“尽人之性”,而且可以“尽物之性”,进而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所谓“尽人之性”,《中庸》又称为“成己”,与仁德内在关联;所谓“尽物之性”,《中庸》又称为“成物”,与智德内在关联,这样看来,儒家诚德实际上意味着仁与智的统一,意味着内外之道的贯通。在意义世界生成的维度上,因为“诚者自成,而道自道”,所以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于同一进程中展开,或者说:人的自我认识、发展和完善,与世界意义的呈现在同一过程中展开。“成己意味着人自身通过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自由、完美之境;成物则是通过变革世界而使之成为合乎人性需要的存在。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人既赋予期望与理想以实质的内涵,也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了内在的意义。”(13)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诚者自诚”——成己与成物,其形上学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所统摄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述,可以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或者是探索真理与创造价值,还可以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甚至也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正因为此种统摄全体的表达,诚德所蕴含的一个极具儒家特质的意义往往被忽视,与“成己”“成物”相对应,可以称之为“成事”。
儒家之“成己”,人们是非常熟悉的,孔子所讲“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是为“成人之道”的经典名句。此外,《论语》中还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成年直到终老,是一个不断“成己”的过程,可谓“成人”的纵线结构,而“道、德、仁、艺、诗、礼、乐”可谓“成人”的横线结构,此种纵横交错式的“为己之学”完全可以理解为“诚者自成”于人生实践的具体落实。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庸》所谓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无疑地,儒家之诚德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实践理性的内在价值。“道德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美满的人生。道德实践是追寻美满的人生的一种不能间断的活动。而道德实践所依赖以及所成就的,就是各种德性。”(14)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11页。
儒家之“成物”,是一个需要郑重审视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为某物”与“成就某物”,或者“视某物为某物”,或者“使之成为某物”。儒家着意的始终是基于人之主体的“为人之物”,而不是尚未与人发生关联的“自然之物”或“本然之物”。这就是说,儒家之诚所彰显的“博厚载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并非是在“自在世界”而言,而是发生于现实的“人化世界”,可以说,儒家诚德赋予“成物”二字以深刻的人类烙印。这与道家思想“法天贵真”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一个遵循任自然而无为,另一个则是“择善而固执之”。《中庸》所讲“成物”,总是内在关联着“成己”,比如“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在这里,“尽人之性”是作为“尽物之性”的前提条件出现的。《中庸》又讲“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如果说“成己”是“内”,那么“成物”便是“外”;如果说“成己”是“体”,那么“成物”便是用。《荀子》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能够非常形象地呈现“成物”的意义:
“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
荀子所谓“礼者,养也”——“养口”“养鼻”“养目”“养耳”“养体”,这种提法显然是就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言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成物”实际上意味着人的创造性和本质力量的不断发挥,是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体现,也体现出儒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在“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上,除了《中庸》的经典表述,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以及张载所谓“民胞物与”的论述,均可相互验证。
儒家之“成事”,《中庸》没有类似“成己”“成物”那样明说,大体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人事;第二,政事。朱熹的解读:“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这是就广义的“人事”而言的。按照儒家一般的轨迹——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可以在狭义上来解读“成事”,就是侧重指向“政事”或“为政之事”。在这个意义上,“成事”可以视作“诚者自成”的一个颇具儒家特质的重要价值,可以看到,《中庸》对此有着力的论述: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
如前所述,“成己”与“成物”具有明显的形上学意义,这里的“成事”主要是就治理国家事务而言的,应该说,前面“成己”“成物”对于“成事”具有统摄的作用。之所以将“成事”专门列出,正是为了突出儒家诚德对于“为政以德”的特殊价值,而这又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比如,《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又如,《荀子》讲:“夫诚者,君子之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再如,宋儒所讲:“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临人则人化……”(16)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0页。由此可见,讨论儒家诚德的意义与价值,除了“成己”“成物”这两个基本的方面,“成事”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中,冯契先生提出:“我有真诚的德性,便体会到与天道合一,而性显现为情,便又能在色、声等情态中直观自身,这就是由诚而明。而转过来,结合感性实践活动来认识和把握天道与人道,经存养而使之凝而成性,这就是由明而诚。”(17)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自诚明”和“自明诚”是《中庸》的两个经典表述,冯契先生赋予其新的意思: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推动“自诚明”和“自明诚”的循环往复,“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不仅在理论上达成宇宙本体论与道德本体论的统一,而且在实践中达成德性与天道的统一。我们今天探讨儒家诚德的现代义理,就是试图在道德哲学的维度上讲清楚儒家之诚是何种意义上的德性,讲清楚“至诚无息”何以成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基础与本体论根据,进而努力呈现“诚者自成”对于儒家伦理和现代道德的意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