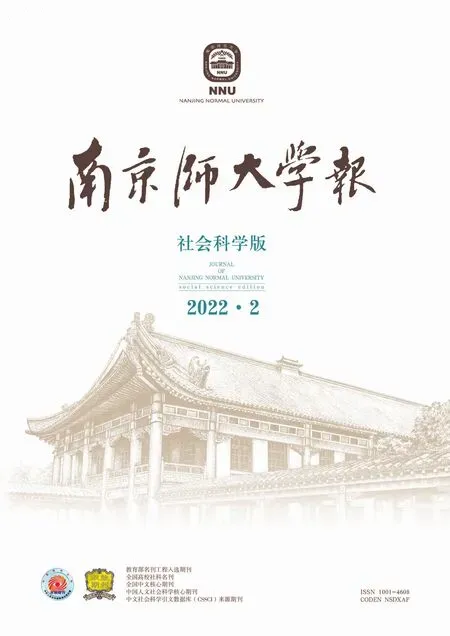教育的拥有、显现、仿真与扬弃异化
2023-01-05孙迎光
孙迎光
审视与克服教育异化与“五唯”现象,是一个思想史上的逻辑寻根过程。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批判到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再到鲍德里亚的仿真社会批判的理论变化,揭示了现代社会异化由拥有到显现再到仿真的变化。这些异化形式渗透到教育中来,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异化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重新再生,“五唯”作为顽瘴痼疾反映了人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异化侵袭。教育异化背离了立德树人的目标。本文借助异化批判理论的厚重历史感的纵向思维,解析异化产生原因与破解之道。
一、 拥有、显现与仿真的异化批判理论要义
拥有、显现与仿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相继产生的三种异化形式,它们的历史脉络分别由马克思、德波、鲍德里亚进行了批判性揭示。马克思揭示了拥有异化。《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商品生产和消费组织起来的,主体的人为客体的物所支配,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在这个颠倒的社会中,人受拥有感所支配。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这对理解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片面”不同于A+B+C+D+E式量的全面相对立的片面,片面的人表现为“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他除了对财富的拥有之外,没有自己的人生。它指以拥有资本那样的心态拥有对象,“片面”表现为除了对对象的拥有感,人们感受不到对象的存在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使物获得了新的物性——价值。例如,在为拥有感所支配的商人眼中,这种新的物性——价值就成为物的真正的物性。马克思指出:“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了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1页。在商人的功利性眼光中,玉仅仅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件商品。商人在面对个别对象(玉)时,由于对象的商品性质(价值)而使对象(玉)“变了形”——成为具有金钱价值的“珠宝”。其感觉发生了异化,沦为马克思所说的“绝对的贫困”。
人必须拥有一定的财物才能生活,然而,如果被拥有感所支配,他就沦为“绝对的贫困”——“片面”。在拥有感支配下,全面发展变成了全面拥有,拥有的最多的人就是在质上最片面的人。拥有感所支配的片面是理解全面发展的一把钥匙,它为教育破解“五唯”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五唯”表面上错在偏激、过分,实质上是拥有感作祟。
从早期竞争资本主义到后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社会现实复杂化了,发生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视觉文化成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商品没有被电子影像生动展示,它作为物在商店中与顾客直接“碰面”,表现为商品——顾客。在德波写作《景观社会》年代,商品通过广告这一影像与顾客间接“碰面”的现象流行起来,表现为商品——广告(商品影像)——顾客。
德波从马克思拥有批判理论中获得灵感,揭示了新异化。《景观社会》开篇模仿马克思的表达方式:“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5)[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景观是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影像。在景观社会中,影像取得了支配地位,景观无处不在。广告商是神奇的操纵者,影像轮番出场的喋喋不休强制性地制造了公众唯一的接受模式——消费模式。资本主义社会在物的依赖阶段中产生了新型的依赖——影像的依赖。由商品、货币与资本的依赖发展出影像依赖,此时,商家通过影像引导、刺激消费。对消费者来说,仿佛比商品使用价值更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品影像,似乎影像胜过商品,产生“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的错觉,(6)[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第1页。影像成为商品物化的新形式。
在早期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使不相容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在后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支配权是间接的,通过影视技术手段设计出来的影像的中介使交换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物的外壳下掩盖的社会关系,人被物所控制。在德波看来,景观就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像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组成景观世界,支配与控制着商品生产和大众生活。这样,继三大拜物教之后,又出现了景观拜物教。物与物的关系进一步颠倒为景观关系,物被影像所控制。
在景观社会中人类出现了继拥有之后的第二次异化。德波指出:“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7)[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第6页。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社会中的异化是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真“存在”的活动)向拥有(即德波的“占有”)活动堕落,人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存在)而是取决于拥有物(占有)。人不是“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而是在拥有物中展示自身;景观异化是从拥有向显现的变异,一切实际的拥有让位给了它的以符号形式出现的表征。异化由第一阶段的拥有异化升级到第二阶段的景观异化。
继德波之后,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另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仿真。他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仿真社会,现实陷入“代码”“仿真”的超现实之中。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建立在复制(时尚、媒介、宣传、信息和交往网络)的层面上,发生在拟象和编码领域。在仿真社会中,时尚、广告和商品的增长增加了符号和景观的数量,导致了“符号价值”的增长。“消费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9)[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成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替代,符号在商品中“植入”虚幻的“名望”,它具有社会区分的价值,消费者通过特定的商品符号(名牌)的追求获得与其他人相区分的“身份”“地位”“名望”的满足。商品通过符号价值获得了许多新的价值方式,产生了时尚的新世界,此世界成为生产象征性身份、地位的地方。在这种社会中,作为霸权的符号侵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符号支配着人,人对符号的迷恋引发了新的拜物教——符号拜物教。
鲍德里亚引巴特尔在《时装系统》的话说:“时尚没有内容,于是它成为人们给予自己的表演,他们所具有的使无意义产生意义这种能力的表演。”(10)[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鲍德里亚认为时尚的魅力和迷惑力就来源于此。“在时尚中,世界的消解是最终的消解。”(11)[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25页。在时尚这一社会实践中,真实事物消失了,客体被编码为构成消费社会的一个符号与意义的体系。时尚领域变成由技术媒介和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所促成的操纵符号的人工场所,个中有“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虚构、伪物品、伪事件和新现实。(1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7页。在这个场所中,仿真“不仅将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的事物表现为现实的事物,而且它还逐渐削弱同现实的任何对比,将现实吸收进自身。”(13)[法]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围绕仿真组织起来的,景观和符号成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人生活在仿真的“超真实”中,“真实死了,写实的符号万岁!”。(14)[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38页。仿真社会超越了景观社会进入了纯粹的符号王国。人们用特定符号炫耀自身,显示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人与人的关系是虚假的象征符号关系,“个体逃离了‘真实的沙漠’,为的是寻求超真实的狂热和由电脑、媒介以及技术经验构成的新领域。”(1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第12页。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相继出现了拥有、显现和仿真的异化,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的经济力量对人的统治。异化批判理论捕捉到了现代社会异化特征,开启了对异化批判的路径,为审视当代教育异化提供了分析方法。
二、 教育中的异化现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需要适度发展资本,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通过物与物的交往媒介和景观、符号的交往媒介来实现的范围不断扩大,必然出现教育异化现象,呈现出背离人民教育的图景,识别与克服异化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议题。
商品化原则渗透到教育中,产生了拥有式教育,它凸显了“五唯”指向:手段取代目的。它以拥有满足个体私欲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为教育目的,以从自己拥有的知识水平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为教育原则,以交换形式为教育方式(交换律表现为:知识交换分数;分数交换学位;学位、科研成果、项目等交换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将教育关系——人与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的关系——变成拥有者与拥有物的财富关系。“双一流”建设中重金挖人引发“帽子”在高校的无序流动,将这种关系推向极致。拥有式教育在有利可图的知识与无利可图的真理之间划上一条“粉笔线”,并屏蔽后者;它在“勤奋”与“多产”、“才智”与“拥有”、“文化”与“财富”之间建立起唯一的、必然的联系。它所谋取的全面教育就是全面拥有,它培养出的人逃避自己的天赋,其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旨在拥有,使拥有“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种人有着越来越亢奋的获取心,是文化的营利者,他殚精竭虑地琢磨怎样借文化以自利,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等成为他为拥有而辛苦攀爬的阶梯,他在创造性上是“不孕的”。注意:在现实的学校中没有纯然的拥有式教育(无一处在),但到处都可以看到其倾向(无处不在)。
拥有式教育的缘何(资本逻辑向教育领域渗透)和为何(教育旨在获得拥有物)使其在教育中造成了弗洛姆所说的拥有心态——“谁一无所有,谁就一无所是”(16)[美]弗洛姆:《占有或存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3页。。拥有式教育使人在价值与意义问题上,让数量起评判作用。在拥有量面前,重要的不是创造性,而是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的数量。受拥有感支配的心灵如此自语:“拥有的越多越善!”托夫勒在《财富与革命》一书中描写道:在未来社会,人一出生就在头脑里安置一块“芯片”,其头脑由于与“芯片”有机融合在一起,“芯片”能装下整个图书馆。这是拥有式教育追求知识拥有量的“理想极限”。然而,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等于智慧”。在拥有式教育中,头脑像弹簧一般,过重的知识拥有量使其失去创造性弹力。在拥有式教育中,学术竞争逻辑与市场竞争逻辑相通,教育场所变成隐性市场,教育行为变成商业行为。
拥有式教育作为顽瘴痼疾,其疾病细胞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升级换代。今天的异化不仅表现在拥有上,而且表现在德波所揭示的显现上,丰富的人被数据清洗为片面的“显现”,教育被表象化和景观化。今天,“学校和科研机构片面追求科研的绩效和功用,不遗余力地制造甚至包装各种评价指标,以争取资源、获得头衔或更好的排名”,(17)孟照海、刘贵华:《教育科研评价如何走出困局》,《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由此产生了“显现编码系统”,即从教育管理部门的宏观评价系统(各种建设指标)到学校管理的微观评价系统,出现追求“光鲜亮丽”的显现异化,产生一种“镀金的贫穷。”(18)[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第16页。教育评价就是在“显现编码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视觉表象化的学术锦标赛使绩效评价专注于显现的指标,拥有物要通过审计“显现”出来才有价值,真实的个体若不能被虚化为“显现”将一无所有。这对“五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博士毕业的论文要求、“非升即走”的教师入职规训使人一进入学术场域就积攒能够显现的拥有物,开启数据输入与算法输出的循环往复的学术生涯。“显现编码系统”检查一切而自身免检。这个系统作为学术生存法则具有强制性暴力,不能被审计的拥有物(有的学校规定省级期刊论文、核心期刊论文、C扩论文和省级出版社的教材等不得计算进科研成果量)就不能被显现,就没有价值。审计作为控制技术使“五唯”滋生出更多的“唯”,“五唯”应和着审计运作方式,挟持着教育。在显现异化影响下,它制造伪需要和虚假创造。“显现编码系统”成为不成文的名誉索引,牵引学者们的思维逻辑,使教育陷入显现泥潭,显现物发出的唯一信息恰如德波所言的“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19)[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第4页。审计使教育评价水平降到了最低点,技术官员与识数孩童具有同样判断力:学术水平高低和贡献大小体现于显现的数字。商品社会中“人受抽象统治”渗透到教育中表现为人受显现的数字统治。不否定教育评价改革中建构多元算法的举措,它能丰富评价体系,但在算法中产生的数字依附却使教育意义等于显现的算数和,滋生更多的“唯”,其中每一变量的数学权重都成为盈利标志。绩效与分配挂钩,“五唯”算法成为资源配置的尺度,影响“分配正义”。通过算法兑现利益来优化教育行为,使人彻底消解在“显现”的数字中。“显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学术天才、常才、庸才却被“显现”抹平了。“显现”制造学术竞争,随着学校间竞争的升级,“显现编码系统”得到进一步加强,显示物的资格也随之升级,原先够格的科研成果、课题、奖项等,随着要求的升级变得级别不够,失去了显现资格,成为没有价值之物。
恰如德波所说的,景观的本质是非理性地拒斥对话的,人从“严肃的精神”对待它。学校的管理理念物化为一套标准化指标体系。它作为强制性的暴力使人的认识、热情、欲望涌向“显现”这一中心,学校精力在于拼显现指标而不是教书育人。学术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而是生产显现的数字活动。这时,弗洛姆所说的“谁一无所有,谁就一无所是”的拥有异化,就发展到德波的“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虚化成为非真实的景观式的名望,他就一无所有”的显现异化,由“我是我拥有的一切”到“我是我显现出的一切”,由我被我的拥有物所取代到我被我的显现物所取代。这种异化造成“炫耀性科研”能力的增长,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追求“显现”的科研欲望消除了创造性的科研欲望。
在显现的竞争性互动的景观社会,无名则无利。迅速出名、迅速致富成为一些人的奋斗目标。一个人的显示物越多,获得的众多光彩的帽子(名号和头衔)就越多,就越是吸引崇敬的目光,越是受到顶礼膜拜,兑换的利益就越多。对名号和头衔的需求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论证会、评审会、鉴定会,滋生越来越多的“帽子”。5G时代为显现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技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变成全面显现。人的片面不仅体现于显现物本身,而且在于以拥有的心态制作显现物,将教育成果都变成显现物,使教育成果变成兑换与拥有活动的手段。犹如景观社会的影像制造运用美学策略,一些高校运用“形象的修辞”乱发“帽子”,通过名山大川来造势,使一些评不上“长江学者”的教师,成为“X河学者”“X山学者”,打造出类似武林小说中的“江湖景观”。据不完全统计,国家级和省级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20)张健:《人才“帽子”泛滥怪象亟待改变》,《人民论坛》2020年第18期。犹如影像控制着商品生产,表象式名望的帽子景观和“显现编码系统”控制着学术生产,所有科研活动都被导入显现物的建构活动之中。景观不是教育的装饰或补充,“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21)[法]居尹·德波:《景观社会》,第4页。这种异化彻底遮蔽了教育现实。
今天的异化不仅表现在拥有和显现上,而且表现在鲍德里亚所揭示的仿真上。时尚永无止息地用一个热点代替另一个热点,将创新与新颖混淆,为教育异化拓殖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空间,教育落入时尚模式的逻辑之中。有学者指出:“时尚界有模特,学术界也有‘模特’。学术界的模特就是人们常说的‘学术超人’。学术超人的一个重要能力就是要能够在学术领域制造‘热点’,从无意义中制造‘意义’……一旦热点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模仿就出现了。但是,正如时尚中的情况一样,一种东西成为时尚就意味着这种东西的‘死亡’。学术中的‘热点’来得快,去得快。花样翻新的各种人物、流派、思潮、领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什么东西热闹就研究什么。”(22)王晓升:《论学术“时尚”——从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分析说起》,《哲学动态》2013年第7期。时尚热点一出现,赶时髦者立刻蜂拥而至,出现新的“语言闹铃”——应景性论文,产生高影响因子成果,使“五唯”滋生影响因子一“唯”,论文影响因子越高越好。“时尚”凸显流行性“敏感因子”,触碰不到创造性的“钝感因子”。“学术超人”以追逐时尚这一“美的形式”(美的编码规则)掩盖逐利行为、炫耀自己的个性,其他人非但不反感,反倒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人物。“学术超人”善于“弄某学”,追逐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制造时尚“热点”,喜欢拙劣地仿制(仿真)。这些效颦者有化西方之神奇为本国之腐朽之能力。时尚具有传染性危害,它使人处于未反思状态,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相互异化和被异化。学者们为避免落伍过时而纷纷追逐学术时尚,彼此竞争和模仿,“痉挛于”时尚的变换之间。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时尚中,意义的消解更为彻底。”(23)[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126页。时尚使人们“陶醉于理性的毁灭,陶醉于意义的消解。”(24)[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126页。学术不再指向现实问题,而成为鲍德里亚所说的在符号上自指的“超真实”。有些博士论文的创新点就像牛仔裤上的“窟窿”,一个“创新点”就是一个从无意义中制作出意义的“时尚的窟窿”。学者成为废纸生产者,学术成为符号制作术。在景观异化中,显现物没有完全消除它所替代的现实物。在仿真异化中,现实完全消失了。“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超真实占据了统治地位,真实与虚假已经无法区分了。究竟哪种学问是真学问呢?不知道。”(25)王晓升:《论学术“时尚”——从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分析说起》。学术时尚化带来了思想的停滞和无意义文本的繁衍,产生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教育异化在学术时尚化中达到高潮,生产了一批徒有虚名、沽名钓誉的学者,损害了国家的学术竞争力,产生出科研成果的“物欲增值”与“学术贬值”的尴尬现象。
拥有、景观、仿真是异化道路上的路标,异化批判理论为教育异化提供了总体性图景。这些异化现象常常标明自己是现代性的,是与过时的传统不同的东西。“五唯”披着数字化、智能化评价外衣,化非结构性教育难题为结构性简易数据,产生貌似具有内在关联的“大数据”,掩盖“排名陷阱”。一些人为了获取名号与追逐时尚,不遗余力地追逐时髦,使教育流入华而不实的猎奇求新之中。由于这些异化具有极强的伪现代性,不仅掩盖了其片面性特征,而且赋予了人的发展的“神圣光环”。这些异化现象比学术不端现象更加普遍且更难识别,它们诱使人不作任何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抵制,并从精神上去适应它们。人们愈是获得了这种适应能力,就愈是深陷在异化的洞穴中而难以自拔。
三、 异化的根源及如何克服教育异化
新时代是创造性旺盛充溢的时代,教育担负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需要用异化批判理论烛照教育问题。异化现象不利于人民性的教育实践。使教育与新时代同步,实现人民满意的教育,化解人民心中的教育疑虑,需要了解异化的根源及克服教育异化。
(一) 教育异化产生的根源
异化凸现为能力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矛盾。卢卡奇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同时是人的才能的发展,但是人的才能的发展却不一定必然导致人的个性的发展,这样,异化问题才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26)[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18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当今一年生产的教授、博士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授与博士的总和。教育“生产能力”的提升使硕士、博士、专家、博导越来越多,学习能力、写作能力、研究策划能力不断提升,这并非必然导致人的本真的全面发展。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和“帽子”不等于创造性能力,但在拥有、显现、仿真道路上却不断发展出对它们的“获取能力”。
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教育不能撇开历史进程去抽象地谈论扬弃异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马克思资本批判深入时代问题的深层,揭示了资本建构现代社会,资本实现了“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的事实,从而揭示了异化现象的秘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通向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以异化的形式进行的,一系列异化形式——拥有、显现、仿真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今天,较之马克思时代,资本逻辑对世界的统治在强度与深度上已经空前扩大,中国教育命运与世界历史进程联系日益紧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精准分析历史条件是认清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新时代的基本国情决定着: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本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显现、仿真等异化迷雾会不断蔓延,成为教育生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将民族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教育要运用资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民族振兴创造基础,为向最终消灭资本关系,扬弃拥有、显现、仿真等异化的社会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异化与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克服教育异化是任重而道远的时代任务。
(二) 准确把握马克思全面发展思想的精髓
异化批判理论使我们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真实促进与虚假促进之间作出区分,使我们不再对异化现象像条件反射那样做出自发反应,而是作出批判性的自觉反应,使我们意识到全面发展在教育中是一个值得甄别的问题。在教育生活中,受拥有感支配的人越是积极地追求“全面”,就越是片面;使教育生活屈从于名望的人,越是急功近利地提升自己“形象”,就越是败坏自我形象;受时尚驱动的人,越是要“跟得上时代步伐”,就越是落后于时代。
在教育异化中,拥有、显现与时尚的异化具有历史连续性,它们互为表里,拥有是异化的内在动力,景观与时尚的目的在于兑换拥有物。在教育中,景观与时尚结盟,追求时尚的目的就是追求名望,追求名望的目的就是追求能够兑换更多物质财富。在教育异化中,拥有关系是人与教育世界的基本关系。这使今天异化与反异化斗争的焦点和核心在拥有感与克服拥有感上凸现出来。破“五唯”是治标,破除拥有感是治本。在新时代,教育要深刻把握马克思全面发展理论。
教育异化具有迷惑人的假象,拥有式教育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变成可计算的A+B+C+D+E全面拥有,上文所引的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此愚蠢而片面”之“片面”是指被拥有感所控制的质的片面,其所对应的“全面”是马克思所说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304页。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地从拥有感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学校的“鲜亮底色”,教育要理解“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必须把握马克思全面发展思想的精髓。这一精髓是破解“五唯”顽瘴痼疾之难题的源头活水。看不到本真的全面,仅仅倡导量的全面,就使全面单纯局限于A+B+C+D+E中。不可否认,拥有感会导致量上的片面,例如,教育中的五唯之一“唯分数”,就是追求量上的拥有感,它使学校只重智育而且是智育中狭窄的获取分数的知识教育,它最终损害智育。同时,德、体、美、劳的教育常常被挤占、被边缘化,导致量上的片面。克服“唯分数”现象,固然要倡导量上的A+B+C+D+E全面,但只有在质上摆脱了拥有感,才会有A+B+C+D+E意义上的真正全面发展。否则,就会沦为全面拥有,以貌似全面的方式走向全面发展教育的对立面。破除“唯分数”不是不要分数,而是要看是什么意义上(拥有感与摆脱拥有感)的分数,完全否定分数会走向教育的反智主义。
(三) 炸开“严肃世界”——破除拥有的学习心理基础
萨特指出具有严肃精神的人其人生状态处于未反思状态:“严肃的精神从世界出发来把握价值并且处于使价值宁静、物化的实体化过程中。”(28)[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74页。美国存在主义伦理学家E·巴恩斯依据萨特这一思想提出了“严肃世界”(the serious world)这个概念(29)[美]H.E.巴恩斯:《冷却的太阳》,万俊人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严肃世界中的标准和价值是绝对的、无须证明的。
拥有式教育中学生学习的心理基础是储存“牢固”知识兑换利益,学生追求大量的确定性知识而不是深刻的不确定性知识,其处在严肃世界中。当学生学习“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等时,把教材的作者对对象的理解与被理解的对象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学生意识不到“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教材都是编辑者眼中的“哲学”“教育学”“经济学”,学生将教材当成不可置疑的真理。
教育的第一步是炸开“严肃世界”,打破未反思的宁静状态。所谓“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30)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这并非否定作者的“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材料,而是拒绝将作者们的理解方式当成唯一的理解方式。若学生从小到大都将所教的“某某学”当成不可置疑的真理,教育过程就成为关于“某某学”命题性真理的“说法”的不断叠加过程:教师陈述着关于“某某学”命题性真理的“说法”,学生接受教师陈述的命题性真理,当轮到他们说话时,就陈述着关于命题性真理的“说法的说法”。说法叠加演变成漂浮无根的陈词,产生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教育现象。“说法”的功效只在于“兑换”,这为景观与时尚异化打下了心理基础。禅宗把祖师悟道的故事编集为《指月录》,学生需要知道所学的“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教材都具有这种性质,它们是指月的手指(编辑者对对象的理解)而不是月亮(被理解的对象)。教育的第二步是激发学生去学。海德格尔说:“为什么教比学更难呢?并不是因为教师应具有更多的知识积累,并得做到有问必答。教比学难是因为,教意味着让人去学。真正的老师让人学习的东西只是学习。所以,这种老师往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学生在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人们把获取知识才看作是‘学习’。真正的教师以身作则,向学生们表明他应学的东西远比学生多,这就是让人去学。”(31)[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17页。学习不仅仅是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教材知识,固然知识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但“把获取知识才看作是‘学习’”就是拥有式教育。历史上有三位教育大师展示了“教比学难”的教育境界: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孔子有“吾有知乎哉?无知也”,释迦牟尼告诉弟子们:“我说法四十九年,却没有说出一点真理。”他们不扮演万事通的角色,对知识毫无拥有之念,向学生展示自己一无所有,从而激发学生去学。好的教育是“教比学难”,它抑制和消除学生对知识的拥有欲望,不用拥有物来装饰自己,激发出真正的学。第三不去“弄某学”。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月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3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08页。“弄某学”是在某学之外、之旁旋转,不能进入某学。“学术超人”在“弄某学”,围绕学科建设,长年累月地筹划完成显现指标任务,造成“弄指标”(实为“弄某学”)就是学科建设的顽固假象。在留校和进校的学生都与指标挂钩的情况下,让学生进入某学显得特别重要。这需要识别与摒弃“弄某学”,独立思考关于“某学”的所未思、未闻、未言之物。海德格尔说最能激发人思的就是人们“尚未去思”,学生只有思考“尚未去思”之物才能进入某学。第四,解构拥有式“知识”。曾几何时,拥有式教育将知与识合并,以知掩盖识。钱穆说:“‘知’只是仅知其事,‘识’乃识其内里之情。内外一体,始为真识。”(3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连言的知识需要分开来说,知是知其事,识是对知的辨别与判断。在拥有式教育中,人被连言的知识麻痹很久了。破除拥有的学习心理需要以“知与识”学习代替未反思的知识学习。“知与识”学习的人越多,被景观和时尚迷惑的人就越少。
(四) 教育弘道——破除拥有的教育心理基础
教育处于“道理合成”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理的地位在道之下。钱穆说:“若我们向外面看世界,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看成为一个道的世界,一是看成为一个理的世界。”(34)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49页。传统教育学只看到“理的世界”,它“开宗明义”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教育规律,将自身定位于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此“宗”与中国教育祖“宗”不沾边。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不说“师者,所以传理授业解惑也。”师者的本分就是弘道。“道”蕴含着“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孔孟之道”“孝悌之道”“中庸之道”“大学之道”的立德树人的“谱系”。传统教育学不靠谱,没有中国文化的“谱系”,看不到“道的世界”,隐含着见物(规律与本质)不见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倾向。
钱穆说:“庄子说:‘道行之而成’。这犹如说,道路是由人走出来的。唐代韩愈在《原道》篇里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是说,道指的由这里往那里的一条路。可见道应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并加上人类的行为与活动,来到达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者始谓之道。”(35)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6—7页。道由目标与行动来完成。对于道,人可以自主选择。中国人讲“人道主义”不讲“人理主义”,有“大学之道”无“大学之理”说法,更无“人能弘理”一说。因为在道中有人的作为,在理中没人的作为。中国人讲“物理”不讲“物道”。用词不同,折射出中国文化大智慧。
传统教育学旨在求理,与“道”失之交臂。钱穆说:“王弼注《易经》,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这是说宇宙间一切万物绝不是随便而成其为这样的,宇宙万物,必有其一个所以然之理。”(36)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9页。这一“所以然之理”就是规律。“郭象注庄子,也说:‘物无不理,但当顺之。’”(37)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10页。事物都有理,人只能顺从理。传统教育学“有理无道”,对于规律“但当顺之”,只以旁观者姿态观察既定的教育规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更像“教理学”。有学者指出:“在规律面前,人们没有想象或创造的自由;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规律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教育活动不过是‘教育规律’的‘例行公事’罢了。谈论教育的主体性、创造性、自由性可以被认为是对规律的破坏。”(38)刘剑玲:《关注教育事件》,《上海教育科研》2005年第1期。在这种教育中,如果说人有自由,这种自由不过是理性地服从规律的命令和受规律支配,充其量是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自由。传统教育学“传理授业解惑”,抑制了人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的教学理论界有一种“教学认识论”,它认为“知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的化身或‘客观规律’的反映,它是普遍的、共同的:不论在专家的工作室还是中小学的课堂里,不论对专家、普通大众还是中小学生及其老师,知识的性质全都一样,改变的只是知识存在或应用的场景,知识本身没有变;知识理所当然应盘踞于课程的核心,甚至是课程的‘本质’;既然教学不能像专家的研究那样创造知识,那么教学的作用只能是忠实、高效而灵活地传递‘现成知识’;老师的‘教’本质上是对知识的传授,学生的‘学’本质上是对知识的接受,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以知识为纽带的授受关系,这种观点在我国的教学理论界被泛泛地称为‘教学认识论’。”(39)张华:《试论教学认识的本质》,《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34(6)期。这种教学认识论属于传统教育学,“穷理”代替“明道”,将教育视为传递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工具。在拥有式教育中教师教育的心理基础是将教育世界变成唯理的世界,使道在教育中失落。
“弘道”是中国教育的“元概念”,“五唯”与“五不唯”是教育“有道”与“无道”、“得道”与“失道”的大问题。解决“五唯”问题,“教理学”必须转变为“弘道学”,后者志于“道”,合于“理”。它将教育的研究对象“改写为”教育“根本问题”,它研究教育(培养什么样人的)目标、(如何培养人的)规律与(为谁培养人的)功能,而不是仅仅研究教育规律。它知道教育现象与规律不会自动呈现在人的面前。试想:没有弘道的目标,哪来的教育规律?以资本拥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教育就不可能研究全面发展教育规律。与之相反,“弘道学”确立(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标,“认识”与“发动”(如何培养人的)规律;“抑制”拥有、显现、仿真的异化教育规律;“忽略”机械记忆、题海战术的应试教育的规律,从而实现(为谁培养人的)教育功能。它以“道”为先,在认识、发动、抵制、忽略不同的“理”上彰显弘道的主体性。
“弘道学”需要弘道的教师。海德格尔说:“成为一个教师,才是更高的事务,这与当一个有名气的大学讲师或教授完全是两码子事。”(40)[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17页。今天,教授一评定终身,成为教授是教育者的一个对象性目标。人在成为教授过程中可能会在拥有、显现与仿真的异化中丧失自我。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成为一个弘道的教师是比教授更高的事务。职称可以被拥有,弘道行为不能被拥有而只能被经历。弘道的教师不是对象化的现成性职业而是非对象化的可能性事业。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1)《论语·学而》。弘道的教师将自己立于此三问的召唤之中,其教育境界(有悦、有乐、不愠)在不断提升,为拥有、显现、时尚所驱动的动机被削弱与废止。弘道的教师生存于道中,他“有价值地生存,而不是占有很多价值。”(42)[美]弗洛姆:《占有或存在》,第13页。
孔子说:“人能弘道”,他所奉行的教育就是弘道的教育。他的学生们都有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般的弘道、传道的使命感。历代中国人不断地弘道,使“道”沛然流行而莫之能御。于今,沿此道开启民族复兴新天地,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是弘道的教育,教育“根本问题”开启了新时代弘道学之路。
(五) 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教育是塑造社会成员的力量,教育评价是塑造教育的力量,必须突破“五唯”茧房。“五唯”不能评价“人才”,更不能评价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人。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本身并非是坏的,是拥有感导致的“五唯”产生了“顽瘴痼疾”,使它们变质了,评价尺度由“维”变成了“唯”。一个全然不关心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奖项的教师不是好教师;一个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奖项的教师也不是好教师。“五唯”(将评价标准的五个向度极端化、绝对化)则完全扭曲了这些评价标准,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与价值的判断,需要清除这一教育评价的“守门人”。
首先,找到顽瘴痼疾的病症。从表层上看,“五唯”是在以企业经营塑造教育管理,它由技术理性、计算理智、简化主义、绩效管理、审计文化共同促成,当今教育反思系于上述问题表层,精于微观分析。从深层上看,它是由拥有、显现与仿真的异化的症候群促成,这在反思中尚未触及,反思缺乏宏观视域。在破解“五唯”上,需要微观分析与宏观视域结合,远离马克思的宏观视域去研究微观领域难以把握住教育现实。“五唯”这一功利化倾向与拥有感相关联,背后隐含着资源、金钱、地位等拥有感意义上的竞争。在“五唯”中,重片面拥有轻全面发展是本质,重外在轻内在、重知识轻能力、重智育轻德育、重功利轻价值、重短效轻长远等等是现象。前者是顽瘴痼疾的病症,后者是病兆。理论反思只有抓住了问题存在的本质,才能为解决问题找到方向。其次,在宏观层面上,教育评价体系以教育“根本问题”为指导思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决定评价体系为何存在,“如何培养人”的规律探索决定了评价体系如何存在,“为谁培养人”的教育功能决定了评价体系承担的功能。只有在“根本问题”的指导下才能在“唯”与“不唯”上做出正确选择,抑制从“只唯”向“多唯”发展,在实现“五不唯”中防止出现“五不要”。最后,在微观层面上,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平等看待。探索文理不同学科及不同的亚学科的科研评估标准,建立有学科个性的评价系统,防止由一种评估标准导致科研同质化。建立合理有效的惩罚制度,加大对于学术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让学术造假者、学术不端者无可趁之机。重视学术批评,发挥学术监督作用,营造民主的学术环境。
宏观与微观都需要贯穿教育弘道精神,它是保障教育评价体系彰显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关键。否则,任何关于教育评价体系的创造性设想的科研成果都可能沦为显现指标的数据,任何一种抵制拥有、显现与时尚的行为都可能被其所反对的异化行为所同化。“破五唯”是陡峭的山路,需要“道”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