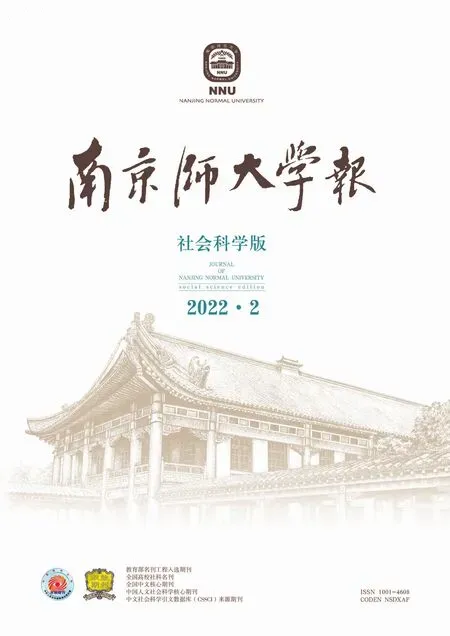同源异境视野下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探索
2023-01-05唐贤清
陆 露 唐贤清
21世纪初,刘俐李最早以“同源异境”为视角进行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实践。(刘俐李,2003、2006、2009)陈晓锦强调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要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其中所指“同一祖籍地方言不同地域变体的比较研究”,(陈晓锦,2016)亦是“同源异境”视野下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具体思路。综合前贤及个人研究实践,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特定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的新视角,可以进行系统化的范式研究。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构架。本文即立足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从同源异境语言比较研究实践、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概况、研究取向与路径等方面对这一研究探索进行理论梳理。
一、 同源异境语言的比较研究实践
自有人类产生,即有因战争、经济等各种原因的人口迁徙及流动,文化亦随之流播,并继而与其他文化互相渗透、交融。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同一种文化会经由不同路径传播并扩散至不同环境之下。本文所指“同源异境”即为此种状态。反映在语言上,则体现为:源自同一移民原乡的语言(或方言)存续在不同语言(或方言)环境中。这里的“异境”特指语言环境,而并不限指地域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同源语言或方言(即源语)受落籍地的不同语言环境(即受语)影响而发生演变,形成各种变体。
宏观来看,同源异境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初显范式化,并逐渐形成新的学科。
18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曾明确指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非“同一源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偶然性绝对解释不了;比较这三者的任何一位语文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来自同一源头。”(侍建国,2011)琼斯将梵语、拉丁语、希腊语联系起来进行共时比较,这是历史语言学初开萌蘖的明确标志。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这段论述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及其对于语言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历史比较法”的价值当然毋庸置疑,透过琼斯对于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近似性的亲属关系解释,语言学家们发现了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从而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构拟出其原始母语形式,为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更科学、更可靠的途径。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换一下,则可以发现:琼斯在语言学上的另一贡献还在于其所使用材料的特殊性。梵语、拉丁语、希腊语的共同源头是原始印欧语,由于分裂后的环境差异,它们形成了既具有共同核心特征又各有创新发展的不同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梵语、拉丁语、希腊语便是同源异境的语言实体,它们由于分隔时间久远、地域相隔,因而成为了同源语言的不同分支。历史语言学借助这些材料对原始母语进行构建,对原始语言状况进行拟测,从而探寻其同源性,这是属于“回顾”(徐通锵,2008)的研究模式。在不同环境下,同源语言还有另一种分化、演变形式,即:在流播至其他语言环境之后,源语在与其他语言长期接触后,其语言系统中的重构程度尚不足以形成不同的语言,但是已经体现出接触影响下的演变特征,这种同源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同源异境语言的一种具体表现。
社会语言学即主要关注于这种“语言地域变体”的研究,如世界英语变体(world Englishes)的相关研究便是其中的范式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英语世界地位的不断提升与国际化发展趋向,英语在传播至各个国家之后,与其他语言及文化长期接触,日渐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英语变体,如威尔士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马来西亚英语、菲律宾英语、南非英语、中国英语、日本英语等。针对世界英语变体的分布及特征,卡奇鲁(Kachru)提出了“三大同轴圈”理论,即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为“内圈”、英语变体作为制度化的第二语言使用的是“外圈”和英语变体作为外语使用、没有制度化的是“扩展圈”。(Kachru,1985)这一理论是针对新历史背景下英语全球传播的现实而进行的理论尝试与探索,对英语的众多变体进行了类型化分阶,强调了语言的多样性及本土化特征,是同源异境语言实体的又一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继有Peter Strenvens、Tom McArthur、Manfred Goörlach等从其他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索,近年来更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及丰富性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意大利语、法语、汉语等其他具有广泛传播特点的语言也在不同环境下形成不同变体,受英语变体研究的影响,其相关研究也有所推进。
考察不同语言变体的接触环境对源语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是在接触语言学的视角下可以拓展的新方向。这是在已知语言同源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比较,顺流而下,从而找寻语言在接触背景下的新变化。由于具有明确的发展动线,从而使得对沿其流而下的“前瞻”研究亦具有了切实深入的可能,是对传统“前瞻”研究方法在语料上的创新。
二、 同源异境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综合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人口迁徙流动密切相关。汉民族历史上自秦朝开始即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后继有魏晋南北朝、两宋、元明等数次大规模迁徙。社会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了语言上的接触、融合,如宋元时期的司豫移民行为形成了客家方言,北宋汴梁地区的移民行为形成了吴语区内特殊的杭州方言。周振鹤、游汝杰曾提出方言形成与移民相关的两种情况:“一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同时向不同地区迁徙,在不同的条件下经过发展演化,成为不同的方言;二是操甲地方言的部分居民在某一历史时期迁移到乙地,久而久之,同一种方言在甲、乙两地演变成两种不同的方言。”(周振鹤、游汝杰,1995)这两种情况都是相对宏观的视角,即接触与融合的时间相对较长,造成了语言本质属性的演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方言。
随着社会发展,汉民族移民活动仍在不断进行,迁徙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向国内其他省份迁徙,如客家人在明末清初由广东、福建迁往湖南、四川、台湾等地;另一方面则是向海外迁徙,如明朝末年即有福建及广东沿海居民向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迁徙,“至迟在15世纪初,东南亚已出现中国移民聚居区”,“至17世纪前期,东亚各贸易港及其周边地区,已形成大小不一的华人聚居区”,“到19世纪初,加里曼丹、马来半岛、缅北和越南北圻的金、银、铜、锡矿区,越南南圻、马来半岛、西爪哇和暹南内陆的垦殖区和种植园,都已形成大小不等的华人社区”,“迄20世纪初,华人……已广布亚洲、美洲、非洲和澳洲各地”,(庄国土,2011)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的范围又扩大到意大利、俄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
因为乡情维系的缘故,海外华人移民通常按地缘、族缘关系集结,自然形成了华人华语社区。游汝杰指出,海外现在有160多个传统的华语社区。(游汝杰,2016)在华语社区内,人们多使用汉语方言进行交流,而且方言的通行也具有相对的区域集中性,如新加坡牛车水、马来西亚吉隆坡通行客家话,马来西亚槟城、菲律宾马尼拉通行闽南话,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尼通行粤语等。这是早期移民多为闽、粤、客人而形成的华人社区的通行方言面貌。近三十年来,随着其他省份华人大量移民海外,也将其他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带到海外,改变了华人社区的传统语言结构,如意大利普拉托即通行温州方言,美国纽约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强势语言即为普通话。自明末清初开始的这一批移民潮,距今大多在400年以内。根据目前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接触深度与接触时间的不足,以及某些群体(如客家人)主观上对于原乡方言的保留意愿,这些迁徙至各地的方言还基本保留着原乡的核心特征,尚未融合发展成为新的方言,而是在不同落籍地语言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与原乡方言不同的诸多变体,即为同源异境汉语方言。
目前学界所关注的多为周振鹤、游汝杰先生提出的两种模式,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多体现为对新旧两种方言的“一一”对应比较。我们认为,结合近代及新时期汉民族移民活动的特点,在这两种模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模式,即本文所提出的“同源异境汉语方言”: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同时或于不同时期向不同地区迁徙,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影响下经过发展演化,成为不同的方言变体。这些变体根据分布的不同又可分为地域变体、地区变体乃至国际变体。在这种模式下,迁出方言既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与其他语言或方言接触,存在不同的演变方向与演变形式,同时,又存有不同迁徙时期的历史特征,时间层次相对复杂。这一研究对象恰好处于方言在外界语言环境影响下尚未被融合的状态,是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将同源方言与不同方言变体共同比较的“一对多”模式更适宜于这种区外流播的方言及其变体的研究,如此更可突显同源方言的本质特征及受到影响后的演变路径与演变机制。实际上,周振鹤、游汝杰也曾提及这一类移民方言情况:“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来远离故乡的地方的,如流布在海外的粤语和闽南话。这些远离故乡的方言久而久之会演变成新的地域方言。”(周振鹤、游汝杰,1995)这里所说的“地域方言”与本文所指的“同源异境汉语方言”实为同体。
李如龙提到一种特殊的演变,即同源方言相对静止,外来移民带给同源方言以不同的影响。如原本通行闽北方言的浦城,由于临近浙南的处州、衢州、婺州三处人群陆续进入浦城,使得县城以北的闽语蜕变为吴语;二是原本通行闽北方言的邵武府,由于江西人的进入而造成了那里的闽语发生了“赣语化”。(李如龙,2021)这种情况不属于本文所指“同源异境”的概念意涵。
三、 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概述
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目前仅有刘俐李最早进行了“同源异境”的比较实践,并结合焉耆话和东干语与关中话的研究实践对“同源异境”的内涵进行阐述:“‘同源’和‘异境’成为既血脉相连又脱胎自立的支柱。‘同源’是历史,是根,故三者面貌相似;‘异境’是现实,是异化的环境和条件,故三者异为三体。”(刘俐李,2003)具体研究体现为将原乡关中话及由关中迁徙到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东干语、新疆焉耆话进行共时比较,对三种方言百余年来发展、裂变和形成新方言的异同及规律进行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具体论证变异速度及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关中话、焉耆话和东干语恰好处于汉语环境“纯—杂—无”的三种阶梯状态,是三种典型的语言环境:焉耆话处于“多语言共处,以汉语、维吾尔语为主,多汉语方言相间,以焉耆话为主”的语言环境中,东干语则处于“多语言共处,以俄语为主”的现实语言环境中。东干语和焉耆话就是在各自复杂的语言环境下相较于同源方言关中话而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文章在语音系统的演变及词汇发展变化上均有所发现:语言接触下,语音系统中的声调是最容易受影响的部分;词汇方面最易丢失的是方言独有词,比较稳固的是分布范围广的共有词,即共有词是方言演变中比较稳固的词。(刘俐李,2003、2006、2009)
在此之后,继有陈秀琪、张屏生、钟荣富、陆露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语客家方言、闽南方言及其变体的演变问题,在刘俐李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拓宽了研究路径与研究视野。陈秀琪所探讨的闽台“诏安客家话”虽然都是处于纯汉语方言环境中,但由于接触环境的差异,同源方言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台湾云林二仑、仑背是闽南方言包围下的诏安客家话方言岛,语音与词汇都呈现‘闽南化’趋势,由于接触较为深入,在音系结构上亦已显示出闽南话语音系统的影响;台湾南兴的诏安客家话则与四县客家话相接触,音韵特征渐趋向于四县客家话。(陈秀琪,2006)张屏生对同安腔闽南话在中国福建、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三地的语音及词汇方面的差异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比较,呈现出台湾同安腔闽南话词汇受日语影响明显、新加坡同安腔闽南话词汇则受马来语影响较为深入的特点。(张屏生,2009)钟荣富发现新加坡客家话的语音系统在闽南方言环境中出现异化,词汇上却不仅受到周边粤方言、闽南方言的影响,也受到英语、马来语的影响:这表明了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受影响程度的不同。语音系统由于结构性相对较强,难以受外族语言影响,但词汇系统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易于被外来语言及外来方言影响。(钟荣富,2011)这是接触演变层级性的体现,即词汇系统的演变与语音系统的演变并不是同步的、平衡的。陆露则着眼于微观语音演变的考察及时间上的链性变化,通过空间差异还原出时间发展线索,利用相类环境背景但是深浅不同的语言接触程度,梳理出闽籍客家方言在台湾闽南方言不同程度影响下所发生变化的时间脉络。(陆露,2016、2018、2020)
陈晓锦虽然未强调以此种视角来分析问题,但书中的语料本身就是丰富的例证。《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共记录了东南亚29个汉语方言点,其中,闽南方言有6个点,潮州方言有7个点,客家方言有三个来源共7个点。这些多点分布的方言即为同源异境汉语方言,如同源广东河婆客家话,在文莱的变体中就夹杂了不少英语和马来语的借词,因而原来的语音系统中就多了一套只在借词中出现的韵母[][m],而印尼山口洋的河婆客家话变体却没有增生这两个韵母。(陈晓锦,2014)
以上研究主要专注于共时比较,马重奇、林清霞、曾晓渝等学者在历时比较研究上有所突破。马重奇、林清霞结合19世纪《厦英大辞典》这一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方言材料,分别对厦门、同安、金门三地具有源脉关系的闽南方言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的动态比较研究,对140年来同安闽南话在三地的横向及纵向发展进行了详细梳理。(马重奇、林清霞,2018)曾晓渝着眼于明代南京官话由于军屯移民而迁徙至天津、云南、贵州、海南等地之后的方言变体研究,具体体现为将田野调查与明清韵书韵图以及历史档案、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考察证实四地方言的共同来源是明代南直隶官话,再通过纵横比较,分析这四地方言里留下的明代官话的痕迹,在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发现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600多年来在南北不同环境中流变的共性与个性差异,从语言接触视角分析四地个性差异的原因并作出解释。(曾晓渝,2021)这是利用同源异境方言材料在汉语史领域进行接触演变研究的实例。以上研究从历时角度拓展了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空间与深度,使之更为立体化、更具比较意义与价值。
综上研究可见,同源异境汉语方言丰富、多样,可以进行规模化、范式化的系统比较。目前研究地域已跨越中国台湾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已涉及关中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北方方言等多种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结合汉民族移民迁徙的历史现实,将原乡方言与不同落籍地的方言变体进行综合比较,已在演变原因、演变速度、演变方向等方面对语言接触中的相关问题有所突破。但由于各位学者多为单独及个案研究,并未构建起学术理论框架,因而尚未形成规模化影响。
四、 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取向与路径
我们认为,综合同源异境语言研究、汉语方言研究的实践及同源异境汉语方言的具体分布情况,这一视角下的观察研究可主要在语言接触演变层面有所贡献。语言演变的触发因素主要有内部结构的影响及外在环境的影响两大类,可概括为自然演变与接触演变。但一直以来,由于两种演变在过程和结果方面基本相同,所以对于何者为具体的触发因素一直无法明确判断,即对于一个确定的演变结果来说,很难判断其为自然演变还是接触演变。同时,起变的时间与机制都是困扰语言学家们的难题,所以布龙菲尔德一度称“不可知”。(布龙菲尔德,1998)在这样的现实问题面前,同源异境视野下的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由于确立了比较对象的同源性,其所发生演变的结构性因素相对一致,即内部语言结构压力相对同质,从而得以集中考察由于接触带来的演变,并可通过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演变而探讨不同语言或方言对于汉语方言的影响机制。
同时,同源异境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由于可以考察到使用者的移民背景及当前的语言环境,从而比较明确地区分不同的接触源,以此更进一步观察语言接触与方言接触下的汉语方言演变的不同模式与机制。这对于相对模糊的语言接触和方言接触的区别问题,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分辨。一直以来,“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方言接触”(dialect in contact)这两个术语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并没有比较明晰的范围区划,学界对于这两个概念也并未做明确的区分,尤其是谈及方言接触时,大多以“语言接触”概称。但实际上,异质语言的接触及同质语言不同方言的接触对于汉语方言的影响是不同的。邢向东也明确指出:“由于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的差异,语言与方言之间互通度的差异及实际接触情况的差异,方言接触不能完全等同于语言接触。因此,我们要根据不同方言之间互相接触的实际情况,检验现有的语言接触理论,总结适用于汉语方言接触的规律,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方言接触的形式、类型、机制及引起的语言演变研究,方言接触对方言演变的触动作用的研究,尤其是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应是该领域接下来研究的重点。”(邢向东,2021)在语言接触研究领域,以Weinreich、Thomaso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机制、类型、规律等已有不少理论阐释;方言接触领域则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方言接触有与语言接触共同的部分,也有相异的部分,我们的研究要针对方言接触演变的现实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
综合同源异境汉语方言变体在不同环境下的“异变”“同变”“同貌”等不同表现,我们认为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汉语方言接触演变的研究取向与具体路径。这是对目前语言接触研究多着重在不同种族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一个有益补充,也是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观察窗口。
(一) 同源方言“异境异变”的影响机制
同源方言在不同语言环境影响下呈现不同的演变路径与演变方向,我们将这种状况简称为“异境异变”。这里所指“不同语言环境”既包括不同语言,也包括汉语的不同方言,如刘俐李、张屏生、钟荣富等学者的研究即涉及哈萨克语、马来语、日语等外族语言,马重奇、曾晓渝、陈秀琪、陆露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涉及闽南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等不同汉语方言。
Thomason曾明确提出源语和受语的类型距离是预测接触性演变的程度和种类的重要影响因子,并认为,两种语言(或方言)在结构类型上相似程度越高,有标记性特征和可并入程度低的特征发生迁移的可能性就越高,结构特征迁移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以方言之间的借贷为例,方言之间借贷甚至可以发生在屈折形态层面。(Thomason,2001)李如龙也曾指出方言借用与语言借用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借用常常通过文字翻译的途径,方言间的借用则主要是由口头接触造成的。两者都会涉及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三个层面,不过方言间的借用在语音上有可能形成借用的系统,例如方言的文读音系统,……方言间的借用在词汇上则有借用‘使用频率’的现象。”(李如龙,2006)
不同语言影响下,变化最迅速的层面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如同安腔闽南话在原乡福建同安保持着原有的词汇系统,但其新加坡方言变体中掺入了马来话,台湾方言变体中则掺入了日语。例如:同安闽南话中“鳄鱼”为[ɡk1h13],新加坡同安腔闽南话受马来语buaya的影响而称为[buai11a11](末仔),其他如“市场”读为[pa35sak3]、“高大”读为[pan33iaŋ33]、“猪”读为[ba33bi55]等分别为受马来语pasar、panjang、babi影响;台湾同安腔闽南话中,“油豆腐”读[a55ge3]、“空瓶”读为[a33khi55bin51]、“洗澡”读为[hu55l3]等则均为受日语的影响。(张屏生2008)这些受影响的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而且分别体现出新加坡与日本社会的相关文化特征,如“洗澡”在日本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词的高频使用因而促使其快速进入到闽南方言的词汇系统中。
汉语方言影响下,变化则会深入至语音系统,促发语音结构系统的演变。如台湾桃园杨梅的四县腔客家话在周边强势的海陆腔客家话的影响下,其语音系统中即增生了一套舌叶音声母,区别于典型的四县腔客家话;台湾太麻里诏安客家话在周边闽南方言的影响下,语音系统中增生了双唇浊塞音声母b-:这些是弱势方言受强势方言影响而产生的新变化,表现出语音演变中的类推作用。我们还发现,语音系统中,声母和韵母相对较为容易发生变化,目前所观察到的变化都在此范围内,声调则几乎没有变化。这也反映出语音系统结构内部演变的不平衡性,即声母、韵母容易受到影响,声调相对稳定。
(二) 同源方言“异境同变”的演变过程及层阶关系
同源方言在不同环境下呈现出相同的演变方向与演变路径,这种状况可以称为“异境同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域的语言环境相似,施加于源语的影响源其实属于同一种类型。如闽南方言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主要受马来语及英语的影响,台湾诏安腔客家话在云林仑背、台东太麻里、宜兰壮围等地均受周边闽南方言之影响。相同环境类型下,演变的方向与路径则基本一致。但是由于移民时间及接触程度的不同,弱势方言受周边语言或方言的影响程度亦各不相同,因而呈现出演变速度的不同。借由同源异境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呈现“异境同变”的演变过程及层阶关系。
张光宇认为汉语史研究存在局限,即由于过于重视文献材料,研究往往是跨越时间的一步到位的比较,而不是真正的演变过程。(张光宇,2019)苏金智曾针对香港的标准汉语受粤语及英语影响的现状而提出“语言连续体模式”这一认知模型,用以弥补谱系树模式与语言区域模式的缺陷,并认为其可以解释语言接触中出现的各种语言变体以及变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为各个变体找到演变链条上相应的位置。(苏金智,2014)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源“异境同变”方言正属于这种“语言连续体模式”在方言演变领域的具体体现。方言的差异是语言发展在空间上的表现,而空间和时间是一对有紧密联系的、相互依存的范畴,因而历史语言学可以在亲属语言或方言的空间差异中去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历程;利用同源异境各方言变体,可进行同源多点的链式比较研究,在空间的差异中累积时间演变的痕迹,从而纵向呈现语言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语音演变过程。
例如:台湾诏安腔客家话在周边闽南方言的影响下增生了b-声母,同时原语音系统中的v-声母逐渐消失。学界多认为这一演变过程是v-声母受闽南方言直接影响而变成了b-。但综合考察同源多点语料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演变过程不尽相同,这表明客家方言接受闽南方言中的b-声母并不是简单的直接使用,而是有其自身的扩散与发展过程。重新整理这些“连续体”可以逆推b-声母的起变源头及扩散过程:微母字最早开始演变,b-声母通过m-声母进入到语音系统,继而影响了与其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相近的声母v-,并进而进行了类化扩散,直至完全代替原先的v-声母。(陆露,2020)
陆露还透过异境同变的语音线索推断出大致的演变时间。如:诏安客家话山摄各韵在与来自中古的非组声母f、m相拼时,读为an(阳声韵)/at(入声韵),如“反”读为[fan51](福建诏安秀篆,以下简称“秀篆”)、[fan31](台湾云林仑背,以下简称“仑背”)、[fan31](台湾台东太麻里,以下简称“太麻里”),“发”读为[fat24](秀篆)、[fat24](仑背)、[fat24](太麻里),“袜”读为[mat24](秀篆)、[mat24](仑背)、[mat24](太麻里)等。在与来自中古船母的唇齿音f相拼时,韵母却表现出不同,读为ien:“船”[fien54](秀篆)[fien53](仑背)[fien53](太麻里)。借由闽台三地的共同读音,可以推断:(1)船母读为唇齿音f,应是比较晚近才发生的变化,因为韵母还保留着不同的分布状况;(2)发生变化的时间亦应在移民台湾之前,这些音作为特殊的指标音保留在移民至台湾的语音系统中,显示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种变化。(陆露,2016)
由于接触深度与时间的不同,同源方言在相似语言环境下的演变速度与程度会有所差异,体现出演变的层阶性:在语音演变过程中即表现为蕴含关系,在词汇演变中则体现为核心词、常用词受影响的程度等。
共时平面的类型学研究中经常发现具有蕴含关系的语言现象。实际上在汉语发展史中亦有蕴含关系的存在:即一个变化发生可以蕴含另一变化也已发生。因为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在同一个方向的演变上,变项只能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逐个发生演变。这种分布态势也表明制约环境的影响具有层级性特征。
何大安曾经探讨过同一种规律在不同方言中的受纳程度,并指出其不同变化可以反映出规律的阶层性:“不同的方言群,在将同一规律本土化的同时,会提供不同的结构上的诠释,从而反映出不同方言群的结构差异与调适幅度。从这个角度着眼,规律影响面的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规律在方言间的传播史。这一规律在各方言中所呈现的各种次规律,或次类型,可以整理出一系列的蕴含关系,或内在秩序。”(何大安,2004)同理,在同类环境、不同程度的接触背景下,规律的发展亦自有其次序。例如:客家方言随着与闽南方言接触深度的不同而在声母系统上有不同的反映:产生了b-声母的未必产生了ɡ-声母,但若产生了ɡ-声母则一定有b-声母。台湾云林仑背、二仑及台东太麻里的诏安腔客家话都在闽南方言的影响下产生了b-声母,但却还没有产生ɡ-声母;而与闽南方言接触程度更深的宜兰壮围诏安腔客家话中则产生了ɡ-声母,同时系统中亦有b-声母的存在。
词汇研究中,刘俐李已提出一种构想,即基于历史语言学通过核心词比较判断语言间亲疏关系的理论背景,利用已知同源关系的方言异域变体来逆推它们的差异度和相似度。如其将焉耆话、东干语的100个核心词分别与“母本语”关中话进行比较,算出三者的相似度均在80%以上,其中,焉耆话与关中话的相似度更高达85%,这恰与周边的环境密切相关。(刘俐李,2003)陈秀琪则发现方言持续接触下,词汇消长明显,首先会产生两方言融合的合璧词,下一个阶段则完全移借外来词汇,原来的词汇则随之消亡。(陈秀琪,2006)从合璧词到完全移借词,表现出接触程度对词汇演变速度的影响。
(三) 同源方言“异境同貌”的保留及其核心特征
不同语言环境下,同源方言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其语言系统内部亦有相对稳定的存在,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异境同貌”。“同貌”即是同源方言的内部核心特征,也可以视为是外在环境影响下的语言重构没有完成的标志。正因为“同貌”的保留,移民方言在新的环境下形成了方言变体,而不是与源语异质的其他语言。
在语音层面,其内部的语音格局及特殊语音都是相对静止的核心特征。萨丕尔已经认识到亲属语言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的语音格局”,这个“内在的语音格局”相对其他成分来说更稳固、更不易变化。(萨丕尔,1921)这是就语音系统的结构本身而言的,也就是说,构成语音系统的语音成分的数量以及相互关系在这个“内在的语音系统”中是相对固定的。如:诏安客家话入声音节部分舒化,-k尾脱落,整个音系呈现出阳声韵尾-m、-n、-ŋ与促声韵尾-p、-t相配的不平衡格局。这一演变路径与一般汉语方言入声韵尾由-p→-t→-k→-再至脱落的演变顺序有所不同。闽台多地同源诏安客家话的周边语言环境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在闽南方言影响下还是优势客家方言腔调的影响下,这一语音格局跨越空间,分布却高度一致,显示出内部特殊音韵结构的稳定性。
在没有改变的部分中,还有些成分是具有地方特点的一组或几组音韵特点,或个别特殊的语音演变。何大安将这些成分称之为“指标音”:“由于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的需要,一个社群会保持字和特别的音韵系统,以作为乡亲的辨认记号。”(何大安,2004)我们发现,有些个别的“一组或几组”音韵特点会比较顽固地保留,如:诏安客家话部分书、禅、船母读为唇齿音f-声母,部分明母字读为h-声母,少部分章母字读为k-声母;知组二等、三等有别;蟹摄开口二等皆韵在明母之后读为-i;阴平调多为低平调,阳去调多为中降调等。这些特殊的“指标音”在福建漳州原乡、台湾仑背、台东太麻里、宜兰壮围等落籍地都有比较稳定的存留。除了相对共时的静态特征,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环境影响下,也有一些共同的演变也许也是不同方言结构聚集到一定条件下所发生的必然变化。比如,以台湾诏安客家话为例,舌尖音声母在与前高元音拼合时,在仑背与太麻里两地都已经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颚化现象,如“进精母字”已经读为-声母,“青清母字”已经读为h-声母。(陈秀琪,2002;陆露,2016)相较而言,太麻里的颚化程度相对更高,这也显示出这一特征的演进在时间及地域上的差异。
语言接触过程中,词汇层面的变化虽然相对较快,甚至有些核心词也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是,李如龙认为各方言中都存在着“特征词”,即“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词汇上的区别特征,即一定批量的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方言词。”(李如龙,2000)这些方言特征词取决于不同的地域及其历史文化条件,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地域及历史文化特点越明显,方言特征词也越丰富。如,“嫲”在客家方言中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征词,其可以表示母的、小的、凹的等特征,如“猪嫲(母猪)”“虱嫲(虱子)”“笠嫲(斗笠)”等,我们考察到这一批词目前在闽南方言(台湾仑背诏安客家话)、马来语(马来西亚河婆客家话)、日语(台湾美浓梅县客家话)的影响下均未发生演变。潘悟云则是将词汇与语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语音特征词”的概念。他认为“方言中的有些词音韵特征很特殊……其中往往反映很深刻的发生学上的原因。”(潘悟云,2000)如,各地客家话中都有“窗聪同韵”现象,“摸”字都有[mia]的音读层次,这都是客家方言非常重要的区别性音韵特征,而且在目前流播至区外的客家方言中都保存完好。
如上文所析,在同源异境的比较研究视野下,关中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的相关研究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解决了一些方言接触演变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已经初步构建起一个研究模式:以上所分析的“异境异变”“异境同变”“异境同貌”等三个不同层面即可较为全面地呈现区外流播方言的演变状态。综合目前同源异境汉语方言语料的实际情况,在此视角下的比较研究还可以进行得更加深入、系统,如,可透过空间上的不同分布,考察各方言异域变体演变的时间路线,追踪不同阶段的变化特点,梳理语言演变的发展轨迹;同时更可观察方言演变发生的关键节点、考察在方言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语言机制,从而在此基础上更深入探讨语言的接触演变机制等问题。同时,还可以进行单个方言的系统比较,以外在环境所无法影响到的层面来确定各区方言的核心特征等。
我们也关注到,流播至原乡之外的方言亦可对迁入地的语言产生作用,如,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以讲马来语为主的国家,由于闽南人的大量迁入(据《世界侨情报告》统计,2020年印尼有2200余万华人,马来西亚有近700万华人,其中大部分为闽籍及粤籍华人),两国的语言文字都受到由华侨带来的闽南方言的影响。有人统计8种印尼语和马来语词典,发现其中有汉语借词511个,其中456个为闽南方言,占全部汉语借词的89.2%。菲律宾的他加禄语也同样受到闽南方言的影响。菲律宾大学语言学家马努厄尔在其《他加禄语》的汉语成分一书中,曾列出381个源自汉语(主要是闽南方言)的他加禄词汇。(《华侨华人概述》,2005)
五、 余论
“根据汉语自身特点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唐贤清,2012)中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从古至今的广泛性群体迁移造成了不同层级文化的跨区域流动,谭其骧在《中国移民史要》中甚至强调“是故中国民族史者,易言之,即以移民之史实,解释中华民族之演化者也”。(谭其骧,2021)语言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及中国人对于“乡音”的文化认知与重视,使中国人在移徙他地后还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母语方言:在国内表现为数量可观的方言岛的存在,在国外则表现为华人方言社区的形成等诸多形式。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是移民在语言上的留证,可与移民史互相印证,并可作为移民史的有益补充。
我们结合汉民族历史考察到,一般500年以上的接触多会造成方言的融合,产生新的方言。自明末清初开始的这一轮大规模迁徙,时间大多在300余年,因而各种方言尚处于演变过程之中,其与同源方言的一致性特征还仍然存在,故而语言接触下所形成的尚为各种方言的变体。这恰好是一个相对中观的视角,可以补上微观与宏观的视角的缺陷,丰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时间层次。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汉语方言传播及发展演变特点的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应当受到关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流播至海外的汉语方言由于使用范围及使用效益的限制,已经日渐萎缩。文字与方言脱节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海外会说汉语方言的多为不认识汉字的老辈,汉语方言因而缺乏相应的书面语及书面文献,这让它们更加难以延续(陈晓锦,2014)。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结构的变化,普通话“有进一步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的共同语的倾向”(游汝杰,2016)。这些现实状况不容乐观,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工作迫在眉睫;在同源异境视野下,对海外汉语方言及其变体进行比较研究也成为亟待推进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