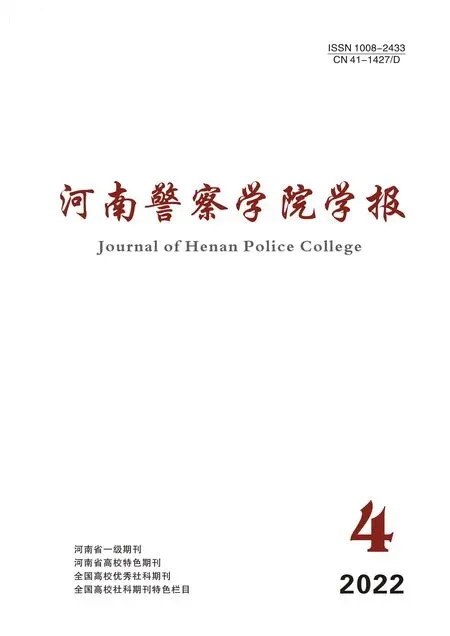生物社会因素对犯罪断念的影响(上)
2023-01-04丹尼尔博伊斯沃特牛智辉
丹尼尔·博伊斯沃特(著),牛智辉(译)
一、犯罪断念的遗传学基础
犯罪学植根于社会学,历来较少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释犯罪的开始、延续和断念。然而,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的进步使研究人员能够使用复杂的技术和统计方法来证明遗传和生物因素影响了近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包括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一)生物社会学视角下的犯罪断念过程
大约15年前,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P.赖特(John P. Wright)写道:“在过去10年里,生物科学在解释犯罪方面取得的进展比社会科学在过去50年里取得的进展还要大。”(1)Robinson, M. B. (2004). Why crime? An integrated systems theor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这句话——也许有所夸大——在今天引起了共鸣,因为我们仍未看到系统地将生物社会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由于过分关注环境和心理因素而忽视了已知的能够影响人的行为的生物和遗传因素,刑事司法系统的矫正工作就没能从这其中获益。倘若刑事司法真正“以证据为基础”,那就应当充分整合各学科知识及专长,共同努力,以实现理解和促进犯罪断念这一目标。
几十年来,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犯罪断念问题,但对于如何最优地将犯罪断念概念化和操作化仍存在争论。一方面,犯罪断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它发生在个体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以这种方式看待犯罪断念时,研究人员所衡量的是犯罪行为是否消失或停止,但对衡量个体犯罪断念所需的时间,犯罪学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然而,一旦犯罪断念完成,该事件就被认为是“静态的”或永久的(2)Maruna, S. (2001).Making good: How ex-convicts reform and rebuild their liv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将犯罪断念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3)Bushway, S. D., Tornberry, T. P., & Krohn, M. D. (2003). Desistance as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A comparison of static and dynamic approache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9(2), 129—153.。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行为的增量变化和相关特征的改变是“动态”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静态的事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测量犯罪行为的减少以及相关风险和保护性因素的改善来把握这一过程。总的来说,这两种关于犯罪断念的立场都对“如何更好地推进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影响。
生物社会学的观点非常适合研究犯罪断念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发生,也可以通过矫正措施来激励其发生。对于实施“激励犯罪断念”计划的从业者和继续研究犯罪断念问题的研究人员来说,这种“发展过程”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研究人员在研究犯罪断念问题时就应考虑在个体不同发展时期——即青年期、青春期或成年期——可能出现的干扰他们正常生活的事件的影响。
同样地,业内人士可能想摆脱(或改善)传统的矫正办法,转而采用一种矫正干预的优化方法。该方法专注于矫正矫治对象,并在关键领域进行基数测量(4)这些指标可能包括与刑事司法有关和与非刑事司法有关的结果。,传统矫正的目的只是纠正某些行为。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解决或持续改进某些特定缺陷的优势;传统矫正旨在实现行为的持久或永久改变,通常以“是”或“否”的方式来衡量行为的存在与否(例如再犯)。同样,如果我们将犯罪断念视为大多数犯罪人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超越“是”或“否”问题的优化方法就是下一步理解犯罪断念的关键举措。在实践中,可以使用与刑事司法和非刑事司法相关的结果来衡量这些优化方法,以便测量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犯罪断念变化。
(二)当前对于犯罪断念的理解
一些研究者认为,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持续犯罪的人,都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停止犯罪(5)Hirschi, T., & Gottfredson, M. (1983). Ag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3), 552—584.。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学者们提出了已为人们熟知的年龄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即“年龄—犯罪曲线”。通过该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犯罪行为在青春期达到顶峰,成年后逐渐减少。
对此,学者们大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这段时间里“年龄增长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犯罪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社会学解释包括:经历日常生活事件,如找到稳定的工作或结婚(6)Laub, J. H., & Sampson, R. J. (2001). Understanding desistance from crime. Crime and Justice, 28, 1—69.;承担公民责任,如投票和缴税(7)Uggen, C., & Manza, J. (2004). Voting and subsequent crime and arrest: Evidence from a community sample. 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36, 193—215.;拥有积极的公民价值观(8)Farrall, S., and Calverley, A. (2006). Understanding desistance from crime: Teoretical directions in rehabilitation and resettlement.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等等。
心理学的解释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人格特征在犯罪断念过程中的作用上,例如,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人格特征——被称为 “五大人格特征”(神经质、合意性、自觉性、对新体验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成熟。而其他特征,如寻求刺激和冲动,往往进入成年期就下降了。心理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个体可以随着社会心理成熟的过程渐渐摆脱犯罪。这也意味着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社会心理成熟度要素的变化——即节制(如冲动控制)、利弊权衡(如关心他人、关注未来)和责任感(如抵制同龄人的影响)——导致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变化。
罗克(Rocque)和威尔士(Welsh)近来为更好地解释犯罪断念过程而整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具体来说,他们的观点综合了五个能够影响犯罪断念的成熟领域,即公民成熟、社会心理成熟、社会角色成熟、认知转变/身份成熟和神经认知成熟(9)Rocque, M., & Welsh, B. C. (2015). Ofender rehabilitation from a maturation perspective. In M. DeLisi & M. Vaughn (eds.). Handbook of biosocial crimi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这表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因果机制可能与生理上、发育上的变化共同发生作用。
斯坦伯格(Steinberg)在2008年提出通过双系统模型来理解年龄—犯罪曲线,该模型将青春期内两个神经生物系统——认知控制系统和社会情感系统——的发育与危险行为的增多相关联。具体而言,双系统模型认为,在青春期观察到的犯罪和危险行为的峰值是个体社会情绪系统的高度反应和其认知尚未成熟的结果。这也说明个体如果拥有不成熟的认知控制系统(如发育不全的前额叶皮质),那么寻求刺激的社会情绪系统的反应就会随之增强。事实上,个体的生物学,特别是与大脑相关的发育状况,可能会影响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越轨行为变化。
(三)大脑发育对犯罪断念的干预
关于大脑发育和成熟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从青春期到成年的犯罪断念模式。从生长的角度来看,犯罪断念可以被认为是神经运动过程的一部分,主要受大脑结构和功能、激素的产生以及神经递质的水平的影响。这些生物变化发生在青少年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
例如,睾丸素水平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同的。第一次峰值出现在男性个体在母体孕育的中期,这次激增使男性的大脑为第二次激增做好准备。第二次激增则发生在青春期。在18至19岁左右,男性和女性的睾丸素水平都达到顶峰,然后在整个成年期的剩余时间里稳步下降。具体而言,男性的睾丸素水平在30岁以后开始下降,每年下降约1%,女性则在更年期开始经历睾丸素水平的下降(10)Sternbach, H. (1998). Age-associated testosterone decline in men: Clinical issues for psychiat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5(10), 1310—1318.。
睾丸素水平通常与攻击性、支配社会地位的相关行为以及减少恐惧感的程度有关。相关文献为睾丸素、社会环境(如虐待、同龄人、社会经济地位)和遗传或生物条件(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5-羟色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大量支持。综上所述,青春期睾丸素水平的提高可能有助于解释青少年早期犯罪行为的发生。然而,睾丸素的分泌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与年龄—犯罪曲线所显示的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犯罪活动的减少没有明显关联。相反,环境和遗传条件可能会减弱睾丸素对犯罪行为与犯罪断念过程的影响。
从青春期到成年,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水平随年龄而产生的变化也会影响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例如,研究表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在成年初期就开始减少(11)Rogers, J., & Bloom, F. E. (1985). Neurotransmitter metabolism and function in the aging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 E. Finch & E. L. Schneider (eds.). Handbook of the biology of aging, 2nd editi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这些神经递质具有兴奋属性并与各种形式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有关。青年期和中年期之间发生的与年龄相关的多巴胺系统功能下降有助于解释随着年龄增长犯罪活动随之减少的现象。许多研究还表明,5-羟色胺的平均水平在青少年末期到成年早期往往会增加(12)Collins, R. E. (2004). Onset and desistance in criminal careers: Neurobiology and the age-crim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Ofender Rehabilitation, 39(3), 1—19.。5-羟色胺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可以调节情绪和情感。同时,5-羟色胺的平均水平较低与情绪失调有关,而情绪失调也是引起反社会行为及其他犯罪行为的因素之一(13)Moore, T. M., Scarpa, A., & Raine, A. (2002). A meta-analysis of serotonin metabolite 5-HIAA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Of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ggression, 28(4), 299—316.。
5-羟色胺的代谢物,即5-羟吲哚乙酸(5-HIAA),可能是研究最多的神经化学物质,因为它与反社会行为有关。摩尔(Moore)、斯卡帕(Scarpa)以及雷恩(Raine)在2002年做的一项元分析表明,5-HIAA在反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水平明显低于非反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水平。关键在于,在这种关系中唯一被发现的调节因素是年龄,即年龄小于30岁的反社会群体相比于年龄较大的群体表现出更大的负效应。这种年龄效应应该能够进一步解释与年龄相关的成年人犯罪率的下降。
神经发育研究也表明,人类的大脑平均需要大约25年才能达到完全成熟。大脑完全发育的最后一个区域是前额叶皮层,它负责大脑的执行功能,包括冲动控制、注意力(集中)、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作为正常发育过程的一部分,执行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正如年龄—犯罪曲线所显示的那样,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成熟”,不再参与反社会和犯罪活动。然而,许多研究发现,执行功能的缺陷与一系列的行为问题有关,包括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14)Steinberg, L. (2008). 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adolescent risk-tak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28(1), 78—106.。例如,奥格尔维(Ogilvie)及其同事在2011年对126项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证明执行功能障碍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呈显著且强大的关系。研究还表明,执行功能障碍与再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这意味着执行功能的缺陷也可能干扰犯罪断念过程(15)Hancock, M., Tapscott, J. L., & Hoaken, P. N. (2010). Role of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predicting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violence. Aggressive Behavior, 36(5), 338—349.。
如前所述,执行功能与个体神经系统发育阶段有着紧密联系,大多数青少年遵循正常发育路径,其中涉及许多从青春期到成年的生理变化,导致在没有太多(如果存在的话)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过渡到犯罪断念。然而,那些神经生物系统功能失调的青少年可能无法成功过渡,无论这种失调是从出生起就具有的,还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由于不利的环境或危险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
如此看来,那些持续犯罪的人和暴力犯罪人很可能没有遵循正常发育路径,而他们的犯罪断念可能需要生物社会学手段的干预。由于关系到犯罪断念过程,对于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来说,了解个体的生物社会心理以便区分“少年限制型”和“生命历程持续型”犯罪者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风险水平和需求可能会有很大区别。
二、少年限制型和生命历程型个体的差异
心理学将青春期定义为一个以成熟过程为标志的时间段,从发育期开始,到成年早期的某个时刻结束(16)Sisk, C. L., & Foster, D. L. (2004). Te neural basis of puberty and adolescence. Nature Neuroscience, 7(10), 1040—1047.。青年和成年之间的这一过渡期充满了生物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个体行为,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反社会的行为和犯罪的行为。
1993年,特里耶·莫菲特(Terrie Moffitt)在犯罪学文献中提出了关于犯罪和越轨行为的最具生物学依据的理论。在该理论中,她提出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犯罪者:少年限制型和生命历程型。具体而言,莫菲特将那些在青少年时期主要以非暴力方式犯罪的人归为一类,并将其称为“少年限制型”。这些人的犯罪时间相对较短,一旦成年就停止了。另一方面,那些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持续犯罪的人,在生命历程的早期就开始出现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并在成年后继续沿着这一轨迹发展。
尽管“生命历程”一词似乎意味着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会有犯罪行为,但这是极为少见的情况,因为大多数人最终会在死亡之前停止犯罪。有观点认为,莫菲特提出的“犯罪二分法”可能过度简化了反社会和犯罪轨迹的实际变化,因为社会个体很难被简单地归入两个类别中的一个。然而,她的理论主张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即那些犯罪率低且较早停止犯罪的人和那些犯罪率高且较晚停止犯罪的人的内部和他们之间确实分别存在着相同和不同之处。
重要的是,莫菲特区分这两组的基本机制是基于生物学理论的。对于那些少年限制型的犯罪者,莫菲特提出了“成熟度差距”——她承认青少年在生物学上是成熟的,但社会还未赋予他们成年人的角色和责任。为了发挥自身独立性,青少年可能会实施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有时也会模仿他们身边同龄人的行为。这些少年限制型个体只在青少年时期实施非暴力形式的犯罪行为,在有机会获得成熟地位(如毕业、就业、结婚)时就会停止犯罪。莫菲特的研究表明,在年龄—犯罪曲线中看到的犯罪峰值是由少年限制型个体所驱动的。
关于大脑发育的研究结果也支持少年限制型犯罪的认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的执行功能会加强,神经递质的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青少年很可能通过发育成熟来“脱离”犯罪与违法行为,几乎不需要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式干预。同样,青春期也与拥有稳定就业、婚姻和承担公民责任的人生阶段大致吻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全职工作和家庭责任限制了参与犯罪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犯罪断念。如此看来,对于这部分少年限制型个体,从业者应该通过强化神经心理功能和执行功能来促进大脑的成熟,并尽量减少可能产生或加剧风险的情况。
另一方面,生命历程型的个体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在所有男性中占5%到10%(17)Moftt, T. E. (1993).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4), 674—701.(原文如此)。根据莫菲特1993年的研究结果,这种类型的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从事各种反社会行为,从很早就开始,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由于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相对稳定,莫菲特将重点放在了生命历程早期的生物和社会因素上,以解释这种犯罪模式。她特别指出,如果一个孩子有神经心理缺陷,而他的父母又没有能力帮助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更有可能走上生命历程型犯罪的道路。这种解释也与大脑发育研究相一致,因为许多研究表明,并非每个个体都遵循正常的大脑发育路径。正如莫菲特所指出的那样,个体间神经心理功能的差异在生命历程早期就可以被发现。这可能是遗传或产前环境条件对个体未来发育所产生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神经疾病,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是预测生命历程型犯罪的重要因素(18)Young, S. (2007). Forensic aspects of ADHD. In M. Fitzgerald, M. Bellgrove, & M. Gill (eds.). Handbook of attention def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pp. 91—108).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多动症患者往往有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等行为表现。大多数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轻,但大约90%的被诊断为ADHD的人在成年后仍表现出此类症状(19)Willoughby, M. (2003).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ADHD symptomolog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review with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3, 609—621.。患有多动症的人还会伴随其他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包括行为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犯罪行为等。
多动症的神经学解释主要集中在神经心理缺陷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不足,如脑电图研究就显示多动症儿童的脑波活动缓慢(20)Loo, S. K., & Barkley, R. A. (2005). Clinical utility of EEG in attention def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pplied Neuropsychology, 12(2), 64—76.。患有多动症的人更有可能感到无聊,并通过冒险和犯罪行为寻求刺激和兴奋。大脑处于低唤醒程度进而寻求刺激,再加上大脑不成熟,就容易导致抑制力减弱和兴奋性增强。这也可能是持续暴力犯罪的关键风险因素。
三、环境因素对犯罪断念的影响
尽管神经心理缺陷可能来自于遗传风险或产前环境,但它们也可能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由于不良环境或危险的生活方式而获得的。以下各种环境因素都可能导致神经心理缺陷的发生,包括:药物滥用;创伤性脑损伤;不良的童年经历(伤害、虐待和漠视);贫穷的环境(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环境污染,包括但不限于铅、石棉污染和水污染)。当这些环境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破坏了大脑的发育,认知和行为功能就会发生巨大改变,并导致反社会行为和长期犯罪。这些后天导致的神经心理缺陷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没有先天性神经心理缺陷的青少年在成年后继续参与犯罪活动,而并未遵循少年限制型犯罪者的途径,即在成年早期就停止犯罪。因此,了解后天的神经心理缺陷对犯罪断念过程的影响是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尽管许多环境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大脑功能,但本文重点讨论三种特定情况:药物滥用、创伤性脑损伤和贫穷的环境。
(一)药物滥用
长期以来,药物滥用一直被认为是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根据美国国家药物成瘾及滥用研究中心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州和联邦矫正机构中,约有65%的矫正人员符合药物使用障碍的标准。美国日益严重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已经进一步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内的问题。越来越多已经在司法系统中的涉案人员正在使用处方止痛药、海洛因和合成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这使他们的再犯风险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心理缺陷和药物使用之间存在联系。也就是说,有神经心理缺陷的人更有可能使用药物,而使用药物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加剧神经心理缺陷。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神经心理缺陷的恶化与各种毒品的滥用有关,包括酒精、大麻、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阿片类药物。这一点对青少年尤其重要,因为此时他们的大脑正处于发育关键期,滥用药物有可能使他们面临长期认知延迟和认知缺陷的风险,并抑制社会心理成熟度的增长。研究表明,有阿片类药物依赖的人更有可能在神经影像学研究中表现出大脑结构异常,那些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的额叶白质和灰质明显减少(21)Wollman, S. C., Alhassoon, O. M., Hall, M. G., Stern, M. J., Connors, E. J., Kimmel, C. L., Allen, K. E., Stephan, R. A., & Radua, J. (2017).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in opioid-dependent patients: A neuroimaging meta-analysis. Te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43(5), 505—517.。这类反常现象可能有助于解释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所表现的神经心理缺陷,即在控制、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注意力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执行功能障碍。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经历过长期药物滥用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事实上,药物滥用被列为“五大犯罪条件”之一,矫正计划应以这些条件为目标,以促进参与者脱离药物成瘾(22)Andrews, D. A., Bonta, J., & Wormith, J. S. (2006). Te recent past and near future of risk and/or need assessment. Crime & Delinquency, 52(1), 7—27.。然而,通常的方法(如匿名酗酒者协会和匿名戒毒者协会)并没有解决与药物滥用相关的犯罪行为的神经心理缺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在戒断药物后依旧有可能提高(23)Forsberg, L. K., & Goldman, M. S. (1987). Experience-dependent recovery of cognitive defcits in alcoholics: Extended transfer of train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6(4), 345.。然而,认知恢复的速度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认知能力可能会自动改善或在药物戒断后的短时间内改善,但也有人可能需要通过认知矫正来恢复认知能力(24)Forsberg, L. K., & Goldman, M. S. (1987). Experience-dependent recovery of cognitive defcits in alcoholics: Extended transfer of train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6(4), 345.。
因此,长期使用药物会对个体的大脑功能产生有害影响。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在药物戒断之后仍会有影响,从而使他们具有继续犯罪的风险,进而成为康复矫正的潜在障碍。另外,也有研究表明,有神经心理缺陷的人不太可能在药物滥用治疗项目中取得成功。通过总结回顾15项考察犯罪和吸毒者的犯罪断念过程的研究,我们了解了亚群体复杂的犯罪断念过程。具体来说,各种个体因素(如认知过程、个体能动性)、结构因素(如矫治、就业)和社会因素(如与家庭和同伴的关系)都会影响犯罪和吸毒者的犯罪断念过程。为了促进犯罪断念,从业者必须首先解决滥用药物的问题和犯罪断念的各种障碍,然后采取协调一致的改进措施以改善认知功能和行为。如前所述,这可能对青少年来说更为关键,因为药物滥用可能会干扰他们大脑的正常发育,如果不加以解决,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二)创伤性脑损伤
将被监禁群体的创伤性脑损伤可能性进行综合分析并与普通人群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被监禁者样本报告有脑损伤史。这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中的对应数值(2%至38.50%)(25)Farrer, T. J., & Hedges, D. W. (2011). Prevalence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incarcerated groups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meta-analysi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35(2), 390—394.。头部受伤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互的,即犯罪的人更有可能在儿童时期受到虐待,或者在青少年及成人时期遭到攻击,并由此造成了头部创伤。同时,头部受伤也会影响认知功能和行为,导致个体继续实施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增加再次受害的概率。尽管头部受伤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相互的,但纵向研究表明,经历头部受伤是之后开始参与犯罪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也可能干扰犯罪断念过程。
这种类型的神经心理缺陷可能会扰乱个体的大脑发育或功能,从而影响到犯罪断念过程。事实上,经历过严重头部创伤的人更有可能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大脑区域表现出神经心理功能障碍,特别是执行功能的障碍,如冲动控制、注意力、工作记忆和认知的灵活性。如果因头部创伤造成的神经心理障碍没有得到解决,就会对认知和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因此,经历创伤性脑损伤不仅使个体处于反社会行为的高风险中,而且有可能成为刑事司法系统进行任何康复矫正的障碍。由于大脑功能和结构在人的成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且健康的大脑发育受到干扰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更好地了解创伤性脑损伤(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如何影响犯罪断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业者应主动去发掘当事人以前是否由于以下原因遭受过任何脑损伤:外伤、虐待、运动、事故或跌倒。虽然去医院获取正规的医疗诊断记录是可行的,但很多遭受脑损伤的人会因为一些情况(如高额费用、虐待以及没有意识到严重性)而不去寻求治疗。因此,从业者可以使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来获取这些生活中出现的事件,如提出关于头颈部受伤时是否失去知觉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体症状(如恶心、失忆),这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多关于头部受伤严重程度的信息。此外,就这些内容对其父母、伙伴或其他相关人士进行询问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因为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头部创伤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
(三)监禁条件
某些环境条件也会抑制大脑的正常发育,造成认知和神经系统的缺陷,从而加剧犯罪风险(26)Meijers, J., Harte, J. M., Jonker, F. A., & Meynen, G. (2015). Prison brain?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prison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43.。有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过度拥挤和嘈杂以及大量毒素(如铅)会对个体的大脑和应激系统功能产生负面影响(27)Baskin-Sommers, A. R., & Fonteneau, K. (2016). Correctional change through neuroscience. Fordham Law Review, 85, 423—436.。由于有限的社会交往、对受害的恐惧、实际受害、饮食不良、缺乏运动、睡眠质量差以及隔离或单独监禁(对部分人而言)等因素,贫困环境的特征可以延伸至矫治环境中。这些条件都是损害青少年认知发育和功能以及妨碍社会心理成熟的风险因素,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中会产生更有害的影响。
巴斯金-萨默斯(Baskin-Sommers)和丰特诺(Fonteneau)在2016年确定了三种监禁的结构性因素,这三种因素都可能会加剧或造成神经心理缺陷:一是过度拥挤或被迫紧挨着他人,二是持续噪音,三是监狱环境中的有害元素(如铅、石棉)。其他研究还发现,这些环境因素也能够影响神经机制的压力处理功能,导致压力激素失调,而这又与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相关。然而,这些监禁条件往往也能折射出个体原来生活的社区的环境。因此,监禁手段有可能因个体先前的邻里和家庭环境条件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理解监禁对认知功能(如情绪调节和识别)和应激系统反应的负面效果至关重要(28)Umbach, R., Raine, A., & Leonard, N. R. (2018). Cognitive decline as a result of incarceration and the efects of a CBT/MT intervention: A cluster-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5(1), 31—55.,州和联邦矫正机构应尽量减少干扰神经心理健康和应激系统功能的客观条件。研究还应当考察服刑时间长短与神经生物功能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矫正系统不解决这些因素,服刑时间最长的人在释放后可能会面临最大的神经系统危机。
关于监禁如何影响认知功能的研究,可以帮助刑事司法系统了解处置犯罪者的方式,特别是对青少年和刚成年的人。正如丽拉·卡泽米安(Lila Kazemian)在2021年所建议的,现在是时候考虑为18至24岁之间的人提供成人刑事司法系统的替代方案了。具体而言,就是以大脑发育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广泛应用青少年法庭的做法,并参考了矫正康复的相关理论,根据个体的风险程度来接受适当的制裁和治疗,以增加他们犯罪断念的可能性(29)Andrews, D. A., Zinger, I., Hoge, R. D., Bonta, J., Gendreau, P., & Cullen, F. T. (1990). Does correctional treatment work? A clinically relevant and psychologically informed meta-analysis.Criminology,28(3), 369—404.。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的、正在经历正常发育的刚成年的人,是典型的低风险个体,因此应该接受最少的干预措施。事实上,研究表明,将低风险的人置于高强度的环境和项目中,可能比什么都不做产生的消极影响还要大(30)Lowenkamp, C. T., & Latessa, E. J. (2004). Understanding the risk principle: How and why correctional interventions can harm low risk cases. In Topic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nual issue 2004: Assessment issues for managers (pp. 3—8).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过往的大脑发育研究表明,对大脑正在正常发育的低风险个体实施监禁,可能会损害其认知功能和应激系统反应,并抑制或延迟大脑发育和社会心理的成熟(31)Baskin-Sommers, A. R., & Fonteneau, K. (2016). Correctional change through neuroscience. Fordham Law Review, 85, 423—436.。因此,对于那些低风险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刚成年的人,监禁应该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使用。另一方面,对于必须被监禁的高风险个体,矫正系统应通过减少与贫困环境有关的风险因素,减轻监禁对认知功能的负面影响,其措施可以包括:改善饮食;增加每天的运动量和睡眠时间;通过探视鼓励被监禁者与亲密的人进行交流;减少隔离和单独监禁;减少监狱中的噪音污染、毒素含量以及拥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