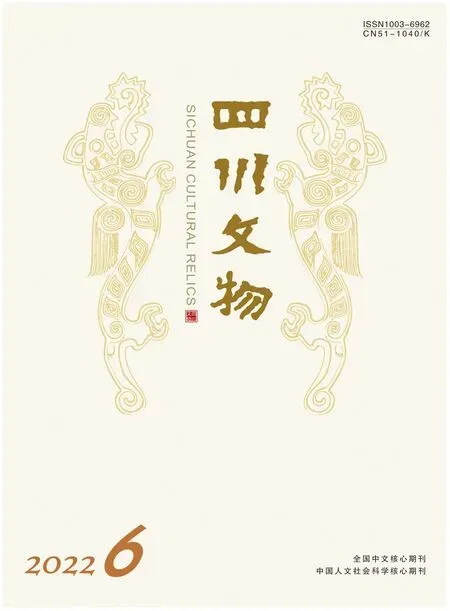前蜀永陵出土随葬品文化因素分析
2023-01-03成都永陵博物馆
韩 莎(成都永陵博物馆)
成都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发掘于20世纪40年代,发掘工作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先后由冯汉骥、吴金鼎两位著名考古学家主持并圆满完成,在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永陵的研究,以冯汉骥1964年撰写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以下简称《报告》)为最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后来有学者相继对永陵的陵墓建筑、石刻等作了进一步探讨[2],而关于随葬品的研究,大多是延续《报告》。近年来,学界对出土随葬品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相关墓葬的不断发掘,为进一步认识永陵随葬品提供了契机。本文在现阶段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通过梳理永陵随葬品的出土情况,结合同时期墓葬与历史文献材料,对永陵出土随葬品所反映的墓葬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一 永陵出土随葬品基本概况
永陵曾遭盗掘,墓内随葬品多被盗扰或破坏。根据《报告》,结合民国档案中陈策能整理的《琴台整理工作团发现古物表》[3](以下简称《古物表》)(图一),现将永陵地宫随葬品出土情况整理如下。

图一 《琴台整理工作团发现古物表》复印件
永陵呈正南北向,为长方形券拱前中后三室墓。前室无随葬品出土。中室东南角、西南角地面各发现1四耳罐;中部稍偏北设置棺床,棺床中部略偏西出土十字形铁顶架。据《古物表》描述,棺床中部发现1方形铜版,铜版东面发现银罐(钵),银罐(钵)内盛放7方玉銙和银猪,铊尾发现于银罐(钵)下[4]。结合《报告》图版可知,铜镜出土时旁边明显有玉大带银扣(图二),推断此铜版即铜镜无疑。银盒出土时与玉大带、银扣、银钵等同在一处,银头杖、银扣饰于银钵口部附近发现,银搔手在棺中呈南北向放置于银碗旁,棺东北端发现水晶珠。另外棺内还见小铁刀、银刀鞘、银颐托、琥珀、小玉片,其相对位置不明。依据莫宗江绘制的王建墓玄堂平面图,紧靠棺床南端床脚东、西两侧的第一、二力士间有一对铁猪与铁牛[5]。棺床北端16厘米处的石缸内发现陶盆和灯台各1件,石缸脚底东侧也出土1灯台,棺床西北靠近券墙处见1六耳罐,棺床西部发现2件陶碗,并有长漆皮痕迹。
王建石像端坐后室石床上,像前约20厘米处放置宝盝,盝内谥宝前方靠右处发现银带扣2件,带扣后依次有银套环、带头玉饰各2件,附近还发现2件小银管。谥宝前稍偏东处发现1件玉环,偏西处有鳞纹玉饰2件。石床前端放2副玉册匣,其上发现铜炉。册匣与谥宝之间发现提梁盏1件。另外还有鎏金小铜片、残铁器,用途不明。在石床前稍偏东位置发现金银胎漆碟,后室门后东面第一券与第二券缺口中发现3套银扣、银套环与玉饰头(图三)。
二 永陵出土随葬品文化因素分析
(一)大唐遗风——帝王礼制类随葬品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均不同程度地延续唐制,永陵后室石床上的玉册、谥宝便是最好的证明。
永陵玉册分两册匣盛放。一副为哀册,共51简,左右两端各有一折褾,其上分别绘金甲神与金龙,文皆深刻敷金(图四)。一副为谥册,共50简,册首有两折褾,册尾一折褾,彩绘贴金图像已不可辨。

图四 永陵出土哀册1~14 简
从保存较为完整的哀册来看,它与唐代帝陵哀册在外形规制和册文结构上均表现一致。首先,在外形规制上,系大理石材质,文字填金,玉册装于匣。玉简长33、宽3.5、厚1.9厘米。虽然较唐代玉册尺寸稍大,但确如冯汉骥在《报告》中所说,永陵玉册长宽比例为10.6%,与唐代玉册十比一的长宽比“相差不过半单位稍强,故可尤谓之唐制之旧”。其次,从册文结构来看,哀册序文以“惟光天元年夏六月壬寅朔,大行皇帝登遐,粤十一月三日,神驾迁座于永陵,礼也”“爰诏宰辅”引出哀文;哀文则以四言先美誉王建身世为王子晋,后述说王建“八海为家,万方作镇”,而后“金承土运,开国于坤”,政治上“去华务实,极思研精”“始因勤倦,寒暑过侵,方药无验,灵威坐沉”,最后四六言则表达哀思之情。而同时期的南汉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外形做碑形,哀册文开头书撰书人信息[6],与唐制不同;南唐钦陵每简长16、宽7厘米,两简拼合为一长简,每简书三行,顺陵用石灰岩制作,文字无填金,内容破坏严重,《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称二陵玉册谥文、哀文合而为一[7],这些均较唐代玉册制度相去甚远。通过对比,发现前蜀永陵玉册更遵循唐代的玉册制度,且文字中叙王建“大功于唐室”“金承土运,开国于坤”,终得“爰正三纲,渐成一统”,可见始终以承继唐运为己任。
永陵谥宝,印座长11.7、宽10.7、厚3.4厘米,钮高7.7、直径4.2、厚3.9厘米。印座四方分别刻青龙、白虎、朱雀与玄武(图五)。宝座下篆体阴刻“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谥宝钮部为兔头龙身,这与文献中“丁卯即位,左右献兔子上金床之谶。帝命饰金为坐,诏蜀人以金徳王,用承唐运”[8]的记载相符。

图五 永陵出土谥宝
将皇家印玺称宝、掌管皇家印玺符节的官员称符宝郎始于唐代,“长寿三年,改为符宝郎。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复为符宝郎”[9]。将刻有帝王谥号的印玺称谥宝亦始于唐代,且不晚于中唐,墓中随葬谥册、谥宝并用之制已经定型[10]。在《通典》中专门记载了谥宝在陵仪中需“礼官一人引符宝郎一人,主宝二人,以赤黄褥案进取谥宝”,“礼部侍郎奉宝绶案”[11],可知宝绶同案放置。在《蜀梼杌》中有“既而宗弼拥兵还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诸子,迁于天启宫,收其玺绶金宝”[12]的记载,可见印绶同用亦为前蜀帝王规制。
这种印绶组合早在汉代就已形成。汉代通过印章的材质和绶带的稀疏、长短以及色彩的不同,配套悬挂于腰间以标识官阶。随着印章尺寸愈来愈大,随身携带不便,印绶同用便仅是效法古礼,而不再具有实际佩戴的功能。到北周时期,“其组绶,皇帝以苍、青、朱、黄、白、玄、、红、紫、緅、碧、绿,十有二色。……其玺印之绶,亦如之。”[13]可知腰间组绶与玺印组绶已分离,但形制相同。隋代,“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14],可见组绶中有双大绶、小双绶之分。唐代亦然。《宋史》中对于皇帝之玺印及绶的形制则有明确记载,“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玉环”[15]。虽用织锦绶代替编织绶,但仍遵循大绶、小绶之制。由此推断,唐五代时期的玺印之绶也应同于佩戴组绶,有大绶和小绶之分,并由玉环连接。
据《报告》所述,组绶饰品分别有银带扣、银套环和玉饰头各2件(图六∶2)、小银管2根(图六∶1)、玉环1枚(图六∶5、6)。从汉代以来形成的印绶组合来看,组绶需垂附于革带,且唐宋文献记载,帝王冕服中也多革带、大带、双绶等并举,可知组绶饰品不可能有活动扣舌的带扣,故此推断这两组银带扣、银套环、玉饰头并非组绶饰物,而为革带构件。另还见2件五节鳞纹可弯曲玉饰(图六∶4),它们和前述玉饰头一样,背面有3个小孔,亦为革带构件。然而它们仅有革带的结构性构件而无装饰,若排除盗墓贼盗取的可能,或许为悬挂组绶的素面革带。除革带外还应有丝织大带的存在,推测应为冕服所用的佩绶带具,它们和谥宝一起组成“宝绶”。从永陵出土的双重宝盝尺寸来看,也有放置腰间组绶的可能,宝盝规格分别为:外重边长67、高19.2厘米;内重边长60.3、高14厘米,而谥宝尺寸仅11厘米左右,盝内剩余空间完全可盛放腰间组绶。
玉环直径9.5厘米,好3.9、厚0.9厘米。唐僖宗靖陵曾出土1件琉璃璧,与永陵出土的玉环纹饰相似[16]。永陵出土小银管长8厘米,此种管饰在同时期李茂贞夫妇墓中也出土有8件,均出于墓室,分别长2.6、4.5厘米[17],较永陵小,应为当时流行的管饰。玉环、银管为组绶饰品无疑,但其为谥宝组绶饰品还是腰间组绶饰品则无从考证。同时在后室东面第一券与第二券缺口中发现的3套银扣、银套环与玉饰头(图六∶3),与石床上发现的一样,关于它们的性质,《报告》未提及,推测亦为革带构件。

图六 永陵后室出土组绶饰物
除后室出土的5组革带,中室出土的玉大带性质应为王建的常服带具,在王建石像上也见此带具。墓中随葬玉带是因其和“宝绶”一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唐上元元年(674年)规定“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
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至景云二年(711年)规定“敕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石。”[18]所以唐代在遵循古礼印绶制度的同时,也出现了以腰带质地与带銙多寡来标明身份的新方式,其中玉銙因其原料紧缺,更是成为带具中的奢侈品。开平二年(908年),吴越国钱镠“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表诣大梁,陈取淮南之策。梁主问进奏吏曰:‘钱王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梁主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王。”[19]可见玉带在五代十国时期仍然难得,并成为各政权间外交的重要手段。
综上,永陵出土的谥宝、谥册、哀册均传承唐代礼制,这得益于前蜀时期“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20]。唐代葬仪中就有对这些帝王礼制用具的详细记载,“至玄宫,太尉奉宝绶入,跪奠于宝帐内神座之西,俯伏,兴,退。礼仪使以谥册跪奠于宝绶之西,又以哀册跪奠于谥册之西,又奉玉币跪奠于神座之东”[21]。《报告》中亦指出永陵出土的玉册、谥宝与宋代的规制极为相似,这也说明五代十国时期,蜀地在唐宋礼制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故土葬俗——反映中原葬俗的随葬品
王建生于大中元年(847年),许州舞阳人,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黄巢起义爆发后投身当地的忠武军,并在唐僖宗避难蜀地时与王宗侃、韩建等八人前去救驾,僖宗返回长安后任王建为神策军使,身居长安。后因人猜忌被调至利州任刺史,从此走上割据之路。王建虽在蜀地自立称帝,但早年生活对其墓葬仍有影响,主要反映在铁猪、铁牛、颐托、银猪等随葬品上。
永陵出土铁牛全长74、通高32厘米(图七∶1),铁猪全长66、通高32 厘米(图七∶2)。随葬铁猪、铁牛的葬俗大概出现于晚唐时期的洛阳、西安一带,这与王建早年活动的区域及时代吻合。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墓葬中,除永陵墓室放置铁猪、铁牛外,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出土铁牛2件[22],宝鸡李茂贞墓也出土铁猪、铁牛各1件[23],但此两例均在北方,南方地区就蜀地永陵1例。“五代的洛阳继续存在此种葬法,并前蜀也受到影响”[24],且“因为王建墓属于王陵级别的墓葬,铁牛铁猪的尺寸自然也大于普通官吏墓葬,这一点也符合《大汉原陵秘藏经》中所描述的从天子到百官随葬铁牛铁猪大小依次递减的情况”[25]。永陵出现铁牛铁猪,而与王建有同样生活轨迹的晋晖、王宗侃二人的墓内却无铁牛、铁猪的发现,因此,这应该属于王建的个人行为。但总体来看,晚唐五代以来,北方人士大量涌入南方才是永陵铁猪、铁牛出现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在宋元时期的浙江、福建一带有较多诸如铁猪、铁牛等随葬品的发现。

图七 永陵出土铁牛与铁猪
银颐托,即下颌托。通高17.3、最大径19厘米,托部长12、宽4.65厘米(图八)。根据吴小平等的研究,此种下颌托在我国境内最先出现于新疆一带,并存在由新疆传入大同再到关中、关东的传播路线,传播方式为点到点,这与人的迁徙有密切关系,时代则从春秋一直延续到宋元[26]。颐托的使用目的与金属面具相类似,用以保护肉身完整,防止灵魂因无法识别肉身而成为孤魂野鬼。在王建生活的晚唐,此种下颌托正在洛阳、偃师一带盛行,王建到蜀地后,又将这一特殊葬具带入墓中。

图八 永陵出土颐托
银猪,长11.3、高3.2厘米(图九),或为手握猪。手握猪与动物模型猪在造型上有明显区别,模型猪多为陶制且立体写实;手握猪则小巧、线条精练修长且呈匍匐状。永陵出土银猪外形与手握猪相似。手握猪最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且以滑石猪较多,后来逐渐出现玉、铜等其他材质,在唐代集中发现于西安、洛阳等地[27]。永陵手握猪为银质或许与王建身份高贵有关。墓主人手握猪的习俗由来已久,其中南京江宁地区发现的一对滑石猪上刻有的“天乙”题字,可帮助了解此类葬俗背后的文化内涵,即是司命信仰的表现,墓主人希望天一、北斗能帮助其脱离死后的苦难并升天成仙[28]。

图九 永陵出土银猪
综上,永陵出土的银猪、颐托、铁猪、铁牛均具有中原的葬俗特点。“唐后期墓葬依照生活信条而出现的惯例做法,……往往超越社会阶层,随葬品中的十二生肖、铁牛、铁猪广泛出现在各个阶层的墓葬中,与人的地位、经济实力关系不大。”[29]正是这样的风俗信仰让永陵随葬品在蜀地成为“孤例”。
(三)接受祭拜——新墓葬文化类随葬品
永陵中室棺床北端置1红砂岩石缸,口径113、高45、厚10厘米,缸下有五层残砖叠砌底座,高42厘米(图一〇∶1)。缸内石饼上设陶盆,盆内及石缸外各发现1盏瓷灯台(图一〇∶2、3),《报告》判断其为墓室内的照明器具。但这组照明器具与唐五代时期墓室内照明器具的摆放传统不同,如唐节愍太子墓出土的石灯位于前室,全器分灯座、高足和灯盏三部分,高足、灯盏外腹部装饰有仰俯莲瓣纹(图一〇∶6)[30];后蜀张虔钊墓棺床脚端发现1青石缸,口径66、高33、厚7厘米[31],其发掘简报虽未交代其性质,但或为照明器具;吴越国康陵墓内也见长明灯(图一〇∶4),位置因盗墓被扰动,其发掘简报称根据钱氏家族墓葬的传统,长明灯位置应在前室[32],同时在中室靠近后室的墓门处发现1张供台桌(图一〇∶7)也值得注意;七子山五代墓后室棺床脚端也发现1盏“孤魂灯”(原文称作“孤魂台”),另外在中室发现1张祭台桌,上还遗有筷子1双(图一〇∶5、8)[33]。从唐节愍太子墓、吴越康陵和七子山五代墓出土的照明器具造型和装饰来看,它们明显受到佛教点灯文化的影响。同时吴越国康陵和七子山五代墓中出现供祭台也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墓室内祭祀风气的盛行。除吴越国外,墓内的祭祀遗存还见于南汉德陵,在墓道南端器物箱内放置规整的青瓷罐190、釉陶罐82件,应为墓前祭奠遗存[34]。北方内蒙古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内也发现1件供案,上隐约可见10个疑似放置器物留下的圆圈状印痕,具体发现位置不详,墓葬年代相当于中原五代晚期[35]。前后蜀墓内也有类似发现:前蜀晋晖墓中室东耳室内有一高75厘米的供台,上置随葬品[36];后蜀高晖夫妇墓石椁前见1石方桌[37]。但两墓均破坏严重,具体使用性质不明。

图一〇 五代时期照明器具
永陵出土照明器具摆放在墓主头部,应该与后室石床上摆放的王建石像有关。相比前述墓例,永陵较为特殊的是其后室石床上端坐有王建石像。如果说七子山五代墓室内以祭台、孤魂灯到棺床形成一组祭祀逻辑空间;康陵墓室内以长明灯、祭台到棺床形成一组祭祀逻辑空间;那永陵的祭祀逻辑空间则是棺床、万年灯、王建石像,这样永陵地宫内的这一组照明器具就兼具了点灯和供祭的双重性质,而后室石床上的王建石像则是奠祭对象。王玉冬也提出永陵后室内以神座为中心布置奉献空间,在葬礼的最后阶段将整个空间作为地下享堂来使用[38]。
王建在生前、死后都曾有不少铸像或塑像,可惜早已不存,永陵地宫出土的石像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尊王建石雕坐像(图一一∶1)。有意思的是,近年在安岳千佛崖发现1尊前后蜀时期的雕像,此像通高96、像高84厘米,面部方圆,双耳硕大,腹部外腆,戴直脚幞头,着圆领长袍,双手拢于袖中,于腹前持笏,足下踏方台,方台前部饰二壸门(图一一∶2)[39]。此尊雕像与永陵出土的王建坐像高度基本一致,整体造型、雕刻手法以及后龛结构均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否也属于王建塑像则不得而知。关于永陵墓主人坐像的性质,已有道教石真说[40]与受写真艺术、僧人影真和灰身塑像的激发而产生的墓室内的祭祀立像[41]两大专论,但无论是哪种性质,这种墓室内设像的葬俗自王建石像后就大肆兴起。

图一一 前后蜀时期石雕坐像
现从墓主人像伴出随葬品的角度来验证这种新文化因素的发展。永陵后室石床上除有谥宝、玉册等器物外,还发现1铜炉,另有1提梁盏与之配套使用。文献中有“内谒者帅香案进于辂前”“内谒者捧香炉”“内谒者捧香炉置座前”[42]“荐香烛于灵幄前”[43]等相关记载,均为葬礼与祭奠中使用香案、香炉的场景。另“(后)晋天福五年正月,御史中丞窦正固奏每遇国忌行香,宰臣跪炉,僧人表赞,文武百官俨然列坐”[44],也可见五代十国时期盛行行香跪炉。目前成都周边墓室内发现墓主人坐像伴出随葬品明确的墓葬有:
1.洪河大道M1:夫妻合葬墓。其中左室出土红砂石雕墓主人像1尊,伴有香炉2件、四系罐1件。墓葬年代报告判断为唐代中晚期[45]。
2.蒲江五星镇M1:后龛正中出土石人1尊,随葬陶俑、钱币等。墓葬年代为北宋[46]。
3.永陵公园M3:系火葬墓。双室券拱墓,出土男、女陶坐像各1尊,各出熏炉1件。墓葬下限至南宋,不排除有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墓葬没有被辨认出来[47]。
4.学府尚郡M5:双室券拱墓。其中西室后壁正中出土石俑1件,伴有提梁小罐4件、瓷盏20件,其中2件瓷盏位于石俑附近,另外18件分列墓室两侧,墓室内发现有零星骨灰。年代为五代至北宋时期[48]。
5.川音大厦M2:系火葬墓。三室并列,其中西室出土陶塑墓主人像1尊,伴出瓷炉2件、提梁罐5件、买地券1方。墓葬年代为南宋早中期[49]。
6.金鱼村M9:系火葬墓。出土红砂石质坐像1尊,伴出五足炉5件,另有提梁小罐、碟、盏托、镇墓券、买地券等。墓葬年代为南宋淳熙至嘉定年间[50]。
以上墓例除蒲江五星镇北宋墓外,墓主人坐像多伴出炉或盏,由此可知墓主人像与炉的组合似为定制。从年代来看,这种墓主人像最开始只见于永陵、洪河大道M1、后妃墓[51]等晚唐、五代时期的高级墓葬,后来也逐渐见于普通墓葬,材质除石质外也有陶质。至南宋时期,较多发现于火葬墓中。张勋燎等通过对此种带墓主人像的火葬墓中道教随葬品的分析,推测其为道教尸解的典型材料[52]。
综上,永陵地宫内的王建石像、铜炉与石缸内的灯台构成了一组墓室内的祭拜组合。永陵以后室墓主人像为祭祀空间中心的做法,一直影响着宋代蜀地墓葬文化的发展。这些墓主人雕像普遍在墓室后部发现,这与前后蜀时期的墓葬形制有关。以前后蜀时期的中、高级墓葬为例,除孟知祥墓为较特殊的并列圆形三室外,其余多在墓室前置棺床,后室(龛)较前室略内收或略高于前室形成一个特殊的墓室空间[53]。在墓室后部设龛的做法最早见于唐贞元二年(786年)爨公墓,但该墓被盗扰,后龛未见随葬品,此后龛与棺床连接,应为前后蜀后室(龛)的雏形[54]。另外唐代王怀珍墓后龛还发现一模印“金□”字样的提梁壶[55]。到宋代,在墓室后部内收形成后室(龛),并放置石雕或陶塑墓主人像的葬俗便普遍流行起来。而在成都以外的其他西南地区发现的宋墓,多在后室(龛)浮雕墓主人坐像、牌位或象征墓主人虚位以待的桌椅等。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成都地区普遍流行砖室墓,墓主人像需立体雕刻单独放入,而成都以外的西南地区则流行石室墓,墓主人像直接浮雕于后壁,且墓主人周围多有侍奉者站立左右,其供奉性质更加明显。
三 结语
前蜀是在战乱中建立的王朝,其希望遵循唐代礼仪以匡正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有一些革新。通过对永陵出土随葬品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其后室石床上的谥宝、谥册、哀册等随葬品传承了唐代帝王礼制,且墓葬根据王建早年的生活经历放置了一些“孤例”随葬品,也更注重墓葬内的祭拜,将王建像置于墓室的核心位置便是永陵的革新所在。这开启了宋代以后以墓主人像为祭祀空间中心的墓葬新风气。
注释:
[1]冯汉骥撰:《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本文所引《报告》相关内容均出自本书,以下不再另注。
[2]a.樊一:《永庆院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b.曾中懋:《简论王建墓墓室结构和稳定性》,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26~128页,巴蜀书社,1994年;
c.[日]岸边成雄著,樊一译:《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乐妓》,《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d.秦方瑜:《王建墓石刻伎乐与霓裳羽衣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e.迟乃鹏:《王建墓棺床石刻乐伎弄佛曲说探证》,《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f.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1033~1041页,线装书局,2006年;
g.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年第6期。
[3]陈策能:《监察开掘抚琴台王建陵墓案》,《监察琴台工整团工作记事录》,第24页,四川省档案馆藏,案卷号041-02-3894,1943年。
[4]关于玉大带玉銙的位置,《报告》记载为“棺底北部,排列散乱”,与《古物表》说法差异较大。现根据玉大带银扣、铊尾的相对位置,判断玉銙应是散布在两银扣之间。
[5]梁思成等著:《未完成的测绘图》,第154~15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
[7]南京博物院编著:《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第86~88页,文物出版社,1957年。
[8]〔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第501页,中华书局,1983年。
[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一《职官三》,第559页,中华书局,1988年。
[10]刘毅:《帝王陵墓之册、宝、志探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
[1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凶礼八》,第2327、2348页。
[12]〔宋〕张唐英撰,冉旭校点:《蜀梼杌》卷上,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084~6085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
[1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六三《嘉礼八》,第1767~1768页。
[1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六一《嘉礼六》,第1721页。
[15]《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第3581页,中华书局,1977年。
[16]崔云:《历代玉璧时代特征举例》,《收藏家》2014年第11期。
[17]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第74、11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六三《嘉礼八》,第1769页。
[19]〔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第1081页。
[20]〔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第501页。
[2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凶礼八》,第2349页。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23]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第117~118页。
[24]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25]孙宇:《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铁牛铁猪研究》,《文博》2018年第3期。
[26]a.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年第8期;
b.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2013年第8期。
[27]古丽扎尔·吐尔逊:《唐代丧葬习俗中手握的综合研究》,第5~17页,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9年。
[28]王煜:《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天乙”滑石猪与司命信仰——也谈玉石猪手握的丧葬意义》,《东南文化》2017年第6期。
[29]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3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
[31]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另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龙泉驿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妇墓》,《考古》2011年第6期所述,墓内出土石座1件,周围凿三层覆莲,顶径35.2、底径56、高19.2厘米,据报告无法判断出土位置,是否为长明灯灯座未可知。
[3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33]苏州市文管会、吴县文管会:《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2期。
[34]同[6]。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第10期。
[3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前蜀晋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0期。
[37]徐鹏章等:《成都北郊站东乡高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
[38]王玉冬:《走近永陵——前蜀王建墓设计方案与思想考论》,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1辑,第2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39]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高升乡千佛岩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2辑,第258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40]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1033~1041页。
[41]李清泉:《墓主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以五代十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中心》,《美术学报》2014年第4期。
[4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凶礼八》,第2330、2346、2347页。
[4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七《凶礼九》,第2384页。
[44]〔宋〕王溥撰:《五代会要》卷四《忌日》,第47页,中华书局,1985年。
[4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管所:《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唐宋墓葬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164~165、176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46]四川省文管会、蒲江县文化馆:《四川蒲江县五星镇宋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4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度永陵公园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389~391、407~409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4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温江区“学府尚郡”工地五代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6)》,第329~33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武侯区川音大厦工地唐宋墓葬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5)》,第593、595、633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50]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火葬墓》,《考古》1997年第10期。
[51]周尔太:《成都市发现前蜀宫廷古墓》,《成都文物》1990年第4期。
[52]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1448页。
[53]以有明确纪年的纪年墓为例:a.前蜀晋晖墓残留的前、中室呈阶梯状抬升,中室设棺床。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前蜀晋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0期;
b.后蜀张虔钊墓分前、中、后三室,中室设棺床,后室内收略呈方形。参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
c.后蜀孙汉韶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整个墓室地面呈缓坡状,后室高前室低,中室设棺床。参见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五代后蜀孙汉韶墓》,《文物》1991年第5期;
d.后蜀徐公夫妇双室墓墓室逐级抬升,棺室后设内收的后龛,后龛高于棺室。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双流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双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后蜀双室合葬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323~36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e.后蜀宋琳墓按照墓底的高低变化分为前中后三室,三室地面逐级抬升。参见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5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发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02~21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5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红色村唐代王怀珍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301~30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