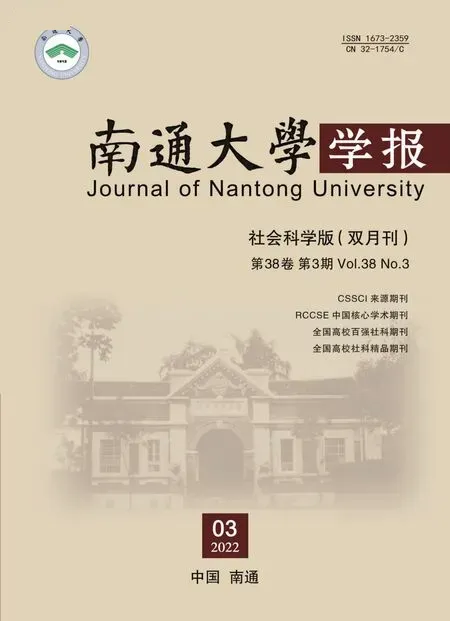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存在问题与展望
2023-01-03柳正权
柳正权,牛 鹏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是指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案件程序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涉外纠纷逐渐增多,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案件日益增加,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涌现。概括而言,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境外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问题,非涉外纠纷能否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第二,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第三,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国籍与执行问题;第四,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采取临时措施的程序问题。
长期以来,《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学界争议较大,法院在相关司法实践中的立场亦不统一。近年来,随着司法支持仲裁理念的树立,法院积极践行司法能动主义,在一些标志性个案中对上述问题陆续作出了回应。这些回应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相关争议,也更符合当前实践需要并体现了司法支持仲裁的精神。但也应当看到,司法上的回应并未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全部问题,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仍存在诸多限制。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晚近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实践中仍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以期推动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
二、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
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主要体现在司法领域,法院通过一系列标志性个案多方面推动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首先,在“黄金置地案”中,法院通过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突破,拓展了境外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其次,在“龙利得案”和“大成产业气体案”中,法院通过对《仲裁法》第16 条中“仲裁委员会”的合理解释,肯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的效力。最后,在“布兰特伍德案”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73 条①2021 年12 月《民事诉讼法》修改后,该条文号变更为第280 条,以下所引《民事诉讼法》条文号均依据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
(一)突破非典型涉外因素的认定拓展受案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1 条之规定,一般认为涉外纠纷当事人有权将纠纷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然而,对非涉外纠纷能否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仲裁法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理出发认为在法律缺乏明确规定的前提下,非涉外纠纷不能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另一种观点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出发认为既然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非涉外纠纷也可以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②两种观点差异的本质是对仲裁权性质认识的差异,相关讨论可参考王婧:《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仲裁效力几何》,载《法制日报》2009 年7 月9 日。
与学界争论不同,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典型案件的裁定逐渐形成了“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司法惯例。比如在“恒鼎实业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71 条仅规定涉外纠纷可以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本案所涉合同主体、标的等皆无涉外因素,因而不适用此条之规定。该案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以违反司法主权原则为由否定了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条款的效力。[1]94-98据此,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或“违反司法主权、公共政策”的逻辑,根据《合同法》第128 条或《民事诉讼法》第271 条③2020 年5 月28 日通过并于2021 年1 月1 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合同编》删除了《合同法》第128 条的相关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271 条之规定仍继续有效。的规定禁止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逐渐成为司法惯例。此后,无论是2012 年的“江苏万源案”[2]126-131还是2013年的“朝来新生案”[3]44-54,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都遵循这一司法惯例确认相关仲裁条款无效[4]。
“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司法惯例在学界招致批判,“法无授权不可为”或“违反司法主权、公共政策”的裁判逻辑并无法完全说服仲裁法学者。一方面从仲裁权的性质看,国际商事仲裁理论通说认为仲裁权不仅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更来源于当事人授权,[5]15-16对仲裁管辖权不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而应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念。另一方面对法院将“司法主权”或“公共政策”作为理由的做法,学界也认为相关裁定在说理上难以令人信服,法院并未对将非涉外纠纷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缘何违反“司法主权”作明确解释或说明。[6]因此,要求改变既有司法惯例的呼声在学界广泛存在,有研究者甚至为之列明了多条路径,比如放宽仲裁协议的涉外性标准,依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等。[7]
从晚近司法实践看,法院显然采取了“放宽仲裁协议的涉外性标准”这一路径。早在2014 年的“宁波新汇公司案”中,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以保税区未清关的货物属未入境货物,案件标的物具有涉外因素为由驳回了宁波新汇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④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5)四中民(商)特字第00152 号民事裁定书。在2015 年的“黄金置地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更是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首次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兜底规定,将“主体为外商独资企业且注册地在自贸区内”“合同履行过程涉及对自贸区货物特殊流转及海关监管制度的运用”等因素综合解释为“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认(外仲)字第2 号民事裁定书。,从而承认并执行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
“黄金置地案”的积极意义在于对非典型涉外因素的认定突破了传统“法律关系三要素”的模式[8],包括当事人双方的企业类型、企业注册地址、企业资本来源、最终利益归属、公司经营决策、与境外投资者的关系密切程度、标的物的流转或运输程序、合同履行是否涉及进出口程序以及合同履行是否涉及海关监管措施等都可能成为合同当事人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连接点。[9]在“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司法惯例下,对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突破拓展了境外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从而有助于推动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该案也因此入选中国仲裁2015 年十大有影响力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等。
(二)肯定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的效力
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内地仲裁曾是仲裁界争议的焦点,肯定论者认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是可行的,其理由包括:一是中国入世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法律并未明确禁止,三是申请执行不存在障碍。[10]否定论者则认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不可行,其理由在于一方面国际商事仲裁是商事性法律服务,我国虽已承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并未承诺开放仲裁市场。[11]另一方面《仲裁法》第16 条规定仲裁协议中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而境外仲裁机构并不属于《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委员会”,允许其在内地仲裁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12]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仲裁是一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与我国仲裁市场开放与否并不相关。[13]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内地仲裁的关键即在于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仲裁法》第16 条规定的“仲裁委员会”。[14]
法院在既往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多持否定立场,认为境外仲裁机构不属于《仲裁法》第16 条规定的“仲裁委员会”。比如在“神华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委员会”仅指依据《仲裁法》第10 条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设立或依据《仲裁法》第66 条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的仲裁机构,而不包括境外仲裁机构。[15]178-182因此,仲裁界普遍认为“神华公司案”的裁判结果为境外仲裁机构的内地仲裁之路蒙上了阴影。可喜的是,在与“神华公司案”仅相隔几个月的“龙利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改变了既往观点与立场,认定境外仲裁机构亦属于《仲裁法》第16条规定的“仲裁委员会”。在该案中,安徽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BP AgnatiS.R.L 公司签署《销售合同》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上海仲裁。对这一约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不是《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委员会”,故仲裁条款无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此案时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中多数意见认为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国际商会仲裁院并非《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委员会”,从而不能在我国境内从事仲裁活动为由认定仲裁条款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少数意见则肯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认为该仲裁条款无效。该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支持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多数意见,肯定了该仲裁条款的效力。[16]126-129
“龙利得案”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国内研究者多认为该案为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扫清了主要的法律障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7]国外研究者则多持谨慎态度,认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龙利得案”中作出了相对肯定的答复,但并未深入解释《仲裁法》中“仲裁委员会”的内涵[18],其观点能否得到坚持与贯彻尚不可知[19]。2020 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等与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在“龙利得案”中的复函,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有效”的观点进行了极有层次和说服力的论证,并明确指出认定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条款的效力不能仅局限于立法的不足,而忽视司法解释的效力和进步。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 民特83 号民事裁定书。“大成产业气体案”的裁判结果与“龙利得案”的裁判结果相呼应,使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条款有效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三)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国籍
“龙利得案”和“大成产业气体案”虽明确肯定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的效力,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该如何承认与执行却仍未得到解决,[20]而解决执行问题的前提则是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国籍。国际商事仲裁理论通说认为,商事仲裁裁决具有国籍属性,仲裁裁决的国籍标志着其法律效力的来源。[21]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看,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主要有地域标准、仲裁程序适用的法律标准、混合标准等。[22]191-199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虽并未对如何判断仲裁裁决的国籍作出明确规定,但结合《民事诉讼法》有关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可以看出,其事实上采取了以“仲裁机构的涉外性和所在地”作为判断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23]
根据这一标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曾长期被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并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与执行。比如在“天利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依据国际商会仲裁院所在地为法国的事实,将其在中国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法国仲裁裁决,并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审查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在仲裁界引发巨大争议,许多研究者认为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将导致该裁决陷入无法执行的困境,[24]其原因在于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 条第1 款之规定,在中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并不能再适用公约在中国领土内申请承认与执行。[25]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解释为“非内国裁决”或许更为合适。[26]
这一观点首先体现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旭普林案”所作的裁定中。在旭普林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的仲裁裁决时,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上海作出的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锡民三仲字第1 号民事裁定书。此后,在“德高钢铁公司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确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北京作出的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并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并执行了该裁决。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甬仲监字第4 号民事裁定书。作为中国法院首例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裁决的案例,“德高钢铁公司案”受到了极大关注,也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讨论。部分研究者认为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并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与执行有违我国提出的“互惠保留”原则[27]93-94,进而认为将此类裁决认定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是最符合实际的选择,并呼吁采取“仲裁地”标准认定仲裁裁决国籍[28]。
然而,尽管有此呼声,司法实践中却一直缺乏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的案例。2020 年8 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布兰特伍德案”中认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广州作出的仲裁裁决可视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应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73 条的规定申请执行④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 号民事裁定书。,使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国籍得以明确。[29]“布兰特伍德案”虽系地方法院的个案,但在依照内部报核规定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后,该案的裁判结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布兰特伍德”案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反映出我国在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上正逐步由“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向“仲裁地”标准靠拢,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布兰特伍德”案明确回应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能否在我国得到执行以及执行的法律依据问题,确认和呼应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有效的观点,将进一步推动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
三、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存在的问题
回顾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可以发现基本是依靠司法的推动。然而,由于《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司法推动的力量有限,不可能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全部问题。当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实践中仍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存在法律障碍
自“黄金置地案”以来,部分研究者认为法院基本放开了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限制,即使是纯国内纠纷也可以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30]但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院在判断此类仲裁协议效力时事实上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判断案件是否具有涉外性,若案件具有涉外性则当然可以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仲裁协议有效,若案件不具有涉外性则进行第二步判断。第二步判断非涉外纠纷能否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若可以则仲裁协议有效,若不可以则仲裁协议无效。从“黄金置地案”的裁判过程看,并未涉及第二步判断的问题,法院采取了放宽仲裁协议涉外性认定标准的办法推动自贸试验区内的民商事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而对于纯国内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则仍持禁止态度。
这一态度可从“黄金置地案”后法院的相关裁定中得到验证。比如在“林德气体(厦门)有限公司、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 月15 日作出裁定认为,约定将非涉外纠纷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因超越法律的许可范围而无效。①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认字第155 号民事裁定书。在“爱耳时代医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诉领先仿生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于2018 年6 月26 日作出裁定认为,当事人约定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纠纷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无效。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申921 号民事裁定书。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法院对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条款的裁判思路是在涉外性的认定上寻求突破,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质“非涉外纠纷能否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而言,则依然坚持了“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司法惯例。
法院之所以禁止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受我国仲裁司法监督的双轨制格局影响。我国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实行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对涉外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仅作程序性审查,对国内仲裁裁决则涉及一定的实体内容,法院不愿当事人以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办法规避司法审查,也就自然不愿意承认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条款的效力。其二,受我国对仲裁权性质认识的影响;我国传统观点认为仲裁权的产生以法律的授权为前提,如果没有法律的授权也就不可能产生仲裁权。受此观点影响,法院在相关裁定中自然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拒绝承认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条款的效力。[31]在上述两点因素未有实质性变更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法院必将继续坚持“非涉外纠纷不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司法惯例。
(二)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采取临时措施的程序不明确
所谓仲裁中的临时措施是指仲裁庭或有管辖权的法院采取的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在内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它既可以在仲裁程序开始前采取也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中采取。[32]早期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多将发布临时措施的权力排他性地授予法院,但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许多国家已在立法中明确赋予仲裁庭发布临时措施的权力。[33]我国现行仲裁立法并无临时措施之概念,与之相应的是有关“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根据《仲裁法》第28 条、第46条、第64 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72 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的,应当由仲裁委员会依照相关规定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定。这一规定排除了仲裁庭发布临时措施的权力,但许多境外仲裁机构都在其仲裁规则中明确仲裁庭有权发布临时措施[34],那么当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时,其仲裁庭是否有权发布临时措施?如果发布将如何承认与执行?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将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措施解释为“临时裁决”的方式,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其理由在于:第一,《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所称“仲裁裁决”是否包括“临时裁决”存在较大争议,甚至通说认为“临时裁决”并不适用公约。[35]第二,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7 条之规定,临时措施不仅可能以“临时裁决”的形式发布也可能以命令的形式发布,对以命令形式发布的临时措施,公约显然不能适用。第三,公约中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之一是满足正当程序要求,给双方当事人平等的陈述机会,而临时措施是依据单方面申请作出的,可能无法满足公约规定的条件。[33]因此,将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措施解释为“临时裁决”的方式并不能解决临时措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即使不考虑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认为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时,其仲裁庭无权采取临时措施,只能通过仲裁机构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转递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申请,那么境外仲裁机构也面临转递时间、转递程序等不明确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司法监督机制不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看,司法监督仲裁的方式主要包括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以及对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36]《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虽对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和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管辖法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时,其所作裁决的审查法院仍存在不够明确的问题。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为例,《仲裁法》第58 条规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由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然而,境外仲裁机构的所在地不可能有中国的法院,从而导致任何中国法院都没有管辖权。即使假定仲裁地的法院有管辖权,如果约定的仲裁地没有明确到特定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仍可能存在管辖不明的问题。比如当事人约定仲裁地为中国上海或北京,而上海或北京都有一个以上的中级人民法院,此时究竟哪一个法院有管辖权有待明确。
(四)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缺乏法律依据
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既可以通过直接组成仲裁庭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程序管理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37]其中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可以在仲裁案件之余起到推广和宣传仲裁机构的作用,因此更为境外仲裁机构所青睐。然而,当前境外仲裁机构却较少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其根源在于法律依据的缺乏。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比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虽在自贸区建设方案或司法局发布的相关管理办法中明确允许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但从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看,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业务机构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业务机构限于特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能否实现普遍化和常态化有待考察。[38]第二,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业务机构的依据效力较低,缺乏法律甚至是行政法规层面的依据。第三,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业务机构的受案范围较窄,仅限于涉外纠纷。第四,设立的业务机构并非我国法律意义上的仲裁机构[39],大多仅能起到推广和宣传仲裁机构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受理仲裁案件并管理仲裁程序。[40]
四、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展望
针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实践中尚存的问题,要进一步推动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不能仅靠司法的力量,更应依靠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的协力。具体而言,可从修改立法消除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法律障碍、统一司法规范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司法审查以及加强管理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等三方面入手。
(一)修改立法消除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法律障碍
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由零散的个案仲裁活动转变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安排,离不开立法的推进。[41]3当前,《仲裁法》修订已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司法部也已组织起草《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于2021 年7 月30 日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看,涉及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规定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增加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设立业务机构的登记管理规定。考虑到国务院文件已经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业务机构,且这一开放政策有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势,《征求意见稿》第12 条第3 款对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业务机构的登记和备案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删除仲裁条款需要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与国际接轨,《征求意见稿》第21 条取消了仲裁协议中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规定。第三,明确引入“仲裁地”标准。针对我国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与国际惯例不符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27 条引入“仲裁地”标准,明确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第四,明确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和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根据国际商事仲裁惯例,《征求意见稿》第28 条及第43 条至第49条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及其管辖权问题的自主审查权和临时措施决定权。
整体上看,《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基本回应了当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然而,结合实践中的问题可以发现,相关规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境外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范围仍限于涉外纠纷。《征求意见稿》第12 条第3 款将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业务限于涉外仲裁业务,意味着非涉外纠纷仍不能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第二,港澳台地区的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业务机构依据何种程序不明确。不同于此前上海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发布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2 条第3 款使用“外国仲裁机构”而未使用“境外仲裁机构”的表述,导致港澳台地区的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业务机构时能否适用该款规定存在争议。第三,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具体程序仍不明确。《征求意见稿》增设“临时措施”一节,不仅扩大了临时措施的范围,更明确赋予仲裁庭临时措施决定权。然而,从临时措施的执行看,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后,应由仲裁机构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执行,有管辖权的法院包括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证据所在地、行为履行地、被申请人所在地或者仲裁地的人民法院,境外仲裁机构就保全事宜需要与多地法院保持联络,可能因工作衔接问题影响保全行为的执行。此外,临时措施的执行还可能涉及对被保全人或第三人异议的审查,变更保全担保、解除保全等申请事项的审查,当此类情形发生时,是仍交由仲裁庭审核,还是直接由人民法院审查裁定,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统一司法规范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司法审查
司法对仲裁的适度审查与监督,有利于提高仲裁的公信力,但司法审查也应保证审查标准的连续和统一,否则将不利于仲裁事业发展。从当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实践看,虽取得了一些发展,但仍存在不完全统一的情况。对这些问题,《仲裁法》作为仲裁领域的基本法无法作出太过详细的规定,具体操作过程中有赖司法解释的统一。因此,应进一步统一司法,规范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具体而言,一方面,《仲裁法》修订工作完成后,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颁布司法解释统一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比如就申请撤销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管辖法院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存在多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各中级人民法院均具有管辖权,由先受理的法院负责管辖。”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可及时将有代表性的司法审查案例上升为指导性案例,通过指导性案例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三)加强管理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
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离不开行政的支持和引导。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先后发布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业务机构。部分境外仲裁机构比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甚至已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了业务机构并开展工作。因此,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应及时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地的管理经验,适时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性质、条件和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
五、结语
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主要是依靠司法推动,但在立法不完善甚至存在一些限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司法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在全球行政法理论下,裁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公众对裁决的接受度是仲裁庭在表决时必须考量的。[42]中国仲裁事业特别是涉外仲裁事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立法、司法与行政三者协调,才能真正推动仲裁制度完善和仲裁事业发展。[43]因此,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发展既离不开司法的推动,更需要立法、司法与行政三者的密切配合,共同发力。纵观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立法,急迫在司法,关键在行政。[38]只有在立法层面消除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法律障碍,在司法层面统一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司法审查,在行政层面支持并服务好境外仲裁在内地仲裁,才可能将我国打造为受欢迎的仲裁地,充分发挥仲裁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