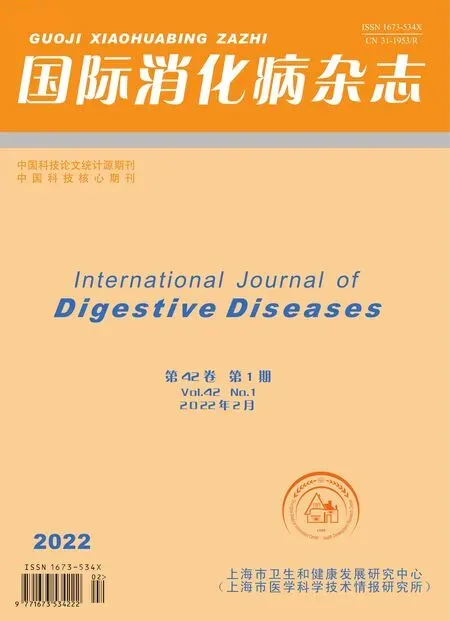乌司奴单抗用于克罗恩病治疗的研究进展
2023-01-03杨婷婷孟立娜
杨婷婷 孟立娜
克罗恩病(CD)是一种由免疫反应介导的慢性肠道疾病,以非干酪性肉芽肿、裂隙状溃疡、黏膜下纤维化,以及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跨肠壁浸润为组织病理学特征。CD的病因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免疫功能失调是肠道炎性反应发生的原因,炎性反应主要由TNF-α、IL-12、IL-23等细胞因子介导[1-2]。针对TNF-α的生物制剂最初被批准用于对常规治疗无效的中、重度CD患者[3]。然而,有约33%的患者在抗TNF-α治疗后病情没有改善,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对TNF-α拮抗剂的治疗反应[4],因此亟需研发作用于其他靶点的新药物。在慢性炎性反应中,抗原刺激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IL-12和IL-23。IL-12可促进Th1细胞释放干扰素-γ(IFN-γ),IL-23可与Th17细胞和巨噬细胞结合,促进IL-17、IL-6、IL-1和TNF-α的释放。有研究显示,CD患者肠黏膜中的IL-12和IL-23表达水平升高[5]。乌司奴单抗(UST)是一种全人源IgG型单克隆抗体,其可作用于IL-12与IL-23相同的p40亚基,以往常被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皮肤病;近年来的临床研究发现,其阻断IL-12/IL-23的作用也可以缓解肠道炎性反应[6-7]。自2016年9月起,UST被美国和欧盟批准用于治疗中、重度CD患者。本文就UST治疗CD的作用机制、有效性、安全性等相关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UST的作用机制
IL-12和IL-23是维持人体正常免疫的细胞因子,主要由抗原递呈细胞产生,两者密切相关[8-10]。 IL-12由IL-12 p35和IL-12 p40两个亚基组成,IL-23由IL-12 p40和IL-23 p19两个亚基组成[9]。从结构上看,两者有着相同的p40亚基和IL-12受体β1(IL-12Rβ1),它们的信号主要由JAK/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TAT)信号通路介导[10]。
CD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在一些可能的诱因下如肠道微生态失衡或特殊病原体导致肠黏膜屏障破坏,刺激固有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使多种细胞因子过量产生,其中包括IL-12和IL-23[1-2]。在CD发展的不同阶段,IL-12和IL-23 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早期阶段,肠道炎性反应主要由IL-12驱动[11]。IL-12由炎性肠段黏膜内的单核巨噬细胞等固有免疫细胞产生,也可由适应性免疫T细胞大量表达,其可促使原始T细胞分化为Th1细胞,进而产生IFN-γ;IL-12还可促进1型固有淋巴细胞(ILC1)的发育,进一步促进IFN-γ、TNF-α的合成;IFN-γ可促进巨噬细胞源性IL-12的产生,从而放大Th1型免疫反应[12-13]。
在维持肠道慢性炎性反应方面,IL-23起着重要的作用[14]。IL-23与Th17细胞密切相关,IL-23/ IL-17信号通路在黏膜免疫和维持肠道内稳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IL-23可诱导不同黏膜组织中IL-17的表达,可与其他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IL-1和IL-6]协 同 促 进Th17细 胞的成熟[14]。研究显示,Th17细胞可表达IL-17、 IL-22、IFN-γ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介导组织的慢性炎性反应;其他免疫细胞如T细胞亚群γδT细胞、巨噬细胞、ILC3等对IL- 23也有反应,这些细胞可产生IL-17家族细胞因子(如IL-12A、IL-17F等),导致局部组织发生炎性反应[15]。
IL-23与肠道慢性炎性反应性纤维化及炎性反应相关性肿瘤也有一定关系[16-18]。肠道纤维化是CD的严重并发症,通常表现为肠腔狭窄。Mathur等[16]的研究发现,IL-23的表达上调在小鼠模型的肠道纤维化中起着重要作用,ILC可能参与了肠道纤维化过程。给予慢性结肠炎小鼠模型注射IL-12/IL-23 p40疫苗可显著逆转持续的结肠炎性反应和纤维化,表明阻断IL-12/IL-23可抑制慢性炎性反应,有可能逆转肠道纤维化进程[17]。研究发现结肠炎小鼠模型、结肠炎相关肿瘤和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的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粒细胞产生的IL-23增加,表明IL-23在慢性肠道炎性反应和结肠炎相关肿瘤中起着调节作用[18]。
因此,通过拮抗IL-12和IL-23可以阻断相关炎性反应的发生。UST通过与IL-12/IL-23的p40亚基结合,阻断它们与免疫细胞表面IL-12Rβ1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IL-12/IL-23介导的免疫反应[6]。然而,UST对已与受体结合的IL-12/IL-23不能再进行结合。UST可能是通过与p40亚基结合,阻断Th1和Th17细胞因子途径从而在CD中发挥治疗作用。
2 UST在CD中的临床应用
UNITI研究是评价UST治疗CD的Ⅲ期临床试验系列研究。Feagan等[19]对中、重度CD患者进行了为期8周的Ⅲ期诱导试验(UNITI-1和UNITI-2)。在UNITI-1研究中,将抗TNF-α治疗失败或不耐受的患者随机分为130 mg UST治疗组、6 mg/kg UST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第6周时130 mg UST治疗组和6 mg/kg UST治疗组的临床反应率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34.3%、33.7%、21.5%);第8周时130 mg UST治疗组和6 mg/kg UST治疗组的临床反应率(33.5%和37.8%)和临床缓解率(15.9%和20.9%)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20.2%和7.3%)。UNITI-2研究纳入了免疫抑制剂或激素治疗失败及不耐受的患者,结果显示130 mg UST治疗组和 6 mg/kg UST治疗组中分别有51.7%和55.5%的患者在第6周时达到克罗恩病疾病活动指数(CDAI)评分降低≥100分或CDAI评分<150分。
在诱导试验第8周时有临床应答的中、重度CD患者继续参与维持试验(IM-UNITI),将其随机分为每8周UST治疗组、每12周UST治疗组和安慰剂组,在44周时两组UST治疗组的临床缓解率(53.1%和48.8%)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35.9%),临床反应率也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P均<0.05)[20]。继续进行为期3年的维持试验,结果显示在第152周时每8周UST治疗组和每12周UST治疗组的缓解率分别为55.1%和56.3%[21]。对上述诱导和维持试验进行内镜下亚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UST治疗组的内镜下黏膜改善情况更明显[22]。
UST在多个国家的临床应用报道也证实了其疗效。德国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在108例CD患者中,有51例在第8周时对UST治疗有临床应答,有24例达到了临床缓解;在48周时有48例对UST治疗有临床应答,有25例达到临床缓解[23]。以色列的一项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在应用UST治疗24周时,106例CD患者中有52%患者的Harvey-Bradshaw指数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01),临床缓解率为31.1%,需要激素治疗的患者减少了66%[24]。西班牙的一项评价UST治疗难治性CD患者的短期疗效研究结果显示,305例患者中分别有101例和126例在第8周和第14周时达到临床缓解[25]。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应用UST治疗16周时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26]。
目前UST治疗肛周CD的研究相对较少,Chapuis-Biron等[27]的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对207例活动性肛周CD患者应用UST治疗后,有38.5%的患者获得肛周病变的缓解,其中205例曾接受至少1种抗TNF药物的治疗。UST可能是潜在的治疗肛周难治性CD的有效治疗选择,但需进一步进行前瞻性研究探讨。
对药物产生耐药抗体可能是影响疗效的原因之一。目前应用UST后产生耐药抗体的CD患者比例较低,在UST治疗诱导期和维持治疗期产生抗UST抗体的患者比例分别仅为0.2%和2.3%[19,28-29]。 Hanauer等[21]的研究发现,在接受UST治疗的患者中仅有4.6%的患者在3年维持注射期间检测抗UST抗体呈阳性。
目前对以下3类患者推荐应用UST治疗:对TNF-α拮抗剂无应答及不耐受者,免疫抑制剂及激素治疗的效果欠佳,以及未应用过TNF-α拮抗剂者。UST的给药方式为第0周予130 mg或6 mg/kg静脉诱导注射后,每8周或每12周予90 mg皮下维持
注射[19-20]。
3 UST的安全性
在安全性方面,CD患者的UST血浆清除率为0.19 L/d,皮下注射生物利用率为78%[29]。Sandborn等[30]的1年期随访研究发现,UST治疗组发生不良事件的患者例数、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感染率、严重感染率和恶性肿瘤(不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近,在临床应用的回顾性研究中未见因使用UST治疗后并发潜伏性结核的病例报道。研究显示,UST治疗组和TNF-α拮抗剂治疗组的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与安慰剂组无明显差异[31]。Hanauer等[21]的研究对567例CD患者应用UST治疗3年,随访数据也显示治疗组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严重感染率均与安慰剂组相近。
UST常见的非胃肠道不良反应包括头痛、关节痛和鼻咽炎[19]。Badat等[32]报道了应用UST治疗1年后有1例患者发生中枢性脱髓鞘,但该患者以往曾应用抗TNF-α生物制剂治疗。
Ghosh等[33]报道了2例应用UST治疗的CD患者出现了短暂的过敏症状,经抗过敏治疗1 h后症状消失。此外,在Ⅲ期临床试验中,UST治疗组的注射反应发生率为0.7%(51/7 055),而安慰剂组为0.4%(26/7 154),较常见的注射反应为注射部位红斑[30]。约5%接受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治疗的IBD患者可出现新发的牛皮癣样皮损[34],而UST可能可以有效缓解牛皮癣样皮损、坏疽性脓皮病和结节性红斑等皮肤病变[35]。
目前尚无UST与其他生物制剂的随机对照研究。Biemans等[36]针对经抗TNF-α治疗(如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失败的CD患者进行队列研究,发现UST的疗效优于整合素拮抗剂维得利珠单抗,且两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UST治疗的CD患者更有可能实现无激素临床缓解(OR=2.58,P=0.004)、生物化学缓解(OR=2.34,P=0.027)及临床联合生物化学的综合缓解(OR=2.74,P=0.014)。两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均显示,对TNF-α拮抗剂耐药的CD患者经UST治疗的临床缓解率高于维得利珠单抗(OR=1.92,95%CI:1.09~3.39,P=0.030;OR=2.79, 95%CI:1.06~7.39,P=0.038)[37-38]。Singh等[39]的荟萃分析比较了UST与其他药物的疗效及排名,结果显示UST和阿达木单抗均优于维得利珠单抗;在既往接受过TNF拮抗剂治疗的CD患者中,UST和阿达木单抗在临床诱导缓解方面的排名均先于维得利珠单抗。
4 小结与展望
生物制剂已成为CD治疗的重要部分,目前TNF-α拮抗剂为主要药物,然而以TNF-α拮抗剂为一线治疗药物时,有13%~40%的患者对起始治疗无应答,有13%的患者为继发性无临床应答[4]。 治疗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机体内药物水平过低或出现耐药抗体。尽管UST是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但也可能产生抗体,或由于药物的清除而影响药物水平和持续疗效。因此,可能需要检测药物水平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UST以其针对IL-12/IL-23的p40亚基的独特作用机制在CD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UST在临床应用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其有潜力成为传统免疫抑制治疗或TNF-α拮抗剂治疗失败后的新选择。对于潜伏性结核患者,UST可能比TNF-α拮抗剂更安全。与其他药物相比,UST维持治疗期间的用药间隔时间更长,其皮下注射方式也较方便,但UST的应用可能因价格昂贵而受限。
综上所述,UST在临床应用中尚存在以下问题:(1)因缺乏与其他药物疗效进行直接比较的研究,故缺乏将其作为临床治疗优先方案的依据;(2)缺乏UST对肛周CD和对CD肠外表现的治疗效果的前瞻性研究;(3)需进一步探索可反映UST疗效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这可能会成为今后IBD精准医疗的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