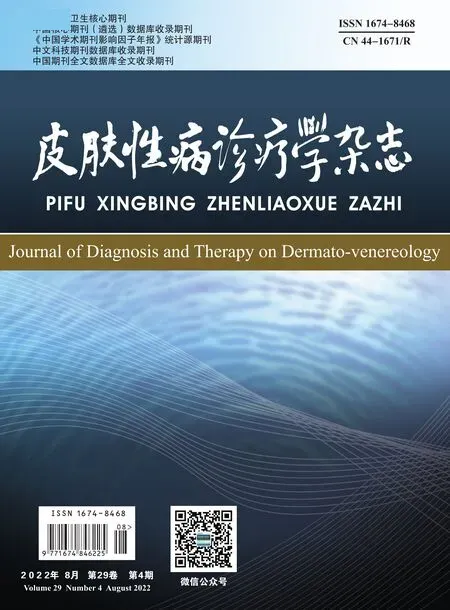坏疽性脓皮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2023-01-03黎晓丽林乃余唐旭华韩建德
黎晓丽, 林乃余, 唐旭华, 韩建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广东 广州 510080
坏疽性脓皮病(pyoderma gangrenosum,PG)是嗜中性皮肤病(neutrophilic dermatoses, NDs)最具代表性的疾病之一,通常表现为下肢和躯干绕以红晕的疼痛性丘疹、脓疱,逐渐扩大形成境界清楚的、潜行性痛性溃疡,边缘多为蓝紫色,临床上病程表现为慢性或复发性经过,病情从轻度到重度不等[1]。坏疽性脓皮病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不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PG的平均发病年龄在40岁左右,美国发病率约为58例/每百万人年,英国则为6例/每百万人年[2],我国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据。既往PG的诊断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主要依靠“排他性诊断”。2018年国际专家德尔菲共识提出了溃疡性坏疽脓皮病的诊断标准,其中包括1个主要标准和8个次要标准。满足4个次要标准时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可达86%和90%,即满足1个主要标准和4个次要标准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诊断区分度[3]。主要标准包括溃疡边缘皮肤病理活检提示中性粒细胞浸润,8个次要标准分别是:①排除感染;②溃疡发生于创伤部位;③有炎症性肠病或炎症性关节炎病史;④近4 d内出现丘疹、脓疱或水疱并破溃;⑤皮疹周围绕以红斑、潜行性边缘、溃疡部位压痛;⑥多发溃疡,且至少一处位于小腿伸侧;⑦溃疡愈合后留下筛状或褶纸样疤痕;⑧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后1个月内溃疡面积减小。另外,Jockenhöfer等[4]制定了Paracelsus评分用以PG的诊断。
PG的病因尚不明确,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体炎症性疾病。PG患者常合并潜在的全身性疾病,如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风湿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等[1]。目前发现多个与PG相关的自身炎症性综合征,如PAPA综合征、PASH综合征、PAPASH综合征等[2]。PAPA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以化脓性无菌性关节炎(pyogenic sterile arthritis)、PG、痤疮(acne)为特征的自身炎性综合征,PASH综合征以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PG、痤疮为特征,PAPASH综合征则以化脓性关节炎(pyogenic arthritis)、PG、化脓性汗腺炎、痤疮为特征。目前对PG及与其相关的多种合并基因突变的自身炎症性综合征的研究显示,PG发病具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临床上PG患者迁延不愈的疾病进程及传统治疗方案的局限性可能源于对该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不足,近年来以细胞因子为治疗靶点的精准治疗为PG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而据此出现的治疗反应亦可能为进一步阐明各个治疗靶点在该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提供线索。现本文就PG发病机制中可能存在的遗传易感因素、免疫异常作一综述。
1 遗传易感性
既往曾有数例家族聚集性PG病例[5],表明遗传因素与PG的病因存在一定关联。尽管在PG患者中未检测出某一特征性的基因突变,但近年数个研究报道了与PG相关的自身炎症性综合征存在不同程度的基因突变[6]。
由MEFV(mediterranean fever)基因突变所致的家族性地中海热(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FMF)是最先被认识及最常见的遗传性自身炎症性综合征[7]。Honda等[8]报道2例伴发化脓性无菌性关节炎的PG患者存在MEFV基因外显子杂合突变,MEFV基因编码的热蛋白(pyrin)可调节炎症小体的功能使IL-1β(interleukin-1β)分泌增加,这是由于炎症小体是由胞浆内模式识别受体参与组装的多蛋白复合物,可招募和激活促炎症蛋白酶Caspase-1,活化的Caspase-1切割IL-1β和IL-18的前体,产生相应的成熟细胞因子。IL-1β分泌增加可诱导细胞在炎症和应激条件下死亡,参与了针对多种病原体的宿主防御反应,进一步诱导角质形成细胞产生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9]。目前秋水仙碱是治疗FMF的主要药物[10],而这2例患者对秋水仙碱和小剂量皮质类固醇的联合治疗反应良好。这表明MEFV基因突变可能与PG的发病有关,但仍需大样本的研究支持。
Marzano等[11]在7例PG和13例PASH综合征患者中不仅发现MEFV基因出现突变,还发现PSTPIP-1、NOD2、NLRP3、NLRP12、LPIN2等多种自体致炎基因发生多重突变。其中,位于15号染色体的PSTPIP-1基因还与PAPA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PSTPIP-1基因编码脯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相互作用蛋白(PSTPIP-1),突变的蛋白质对吡啶具有更高的亲和力,并导致炎症小体过度组装,最终激活IL-1β、TNF-α和IL-8[12]。而NOD2基因编码的NOD2蛋白(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2)在协调自噬相关蛋白的正确组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其突变会导致自噬功能受损,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另外,一项基因表达差异研究提示Ptpn6基因缺陷导致小鼠出现了NDs样皮损,且在部分PG患者中检测出Ptpn6基因杂合突变[13]。
这些研究结果为PG的遗传学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提示PG及其相关综合征可能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并有助于建立NDs在自体炎症性疾病中的分类。虽然目前仍未在PG中发现明确致病基因,但关于PG遗传易感性的研究对疾病的预防及诊断有着重要意义,并可能为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帮助。
2 免疫系统异常
2.1 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
中性粒细胞抗感染主要通过直接吞噬病原体或利用中性粒细胞坏死或者凋亡后释放缩合染色质、组蛋白和抗菌肽形成的网状结构以捕杀病原体,即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14]。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与PG的发病机理密切相关,中性粒细胞活化失调、凋亡延迟、吞噬功能异常被认为在PG的发病机理中起重要作用[15]。NETs 与包括PG在内的多种炎症性皮肤病的发病机制有关[16],示例性荧光图像显示PG患者皮损中存在密集的中性粒细胞浸润,且观察到大量的NETs聚集[17],这提示NETs参与了PG的发病过程。Mistry等[18]亦强调这一观点,认为在PAPA综合征中NETs净形成增强和净降解减少是导致炎症的重要原因。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cyte-clone stimulate factor, G-CSF)是中性粒细胞最重要的调节剂之一,可延长中性粒细胞的存活时间,同时增强其趋化性、吞噬作用、产生超氧化物和其他代谢功能[19]。高G-CSF水平还会导致内皮细胞迁移和增殖,并诱导细胞因子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产生,进一步导致中性粒细胞的异常聚集[20]。血清或组织中G-CSF水平的升高可能会显著影响中性粒细胞募集和释放,因此G-CSF现被广泛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化疗后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有研究者发现PG患者在治疗前血清G-CSF显著升高,治疗后急剧下降至正常水平,且有部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在使用G-CSF 后发生了包括 PG 在内的多种NDs[19]。
2.2 补体系统
PG与补体C2、C4、C7的先天性缺陷有关[21],其中,C7的缺乏可导致中性粒细胞趋化性、调理作用和吞噬作用的降低,提示该途径的失调可能参与PG的发生与发展。此外,补体过敏毒素(例如C3a和C5a)在中性粒细胞的募集和激活中被上调,Rafail等[22]发现在C5a受体缺陷小鼠中皮肤伤口早期愈合率更高,阻断C5a受体激活可加速早期愈合,推测加速愈合的机制与缺乏 C5a受体信号传导和炎症细胞向伤口的募集减少有关。IFX-1(vilobelimab)是一种IgG4单克隆嵌合抗体,它是补体 C5a 抑制剂,可抑制中性粒细胞活化、趋化,并减少炎症信号传导,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IFX-1 对 PG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Ⅱa期开放性试验(NCT03971643)中,5例PG患者中有 2例可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且没有报告严重的不良事件[21]。
2.3 多种细胞因子异常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之间的关联在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互有交叉,有学者认为中性粒细胞趋化性的改变仅是炎症级联反应的终点之一。既往大量研究集中于中性粒细胞趋化性缺陷在PG发病机理中的作用[5-6],但最新的研究试图将PG中异常的中性粒细胞凝集追溯到引发炎性级联反应并最终招募中性粒细胞的来源,潜在的炎症异常来源包括T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角质形成细胞等。
通过蛋白质抗体矩阵方法发现PG患者皮肤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过度表达,其中包括IL-1α、IL-1β、IL-8、IL-17、CXCL1/2/3、CXCL16、TNF-α、CD40/CD40L和FAS/FASL等[23]。其中,IL-1β可诱导TNF-α和趋化因子IL-8的产生,IL-1β和IL-1α是参与自身炎症的重要多效细胞因子[24],并导致中性粒细胞炎症浸润,IL-1β及其受体在 PG 中过度表达可能与炎症小体功能失调有关[11]。在Ptpn6小鼠模型中发现,中性粒细胞介导的皮肤自炎关键调节成分是IL-1α而不是IL-1β,该研究阐述了IL-1α通路的复杂调控,并确定了一些在Ptpn6小鼠皮肤炎症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信号成分,如IL-1受体(IL-1R)、髓系分化初级反应基因88(MyD88)、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1(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1,RIPK1)、转化生长因子-β激活激酶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activated kinase 1,TAK1)和凋亡信号调节激酶1(apoptosis signal-regulating kinase 1,ASK1)等[25]。另外,IL-17是中性粒细胞激活和诱导产生IL-8的关键细胞因子,而IL-8是中性粒细胞的主要趋化因子,在PG中与TNF-α协同增强和维持促炎状态[26-27]。PG患者中亦出现IL-25表达上调[28]。
这些炎症介质为靶向免疫疗法提供了多种机会,例如临床上部分PG患者使用TNF-α拮抗剂、IL-1 受体拮抗剂[29]、IL-17受体拮抗剂[30]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但由于目前PG发病率低,诊疗相对困难,这些疗法均缺乏较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仅能为部分难治性患者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3 结语
PG是一种系统性免疫炎症性疾病。现有研究表明,包括MEFV、PSTPIP-1、NOD2、Ptpn6等多种自身炎症性基因的突变、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补体系统功能缺陷以及细胞因子级联反应均可能在其发病中起重要作用。深入探讨PG遗传因素基础及免疫系统紊乱的发病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为PG的准确诊断及个体化治疗提供更清晰明朗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