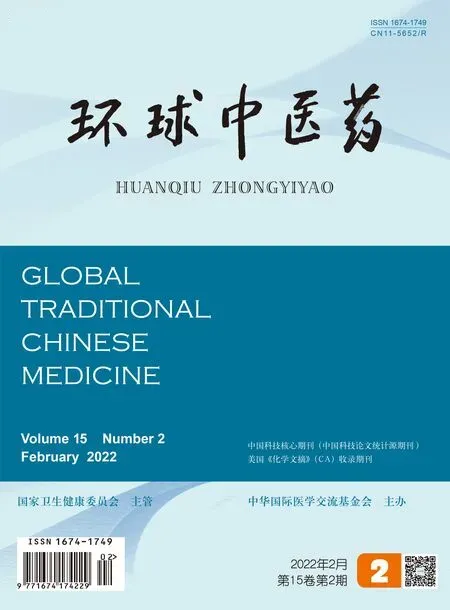袁红霞教授基于“中和平衡”思维治疗脾胃病经验
2023-01-02郭孝伟耿强
郭孝伟 耿强
基金项目: 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20171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6M601236)
作者单位: 300193 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郭孝伟(硕士研究生)];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耿强)
作者简介: 郭孝伟(1993- ),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男科临床研究。E-mail:guoxiaowei20131993@163.com
通信作者: 耿强(1980- ),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男科临床研究。E-mail:gengni1980@163.com
袁红霞教授是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第二批天津市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天津市名中医。袁红霞教授注重“读经典,做临床”,尤其擅长经方的临证应用,形成了经方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及相关内科疑难杂症的特色与优势。
《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征的哲学思想,既是治国安邦的法宝,也是治病救人的准则[1]。《黄帝内经》也说:“因而和之,是谓圣度。”脾胃居中焦,内宅中和之气,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与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运一纳,一升一降,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共同维持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和物质能量代谢,是人体生命活动平衡中枢。袁红霞教授深谙“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思想,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将“执中致和”作为治疗脾胃病准绳[2],通过斡旋升降、平调寒热、燮理润燥、把握动静、平衡阴阳达到脾胃纳运相助、升降相因、寒热相调、润燥相济的和谐与平衡。
1 升清降浊,化生气血
1.1 升脾阳,降胃浊,调畅中焦
《景岳全书》说:“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而脾胃居于中焦,互为表里,为气机升降的枢纽,使一身之气得以调畅,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升降相因,相反相成,共同维持正常的脾胃生理功能[3]。正如《黄帝内经》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气机升降是脏腑功能的主要表现。袁教授常说,脾胃之于人体犹如发动机对汽车的重要性,只有机器把汽油转化为动力,把尾气排出车外,汽车才能奔驰。脾摄取水谷精微上达心肺头面,布达运行于全身,胃腐熟水谷化为糟粕排出体外,全赖脾胃升清降浊正常。若脾胃升降失调,则清浊难分,以致中焦失衡。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所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吴医汇讲》亦云:“治脾胃之法,莫精乎升降。”袁教授临证注重升降理论在脾胃病的应用,针对痰湿重着黏滞,郁堵中焦,甚则化热,气血凝滞不通等特点,多采用通腑化湿清热法调畅胃气,临床多用黄连温胆汤、藿朴夏苓汤、旋覆代赭汤、升降散、承气汤等治疗以烧心、反酸为主要症状的胃食管反流病;针对脾阳不升导致的头重如裹、眩晕乏力、少气懒言等症,多用补脾升清法来升散脾阳,临床常以葛根汤、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进行治疗。同时袁教授深谙升降理论,于升清剂中少佐通降,于通降药中佐以升散,权衡升与降,使升中有降,降中见升,升降相因,气机调畅[4]。常用升麻与枳壳以补中益气,桔梗与牛膝以活血化瘀,菖蒲与厚朴以化湿降浊,葛根与黄芩以清肠止泻。
1.2 疏肝气,降肺气,调畅气机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土疏泄,苍气达。”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有利于中焦脾土的升发,同时反映肝为罢极之本,刚脏主动、主升的特点,是维持肝脏本身及其他各脏腑功能协调的保障,对各脏腑经络之气升降出入协调有序,平衡有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学海《读医随笔》道:“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借肝胆之气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一则通过调畅全身气机有助于维持脾胃升清降浊功能,二则调畅中焦脾胃之气的升降,促进脾胃消化吸收功能正常运转而达到升清降浊之用。《灵枢·邪客》有言:“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诸气皆统于肺,肺主治节,主一身之气并参与宗气的生成。脾胃运化水谷精气与肺吸入天地之清气合而为宗气,再加肾所藏之先天之精气共同组成一身之气,通过肺之宣发肃降,有节律呼吸,调节全身气机。又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肃降有助于大肠腑气之通畅,浊气畅通,则清气更能输布上达头面。因此,肝体阴用阳,肺宣肃有节,共同调畅气机,使一身之气升降有常,脾胃消化吸收功能正常发挥。
《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中提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袁教授认为调节肝气疏泄有轻重缓急之分,对久病所致情绪不畅者喜用轻灵馨香之花类药来醒脾疏肝、调畅情志,常用玫瑰花、绿梅花、佛手花、凌霄花之品疏肝和胃,调畅气机;对肝气不能正常升发者喜用根茎叶类之柴胡、香附、陈皮、青皮、合欢皮、川芎、当归、白芍等疏肝理气、柔肝缓急;对肝气疏发太过导致情绪急躁易怒者喜用代赭石、龙骨、牡蛎等沉重之品重镇安神;对于肝气升发太过导致肝气犯肺、犯胃者通过肃降肺气来疏泄肝气,进而斡旋中焦脾胃之气,临床常用龙胆泻肝汤、连朴饮、清金化痰汤、茵陈五苓散等疏肝降肺、和中理脾。
2 寒热为纲,温脾清胃
2.1 寒温并用法
《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曰:“阳道实,阴道虚。”脾为太阴,其气易虚,虚则易生寒;胃为阳明,感邪易实,实则易化热。脾胃一脏一腑,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往往出现脏腑同病,寒热错杂之证[5]。因而治疗上以寒热并用为基本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为治疗寒热证的治疗大法。然单用辛温芳香之剂则有助热化燥之弊,纯用苦寒清热又有损阳伤气之嫌。临床遵《伤寒杂病论》寒热并用之理论施法于临床,如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黄连汤、大黄附子汤、乌梅丸等。万全在《幼科发挥》中主张:“脾喜温而恶寒,胃喜清而恶热,用药偏寒则伤脾,偏热则伤胃也。制方之法,宜五味相济,四气俱备可也。”针对脾胃的生理特点,袁教授在治疗脾胃病方面将寒热并用的和中思想应用于药物加减配伍,处以寒热相调药对进行配伍使用,如黄连与干姜、黄芩与半夏、黄连与吴茱萸、黄芩与生姜、黄连与肉桂、石膏与细辛、柿蒂与丁香、大黄与附子等。
2.2 温脾散寒法
《内经》云:“饮食不节,疾生于肠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过度饮食和饮食偏嗜成为目前脾胃病多发的主要因素。而食物外有生冷热烫之别,内有寒热温良之性,袁教授通过多年观察发现,当代之人多以快生活节奏为显著特点,所以饮食多寒凉,穿着多单薄露体,体质多虚寒,而寒凉之物易伤脾胃阳气,故久而久之可致胃痛、泄泻、痰饮、痹病、虚劳等病证。此证以中焦阳气衰退,气化无权,失于温煦为主要特点,临床常见脘腹冷痛、四肢不温、形寒怕冷、久泄便溏、面白无华、舌淡胖或齿痕、苔白滑、脉沉迟无力。故袁教授对于典型以虚寒为辨证要点的病证采用温中散寒、健脾益气的治法,对症轻者,以大枣、灶心土、生姜、饴糖等偏温润之品补益脾胃;对症重者,以干姜、附子、肉桂、吴茱萸等偏温热之品温中散寒。
2.3 清胃泄热法
针对脾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特点,内热又分实热和虚热。明代王伦《明医杂著》说:“胃火愈旺,脾阴愈伤。”对于疾病初期,胃火炽盛,内热以实热为主,袁教授喜用生石膏、知母、黄芩、黄连、栀子等苦寒、咸寒之品清泻三焦之热;对于疾病后期,久病热伤津液,阴液不足,阴虚生内热,以虚热为主,袁教授喜用沙参、麦冬、玄参、生地、玉竹、芦根、天花粉等甘凉清热之品滋阴清热,从而使胃热得清,阴液恢复。
3 刚柔相济,以润为要
脾胃二脏,坐镇中州,一阴一阳,喜恶相反。脾为阴土,喜燥恶湿,多宜甘温之性以助其升;胃为阳土,喜润恶燥,多宜甘凉之性以助其降。《临证指南医案》曰:“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则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故也。”脾湿的健运有赖于胃阳的温煦,胃燥的受纳又依凭于脾阴的滋润。胃柔润顺降,脾刚燥升发,二者刚柔并济,相互为用,保证了胃纳脾运的正常运行。
袁教授认为,临床针对久病气滞胃痛者,不可再行大剂量疏肝理气之品,因宣通理气药大多辛香温燥,燥属阳、属刚易伤阴,要注意润养胃腑,善于顾护阴津,《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但气之所以滞,本由液之不能充,芳香气药,可以助运行,而不能滋血液。且香者必燥,燥更伤阴,频频投之,液尤耗而气尤滞,无不频频发作,日以益盛,而香药气药,不足恃矣。”袁教授临床常用麦门冬汤、益胃汤、竹叶石膏汤、沙参麦冬汤等方剂来治疗胃阴不足之胃痛,对于老年人因久病营血亏虚者喜用白芍、乌梅、石斛、芦根、玉竹、黄精之类来滋养胃阴。
4 动静结合,以动带静
4.1 静养调神,运动调身
《脾胃论》曰:“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作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需时时顾护。基于《黄帝内经》“动则生阳,静以养神”理论,袁教授认为合理的肢体关节活动和锻炼能促进脾胃气血的流通,有助于运化水谷精微,使脾胃得到滋养。《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因此,针对脾胃病寒热虚实错杂、易调难养的特点,袁教授提倡治疗应“动静结合,以动带静”,急性期以静养为主,配合微量运动;慢性期以运动为主,配合规律作息。并推崇中国古代功法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锻炼,认为其功法动作柔和缓慢,柔中带刚,圆活连贯,松紧结合,动静相兼,神形合一,气寓其中,可以通过调理身心,使精、气、神人身三宝达到最佳状态,既能使气血畅通,也能增强气血的运行,起到阴阳互补、阴平阳秘的养生功效,使机体处于稳定、和谐的健康状态之中[6-10]。
4.2 静药调形,动药调气
组方用药方面,袁教授认为药有四气五味、动静阴阳的特点,故配伍调和宜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强调动药与静药相结合,动中有静以防脾胃阴精之妄动耗散,静中有动以助脾胃阳气之蓬勃生机。具体表现在滋阴药配伍补阳之品以助运化,如熟地配砂仁、附子;补气药配伍理气之品以消庸滞,如黄芪配陈皮、佩兰;发散药配伍收敛之品以防耗散,桂枝配黄精、五味子。对于久病气血瘀滞者,扶助正气时不忘祛邪,常常于补气生血之品中配伍搜剔通络之虫类药,如人参配九香虫、黄芪配地龙、红景天配土鳖虫等。
5 阴阳相衡,以平为期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又言“生之本,本于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脾胃亦本于阴阳,脾在脏为阴,胃在腑属阳。脾主运化而升清,以阳气用事,体阴而用阳;胃主受纳而降浊,以阴津为养,体阳而用阴。正如《临证指南医案》道:“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若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胃属土居于中焦,位于五脏之中位,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纳一运,一升一降,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共同维持着人体物质和能量代谢得协调平衡。《金匮翼》说:“土具冲和之德,而为生物之本,冲和者不燥不湿,不冷不热,乃能生化万物,是以湿土宜燥,燥土宜润,使归于平也。”
袁教授秉承《温病条辨》“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宗旨,顺应脾胃冲和敦厚之生理功能,以平衡中焦阴阳为纲[11],临床在治疗脾胃阴阳不和之证时,根据阴阳互根互用原理,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在温补脾胃之阳方药中适量加入滋补脾胃之阴的药物,在滋养脾胃之阴方药中适量加入温补脾胃之阳的药物,如此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阴得阳助而泉源不竭。例如胃脘痛临床多用理气止痛之品,而此类宣通行气药多辛温香燥,易伤脾胃之阴,可配伍阴柔滋养之药以制其弊,顾护阴津,如芦根、茅根、石斛、乌梅之类;而胃津亏损需柔润甘凉之品酸甘化阴,但难免滋腻碍脾,阻滞气机宣畅,故少佐辛温之药运药和中,平衡阴阳,如枳壳、桂枝、陈皮、佛手之类。再者,胃不和则卧不安,精神心理因素是脾胃病重要致病因素。相反,长期脾胃不和者多伴有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袁教授调理脾胃时常常关注患者情志和睡眠情况,重视情志和心理调节,认为此多由阳不入于阴而成阴阳失和之态所致[12],选方多选交泰丸、黄连阿胶汤、酸枣仁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之类调和阴阳,同时通过劝导、安慰、鼓励来解除患者心理负担,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
6 典型验案
患者,男,62岁,2019年5月16日初诊。患者胃癌术后1年,术后多次行化疗,具体用药、剂量不详,伴烧心、反酸2月余,平素性情急躁。胃镜及病理活体检查结果显示:贲门胃癌出血、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腺体重度肠化,中度非典型增生。CT诊断:胃癌伴肠化、腹腔淋巴结肿大考虑转移、胸下段淋巴结肿大、右侧胁裂结节灶。患者神清,面色萎黄,周身乏力,时有反酸烧心,胸骨后不适,纳呆,胃脘胀满,嗳气不畅,口干苦,喜温饮,夜寐欠安,大便2~3日一行,小便调,舌淡黯、苔白腻,脉细数。中医诊断:胃痞,辨证: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证,治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之法,方用旋覆代赭汤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处方:旋覆花包煎15 g、代赭石5 g、柴胡15 g、黄芩10 g、红参30 g、半夏10 g、茯苓15 g、桂枝6 g、生龙牡各30 g、酒大黄6 g、生白术30 g、炙甘草15 g、枳壳15 g、黄连20 g、吴茱萸3 g、生薏苡仁30 g、仙鹤草30 g、生姜8片、大枣5枚。7剂,每日1剂,水煎服,早晚各一次。
2019年5月23日二诊:患者神清,面色转佳,乏力缓解,反酸烧心较前明显缓解,胃脘胀满减轻,食欲渐增,口苦减轻,夜寐易醒,多梦,精神情绪紧张,大便仍干,舌淡胖、苔白,脉细濡,故以初诊方减去桂枝,茯苓改茯神30 g,黄连减至10 g,生白术增至50 g,酒大黄加至10 g,加合欢花15 g、佛手花15 g。7剂,煎服法同前。
2019年5月30日三诊:患者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乏力感消失,面色红润,无胃胀、反酸、烧心等症,食欲大增,夜寐较前明显改善,大便正常,每日一行。效不更方,继续以本法调治,服用汤药至2020年1月,诸症未见明显不适,后为进一步巩固疗效做成丸药善后调理。
按 本案患者处于胃癌术后疾病缓慢进展期,同时患有重症胃食管反流病多年,经多种西医现代化手段治疗效果不佳,为求中医治疗前来就诊。初诊时根据患者既往病史和刻诊情况分析,患者病位在脾胃,平素急躁易怒,肝气不舒,气机不畅,郁而化火,横逆犯胃,故时有反酸烧心、嗳气不舒、胃脘痞满等症状。加之本病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久病必虚,又因术后食欲较差,脾胃虚弱,气血乏源,故见面色萎黄,周身乏力,精神萎靡等脾胃气虚之象。袁教授认为本病系脾胃升降失常、气血失和、寒热失调、阴阳失衡所致,以脾胃气虚为本,反酸为标,治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之法,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疏肝和胃、抑木扶土,旋覆代赭汤降逆止呕、和胃制酸,左金丸清肝和胃、平调寒热。方中代赭石质重味苦性寒,寒以清热,苦以燥湿,质重以降逆;旋覆花味甘、辛、咸,性温,辛以温通宣散,咸以消痰软坚,二药相配,宣降相因,相须为用,斡旋气机;柴胡、黄连、黄芩、大黄清泻肝胃郁火,少佐吴茱萸、桂枝调达肝气、开解郁热;生姜、半夏和胃降逆以化痰湿;白术、枳壳健脾燥湿、益气助运,大便秘者生白术尤良;茯苓、生薏苡仁健脾益中、甘淡渗湿,失眠者茯神效佳;党参、大枣、甘草、仙鹤草健脾益气以补中。诸药相伍,升降相因,寒热平调,润燥相济,阴阳相衡,共奏中和平衡之功效。二诊诸症减轻,但考虑患者睡眠、大便仍未明显改善,遂去辛温香燥之桂枝,加量生白术、酒大黄以通便,茯苓改茯神助睡眠,因精神情绪紧张加轻灵之合欢花、佛手花疏肝调情畅气机。三诊疗效显著,效不更方,守原方继服,汤药荡其前,丸药缓其后,对于病情稳定后的患者,不能突然断药,要逐步善后调理以固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