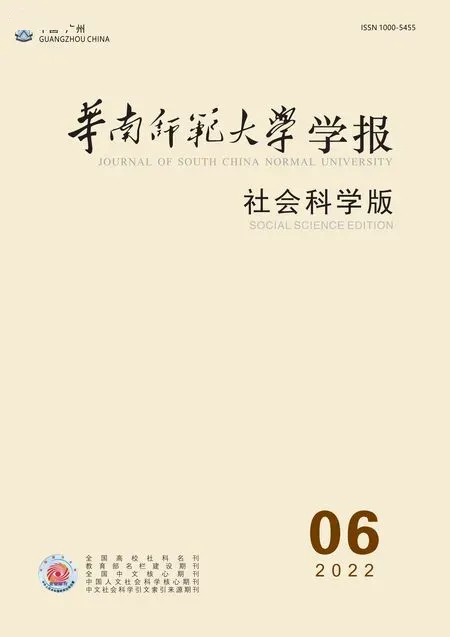《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是怎样传钞流转的
——瞿兑之传承近世珍稀文献的重要一页
2022-12-31韩策
韩 策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清道光末年两江总督李星沅的日记,涵盖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爆发前的关键十年(1840—1849),记载详赡,描绘如生,尤其难得的是“质直无所讳”,诚为“治近世史者之瑰宝”。(1)觉园老人(瞿觉园):《李星沅日记》“钞本序”,载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1页。1987年,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藏《李星沅日记》钞本由袁英光、童浩二位先生整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关注。(2)在袁英光、童浩整理版之前,陈左高先生曾辑录上海图书馆藏《李星沅日记》钞本中有关上海史事的内容,收入《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07-219页。评介《李星沅日记》的有: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前言”第1-3页;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72-73页;何汉威:《〈李星沅日记〉中所见道光朝后期的政治社会》,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5),1998,第311-342页;何汉威:《读〈李星沅日记〉——兼论李星沅其人》,载《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8,第305-352页;何沛东:《一座有待发掘的史料宝库——读〈李星沅日记〉》,《城市学刊》2015年第5期。其中尤以何汉威两文讨论最详尽深入。2022年9月6日,笔者在中国知网和读秀检索“《李星沅日记》”词条,分别有186和139项记录。后来,笔者在沈津编著的《顾廷龙年谱》中惊喜地看到,上图钞本及其入藏上图的曲折可能与大名鼎鼎的瞿兑之(宣颖)极有关系。2019年,承蒙马忠文老师之约,给《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撰写几部日记的提要,有幸发现该丛刊所收《李星沅日记》,原来正是上图钞本所据之稿本。
无独有偶,《道咸宦海见闻录》由《张集馨年谱》及附录张集馨残余日记等组成,1981年由杜春和、张秀清二位先生点校出版,被誉为自订年谱版的“官场现形记”,其后多次重印,印数甚大,各种引用和讨论极多。(3)杜春和、张秀清点校:《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该书2014年第6次印刷已印至57 700册。2022年9月6日,笔者在中国知网和读秀检索“《道咸宦海见闻录》”词条,分别有高达1 126和1 091项记录。《张集馨年谱》大抵系据日记写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钞本流传,1955年钞本入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前身);杜、张二公的整理本即以近代史所藏钞本为底本,再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而成。(4)杜春和、张秀清点校:《道咸宦海见闻录》,“编辑说明”第1-3页。其实,此钞本正是瞿兑之据稿本抄录的,并于1945和1948年分别在上海的杂志中撰文介绍(详下文)。1948年,沈云龙(后以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享誉学林)为瞿兑之的文章所吸引,曾辗转借阅这一钞本,然后又抄录了一部分。沈先生去台湾后,曾于1967年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张集馨及其自订年谱》一文,后收入《近代史料考释》一书。(5)沈云龙:《近代史料考释》(第二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1-42页。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67年第10卷第4、5期。
有意思的是,李星沅和张集馨年岁相仿,科名相近,也有交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十二日,《李星沅日记》有云:“新粮道张椒云(集馨)见,人明爽。” 张集馨为李星沅带来了协办大学士陈官俊透露的道光属意于李星沅的消息,以及穆彰阿讽刺前任陕西粮道方仲鸿“只有入帐无出帐”的雅谑。随后两人也多次见面。(6)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第598、599、601、603、609、610页。整理本作张树云,已据稿本改。《张集馨年谱》亦称:“余初到陕,李石梧(星沅)为中丞,后调江苏,手书问况,余复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7)同②书,第80页。更重要的是,《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多有内容交集,比如山西的武备废弛,甘肃的钱粮腐败,四川的流民和刑狱,陕西督粮道的无穷应酬,琦善、桂良、讷尔经额等旗人高官的形象,地方官与军机处及京官的频繁互动等,可以两相参照。(8)何汉威的《读李星沅日记:兼论李星沅其人》一文已有所论述。
如此互有关联而为大家熟知并广为利用的两种重要文献,均与瞿兑之有意想不到的巧妙联系,实为读书人与日记传钞保存的一段佳话,也反映了瞿兑之的学术文化旨趣。其在1949年前后的售让,也是近世珍稀文献流转的有趣案例,折射出剧变时代读书人和珍稀文献的曲折命运。有鉴于此,本文以《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为例,讨论瞿兑之与近世珍稀文献传钞流转的问题。
二、《李星沅日记》的传钞流转
李星沅(1797—1851),湖南湘阴人,字子湘,号石梧,谥文恭。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授编修。十五年(1835)提督广东学政。十八年(1838)简放陕西汉中知府,旋升河南粮储盐法道,历官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授江苏布政使。二十二年(1842)擢陕西巡抚,后调江苏巡抚,升云贵总督。二十七年(1847)调两江总督。二十九年(1849)因病开缺回籍。短短十余年,由翰林院编修洊至两江总督,确乎“主恩非常”,升迁之速,“为近今所未有”。(9)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第669页。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廷起李星沅于家,授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翌年四月十二日病逝于广西武宣军中。有《李文恭公遗集》四十六卷,另与夫人郭润玉酬唱诗,编为《梧笙唱和初集》二卷。
《李星沅日记》手稿本共二十一册,行草手书,偶有涂改。前十三册用“读书延年堂”朱丝栏稿纸,后八册用“芋香山馆”朱丝栏稿纸,均四周双边,单上鱼尾,半叶八行,行字不等。每册内封均有李星沅亲笔行楷题字,比如“勿自弃室庚子日记”“勿自弃室辛丑日记”“勿自弃室壬寅日记”“勿自弃室癸卯日记”“勿自弃室甲辰日记”“勿自弃室乙巳日记”“勿自弃室抚吴日记”“勿自弃室督滇日记”“勿自弃室两江日记”,右侧题本册起止时间。钤盖之印章,除“星沅”“石梧”“芋香山馆”明显是李星沅的外,“勉为国家梁栋之材”,“勿失书生本色”,“勿自弃”,均源于道光皇帝勉励李星沅的口谕和朱批,(10)道光十八年(1838),李星沅放陕西汉中府,道光召对,有“岂不是国家梁栋之材”的褒奖;旋升河南粮储盐法道,十九年署河南按察使,谢恩折奉朱批:“勿失书生本色”,“勿自弃之”云云。李概等:《李文恭公行述》,载《李文恭公(星沅)遗集》,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8页。自然也是李氏的印章。所以,从手迹、稿纸和印章综合判断,此为《李星沅日记》手稿无疑。每册外封左上均题“李文恭公日记”(篆书),左下皆题“庚申日长至,易宗鹄署”(楷书),右上均题“共二十一册”,其下分别标一至二十一字样,以为次序。易宗鹄也是湖南人,他称李星沅之孙李辅燿为世丈,曾为李辅燿的家庭教师。(11)易宗鹄:《玩止水斋遗稿序》,载李崧峻主编《李辅燿诗词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167-170页。“庚申日长至”为1920年夏至,或可推知《李星沅日记》手稿在这时重新装订过。李辅燿已于1916年辞世,《李星沅日记》手稿本即由李辅燿子孙保存。
《李星沅日记》手稿本起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一日,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二十三日止。上海图书馆藏《李星沅日记》钞本二十册,有“觉园老人”序,称“兹于假阅之余摘抄一过”。(12)觉园老人(瞿觉园):《李星沅日记》“钞本序”,载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第1页。它的起讫时日与稿本日记完全一致。稿本日记起首有李星沅自述一段,钞本也照录无遗。可见觉园老人钞本即是据此稿本摘抄一过。钞本保留了一份珍贵副本,后入藏上海图书馆供读者阅览,继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记标点本的底本。而且,钞本序称“行款均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阙疑焉”,行事甚为郑重。故必须说,“觉园老人”不仅是李氏功臣,更是近代文献功臣。那么,其人到底为谁呢?
对此,陈左高、袁英光及童浩诸先生整理介绍钞本日记时都未注出姓名。现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湘阴李星沅氏日记钞》的“出版”项,已明确标为“瞿觉园,民国(1912—1949)”。(13)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線善T47308-17”。2012年出版的《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也将《李星沅日记》的版本信息标为“清瞿觉园抄本20册”,似即据上图的藏书信息注录。(14)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岳麓书社,2012,第64页。或许陈左高诸先生早已知道觉园老人姓瞿,只是当时没有明说。
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1951年9月30日的日记显示,觉园老人与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著名学人瞿兑之密切相关。该日日记云:“兑之来,以兄弟钞录之《李星沅日记》廿本求售,索四百万,无从协商矣。”(15)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1,第585页。沈津最先引过此条,有云:瞿兑之来,以兄弟钞录之《李星沅日记》廿本求售,索四百万,“无从协商矣”。见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88页。由“兄弟钞录”的说法看,觉园老人(瞿觉园)应是瞿兑之的兄弟辈。
据李辅燿之孙李崧峻说:“早在1950年,李青崖就在李庸、李亦怀两位长辈的支持下,将由他保存的高祖《李文恭公日记》手稿,亲交郭沫若先生转赠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6)李崧峻:《留得春风属后生》,2022,自印本,第208-209页。此书承马忠文老师赐赠,特致谢忱。查日记稿本每册正文首页右下角均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印,页脚右侧均有“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戳记,与李先生的说法可以大体印证。李庸(相纶)、李亦怀(相慈)是李辅燿的次子和三子,李青崖之父李相钧是李辅燿长子。李青崖是李辅燿长孙,清末民初留学比利时,后以翻译莫泊桑小说著称。瞿鸿禨、余肇康和李辅燿均是同乡世交,晚年仍书信往来不断。(17)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燿日记》第10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63、191、226、284、317、334、395、406、536、641、650页。1914年,受李辅燿之托,瞿鸿禨还曾致书其门生张缉光(少熙),转托张氏向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省之)介绍,为李青崖谋陇海铁路翻译差使。(18)《李辅燿日记》第10册,第175-176、226页。李辅燿称李青崖为丙孙,殆生于光绪丙戌年(1886)。李辅燿听说张缉光与施肇曾“有交”,故有此托。李青崖随后即在陇海铁路任职。张缉光既师事瞿鸿禨,又曾教授瞿鸿禨之子瞿宣治(希马)等。参见韩策:《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余肇康是瞿宣治的岳父,他在七十之年仍为李辅燿的诗词集作序,也看过《李星沅日记》。(19)余肇康:《玩止水斋遗稿序》,载李崧峻主编《李辅燿诗词集》,第163-166页。故瞿兑之、瞿觉园兄弟有机会借阅李青崖珍藏的《李星沅日记》稿本。考虑到李青崖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京和上海,1950年9月出任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20)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第165页。故有理由推测,瞿氏兄弟借阅、抄录《李星沅日记》的时间,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旅居沪上之时。抄录工作主要由瞿觉园完成,瞿兑之似也有所参与,顾廷龙所谓“兄弟钞录”的说法,或可作此理解。(21)1951年1月26日,瞿兑之兄弟曾拜访顾廷龙。当日顾廷龙日记有云:“兑之昆仲、闻韶先后来。”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560页。
查瞿宣颖之兄瞿宣朴有羸疾,精神恍惚,其三兄瞿宣治(希马)于1923年去世,均无可能参与抄录。而其从兄瞿兆奎,亦名瞿汉,派名宣绩,字仙槎,在北京做官,(22)《长沙瞿氏家乘》卷3,1934,铅印本,第15b页。20世纪30年代与瞿兑之同寓北京。(23)瞿宣颖:《天逸道人存稿序》(1933),载《长沙瞿氏丛刊》,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1页。同时,瞿汉也是有功力的学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写湖南地方志提要。(2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册,齐鲁书社,1996,“提要撰者表”第3页;第33册,第235-329页。据田吉《瞿宣颖年谱》,瞿兑之于1946年南下流寓上海。当年7月7日,瞿兑之确曾参观上海合众图书馆。(25)田吉:《瞿宣颖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12,第175页。顾廷龙日记1946年7月7日有云:“聂云台子偕伪华北编译馆馆长、《中和月刊》主编瞿兑之来参观。”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464页。此后瞿兆奎当亦来沪。瞿兑之就称:“岁戊子,宣颖与从兄兆奎皆旅居上海。”(26)田吉:《瞿宣颖年谱》,第179页。瞿兆奎生于光绪九年(1883)七月初七日,(27)《长沙瞿氏家乘》卷3,第15b页。长瞿兑之11岁,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在65岁上下,自称“觉园老人”不无恰当。瞿兑之此时改号“蜕园”,其兄自号“觉园”,亦颇相称。所以,觉园老人(瞿觉园)有可能是瞿兆奎(瞿汉)。
前引《顾廷龙日记》表明,1951年瞿兑之为钞本《李星沅日记》索价四百万(相当于后来的四百元),因价昂而未能成交。查1952年瞿兆奎自沪返湘,瞿兑之有诗赠之。(28)同②书,第190页。当时瞿兑之在沪上卖文为生,也不时变卖书籍文献。1947年,他就在求售《张集馨年谱》(详下文)。1951年9月30日求售钞本《李星沅日记》,或即是为瞿兆奎筹措回湘盘费。据新出《杨树达日记》,1953年3月29日,瞿兆奎(瞿汉,仙槎)在长沙拜访过杨树达。(29)杨柳岸整理《杨树达日记》,中华书局,2021,第130页。日记注释:他们抗战前一道在北平编纂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53年,《李星沅日记》钞本终于还是入藏上海合众图书馆。当年9月,上海合众图书馆工作简报“采编方面”有云:“本月收购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前清曾几任督抚的湘阴李星沅自道光二十年至廿八年的日记钞。他曾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颇有些当时的史料。其他有关朝政掌故、地方情形,尤为丰富。”(30)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附录《一个图书馆的发展》,第764页。这就是后来陈左高、袁英光、童浩诸先生所见之觉园老人钞本《李星沅日记》。
袁英光、童浩二位先生的整理本为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居功甚高。但因当时仅能根据钞本,且限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条件,不完善之处尚多。张积曾撰文献疑纠误,多有匡正,但也偶有推测失误之处。(31)张积:《李星沅日记标点献疑》,《文献》1993年第4期;张吉、张言梦:《李星沅日记标点纠误》,《集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期。现据稿本可以一一校定,俾成善本。略举二例,以概其余。整理本第15页“与人交出于知识”,知识应为“至诚”。整理本第18页“季仙九同年(芝昌)得浙江提学官,运差□,近今词馆中无出其右者”。张积先生献疑曰:“官字应属下,空缺处疑作可。”(32)张积:《李星沅日记标点献疑》,《文献》1993年第4期,第224页。而稿本为“季仙九同年(芝昌)得浙江提学,官运差运,近今词馆中无出其右者”。盖浙江学政为差,故云“差运”。
此外,抄错、漏抄、不抄的情况都在所难免。这也是摘抄本的常态。比如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正文及眉批,均有漏抄者,大抵为读书评论之类。稿本中多有诗文,然觉园老人常不抄诗,记作“诗不录”。而整理本也照写“诗不录”三字,实稿本所无。稿本为21册,钞本则20册,钞本原序称“行款均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阙疑焉”(33)觉园老人(瞿觉园):《李星沅日记》“钞本序”,载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第1页。,之所以钞本少1册,殆即因摘抄且不录诗之故欤?
三、《张集馨年谱》的传钞流转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字椒云,号时晴斋主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官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多省,旋起旋仆,官至署理陕西巡抚,曾佐向荣、胜保军幕,见闻甚广。相较于《李星沅日记》稿本、钞本长期深藏北京、上海两地,知者有限,《张集馨年谱》的巨大价值则在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本出版前的几十年已多为人知。
1967年,沈云龙在著名的台北《传记文学》发表《张集馨及其自订年谱》一文,连载两期。他介绍缘起道:“在三十七年(1948)八月改革币制的时候,上海马路边书报摊有一本名叫《好文章》的小册子出售……包括丰子恺、胡适之、林语堂诸名家的旧文在内。其中第一篇题名《最早的一部官场现形记》,作者署名‘朱菴’,主要在介绍张集馨的自订年谱,认为这是一部珍贵的手稿,将作者一生所经历的官场事态,毫无顾忌写将出来,绘影绘声,简直比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要穷形尽相。我阅过该文以后,引起极大的兴趣。不久,由于武进刘厚生(垣)丈的关系,辗转设法获睹这部张集馨自订年谱的原稿,本为七卷,已缺失两卷,而且仅写到咸丰十年他六十一岁任江西藩司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劾去职时止,编次尚未完全。作者并不为传统的年谱的体裁所拘束,泰半用日记的方式来写,文字不免琐屑繁冗,但确是真实可信的直接史料。所以我又借钞了一部分,留存箧中。”(34)沈云龙:《近代史料考释》(第二集),第1-2页。引文黑体为笔者所加。《张集馨及其自订年谱》后来也收入沈云龙所著《近代史料考释》中,读者应该不少。
引起沈云龙“极大的兴趣”的那篇题名为《最早的一部官场现形记》的长文,收入《好文章》杂志1948年第1期第1-24页,署名“朱庵”。该文感慨清代官书之外,揭露各级官场实在“内幕”的文献不仅数量太少,也没人搜辑整理,故真正好的清史便不容易做出来。他说:
描写清末官场情态之记载,大约以《官场现形记》为集大成,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也与之相辅……我因之想到有清一朝官治局面下之形形色色,都只在若有若无之间,供人想像,而实在的文献竟没有人搜辑整理,年深月久,恐怕着手更不易了。嘉道中人尚有些作诗作词作对联来讽刺的,而笔记中亦往往有些零星的资料,但是这些还是不彀。我们愿意知道的是什么呢?比如在京各部书吏舞弊的情形,各仓库丁书舞弊的情形,工部、内务府承办大工的情形,在外州县衙门日常事务之运行,武营之陋习,幕友长随之衣钵,河漕盐之弊端,捕皁班馆之黑幕等等。这种情形,都是当时的风气,以种种因缘酝酿而成的。在正式的官书上,决找不着痕迹,而这班身历其境的,也绝不会笔之于书,信今传后。所以从纯正的史学立场来说,将来缺乏这种根据便不容易有一部真正好的清史来。
然后,作者下一转语,开始介绍新发现的《张集馨年谱》手稿。他说:
不料最近忽然在破书丛里发见一部珍贵的手稿,将作者一生所经历的官场事态毫无顾忌写将出来,而且琐琐屑屑,绘影绘声,简直比《官场现形记》还要穷形尽相。这位作者张椒云集馨,是嘉庆年间生人,从道光中叶出任道府,直至光绪初年才死。他的仕履又非常丰富,所历的时代又非常复杂,其价值又不仅是光绪年中《官场现形记》所可比拟的……他的际遇也可算非常坎坷,所以一腔牢骚发泄在他这部自订年谱之内。不幸编次并未完全,刚刚编到江西藩司时为止,就绝笔了。本是七卷,其中又缺掉二卷,如今仅存这一点,却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宝贵资料。在别人一定不肯说的,而他却毫无忌讳,不拘定普通年谱的体裁,一半日记式的拉拉杂杂写来,很有点像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这样的书,听其湮没,实在可惜极了。(35)朱庵(瞿兑之):《最早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好文章》1948年第1期。
比较沈云龙和“朱庵”的记述,可知沈先生对《张集馨年谱》的介绍实本“朱庵”之文。那么“朱庵”究竟是谁呢?我们知道,瞿兑之有一别号“铢庵”较为有名。(36)早在1935年,瞿兑之在《申报月刊》连载的《杶庐所闻录》结集出版时,署名“瞿兑之”,而俞颂华的序言即称“吾友铢庵”,瞿兑之自序也署“铢庵居士”。故“铢庵”一号当为读者所知。瞿兑之:《杶庐所闻录》(甲集),申报月刊社,1935,俞颂华“序”第1页,“自序”第1页。从该文所显露出作者的清史底蕴、兴趣所在和行文风格来看,这里的“朱庵”很可能正是瞿兑之,类似他将“兑园”改号“蜕园”。或许因有种种嫌疑,他在抗战胜利后尽量低调,甚至隐姓改名。
事实上,《张集馨年谱》钞本确在瞿兑之手上。在发表《最早的一部官场现形记》一文前一年,瞿兑之就向上海合众图书馆求售《张集馨年谱》。《顾廷龙日记》1947年4月22日有云:“访菊老(张元济),为瞿兑之之《张椒云年谱》,价太昂,不能购,面复之……瞿兑之来阅书,改名铢安。”(37)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480页。也可能因求售未成,瞿兑之遂写一介绍长文先赚稿费,同时也为《张集馨年谱》再做宣传。
进言之,这并非瞿兑之第一次撰文介绍《张集馨年谱》。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已经用“铢庵”的笔名,在上海《杂志》月刊发表《剪韭谈》一文。其中“官场现形”部分,即在介绍新发现的《张集馨年谱》。他说:“近见道光年间《张集馨手定年谱(未刊本)》中有几段极珍贵的史料,都是官场受贿的事,向来不能形于笔墨的。”又说:“张氏年谱缕述道咸两朝官场之形形色色,有甚于《官场现形记》者,从来还没有这样大胆公开的记载,实为社会史料之珍品。”(38)铢庵:《剪韭谈》,《杂志》1945年第15卷第3期。《张集馨年谱》的独特文献价值,正是瞿兑之特别关注的兴趣所在。
根据《李盛铎藏书目录》,尤其是《道咸宦海见闻录》的编辑说明,读者后来都知道《张集馨年谱》手稿先在李盛铎藏书中,后来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39)编辑说明云:“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李氏(盛铎)藏书目录》中查到这部书。全书一函五册,封面题《椒云年谱》一二五六七册(缺三四册)……判定北大收藏的本子是作者的亲笔原稿。又将钞本和原稿本校对,发现钞本不仅掉字、句、段的地方很多,而且钞者随意增删的地方也不少。现在依照原稿本订正。”《道咸宦海见闻录》,“编辑说明”第1-2页。据栾伟平女士最近的研究,1940年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在汤尔和、周作人和钱稻孙的努力下,售给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至1942年木犀轩藏书全部入藏北大图书馆,并由吴丰培和华忱之做了整理编目。(40)栾伟平:《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瞿兑之与汤尔和、周作人、钱稻孙均相熟。1940年11月,教育总署督办兼国立北京大学总监督汤尔和去世后,瞿兑之(时名瞿益锴)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长兼任伪北大总监督。1941年3月,瞿兑之任华北编译馆馆长,钱稻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所以,瞿兑之有便利条件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木犀轩藏书。由前引他在1945年发表的《剪韭谈》中称“近见《张集馨手定年谱》”,可推测他大约于1944年前后在北大图书馆借阅《张集馨年谱》手稿,并抄录了一份。
同时,瞿兑之的好友、掌故大家徐一士也看过《张集馨年谱》。1947年,他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文章称:“集馨有自编《椒云年谱》,多珍贵之史料,未经印行,曾获睹其手稿。”徐氏这篇文章即利用《张集馨年谱》资料,介绍张集馨和桂良的恩怨及当时官场状况。徐一士也称赞《张集馨年谱》“写来穷形尽相,读之如读《官场现形记》,而《官场现形记》之写状,逊其深刻也”(41)徐一士:《张集馨与桂良》,《经世日报》1947年4月19日、4月26日、5月3日连载,均在第3版。。此外,瞿兑之的朋友刘厚生(垣)在1958年出版的名著《张謇传记》中,也提过《张集馨年谱》。他说:“我曾见到江苏仪征县人《张集馨自述年谱》的手钞本。对于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各省的吏治、军事、财政内容的腐化情形,叙述极为详细。”(4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影印版(据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4-126页。1949年,刘垣在上海开始集中搜集资料,1950年3月动笔写张謇传。他的主要资料来自上海合众图书馆及其后身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得到馆长顾廷龙许多帮助。(43)同上书,“叙言”第1页,“后记”第288页。刘厚生和瞿兑之也颇熟识。1950年5月24日,刘厚生约瞿兑之晚餐,即由顾廷龙作陪。(44)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538页。故刘厚生见到的“《张集馨自述年谱》手钞本”,当即是瞿兑之所藏之钞本。
沈云龙和刘厚生熟识,他之所以能看到《张集馨年谱》,即是通过刘厚生的关系而“辗转设法获睹”的。沈先生称他看到的“张集馨自订年谱的原稿”,恐怕不能理解为是原稿本,而实为瞿兑之所藏之钞本。所以,沈云龙应该知道此书从瞿兑之手上借来,而他感兴趣的“朱庵”就是瞿兑之。1967年他在台湾撰文介绍《张集馨年谱》的时候,也把这一段“因缘”写了出来。之所以没有点出瞿兑之的大名,或有不方便之处,想必也是出于好意。
前文已述,瞿兑之分别在1947年和1951年向顾廷龙主持的上海合众图书馆求售钞本《张集馨年谱》和钞本《李星沅日记》,均因价昂而未能成交。但1953年《李星沅日记》最终仍售让给上海合众图书馆,只是价格不明。《张集馨年谱》也在1955年辗转售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第三所),实价九十元。(45)佚名:《张椒云年谱提要》,载《张椒云年谱》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查阅《张集馨年谱》钞本时,承茹静女士、毕成先生费心帮助,特致谢忱。1981年《道咸宦海见闻录》的编辑说明有云:“一九五五年,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购到一部钞本的《椒云年谱》(十六开毛边纸本,上下册)。钞者在简短的提要中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于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46)杜春和、张秀清点校:《道咸宦海见闻录》,“编辑说明”第1页。这段编辑说明来自钞本《张集馨年谱》开头所附的一页钢笔书写的《张椒云年谱提要》。其首段云:
著者张集馨,在道光中叶由翰林出任知府。历任各省按察、布政使甚久,直到光绪初年方才身故,所以经历很丰富。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于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廿年来目睹之怪现象》等书。张氏写此书时,正当太平军还在与曾国藩激战的时代,手稿系张绝笔,以后就被曾贼参劾罢官,所以他对曾贼很有不满的话。张氏后人零落,此项残稿流落市上,为天津李牧斋所收,已缺其中一本,看纸色和字迹,的确是张氏亲手写的,现在这一部是借钞的。总之,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47)佚名:《张椒云年谱提要》,载《张椒云年谱》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这页钢笔手迹并非瞿兑之的笔迹。其中称曾国藩为“曾贼”,更非曾国藩外孙女婿瞿兑之的口吻。而钞本正文及天头朱笔注释,均系毛笔行楷,正是瞿兑之的笔迹,注释中称曾国藩为“曾文正公”,也正是瞿兑之的口吻。因此,这一提要或是卖书者(提要最后标明实价九十元)或是近代史所整理文献的前辈之手笔。但由于提要有云,“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于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廿年来目睹之怪现象》”,正是瞿兑之以前介绍文章中的用语,而且提要后面列举的种种史料价值之处,也正是瞿兑之以前文章中着重谈及者;所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钞本原有瞿兑之所写之提要,但后来卖书者或近代史所的前辈认为所写内容及瞿兑之其人不合时宜,(48)周一良先生1946年归国后,购于市场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页瞿兑之所作之序,就已被人撕去。周启锐整理《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第117页。故据瞿氏所写提要又改写了一份。
四、余论:瞿兑之与近世珍稀文献的保护传承
在摄影、复印普及以前,传钞实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献复制和保护方法。顾廷龙曾说:“解放前旧书店多,学徒亦多,有空闲时间,即令抄书。收得一本名人抄本或稿本,即令传抄,一化几本。”(49)顾廷龙:《致徐小蛮》(1994年8月18日),载《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第510页。当然,书店学徒抄录稿钞本,主观意图或在“商机”,而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传承的作用。不仅书店学徒经常抄录稿钞本,包括著名学人在内的诸多读书人,一生都花过许多时间和精力传钞文献。具体到近世珍稀的日记文献,曾国藩、李慈铭、翁同龢、王闿运、叶昌炽诸家大部头日记在清末民国时期陆续出版,风行一时。但因时局不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或欲出版而未能,或在藏家手中不易获见。(50)《江标日记》在20世纪40年代欲印行而未果。黄政:《江标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整理前言”第8页。《黄彭年日记》则其后人秘不示人。瞿蜕园(宣颖):《陶楼诗钞》“序”,朱启钤:《陶楼诗钞》“识语”,载黄益整理《陶楼诗文辑校》,齐鲁书社,2015,第546-548页。在此背景下,传钞日记也成为一种风气。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能静居日记》均有钞本。(51)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前言”第1-4页。顾廷龙曾费心抄录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52)顾廷龙:《忘山庐日记跋》,载《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第1007页。张元济也摘抄了《翁心存日记》,计划排印而未成。(53)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前言”第1-5页。书札的传钞亦然,著名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就是顾廷龙特意为上海合众图书馆“乞假录副”的。(54)顾廷龙:《艺风堂友朋书札跋》,载《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册,第1036页。20世纪40年代,瞿觉园、瞿兑之兄弟传钞《李星沅日记》,瞿兑之传钞《张集馨年谱》,也可在这一文化脉络中观察。上述抄录的近世珍稀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甚有裨益于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这些钞本不仅类似以防万一的备份,而且也便于传播。所以,在以上诸例中,有的后来已无稿本,只好借钞本以传世;有的稿本虽在,比如《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但带来更大的实际影响的,却是钞本。
传钞《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并撰文介绍,也与瞿兑之的学术旨趣和文化使命有关。瞿兑之在历代官制、社会史料、地方志、北京史地,以及唐史和唐诗方面都有既广又深的研究。(55)陈尚君:《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评述》,载《唐诗求是》(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525-544页。此外,他对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掌故学有很多贡献。(56)袁一丹:《瞿兑之与掌故学》,载《此时怀抱向谁开》,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第199-208页;姜德明:《瞿兑之与掌故学》,载《燕城杂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217-222页。在这一领域,自以黄濬与徐一士兄弟南北双峰并峙,最为擅场。瞿兑之介乎其间,发表数量甚多,虽不如黄濬和徐氏兄弟更有系统,但他对黄、徐二氏的掌故学事业多有赞助。比如他不仅为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写长序阐发掌故学的价值,而且为获罪而死的黄濬出版《花随人圣庵摭忆》。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赏瞿兑之编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为人熟知。对陈、瞿两家而言,晚清史既是国史,也是家史。陈氏在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前,尽管一直很注意晚清史,但并不亲手研究。(57)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自序”第1-3页,刘桂生“序”第2-4页。与之相对,瞿兑之则有保存近世文献和亲手研究的不懈动力。他曾说,“治掌故必从清代始”(58)徐一士:《一士类稿》,中华书局,2007,瞿兑之“序”第8页。,则他自然注重近世史。他在谈历史教学时也说:“过去习惯偏重古史而忽略近代史,也是因为近代史容或有避忌的地方,但是这极不合理。试问近三四十年亲身经过的事尚不清楚,何以成为一个近代人。”(59)瞿兑之:《关于历史教学的几点》,(东京)《学术界》1944年第2卷第4期。在近世史中,瞿兑之对道光朝尤为重视。1940年,他主编的《中和月刊》征集鸦片战争文献。他在征文启事中说:“道光二十年中英间以鸦片开衅,至今年正值百年矣。自此以后,西方势力逐渐侵入中国,文化经济无一不受剧烈影响。此一时期实为中国历史变动最大之时期。由于在东方权益之竞争,酿成列强间之争斗,其间接影响,厥惟上次与今次之欧战。故其影响可谓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征集“与鸦片战争有关之逸事;鸦片战争时代罕见之官私纪载;与鸦片战争时代有关之风俗事迹图画;对于鸦片战争之论述文字”。(60)瞿兑之:《本刊征文启事一·征求关于鸦片战争之文献》,《中和月刊》1940年第2卷第1期。次年,他更撰长文详论道光学术的大变曰:“夫学术者何,亦时势为之耳。时势相迫,人之耳目心性不得不振奋以应之。道光之时势为吾华民族从未经历之时势,是以秀桀之士莫不穷思眇虑,以求胜此时艰。综厥波流,凡有数变。”(61)楚金(瞿兑之):《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1944年,他仍接续上文所论,认为“道光一朝不只有清兴亡之关键,实秦以来陈陈相因之局一大结束”(62)楚金(瞿兑之):《道光学术余义》,《中和月刊》1944年第5卷第9期。。《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正包含了瞿兑之关心的许多道光朝史事。而这两种文献均直言不讳,大揭官场和社会黑幕,代表了道光以来的剧变时代日记和自订年谱写作中的“扒黑”风气,(63)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大抵据日记而作,其记道咸同时代也是类似写法。此前及之后,这种在日记或自订年谱中直言不讳地大揭官场和社会黑幕的写法,尚不多见。关于《镜湖自撰年谱》及道咸之际官员自述史料,可参看刘广京:《晚清地方官自述之史料价值:道咸之际官绅官民关系初探》,载《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189-245页。很对瞿兑之口味。这或许也是他特意传钞这两种文献的原因所在。
最后,从《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及其他例子可知,传钞珍稀文献除了学术文化的传承价值之外,有时也可变为一种“生意”。瞿兑之兄弟流寓上海生计艰难之时,《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便可换取高价,以供米盐之资。不过,相对于1949和1950年瞿兑之捐赠给上海合众图书馆的“长沙瞿氏文献”——包括瞿家大量的“先世手稿函札书画遗物、个人著述稿件,以及各种纪念品”(64)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552页,附录《一个图书馆的发展》,第916页。,他售让《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所获得的数百元,则显得微不足道。毕竟,传钞的珍稀文献可以出售,自家的手泽则只能捐而不能卖。最近彩印出版的上海图书馆珍藏《瞿鸿禨亲友书札》和《瞿鸿禨家书》,正是瞿兑之传承近世珍稀文献的另一大贡献,意义格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