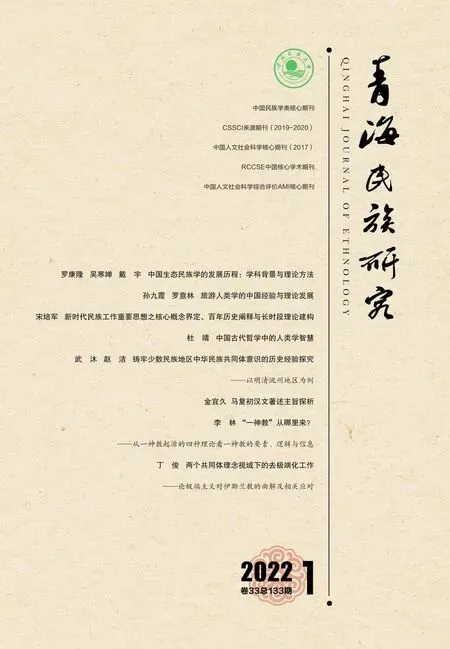新中国初期中共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的根除
——以西南为中心的考察
2022-12-29刘喜凤
刘 鹤 刘喜凤
(贵州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4)
学术界对土司制度的探讨颇为热烈, 成果累累。 近年来,学界对土司制度的废除和终结的讨论亦逐渐升温,“因为所持的资料与理论具有差异”[1]主要产生了三种观点:一是“辛亥革命说”,主要代表为杨庭硕、李良品;二是“民国说”,主要代表为黄家信、蓝武;三是“新中国民主改革说”,主要代表为龚荫、林文超、成臻铭、王文成、杨炳堃、秦和平,等等①。 显然,厘清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土司制度研究,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有裨益。 由于“土官是土司制度内容的核心,集政权、军权、财权、文权于一身”[2],而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世袭,“那种由土官和乡土衙门一体形成的‘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特点,反映了土司本质”[3],因此,探讨土司制度的废除, 不能离开土官及其接任者的探讨。 事实上,新中国初期,中共对土官及其继任者采取了有效措施,促成了土官民族干部化和新型民族干部的崛起,从而终结了土司制度。 有鉴于此,我们拟从土官及其接任者的角度, 动态地考察其变化,进而分析土司制度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
一、化茧为蝶: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改造式培养及其民族干部化
由于西南地区“某些土司在辛亥革命以后还长期存在”[4],因此,新中国前夕,西南地区“土流并存”,存在两套政治制度:一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民党反动政治制度,二是处于补充地位的土司制度。 新中国初期,为了维护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中共在破除西南地区国民党旧政权建立民主新政权的同时,并不急于摧毁土司制度,而是暂时保留“土流并治”政局。 以新政权建设为契机,中共对西南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和教育改造, 将他们改造成民族干部。西南土官化茧为蝶,转变为民族干部,从土司制度的维护者变为掘墓人。
(一)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政治安排
新中国初期,西南土官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南民族关系的走向。 因此,在保留土司制度的同时,中共非常注意对土官的政治安排, 并分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50 年代初期,由于新政权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控制力还不够强,加之土官对新政权心存疑虑,所以,中共普遍地将西南土官安排在新政权中任职,并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待遇,有职有权。50 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内外形势趋于稳定,中共不再在新政权中普遍地安排土官,而且将大量的土官调整到政协,甚至上调到县、州、省一级,“虚化”其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政治安排消除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恐惧心理,是对他们进行改造式培养的第一步。
1.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政治安排
新中国初期,中共积极动员并普遍安排土官参加西南新政权建设,尽可能多地将土官从土司制度中拉出来。 1950 年6 月,在车里县临时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39 师政委、 宁洱地委书记侯德才特意给外逃的车里代理宣慰使刀庭栋虚位以待,并宣布:“我们有信心争取他回到祖国的怀抱,请他在人民政府中任职”[5]。 新中国成立初的五年中,甘孜涉藏地区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土官达700 多人[6]。 德宏州对“原土司家属、属官、土司衙门人员等,都进行妥善安置。 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先后任潞西县协商委员会主任委员、保山专区各民族联合政府副主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其妻方爱德也被安排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译室工作”[7]。 进驻莲山县的解放军工作团在与当地土司思鸿升协商后, 组织了行政委员会, 原土司司署的28 位职员全部参加行政委员会工作,土司思鸿升担任行政委员会主任[8]。 1950 年12 月,保山专区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酝酿成立保山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名望的土官安排当选为副主任或委员。 1950 年11 月和1951 年6 月,保山专区两次召开专区各族各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联合政府组成人员、政协委员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安排了一批土官。 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一批区乡基层政府,对各级各类土官做了安排[9]。
由于普遍地安排了土官,所以,在一些地方的新政权中,土官明显占据优势。 其时,盈江县“县政府就设在新城刀京版的土司衙门内,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土司衙门的人,只有财政局、税务科(局)是我们的人掌握”。 因此,“那时的县政府,有些近似于现在的统战部门,主要日常事务是传递公文和民族团结”[10]。
为了动员更多土官参加新政权建设,中共一般对应土官原来的职务进行拔高,“大多数土官超过原有地位”[11],而且有职有权。 西双版纳自治区建立时,分别对全区有代表性的100 余名土官做了安排。其中,担任自治区正副主席的4 人,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的4 人;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的22 人,协商委员会委员23 人;自治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8 人,各版纳和自治区委员(区级)正副主席26 人[12]。1953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成立时,刀京版当选为主席,龚绶、多永安、雷春国、排启仁、司拉山、段华民等七人当选为副主席。 主席、副主席中,除段华民之外,都是土司、山官[13]。 其时,甘孜全州20 个县的正县长都由土官担任[14]。显然,这些人的职务普遍高于其在土司制度中的职务。 同时,被安置在新政权中的土官有职有权,而且工作比较轻松。 “刀京版任县长时,基本上不到办公室上班,日常行政事务都由我们办理,他的私章也交给我管理,行文办事,他从不过问。 但大一点的事则要同他商量,例如在盈江修补电线杆和电话线, 我就和他协商过好几次,经他同意后才能动工伐木[15]”。
经过政治赎买,土官的经济待遇也得到了保障。其时,大多数土官既在新政权中任职,又在土司制度中任职。 在一段时间里,土官出现了“吃两碗饭”的情况。 如德宏的土司头人,既领国家发的工资,又收取官租[16]。在土司同意不收官租之后,当地政府又给予经济补助。 如芒市方化龙宣布从1954 年起停止收取官租后,工委书记王泽民表态决定每个月给方化龙的家属和司属人员补助生活费3500 元[17]。衎景泰除了他任县长的工资外,原由他供养的直系亲属、警卫、佣人等分别按月发放生活补助费,其祖母方氏及随身佣人也按月发补助费。 主要属官如衎国斌、衎国安、龚辅勐、思汉章等均在政府或政协安排职务,领取工资;其子女保送学习,部分旁系亲属发放生活补助费。 有一定声望的村寨老、老幸、山官均安排职位领取工资,或发放生活补助费[18]。
2.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政治安排
到50 年代中期,国内外局势日趋稳定。 西南地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新政权日益巩固,新型民族干部崛起, 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要求废除土司制度。 另一方面,土司势力式微,土司制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中共调整了对土官的政治安排方式,将大量的土官调整到政协,部分土官上调到县、州、省。 简而言之,即“虚化”。
1955 年7 月,中共保山地委在《关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傣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意见》中比较清晰地勾画了将土官调整到政协的思路:“在改革期间,对土司属官及头以上的头人,本长期团结合作的政策,一律保护过关,不算旧账,政治上并对他们进行适当安置,过去安置不当的须以适当解决。 为了纯洁农村基层政权,今后在基层政权中,一般不再安置头人。 为照顾原在农村政权机关担任职务的主要头人(头、布胜等),建议仍保留县的协商委员会,予以安置”[19]。 地处大凉山的金阳县的做法则是将土官调整到政协的典型。 1955 年前,金阳县各区乡主要领导均由土司头人等土官担任, 但从1956年民主改革开始后,他们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为安置他们,1956 年6 月22 日, 正式成立金阳县视察团。 安登银(彝族)、蒋道伦(彝族)任团长,阿黎五撒(彝族)、马黑阿地(彝族)、比补搓搓(彝族)为副团长。 视察团由132 人组成,分为6 个视察组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主要任务是宣传民主改革的政策,协助政府做分化瓦解叛乱分子的工作,规劝外逃叛乱人员向政府投诚,保障民主改革运动和平息叛乱顺利进行。 1958 年1 月,视察团撤销。 视察团成员中,拥护党的政策,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中做出较大成绩的安排在政协,其余的大部分动员回乡参加生产[20]。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宋任穷回忆:云南和平协商土改前夕,“有少数土司头人,群众对他们的仇恨很深,要求斗争他们。 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本地,我们的工作很难做。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土司头人接到昆明,给一幢房子,安排个适当的职务,让他们吃好住好,一切花费我们包下来,避免留在当地与群众的矛盾激化。 这些人在本地住不下去了,也愿意留在昆明”[21]。 据曾代理土司的白张惠仙回忆,“土改前夕,各专州的土司,都逐渐集中到昆明,省民委建了房,都住在民委,我也调到昆明,任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22]。
(二)中共对西南土官的教育改造
对土官的政治赎买只是中共对他们进行改造式培养的第一步。 在初步稳定土官以后,中共启动了对他们改造式培养的第二步,即教育改造,促使他们转化为民族干部, 借此削弱并废除土司制度。中共“采用多种形式,结合形势,对他们实施教育、影响及引导,改变思想,改变管理方式,接受党的领导,树立国家整体观念,培植组织性,达到转变观念,培养成人民干部的目的”。 甘孜州“利用机关的当期干部学习制度,对政府内工作的上层人士进行政策宣讲,时事及前途教育,灌输国家观念,确立祖国观念,培养或激发爱国意识;通过诸如代表会议、政府委员会会议、行政会议等,采取学习、讨论、决议及执行等方式方法, 教育并逐步改造上层人士,从‘制度’外融入‘制度’中;建立及健全报告制度,培养其整体观念、服从意识、接受及遵守纪律,有所约束,构建并逐步实施新型管理体制。 期间,有关部门还多次组织民族上层人士及宗教上层到内地参观,全面认识祖国,了解发展变化,拓展眼界,破除部落思想,增强内向意识,靠拢党和政府”[23]。总体来看,主要采取了四种方式:一是组织参加各种会议,交流提高认识;二是组织参观访问,扩大视野;三是参加短期培训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四是个别交流谈话,提高认识。
在对土官的教育改造中,中共以诚相待,并针对土官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当时,个别在新政权中任职的土官 “由于受旧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影响较深, 对新的工作很不适应, 经常不假自归,或长期在家里不愿出来工作。汉族干部不辞辛苦,爬山涉水,深入家中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开导工作,有时还按月把工资送到他们手里,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工作中出了问题,汉族干部主动承担责任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24]。 峨边县成立联合政府时,彝族土官甘点诺、甘木沙沙当选为副县长。 由于生活不习惯,他们长期住在农村家里,未到县上任职,只在开会或有事时才偶尔去县政府。1951 年11 月,彝族年节期间,新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李臣保和县长张在福携带了两罐白酒和火腿、针线、花边等礼物,冒着严寒,爬山涉水,亲往彝区给两位副县长拜年[25]。 新中国初期,德格土司降央伯姆担心自己 “将是被斗争和消灭的对象”“感到十分恐惧和不安”。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开展了对她的教育改造。 据她回忆:“党派驻德格县的第一任军事代表,针对我的思想顾虑,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宣传教育, 反复给我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从他谈话中阐述的新颖道理,诚恳态度,都是我一生中所没有听到和见到过的”[26]。
(三)西南土官的民族干部化
中共对土官的政治赎买和教育改造, 一方面,使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土官,又是流官;另一方面,促使他们由土官向民族干部转化。 “土”的本色日淡,“流”的色彩越浓。
第一,从新政权职员内部设置来看,有利于土官民族干部化。 尽管土官在新政权中有职有权,甚至担任政府主要领导,但新政权完全是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之下的, 而且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 同时,当时的政府副职往往由政治立场坚定的党员或积极分子担任,因此,土官实际上失去了土司制度时代的权威。1950 年,德宏州辖境内的瑞丽、陇川、盈江、莲山、潞西、梁河六县行政委员会建立时,主任都由土司担任,但副主任则由当地工作团的一把手担任[27]。 1951—1952 年间,上述六县都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主席,除潞西外均由土司担任,但副主席则由工作团的领导兼任[28]。由于区乡政权的建立较晚,因此,在区乡基层政权中,对土官的掣肘则更加明显。 德宏州新成立的乡政权中,乡长多由原来的老或山官担任,副乡长由爱国团结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担任[29]。 1952 年12 月,潞西县轩岗坝(勐冒)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宏州第一个自治区人民政府,选举老线永贵为人民政府主席,农民出身的李二喜选为副主席,23 名委员中, 大多数是开展民族工作以来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30]。显然,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土官民族干部化。
第二,从新政权职员产生程序来看,有利于土官民族干部化。 土官作为新政权的成员,他们是作为“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而被选举出来的。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前,与会代表提出首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是: 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蒋匪特;三是与群众有联系。 对政府委员的要求是:一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同纲领的;二是能分清敌我,不听信谣言,并能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匪的;三是大公无私,不分民族界限,为各族人民办事的;四是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五是肯学习进步的[31]。 1953 年,在版纳勐遮筹委会第五次会议上, 个别代表公开批评景真土司说:“选你当副主席是可以的,但你的旧思想作风一定要改”。 有的说:“你吃人民的饭,不办人民的事,以后还这样, 就不选你了”。 景真土司当场接受意见,并表示:一定积极学习,办好人民事情,还希望大家再提意见。 到会代表对愿意进步的土官投了赞成票, 并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过去办事不公平的、有私心的,事情已过去了,不说了,以后要大公无私”[32]。由于土官是因“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缘故而进入各级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所以,他们是群众的代表,必须服务民众,并非指挥者、支使者。显然,这样的选举程序,有利于土官民族干部化[33]。
随着中共对土官政治安排和教育改造的深入,土官的民族干部化趋势更加明显。 50 年代中后期,中共“虚化”了土官对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土官进一步民族干部化。 一方面,土官之所以被安置,是因为他们已经转变成服从党的指挥的民族干部。 他们表示:“官比以前大了,而且还有经济补助,党的政策真好! ”[34]另一方面,由于新政权不再普遍地安排土官,土官必须拥护党的领导才能在新政权中获得一席之地。 土官“普遍地要求参加工作,向我们找官做。 没当官的积极找官做……一般安排了位置的上层人士则怕丢了官,比以前工作更积极了”[35]。同时,土官被上调到县、州、省,尽管满足了他们的政治需求,但也使他们离开了他们长期控制的地盘,带有“调虎离山”的意味。 对于那些被安排到省城的土官而言,更是如此。 被安排在政协任职的土官,其权限也大大缩水。 这些土官与土司制度渐行渐远,不再盘踞一方,进一步民族干部化。 因此,长期割据一方的土官逐渐转变为服从组织安排、 听从党的指挥、为人民服务的民族干部。
二、推陈出新:中共对西南新型民族干部的塑造式培养
对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和改造教育,对于废除土司制度有极大作用。 但受其阶级立场、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土官往往或多或少地眷念于土司制度。 因此,要废除土司制度,还得从民族内部培养坚定的反对派,斩断土司制度的承袭链条,从土官的接任者方面做文章。 新中国初期,中共以新政权建设为契机,在西南土官的子女和普通群众的积极分子中培养了一大批听党指挥的新型民族干部,并逐步取代土官群体。 这从根本上改变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土壤,彻底改变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进而从根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
(一)西南新型民族干部的来源
新中国初期,中共深刻地认识到,要削弱并废除土司制度,主要还得要靠少数民族自己。 因此,中共在安排和改造西南土官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西南新型民族干部的培养, 以期实现民族内部的政治替代。其时,西南新型民族干部主要来源是传统土官群体的子女和普通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当时,中共大力从西南各类土官的子女中培养新型民族干部。1950 年,在一次县委书记(含工委书记) 会议上,39 师政委、 宁洱地委书记侯德才就谈到:“你们在宣慰街民族上层子女中, 发展一批团员,带领他们工作,进行培养,将来有条件时,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自己起来反封建,挖封建主义的墙角”。 根据这一指示,宁洱各地大力吸收一批上层人士的子女参加工作。 他们被安排在民族工作队中,在联系群众中接受思想作风改造,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有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成为了新政权的重要力量。 如土改前培养了原宣慰使司内务总管都竜稿的女儿刀芝秀,后来担任土改工作队大组长;景讷土司的儿子刀治国参加工作后,表现积极,加入了党团组织,也担任了土改工作队大组长。 这一批参加工作的民族上层子女还有召珍、刀维汉、刀桂芳、刀述仁、刀兴平等人[36]。1950 年,保山地区民族干部培训班成立,招收对象主要是边疆土司头人及其亲属,招收第一二三期学员时,均由勐卯土司指定民族上层子弟、司署职员以及其贴身警卫蔡有寿、饶华等前往学习[37]。在莲山县,当地党委政府决定让土司思鸿升的女儿担任小平原镇镇长[38]。 景颇族山官的女婿雷老孔经过工作队的培养教育,带领20 多个青年开荒生产,因为没有祭官庙,遭到其岳父训斥。 在民族工作队的支持下,雷老孔与岳父进行说理,最后说得岳父理屈词穷,以喝酒过量说错话而了事[39]。显然,土官子女“自己起来反封建”这一釜底抽薪的举措,严重削弱了土司制度的基础。
与此同时, 中共也非常注重从普通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里培养新型民族干部, 借此动摇土司制度的根基。 其时,西南创办了三所民族院校,分别是西南民族学院、 云南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 这三所学校都在普通群众中招收新生。 “借助院校的系统教育形式, 系统学习,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 有严密组织纪律和积极奉献精神的民族干部,锻炼成长,推上领导岗位,逐步替代,掌握基层政权”[40]。 此外,各地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干部培训班。 到1953 年,仅潞西县就培养了脱产干部139 人,积极分子约800 多人,绝大部分来自普通群众[41]。 1954 年10 月,西双版纳民族干部学校第三批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班开学。 这一批学员共218 人,主要是傣族,其中女学员23 人。学员大部分是已经建乡的乡主任、 副主任、 生产代表、委员和农村骨干分子[42]。
(二)中共对西南新型干部的特殊培养方式
为既快又好地培植新势力破除旧制度,中共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民族干部培养措施削弱土司制度。 根据西南新型民族干部年龄普遍较低的特殊情况,采取了“先当仙人后当凡人”的特殊方式予以迅速提拔,为实现民族内部的政治替代、削弱土司制度提供了组织保障。 1956 年德宏自治州成立时,有4 个年轻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越级”进入了州级领导班子,他们分别是思伟章,傣族,当年27 岁,直接从瑞丽县副县长之职提拔;张文才,傈傈族,当年30岁,直接从保山县副县长之职提拔;石老二,景颇族,当年24 岁,直接从潞西县民族连副连长之职提拔;方吉龙,傣族,当年22 岁,从潞西县法帕区副区长之职提拔。 “这4 位同志,从他们当时的经历、学历、 工作能力来看都不具备担任州级领导条件,但因当时形势所需,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破格方式提拔起来”。 “除了这4 位州级干部外,对其他许多县处级的民族干部也曾采取过此种培养办法。 实践证明,对这些同志采取‘先当仙人后当凡人’的培养方法是符合当时情况的”[43]。 据调查,1951—1954 年间,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培养出近2000 名新型的藏族干部,他们得到快速提拔。 这些新型民族干部“多出身农牧民家庭,有的本身就是农牧民”[44]。
在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对于削弱土司制度作用很大, 但在一些地方, 由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因此,中共采取了特殊办法。 其一,采取秘密发展党员的方式。1954 年5 月到8 月,根据保山地委指示,在潞西县开展了秘密发展党员的工作,先后办了6 批336 人参加的入党对象训练班,在最后两批中秘密发展了15 名农村共产党员, 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和党小组[45];其二,灵活变通少数民族干部入党条件。 其时,“中共中央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指示各地党组织,应依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灵活地运用建党的原则,适当地吸收少数民族中那些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忠心拥护党并愿为党积极工作的积极分子入党,在党内教育和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步地达到党员标准的8 个条件”[46]。 根据这一指示,陇川县“当时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建党的要求,是从边疆少数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从党员八项标准中概括出来的五项条件执行, 五项条件是历史清楚、.政治可靠、衷心拥护党、愿为党积极工作、热爱祖国。 具备这些条件就可以吸收入党,入党后再加强教育锻炼, 使之逐步达到八条标准”[47]。 潞西县“秘密发展党员并没有把条件卡得过死, 也没有把不够党员标准和条件的人拉入党内,滥竽充数。 因此,中共潞西工委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的指导思想是对的,方法是稳妥的,效果也非常明显。既发展了党员,又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积极分子,为潞西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48]。
显然, 在共产党已经完全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西南一些地区还在秘密发展党员,并灵活变通少数民族干部入党条件,充分体现了中共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
三、不废而除:西南土司制度的根除
土司制度行将瓦解之际,1955 年7 月, 保山地委指出:“为照顾对外影响,不公开提出废除土司制度”[49]。 长期从事民主改革研究的专家秦和平认为,新中国初期,中共废除土司制度采取的方式是“只干不说”[50]。中共从对传统土官的改造和对新型民族干部的培养两方面入手,兵不血刃地根除了土司制度。
(一)自我“背叛”:西南土官民族干部化与土司制度的废除
通过政治安排, 土官一方面在土司衙署任职,另一方面又在新政权任职,既是土官,又是流官。 在与新政权中的“新汉人”共事的过程中,他们对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新汉人”和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新政权越来越有感情,不再留恋土司制度。 同时,西南各地对土官的教育改造“非常耐心、细致、非常讲究政策和策略”“既是针锋相对,但又留有余地,效果非常好,完全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51]。 因此,土官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提升。1954 年初,甘孜地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统计:在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上,表现进步的约25%,中间的约占50%, 落后的约24%, 敌对的仅鱼通土司1人。 “随着相关工作的开展,这种分化持续下去,更多上层人士表现进步”[52],如德格土司降央伯姆。 经过多次教育,她洗心革面,“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保证了从德格的马尼干戈到昌都以西的察雅、吉塘一线的支前运输……并在加强团结,维护治安,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53]。
随着思想认识水平的提升,民族干部化的土官脱离甚至“背叛”了土司制度。1953 年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庭长召存信郑重宣布:“放弃官租剥削,交出原有武器”。 经过民主改革的洗礼,他于1957 年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4]。 1953 年底,瑞丽土司衎景泰宣布,从1954 年起,撤销土司衙门,并不再收取官租,撤销土司自卫武装,向人民政府交枪80 支[55]。“至1955 年前后, 在整个云南边疆的绝大多数地区,土司制度的主人——土司司官用实际行动宣告了自己对土司制度的背叛”[56]。
土官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废除相邻地区的土司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康定明正土司后裔甲联升(藏族)。通过教育改造,甲联升被培养成民族干部,并当选为康定县第一任县长,“他积极拥护党的政策,协助党和政府做了不少工作”, 在对色达县藏族土司制度的削弱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色达县长期是“化外之地”,新中国初期,由于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当地土官拒绝工作组入境。 为完成国家统一,以甲联升为团长的慰问团冒险前往色达开展工作。 甲联升现身说法,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当地土官深受教育,愿意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57],从而为废除色达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
事实表明,新中国初期,西南地区虽然不明确提出废除土司制度, 但各地以新政权建设为契机,通过对土官采取政治安排和改造教育的方法,培养了土官对新政权的认同感, 将他们培养成民族干部,“艺术”地废除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主体——土司头人等“土官”皮之不存,土司制度毛将焉附?!1954 年1 月22 日,《保山地委关于边疆建政指示》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建政, 增强了民族团结,更进一步稳定了上层,更好地创造了争取团结改造上层的有利条件,改变了我们和上层头人的关系,有利工作,这亦是我们在边疆‘以人民民主制度代替土司制度’的必经过程”[58]。
(二)政治替代:西南新型民族干部发展壮大与土司制度的根除
新中国初期,西南多措并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新型民族干部的培养及使用有个时间的过程”,因此,民主建政之初的本土干部中,多数还是传统土官。 但“从1954 年起,各地政府着手调整任用上层人士的做法: 对那些已在政府中任职者,同职互换,在人大或政协任职;未安置者,直接在人大或政协内安排职位;同时,采取措施,广泛物色,加大选择力度,发展农牧民党团员,采取‘传、帮、带’形式,‘培养自己的上级’,成为新型民族干部,破格提拔”[59]。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后,要求做到自治区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 此后,新型干部不断涌现,茁壮成长,逐步替代了传统土官,担任各级政府的领导职务。 到1955 时,少数民族干部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云南边疆地区农民出身的干部多达3942 人,民族上层出身的干部仅为332 人,新型民族干部数量明显超过传统土官出身的干部。1955 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各基层政权的正副乡长346 人,农民出身的干部为187 人,上层人士为159 人;乡委员1849 人中,农民出身的1524 人,上层人士为325 人[60]。显然,新型民族干部对传统土官的政治替代越来明显。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动摇了土司制度的根基。
1956 年7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四川甘孜、凉山地区民主改革的专题会,毛泽东指出:“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61],并强调“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62],加大培养及发展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新型民族干部的力度和速度。 到1958 年3 月底,凉山州在农村中,共发展党员2300 名,建立党支部251 个;发展共青团员8060名, 建立团支部363 个, 并在运动中培养选拔了2300 余名彝族干部[63],这些民族干部主要是新型民族干部。 其时,云南省委提出“大胆破格提拔”和“放手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根据这一指示,云南区乡政权中基本上都由劳动人民出身的新型民族干部担任主要职务[64],从而进一步瓦解了土司制度的基层体系。
民主改革前, 潞西县的乡一级政权成员中,70%—80%以上都是农村头人,而且大多是地主及富农。改革后, 乡政权在形式上仍然是统一战线的形式,但以贫雇农为主的新型民族干部已经占绝对优势。 虽然仍吸收个别表现进步的农民成分的头人参加,但不再让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也就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 在数量上,一般的贫雇农(包括原为贫雇农的新下中农) 占2/3, 中农及农村中的其他劳动人民(包括个别进步的农民成分的旧头人)占1/3。 至于老以上的农村头人,在取消了他们乡政权中的职务后,适当安排到县的协商机构或其他适当机构中[65]。潞西县二期土改中,11 个乡选出人民委员会委员中,雇贫农占82.43%,中农占15.38%,进步头人仅仅占2.7%。 因此,土改前为土司、头人主导的乡政权,变成了以雇贫农为核心、农民占绝对优势的乡政权[66]。 1958 年,四川民族地区“区乡基层政权,已是干部‘民族化’。 当然,这些民族干部主要是中共培养的新型干部,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安排,执行指示”[67]。显然,这样的干部结构,充分表明原来由土官群体长期控制的基层社会已经彻底改观,土司制度的根基已经荡然无存。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各地特别注重培养新型民族干部,多措并举,成效也相当明显。 随着新型民族干部的崛起,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彻底改组,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新型民族干部手中。 传统土官失去了对民族地区的实质性控制,土司制度失去了最后的依托,从而被彻底废除了。 原户撒长官司政区的阿昌族农民说得好: “我们祖祖辈辈反土司,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总是逃不出土司的天土司的地。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把压在头上的土司制度消灭掉”[68]。现了民族干部培养与土司制度根除的完美结合。
其时,中共以新政权建设为契机,从两方面不断削弱土司制度的基础,重塑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达到根除土司制度目的。 一是对土官采取“改造式培养”的方式,将他们改造成民族干部,使他们从土司制度中自我解放出来。 各地通过政治安排,动员并妥善安排大多数土官参加到新政权中,减少他们“土”的因素,并通过教育改造培植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心理, 从而使他们不再留恋土司制度,一部分土官还从土司制度的维护者转变为掘墓人;二是采用“塑造式培养”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领导的新型民族干部,为废除土司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中共结合实际,采取多种举措从传统土官群体的子女和各族群众中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一大批拥护党的领导的新型民族干部出现在西南大地。 这一釜底抽薪的策略彻底改变了民族地区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实现了民族内部的政治替代,从根本上瓦解了土司制度的基础,可谓斩草除根之举。
在废除土司制度过程中,西南各地采取的并不是革命流血式的破旧立新,而是温和渐进式的立新破旧。 在民族精英方面,各地以新政权的植入为基点,在承认土司制度的同时,通过政治安排和教育改造传统土官及培养和壮大新型民族干部两方面入手,达到了从民族内部削弱、废除乃至根除土司制度的目的。 在普通群众方面,则通过他们自己对新政权与旧政权的比较,最终将土司制度消灭于无形之中。 “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看到党和人民政府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当时土司头人还继续对人民进行各种剥削,因而感到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自己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事情不再通过宣慰使议事庭和司署,而直接找人民政府解决,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69]。 西南土司制度根除的 “艺术”,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治国理政能力,也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感谢吉首大学成臻铭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文责由作者自负!
四、结 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土司制度的废除也是如此。 新中国初期,中共在与西南各族人民特别是土官协商的基础上,开始了民主建政工作。 以新政权建设为契机,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了培养民族干部和废除土司制度的工作。 西南各地废除土司制度,不是简单粗暴地从土司制度入手,而是迂回温和地从土司制度中的“人”入手。 既创新了民族干部的培养方式,又从根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实
注释:
①李超:《土司制度终结新论》,《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杨庭硕:《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杨庭硕,彭兵:《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吉首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吉首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黄家信:《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蓝武:《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期;王文成:《云南边疆土司制度的终结述论》,《云南学术探索》,1994年第3期;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成臻铭,刘中:《论民国档案中的土司承袭》,《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杨正文:《“民主改革口述历史” 课题缘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罗群:《云南土司制度发展与嬗变的制度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林超民:《云南傣族土司制度的终结》//民族学通报(第1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秦和平:《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终结土司制度的认识》,《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