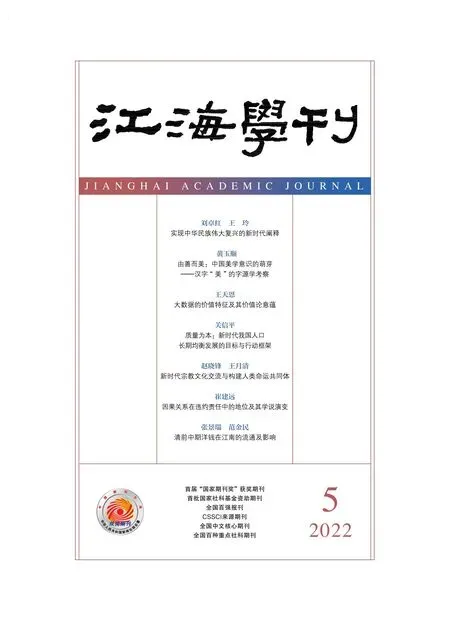张潮的“士商”身份及其文化活动
2022-12-29杨丽莉
杨丽莉
张潮(1650—1708?),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歙县(今属安徽)人。父黄岳公张习孔,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山东提学佥事。张潮年十五“受知于温陵孙清溪夫子,得补博士弟子员”,(1)张潮:《张潮全集》(第二册),刘和文校点,黄山书社2021年版,第23页。后数次应试不第,侨寓扬州经营盐业,并以诒清堂刊刻书籍,后“捐纳京衔”,授翰林院孔目,未出仕。在康熙年间的扬州,他从一个屡试不售的落第文人成长为一方“风雅主盟”。其父张习孔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凭借商业资本积极从事文化活动,在文化领域中获得了相应的文化权力,从而赢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他获得文化权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士人类型——“士商”对康熙年间的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何谓“士商”张潮
士与商本是两种职业身份,他们的区分源自《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2)赵守正:《管子译注》(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此所谓“四民”是基于职业的分类,统治者划分不同职业是为了定民之居、安民之业,而后“四民”逐渐变成有等级意味的社会身份划分,士、商之间界限分明,处于阶层的两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之间的界限逐渐松动,明以来士商相混、由商入儒、弃儒从商等现象逐渐普遍。(3)参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士、商界限松散,二者互动密切的现象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就详细讨论了士、商这两种不同社会身份之间的流动。一方面,他们立足时代社会背景,以商业利润吸引、人口激增、入仕困难等原因分析落第文人“弃儒服贾”;另一方面,勾勒出由商及士,商人阶层逐渐崛起的过程。商人凭借经济资源的优势,后代往往举业有成。唐力行、范金民、明光等学者从商人特别是明清时的盐商入手,关注商人对文化、社会的贡献。陈书录先生则是从文学内部问题切入,《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以士与商性格特性来探析士人与商人的契合及相互影响,以及商业文化与明清性灵思潮的关系。这些成果都关注到了明清商人群体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影响。(4)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中西书局2019年版;明光:《清代扬州盐商的诗酒风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
但是这些解释的立足点是士与商的关系,是两个阶层的互动与互相影响,而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了一类新型的文人,他们是商人,但有着“士”的文化属性、文化品格,利用商业资本跻身于文士圈层。“士商”概念可用来指称这类兼具商人特点与文人品格的特殊群体。
“士商”不同于历史发展中汉代的“士吏”、六朝与唐代的“士族”、宋代的“士人文官”以及明清的“士绅”,当然也不同于周启荣教授说的“经营型士商”和“服务型士商”。(5)See Kai-wing Chow, Print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Three.周启荣先生也提出过“士商”的概念,他认为士商是在经济领域担任文学工作和商人职务的人,利用写作、出版、编辑等文学技能谋生盈利,以这种士与商的融合形成知识商品化和写作商品化模式,如李渔、冯梦龙等人,以及专业从事政府事务、诉讼的幕友、讼师等。我认为这样的“士商”太过于宽泛,几乎可等同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与本文的“士商”概念不同。Kai-wing Chow, “The Merging of Shi and Shang in Travel: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for Travel in Late Ming Book”,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6, No.2, 2011, pp.163-182.在这篇论文中,周启荣先生以《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这类具有实用用途的商业书籍的出版和流行,来说明士与商群体共享地理信息等知识,以及同样追求勤奋、节俭、诚实等道德品质来说明士与商的进一步融合,但此文中的“士商”仍聚焦的是士与商两个阶层的互动,而未揭示出“士商”作为士人类型本身的特点与意义。“士商”不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行业人士,也不只是放弃科举之路,转而经营商业的知识分子,而是将商业利润慷慨地投入文化活动,以换取“士”的身份的人。明末清初的商业发展为这批人提供了土壤,他们利用商业资本积极从事文化事业,提升社会地位,最终获得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类不同于历史上种种“士”的文士群体,是士的近代转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类型,张潮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张潮志学之年已是社会趋于安定的康熙初。他13岁起学作八股文,热衷于考取功名,虽然与冒襄、黄周星等遗民有广泛交往,但本身并没有对新朝的抵触心理。他的父亲张习孔,也是在经历鼎革之后考取清朝的进士并出任官职。出生于士大夫家庭的张潮接受了传统的文士教育,有着士的文化属性,但科举不第的现实挫折,又使他无法获得士的政治属性,只好放弃举业,另寻出路。他没有像其他出身低微的文人那样,做幕府幕僚寄居人下或当教书先生,而是走上了经商之路。
关于张潮的盐商身份,可以在如下记载中得到印证。如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给曹贞吉的回信中称:“第是邗江盐业,全在汉上,尤为剥肤。闻已大受其毒,则涓滴微赀,不知作何究竟,将来糊口无策。言念及此,曷胜于邑。”(6)张潮:《尺牍友声集》,王定勇点校,黄山书社2020年版,第327页。由此可知张潮经营的是由扬州至江汉一代的盐业转运。
再如,由谢开宠编修、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行的《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八中收有张潮《盐价叹》《私盐行》《灶户谣》三篇,都与经营盐业有关。《盐价叹》云:“民间日用物,米最而盐殿。贱亦不足喜,贵亦不须睊。即使相倍蓰,亦不关戚忭。若取薪米类,一一细穷谳。孰不昂于盐,未闻遭锻炼。盐商亦何辜,乃独受谗谴。”(7)谢开宠:《两淮盐法志》第四册,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271页。诗中抱怨盐价遭受不公平对待:盐商既为朝廷提供数目可观的岁贡,同时盐绝对数量的消耗量少,盐的价格并不会对百姓造成很大影响,所谓“盐贵不病民”。但即便如此,盐商仍然受到无辜责备。《私盐行》则表达了对私盐奸商欲壑难填、唯利是图、横行霸道的痛恨:“私盐自古为盐蠹,赖有王章使之惧。烦者应论城旦舂,拒捕当斩谁敢护。”(8)谢开宠:《两淮盐法志》第四册,第2273页。《灶户谣》又指责蛮横的灶户:“吁嗟若辈乃枭獍,何为削义而崇奸。刁风从此不可遏,灶户逢商恣呼喝。招要恶党随成群,捉去商人供剽割。手持木棍长齐眉,不顾王章肆鞭挞。血流遍体无完肤,但有速死宁望活。”(9)谢开宠:《两淮盐法志》第四册,第2276页。盐价被非议,私盐横行,灶户蛮横,这些都是他经营盐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真切感受,但从中看不到他解决商业问题的尝试,而只是用诗歌抒发愤懑和不满,将希望寄托于朝廷的政策与隆恩。这些材料都显示,张潮的确是从事盐业经营的商人,但同时也表明他不仅仅是商人。
经营盐业是张潮的生存基础和经济来源,但从精神信仰层面上来看,张潮并没有满足于商业活动。虽然科举的失败让他无法进入传统的士人阶层,但是他凭借商业财富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积累社会声望,以求跻身于文士圈层。张潮对商人身份持缄默的态度,常以文士身份处世,也表明了他内心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
张潮“山来”“心斋居士”“三在道人”的字、号都指向他对山人、隐士文化的崇尚。“隐士”自陶渊明以来,已成为与文学有着天然联系的文化符号。张潮在陈鼎的《留溪外传》中被列为隐士,收入“隐逸部”。由于陈鼎与张潮私交甚密,张潮编刻《虞初新志》收录了13篇陈鼎的作品,《昭代丛书》收录7篇,《尺牍友声》收录书札8通,不难想见陈鼎对张潮“隐士”身份的认定多半出于迎合张潮的喜好。正如四库馆臣评价《留溪外传》所说:“其事迹由于征送……则仍然征选诗文、标榜声气之风,未可据为实录。如张潮诸人生而立传,殊非盖棺论定之义。”(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三,史部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7页。也就是说,张潮的山人文化身份是通过征选诗文、标榜声气之举获得的,与一般意义上的隐士还有很大的距离。张潮虽与山人群体同样是未入仕途,没有功名,但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却是截然不同的。“山人者,客之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者之号也。”(11)谭元春:《鹄湾文草》,张国光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68页。所谓“薄技”无非是山人以诗文、书画为谋生的手段,张潮的生计显然并不依赖于此,而是来自父辈积累的家业和自己经营的盐业。他是通过刻书与士人阶层结交,从而使他标榜的山人名号得到传扬。尽管张潮的隐士、文士身份在一些正统文人那里得不到认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自己对这个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追求。既然无法通过入仕获得体制内文士的身份,他就试图以商业资本为依托傍身,由另一个路径谋求文士身份,而且同时向人们表明,即使在山人辈赖以为生的“薄技”上他也不遑多让。
游戏文字历来是炫耀文才的长技,张潮留下的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此类。如《下酒物》《集杜雁字诗》《奚囊寸锦》等。他在《八股诗自序》中也谈到了编刻诗文自娱的初衷:“然花晨月夕,逸兴闲情,无所寄托,往往发为诗歌,以自写其抑郁牢骚之概。而同人之治举子业者,时犹以八股相质正,见猎心喜,辄成是编,亦只游戏自娱,初无关于诗文之轻重。”(12)张潮:《张潮全集》(第二册),第23—24页。序中还提到尤侗以《临去秋波》制义获得顺治帝赏识的逸事,《临去秋波》是一篇游戏体八股文,以《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为题,尤侗以这样的新奇之作被目为才子,张潮企羡之余,不免也想要模仿,所以就有了《下酒物》等一系列游戏文字。这些游戏之作既投射出文人雅趣,又通过复杂规则彰显文学造诣,从趣味、知识方面都能标识出文士的品位,彰显文士的文化身份。
张潮举业无成转而经商,并倾注心力创作诗文,编刻书籍,结交文士,追求风雅,最终以文化事业成就一种新型的士人典型。无论是持有功名、在地方上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士绅”还是强调儒家经世济民的“儒商”,都难以概括他的身份特点,将其称为“士商”更为合适。
“士商”和“儒商”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所不同,“儒”强调的是伦理品质,意味着约束、调节自身的一种道德规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士”则是由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身份。儒商是有德行的商人,“士商”则是经商的士人,也就是兼具职业属性和文化品格的文士。其次,“儒商”太过于抽象和宽泛,无论是被赞誉,还是为了扬名的自我标榜,所有具有道德修养的商人都可以被称为“儒商”。“士商”比“儒商”有更为清晰的外延,更适合作为一个形容士人类型的学术概念。
“士商”是以商业资本来推动文化事业的人,其性质与经营书籍牟利的书商也有所不同。像南宋陈起、清初李渔等人,虽与张潮一样科举失利转而为商,但他们是以出版畅销书和时文来营利,而张潮则是不惜消耗商业资本,不计回报地投身于刻书、资助文士等文化活动去追逐“士”的身份。“士商”在历史上不止张潮一个孤例,还有如马曰琯、马曰璐、江春等人,他们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以此来获得文化地位和荣誉。就“士商”张潮而言,商人身份是其生存底色,而精神追求、文化影响力则是决定他归属士人阶层的身份特征。这种文化身份的获得,既来自士人阶层对其才华的认可,也来自操持选政的文化权力的施展,并且一旦有机会,这种文化资本也可能转化为政治资本。
诒清堂刻书与张潮文坛地位的确立
张潮放弃举业之后,以商业为资本编刻、出版书籍,将他从事盐业获得的利润花费在刻书活动上,并以此资助落魄文士、结交文坛巨匠,追寻风雅文人的身份归属。诒清堂刻书就是他由商而士、获取文化身份的具体方式。诒清堂作为私人的书坊,刊行了张潮编选的《虞初新志》《昭代丛书》等重要书籍,其中《尺牍友声》和《尺牍偶存》保留的友朋往来信札记录了诒清堂编书、刻书过程中选文、收费的具体情况。这些出版活动及其交游网络见证了张潮跻身士人圈层的努力,也向我们展示了“士商”如何利用商业资本提升社会地位,获得文化权力,最终成为文士圈层的接驳者的具体过程。
张潮慷慨地为有声誉的遗民、掌握权力的朝廷官员、有才华的文人刻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场所,同时也为自己铺设了与传统文士进行交往的途径。通过编刻、发行图书,以图书作为赠礼等方式,张潮一步步地积累起他的社会资本。
由《尺牍友声》初集可见,康熙十六年(1677)冒襄这位在文坛有显赫声名的遗民即与张潮有书信交往。冒襄由明入清后,因隐逸不仕清而赢得世人的尊重,他在“仕”与“隐”的冲突下坚守“道义”,为政治、社会巨变下的人们提供了情感归属。张潮对冒襄的避世隐逸也表达了由衷的企羡之情:“先生漫说疏慵,尽诗酒终朝乏倦容。况哑哑欢呼,顿忘夏日,怡怡笑语,俨坐春风。”(13)万久富、丁富生主编:《冒辟疆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8页。张潮的这种认同与企羡不一定是对遗民政治立场的肯定,但一定是对文士情怀以及文化身份的肯定。
然而,遗民们的文化影响力并不能改善他们入清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冒襄给张潮的信自述“家落累重,弟卖字,小妾辈卖画”,(1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6页。原名列明末四公子的冒襄,此时已落魄到卖字维持生计,而张潮予其瓜豉、橙匏等生活急需的物品,冒襄对这些馈赠十分感激。冒襄去世后,张潮有文吊唁,并对其子冒丹书仍有照拂,丹书致信张潮:“屡荷枉顾垂恤,深念先君赐以哀挽大章,至情真切,溢于笔墨。”(1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37页。除日常生活中周济之外,张潮还取冒襄《岕茶汇钞》《宣炉歌注》《兰言》收入《昭代丛书》以为表彰。冒襄身后留下丰富的著述,但其后裔家道不振,“恨无点金之术,广为印行”。(16)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51页。《六十年师友同人集》全靠张潮等人为之刊刻,才得以保存和流传。当然,他们的交往是互助的,冒襄所辑《同人集》中也收录了张潮的词作《沁园春》二首,这为张潮步入文士圈层开启了重要的一步。
张潮通过刻书与清朝新贵官员亦有交往。最典型的是曹贞吉,康熙三年(1664)进士,康熙九年(1670)考授内阁中书,其《珂雪词》作为唯一的本朝词别集入选《四库全书》。据段晓华考证,“其最初锓版,或称祖本,是康熙年间张潮本”,(17)曹贞吉:《珂雪词笺注》,段晓华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5页。有陈维崧词序、高珩序、王士禛评、曹禾词话、张潮跋。陈维崧授官翰林院检讨;高珩顺治朝授秘书院检讨,升国子监祭酒;王士禛是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顺治十八年(1661)任扬州推官,康熙十七(1678)年任翰林院侍读,官至刑部尚书;曹禾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内阁中书,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而此时的张潮并无任何功名,诗坛地位也与这几位相差甚远,然而他凭借商业积累的资本为曹贞吉刻《珂雪词》,所施评语与王士禛数量相当,并在卷尾附以跋语。以他一介布衣,能为当世名公达宦刻书,并作评作跋,厕身于名家之间,正是他出资刊刻的缘故。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张潮由商变身为“士商”的方式与途径于此可见。
《尺牍友声》收有曹贞吉为刻词集致张潮的书札:“粗纸原欲印诗,不知老世翁已预为之地矣。如此云谊,其可忘耶?”(1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4页。又一札云:“五十部拜领,大费经营,奈何奈何。”(19)张潮:《尺牍友声集》,第53页。可知曹贞吉曾寄去纸张,拟备印诗集用,但张潮已为曹贞吉作了准备,并赠送五十部,花费不菲。同时,张潮将《珂雪词》板片寄送曹贞吉时,也顺便为其父张习孔《大易辨志》求序。《尺牍友声》丙集载曹贞吉回函:“见委《辨志》序言,弟斋心领略,知为先夫子一生得力之书,鸿宝光华,久而弥著。谨草数行以志向往,恐不足为佛头之秽也。至于师生二字,乃功令所禁,故序中不敢及之。”(20)张潮:《尺牍友声集》,第60页。可见,张潮在与官僚文人交往时,也积极争取他们的认可。
这里的“师生”二字值得注意,它说明了曹贞吉(山东安丘人)与张潮父亲张习孔有师生渊源。所谓“功令所禁”,就是岸本美绪所讨论过的,“就社会性的结合来看,清朝的基本方针之一是严禁在明末绅士阶层中形成非常发达的门生、‘盟’等等拟制性血缘关系。……憎恶官场中如门生等私人间的结合,强化官僚与皇帝一元化的隶属关系”。(21)[日]森正夫等:《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83页。商业资本的积累是张潮刻书事业的基础,而父亲张习孔作为山东提学佥事积累的文化资本是张潮胜过一般商人的优势。在清廷抑制官场门人关系的背景下,这层关系由台前转向幕后,成为左右张潮跻身士人圈层的潜在力量。
张潮与王士禛的交往也显示出商业资本、政治资本、文化权力之间的制衡和转化之迹。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士禛托孔尚任致书张潮:“特托者,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对弟咨嗟,以未获识韩为怅。”(2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74页。两人自此开始书翰往来,王士禛来信12札,张潮回信18札尚存于《尺牍偶存》中。张潮辑刊《虞初新志》,卷九收录王士禛《剑侠传》《皇华纪闻》,《檀几丛书》二集收录《长白山录》《水月令》《渔洋诗话》,《昭代丛书》乙集收录《国朝谥法考》《纪琉球入太学始末》《纪恩录》《广州游览小志》《陇蜀余闻》《东西二汉水辩》。王士禛信嘱张潮刻入丛书的诸书,篇幅虽都不大,但种数颇多,“《长白山录》止见三叶,似未刊完,伏祈留神,将此卷全刻,庶有可观。……如刻竣,每种祈印百本寄下”。(23)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91页。此外还有王士禛岳父张万钟的《鸽经》,亡兄西樵的《然脂集例》,刻竣都嘱张潮各寄几十本样书,“《鸽经》《华山经》祈各先惠五十本”,(2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94页。“先兄《然脂集例》希惠寄三四十本,以为家藏之秘,且识雅谊也”。(2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38页。据“康熙末章藻功《注释思绮堂四六文集》十册,刻金三百余金”推算,(26)蒋寅:《金陵生小言》,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31页。康熙年间刻书的价格,一卷两百页的书约需三十金,可见张潮为结纳时任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以求博得其青睐和揄扬,投入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王士禛以其政治资本的优势请张潮为其刻书,以及为其兄王士禄甚至为其门人张力臣、林吉人等人刻书,张潮都一一遵从并将书装缮呈送。这种交往多少有些各取所需的意味。
当然,张潮也并非一味根据地位、亲疏来选择交往对象,他也很尊崇那些老名士的文学才能、社会声望。比如《板桥杂记》作者余怀,徐釚《本事诗》称其“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清军占领南京后,余怀破产丧家,陷入清贫,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致书张潮:“鄙意窃欲年翁辍一日宴赏之费,为弟刻《冷云集》之资,成不朽之业。”(27)张潮:《尺牍友声集》,第97页。主动向张潮索要经济上的资助,并讨要生活上的物品:“好松萝或真毛尖,乞惠少少许,涤老人诗脾,感甚。”(2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40页。张潮慷慨以应,并将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王翠翘传》收入《虞初新志》,《妇人鞋袜考》收入《檀几丛书》,《板桥杂记》收入《昭代丛书》甲集第四帙,《砚林》收入第六帙。张潮虽然大为表彰余怀的作品,广为印刻,但得知余怀编《文救》,想请他收入先君遗文时,却仍声明将付刻资:“又《文救》大选定是斯道干城,谨以先君文集呈览,倘蒙采录若干首,殁存均感隆施。其刻资自当补上,决不敢有负清心也。”(29)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44页。由此可见,他接济寒士、助其刻书,颇为慷慨仗义,宽人律己。余怀以“王修龄饥则就谢仁祖食,不受陶胡奴米也”(30)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28页。来比拟他与张潮的道义之交,一方面是淡化自己沿门托钵的道德压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张潮风雅文士身份的认可。
编刻、出版书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对于各个阶层的士人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况且张潮性格通达、热情好客,礼贤待士,热爱刻书事业,自然受到文士们的赞赏。由《尺牍友声》可见,求书,求文章刻入丛书的来信络绎不绝。如闵麟嗣转述靳治荆“醉心大刻《丛书》,去春以《思旧录》一册欲求收入三集”,(3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69页。桐城杨文晃“每于友人处假阅,不忍释手,奈购求无自,不胜怏悒。是以斗胆丐惠”。(3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52页。随着张潮刻书的影响愈益扩大,他“风雅盟主”的形象也逐渐树立起来。
修墓、征诗与“士商”的文化品格
业盐解决了张潮“治生”的问题,并使他获得充分的经济实力来从事刻书业,但这毕竟是小众的文化行为,张潮并不止步于此,他为了赢得更大的名声,还需要一些能制造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活动。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张潮游虎丘,出资重修真娘墓,并广征“真娘墓诗”,就是一桩影响广泛的风流盛事,体现了“士商”风雅好事的文化品格。
真娘是唐代苏州名妓,本名为胡瑞珍,以歌舞闻名,流落被骗至乐云楼,卖艺守身,后为保贞洁,悬梁自尽。真娘死后被厚葬于虎丘,过往文人题咏不绝。落款“新安心斋居士张潮山来氏重建”的“古真娘墓”石碑至今矗立在苏州虎丘。张潮重修真娘墓并立碑,同王渔洋修葺臧洪、陈容二烈士祠,唐仲冕修唐寅墓,陈文述修冯小青墓一样,都是清代颇具影响的文化事件。修墓立碑或表彰慷慨义烈之士,或追忆才子佳人,使文化记忆有了物质载体,风雅传统得以延续,士人们得以在抚今追昔中追寻意义归属。所以这样的文化事件往往云集响应,为士人们所称道。
张潮这次修墓征诗对他文士身份的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立碑”活动加强了张潮与文士圈层的情感联结。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潮寄余怀书提到:“《真娘墓诗》呈政。云坡上人处,已嘱三世兄询其曾否立碑。如尚未举行,敢乞鼎吕促之。”(33)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56页。余怀回信:“虎丘立碑之事,小儿往觅主僧未遇,俟弟归督之以报。”(3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28页。张潮将《真娘墓诗》呈寄余怀,并嘱托余怀促成为真娘立碑之事。余怀著有《宫闺小名后录》一卷附在尤侗撰《宫闺小名录》后,其中“真娘”也列名书中。在来往商定刻碑修墓事宜中,张潮加强了与文士们的联络。他为此作有《甲戌夏五,舟过虎丘访真娘墓,知在枯树下仅一断碑零落于颓垣败砌间,因重为勒石立之旧处,虽芳魂缥缈,未必恋此一抔,而我辈千古情痴,或可籍以风后世云》一诗:“不辞蜡屐破苔痕,频款禅扉吊倩魂。古墓只余枯树在,短垣惟有断碑存。重埋片石题丹篆,旋汲芳泉荐素尊。试问夜台曾识否?情痴应向梦中论。”(35)张潮:《张潮全集》(第一册),第35页。真娘墓一片凄黯,只剩断碑残垣、古墓枯树,真娘的倩魂无处依傍,张潮叹其痴情,为其重立新碑。这种行为正是探古寻幽、为情而歌的风流情怀的体现,无疑将增强文士群体对张潮的情感认同,有助于他们把张潮接纳为同道。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张潮重修真娘墓并广征《真娘墓诗》,受到文士们的广泛称誉。姜实节来信说:“修复真娘墓、短簿祠二事,为虎丘生色,文人所至,山水附之以远。非我山来,曷以有此!祠栅已增,墓碑久立,过者健羡,不独弟也。”(36)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34页。姜实节,字学在,号鹤涧,山东莱阳人,居吴中(今江苏苏州),入清以布衣终老。其父亲是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谏闻名的姜埰,同人私谥“贞毅先生”。毛奇龄有《吊姜贞毅诗》,施闰章有《过故给谏姜贞毅公吴门旧寓》,王士禛有《挽姜贞毅先生》,可见姜氏在清初的声誉与名望,而张潮以此与姜实节有了更亲切的交往,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入士人圈层积累了文化资本。
同样,黄云也收到张潮的征诗启和诗题,并称赞“‘闰五日’‘真娘墓’两题绝佳,一吊幽魂,一志佳节,可见钟情决在我辈”。(37)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23页。黄云,字仙裳,明末诸生,与方文、杜濬、陈维崧交好。方文有《次韵黄仙裳见过小饮》、杜濬有《樵青歌为黄仙裳作》,都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说明黄云身为明末布衣在江淮一带颇有盛名。孔尚任初来扬州,亦是先拜访黄云,经他引介才融入当地文人圈层。
张潮“真娘墓”的立碑活动加深了他与余怀、姜实节、黄云等明末遗民的情感联结,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加深他们联结的关键因素正是“情”。遗民们不是新朝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社会资源的弱者,他们赖以生存的价值感,是源自道德伦理上的尊严和情感上的真诚真挚。遗民对明王朝及汉文化的眷恋与真娘的忠贞品格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这也是“真娘”的故事为何能引起强烈反响的深层原因。在改朝换代后的特定心态下,余怀、姜实节、黄云等遗民对张潮重修“真娘墓”的赞赏,也是寄托了一种自尊之情。“真娘墓”诗的征集酬唱,不仅是文士间关系的维系,更是情感与精神的共享。这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文化接续传递的一种独特方式。张潮的文士身份之所以能够顺利获得,也是得力于这种文化背景。
其次,将“立碑”活动放在“社会文化象征”的框架中看,张潮立碑悼念真娘,也与前人的诗歌传统相呼应,是跨越时代的文化象征。据苏州地方文献记载,真娘为唐时吴地人,墓在云岩寺西南山下。唐范摅《云溪友议》载:“吴门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时人比之苏小小,行客题墓甚多。”(38)陆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张维明校补,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李绅、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诗人有题咏。李绅诗云:“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尘有梵声。还似钱塘苏小小,只应回首是卿卿。”(39)卢燕平校注:《李绅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5页。李商隐《和人题真娘墓》云:“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40)朱鹤龄注:《李义山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黛消波月”“香魂”飘散,诗人们为真娘的玉碎珠沉叹惋,为美好事物的消逝哀怜痛惜。
悼念真娘的诗歌作为文化“符号”有特别的意味。在符号的所指层面,士人们所追悼的是亡殁的名妓,但在符号的象征意涵层面,士人们抒发的是对真娘刚正不阿高洁人格的敬仰,对真情和精神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文士们以绝代红颜来作为自己身为才华横溢文士的隐喻,名士对红颜的怜惜和怀念,也寄寓了对自身命运的感怀。于是“高洁”的品质和“真情”的向往成了连接符号表层所指与深层象征意涵的纽带。诗人们凭吊、悼念真娘,唤起的是诗人个体情感和精神叹怀,用“表征”方式来解读张潮重修真娘墓的活动,可以看到他对文人共同体的主动融入,以此来追求士的文化身份。
张潮对真娘墓的修葺,对美好事物消泯的伤悼,迎合了《板桥杂记》《影梅庵忆语》等中所描绘的清初遗民的回忆、悼念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为大量科举失败的下层文人提供了抒发情感的空间与途径,营造了心理上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重修墓碑,征集题咏诗文,也成为张潮以文化活动来确证其社会身份和号召力的一种手段,为无法入仕的匮乏寻求一种补偿,而这与传统商人的社会活动大不相同。一般的商人会关注有关社会民生的公共事务,如修桥补路、赈灾济贫等,以此积累社会声望和民众号召力,进而拓展商业版图。相较之下,张潮更关注文化活动。重修真娘墓之举正体现了他士人的精神内核,折射出“士商”风雅好事的文化品格。士人群体不仅仅是通过结社这种外在形式形成的团体,更是以共享文化符码的方式连接起来的精神与情感的共同体,张潮重修真娘墓正是实现这种连接的文化活动。明清易代之际,服饰、衣冠等传统士大夫的身份象征系统因满族统治者的政治管束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与破坏,据《启祯记闻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初,复严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责,巾即扯毁,由是举监生儒者皆戴小帽,士庶漫无分别”。(41)乐天居士辑:《启祯记闻录》第四册卷七,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4页。如果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悼妓”、立碑这样不触及政治高压线的文化活动作为文士们对身份的一种识别和凝聚就更显出特殊的意味。
结 语
国家权威的崩坍和新秩序重新建立的时期,社会关系在不断地形成、变化、分解,同时又建立起新的联结。入仕功业无路转而为商,利用商业资本投身于文化事业建设,以张潮作为典型的“士商”是士的近代转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态。“士商”张潮慷慨地为冒襄、曹贞吉、王士禛等人刻书、赠书,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影响力,赢得士的身份,成为士化的商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从商业资本获得的文化权力也并没有完全拥有绝对的效力,张潮多次向王士禛、宋荦求序,如请王士禛为《檀几丛书》二集作序,都未得到回应。后世对其凭借交游关系标榜声誉的行为也多有批评,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所刻《珂雪词》,说“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42)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集部五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9页。这似乎都隐约显示出正统士大夫阵营对张潮这类由商进而为士的文化暴发户的某种抵触,毕竟他们有着科举成功带来的身份荣誉感。这份荣誉所划定的界限,恰恰是张潮想要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跨越的。
张潮为代表的“士商”,以商业的获利为资本慷慨地从事于世有益的文化活动,结交、资助文人雅士,逐渐获得相应的文化影响力;同时又以崇尚“真情”而融入传统文士的情感共同体,最终跻身于文士圈层。关于“士商”这一新的士人类型在明清之际的崛起及其文化贡献和历史意义,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