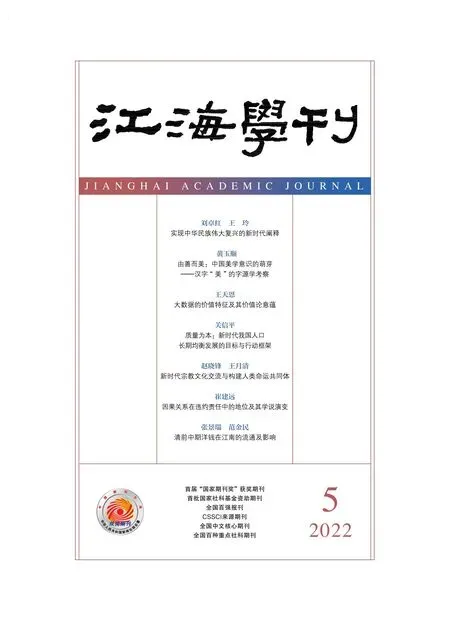因果关系在违约责任中的地位及其学说演变
2022-12-29崔建远
崔建远
因果关系在违约责任成立方面的地位
一般地说,两方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身份疏远,大多互不相干,一个陌生人受到损害由何种原因引起?凭什么就认定这是由另外的陌生人引起的?因果关系(causation)不得不起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并且,场合不同,情境差异,因果关系的形态和判断也就不同。与此有别,合同关系中的双方联系密切,债务履行与债权实现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债权实现受阻这种损害后果系债务不履行引起,二者之间有一个“直接与自然”(direct and natural)的关系,(1)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即因果关系清晰可见,只有在介入原因出现时才会相对复杂些。所以,在违约责任的成立上,因果关系似乎不是难题,远没有侵权责任领域那么复杂、多样。难怪有人断言:合同法中的因果关系并不起主要的作用,被赋予了次要作用,应当预见性规则似乎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很多间接的损害赔偿(remote damages)不可赔偿,即使违约属于其近因(proximate cause)。如果损害赔偿为违约方在缔约时不可预见,则不可赔偿。因此,在不可预见的损害上,因果关系的问题从不重要。依据减轻损失(mitigation)的理论和确定性理论,因果关系对合同的损害赔偿法具有辅助的作用。同样,损害赔偿必须“存在合理的确定性”规则也会产生因果关系问题。(2)[美]杰弗里·费里尔、迈克尔·纳文:《美国合同法》(第4版),陈彦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如果这描述的是英美法的现状,那么,因果关系规则在中国合同法及理论上不会如此地位卑微,其重要性肯定高于减轻损失规则,与合理预见规则至少比翼双飞。
因果关系学说之梳理
(一)双重的因果关系
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或者叫作事实上的因果关系(causation in fact)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causation in law)。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涉及加害人的行为与特定后果尤其是法益侵害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之相对的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它以侵害后果与损害之间的联系为前提。因此,进行双重的因果关系检验是必要的。(3)[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沈小军、张金海译,沈小军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35页。
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为事实的因果关系,遵循自然因果律或社会因果律,不包含法的价值判断,而是对纯粹的事实过程的认识,“因果关系中的唯一的‘事实上的’或者独立于法政策或者规范的因素是sine qua non关系”。(4)Hart and Honoré, Causation in the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110(2nd ed., 1985).
必须注意,这种认识并不周延,因为若干民事责任成立需要的因果关系的确出于法政策的考量,伴有立法者或裁判者的价值判断。所谓赔偿金同样可能填补因果关系链上较远的或者不可能证明或很难证明的损害项目。(5)Steltmann, 2000, 41.Treitel, 1995, The Law of Contract, pp.899-901.Treitl, Outline, 1995, pp.381-383.这表现出因果关系的考量和认定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590条第2款关于“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的规定,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法政策。因为迟延履行恰逢不可抗力发生,造成损失的原因至少是双重的,既有不可抗力这个原因,又有迟延履行这个原因。实际案型可能不尽相同:(1)不可抗力和迟延履行共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债权人因此遭受了损失,该损失与原因难以清楚地区分;(2)债权人因合同不能履行所遭受的损失完全是因迟延履行所致,若无迟延履行,合同会正常履行,就不会遇上不可抗力,也就没有损失;(3)债权人因合同不能履行所受损失完全是不可抗力所致;(4)迟延履行和不可抗力分别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该损失与原因完全可以区分开来。在上述“(1)”“(3)”和“(4)”中,依《民法典》第590条第2款的规定,债务人仍须承担全部责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果关系(自然因果律、社会因果律)的要求,完全是立法政策使然。
若将视野放宽,《民法典》第1170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第1230条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举证因果关系规定的反面推论,第1239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在侵权责任成立所需因果关系方面,都有法政策的考虑,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清楚可见。
(二)条件关系:因果关系的等值性
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均须具有条件关系(conditio sine qua non),或者说条件关系是损害归责的“必要要件”,具有过滤作用,即不具条件关系的,其权益侵害或损害项目(责任范围),均不由行为人负责。条件关系的认定系采“若无,则不”(condicio sine qua non,but-for)的检验方式,中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学说常用“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表达。“若无,则不”的公式/程序是一种反证规则,旨在认定:“若A不存在,B仍会发生,则A非B的条件。”德国民法学说称之为假设的消除程序,其功能在于排除与造成某种结果无关的事物,具有过滤的作用。条件系一种具自然科学意义的事实,在因果关系所有的条件均属等值,又称等值说。(6)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88页。
对“若无,则不”检验的举证证明责任是在原告。但该举证证明责任只需要达到超过50%的可能性,就可以满足对民事诉讼的要求。关键是举证要成功说服法院肯推断被告的错误/疏忽是与原告的损失有一定的关系。(7)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利昂·格林持与此不同的见解,其名言是:“过失”不可能造成损害,而只能引起“行为”。参见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法院对“因果关系的法律推断”(legal inference of causation)会根据提供的证据作出,这可以是“几乎肯定”(almost certain)的程度或只能是“合理可能”(reasonable probable)的程度下作出对原告有利的推断。但如果提供的证据不能满足这一个对原告有利的推断,就会判原告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上败诉。(8)Popi M.(1985)2 Lloyd’s Rep.1; Davis and Docherty v.Balfour Kilpatrick Ltd(2002)EWCA Cir.736; 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37页。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原告举证不了,其原因是被告的行为所导致,法院会认为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更为公道。(9)Cook v.Lewis(1951)SCR 830.转引自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39页。
在适用条件公式/程序时应当注意,它只是一个“基本原则”,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中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某乡镇S往小溪中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小溪的水污染了G的养鱼设施,G鱼塘中的鱼开始死亡。在调查过程中确定鱼死亡的其他原因:V提供了不适当的干饲料。两个原因的任何一项可能都足以引起鱼的死亡。该案中发生了竞合因果关系(双重因果关系)的问题。对同一结果的发生存在着两个份额,并且其中每一份额都足以引起结果。以条件公式为基础人们会得出荒谬的结果,没有一个份额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其中任何一项份额本身都可以放弃,而不会不发生结果。于是,通说以修正条件公式来应付。如果多个条件虽然是择一的,但是却不能全部放弃,而不至于不发生结果,则其中每一个条件都应当视为具有因果关系。(10)Vgl.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Rn.121; Larenz, SchuldrechtⅠ,§27 Ⅲa.转引自[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2—323页。
(三)合法条件说
为修正等值说,恩吉斯教授提出合法条件说。该说以具体行为在具体后果中因为合法的联系在事实上是否已经发生效力,或者没有实施的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可能已经阻碍了具体结果的发生为标准。(11)Engisch, Kausalität, S.21f.转引自[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3页。据此理论,在养鱼案中可以肯定,S排放废水以及V交付不适当的干饲料都对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因为两个行为以自然科学上可以证明的方式都对鱼的死亡起了促进作用。(12)[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3页。
(四)规范性的规则标准
合法条件说虽然修正了等值说,然而归根结底涉及的同样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确定。然而,判例和学术文献都承认,人们不能停留在这种“与价值无关”的考察上,因为肇致权利侵害的原因众多,其中一些对因果关系有促成作用,导致了一连串的因果连锁,其后果全由加害人负责,或由距离损害后果遥远(remoteness)的人或物负责,都不适当。因此,等值说的“漫无边际的宽度”必须通过规范性的归责标准加以限制。(13)[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4页。此处所谓规范性的归责标准,也叫具有法律评价规范性的归责原则,有两种:一是条件的相当性,即相当因果关系;二是法规目的论。(14)王泽鉴:《损害赔偿》,第88—89页。在英美,也认为“若无,则不”的测试并不代表法律上的原因,因为原因或始因即使与损失有一定关系,法律上也会有其他考量,不接受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人说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与法律混合的问题。(15)McCregor on Damages,18th edn 2009; Coxworld(1941)70 LⅠ L.Rep.160;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36页。
对客观归责进行规范限制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的框架内。过错不必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相关,即加害人的责任在这一领域内不能再限于主观的层面。相反,在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中,总的来说,过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矫正。当然,这里的客观归责也经常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标准来限制加害人的责任。(16)[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4页。
(五)相当因果关系:条件关系的相当性
相当因果关系说由条件关系及条件关系的相当性(Adäquanz)构成。在适用上须先肯定某个事由系肇致权益侵害(责任成立)及结果损害(责任范围)的条件(若无,则不),然后再检视该条件对权益侵害及结果损害的相当性。相当因果关系具有规范性的功能,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应否归责之法的价值判断。(17)王泽鉴:《损害赔偿》,第89页。在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学说,而是基于价值考察来限制损害后果的归责。(18)[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4页;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第8—13页。
判例学说对相当因果关系采如下认定公式:无此行为,虽必不生此损害(采条件说,用以排除与损害不具因果关系的行为),但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指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并从积极方面加以界定)的,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从消极方面加以界定,其目的在于排除“非通常”的条件因果关系)的,即无因果关系。(19)王泽鉴:《损害赔偿》,第89页。
由谁来运用“若无,则不”的公式?以谁的能力作判断基准?有观点认为,对于特定因果关系过程的可预见性或可能性来说,既不取决于加害人的主观预测,也不取决于加害人所属的交往圈之中普通成员的判断。相当性理论使客观的归责性取决于理想判断者的预测。(20)Vgl.Brox/Waiker, Schuldrecht AT.§30 Rn.9.转引自[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4页。英美法的表述是“因果关系被说是根据一般人的‘常识’(common sense),而不是根据‘哲理’(philosophical)或‘科学’(science)吹毛求疵。”(21)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32页。有人据此认为,条件关系的相当性理论仅在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的领域具有独立意义。因为在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中,反正在过错层面上还必须检验后果是不是加害人所属的交往圈子的普通成员可以预见的。在这里,借助客观判断者的标准进行“预先检验”是没有意义的。(22)So etwa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Rn.126; a.A.Lange/Schiemann, Schadensersatz,§3Ⅶ 1.转引自[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4页。
相当因果关系上的“条件关系”,原则上应由被害人负举证证明责任。至于“相当性”的举证证明责任,既采客观认定基准,原则上应由加害人负担证明该条件关系不具相当性。(23)王泽鉴:《损害赔偿》,第90页。
(六)规范目的论与相当因果关系
条件关系的相当性理论会受到一些原则性的质疑:(1)在个案中,理想的观察者本来可以预见到什么,这是很难确定的。在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人们赋予理想的判断者以什么样的特性和知识。法律的适用者根据自己的喜好以理想判断者的定义来预测结果的可能性。(2)条件关系的相当性理论还存在关键的价值被掩盖的危险。(24)[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5页。(3)条件关系的相当性理论不能给出排除不可能的损害后果的规范解释。实际上,在最终的意义上,可能性的必要程度总是取决于各具体规范,条件关系的相当性只是在确定规范的保护目的时的一个非独立的标准。(25)Vgl.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Rn 145;MünchKomm-Oetker §249 Rn.113.转引自[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5页。
为了克服条件关系的相当性理论的弱点,规范目的论/法规目的论应运而生。该说强调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所生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探究合同目的或侵权责任规范的保护目的而定。其理论依据有二:(1)行为人就其加害行为所生的损害应否负责,系法律问题,属于法之价值判断,应依规范目的加以认定。(2)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内容抽象,不确定,难以合理地界定损害赔偿的范围。规范目的论由Label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20世纪50年代再经v.Caemmerer教授加以阐发而成为德国民法的通说。他们认为规范目的与相当因果关系在适用上可以并存,并且综合考量,即损害应否赔偿,首先须认定其有无相当因果关系,其次要探究其是否符合规范目的。易言之,损害的发生虽然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但在规范目的之外的,仍不得请求损害赔偿。(26)王泽鉴:《损害赔偿》,第97页;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第13—16页。
规范目的论使归责性最为重要的限制成为可能,出发点是被违反的义务是否旨在保护个案存在的法益侵害或损害方式。在合同领域,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其他标准可以从合同的意义、目的以及诚信原则中得出。(27)[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5页。
上述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与规范目的论相结合,来认定包括违约行为在内的加害行为与损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使存在,也要审视其是否符合规范目的,是迄今为止最为可取的学说及方法,其有用性和不小的贡献在确定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中十分明显,在寻觅到更为优越的学说即方法之前,中国民法理论可以借鉴之。
(七)假设因果关系
加害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符合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他可否主张:“若无我的侵害行为,该损害也必然在其后因其他事由而发生,故我应该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例如,甲驾车毁损乙屋的玻璃,3日后因附近瓦斯管线爆炸,乙屋全毁。于此场合,甲的驾车行为肇致乙屋的玻璃毁损,系真实的因果关系。其后该屋遭瓦斯管线爆炸全毁,并未实际导致乙屋玻璃的灭失,故称乙屋玻璃因瓦斯管线爆炸而毁损,乃属假设,认为乙屋玻璃毁损与瓦斯管线爆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处所谓因果关系便被称作假设因果关系(hypothetische Kausalität),其原因为保留原因/后备原因(Reserveursache)。对此,早期见解认为这涉及的是因果关系,在假设因果关系的场合,既未有效造成损害,就不应斟酌该种损害要不要由行为人负责,即不成立损害赔偿责任。其后认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损害估算的问题。例如,原告的货物依计划应交由甲船运送,但被告交由乙船运送。其后,甲乙二船均遭海难,原告的货物全毁。依据差额说,原告可以请求的损害是指目前的损害与被告依法行事所生损害的差额。既然无论交由甲船或乙船,原告的损害均将发生,其经济上利益的差额便不存在,因此,被告无需负责。但若依据客观的货物的价值计算,原告可以请求损害发生时货物的价值。此时,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价值。(28)A.M.Honore, Causation and Remotess of Damages, in Andre Tunc(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Ch.7),81(1983);陈聪富:《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载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3页。另有学说认为,假设因果关系涉及的是损害归责的规范性问题,应以假设保留原因及其情事发展计算损害赔偿,依损害赔偿法填补损害的功能,区分类型,加以认定。(29)Fuchs, Delikts-und Schadensersatzrecht(8.Aufl.2012),S.363;Staudinger/Schiemann§249 Rn.97;王泽鉴:《损害赔偿》,第105—106页;[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第327页。
中国民法学说虽然尚无假设因果关系的理论,但《民法典》第590条第2款关于“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的规定,系假设因果关系的体现,贯彻了对此种类型的损害如何分配应予斟酌的精神。
(八)超越因果关系
所谓超越因果关系,也叫作修补因果关系,例如,原告因被告的医疗过失而失明,但原告因其体质,即使没有被告的医疗过失,最后也将失明。原告必然失明,在学说上称作“超越原因”(overtaking cause),系损害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被告的不法行为使该充分条件无法发生效果,被告可否以该超越原因存在为由,主张其行为未引起全部或一部损害,从而免负责任?关于此,意见不一。第一说认为,被告既已实际上引起损害结果,事后发生的事件对被告的行为的因果关系不发生影响。第二说以规范目的与公平正义的观念,决定是否对超越因果关系加以考虑。第三说以超越原因于被告的不法行为发生时是否确定存在或可能介入因果关系,为决定是否考虑超越因果关系的标准。第四说则认为,超越因果关系非属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损害赔偿的问题,因而以差额说决定被告的赔偿范围。(30)A.M.Honore, Causation and Remotess of Damages, in Andre Tunc(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Ch.7), pp.85-86(1983);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02页;陈聪富:《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载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第64—65页。
超越因果关系与假设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原告以外的行为或事件实际上已经发生;在后者,原告应为合法行为而实际上未为之,属于“假设”存在的原因。(31)陈聪富:《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载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第64页。
介入原因与因果关系中断
(一)总说
介入原因,又叫中断原因,或是介入的事件(intervening event),或是介入的行为(intervening act),它导致了最后的损失或额外损失。介入原因有第三人的行为,还包括不可抗力以及其他自然事件,甚至有守约方的行为,如减轻损失的行为。
如果违约行为与最后损失之间只是有“间接义务”(indirect relationship),就显示有了介入原因。在现实中有不少这种实例,因果关系更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况。常要看新的一波或新介入事件或行为是否足够分量中断因果链条(chain of causation),或者说不同性质的介入原因在中断因果关系方面有不同的后果。(32)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49、250页。
下文介绍的判例、学说所持的认定、观点和结论,有些纯为客观的方面——因果关系中断或不中断,另有些则把客观的方面(因果关系的中断与否)和主观的方面(预见到与否、过错)在整体上审视、把握,然后得出结论。由于中国《民法典》设置了应当预见规则(第584条但书),理论上都赞同因果关系,笔者不反对整体审视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思路及观点。
(二)新介入事件或行为能合理预见才不会中断因果链条
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介入事件或行为,就会有争议最后的损失到底是上一波还是下一波所导致,或者第二波是否中断了第一波的前因与最后损失的因果关系或因果链条。一个关键的检验是上一波能否“合理预见”(reasonably foresee)有这下一波。而如果第二波是不可合理预见,也往往表示第二波带来的损失与上一波的违约事件或行为没有直接关系,违约方也不必负责最后的或第二波造成的额外损失。但如果第二波是第一波引发后可以合理预见,就表示要对第一波负责的违约方还是要赔偿最后造成的损失。例如,船舶因航次中不合理地绕航或不适航导致延误开航,会为该航次带来延误,这构成违约并且船东要对延误的损失负责。但如果延误开航导致在航次中遭到“雷击”(thunderbolt)而船货被毁,就不应责怪船东为什么不准时开航以避过雷击。原因是两者(船东违约与新介入事件的雷击)没有一定的直接与自然关系,船东也不能合理预见。不过,太轻易让第二波中断因果链条,对守约方保护得不够,所以,不少先例坚持:只要不是“不自然与不正常”(unnatural & extraordinary)与完全独立的新介入事件,一般不会认定和判决中断了因果链条。(33)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49—251页。中国《民法典》第590条第2款关于“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的规定,没有认定不可抗力中断了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链条。
在英国,一位与违约方无关的独立之人所实施的行为能否中断既存的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链条,应当根据该行为的分量而判断到底能否中断因果链条。在该行为系因独立之人疏忽或故意所致,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更容易中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链条。(34)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0页。
根据中国民法及法理处理此类问题,应当区分类型而后下结论。其一,在多数情况下适用《民法典》第593条的规定,如此,第三人的行为不中断因果链条,债务人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其二,在诸如演员前往剧场的途中被出租车撞伤而无法演出之类的案件中,出租车肇事中断因果链条,演员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新介入事件或行为必须是守约方的合理行为才不会中断因果链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不少的情况下是守约方减轻损失(mitigation of damage),如:船舶碰撞后被害人安排救助;或是承租人在一个长期租约中违约后,船东另找替代租赁合同,让有关船舶可以赚一点租金与减轻损失;或是雇员被非法解雇后另找替代工作而不是待在家中等待索赔所有失去的工资;等等。但在这些减轻损失的过程中,被害人不幸地遇上了第二波的事件或行为。例如:船舶被救助时发生另一宗海难,如碰撞或搁浅;或是雇员在寻找替代工作时被新雇主欺骗而蒙受更大的损失。可见,因果关系与减轻损失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减轻损失的行为这种介入原因是否“合理”难以确定。(35)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4页。如果减轻损失的行为做得不好,甚至是守约方疏忽了,那么,这就给了违约方一个抗辩机会:最后造成的损失或额外损失主要且有效的原因是守约方减轻损失的不当措施所致,即可认为在违约行为与最后损失或额外损失之间中断了因果关系。当然,对守约方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的注意义务,不得要求过高,守约方的困境毕竟是由于违约方造成的,不宜“事后诸葛亮”式地认定减轻损失的这项措施适当与否。在船舶碰撞之类的案件中必须考虑在出了第一波事故,船舶身处危险,或失去动力,或操纵困难,通常船长在当时有高度压力,会造成船长在危急时候作出的决定在事后看并非最好的反应或行为。所以要现实地考虑这种因素。只要船长当时的决定谈不上不合理,仍然可说是这第二波的船长行为是第一波持续的直接与自然的后果,也可以合理预见到。所以,不应把第二波的行为轻易地当作为新介入行为,令因果链条中断。换言之,第二波行为产生的损失应与第一波的损失加在一起。(36)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49、271页。但是,守约方减轻损失是“不自然与不正常”(unnatural & extraordinary)的,通常会中断因果链条。例如,守约方在事后减少损失中有相对独立、严重与不能预见的错误或疏忽。这与“合理预见”的要求实际上相同,因为不自然与不正常的行为和损失,是不能合理预见的。(37)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70页。还有,如果守约方采取减轻损失的错误无可挑剔,则不中断因果链条,违约方须承担完整的违约责任。(38)The“Metagama”(1927)29 L1 L Rep.253; Canadian Pacific Ry v.Kelvin Shipping Co.(1927)138 LT369 HL.;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69页。
在债务人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债权人有错误或疏忽,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中断因果关系?在Borealisv.GeogasTrading(39)Borealis v.Geogas Trading(2011)1 Lloyd’s 482(CA).案中,针对债权人错误或疏忽的程度与中断因果关系之间的关联,Cross大法官发表了五个方面的斟酌意见,具有启发性:A.虽然对中断因果关系的指控,举证证明责任在被告一方,但原告还是应全程地举证证明损失系被告违约所致。B.要成功中断因果关系,债权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擦去”被告的错误的程度。真正的损失变为债权人的行为多于被告的违约所导致。如果债权人后来的行为只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损失,就不大可能会中断因果关系的。在一些情况下是被告的违约仍然属于导致损失的有效原因,因果关系不会中断。C.任何谈不上是原告不合理的行为是不大会中断因果关系。但仅是不合理行为并不一定会有这个效果,如被告的违约仍然属于导致损失的有效原因,虽然这也同时发生了原告没有采取合理行为保障他自己的利益。但原告轻率、鲁莽和不顾危险的行为通常是会中断因果关系的。D.原告对被告违约的知识和了解程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原告并不需要知道是否在有关的合同下有违约,否则,会让一个无知的原告得益,说是他不知道违约,所以不合理减轻损失。但在原告对违约事实知道得越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危险的情况,就是原告越应知道需要采取救济行动和采取什么行动。相反,原告合理看是应当知道得较少,不充分理解有关的危险,就会只在他轻率、鲁莽和不顾危险的情况下才会中断因果关系。E.中断因果关系是以个别案件的不同事实为准,法院或仲裁庭需要调查被告违约和原告事后行为的情况。通常是看程度的问题,就是从哪一点开始有关的损失再也不是由起初违约所导致的有效原因。(40)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72—273页。
债权人没有错误或疏忽,但其行为属于自由选择的范畴,中断因果关系吗?(1)适用货物买卖的市场规则,假设债权人作出的选择与中断因果关系之间存在关系。在国际货物买卖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争议是市场价格暴涨或暴跌时,受严重影响或亏损的出卖人或买受人发生扯皮,如出卖人拒绝交货,或是买受人拒绝受领货物。如此,债权人在同意终止合同时就有减轻损失的义务。最常见的处理是转售(债权人为出卖人),或是买进替代货物(债权人是买受人)。但实践中债权人即使这样做,也会在每一个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做法,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经常是买受人自己预测市场的走势后决定尽快或稍后买进替代货物。这就涉及债权人的自由选择。如果买受人预测得正确,这对出卖人有利,因为买受人成功地减轻损失,出卖人实际承担的责任相应地降低了。但是,如果买受人预测得失策,买进了更为昂贵的替代货物,已经违约的出卖人会抗辩:这额外的损失乃因买受人自主选择这种新介入行为所致,事后证明买受人处理得不明智,就这部分损失而言中断了因果关系。鉴于评断其中的是非曲直相当困难,英国法总结出一套相对简单和快捷的办法来计算损失。该办法就是“市场规则”(market rule),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50条第3款、第51条第3款对此有所规定。依据该规则,不纠缠于债权人因为相对人违约而蒙受的“实际损失”(actual loss),而是针对一个“客观损失”(objective loss)或“推断损失”(notional loss),判予赔偿,无须甄别减轻损失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市场规则”假设或曰推断作为违约方的出卖人拒绝交货,无辜的买受人马上去市场买进替代货物,将来向出卖人索赔的就是违约这天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与当天市场价格的差价。反过来,买受人拒绝受领货物,无辜的出卖人马上去市场转售货物,转售的价格与合同约定的价格之差,就是买受人赔偿的数额。至于其他类型的违约,如瑕疵给付,只要瑕疵货物也有市场价格,损失的计算也同样遵循“市场规则”。(41)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74—276页。美国法也确立类似的规则,只是买进替代货物、转售货物的期限不刻板地限于“当天”,而是一个“合理期限”。(42)[美]杰弗里·费里尔、迈克尔·纳文:《美国合同法》(第4版),陈彦明译,第549—555页。(2)债权人行使选择权(exercise an option),也可能是新介入事件,中断因果链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船东因承租人迟付租金而乘机撤船,这违反了普通法的下述规则:如果承租人迟付租金或少付租金,即使构成违约,也只是违反担保(warranty),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不足以解除租赁合同。在提单持有人索赔完成航次所花费的时间、燃油费用和港口费用等损失时,船东要承担之。因为如果船东不行使撤销权造成撤船,承租人肯定要继续支付租金直到航次完成,并要支付燃油费和港口费等费用。所以,船东蒙受的损失完全来自他自己选择撤船,中断了承租人不付租金与船东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43)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78—280页。在这里并非没有疑问,若根据中国民法及法理,则应有如下规则:如果债权人行使选择权源自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属于选择之债中的现象,那么,行使选择权乃合法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不应影响此前债务人的违约及责任的承担;就是说,行使选择权不属于新介入行为,不中断因果关系。相反,如果债权人名为行使选择权实为“师出无名”,或是根本没有选择权,或是虽有选择权但纯属滥用,那么,债权人的行为或是构成违约,或是违反不真正义务,属于新介入行为,中断因果链条。不过,此前债务人的违约及责任依然存在,当然,债务人可视情况而主张抵销、履行抗辩。受害人的自由选择若涉及有错误或疏忽的行为,则有很大可能中断因果链条。从合理的角度看,受害人的错误或疏忽越是严重,就表示该行为越不合理和越无法合理预见,也就越有可能中断因果链条。(44)Quinn v.Burch Bros.(Buildings)(1966)2 Q.B.370;Lexmend v.Lewis and others(1981)2 Lloyd’s Rep.17;The“Houston City”(1954)2 Lloyd’s Rep.148;The“Dagmar”(1968)2 Lloyd’s Rep.563;The“Polyglory”(1977)2 Lloyd’s 353;The“Mary Lou”(1981)2 Lloyd’s Rep.272.转引自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81—282页。这里同样涉及受害人的自由选择有无法律根据,若有,则不中断因果关系;若无,则构成违约或不真正义务的违反,受害人应当承受相应的后果,中断因果关系。
看来,介入原因表现为守约方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时是否中断因果链条,可从每一方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状态的视角审视,而后作出结论:在守约方一侧要求具有明显的不当,如故意或重大过失地采取不当的措施,不从预见到与否的视角着眼,在违约方一侧有无主观状态的要求?笔者倾向于不考虑违约方对守约方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及其妥当与否的预见,就是说,即使违约方预见到守约方会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甚至预见到措施失当,只要守约方在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也中断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链条,违约方对减轻损失的措施失当引起的损失不承担责任;更遑论违约方预见不到了。
债权人的行为非属减轻损失的措施,很可能构成违约,从而出现双方违约,应按《民法典》第592条第1款的规定,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新介入事件或行为改变不了违约的后果
有观点认为,即使新介入事件或行为在分量和性质上很严重(如守约方严重疏忽),足可中断因果关系,但由于改变不了既有违约造成的后果,还是不会中断因果关系。例如,患者甲因砒霜中毒,医院乙抢救时存在疏忽,但该疏忽不能满足“若无,则不”的检验,满足这一检验的还是起初的砒霜中毒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死亡后果。(45)Barnett v.Chelesea and Kensington Hos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1969)1 QB 428;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5页。
在这里,需要澄清:在投毒砒霜者与患者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医院的疏忽行为这个介入原因不中断因果关系。但在医院的疏忽行为与患者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没有介入原因,医院本应就患者受损承担一定的责任,只是因为前一个因果关系不中断,立法政策不令医院对患者之死负责任。在这方面,再举一例,加以说明。
债务人甲违约在先,给债权人乙造成损失1000万元人民币,地震发生,使债权人的损失增多至2000万元人民币。于此场合,应当认定不可抗力中断了债务人甲违约和债权人乙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债务人甲仅向债权人乙赔偿1000万元人民币,而不应认为“由于改变不了既有违约造成的后果,还是不会中断因果关系”,令债务人甲向债权人乙赔偿2000万元人民币。
(五)新介入事件或行为必须是造成损失或额外损失的主要或有效原因,才会中断因果链条
如果新介入事件或行为能够中断因果链条,就必须是既有的违约再也不是损失或额外损失的有效原因,既有的违约变为“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的部分,而新介入事件或行为才是主要或有效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这往往要求新介入事件或行为不能太轻微或无关紧要。(46)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6页。再细致些分析:既有的违约已经造成损失,特别是约定有违约金的,违约行为已经导致违约损害赔偿或违约金责任成立,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该历史事实不会因新介入事件或行为的出现而消失殆尽。既然如此,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违约损害赔偿、违约金责任应当由违约方承担,新介入事件或行为依法或依约成立另外的责任或不成立责任,似乎更为合理。当然,究竟采取哪种方案,应当根据个案案情而定。
(六)违约之前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属于新介入事实,不中断因果链条
在理念上,在侵权或违约之前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很难被接受为新介入事件或行为,更不可中断因果链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名为“脆弱头壳”或“鸡蛋壳头壳”(thin-skull,egg-shell skull)的想象案例。(47)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6页。在该案中,原告的脑壳非常薄,被告在不知道原告这种特殊脆弱性的情况下,过失击打原告的头部。这种程度的击打仅会给正常人造成轻微不适,但是却使原告的头骨骨折,原告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害。普遍接受的结论是,原告有权就全部损害获得赔偿,即使被告根本无法预见头骨骨折这一结果。(48)Chicago City Ry.Co.v.Saxby,213 Ⅲ.274,72 N.E.755(1904);转引自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第296页。法院总是说,被告应该接受原告的现状(takes the plaintiff as he finds her)。(49)E.g.David v.Deleon,250 Neb.109,547 N.W.2d 726(1996);转引自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第296页。这就是说,脆弱脑壳不属于新介入事实,不中断因果链条。
但在违约领域,上述意见很有疑问,“Eurus”(50)Eurus(1998)1 Lloyd’s Rep.351.先例就持相反的立场。在该案中,有关船舶被航次租用去尼日利亚装12.2万吨原油,在该买卖合同中,该批原油价格是按照提单日期为准。在船舶抵达装港前的1月23日,承租人(也是FOB买受人)就知道2月的原油价格会比1月低,很希望取得2月日期的提单。所以,承租人命令船长不要在1月31日的11∶00之前递交“准备就绪通知书”(Notice of Readiness)并且不要进港靠泊,这就有保证船舶会在2月才装完货。而有关的程租合同中,有一条(第36条)要求船东按照承租人的航次指示,否则,要赔偿承租人所有的损失。但船长在1月31日的00∶30就进港靠泊,而在11∶00递交通知书时,船舶实际上已经在装货的中途。当承租人知道后,马上想办法让装货放慢。事实上,船舶是在2月1日的01∶30装完货物。但在尼日利亚港有一个已经有18年历史的习惯做法是船东与承租人都不知道的,所以,承租人并未通知船长要想办法拖延至2月1日08∶00之后才装完货物。反正是承租人作为FOB买受人最后多支付了约70万美元的额外货价给尼日利亚的出卖人,并向船东提出索赔。在这里,涉及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船长没有按照承租人的航次指示不要在1月31日的11∶00时之前递交通知书,而不递交也表示不应靠泊;二是尼日利亚装港特殊的“08∶00规定”(8 a.m.rule)。(51)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7—259页。
如果是按照一般人的常识,承租人的损失是由何种主要或有效的原因所造成,而估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是“08∶00规定”所造成。但由于这是已经在违约前存在的事实,所以“08∶00规定”能否被视为是新介入事件中断因果关系,是有疑问的,观点不一。其中一种意见认为,“08∶00时规定”所造成的损失应属不大可能、不正常与不能合理预见的损失,故不予赔偿。(52)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9页。
(七)违约行为只是提供了产生损失的机会,但不是造成损失的有效原因
在GalooLtdv.BrightCrahameMurray(53)Galoo Ltd v.Bright Crahame Murray(1994)1 WLR 1360.案中,作为核数师的被告在审计原告公司账目时犯了错误,导致没有显示该公司实际上已经是无力偿付债务。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诉求是:如果审计正确,让原告知道了本公司无力偿付债务,它就不会继续运营,也就不会产生额外的损失,故被告应赔偿原告的额外损失。上诉庭则判该核数师的错误或疏忽只是提供了可能产生损失的机会,但并非导致后来的原告营运损失的主要或有效的原因。而提供产生损失的机会跟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运营损失的有效原因终究可以有很多,如原告自己经营不善或运气不好,毕竟在正常的情况下运营是可以赚钱,而不是蒙受损失。(54)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第259页。在中国法上,核数师审计原告的账目时疏忽而未能审计出原告已无偿付能力,这构成被告违约,被告应当就此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况且《民法典》在违约责任的领域奉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577条等)!但至于被告是否赔偿原告的损失,则取决于原告能否举证证明被告的过失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如果举证证明不成功,则被告就没有义务赔偿原告的损失。换言之,处理此类案件,不应武断地以“违约行为只是提供了产生损失的机会,但不是造成损失的有效原因”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应柔和地交由举证证明责任规则去解决,可能更容易使人接受。
(八)介入原因系不可抗力时原则上中断因果链条
在债务人没有违约的情况下,不可抗力发生,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民法典》以不成立违约责任为原则(第180条第1款、第590条第1款等)。这从因果关系的视角看,就是不可抗力中断了因果链条。此其一。在不可抗力影响了合同的履行,但未造成债务全部不能履行,债务人不履行尚能履行而债权人又需要的部分,债务人在这部分构成违约,影响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此其二。债务人迟延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适用《民法典》第590条第2款的规定,不可抗力没有中断因果链条。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