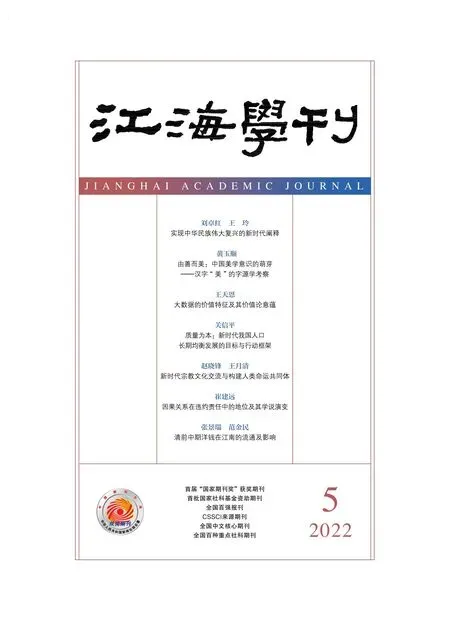复合、经验、实践的归纳法*
——中国传统归纳逻辑探赜
2022-12-29黄海
黄 海
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需要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承的视野下予以考察。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统演绎逻辑,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统归纳逻辑,中国古代传统归纳推理在归纳中有追求必然性的成分,即在归纳中有演绎的成分,是一个复合的推理形式。因此要结合中国古代归纳推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归纳推理形式。中国传统归纳推理就性质而言是实践的推理,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逻辑的个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对归纳推理的研究构成了新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统归纳推理是一个复合的推理形式
研究中国传统归纳推理,自然同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一样,将《墨子》一书看成我们研究的重要的经典文本。例如: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墨子·非攻上》)
治中国逻辑史的学者通常把这段话理解成中国古代逻辑中的典型推理形式——“推类”。
总结这种推类的特征,可以说是与西方的类比推理相近似,只是前提中不局限在两个事物罢了:
A:窃人桃李,亏人自利,不义。
B:攘人鸡犬,亏人自利,不义。
C:取人牛马,亏人自利,不义。
D:杀不辜人,亏人自利,不义。
所以E:攻国,亏人自利,不义。
从前提A、B、C、D到结论E,层层推类(1)王克喜:《语言与逻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这种理解被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思维“一叶障目”,忽视了墨家在实际推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性质:归纳推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墨家在上述引文中的推理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各种示例,而是追求在说理过程中对一类现象的归纳推理。这是因为归纳推理涉及的都是同一类的相同事例,而墨家在这里所做的论证,就包含着一种所引事例在“量”维度上的增加,这在论证中能够有效提升论点的可信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墨辩》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非形式逻辑。”(2)赵继伦:《〈墨辩〉是中国古典的非形式逻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
如果我们从上述视角再来回顾墨子的论述,就会发现墨子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有一个人进入他家园圃,偷窃他家的桃、李,这类“质”的事实很快被导向了一种一般性的描述——“亏人以自利”。随着墨子不断地列举其他同类事件,这个一般表述在“量”层面上越来越大:
(1)盗窃他家的鸡犬、牲猪的行为;
(2)偷取他家的牛马的行为;
(3)枉杀无辜、夺人钱财的行为;
(4)攻伐别国,掠夺领土和资源的行为。
按照墨子所使用的同类事例在“量”层面上的增加,由此递进,对于“亏人以自利”的一般性描述的最大值正是“攻”这种行为。即是说,攻伐别国,掠夺领土和资源的行为,是最大化的“亏人以自利”。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简化墨子的推理:如果为了抢夺他人财产而杀人的行为是犯罪,那么为了掠夺土地、财富而大规模杀人的行为难道不是最大的犯罪吗?由此可见,墨子是在最高层面上严厉谴责攻占他国的行为。
墨子将这类掠夺战争称为“攻”,并对之给予严厉谴责,因为“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的屠杀和悲剧,却不会使攻击发起国永久地保全自己的利益。一旦揭示出墨子在论证和推理中想要表达的真正意义,接下来要探寻的就是墨子是否成功地按照归纳的理念进行推理,答案是肯定的。在这样一段论述中,墨家实现了从个别事实上升到一般性的结论。他所谴责的是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名的战争行为,而这类战争行为在墨家所处的时代是极为常见的,从春秋到战国,先秦时期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从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事例,到一般的“攻”,墨家在推理和论证中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升华,构成了一个归纳推理。
然而,墨家的推理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出归纳,墨家在这里想作的论证是:
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中》)
墨家在这里指出“攻”是不义的,而那些“饰战者”正是要攻,所以是不义的。做不义的事,是不会成功的,由此可以推出,好战者肯定是不吉而凶的。
罗马尼亚逻辑学家安东·杜米特留在《逻辑史》一书中提出了“深入归纳法”:
刘家惠认为,欧洲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前者受后者影响)所说的类比推理,实际上是深入归纳。这种深入归纳不是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而是包含从特殊开始,建立一般原理。下面就是作者(指刘家惠——引者注)给这种归纳下的定义:“深入归纳是一个由类比进行的推理,它在推演之下产生。推理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关于特殊族类的规律。但是,它不是建立于S.穆勒归纳法基础上的从一个特殊到另一特殊的过程。”(3)[罗马尼亚]安东·杜米特留:《逻辑史》,李廉主译,打印本,第2章,第38页。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西方研究者们实际上未能准确把握住中国古代传统归纳推理的精髓。
中国传统归纳推理是作为经验存在的
国内有学者在杜米特留的基础上对“深入归纳法”进行了研究,孙中原认为《墨经》所说的“擢虑不疑,说在有无”(《墨经·下》)的“擢”就是讨论归纳推理的,并引“擢,引也”(《说文》)和“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之死也可”(《经说·下》)为佐证,称这种归纳法是典型分析式的归纳推论。在《中国逻辑学趣谈》一书中,孙中原认为“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墨经·上》)说的是一种简单枚举归纳。“这是说,对方举出一些正面例证,就归纳出一个一般结论,认为所有该类事物都是怎样的,‘然’指正面的例证或肯定的判断,如《小取》‘是而然’的‘然’。‘以为’指不符合实际的主观推论,如《经下》‘以楹为搏,于“以为”无知也’的‘以为’。‘此’指一类事物。”(4)孙中原:《中国逻辑学趣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3页。并且把这种归纳推理用公式表示出来:
M1是P;
M2是P;
M3是P;
……(然者)
M1M2M3……是M类的部分分子
所以,M是P。(此其然也)
孙中原还以《墨经》为例,给出了如下的推理:“甲是黑的;乙是黑的;丙是黑的;……(然者)甲,乙,丙……是人;所以,所有人是黑的。(此其然也)”(5)孙中原:《中国逻辑学趣谈》,第293页。
然而,中国古代先哲们进行归纳是有目的的,他们绝不是以简单枚举归纳得出结论即可,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结论随时来解决具体问题。他们经常会用此结论作为大前提,来演绎出个别结论。孙中原用西方传统逻辑的结构形式将其表达为:“有M是P;所有S是M;所以,所有S是P。例如:所有人是黑的;张三是人;所以,张三是黑的。”(6)孙中原:《中国逻辑学趣谈》,第294页。
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原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解读《墨经》中的“止”的逻辑性质,而不是为了探讨中国古代归纳推理的性质及形式。他没有区分这两种归纳法的不同,仅就两种归纳推理的性质形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的“擢”式归纳推理与西方传统归纳推理无异,有探讨的余地。据此,本文认为,这两种归纳推理都是属于中国逻辑的“深入归纳法”。
中国传统归纳推理虽然不像西方传统逻辑那样可以方便地进行形式刻画,但中国传统归纳逻辑具有与西方传统归纳推理不同的鲜明民族特征。有研究者认为这种难以给予形式刻画的思维形式是所谓的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缺陷之一,称之为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7)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5页。然而,一旦我们结合古代文本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中国传统归纳推理虽然很难达到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所谓的“有效性”,但在说理的层面上而言,这些归纳推理却是成立的。在现有典籍中,中国传统逻辑对简单枚举法和以偏概全并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往往是以结论的正确与否作为标准,而结论的正确与否需要对实际推理情况进行考察才能获知。
中国传统逻辑思维中的确没有清晰地提出“有效性”的概念,更遑论对“有效性”进行学理研究,有学者甚至据此认为这是区分中国有无逻辑学的一个主要标志。由于没有明晰的“有效性”的概念,中国传统归纳推理不追求结论的可靠性,而是要追求以这个归纳的结论作为前提,开展进一步的演绎推理。因此,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兼具“或然性”的归纳性质和追求“必然性”的演绎性质。比如:
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墨子·尚贤中》)
通过对“不尚贤”所导致的种种严重后果进行归纳,发现都具有共同的性质:“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但是墨家在这里不是要追求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是追求一种说理的效果。总的来看,墨家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两个推理模式:
第一个归纳推理:
“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具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属性;
所以,凡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都会导致举措失当,危及国家。
这个推理,使用了简单枚举法,通过部分事物和现象之间反复出现并且没有反例的枚举,推断出所有事物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墨家在这里绝对不是仅仅要推出这样的结论,而是为了做出如下的进一步推论。
第二个演绎推理:
所有“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就会导致举措不当,危及国家;
今天下士君子“明小物而不明大物”;
所以,今天下士君子的举措就是不当的,会危及国家。
这种归纳推理在传统的谚语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例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就是中国人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用这个谚语去验证今年的正月十五下不下雪。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的第一步,先通过归纳得出一个一般性的大前提;第二步,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演绎验证这个一般性的结论是否可靠。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或按照杜米特留的说法将其称之为“深入归纳法”)囊括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两种推理机制,在说理过程中是把归纳和演绎有机融合在一起使用的。这种“深入归纳法”在连珠体式的推理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一些。比如:
假言前提:“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
通过四个故事,提供正面例证:“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通过三个故事,提供反面例证:“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
结论:“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8)《韩非刑名之学·下》,马骕撰:《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45页。
整个推论从正面列举了侏儒讽卫灵公、孔子劝谏鲁哀公、齐人以鱼充为河神欺骗齐王、惠施谏魏王这四则故事,又从反面列举叔孙听信谗言诛杀自己儿子、楚国白公之乱、卫嗣君被臣下蒙蔽的历史教训。通过以上正面和反面的诸多故事或者历史事实归纳出一个结论:“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得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让人们在现实中不再出现“观听不参”“听有门户”的错误。(9)沈剑英:《论连珠体》,《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再比如: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10)《陆机·演连珠》,王志坚选编:《四六法海》,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716页。
这个连珠体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对自然现象做了简单归纳,归纳的思维模式如下:
春天,自然界齐物;
夏天,自然界齐物;
秋天,自然界齐物;
冬天,自然界齐物;
所以,自然界齐物。
自然界齐物;
人事界齐物;
所以,宇宙齐物。
既然宇宙都齐物了,所以国君对待人间万事万物也要平等,一视同仁,即“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而不能有亲疏远近之分。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推类逻辑具有演绎性质。“中国古代有关于‘推类’的‘必然性’观念。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关于推类的‘必然性’观念,那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当然,它没有针对某种推类方法来专门讨论‘必然性’问题。这也是事实。”(11)刘明明:《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这种说法有其科学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推类逻辑中,特别是在连珠体中,除了包含有类比、归纳推理的成分,还包含有演绎推理的成分。上述连珠体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推类推理的演绎性质:从自然界的一年四季齐物,归纳出自然界具有齐物的性质;人事社会与自然界有相同的地方,类推出人事社会也要齐物;再从自然和人事齐物归纳出万事万物即宇宙要齐物。如果说,这样的推论不具有必然性,但下述的推论就具有必然性了:万事万物即宇宙齐物,国君治理国家是万事万物的一种,当然也要齐物。只要归纳得到的结论为真,这个演绎的结论毫无疑问也为真。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归纳逻辑虽然具有归纳和演绎两个组成部分,兼具演绎和归纳的性质,但由于其归纳而得的结论本身具有或然性,以或然性的结论为前提再进行演绎,所得到的结论还是不具有必然性。换言之,就整个逻辑推理过程而言,中国传统归纳逻辑本身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但是这种或然性往往被先贤们所忽略,他们理所应当地将归纳的结论作为可信的大前提,继续进行演绎推理。尽管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大前提也是归纳总结而来的,但通过西方传统归纳逻辑的技术处理,通过归纳总结而得到的结论往往可信度更高。一般意义上而言,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关系是:归纳推理为演绎推理提供了大前提,而演绎推理则检验归纳总结出的结论可靠与否。首先,从思维进程来看,演绎是一般到个别,归纳是个别到一般。其次,演绎推理的结论虽然得出了新的判断,但依然蕴含在前提中,没有超出前提原有的判断范围。最后,演绎推理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是一种必然性推理;而归纳推理,是一种可信度较高的或然性推理。就中国传统归纳逻辑而言,是把归纳和演绎合二为一,就如同连珠体推理一样,也类似因明三支,是包含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逻辑形式的推理。
中国传统归纳推理是实践的推理
汉代王充的《论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论证逻辑的代表,王充在反驳论证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其中归纳法运用得最多。“引物事以验其行”,对一个论题,王充往往提问“何以验之”“何以效之”,然后列举一些事物作效验,进行推论,得出一个结论,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他的主要论证方法就是归纳推理,即在实践中检验一般性的道理。王充用实践加以验证的归纳推理思想大大发展了前人的逻辑思想。他所运用的归纳方法,包括简单枚举法、探求因果联系等方法。他在反驳汉儒“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时,就是运用简单枚举归纳法的典型事例,一连列举了十六个“效验”,推出“圣人不能先知”这个一般性的结论。
以《雷虚》篇为例,在论证“雷者,火也”这一论题时,所用的方法就是简单枚举归纳法。
何以验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灼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论衡·雷虚》)
这“五验”所引的都是事实,“一验”是对被雷击中而死的人进行观察,说明人被雷击中而死实际上是被雷火所杀;“二验”是通过将火烧之石投入寒井中,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声音的实例,进行推类,说明雷是阴阳二气纷争产生的;“三验”是以寒气入人腹中,温寒纷争,激起雷鸣的实例,进一步说明雷是阴阳二气纷争产生的;“四验”是在打雷时进行观察,发现电光如火,以此证明雷是火;“五验”是以雷击之时,会烧人房屋、草木的现象,证明雷是火。从这“五验”概括出“雷者,火也”这个一般性的结论。王充通过列举大量实例,引用历史事实或者社会共识进行验证,最终总结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结论。这种推理形式,王充运用得较为娴熟而且形式上整齐规范。
对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法,王充在《论衡》中也有下面的这些表述:
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论衡·实知》)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贤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论衡·实知》)
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论衡·实知》)
但是对于这样的简单枚举归纳法而言,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其推理的逻辑基本范畴——“类”概念。在王充的论证逻辑思想中,不是筑基于严谨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王充也很重视“类”概念,他指出,“物类可察,上下可知”(《论衡·龙虚》),但是王充对怎么分类、事物或现象哪些应归为一类、哪些物类之间可以推类、哪些物类之间是不能推类的等,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清晰、正确的认识。因此在王充的论证中,不仅出现形式整齐规范、言之凿凿的归纳推理,也会出现很多应用不当、牵强附会的归纳推理,这种前后不一在王充的其他论证方法中也经常出现,极大影响了王充在逻辑领域的成就和贡献。
在《论衡》中,王充错误地运用归纳法的例子有很多,在《吉验》篇中,王充为了证明:
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论衡·吉验》)
这一论题,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
传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大率诸侯,诸侯归之;教熊罴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性与人异,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当为帝,故能教物,物为之使。(《论衡·吉验》)
后稷之母,履大人迹,或言衣帝喾之服,坐息帝喾之处,妊身。(《论衡·吉验》)
王充运用归纳法,用如此类十几件事来证明其论点。但是与《雷虚》篇中论证“雷者,火也”这一论题时不同,这里对归纳法的应用,明显是错误的。再如,在《骨相》篇中,为了论证: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於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论衡·骨相》)
王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予以证明:
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论衡·骨相》)
高祖隆准、龙颜、美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单父吕公善相,见高祖状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吕后是也,卒生孝惠帝、鲁元公主。(《论衡·骨相》)
由于在中国传统逻辑中,简单枚举法和以偏概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二者的区分往往困难重重,而归纳推理在实际使用中也很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王充所举的例证,表面看来似乎有理有据,具有普遍意义,但实际上往往经不起严谨的推敲,有学者据此认为以偏概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逻辑欠缺的体现。然而,这恰恰是后人对中国古代传统归纳逻辑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归纳逻辑的主要任务不是要作归纳,其着眼点是演绎的大前提,思维过程以演绎得到最终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与西方传统归纳推理具有如下不同的特质。首先,从形式上看,西方传统归纳推理仅是归纳推理,不含有演绎的成分;而中国古代传统归纳推理既有归纳也有演绎的成分,有时还会有推类的成分,是一个复合的推理形式,这一点和中国古代连珠体的推理形式是一致的,也和印度古代的因明推理具有类似的地方。其次,从推理的最终目标来看,西方传统归纳推理的目标是通过对一类事物中的个别事物具有某种属性获得一个关于这类事物都具有某种属性的一般性结论,即从个别到一般;而中国传统归纳推理的目标是通过归纳到的一般性结论演绎生活中的经验准则,即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归纳的结论往往不是作为一般性结论存在,而是作为经验存在的,并且以这种经验作为预测未来,推得未知的大前提。最后,由于中国传统逻辑没有对“有效性”这个概念进行探究,所以,“有效性”就不是中国传统归纳推理的核心概念(尽管中国古代传统归纳推理中具有演绎成分),所以也就不追求“有效性”,转而追求通过经验验证现实(实践)。因此,中国古代的归纳推理是实践的推理,不是理论的推演,这也许就是温公颐先生所说的“内涵的逻辑”。
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既不是单纯的演绎推理,也不是简单的归纳推理,而是对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综合运用,是把归纳的结论作为一种经验固化下来,并把这种固化了的经验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用以指导人们后来的实践活动,其中又隐含有作为范例引起人们注意的意义。所以这种推理,其着眼点不是推出结论,而是重在镜鉴后来,推出未知。
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推理和当代西方逻辑学界关于实践推理的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西方逻辑所讨论的实践推理是“一种直接针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推理。其依据在于对当事者情况的了解以及知道某种行动是达到该目标的途径。它的结论就是命令特定当事者实现行动进程。这一推理的序列之所以被称之为实践推理,是因为其目的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12)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体系之语言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实践推理因其为行动或要求提供理由,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推理,也是一种应用逻辑。诚如张建军指出的那样:“所谓‘敏感于主体认知目标及相应认知资源的逻辑学’,就是本文阐释的‘应用逻辑学科群’;而所谓‘更为一般的转型’,就是本文阐释的‘应用转向’。”(13)张建军:《当代逻辑科学的“应用转向”探纲》,《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
首先,中国传统归纳推理是一种实践推理,是应用于日常思维过程中的,具有极强实践意义的推理,其推理关照的核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运用,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其次,中国传统归纳推理和西方的实践推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西方意义上的实践推理关注的核心是逻辑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中国传统的归纳推理并不是以逻辑理论为先导,而是一种不自觉的逻辑思维过程。没有逻辑理论的指导,很容易推出不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主张,应该把西方的应用逻辑理论拿来用以指导日常思维过程的“实践推理”。
中国传统归纳推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类比推理:其通过列举一个个特殊的实例,试图在这些同“类”实例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结论,再把这个一般性意义的结论置于历史和实践中予以考察,通过正面的和反面的各种情形,得到具有普适性的结论,最后再将这个结论应用于现实指导人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逻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直觉性和便捷性。其直觉性和便捷性在于能够从某“类”特色实例中发现普适性的准则,然后再依据普适性的准则进行实验演绎性的推导。这就如同我们今天使用谚语等熟语时所做的那样:当我们使用一条谚语时,就是在接受前人对一个普遍事实的肯定,然后再从这个普遍事实推论未知,比如“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这样的事实是归纳得来的,使用这条谚语的目的在于推出大雨即将到来。此外,传统的西方归纳法与作为典型中式归纳法的中国传统归纳逻辑并不是那么不同。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归纳逻辑的这种开放性,导致中国古代先贤的思维具有灵动的跳跃性,所以我们很难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严格地将类比推理和中国古代传统归纳逻辑区分开来。
或者换一种说法,类比推理是一种“松弛”的归纳推理,或然性程度非常高,从一个特殊实例到另一个特殊实例。而中国古代的传统归纳逻辑与之相比较,则是一种“紧张”的归纳推理,其推理的着眼点是从一“类”特殊实例中探寻出具有普适性的准则。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归纳逻辑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表面上看似类比推理,而实际上是追求普适性的特殊的归纳推理形式。它既不是独立于西方传统演绎和归纳的特殊形态,也不是和西方传统逻辑的演绎归纳毫无关联,而是对西方传统逻辑的一种综合应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