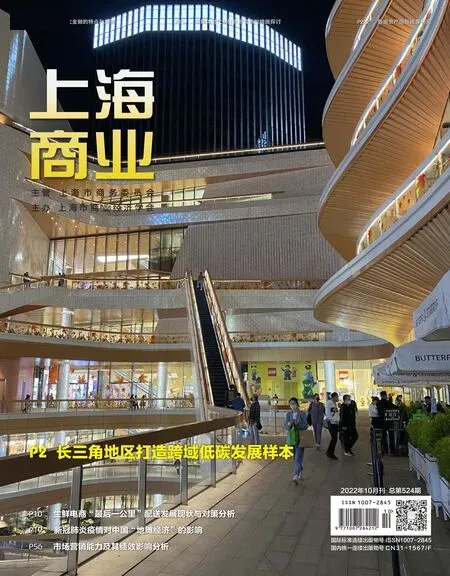从农村宅基地改革看基层治理中的多方主体
——以浙江省为例
2022-12-29蔡甜甜
蔡甜甜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要将重点放在基层。将法治纳入基层治理中,就是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乡村,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和村集体组织、乡村政府的运行都按照现行的法律框架。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闲置宅基地,致使农村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大大限制了乡村振兴的发展。2018年2月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三权分置”,在《土地管理法》确立“一户一宅”的基础上,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促进宅基地的流转盘活。至此,宅基地的退出和盘活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事项。为了深入考查基层治理,笔者以宅基地的退出盘活为主要考察事项,以浙江省为主要考查对象,前往德清县、安吉县、绍兴市和义乌市展开实地调研,通过与村民、村集体组织和基层政府的访谈,了解到宅基地改革遇到的困境和面临的瓶颈,背后所隐含的由于村民、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三方自身不足所导致的基层治理的问题。
二、村民对集体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宅基地闲置在村民之间普遍存在,以“一户多宅”为主要表现形式。村民对于“一户多宅”的违法性质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闲置”的其他表现形式如“长期在外打工,家中的房子空置”和“家中实际使用面积占总面积较小比例”等都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自己超占宅基地的行为是违法的,自己的宅基地是符合闲置要件的,但村民将超占宅基地自动退回村集体的配合度低,将闲置宅基地投入流转利用的意愿不强,其中退回村集体流转利用的更是寥寥。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村民自治力强,自发地利用家中闲置的宅基地如出租、抵押、租赁比例较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村内以老人和小孩为主,村民自发利用家中闲置宅基地的比例较低。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归纳到以下几点:
1.村民自身法律意识淡薄
在基层治理中,村民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而存在,每个村民都享有参与基层治理的权利。但是,村民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法治思想直接影响着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村民的法律意识不强,不仅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影响着上级政策的开展落实,同时对于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参与,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因此,要加强对村民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内涵。
2.参与村内事务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低
现实生活中,村民对于村内的事务关注度低,即使有重要的政策下发,村民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参与除非涉及自身的利益。因此,在村集体组织开展的宅基地确权和“一户多宅”整治等活动中,村民的配合度低,改革活动的推进速度慢。村民是宅基地改革的参与者、受益者。“三权分置”的制度之所以被设计,就是为了提高闲置宅基地的流转利用,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只有激发作为宅基地改革主体的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宅基地改革才能从源头上得到落实,形成长效机制。
3.对村集体的信任度低
根据调研结果,笔者发现在愿意将宅基地退出利用的人群中,愿意退回村集体的人群所占比例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信任村集体组织。村民在接受访谈中,普遍认为村集体组织内的成员不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只关注个人利益,对村民的需求置若罔闻,并不是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村民不信任村集体组织,双方主体之间存在间隙,这会极大地影响村集体组织工作的效力,不利于政策的落实。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协调能力不足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各地的村集体组织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都有一个总括的认识,但具体的理解水平各村庄参差不齐。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如德清县莫干山镇的后坞村、安吉县碧门村和义乌的鲁雅村,村书记对于2018年2月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一定的了解,其中关于资格权、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概念认定和权利归属也理解得比较透彻,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稍微落后的村庄如高坞岭村和小六石村,村集体只是对“三权分置”的概念有所耳闻,但是没有具体的了解,因此在这些村庄,宅基地改革的活动也比较少。此外,不论在哪个地区,闲置宅基地的流转利用大都是以村民自身为主体,村集体组织所起作用小。对于宅基地改革最重要的“一户多宅”现象的整治,除了义乌的鲁雅村因为“旧村改造”基本上消灭了“一户多宅”,其余地区“一户多宅”现象都普遍存在。其背后原因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村集体根本没有着手“一户多宅”现象的整治,二是如安吉碧门村一般曾经开展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不好便作罢了。村集体组织作为联系村民和村政府的中间主体,普遍反映村民对村内事务参与积极性较弱。究其原因,主要因为:
1.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不充分,无法就事项达成统一的认识
在高坞岭村调研时,笔者发现村内的年轻劳动力基本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大量的住房被闲置。采访村民时,提及村集体是否有帮助她们去出租或者利用闲宅,村民普遍反映没有,也不知道如何去出租和其他的利用方式。比照与村集体组织的对话,村干部明知本村有大量的房屋闲置,但从未主动与村民交流闲置宅基地的具体利用方式。当下,部分地区的村集体组织的主要工作都用于应对上级要求,填报数据、整理资料等,应付上级的检查占据了村干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真正与村民之间沟通交流,为村民服务的时间相对较少。
2.村务没有得到及时公开,村集体组织对外公信力弱
乡村基层法律体系是否健全体现在乡村政务是否公开和制度的落实是否到位。从整体上看,大多数的村集体组织都会主动地公开村内的事务,但并不排除有些村集体组织对本村事务选择性地公开甚至不公开。村民作为享有基层的重要主体,对本村事务享有知情权。村集体组织隐瞒或者选择性地掩盖部分村内事务,只能让村民更加不信任村集体组织的工作。此外,村集体组织有落实上级政府下发政策的义务。村民由于不能直接接收上级政府下发的文件,因此对政策的知晓率不高,这就需要村集体组织作为中介去将上级下发的政策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内化”,通过执行的方式来落实。但是,部分村集体组织反而会利用村民对政策的知晓率不高这个特点,对上级的文件和政策进行选择性地执行甚至不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和制度一直停留在纸面,成为“摆设”。
3.村集体对宅基地的退出盘活工作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村集体组织是宅基地改革的组织者、引导者,理应走在前列,但是村集体在实际过程中却并未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村集体没有进行自我管理,逐渐沦为基层政府的附庸
在现实的村治活动中,村集体组织只是机械地将上级领导的政策传达下来,并没有自发地去理解,致使村集体组织的工作趋于行政化,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
法治只有通过落实才能体现其价值,制定好的法律如果没有人实施也只是“白纸一张”。法律法规在乡村的有效落实离不开村集体,但村集体不是行政组织,究其根本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它的一切事务开展离不开村民。只有村干部用心治理好村内的各项事务,村民才会信任村干部并且积极地参与村内开展的各项事务。增强村民信任感的最好途径就是增加村民的收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村集体虽然无法制定政策,但是他们可以积极地挖掘本村的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经济。莫干山镇的后坞村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游客的涌入给后坞村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村民不仅不需要外出打工,更有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安吉的碧门村凭借着丰富的毛竹资源,发展家庭小作坊和直播带货,创立了特色品牌。村集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增强与村民之间的信任,还能保障政策实施,促进乡村振兴。此外,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村干部需要强化法律意识,养成法治思维,主动地将治理主体的行为和治理的具体事务进行全方面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和批评建议,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履职、依法治村。
四、基层管理组织体系与监督机制有待提高
在对基层管理组织调研中,笔者重点访谈了安吉的天荒坪镇和绍兴的稽东镇。笔者发现政府管理在下列几个方面存在稍许不足:
1.政府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明晰,影响办事效率
在与天荒坪镇的农业办人员访谈中可以了解到,天荒坪镇内部一方面各部门分管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宅基地审批事项,没有专管宅基地相关的部门,致使系统性地管理难以形成;另一方面,部门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甚至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宅基地在盘活流转环节被割裂。
2.基层管理组织与村集体组织、村民的联系仍需加强
在与稽东镇的工作人员访谈中了解到稽东镇在“三权分置”政策出台后并没有及时跟进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倘若农民要办理使用权证就必须要经过城建、林业、国土和农业等部门的联合审查。层层的手续不仅使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也让村民心生“疲惫”,致使部分村民选择私建违章建筑,因为违章建筑的成本更低。最终使得一些基层管理组织的管理职能处于一种“失效”的状态。
基层政府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司令部,其统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与发挥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应在政府内部成立专门负责农村宅基地的部门,增强执行力与政府和村集体之间的联动性,更好地落实政策。此外,还应进一步发挥基层管理组织在宅基地管理方面的统筹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充分挖掘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