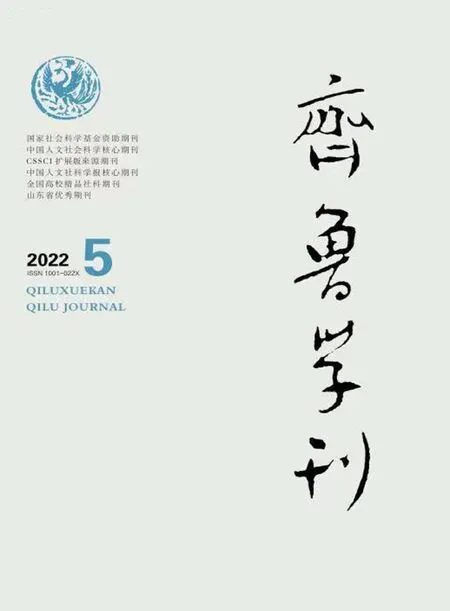从志怪传说论汉《孝女曹娥碑》之伪
2022-12-28李剑锋
李剑锋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99)
所谓王羲之(或称“晋人”)书《孝女曹娥碑》卷,宋末《云烟过眼录》卷一、明《清河书画舫》丑集、清《石渠宝籍初编》“养心殿”等皆有著录,今藏辽宁省博物馆,书法界对其真伪莫衷一是。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七人鉴定小组”鉴定为真迹。杨仁恺《晋人书〈曹娥碑〉墨迹泛考》亦以为真迹,其论略云:“晋人卷轴墨迹,流传甚少。早于《曹娥碑》的《陆机平复贴》同属瑰宝……而《曹娥碑》墨迹的流传,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讨东晋楷书的风格,从而搞清这一时期楷书发展的新貌,还可以通过它推知唐代以来摹刻晋人小楷的真实效果,究竟达到如何的程度。”(1)杨仁恺:《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95-296页。启功《“绝妙好辞”辨》一文主要从用典不切等方面分析了碑文的荒诞。徐邦达《传世王羲之〈曹娥碑〉墨迹考》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比较谨慎,以为属于晚唐以后人临写本;诸临写本“原来不是一个嫡系,但‘远祖’想来还是一样的”,这个“远祖”“不能超过第二代北周临本”,而“文句的伪造,总是要早到晋代”(2)徐邦达:《传世王羲之〈曹娥碑〉墨迹考》,《书学论集——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246、243页。。
书家之论已为周详,然所论角度大多为书法,较少从文本着眼。下文从史实和文本着眼作一考论,以明今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文本及书法实际出于后人杜撰。
一、史书所载曹娥事基本无神异现象
关于孝女曹娥最早的正史记载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4《列女传》,全文如下: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94页。
根据范晔《后汉书》推论,度尚是与曹娥同时代的人。按,“汉安二年”是公元142年,“汉安”是汉顺帝的年号;“元嘉元年”是公元151年,“元嘉”是汉桓帝的年号。也就是说,县长度尚改葬曹娥仅在曹娥死后9年,这一年度尚35岁(4)《后汉书·度尚传》:“(度尚)年五十,延熹九年(166)卒于官。”(范晔:《后汉书》,第1287页)据此知度尚生于117年,按旧历推算,度尚151年为35岁。,比曹娥年长11岁,因此,度尚与曹娥同时代,他对曹娥投江事实的了解是最接近真相的。范晔《后汉书》卷38《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有度尚传记,赞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5)范晔:《后汉书》,第1288页。。范晔是史学家,他记述曹娥投江之事,与对度尚的记述一样,都是遵从实录精神,其记述曹娥投江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怪异传说,写到“投江而死”便戛然而止,不见今传《孝女曹娥碑》“负父尸而出”等内容。
而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捷悟第十一》中引《会稽典录》云: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宋本作“祝”)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6)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79页。按,该段独立引文中的“瓜”字,唐人注范晔《后汉书》引项原《列女传》作“衣”。
《会稽典录》为东晋虞预所撰,所记虽涉及怪异内容,但仅是提到“瓜”似有灵性,在曹娥祷祝17天后忽然沉没,曹娥以为这是神灵显示她父亲已经淹死了,所以自杀殉葬,并没有谈到抱父尸出之事。在范晔《后汉书·曹娥传》李贤注引项原(生平不详,当为唐前人)《列女传》中,“瓜”换为她父亲的衣服,情况类似。《后汉书》李贤注又引东晋虞预《会稽典录》云:“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7)范晔:《后汉书》,第2795页。这里所记度尚与邯郸淳的关系与《世说新语》所引《会稽典录》是相合的。又《会稽典录》和《后汉书》所记一样,度尚改葬的只是曹娥,至于其父葬处和所葬有无尸首都不得而知。如果如今传《孝女曹娥碑》所云是“抱父尸出”,那么父女安葬之处当相邻,若只改葬女儿而不涉及父亲,于常理不合。可见在东晋南北朝的记载中,改葬只涉及曹娥,不涉及其父,且改葬的是骨殖还是衣冠不得而知。如果改葬只涉及曹娥,那么最大的一种可能是时人只发现了曹娥尸首,至于其父尸首,因大潮冲击、又过去了至少17天,当仍未发现。
清严可均所校辑的邯郸淳《孝女曹娥碑》却出现了关于曹娥父尸的记述,其序文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王羲之书作“景”)沉(一作“流”),爰来適居。盱能抚节案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8)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秦汉三国六朝文·三国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96页。辽宁图书馆藏王羲之书《孝女曹娥碑》影印本,据《王羲之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据严可均注,此文辑录于《古文苑》。《古文苑》是北宋孙洙发现的,相传为唐人旧本,所录乃“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9)章樵:《古文苑序》,章樵注、钱熙祚校:《古文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第8页。,《古文苑》之前不见该碑文的引录。这篇碑文序文所记内容与《会稽典录》《后汉书》等史籍所载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曹娥抱父尸复出的神异传说。晋宋史书所载是曹娥投江而死,而《古文苑》所载却出现了曹娥死后五天“抱父尸出”的奇异之事。此碑文与辽宁博物馆所藏文字相同,尤其是都有“经五日,抱父尸出”的奇异记述,且丝毫没有提到正史中所言改葬之事。这显然与历史记述基本没有神异传说的情况不合,即真实的历史只是曹娥因悲痛过度等原因投江殉葬,并没有投江五天之后抱父尸而出的记载。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邯郸淳所作碑文中真有这样的记述,那么,对于如此非常之事,范晔不会看到了而不采择。
一言以蔽之,从最初的可靠历史记载来看,孝女曹娥的故事没有今传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所谓死后五天“抱父尸出”的神异传说。
二、曹娥神异情节乃基于历史的时代传说
如果联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今传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所记曹娥“抱父尸出”的神异故事实际上属于魏晋志怪小说中“孝感”故事中的一类。
李剑国《略论孝子故事中的“孝感”母题》把孝感故事分为6个类型:一是“感天得食”,如《太平御览》卷836及卷922引《孝子传》所载王祥扣冰得鱼;二是“感天愈疾”,如句道兴本《搜神记》所记张嵩因母病大哭得天赐堇菜,母食疾愈;三是“感天得金”,如原出刘向《孝子传》,为《搜神记》等转载的郭巨埋儿得金事;四是“丧葬感物”,如《艺文类聚》卷92引王韶《孝子传》云李陶之孝感得群乌衔土筑坟;五是“感天偿债”,如《搜神记》所记孝子董永卖身丧父得织女帮助偿还债务;六是“感天明冤”,如《搜神记》所记东海孝妇受冤死后所发三桩誓愿得到实现(10)李剑国:《略论孝子故事中的“孝感”母题》,《文史哲》2014年第5期,第55-60页。。如果把曹娥投江“抱父尸出”的故事进行归类的话,勉强可以归入“丧葬感物”类,但曹娥感动的是神灵,而不是事物。因此,不妨把曹娥故事归纳为“孝女感神”类,可作孝感母题故事的第七类。这类故事在干宝《搜神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记述。
《水经注》卷33“江水”记“先络托梦”故事如下:
县长赵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诣巴郡,没死成湍滩,子贤求丧不得。女络年二十五岁,有二子,五岁以还,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丧,络乃乘小船至父没处,哀哭自沉,见梦告贤曰: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县上言,为之立碑,以旌孝诚也。(11)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2-773页。
女子先络孝感故事属于因孝女至孝而感动神明的故事类型。先络父亲淹死沉尸江中后,她求尸不得,便投江自沉,死后,她的魂灵托梦给自己的兄弟说在某日浮出水面,至期果然。先络孝诚感动郡县,遂得立碑嘉奖。这个故事又见于《后汉书》卷84《列女传》,《太平御览》卷396引晋陈寿《益部耆旧传》,《法苑珠林》卷49引晋干宝《搜神记》,故事基本情节相同,尤其是自沉托梦的情节完全一致,只是人名和个别细节有出入,如孝女的名字作“雄”。值得注意的是,先络(或者先雄)托梦之事发生在汉顺帝永建元年(126),早于曹娥投江16年。同是载入《后汉书·列女传》的孝女,叔先雄传中有托梦告诉其弟“当共父同出”的奇异之事(12)范晔:《后汉书》,第2800页。,而曹娥传则丝毫不及后世所传“抱父尸出”的神异传说。这也可以说明范晔所见材料并没有“抱父尸出”的情节内容。
《水经注》同卷又引晋陈寿《益部耆旧传》所载“张真妻”的故事,其事与先络故事相类:
张真妻,黄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没,求尸不得,帛至没处滩头,仰天而叹,遂自沉渊,积十四日,帛持真手于滩下出。时人为说曰:符有先络,僰道有张帛者也。(13)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71页。
黄氏女可以说是第二个先络,既然是“积十四日”方出,当然也是死后与张真同出,只是她所以死求索的尸体不是父亲的,而是丈夫的。同卷又有 “姚精二女”的故事:
江水又东北迳郫县下,县民有姚精者,为叛夷所杀,掠其二女,二女见梦其兄,当以明日自沉江中,丧后日当至,可伺候之,果如所梦,得二女之尸于水,郡县表异焉。(14)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67页。
在父亲为叛贼所杀后,二女遭受劫掠,不愿苟活,以死明志,她们死前托梦给自己兄长,说明自己尸体出现的日期和地点,后来“果如所梦”。这又变亲人托梦为亲自托梦以得安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论》也记载了“二姚见灵”的传说,其记述较为周详:
广柔长郫姚超二女,姚妣、饶,未许嫁,随父在官。值九种夷反,杀超,获二女,欲使牧羊。二女誓不辱,乃以衣连腰,自沉水中死。见梦告兄慰,曰:“姊妹之丧,当以某日至溉下。”慰寤哀愕。如梦日得丧。郡、县图像府庭。(15)常璩著,刘琳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36页。
这类精诚见灵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起因,都是人淹死后亲人不能搜寻到尸首;还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获得亲人尸首的模式,即活着的亲人精诚所至,以自杀殉葬感动神明或托梦的方式,最终使得尸首浮出江面,入土安葬。他们的孝行、真情和贞洁感动了世人,受到后人的嘉奖和怀念。这类故事产生的地点都在江水边,与曹娥故事产生的地点有相似性。
《水经注》卷40《渐江水注》“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条也记载了曹娥的故事:
(上虞浦阳)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 若值父尸,衣当沉; 若不值,衣当浮。裁落便沉,娥遂于沉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16)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947页。
上述引文有两点令人疑惑。一是,邯郸淳在《后汉书》和《会稽典录》中是度尚“弟子”,这里变为“外甥”,启功以为“弟子”乃是女弟之子,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外甥’一词不可能是郦道元杜撰而来的,而后世所传碑文中,却并不见‘外甥’、‘弟子’的字样。”(17)启功:《“绝妙好辞”辨》,《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香港:大公报编辑部,1978年,第349页。二是,《水经注》虽然记述了衣服落水便沉的怪异之事,但没有记述“抱父尸出”的神异之事。联系《搜神记》等所记孝感故事来看,李剑国所论6类孝感故事中的父母都是健在或者正常死亡,而“孝女感神”故事中的父亲却是出于意外无常死亡,且尸体失踪。《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引孔子语曰:“孝子之事亲也……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又《丧亲章第十八》云:“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18)邢邴等注疏:《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57、5570-5571页。礼以入土为安,连尸首都不能找到,《孝经》所云致哀、致祭之礼都无从谈起,孝女欲尽孝而不能,在过分突出孝又深受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影响的时代遂产生了以死殉父的悲剧。先络故事是如此,曹娥故事也是如此。联系上面所引诸女感应的志怪记述来看,《后汉书》《水经注》记述曹娥而基本不涉及神异的合理解释是:曹娥故事与“先络托梦”彼此没有相互影响的联系,也就是说,“先络托梦”是在孝感故事的时代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同类型模式故事中的具体个案,曹娥故事不是因为受到先络故事的影响而产生的。
由此也可以推论,曹娥故事在郦道元的时代还没有过分神异化,其所神异的只是借助衣服或者瓜果寻求神示的举动,总体上仍然保存着历史的质朴状态。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的话,今传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的记述文字是值得怀疑的。《水经注》记述的水道沿途故事大量涉及神话传说,有搜奇记异的倾向。在本该出现志怪传说的《水经注》里都没有“抱父尸出”的神异之事,何况在离曹娥投水仅仅9年的《孝女曹娥碑》里呢?曹娥投水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时并没有违反现实常识的怪异之事。但经过县令度尚表彰之后,为世人所知,在尊崇孝道、鬼神繁多的文化氛围中,遂演化为一个孝感故事,最迟到东晋出现了借助瓜、衣服沉浮测验是否找到父尸的奇异情节。至于 “抱父尸出”的情节还在其后,最为晚出。
因此,既然原始的邯郸淳《孝女曹娥碑》不会有“抱父尸出”的记载,那么不但王羲之不可能书写有记述“抱父尸出”的神异之事的《孝女曹娥碑》,其他晋人恐怕也没有这种可能。
三、曹娥“抱父尸出”的传说乃出唐代
那么曹娥“抱父尸出”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与唐人当脱不了干系。
从现存史料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10最早记载曹娥“三日后与父尸俱出”: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旰,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19)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5页。这段引文之后,还接着记述了蔡邕、曹操读碑二事。旰,应作“盱”。
此与前面所引东晋时《会稽典录》的记述类似,但明显增加了“三日后与父尸俱出”的怪异情节,这是此前史料所没有涉及的。之后唐修《晋书·夏统传》又记载说:
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20)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29页。
以上引文是西晋隐士夏统所言,夏统本是会稽永兴人,他因地理之便而熟悉曹娥之事,对照《后汉书》记载,他所说的“后乃俱出”虽有历史传说化的意味,但也只是说父女之尸体“后乃俱出”而已,没有说曹娥“抱父尸出”。但这已经为“抱父尸出”埋下了种子。
盛唐时康子季有《对孝女抱父尸出判》为他人所未注意,其文云:
钱塘人孙戬少以迎涛为事,因八月迎涛(一作“潮”),乘船冲涛,船覆至死。戬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设祭,而因自投江水,抱父尸出。县司以为纯孝,欲立碑,州司不许,乃禁媚容数日(一作“月”)。
……初均洛媛,持弱态以凌波;竟学曹娥,抱沉骸而出浪。(21)董诰等:《全唐文》(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78页。
媚容“自投江水,抱父尸出”,作者以为是“竟学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这里可有两解:一是“竟学曹娥”投江而死,二是不但学曹娥投江而死,而且学她“抱父尸出”。如果是后者,则盛唐时关于曹娥的传说已经有“抱父尸出”的情节了。而从该判文的上下语境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又阙名《对男取江水溺死判》云:
顾乙从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为之服。
顾乙……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将植杖之男,当其抱瓮之役。异曹娥之父,无复还尸;均屈原之妻,空余往恨。(22)董诰等:《全唐文》(第10册),第10177页。
这里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溺死的某男“均屈原之妻,空余往恨”,如沉江的屈原一样,尸首无回,而与曹娥之父尸体的结果不同;“异曹娥之父,无复还尸”向我们传达了一个确切信息,即曹娥“父子丧尸,后乃俱出”或者“抱父尸出”!如此则知唐代曹娥故事肯定有类似“抱父尸出”的情节了,而且很可能在盛唐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度尚所立曹娥碑,闻名久远,至唐代尚传。《会稽典录》载:“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23)范晔:《后汉书》,第2795页。,刘敬叔《异苑》卷10亦云:“陈留蔡邕字伯喈,避难过吴,读《曹娥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24)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第95页。《世说新语》亦载此事,只是移祢衡作杨修。此事真伪姑且不论,但有一点信息应该是确切的,即此碑南北朝时可能尚存。又有论者指出:“盛唐时此碑尚存,故李白云游吴越之地,亦曾游历曹娥庙,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云:‘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人延伫,入剡寻王许。笑谈曹娥碑,沉吟黄绢语。’然至中唐以后,此碑不幸毁坏,故刘长卿《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有‘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之语,赵嘏《题曹娥庙》亦有‘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晚唐释贯休《曹娥碑》:‘高碑说尔孝应难,弹指端思白浪间’,可知此碑中唐时已损坏,至晚唐时尚存残碑,其文尚可识。然至北宋,则碑文亦摩灭而不可识,故《集古录》、《金石录》、《隶释》均未著录,另据《宝刻丛编》引《会稽志》云:‘其碑岁久,字多讹缺,至景德中重立’,可知此碑于北宋景德年间被人翻刻,但后世不传。”(25)张鹏飞:《汉孝女曹娥碑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 年第5 期,第11页。这些唐人的诗歌言论里没有涉及“抱父尸出”的内容。
今世所传“王羲之所书碑”是诸曹娥碑中最古者,“原碑今已不存,唯存清翻刻碑”(26)张鹏飞:《汉孝女曹娥碑考》,第11页。。据此刻碑文,蔡邕题识曰:“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欲堕不堕逢王叵。”文末属“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之”。此碑题识似乎在说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王羲之重新书题了曹娥碑文和相关说明。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一者,据上考述,此时曹娥碑尚存,王羲之何必多此一举?二者,“欲堕不堕逢王叵”不似汉魏语,乃唐人俗语。鲁迅从唐李瀚撰、宋徐子光注《蒙求集注》卷上等辑唐人孔慎言《神怪志》佚文云:“将军王果,昔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悬之在半崖,似棺椁,令人缘崖就视,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有石志云:‘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果视铭怆然云:‘数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为营敛葬埋,设祭而去。”(27)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6页。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卷65“葬”类“欲堕不堕逢王果”条注解云:“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据《太平广记》补)重收我。’果叹曰:‘吾今葬此,今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广记》)”(28)白居易原本,孔传续撰:《白孔六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既然注解末标明的引文出处乃宋人《(太平)广记》,则该条注解实出宋人孔传,其所记王果为唐人甚明(29)据余寅撰《同姓名录》卷5等知历史上有三位“王果”,一出《南华经》,为先秦王果,一为宋王果,一为唐王果。《神怪录》乃唐人小说,所记为唐王果无疑。,《旧唐书》卷192《隐逸传》之《卫大经传》曾记述到王果,乃开元间人。启功在《“绝妙好辞”辨》一文中还引到唐刘餗《隋唐嘉话》所记王果铭文:“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30)启功:《“绝妙好辞”辨》,《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第356页。因此,“欲堕不堕逢某某”句式乃唐人俗语,蔡邕何由题写?唐袁郊《甘泽谣》有三生石传说,三生乃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生百年,三生三百年,故“三百年后”云云乃佛教因果三生轮回语,东汉末年佛教尚未流行,蔡邕如何先知?
总而言之,从曹娥故事的历史记载和南北朝传播状况来看,今传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文乃伪作,所谓王羲之重书《孝女曹娥碑》文字内容与《古文苑》所录相同,当然也是伪作。而从唐代已经流传曹娥“抱父尸出”的传说和“欲堕不堕逢某某”句式乃唐人俗语等来看,今传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书法当是唐人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