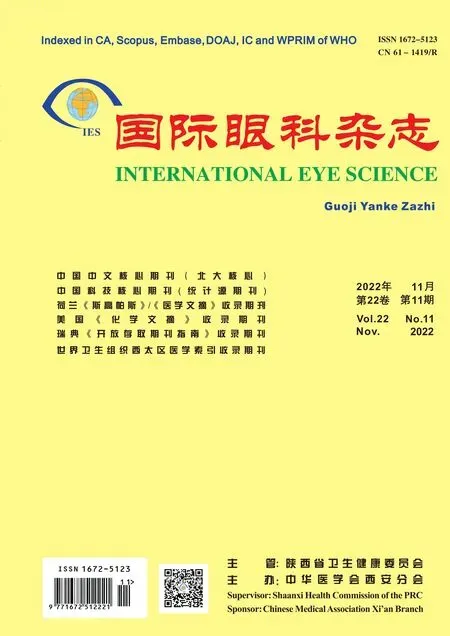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方法与进展
2022-12-24尤佳璐惠延年
尤佳璐,惠延年,张 乐
0 引言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状态,指在调节放松状态时,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不能落在视网膜上而聚集于视网膜前导致视物不清。通常是由于屈光介质的屈光率过大(屈光性近视)或眼轴过长(轴性近视)造成,且受到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1]。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造成严重的损害(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等)甚至致盲[2-3],还会影响患者心理健康[4-5]。青少年时期是心理障碍最容易出现的时期[6],其心理健康会受到全身疾病的影响,进而对成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以往已有一些研究关注此方面的问题,但内容多有局限性。对于青少年近视患者的心理健康研究方法也很少涉及。基于此,本篇综述重点介绍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研究方法和防治策略等内容,以期有助于对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全方位防控。
1 近视的流行病学
1.1青少年儿童近视患病率及特点近视作为常见的眼部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7]且患病率逐年上升,尤其在东亚地区高发。Holden等[8]预测2050年全球将有47.58亿人罹患近视(占全球人口的49.8%),其中高度近视患者9.38亿,占世界人口9.8%。另外,近视患病率存在地域差异,中国近视患病率高于全世界其他国家[9]。其中青少年群体近视更是呈现患病率高、增长速度快、发病年龄小的特点[10],到2050年青少年儿童的近视患病率约为84%[11]。我国学生升学压力大、近距离阅读时间长,导致近视年龄越来越小,青少年成为近视患病率最高的群体[12]。特别是6~9岁是近视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儿童更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13]。近视在年轻时进展快[14],早发近视又增加了成年后高度近视的风险[1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近视率52.7%,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14.3%,与2019年底相比我国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1.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最多,可达15.2%[16]。2021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超过60%[17]。
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是评估研究结论随时间变化的可靠证据。为了解青少年近视特点并将其推测到更大的学生群体,Li等[10]将北京市海淀区37 424名学生按照视力分为非近视组、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进行了为期10a的观察,结果显示近视率逐年上升,其中高度近视组在所有亚组中增幅最显著,而非近视组和低度近视组患病率逐年降低。进一步对比性别差异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容易罹患近视,特别是中、高度近视。这可能与女生近视率基线高,倾向于室内活动等特点有关。Dong等[11]对中国青少年近视情况进行文献检索汇总后得出相同结论,并指出近视趋于低龄化且与学习年份、城市居住地等相关。
1.2与近视相关的心理障碍发生率青少年处于身体和心理快速发展时期,在心理发育不成熟、竞争激烈的教育体制及更多新事物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心理障碍的发生逐年增多[18-19]。何玉萍等[20]发现近视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诊断焦虑者达21.70%,抑郁者24.30%,合并焦虑和抑郁情绪者16.52%。赵荣凤等[21]发现在196名心理健康不达标的小学生中,近视患病率达43.86%,而120名心理健康达标的小学生中,近视率仅为10%。由此可见,近视相关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小觑,如果不及时干预心理问题,情况会随年龄增长逐渐加重,进而影响生活质量[22-23],甚至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视力下降与心理障碍密切相关[20],心理障碍通常与身体疾病合并存在[24-25]。Ayaki等[26]和Wu等[27]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对近视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远大于视功能,说明心理障碍可能是影响近视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重视近视患者心理问题对其生长发育更有益。
2 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量表是有效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合理选择量表是评价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前提。多数关于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均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及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此类量表简便易行、操作易掌握,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信息,特别是在大群体测量时效率较高[28]。此外,该类量表针对中国人口特点进行标准化[29],不仅可以定性焦虑、抑郁状态,还可以定量症状程度[30-31]。但以上量表可评估的疾病局限,不能全面反映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且初始样本量较小在筛查中准确性不稳定[32]。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可以解决上述疾病局限的问题综合评价心理状态,但SCL-90量表是一种标准参照测验,初衷用于存在心理疾病患者自评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病情变化,不适合评价正常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且此量表引进时间较早,常模不更新易造成评价结果偏差[32],故使用SCL-90量表评价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恰当。
2.1沃里克-爱丁堡量表虽有证据表明青少年儿童和成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存在大量重叠,但两个群体心理发育存在差异,故不能一味套用成人量表。用于青少年心理测评的沃里克-爱丁堡量表原版即是青少年作为被试评估积极心理健康水平[33],在多国青少年人群中得到验证[34-35],且在性别与年龄组的标量具有测量不变性[33]。目前心理健康问题很重要的是缺乏适当的基于人群的措施,沃里克-爱丁堡量表既可应用于患者群体也可应用于一般人群,解决了评价一般人群心理健康的难题。合格的量表需要良好的项目分析,同时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32],赵必华等[36]测试沃里克-爱丁堡中文版量表后得出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2wk后结果相关系数为0.67,表明其具有较好的校标关联效度及跨时间稳定性。
2.2青少年焦虑与抑郁测试量表青少年儿童焦虑、抑郁高度共病,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C)既可以定义受个人状态限制的暂时性焦虑又可以定义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焦虑。中文修订版可以体现抑郁患者与正常人焦虑水平的差异,其有效性在中国青少年儿童中已得到验证[37]。Han等[38]对2 117名中国在校学生进行量表测试并通过因子分析和探索性结构方程建模决定最优因子结构,结果显示在中国学生群体中具备最优四因子结构、跨性别严格不变性,且在患者与正常人群之间具备跨组测量等值性。针对青少年学生焦虑症状量表准确性较好的还有学前儿童焦虑量表和儿童焦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学前儿童焦虑量表用于评估广泛的焦虑症状,侧重于一般焦虑生理、情绪和行为[39],而儿童焦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最初就是由儿童社区样本开发,主要评估与特定焦虑相关(如分离焦虑、社交恐惧等)的焦虑症状[40]。
总体而言,青少年儿童近视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选择沃里克-爱丁堡量表较为合适,针对特定疾病需求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学前儿童焦虑量表及儿童焦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也有不错的表现。而多数此类研究采用的SAS、SDS、HADS及SCL-90量表可能不适合,具体量表的选择还需要依据研究设计而定。
3 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3.1焦虑与抑郁早期感觉受损与心理适应不良相关,青少年心理发育呈现明显阶段性及可变性,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近视青少年儿童面临更多潜在压力,是否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为了探究二者联系,Li等[41]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1 103名平均年龄15.3岁的学生,依据球镜度数分组并进行SAS及SDS测试,结果发现近视学生无论近视度数高低焦虑情绪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视力学生,且SAS评分每增加1分球镜度数增加0.0848D,而抑郁情绪发生率在近视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对比量表得分发现,近视组与正常对照组在严重抑郁时存在差异,可见评估抑郁症使用SDS评分更准确,能检测到抑郁状态更微妙的变化。该研究表明青少年儿童近视与焦虑的相关性比抑郁紧密,并提示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与屈光不正的程度呈正相关。分析可能是由于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患者在生活中担心发生眼部并发症甚至失明,遭遇更多他人嘲笑及人际关系、学习遇到阻碍等。其他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也发现,近视学生焦虑、抑郁发生率高且与眼轴长度、近视时间、戴镜时间呈正相关,尤其在女生中表现更为明显[42-43]。除上述针对焦虑、抑郁的评估,郭秀伟等[44]使用SCL-90量表综合评估青少年心理健康情况,结果发现近视组SCL-90总分、阳性项目数量、阳性项目均分与正常视力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焦虑、抑郁两项差异尤为显著,其程度可以认为存在该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说明近视青少年儿童整体心理健康情况不佳,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更突出。azarczyk等[45]提出近视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是否会在成年后长久存在并形成稳定特质焦虑?为解决这一疑惑该研究对239名学生进行STAIC测试,结果显示近视组焦虑症状的发生率高于正常视力组且发生恒定焦虑倾向的几率更高。
近距离学习、屏幕使用时间长是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近距离工作时间长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46]。不少青少年儿童就诊时发现存在调节痉挛(即假性近视),现有研究显示视疲劳造成调节痉挛也可以表现为焦虑、抑郁等内化疾病,故调节痉挛也应引起足够重视。Kara等[47]随机纳入21名调节痉挛患者进行SCL-90量表评估,其中15名患者(71.4%)在测试期间接受精神科诊治,进一步相关性分析后得出心理健康障碍严重程度与调节痉挛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提示近视发生之前可能已经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此外,现有研究提示近视青少年较正常视力青少年更容易焦虑、抑郁,但部分研究使用量表不恰当,还需要更多大样本量、恰当量表工具的研究将此结论重复于更大样本的青少年群体。
3.2情绪化与内向型人格偏向人格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情绪和行为特征,相对稳定且可被预测,健康稳定的人格是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基于临床上对近视学生安静、内向趋势的观察,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眼健康对人格特征的影响。郭秀伟等[44]对365名近视学生与285名正常视力学生(对照组)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发现近视组以情绪型人格为主,对照组以外向型人格为主。情绪型人格群体心理压力大、面对变化往往产生过分激烈反应;外向型人格在面对变化时多呈现积极反应,这种人格差异造成近视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刘晓玲等[48]比较143名近视学生和143名正常学生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结果发现近视青少年以情绪型人格为主。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近视程度青少年人格特点,刘晓玲等[49]收集286名近视学生并分为高度近视组和中低度近视组,比较两组学生人格特点测试结果发现高度近视组学生心理压力大于中低度近视组,人格特质更趋于不稳定。
Coren等[50]早在1994年就近视学生人格问题进行两项大样本研究,首先将1 014名在校大学生根据眼部检查结果分为正常视力组和视力下降组,对受试者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并从外向-内向、神经质-稳定性两个维度评判,发现视力下降组学生外向维度得分低于正常视力组。在此结果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评估近视学生人格特点,选取1 148名大学生使用大五人格量表(Neuroticism,NEO)再次进行相同试验。NEO人格量表是对人格五因素理论中主要维度的合理度量,能更全面反映被试者人格特性。研究结论与之前相同,即近视学生更倾向于内向。周艳丽等[51]对823名近视本科生进行性格问卷调查发现近视学生有一定心理负担,较正常视力学生心理状态差,最突出的就是性格内向。为临床上近视学生人格不同于其他群体提供了证据支持。近视学生人格除内向、情绪化外还具有高敏感、低怀疑、低稳定、偏执的特点[52-53],长此以往这些特点使近视学生心理健康受到损害,严重影响心理发育。
3.3孤独感与社交障碍蔡晶晶等[54]随机抽取3所在校学生,使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儿童孤独量表和儿童自尊量表测试,发现近视学生有较强孤独感,较低自尊心,且存在社交障碍。进一步分为正常视力组、初发近视组、中度及以上近视组比较发现,初发近视组社交焦虑更严重,这可能由于初发近视学生还无法适应近视生活带来的诸多变化。林素兰等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8~14岁学生552例进行类似研究也发现近视学生社交焦虑发生率大于非近视学生,并指出更高年级学生、更高度数近视、更长戴镜时间、女生更容易发生社交焦虑[55]。
3.4睡眠障碍近视青少年睡眠质量更差,Ayaki等[26]对278名20岁以下高度近视学生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估睡眠情况,发现高度近视学生具有主观睡眠质量差、入睡时间晚的特点。睡眠质量差使视觉相关生活质量下降导致心理障碍。何娟等[56]在一项涉及354名8~18岁学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结论,该研究发现,青少年中高度近视影响视觉相关生活质量,且近视越严重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越差,女生相较于男生受到近视的不良影响更大。不良心理状态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呈负相关,且大于近视视功能对患者的影响。
3.5学习适应性与认知障碍赵荣凤等[21]对316名小学生进行《中小学心理健康系统》学习适应性调查(AAT),结果显示近视组在学习适应性方面明显差于正常对照组。近视提高认知功能过早下降的风险[57]并更容易出现注意力缺陷等问题[58-61]。这些不良心理健康问题互相影响,严重阻碍学生成长发育及社会发展。
4 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防治策略
近视学生总体心理健康较正常视力学生差,WHO(Word Health Organization)报道全球约有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导致的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62]。青少年时期是预防精神疾病的重要阶段,防治近视的同时要遵循青少年学生心理特点,抓住可塑阶段,关注心理健康。
4.1矫正近视获得最佳视功能我国青少年近视矫正率及矫正合格率较低[63],要大力宣传和纠正一些家长关于配戴眼镜的误区,如不愿验配眼镜,认为眼镜会增加近视度数等错误观念。近视患者及时、适当矫正视力获得最佳视功能是首要措施。研究表明,视力提高可以改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提高视觉相关生活质量[56]。青少年儿童多采用框镜和直接接触镜矫正视力,蔡晶晶等[54]根据矫正手段不同将732名近视学生分为框镜组和角膜塑形镜组评估学生心理状况,发现角膜塑形镜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好,社交焦虑较小,框镜组学生自尊感较低。Guan等[64]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252所学校的2 851名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试(MHT),结果显示戴镜治疗可以提高学生标准化成绩,但除了降低身体焦虑外对心理健康影响不十分显著,分析可能是由于不同学习强度学生相反效应相互抵消所致。该研究进一步评判学习强度异质性影响发现,戴镜治疗加剧了学习强度低的学生学习焦虑,而改善了学习强度较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低强度及中强度学习的学生戴镜后被嘲笑的几率分别上升了13%和11%,均有统计学上的明显上升,而高强度学习的学生无上升。提示眼科医生在选择矫正方式时应考虑心理健康方面因素,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制定方案,并在长期随访过程中严密观察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方案。
4.2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近视学生还应该养成良好用眼姿势及习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表明,每周户外活动时间增加1h,近视率降低2%[65]。久坐、长时间近距离学习会增加注意力不集中、自尊感降低等心理健康问题[59, 61],青少年儿童就诊时应该多次强调护眼规范,敏锐识别近视学生是否存在潜在心理障碍风险,并针对这些影响心理健康的可变因素进行多方面防治。
4.3心理辅导与积极参加群体活动由于青少年发育的特殊性及对一般人群筛查灵敏度的要求,高危青少年儿童就诊时,眼科医生应常规选择合适量表评估心理健康状态。根据筛查情况请相关科室协助辅导心理健康,并在此基础上引导青少年儿童正确认识近视。此外,父母的最佳养育方式可能会缓解青少年外化症状[66],因此近视儿童父母的关心及正确引导有益于心理健康。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应贯穿青少年儿童校园教育中,注重同伴教育,提高心理资本。
5 小结与展望
国内外关于青少年儿童近视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局限性。近视可能会导致不良情绪及人格已基本得到证实,但仍存在不少待解决问题,如部分研究通过不恰当的评估量表得出结论的可靠性需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更简便且客观的针对近视青少年儿童心理状态评价的工具,除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状态外,近视是否会对其同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认知功能[67]等造成影响。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已成为不容小觑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心理健康也是全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关注青少年儿童近视问题的同时,应筛查其心理健康状态并及时进行干预。未来临床工作中,近视防治应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并联合多学科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将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作为整体十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