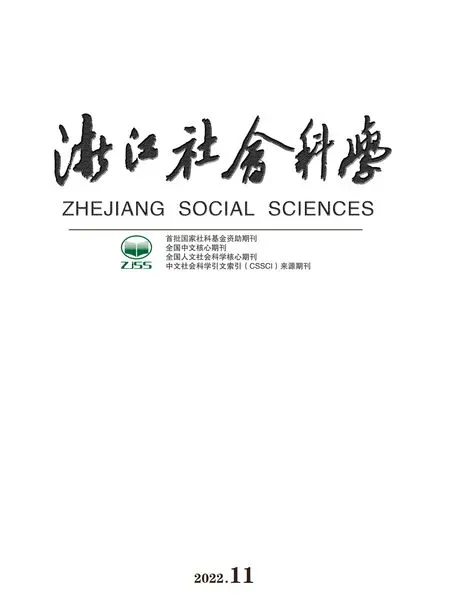法治思维: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
2022-12-23张志铭钟欣
□张志铭 钟欣
内容提要 法治思维要求社会生活主体按照法治的要求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法治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国家治理中的一切事务,故而法治思维最为简约的定义是思维主体按照法律的规定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立场认识法治思维应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从权利概念入手,辨析利益与权利,并动态展示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的进程。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利益转化为权利应经过利益识别、利益正当性证明和利益被权威认可三个步骤,以此为基础,从利益主张中转化生成权利诉求的过程包括应予识别的四个环节,即主张利益、主张正当的利益、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以及主张可以或可能归入权利的权益。
引言
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并在其中指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①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构设之中。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别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两个标题之下要求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②,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③。
在顶层制度设计的指引下,“法治思维”被逐渐写入地方性文件,在部分地方性文件中,法治思维的运用主体不限于“领导干部”、“党员干部”,而是包括两者在内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④、“司法行政工作人员”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⑥或“全体工作人员”⑦。同时,作为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之一,“法治思维”亦成为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中的热门词汇,比如,把握法治思维的体系性内涵科学立法,⑧运用法治思维处理信息化社会矛盾冲突和办理涉疫情刑事案件,⑨运用法治思维应对突发事件、破解交通管理难题、建立食品安全司法监督机制和解决税收行政争议等等。⑩
显然,法治思维的运用已经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之一,正确运用法治思维不仅能够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目标,还能划定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底线、判断纠纷解决方案的恰当与否。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如何理解和运用法治思维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一、法治思维的概念梳理
理论研究认同法治思维是一种区别于人治思维的治国理念,并在此基础上从规制权力、保护权利、遵守规则和依法裁判四个角度分析法治思维的概念。以权力规制为目标所展开的研究将公权力的行使者视为法治思维最主要的运用主体,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运用法治思维阻止权力的滥用,站在权利保护立场之上的论述将法治思维理解为多种思维方式的统一体,相关研究倾向于从不同的维度解读法治思维的特性和内涵。与注重观念养成的权力规制思维和权利保护思维略有不同的是,规则思维和法律思维更加关注法治思维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学者大多将法治思维看作是一种用于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并在法治实践的场景之中探讨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具体事务,规则思维和法律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法治思维的运用主体扩大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后者则侧重于对法律职业技能的探讨。
权力规制视角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认为,法治思维的精髓是“根据法治理念,对‘依照法律进行治理’问题的系统思考”,运用法治思维的目标之一是消除“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的两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其中,“来自上面”的问题关注如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来自下面”的问题包括如何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等。相关学者认为,法治思维引导下的“法制”能够有效抑制领导干部“无法无天”、“恣意妄断”的行为,法治思维引导下的“法治”能够实现“用法律的权威性”替代“领导的权威性”、用“法律的公正性”替代“领导的不可错性”的目标。⑪与此相似的研究认为,法治思维是“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观念”,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消除“维稳型”、“强权型”等人治思维的过程。⑫在权力规制思维相关的研究中,部分论述在定义法治思维的同时,也针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和运用提出建议,比如,建议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做到“六问”,以保持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⑬提倡领导干部树立“国家权力来源的契约观念”、“限制国家权力观念”、“尊重个人自由观念”和“执政党守法观念”。⑭
在权利保护思维相关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将法治思维看作是以合法性思维为基础的复合型思维,比如,认为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是“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和“公平正义思维”的统一,⑮或者将法治思维定义为“以合法性为出发点,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按照法律逻辑和法律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并建议领导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时保持权力法定、权利义务统一、重视程序和证据。⑯另有部分研究以人权保护、程序公正、文明执法等关键词揭示法治思维在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中的积极作用,比如,认为法治思维是“理性之治的思维”、“动态之治的思维”、“合法之治的思维”,从“宪法法律至上、倡导良法为治”、“尊重人权和自由、维护秩序和安全”、“依循职权法定、主张正当行权”、“要求公平对待、允许合理等差”、“坚持程序正当、注重实体正义”,以及“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监督”等六个方面阐释法治思维的内涵,⑰或者认为法治思维是“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和“契约思维”的统一,并从权力规制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探讨领导干部应如何运用法治思维,⑱抑或从“坚持人民主权”、“切实保障人权”、“保障社会公平”、“遵循正当程序”、“平和文明执法”、“维护法制尊严和权威”等六个方面分析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⑲
认为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是规则思维的研究强调包括法律在内的多元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⑳有学者提出,法治思维作为规则思维的用意在于坚持“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和“恪守非人格化权威”,“普遍性优于特殊性”要求领导干部在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时优先考虑普遍性,其次考虑特殊性,“恪守非人格化权威”禁止“权力的主体人格化”,以防止出现“公器私用、以权谋私”的现象。㉑规则思维相关的部分研究将法治思维的运用主体扩大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有学者认为,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社会管理实则是运用法律手段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多元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并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防止权利滥用和对权利的“超前消费”。㉒也有学者直接提出规则思维的概念,即“以法律规则为基准,强调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依据规则、运用规则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规范认识、分析、评判、推理和形成结论”,该学者认为,作为规则思维的法治思维不仅能够提升公权力机关的社会治理能力,也能够为公民理性思考利益主张和寻求权利救济提供行为指引。㉓
与规则思维相似的另一种理论观点是在方法论的层面将法治思维等同为法律思维,相关学者将法治思维解读为“根据法律进行的思考和决断”㉔,认为法治思维是法律技术性规定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㉕对此,部分研究在区分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法治思维具有系统性特点,除了涵盖“法律关系思维”、“权利义务思维”、“正当程序思维”等法律思维模式之外,还包括法治实践中所应遵循的“规则治理思维”㉖,或者认为法治思维是“政治思维”、“战略思维”、“治理思维”、“大众思维”,而法律思维则是“司法思维”、“技术思维”、“裁判思维”和“职业思维”。㉗
在理论研究中,法治思维的运用主体从领导干部扩大至公民个体,所关注的问题不限于如何运用法治思维规范权力的行使,还包括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开展社会治理和解决纠纷,研究视野随之延伸至多元利益协调和权利救济等场景之中。对现有的、主要的法治思维的概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由于主体立场、拟解决的问题和问题所处的场景的差别,不同学者剖析法治思维内涵和阐释法治思维功能的角度有所不同,所形成的概念之间既有交叉和重叠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分歧。纷繁复杂的定义显示出学界对法治思维的重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种法治思维无法直接规范多种主体的行为,同一法律问题在不同法治思维的指导下或将生成互相排斥的结果,适用于一种实践场景的法治思维在其它场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这将造成公民在选择时的无所适从和进退失据,因此,理论研究有必要对法治思维的概念进行化繁就简,用简约的风格为法治思维寻求一种具有理论和实践穿透力的阐释。
二、法治思维的化繁就简
思维是人类认知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其重点在于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路径、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方向,法治思维要求思维主体按照法治的要求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什么是法治”这一经典命题,学者的回答见仁见智,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中,无论是追求规则之治的法治,还是强调法律至上的法治,抑或是崇尚良法善治的法治,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都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国家治理中的一切事务,㉘据此,法治思维最为简约的定义是思维主体按照法律的规定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从形式上看,法律由权利和义务组成,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实则是调整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作为法律的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与法律、法治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使得法治思维的运用始终伴随对权利义务的思考,以及对权利义务调整方案的追问。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看,尽管二者是相伴相生的,但比较而言,权利处于主动地位,义务处于被动地位,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义务需要被某种权利所约束和支配,义务主体应按照权利主体的指示和要求去做或不做某事,㉙因此,在“权利是第一性的要素,义务是第二性的要素”㉚的关系格局之中,权利成为法治思维的运行起点。
伴随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充实,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随之提高、行使权利和为权利而斗争的愿望愈加明显。在公共领域,公民通过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其它主体进行平等交流、诉求表达和协商对话,㉛或者通过行使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监督权力主体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平等、自由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达成或履行约定获得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在当前的法治实践中,依旧存在以权利为起点,但与法律渐行渐远,甚至脱离法治轨道的行为,比如,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直接侵害他人的名誉,未获批准而进行集会活动,利用政府“维稳”心理和地方政府信访工作的缝隙建立信访产业链,将“上访路”转化为“致富路”,试图激发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以干扰法官裁判,并与司法机关进行对抗和“死磕”,㉜为了实现特事特办的要求,甚至做出“声泪俱下的哭喊”、“牢骚满腹的诉说”和“不分青红皂白拍桌子、出言不逊”㉝等戏剧化的行为。
“以权利之名、行违法之实”的行为折射出公民权利观念尚未成熟的现实,由于缺乏对权利范围,以及利益和权利边界的清晰认知,公民在表述、行使和救济权利时,难免将利益等同为权利、以利益指代权利。与权利相比,利益的范围更广泛、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个性,故而利益思维比法治思维更容易被接受、理解和运用,在利益思维的引导下,公民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不是权利而是利益,所提出的主张不是为了实现权利而是为了满足利益,以权利为开端所展开的思考终将转向对利益的争夺。超出权利范围的利益主张若被满足,可能实现个案公平和短期的、小范围的社会稳定,但却将在全社会范围内挤压法治思维的运行空间,如若公民的个体需求被忽视、被压制,则极有可能激化矛盾、衍生出极端行为和违法行为,进而与法治和法治思维渐行渐远,故而法治思维的正确运用应排除利益思维的干扰、防止利益思维的误导,其关键在于树立公民正确的权利观念,使其有能力区分利益与权利,并从利益主张中提炼出权利诉求。据此,本文认为,以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立场认识法治思维应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从权利概念入手,辨析利益与权利,并动态展示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的进程。
三、利益、权益、权利
权利理论中对权利本质的认识大致包括“自由说(意志论)”、“利益说”、“力量说(能力说、资格说)”、“选择说”、“规范说”、“手段说”、“过程说”和“价值说”,㉞其中与利益最为相关的学说当属“利益说”。“利益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利益,法律设定权利的目的在于保护利益,权利主体也是利益主体,拥有权利的主体同时获得某种实际利益。㉟利益可以朴素地理解为人类的某种需要或愿望,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所需之物,㊱另外,也有学者将利益视为一种由“客观规律的许可程度”、“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非常重要的生活资源”,资源的持有者能够获得好处,并实现某些愿望、满足某些需求。㊲
利益是权利的基础,但利益不能当然地成为权利,唯有“经过社会权衡、协调、界定而得到公认和一定保障应受分配”㊳的正当利益才能被确认为权利。㊴利益转化为权利应经过利益识别、利益正当性证明和利益被权威认可三个步骤。其中,利益识别环节是利益转化为权利的基础步骤,包括利益主体识别和利益主张识别,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即谁是适格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利益正当性证明环节是利益转化为权利的关键步骤,判断利益是否正当的标准是利益能否普及至所有公民,正当的利益应该是共性的,而不是个性的,应该是由全体公民所普遍享有的,而不是由某些个体所独有的。在主体适格、正当性显现后,利益进入被权威主体审视、评价的环节,具体表现为,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将利益纳入法律之中,以权利的形式对其进行确认和分配。㊵
权益是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可被视为“权利束”,一项权益可以对应多种权利。比如,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考虑无过错方权益,此处的“无过错方权益”除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之外,还可能包括在家庭生活中付出较多的一方请求对方给予补偿的权利、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请求对方给予适当帮助的权利,以及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㊶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权益与合法权益可做相同理解,由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组成,其中,权利是主体明确、具有正当性,且经过立法活动确认和命名的利益,其他合法权益与权利并列存在于法律之中,蕴含权利要件、法律原则或立法宗旨,名称尚不具体、外延尚未明确,其功能在于承认和保护部分“漏列的权利”、“应(固)有权利”和“新生权利”等。㊷由于权益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故而为权益寻找匹配的权利不应仅限于权益所在的法律,还可以扩大至其它法律,甚至整个法律体系。比如,国家对其出资的企业享有“出资人权益”,该权益可与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相对应,包括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管理者权,以及查阅、复制公司章程、三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等;㊸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规定的“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婚姻家庭权益”可分别借助著作权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权利而实现;数据安全法所保护的“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能触碰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所拥有的法人财产权、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民法典所规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等。㊹
四、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以司法为场景
利益转化为权利的过程包括利益识别、利益正当性证明、利益被权威认可三个步骤,以此为基础,从利益主张中转化生成权利诉求的过程包括应予识别的四个环节,即主张利益、主张正当的利益、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以及主张可以或可能归入权利的权益。主张利益的前提是完成利益识别,主张正当的利益的关键在于揭示利益主张的正当性,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发生在利益被权威认可后,需要权利主体在“权利束”中寻找权利诉求的基础,主张可以或可能归入权利的权益则为其它合法权益的行使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司法是独立而中立的法庭针对案件争议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解释和适用法律,并做出权威性法律决定的活动,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是裁判者理顺争讼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解释和适用法律的结果是生成权利义务的调整方案,法庭针对所争之事(利)做出权威性法律决定实则是以一种权威的、确定的语言表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在司法过程中,公民因受到尊重而得以平等参与程序、充分交涉问题,并在公平、完整的程序中提出、证明和实现权利诉求,㊺一个认真对待权利、公平界定权利的司法活动能够为法治思维的运用提供充分的环境,因此,下文将以司法为场景阐释法治思维的操作路线。
(一)主张利益
主张利益是利益主体依据自身的“意欲”表明需求的行为,提出利益主张的行为主体应具备利益主体资格。通常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主张与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相关的利益,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利益主体仅限于部分人群,比如,专属于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的利益,男性、成年人、健康人不得享受;监护人、律师、警察、法官所拥有的与身份和职务相关的利益,其他公民不得主张。㊻在司法活动中,公民所主张的利益应该是自己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或尚未遭受威胁或侵害的利益,比如,房屋的所有权人能够获得拆迁补偿,而未获得合法居住权或临时居住人不属于适格的利益主体;养老保险待遇的利益主体是退休人员而非其子女或其他亲属;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是遭受精神伤害的被侵权人或其他受害者,而不是其亲属或单位。
在司法活动中主张利益实则是要求争讼的相对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比如,要求造谣者停止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请求离异的配偶按照离婚协议支付子女抚养费、申请城市规划部门公开建筑规划图等。利益主体针对他人的行动或资源所提出的要求是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和司法裁判范围的基础,如若主张利益所使用的语言含糊不清、所主张的内容模棱两可,则极易导致司法活动的方向发生偏转,进而得出与利益主体的预估相去甚远的裁判结果,故而在司法活动中主张利益应运用清晰的表达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另外,在司法中主张利益时,利益主体往往期待通过指挥他人行动或借助他人的资源与能力来满足自身利益,因此,为保证信息的接收者准确理解利益主体的真实意思,主张利益的信号应直接发送至利益主体所期望的对象。
(二)主张正当的利益
主张正当的利益与利益正当性证明环节相对应,利益主体需要揭示利益主张中所包含的正义基因,并说明所主张的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而言,主张正当的利益要求利益主体所提出的需求和方案将私欲控制在利己但不损人的范围内,且允许其他社会成员依据同样的理由索要同样的资源。在司法实践中,公民主张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希望获得高于拆迁补偿协议约定金额的补偿,要求债务人按照“利滚利”的方式支付借款利息,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诉为民事被告,并期待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开展行政和解等,上述利益主张脱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正义基础,特事特办的纠纷解决方案不具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的可行性,因而不属于正当的利益主张、无法转化为权利诉求。
在司法活动中主张正当的利益要求当事人的利益主张是正义的、可普遍的。以违法建筑拆除相关的行政赔偿案件为例,行政机关违反程序性规定而拆除违法建筑的行为被判为“行政行为违法”,房屋所有人据此要求行政机关赔偿屋内财产损失,并按照市场价格赔偿房屋被拆除的损失。站在行政相对人的立场,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屋内财产的损毁、灭失,客观上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利益,由于财产利益由公民所普遍享有,故而行政相对人所提出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分析另一个利益主张,自建房屋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体的住房需求,但未经审批而搭建房屋的行为将扰乱城市治安和房地产市场,因此,违法建设行为不具有可普遍性,行政相对人针对房屋所提出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不满足正当性要求。
在司法活动中,当某些利益主张的正当性不甚明显或被遮蔽时,利益主体需补强、擦亮、挖掘和放大展示利益主张中所蕴含的良善基因,剔除或转变利益主张中所隐藏的“恶”,甚至从“恶”中挖掘出“善”的因子。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为例,于欢的上诉请求中所主张的利益是保留生命、拥有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在该案中,于欢对被害人的捅刺行为造成了杜某2的死亡、严某和郭某1的重伤,以及程某的轻伤,㊼触碰了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为了证明利益主张的正当性,辩护需在降低于欢的主观恶性方面着力,并强调“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符合普遍价值观和社会共识,任何人在面临与于欢相同的处境时,为了维护人所应有的尊严和人格、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都会采取与其相同的行为。
(三)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
在利益被权威认可环节,主体明确、正当性明显的利益被确认为权益,在法律之中,权益以“权利束”的形式存在,一项权益可以对应多种权利,享有权益的利益主体同时获得权利主体的身份,权利主体在“权利束”中选择一项权利并针对该项权利提出具体的要求是为权利诉求。
在司法的语境中,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纠纷的过程是权利主体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提出权利诉求、证明权利诉求和实现权利诉求的过程,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实现权利诉求的具体方案,诉状中载明的事实和理由是对权利诉求的正当性的说明,争讼各方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展开辩论的目的在于说服裁判者肯定己方的权利诉求、否定对方的权利诉求。可以说,权利主体在此权利和彼权利之间进行比较、衡量和取舍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司法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针对相似的权利所形成的权利诉求可能生发出完全不同的诉讼请求,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之下,选择此权利可能导致彼权利“可诉性”的丧失,因此,在司法活动中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要求权利主体在比较和衡量后做出理智而慎重的取舍。
以“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为例,按照案件的基本事实,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参加考试、接受良好教育和获得工作岗位,造成齐玉苓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㊽从客观结果上看,陈晓琪的行为导致齐玉苓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优质工作岗位的可能,但从因果关系上看,陈晓琪直接侵犯的是齐玉苓的姓名权而非受教育权,侵权行为与受教育权的减损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因此,从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率的角度看,以姓名权为基础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是更加经济、高效的选择。再如,在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非法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考试的过程中,部分考生在自建的微信群内分享复试题目,人大法学院接到举报后进行调查、取证,确认22名考生在专业复试进行过程中向他人透露复试题目,最终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取消该22名考生一志愿复试相应科目考试成绩,给予计零分处理,对此,部分考生提起“取消成绩决定及行政赔偿”诉讼。㊾在该案中,考生的利益主张是恢复考试成绩和获得经济赔偿,从表面上看,与考生的利益主张相关的权益是受教育权和名誉权,然而,法学院按照考试纪律取消考生在本年、本院、本场的成绩不会威胁和消减考生的受教育权,尽管取消成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考生的名誉,但该决定系建立在查明的事实和公开的考试规则的基础上,法学院不具有侵害考生名誉权的主观故意,故而受教育权和名誉权都不是与考生的利益主张明显相关的权利。
(四)主张可以或可能归入权利的权益
权益具有流动性和包容性,一方面,权益对应多种权利,能够在必要时流入一种权利之中并转化为权利诉求,另一方面,权益面向法律实践,能够吸收与权利相关的多种利益。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权益包括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能够直接匹配至某项权利,在司法活动中被表达、被争夺,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尚未稳定、无法与权利直接关联的利益主张,它们或者游走在其他合法权益的边缘,或者在获得其他合法权益的身份后无法即刻与权利相勾连,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利益主张无法在“权利束”中寻得对应的权利时,利益主体可在利益主张与某种其他合法权益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以其他合法权益为基础提炼权利诉求,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将利益主张转化为权利诉求的关键是,证明所主张的利益拥有权利的构成要件、内涵权利背后的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
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所规定的人格权和其他人格权益为例。权利主体认为自身人格权受到侵犯,但所提出的主张明显不属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的范畴,在此情况下,权利主体可退至“其他人格权益”,从保护“人身自由”、“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角度出发,说明自己之主张符合人格权的构成要件。㊿比如,在欺诈性抚养中,无抚养义务人若以一般人格权为基础请求欺诈人返还抚养费、支付精神损失费,应该说明对方的欺骗和隐瞒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和人伦道德、挫伤了自己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并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51]或如,物业公司通过停水的方式催缴代收的水费,业主可以物业公司切断生命之源、剥夺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为由,要求其停止侵犯一般人格权,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52]再如,在考生诉人民大学法学院“取消成绩决定及行政赔偿”案中,群内可能存在部分因他人分享题目而获益的考生,按照考场纪律和考试规则,泄漏考试题目的行为和使用被泄漏的考试题目的行为都应受到处分,而仅取消泄漏考试题目的考生成绩有违公平,因此,被取消成绩的考生或许可以“其他人格权益”为基础、从人格尊严平等的角度提炼权利诉求。
以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立场认识法治思维的目的在于,为法治思维寻找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使其易于被公民所理解和掌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开展平等、公开的程序而使公民直观地、真切地与权利发生互动,为公民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纠纷提供充分的空间。在司法活动中,由于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和诉讼案件的个性化,法治思维操作路线的四个步骤可能无法在一场司法活动中全部凸显,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技术,法治思维在司法中的实施效果除了受到社会成员习得能力的影响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裁判者职业技能的高低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充分程度。
注释:
①参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2010年10月10日发布(已失效)。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④《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决议》,2011年9月30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⑤《黑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第二条第(七)款。
⑥《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2021—2025年)》第七条。
⑦《2021年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第四条第(一)款。
⑧参见杨宗科:《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履职履责的内在自觉》,载《光明日报》2019年7月17日,第6版。
⑨参见周强:《用法治思维处理信息化社会矛盾冲突》,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3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11/c64102-20745200.html;参见蒋安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上)——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载《法制日报》2020年4月29日,第9版。
⑩参见江必新:《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载《求是》2020年第5期;参见《特大城市如何破解拥堵“顽疾”——来自上海交通大整治一线的视察思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6年11月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7/content_5129700.htm;参见于双:《延吉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食品安全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力》,载《中国食品报》2014年6月11日,第A7版;参见张学瑞:《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税收行政争议》,载《中国税务报》2013年2月6日,第6版。
⑪⑳参见吕世伦、金若山:《法治思维探析》,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1期。
⑫参见王江燕、樊石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20期。
⑬参见姜明安:《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载《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⑭张恒山:《论法治思维的观念基础》,载《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4期。
⑮参见《徐显明解读十八大报告依法治国亮点》,载北方网2012年11月14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m/2012/11/14/010273482.shtml。
⑯参见胡建淼:《法治思维的定性及基本内容——兼论从传统思维走向法治思维》,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⑰㉖参见江必新:《法治思维:社会转型时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⑱参见殷啸虎:《法治思维内涵的四个维度》,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⑲参见张文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
㉑参见汪永清:《法治思维及其养成》,载《求是》2014年第12期。
㉒参见蒋传光:《法治思维: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㉓参见庞凌:《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及其运用》,载《法学》2015年第8期。
㉔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㉕参见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㉗参见谢晖:《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
㉘参见张志铭、于浩:《现代法治释义》,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1期。
㉙参见郑成良:《权利本位说》,载《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参见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参见殷啸虎:《法治思维内涵的四个维度》,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㉚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㉛参见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载《政法论丛》2007年第5期;参见江国华、刘文君:《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理论释读》,载《求索》2018年第1期;参见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㉜参见凌河:《“死磕派”与“勾兑派”》,载《解放日报》2015年7月16日,第2版。
㉝《王颖:“把责任和群众永远装在心里”》,载国家信访局网站,https://www.gjxfj.gov.cn/2021-12/06/c_13103542 49.htm。
㉞参见徐显明主编:《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㉟参见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参见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㊱参见漆多俊:《论权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参见沈宗灵:《法·正义·利益》,载《中外法学杂志》1993年第5期。
㊲参见周旺生:《论法律利益》,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2期。
㊳参见漆多俊:《论权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㊴参见郑成良:《权利本位说》,载《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参见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㊵参见吕世伦、公丕祥主编:《现代理论法学原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245、258~262页;参见周旺生主编:《法理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202页;参见黄文艺、杨亚非主编:《立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3~77、112~114页。
㊶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第一千零九十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㊷参见郭道晖:《论权利推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
㊸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第四条、第三十三条。
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一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第三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年)第十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第九条、第二十一条。
㊺参见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载《现代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参见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参见沈宗灵:《法·正义·利益》,载《中外法学杂志》1993年第5期;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㊻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
㊼参见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刑终1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㊽参见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
㊾参见《关于部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非法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的考生因违反考场规则和考试纪律受到处理的情况说明》,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http://www.law.ruc.edu.cn/home/t/?id=57060;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硕复试成绩取消案开庭,2名法学学生亲自上阵》,载搜狐网,https://learning.sohu.com/a/518080710_121 289162。
㊿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254页;参见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5页;参见王利明:《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1期。
[51]参见步某2与孔某、步某1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8民终3539号民事判决书。
[52]参见周振华、魏亚丽等与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孝感分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9民终198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