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图景的层次与上位制作义动词
2022-12-22张宝
张 宝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3)
制作行为是由人发出的、有目标、有预期的产品创造行为,表达制作行为的动词是制作义动词。现代汉语制作义动词数量众多,表达同一制作事件可能会用到不同的动词,请看:
(1)a.做了一顿饭 b.煮了一顿饭 c.烧了一顿饭
(2)a.做了一道菜 b.炒了一道菜 c.蒸了一道菜
(3)a.做了一幅画 b.画了一幅画 c.描了一幅画
但是不同的动词各自概念化的程度并不相同:例(1)至(3)中“做”的语义非常概括,其他制作义动词的语义则相对具体。这种语义上的概括与具体反映了人们对“做”与以“做”为语义基础的其他制作义动词的认知差别。那么这种认知差别该如何表述?再请看:
(4)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格非《江南三部曲》)
(5)晚上是两个鸡蛋蒸一碗蛋羹的,还有一杯鲜羊奶。(贾平凹《废都》)
(6)她又忙着去泡青果茶,煮五香蛋……(张恨水《金粉世家》)
例(4)的“煎”是先用少量食用油蘸一下锅底,再用温火把锅烧热,最后把打碎的生蛋放入锅中煎制,一般是先煎一面再煎另一面,煎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晃动炊具使原料受热均匀色泽一致。“荷包蛋”薄脆的外皮形似荷花,里面的蛋黄形似莲蓬,这种效果是“蒸”“煮”等烹饪方法难以做到的;例(5)的“蒸”是以蒸汽导热将经过调味的原料用火加热使之熟嫩酥烂,鸡蛋经过“蒸”会变成“蛋羹”,而“* 煎蛋羹”和“* 煮蛋羹”却是不能说的;例(6)的“煮”是把原料放于汤汁或清水中先用大火烧开再用中火或小火慢慢煮熟,“煮”的特点就是用时长久,只有这样鸡蛋才能够入味变成“五香蛋”。
上述例(4)至(6)显示了对鸡蛋(也可能是别的蛋)的不同制作方法,其中的动词“煎”“蒸”“煮”都可被“做”替换,但三者之间却不能相互替换,因为它们各自显示了不同的制作特色。虽然“炒”“ 爆 ”“ 熘 ”“ 炸 ”“ 烹 ”“ 煎 ”“ 贴 ”“ 烧 ”“ 焖 ”“ 炖 ”“ 蒸 ”“ 氽 ”“ 煮 ”“ 烩 ”“ 炝 ”“ 腌 ”“ 拌 ”“ 烤 ”“ 卤 ”“ 冻 ”“ 熏 ”“卷”“滑”“焗”等24 种烹饪类制作义动词都各具特色且不能相互替换,但它们却都可以被“做”所替换。这种不可替换与可替换的不对称性又表明了什么?其实也不光烹饪类制作义动词,如不特别强调制作方式,具体的制作义动词一般都能被“做”所替换,下面例(7)至(12)中的几个动词也是如此。
(7)哪家一煮了好菜饭,就要请他一同去吃。(文龙《看家》)
(8)我和亮子先在火堆旁边歇歇腿,烧了顿饭吃。(奚青《天涯孤旅》)
(9)织云正要炒菜,何绍祥就回来了。(赵淑侠《我们的歌》)
(10)她蒸好两屉馍馍,又熬了一大锅白菜土豆。(张贤亮《绿化树》)
(11)苦禅……在纸上画了一幅兰草。(李向明《李苦禅传》)
(12)两道黑色的鬣毛如同用画笔专门描了边一般。(奚青《天涯孤旅》)
可见“做”在句法搭配上所受的语义限制较少,其他制作义动词在句法搭配上所受的语义限制较多。石毓智[1]指出:动词的概念化越复杂、内涵越丰富,其语法表达式则越简单;反之,则语法表现越复杂。本文将从认知图景的层次性理论出发,展示上位制作义动词与下位制作义动词的认知差别,并对现代汉语的某些上位制作义动词进行相关说明。
一 认知图景的层次
施关淦[2]认为语言不同不是因为“逻辑基础和意义有什么大的不同”,而是因为“意义的形式系统各异”,所以语法研究的重点并非揭示意义的区别。但形式是意义的结构化(或者说符号化),语法形式因意义的改变而改变。意义是对象、现象和关系在意识中的主观反映,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3],所以不同语言由于情感心理和文化背景的区别,反映结果也不尽一致。“每一个语言有不同的概念化”[4],比如汉语的“借”相当于英语“lend”和“borrow”的总和(“借”把“lend”和“borrow”概念化为一体),“概念化是一种动态的主观化活动(subjectification)”[5],比如“法语对‘租入’和‘租出’都说‘louer’,而德语却用‘mieten(租入)’和‘vermieten(租出)’两个要素”[6];再比如“德国人用‘reiten’表示骑在动物上,而用‘fahren’表示骑在其他东西上,而英语只用一个词‘ride’来表示二者”[7]。可见“借”“louer”和“ride”都激活了某种概括的上位认知图景,“lend/borrow”“mieten/vermieten”和“reiten/fahren”都激活了与之相对的下位认知图景,词语的表达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认知图景的层次差异。
(一)概念提出
范畴划分与层次划分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必由之路,范畴划分是横向的分类别,层次划分是纵向的分等级。经典范畴理论认为所有的范畴都具有清晰界限,各个范畴内部成员之间地位也都平等——没有哪个成员更具代表性。但事实上每个范畴的内部是有等级和层次的,以“植物”这个范畴为例,其内部既有成员“树木”也有成员“槐树”;既有成员“花草”也有成员“玫瑰”。“树木”与“槐树”相比概念化程度更高,因而显得更为抽象和概括,所以前者是后者的上位范畴;反之,“槐树”与“树木”相比,其概念化程度更低,因而显得更为具体和丰富,所以前者是后者的下位概念。这样看来,“树木”与“槐树”是有层次差别的,这种层次差别导致了“槐树是一种树木”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而“* 树木是一种槐树”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当然,同一范畴内的层次差别也是相对的,“槐树”与“树木”相比是下位范畴,但它与“国槐、刺槐”等相比又成了上位概念。同样,“玫瑰”是“花草”的下位概念,但“玫瑰”又是“红玫瑰、白玫瑰”的上位概念。
如何把概念层次性理论应用到句法语义分析,Taylor[8]、Ungerer 和 Schmid[9]等人作过相关尝试,但在汉语研究中效果不甚理想。卢英顺[10-11]在认知图景理论构建中认为:认知图景是通过特定的词语激活的,特定的词语表示的是一个概念,这样,概念的层次性自然会影响到认知图景的层次性。认知图景的层次性是指有关词语激活人们对认知图景想象层次的不同,有的比较具体,有的则比较概括。处于较高层次的可以称为上位认知图景,处于较低层次的可以称为下位认知图景。较之上位认知图景,下位认知图景所能激活的认知要素会更具体、丰富。属于同一上位认知图景之下不同的下位认知图景可以称为同位认知图景。
可见,认知图景层次理论基于特定事物的“概念化”。但对于“概念化”这一术语,前人时贤有不同理解,Saussure[12]认为能指(语言符号)的所指(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概念,概念化就是形成意义(词义)的过程;Langacker[13]指出意义不是概念(concept)而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Langacker[14-15]、Evans 和 Green[16]等不仅认为意义可以被描述为概念化(meaning is characterized as conceptualization),更认为意义只是概念化的一部分,概念化是人类处理意义的认知加工和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不仅对语言形式进行编码,还将编码后的语言形式与语音结构相联系;Croft等[17]将概念化视为更宽泛的语法操作,包括构形/构词形态、词类/句型以及语篇选择。
认知图景理论对“概念化”只作狭义理解,赋予某词项以一定的语义,典型地体现在实词上。就词语的意义对句法、语义成分的影响来看,动词和名词的概念化对句法、语义成分的影响直接而明显。[18]名词与动词是汉语最基本的两个词类,前者指称某客体事物(可具体可抽象)的存在,多激活认知图景的静态模式;后者陈述某行为活动的过程,多激活认知图景的动态模式(名/动词与静/动态模式之间虽有自然关联,但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指称语与述谓语在语言运用中都表现为概念,概念化的程度高低决定了静/动态认知图景层次的高低。词语的概念化程度越高,其认知图景就越概括越抽象,其认知要素就越少越简单;词语的概念化程度越低,其认知图景就越具体越丰富,其认知要素就越多越复杂。
概念化情况不同,不同语言或者不同时期的同一语言就会有不同的语法结构。而“动词是组织句子的核心”,其概念化方式在各个词类中“对句子结构的影响最大”[19]。比如动词“写”的认知图景相对概括,其所激活的认知要素也不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写”(无论书写还是写作)的主体“人”,二是“写”的对象(“字”或者由“字”组成的“论文”“小说”等)。此外,“写”的工具(书写工具无疑是“笔”;写作工具最初也是“笔”,进入现代社会多为“电脑”)也是被“写”所激活的认知要素之一。典型工具“笔”可充当“写”的宾语(比如“写毛笔”“写钢笔”),其他工具却不能(没有“* 写电脑”的说法)。
与“写”相比,“写书法”所激活的认知图景就相对具体,其所激活的认知要素也更为丰富。除了“书法”这个对象本身,还有与“书法”相关的字的体量(如榜书、蝇头小字等)、书体(如篆隶行草楷等)、字体(如颜柳欧赵等)、法帖(如《十七帖》等)。同样是“写”的下位认知图景,“写小说”所激活的认知要素有“小说”的篇幅长短(如微型、短篇、中篇、长篇等)、主义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讽刺主义、存在主义等)、年代地域(如古典、现代、城市、乡土等)、语言文字(如文言、古白话、普通话、方言等)、故事内容(如言情、武侠、悬疑、历史等)。不同层次的认知图景决定不同的句法语义成分。
根据“写书法”的认知图景,可以看到如下表达:
(13)这书房似乎是老于给人写草书留墨宝的地方。(王火《战争和人》)
(14)他还会写字,写刘石庵体的行书。(汪曾祺《故里杂记》)
(15)他……写篆书之体,其恣肆不下于郑板桥。(梁实秋《雅舍菁华》)
(16)因为盼望所抄的诗被人嘉奖,我开始来写小楷字帖。(沈从文《从文自传》)
根据“写小说”的认知图景,可以看到如下表达:
(17)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鲁迅《〈总退却〉序》)
(18)我最希望写白话诗的人先说白话,写白话,研究白话。(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19)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20)庄之蝶……又告诉柳月他要写一组魔幻主义小说……(贾平凹《废都》)
由于受各自认知图景的制约,有些错位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如:
(21)*你喜欢写谁的小说?
(比较:你喜欢写谁的字体?)
(22)*我去年写了三部字。
(比较:我去年写了三部小说。)
(23)*小说我擅长写颜体。
(比较:书法我擅长写颜体。)
例(21)中,字体是“书法的派别”[20],它是由个人书写形成的书法风格和特点,比如“颜体”是颜真卿的楷书字体,“欧体”是欧阳询的楷书字体。显示优秀书法风格的字体往往流传后世并为大众所模仿学习,写颜体就是“写颜真卿的字体”,写欧体就是“写欧阳询的字体”,所以我们可以说“写某人的字体”。而小说是个人创作形成的“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21],创作活动一旦完成就有了文本与作者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既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复制,所以“写作”与作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当然,其他人可以“阅读”“评论”小说甚至“翻译”“出版”小说。例(22)的“部”作为量词多“用于书籍、影视片等”[22],“小说”多以书籍形式呈现,以“部”而论体现了转喻关系;但“字”再多也不能以“部”论,因为“写书法”的认知图景不能激活“书籍”这一认知要素,但其可激活“页数”这一认知要素,因而下例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24)他……先就坐到桌子边来,写了半页字。(张恨水《美人恩》)
例(23)所激活的是“写小说”的认知图景,“小说”没有“颜体”这样的认知要素,所以也不能说。总之,不能说的句子都是因为某些认知要素不属于其相应的认知图景。
“写”所激活的是上位认知图景,因而与它一起搭配的成分可以非常广泛。当“写”与其他成分结合时,其所激活的上位认知图景就会具体化为下位认知图景。与“写”搭配的认知要素越有特色,整个表达就越容易激活特别的下位认知图景。与“写”搭配的认知要素越没有特色,越容易产生歧义。请看:
(25)写短篇。
(26)写乡土题材。
(27)写了一整天。
(28)A:你喜欢鲁迅写的吗?
B:你是指小说还是指书法?
例(25)、(26)中的“短篇”“乡土题材”在相关的认知图景中很有特色,它们一下子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指“写小说”;例(27)中的“一整天”表示时间量,非瞬间完成的动作行为都会激活时间量这个认知要素,所以时间量要素并没有特色,它无法使我们确定“写”的对象;例(28)“写的”转指写的东西,鲁迅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作家,但有些研究者知道其书法也非常不错,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小说”和“书法”都是“写”出来的,他们并不确定提问中的“写的”到底转指什么,所以才有“你是指小说还是指书法”这样追求精准的回问。但对于只知鲁迅是作家的普通人来说,则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影响因素
卢英顺[23]认为,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关句法成分对认知图景层次的影响,其中包括宾语和状语;二是构词因素的影响。我们已通过“写”与“写书法”“写小说”的对比分析证明了宾语对认知图景层次的影响;后面还将通过“制作”“制造”等词与“X 制”类动词的对比分析证明构词因素对认知图景层次的影响。
语义要素既可融合在词义构成当中,也可作为单独的词出现在句法层面。根据位移路径编码方式的两大类型,Talmy[24]认为上古汉语是动词构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现代汉语是附加语构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由此看来,句法成分对现代汉语词汇认知图景的层次影响更大。
我们将考察状语和其他句法成分对认知图景层次的影响。首先看状语。
表示“制作”的“做”语义非常概括,激活了制作行为上位认知图景,它最容易激活的认知要素只有施行“做”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一般是制成品)两个要素。例如:

动词前的状语一般表示行为方式,从不同视角切入能表达不同的方式内容。例(32)“做”前的状语指向制作行为本身,描摹了没有停顿的制作行为;例(33)与例(34)的“认认真真”与“照本宣科”指向制作行为的主体制作人,描摹了他们在制作行为中的态度。显然,因为表达不同方式的状语部分,例(32)至(34)的制作行为激活了“做”的下位认知图景。
此外,不同视角的方式描写可以共同修饰同一个动词,共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所以“一针不停”与“认认真真”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她认认真真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反之,若以同一视角的方式描写共同修饰同一个动词,句子的语义不是冲突就是冗余。“*她认认真真马马虎虎地做着布鞋”和“* 她干干歇歇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的说法因为语义冲突都不能成立。“?她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着布鞋”和“?她马不停蹄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的说法则因为语义冗余很有问题。
胡裕树[25]指出:动词性谓语中,最常见的是动宾谓语,其次是动补谓语。动宾谓语中的宾语能够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那么动补谓语中的补语是什么情况呢?金立鑫[26-27]从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角度出发,看到了汉语补语与状语的某些相通性,认为“凡是修饰或限定动词的都是状语”,把“与谓语核心谓词有直接句法依存关系的”补语称为“后置状语”。从这一点来看,补语有成为认知图景层次影响因素的潜质。但是,汉语的补语内涵大、小类多,语法性质参差不齐,我们在此仅观照与制作义动词相关的几类主要补语。
第一类是结果补语。请看例句:
(35)……新房里边的床、桌和椅子刚刚做完……(周大新《湖光山色》)
(36)……大绸新旗袍已经做成……(茅盾《林家铺子》)
(37)……上面有一只鸡,刚刚做好,预备中午吃的。(林语堂《京华烟云》)
刘月华[28]认为“功课做完了”中的“完”作为结果补语是对动作“做”的“判断”和“评价”。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判断”和“评价”是从言者视角出发的,但言者的“判断”和“评价”都基于动作行为的客观事实。与其说“判断”和“评价”,不如说“完”作为结果补语叙述了动作“做”的终结状态。事实上任何行为都有从起始到结束的过程,制作行为也不例外。例(35)至(37)中的制作行为已经结束,其标志就是“床、桌和椅子”“大绸新旗袍”和“鸡”已经“做完/成/好”。这种表完成的结果补语激活了完成态的制作行为认知图景,完成态制作行为认知图景是全程态制作行为认知图景的一个阶段,所以结果补语可以成为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至少完成态的结果补语可以。
第二类是情状补语。请看例句:
(38)这莴笋圆子做得非常精致……(张爱玲《半生缘》)
(39)该死的李裁缝,他把我这件衣服,做得不合腰身……(张恨水《春明外史》)
(40)那小花褂做得可真巧,五块多钱,不要布票。(史铁生《绵绵的秋雨》)
情态补语虽然复杂,但其基本功能就是描写,要么针对动作本身,要么针对动作结果。在制作义动词所构成的句子中,情态补语一般指向制成品要素(即动作结果)。例(38)至(40)中的制作行为已经完成,有下划线的补语部分虽然紧邻制作义动词“做”,但其语义是指向制作行为成品(“莴笋圆子”“我这件衣服”和“小花褂”)的。制成品是制作行为的终结点,对制成品要素进行描写与制作行为没有直接关系。有些情态补语的描写表面看是指向制作义动词本身的(比如“做得好”),但实际上这种描写也是在制成品好坏的基础上落实的。所以情态补语不是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至少制作义动词的情态补语不是。
第三类是可能补语。请看例句:
(41)……你连钢索电缆和一根简单的长钢电线都做不出来。(林语堂《朱门》)
(42)……尸体无法复元,标本当然也做不成。(高行健《灵山》)
(43)但这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路遥《平凡的世界》)
例(41)中的可能补语由“不+趋向补语”构成,例(42)、(43)中的可能补语由“不+结果补语”构成,它们都表达了主客观条件不允许制作行为完成和结束。但可能性的判断并未改变制作行为认知图景的概念化程度,因此可能补语也不是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
第四类是数量补语。请看例句:
(44)反正我不能做两回早饭!(老舍《二马》)
(45)有些家还要给牲口做一顿面条吃。(李凖《黄河东流去》)
(46)……他曾偷偷地要求阿萍奶奶做一次醉虾,阿萍奶奶做了。(张炜《你在高原》)
例(44)至(46)中的“两回”“一顿”和“一次”都是动量补语,表示了制作行为“做”的数量。数量描述虽对制作行为有一定细化,但对认知图景层次的改变微乎其微,因此也算不上是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
接下来看定语与认知图景层次的关系。请看例句:
(47)杜嫂能做出非常可口的饭菜。(陈艰《生命的热量》)
(48)基修和丘鲁克都是贵族,绝对无法忍受难吃的饭菜的。(山口升《零之使魔》)
(49)尽管如此,母亲还是用最丰盛的饭菜,隆重地接待了鸟儿韩。(莫言《丰乳肥臀》)
(50)就像厨师在自己家里,只吃最简单的饭菜。(毕淑敏《预约死亡》)
(51)王家的饭菜是带点南洋风味的……(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52)只是家常便饭,不配说请,不过总比学校的饭菜好些。(冰心《繁星春水》)
(53)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路遥《平凡的世界》)
(54)我们这个店,一天只做五十位客人的饭菜,多一个都不行。(裘山山《打平伙》)
例(47)、(48)的“可口”与“难吃”着眼于“饭菜”的好吃与否,例(49)、(50)的“丰盛”与“简单”着眼于“饭菜”的复杂程度,这四个定语都是描写性定语,它们对中心语的性质和特点予以描写;例(51)、(52)的“王家”与“学校”着眼于“饭菜”的归属,例(53)、(54)的“一桌”与“五十位客人”着眼于“饭菜”的数量,这四个定语都是限制性定语,它们对中心语的归属或数量加以限定。从好吃与否、复杂程度和归属、数量等方面对中心语“饭菜”进行修饰,就是从不同角度激活了“饭菜”的下位认知图景。所以定语可以成为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因素,只是它只针对认知图景的静态模式(也叫“物体模式”)。而定中结构的极致状态就是词化(lexiconization),所以“毛笔、铅笔、钢笔、圆珠笔、粉笔”都激活了“笔”的下位认知图景。
(三)具体应用
卢英顺[29]从词语的概念化对语言形式的影响着手,认为同一个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认知要素虽然是一定的,但由于动词概念化的不同,不同动词所包含的认知要素的多少是不同的,表现在句法上,同样的语义内容在句法成分的映射上就有所差别。分案例予以证明。(1)英语“peel”的词义固定蕴含削去物要素,所以“Have you peeled the potatoes’skin”的说法不妥;与之相比,汉语的“剥”和“削”没有固定蕴含削去物要素,所以“你削了土豆皮没有”的说法也可成立。但是“剥”和“削”的词义蕴含了工具要素,前者激活了工具要素“手”,后者激活了工具要素“刀”;英语与之相比没有这个区分,所以“剥”“削”都是“peel”。(2)汉语的“杀”蕴含了“有意识”的实施者要素,英语的“kill”未蕴含这个语义要素,所以“The crash killed three people”不能译为“事故杀死了三个人”,只能译为“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汉语“杀”的对象只能是“人或动物”,英语的“kill”也没有这个要求,所以“The sun has killed most of the plants”不能译为“太阳把大部分植物杀死了”,只能译为“太阳把大部分植物晒死了”。此外,与“杀”相比,“自杀”因为蕴含了对象要素“自己”所以不能再带宾语。(3)“授权”与“授予”相比,蕴含了“授予”行为的“内容要素——‘权’”,所以“丹麦女王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中的“授予”不能被“授权”所替换。(4)英语的“slice”“dice”“shred”因为蕴含了“所切对象最终呈现状态”这一语义要素,所以译成汉语就成了述宾结构或述补结构的词组“切片”“切丁”“切碎”。(5)“shelve”因为蕴含了“所放置的对象的位置”这一语义要素,所以在句法表现上与“put”有了差别。后者需要复杂的句法表达“She put the books on the shelf”,前者只需表达为“She shelved the books”。
卢英顺[30]还根据认知图景的层次区别对“换”类动词的内部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交换、替换、更换、调换、兑换”等动词以“换”为语义基础,概念化的程度差异导致认知图景的层次差异。激活上位认知图景的“换”所搭配的词语比较广泛,激活下位认知图景的“交换、替换、更换、调换、兑换”等动词在搭配上则受较多的限制。
比如“交换”一般要凸显“交换对象”这一认知要素,未凸显“交换对象”的“交换”句可接受度很低。例如:
(55)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格非《江南三部曲》)
(比较:*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 )做了交换。)
再比如“替换”类所凸显的两个认知要素“用来替换的东西”与“被替换的对象”多属同类,“更换、改换、调换”也是如此。例如:
(56)宝能一边用银行理财资金替换了之前券商的资金,一边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获得银行的理财资金,继续增持万科股票,银行资金间接投资于二级市场。(《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3 日)(A 资金替换 B 资金)
(57)10 月21 日,浙江桐乡公司电力员工正加紧对110 千伏屠甸变重负荷线路—10 千伏同裕线进升压改造,通过将同裕线原10 千伏裸导线更换为20 千伏绝缘导线,同步更换线路装置……(《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 年 11 月 6 日)(A 导线更换为B 导线)
(58)它是在东方号的基础上改进的,即把笨重的弹射坐椅改换为普通的椅子,为的是抢在美国之前载人飞行。(《人民日报》1999 年 11 月 22 日)(A椅改换为B 椅)
(59)……国家拨给了他们一万新纱锭,工人们都很高兴,想用这一万新纱锭把一部分老纱锭调换下来。(《人民日报》1972 年 10 月 22 日)(A 纱锭把B 纱锭调换下来)
“兑换”所凸显的两个认知要素更为精准,一般都是“金钱类或者是金钱的替代品,如各种券类”。例如:
(60)十天前用四点七四法郎可以兑换一美元,到七月二十日需要四点九四或五法郎才能兑换一美元。(《人民日报》1976 年 8 月 6 日)(法郎兑换美元)
卢文还指出:表示下位认知图景的动词可以换为表示其上位认知图景的动词,反之则不一定;处于同位认知图景的不同动词彼此之间也不能互换[31]。
二 上位制作义动词的语义特点
受认知图景层次的影响,制作义动词也可分为上位制作义动词和下位制作义动词。我们把显示制作行为上位认知图景的动词称为上位制作义动词,把显示制作行为下位认知图景的动词称为下位制作义动词。上位制作义动词主要是表制作的抽象动词,比如“制作”“制造”“制”和“做”。还有个别泛义动词的制作义是在语境当中确定的,比如“弄”“搞”“打”。
(一)抽象制作义动词
“制作”“制造”等都表示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32],这些实义动词的概念化程度很高,它们所激活的认知图景也很概括:制作主体凭借某种工具对某种材料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制成品。该认知图景中的认知要素也很简单,只有制作人、工具、材料和制成品。“制作”的用例如:(王小波《怀疑三部曲》)

可见,无论“制作”“制造”还是“制”“制成”,都是概括地陈述制作行为。与之相比,如下几组制作义动词因构词因素的影响显示了特别的地方。
第一组:“捏制”“揉制”“搓制”和“剥制”,该组制作行为均需徒手完成。

上述四组制作义动词的基本结构都是“X 制”,它们不仅内涵“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这层基础语义,还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不同的制作方式,不同制作方式所凭借的工具也有不同——或徒手完成,或以手使用工具完成,或借助水火甚至日光等条件完成,比如“晾制”与“晒制”。

“赶制”虽也表制作方式,但是指“为了不耽误时间,加快行动进行制作”,与工具没有任何关系,是指向制作人的。例(91)至(93)中的“女技师”“大娘们”和“化工车间”是制作行为的制作人,只有制作人才能决定制作的速度。
还有些标明制作方式的“X 制”类动词,其语义并不明显指向制作人、工具或材料,比如“研制”“配制”“调制”。

“X 制”类制作义动词构词成分中的语素“X”在词语概念中融入了具体而特别的制作方式,所以与单纯仅表制作义的词语相比也显示了制作行为的下位认知图景。与各种各样的“X 制”类制作义动词相比,“制作”“制造”等词语显示了制作行为的上位认知图景。
(二)表制作的泛义动词
“弄”“搞”“打”等泛义动词的制作义是在语境当中确定的,请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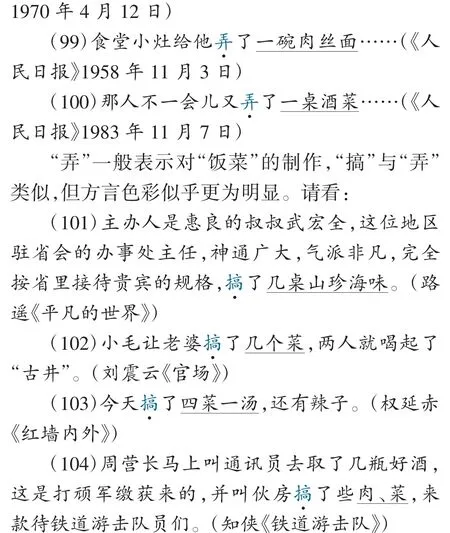
与“搞”“弄”只表示“饭菜制作”比起来,“打”更复杂一些。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打”虽不表“饭菜制作”,但可以表某些特定的“食物制作”。“打”与例(97)至(104)中标下划线的制成品要素均无法形成搭配关系,请看:
*打吃的 ?打饭 ?打一碗肉丝面
*打一桌酒菜 *打几桌山珍海味
?打几个菜 ?打四菜一汤 ?打肉、菜
“* 打吃的”“* 打一桌酒菜”“* 打几桌山珍海味”都无法成立,其他的说法即使成立也与“饭菜制作”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表示与如下三例相同的“买”或“取”。请比较:
(105)我知道她又在避我,只好打了一碗菜,筷子插了两个蒸馍回到后殿去。(贾平凹《秦腔》)
(106)戈玲被哭难受了,又无权丧失原则,便到食堂打了份肉菜包子,请他吃了再哭,自已当场坐下看林一洲的稿子。(王朔《修改后发表》)
(107)下班的人流过去了,刘絮云的道路比较通畅了,她把药箱放在家里,到食堂打了一点饭回宿舍关起门来吃。(莫应丰《将军吟》)
我国江南地区有一种习俗,每到农历年底都会用糯米磨成粉制作年糕,并以之作为新年走亲串户的传统礼物,这时会用到动词“打”,因为年糕制作有四个步骤———“掺米→蒸米→打糕→切糕”,“打糕”就是用特别的工具把刚蒸出来的松糕通过不断撞击来压实,这符合“打”最本质的动态认知图景。此外,北方农村把制作月饼叫“打月饼”(而不叫“烤月饼”或“做月饼”),这也与其认知图景分不开:月饼制作是将裹好馅料的饼坯放入模中挤压成型,然后再将月饼从模子里脱出来进行烤制。这里面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脱模,脱模是将月饼模子反转后进行有技巧的敲击,由于月饼和模子粘得很紧,若敲击不当,脱出来的月饼就会变形,所以这种技术活儿一般由糕点店中最有经验的大师傅来操作。请看:

其二,“打”主要是表示“器物制作”,这里的“器物”一般可分为三类:“家具”“首饰”和“工具”。“家具”“首饰”和“工具”作为三个集合名词本身就能充当制成品要素作“打”所支配的宾语,请看:

例(113)至(115)中的“柜子”“椅子”和“床”都是典型的家具,例(116)中的“棺材”虽不是“家具”(也许也可看作过世之人的“家具”),但与家具的制作材料相同(一般都是木料)。表示家具制作用泛义动词“打”,可从家具制作的认知图景寻找理据:制作家具的过程就是把零散木料组构起来的过程,而要把零散的木料组构起来,肯定少不了“钉钉子”或者“凿榫头”等环节。“钉钉子”是“把钉或楔子打入他物,把东西固定或组合起来”;“凿榫头”是“敲击、捶打榫头,使榫头嵌入榫槽,利用卯榫结构加固物件”。再请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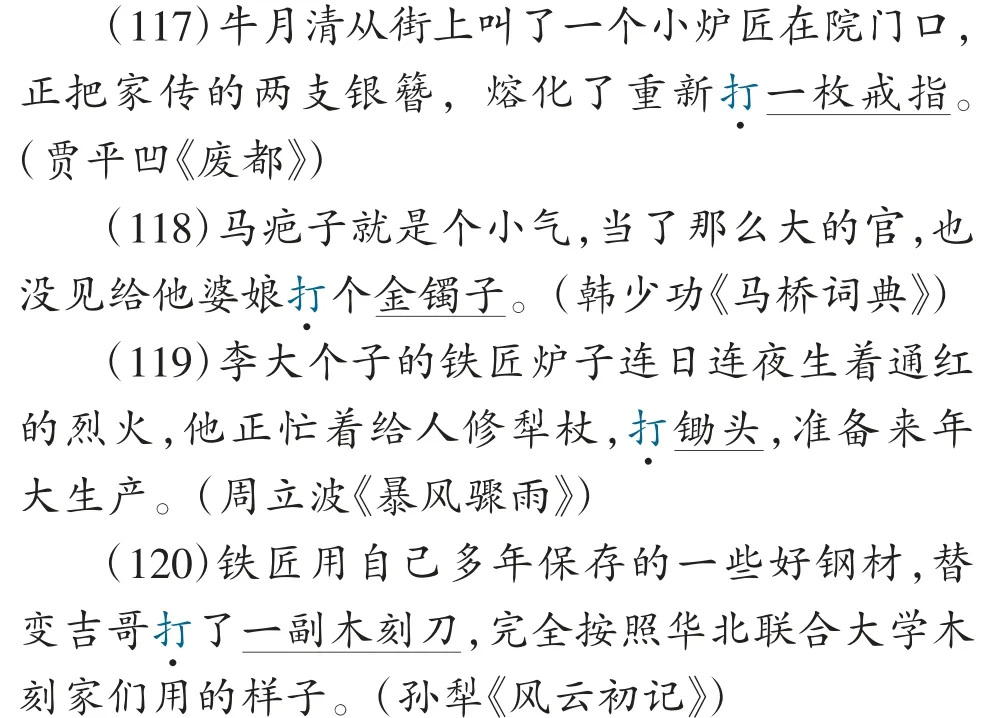
例(117)、(118)中的“戒指”“金镯子”都是金属“首饰”,例(119)、(120)中的“锄头”“木刻刀”都是金属“工具”。“首饰”与“工具”在制作过程中,作为材料的金属也要受到“专业的击打”。
综上所述,表示“器物制作”的“打”都是在“击打、撞击”的意义上实现的,而“击打、撞击”正是“打”最本质的认知图景。
其三,除了某些“食物制作”与“器物制作”,“打”还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实现为“制作义”,这与“打”能表示多种动作方式密切相关。请看:

例(121)中的“打”是指“搅拌”,例(122)中的“打”是指“编织”,例(123)中的“打”是指“涂抹”,例(124)中的“打”是指“挖凿”;“搅拌”“编织”“涂抹”“挖凿”是复杂度更高的“打击、撞击”,“打糨糊”“打毛衣”“打花脸”和“打深井”都是制作行为。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回顾了认知图景层次理论的概念构建及其具体应用,考察了影响认知图景层次的构词因素与句法成分(主要是补语),展示了上、下位制作义动词的认知差别。本文还对现代汉语的某些上位制作义动词——比如抽象动词(“制作”“制造”“制”)与在语境当中确定含义的泛义动词(“弄”“搞”“打”)进行了相关说明。
当然,在现代汉语中首屈一指的上位制作义动词无疑是“做”。因为“做”是汉语的核心动词和基础词汇,其在制作义动词中的使用最为频繁。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33]显示,“做”的频序号是77(共56008 个常用词),它不仅比其他所有制作义动词(不只单音节,也包括双音节)的频率都高,而且也是现代汉语中绝对的高频词。“做”还具有原型特征,它既能表示单纯具体的制作行为,也能表示“写作”“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充当、担任”“当作”“结成(某种关系)”“假装出(某种模样)”等众多引申义。对于原型高频单音节制作义动词“做”,我们将另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