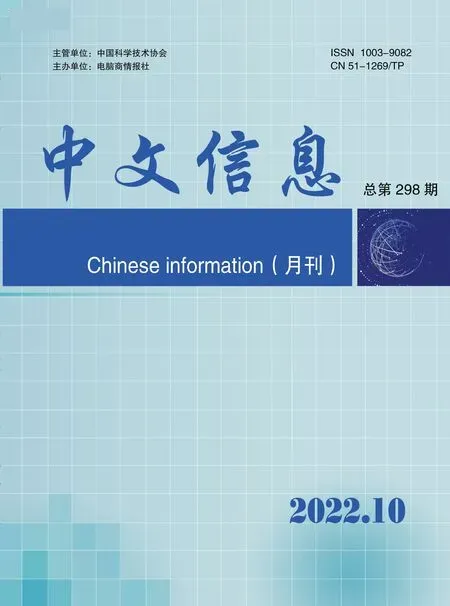汉字构造中的认知思维
2022-12-22杨鑫悦
杨鑫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引言
“六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周礼》中,“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时“六书”指周朝官学学生应掌握的六种才能。东汉班固把六书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玄提出“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他们分别对六书的概念进行解释,但指称并不明确,语焉不详。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归纳总结了古文字构造的特点,在举例说明的基础上,明确了“六书”的定义,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据此,清代学者戴震提出“四体两用”理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四种造字方法,转注和假借为两种用字方法。
20世纪70代中期,随着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认知语言学逐渐兴起,提出语言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认知系统,语言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语言是人们通过认知思维和心理活动,对客观世界经验进行概念化和结构化的结果。认知包括感知觉、知识表征、概念形成、范畴化等,生理构造、身体经验、感知觉能力、想象力等因素也在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认知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领域的主流研究之一,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
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理据性及意象图式理论应用于对汉字字形构造的分析中,用当代语言学理论解释我国传统语言学专著《说文解字》。由于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方法,本文不对它们进行分析,对汉字构造中认知思维的阐释主要集中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方法上。
一、汉字构造的范畴观
人们在互动体验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和反应,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这些完型概念即为范畴。范畴化以经验为基础,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出发点,是对外部事物、事件、现象等进行主观概括和分类的心理过程,赋予世界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结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2]。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共划分了540个部首。从汉字形体来看,汉字的形符大多来自独体字中的象形字,象形字是基于事物的外形特征,用笔画勾勒和描摹外观的文字,依据字形即可理解字义。象形字既能单独使用,也可以充当其他文字的部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说文》界定的象形字基本都是对生活实际存在的事物进行刻画和书写,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最先感受到的是有形具体的物体,象形字是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其他文字的基础。以指事字“上”“下”为例,“上”本义是高,短横为指事符号,表明事物位于大地之上;“下”本义是低,短横指事物位于天空之下,指事字在象形字上添加指事符号而形成。当象形字充当其他文字的构件时,它成为表示意义范畴的形符,也叫义符。
尽管象形字是人们通过感受具体有形的事物而描摹出的文字,但图画转换为文字的过程也体现了人们认知思维的抽象性和归纳性。比如象形字“月”作偏旁时,本义指肉,所以“月”作偏旁的字多与身体部位相关,“月”成为表示身体部位范畴的原型,对范畴进行抽象的图式表征。在字形上,与身体部位范畴相关的事物表现为以“月”作为构形部件,生成以“月”为部首的汉字,如“腿”“脸”“腰”“脚”“膝”“肩”等。有些象形字从独体字转变为形符时,原有形体发生变化,比如“火”变为“灬”“水”变为“氵”“手”变为“扌”等,但变化前后的语义没有差别。以“火”为例,“火”分化出的偏旁“灬”成为常见的构字部件,“燃”“焦”“熟”“热”“煮”“煎”等字在语音上虽与“火”没有关联,但在意义上与“火”联系紧密,表示了“火”的不同状态和用途。
范畴凭借典型特征和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其内部不同成员的隶属程度存在差异,范畴具有模糊性和层次性,包括基本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在认知过程中,基本层次的显著度比其他范畴层次更高,所以人们通常在基本层次上称呼事物[3]。当基本范畴相同时,对事物特征的分类依据不同,划分出来的下位范畴也有所不同。比如基本范畴是“木”,根据树木的集合状态,可以划分下位范畴“林”“森”;根据树木的组成部件,可以划分下位范畴“根”“枝”;根据树木的繁盛状态,可以划分下位范畴“荣”“枯”;根据树木材料的功能,可以划分下位范畴“柜”“框”等。下位范畴是按照感知、功能、交际、知识结构的顺序进行划分归类的,体现了人们认知思维的渐进性和组织性。
二、汉字构造的理据性
汉字字形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一些基础部件的原有形态发生变化,逐渐趋于符号化,但中华民族的认知思维在文字符号的演变中是一以贯之的,汉字构造体现的理据性与语言认知中的隐喻密切相关。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遍及人类常规的概念系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概念化经验方式及说话方式都产生了广泛作用[4]。隐喻蕴含人类思维的认知规律,通过映射在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建立相互联系,帮助人们用已知的、具体的事物去认识全新的、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思维方式,也是文字字义扩展和引申的途径。
象形和指事一般只对单一静态事物进行图形示意,而会意和形声能够展示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关联。根据事物间的联系,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的文组合起来,使其意义相互融合,即为会意。会意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构造是人们对外界事物认知和表达的结果。以“习”字为例,“羽”指鸟的翅膀,“白”表示“自己”,“习”用“羽”“白”会意,本义指鸟类反复飞翔。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深化,人们赋予“习”新的含义,把它从具体概念域映射到抽象概念域,引申出学习、练习、熟悉等隐喻含义。汉字本义体现字形与字义的关系,而本义与引申义的关联则表现为汉字基于认知思维而产生的理据性。形声字由两个文或字复合组成,义符或形符表示事物类别,声符或音符起标音作用。以“江”字为例,形符“氵”表示类别,声符“工”表示读音,形声字的构造明确体现了汉字的理据性。
人类思维认知机制还包括侧重表示指代功能的转喻,转喻用一种实体代替另一种实体,其映射发生在单一认知域矩阵中,《说文》中某些部首体现的理据性也能对转喻思维加以解释。比如“品”字部首,“口”表示人,“品”用聚集状态代指“众多”之意,通过事物或人物的出现场景表示状态特征,是用整体指代部分的转喻。而“晨”字部首的甲骨文字形上部分象双手之形,下部分象农具之形,两者会双手持农具耕作之意,古人的生活作息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的汉字构造通过对特定时间内人物习惯动作的描摹,代指动作事件发生的时间,是部分指代整体的转喻。
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汉字的理据性也在经历着显隐变化。有的汉字构造在字形演变中理据清晰,意象明确。如会意字“明”,从月从囧,字形直观展现字义,月光照射在窗棂上,表示明亮的意思。有的汉字字形演变体现了经济性原则,某些部件的意象走向符号化,理据性比较模糊。如“彡”本义指须毛和画饰的花纹,根据花纹的波浪形状,“彡”从源域引申到视觉概念域,“髮”表示头发飘逸的样子,“彡”还引申到嗅觉概念域,“鬱”表示香气弥漫的意思,而“髮”和“鬱”简化后的汉字“发”和“郁”均已看不出原有部件的意义。还有些文字构件发生讹变,掩盖了原始意象,使理据性难以辨析。比如象形字“囧”描绘竹子或木杆撑起窗子的图画,本义指明亮。近年来随着网络用语的盛行,由于“囧”字形与人脸形状和表情较为相似,被赋予了网络时代的象形意义,成为流行的表情符号,表示郁闷、尴尬之意,字形构造的理据性存在模糊混淆的情况。
此外,假借和转注也体现了汉字的理据性。由于汉字数量有限,人们在用字过程中假借已有的汉字字形来表达新的含义,为区别意义,有的汉字在原有字形基础上添加其他表示字义的部件,成为分担源字记录职能的分化字。比如“着”从“著”中分化出来,表示进行、着手等含义,而“著”侧重表示与写作、书籍相关的意义。
三、汉字构造与意象图式的关系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古人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体验和描摹,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是根据天象、地理、鸟兽的斑纹、土地所宜等可以观察的对象创造象征符号。到了皇帝时代,仓颉看到鸟兽足迹,意识到不同纹理具备不同含义,开始文字的创造,仓颉造字的主要方法是描摹物象形体,其后对文进行注音,使之成为字。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表音文字记录和模写词中声音,表意文字用符号代表词,该符号与词的含义有关。由于汉字字义与读音没有必然联系,而是通过字符本身所表达的观念记录语言意义,所以汉字为表意文字。汉字形成初期,古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依类象形”的描摹、储存及记忆阶段,随着对周围世界的日渐熟悉和认知思维能力的提升,汉字的创造逐渐走向“因义赋形”“以形表义”的阶段[5]。汉字从单体字向合体字发展,从象形字、指事字向会意字、形声字演变,义符和声符共同构成的汉字使意象符号化,生成能够传达所指概念的意象图式,反映了人们在心理认知上对客观事物的把握。
意象图式和隐喻投射是想象和理解的两种基本结构,意象图式基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多次接触和经验积累,总结出能够联系具体意象与抽象概念的组织结构,从一个领域投射到另一个领域,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相似关系进行延伸推理,解释其他领域的抽象概念[6]。意象图式源自人类概念化认识事物的能力,人们可以通过隐喻将具体事物、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与抽象事物、复杂概念、一般范畴联系起来,理解语言运用的更多情况。空间关系是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基础,汉字构造反映了古人的空间意识,他们通过生理基础和身体经验,感知事物的空间位置,把对汉字形态的认识从现实空间映射到概念空间,生成有关字形结构的意象图式,具体包括左右图式、上下图式、容器图式等。
左右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人体器官是左右对称的,人们借用左右手的位置关系表示相应的空间概念。比如“江”“河”“海”的义符都是“氵”,表示字义与水相关,而右侧偏旁的不同决定了它们读音的不同,在表音过程中,左侧义符被空白化,右侧声符被凸显窗口化。“脑”“恼”“垴”的读音相同,但意义不同,“脑”从月,表示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恼”从心,表示发怒或苦闷的情绪;“垴”从土,表示山岗或丘陵较平的顶部,左侧义符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表达意义,在表意过程中,右侧声符空白化,左侧义符被凸显窗口化。
上下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人们借用头和脚的位置关系表示上下的空间概念,人类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观察,能够感受物体在空间位置上的高低差异。上下图式字形结构中义符、声符的空白化和窗口化也是互相对应的,比如“煮”“蒸”“熟”下部义符相同,字义均与火相关,而上部声符不同,所以整体发音不同,上部声符窗口化,下部义符空白化。而“萧”“箫”“霄”的读音相同,意义不同,则体现了下部声符空白化,上部义符窗口化的意象图式特点。
容器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完整的身体由不同的器官组成,其构成要素是内部、外部及内外边界。比如“国”由“囗”和“玉”构成,表示疆域内的美好事物,引申指代国家之意,“玉”只有包含在“囗”的范围内才是“国”。汉字构造中的容器图式不仅包括全包围结构,还包括半包围结构,比如以“辶”为偏旁的字是半包围结构,字义与走路或跑步相关,部首为“凵”“匚”的字也是半包围结构,如“凶”“区”等。
结语
在对汉字构造进行多样化分析后,可以发现古人在创造文字和记录语言的过程中,已经带入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汉字的字形构造是认知思维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这在当时虽然是无意识的,不具备系统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观念有所重合。
《说文解字》部首的编排方式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象形字可以演变为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构件或偏旁部首,该过程涉及原型范畴、基本层次理论,汉字形体能体现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印证了人们认知思维的归纳性、渐进性及组织性。汉字字形和字义演变体现的理据性,与隐喻和转喻密切相关,随着认知思维水平的发展,字义从具体概念域映射到抽象概念域,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出其他含义,证明人类认知思维存在理据性,理据性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也经历着显隐变化。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构造是视觉观察和思维认知的共同结果,人们在观察事物的具体形象后,抽象总结出某类事物的共同特征,赋予客观事物主观认识的印记,使物象具备特定含义。义符和声符构成的字形使意象符号化,人们通过生理基础和身体经验感知事物的空间位置,生成有关字形构造的意象图式,反映了认知思维中的空间意识。
语言研究需要具备宏大的研究视野,虽然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产生于西方的语言学流派,但我国东汉时期的传统语言学专著《说文解字》中关于汉字构造的解释已经传达了认知思维的观念,汉字和汉语具有不容忽视的语言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