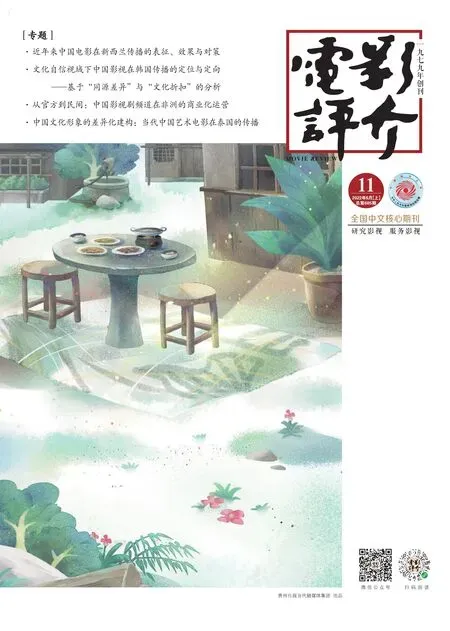《我和我的父辈》:“家国一体”的历史叙事及其情感表达
2022-12-21赵柯益
赵柯益
从歌颂祖国、凝思故土再到回望父辈,“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在保证主题表达一致性的前提下,故事讲述也由宏大叙事逐渐回归到个体生活。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我和我的父辈》在情感表达上发生了“由广向内”的叙事转变,着重探讨生命延续和精神传承这一深邃主题。该片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单元组成,沿着纵向时空轴线讲述了冀中骑兵团抗击日寇,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开启航天新纪元,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和新时代的科技创新梦等四个故事。四个故事在叙事主题上具备统一明确的指向性,即通过“我”的回忆视角再现父辈们的热血青春,展现小家与大国的同频共振。影片在致敬父辈的同时,没有单纯地书写他们的人性光辉,而是在“我”与“我的父辈”的平衡视点下进行双向度的情感沟通,将他们还原为最普通的父亲、母亲,既刻画了他们所经历的苦痛、迷茫,以及在“两难全”的境遇中对“我”的情感亏欠,也表现了“我”在多年之后对他们的精神承继和深切体谅。从艺术风格来看,《乘风》和《诗》两个篇章营造了悲壮沉郁的情感基调,呈现出传统的、“中国式”的父子之情,《鸭先知》和《少年行》则采用了幽默诙谐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市井生活中父辈对子辈的精神指引。除此之外,作品也在视点、节奏和影像风格等方面,体现了单元集锦式电影的创作特点。
一、“家国一体”的主题延续
不同于祖国篇、家乡篇对家国情怀的直接表达,《我和我的父辈》以四个时间段里父辈们承担的时代责任,婉转地表达了家国融一的中心主题。影片中的父辈形象分别以革命者、创造者、开拓者、圆梦者的身份出现,通过时空的纵向轴线烙印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其中《乘风》篇和《诗》篇在悲怆的基调中塑造了两代父辈形象,战场上挥洒热血的马仁兴父子和在荒漠中助推航天事业的施儒宏夫妇,代表了为新中国奉献终生的牺牲者和建设者群体。影片将他们还原为普通的个体,用细腻的手法书写着这些时代奠基人的艰难取舍和拓荒精神。《鸭先知》和《少年行》两个篇章,一个是在小诙谐中展现大时代,用市井幽默的方式讲述父辈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个是用科幻喜剧的形式来包裹爱与成长的内核,通过机器人老爸和鬼马少年之间的特殊父子关系,紧扣当下科技兴国的时代命题。四个故事折射了四个时代,内容多变、形式不一,但是在精神内蕴上却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家国一体”的终极主题。
(一)超越时代的精神肖像
吴京执导的《乘风》篇,选择在万马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找寻父辈形象。在这个单元中,创作者撷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真实事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加工。片中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为了把百姓转移到根据地,忍痛向日寇暴露了儿子乘风的位置,最终以乘风4人壮烈牺牲的代价,换取了老幼妇孺的安全转移。在整部电影中,《乘风》篇的情感基调最为悲壮豪迈,片中马仁兴和马乘风既是父子又是上下级,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父亲果敢刚烈、嘴硬心软,儿子性格倔强,事事不服输。电影开篇便展示了两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在骑兵团帮村民抢收庄稼时,乘风作为通讯员到上级处接受任务,马仁兴误会其偷奸耍滑,还没容乘风解释就把他一脚踹进了河里,在众人面前上一刻还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下一刻被教训得狼狈不堪却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当乘风壮烈牺牲后,马仁兴摸着战马上的血迹泪如雨下,作为父亲他对乘风满心愧疚,但是作为军人,他又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去保护大多数人。《乘风》篇将父子情穿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通过残酷的抉择,展现军人的血性和铁骨柔情,为观众树立了以生命践行使命的精神肖像。
《诗》的单元将视角对准了西北戈壁滩上的第一代航天人。电影开篇通过一组长镜头将观众的视线拉回到1969年的艰苦岁月,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黄沙尘土中孩子们的嬉笑随着一声巨响而停止,爆炸不仅仅代表设备实验的运行失败,还意味着有人可能为此丧命,其中就有这些孩子的父母。片中章子怡饰演的母亲是一名“与死亡共舞”的火药雕刻师,丈夫的突然殉职打破了一家四口的平静生活,使本就清贫的日子更为艰难,作为母亲的她,还要想办法弥补孩子的亲情缺位。《诗》篇虽然以很少的篇幅去展现父亲的形象,但从格局上来说,却是整部电影中意蕴最为深远的一个单元。首先是创作者在以“父辈”为主题的影片中,加入了不可或缺的女性视角(当然“父辈”并非特指父亲),展现了女性既当爹又当妈的坚韧强大。其次是影片没有将“我的父辈”限定为仅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在这个四口之家中,作为养子的哥哥经历了两次丧父之痛,在生父和养父的牺牲中懂得“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道理,这样的情节安排不仅颂扬了隐秘而伟大的奉献群体,同时还进一步拓宽了“父辈”主题的深远含义。
(二)敢于创新的先锋人物
在第三个单元《鸭先知》中,导演徐峥将视角放回到充满着上海意象的弄堂生活,通过对市井生活的书写,让观众感受到个体、群体再到整个时代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故事取材于中国首支电视广告的诞生,影片主人公赵平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将至未至之际,率先嗅到了机遇的味道,成为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在那个思想较为保守的年代,他预见“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却被邻居们嘲笑“大白天说胡话”。在面临产品的滞销困境时,赵平洋适时求变,凭借参桂养荣酒的电视宣传,让“广告”这个词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使国人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变,并以此拉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序幕。作品于诙谐中见温情,通过“鸭先知”的父辈形象,向后辈传递了敢为人先、奋勇探索的时代精神。
与前三个单元相比,《少年行》是一篇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创作者在这个单元中将父辈的概念进一步延伸,塑造了一位身兼父辈与子辈双重身份的人物形象。沈腾饰演的机器人肩负着特别使命从2050年穿越而来,邂逅了心怀科技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个人组成临时父子,开始了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机器人以父亲的身份弥补了少年的情感缺憾,并助其完成了自己的科技梦,少年长大成人后,参与了机器人穿越时空的实验,通过机器人的身份与30年前的自己相会。在这个篇章中,父辈的身份在未来人物和当代人物的身上发生了重叠。“你创造了我,其实你也是我的父亲”,寓指科技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代代不息的传承中,承担起继承和发扬的双重使命,以此实现民族和时代精神的赓续不断。
二、多重视角下的互补叙事
“视角不仅关系到一部作品的叙事风格,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叙事角度,即谁在看、如何看的问题。”[1]所以,一部作品的叙事视角直接影响到建构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当叙事者在影片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时,无论这个人物是否出现在作品中,影片都会从该人物的视角出发,最大程度地表达叙事者的倾诉之语。但是当叙事者隐藏身份,仅以观察角度、非人称的身份进行叙述时,作品往往会给观众带来电影自行讲述的幻觉,这种不受人物视角限制的叙述方式,也被称为“无聚焦型叙事视角”或者“全知视角”。由于集锦式电影的板块状结构特性,以及创作者不同的影像风格和类型架构,使得《我和我的父辈》带有多重视角和丰富的历史表达内涵。
首先,在第一人称叙事中,故事的叙事主体担当着双重身份,他既是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也是故事本身的叙述者,这样的叙事语境往往需要作品呈现双重视角,来保证故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使故事更有说服力,让观众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感。比如在《鸭先知》的单元中,开篇以冬冬的班级作文《我的爸爸》引出了一个在邻居眼里总搞歪门邪道,但在儿子眼里却善于学习新鲜知识的父亲形象。通过儿子的视角和影像画面的同步叙事,观众在短时间内便接收到了密集的信息,为了省钱自己做沙发、为邻居安装独立水表、帮生产队卖鸭蛋、囤酒自销等等。创作者仅用儿子的一篇作文,便立体地展现出父亲赵平洋是一个精打细算、头脑灵活的市井人物。此时叙事者的有限视角占据主导地位,在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情感时,也调动了观众的好奇心。但在这个场景之后,儿子的主观视角就转变成全知视角,观众在全知视角下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信息,沙发因为尺寸超标卡在了楼梯口,安装独立水表引起邻居侧目,在学校门口卖鸭蛋让孩子丢脸,囤酒自销被厂长痛批。视角转换造成的巨大反差,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张力和说服力,也让影片产生了幽默诙谐的艺术效果。
其次,在《诗》的单元中,作品在全知视角下也适时地穿插了“我”对我的父辈们的回忆视角,尤其是对这个四口之家生活日常的回忆,常常会以小女儿的视角建立创作者与观众的连接关系。比如父亲把航天工作比作在天上写诗,牺牲之后母亲又继续以父亲的名义写诗,向孩子们传递勇气和希望,但在一个雨夜,大儿子意外得知了父亲已逝的真相,与母亲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此时站在角落里一直哭泣的小女儿作为主观视角,成为了这场冲突的“隐形叙述者”。“我”的主观独特性和“他”的客观真实性相结合,呈现了一段细腻丰满又客观真实的故事情节。除此之外,还有妹妹趴在门口聆听母亲与哥哥的长谈,哥哥带着妹妹放孔明灯并许愿“希望妈妈不会死”等情节,都采用了多重视角结合的叙事方式。作品最后,小女儿施天诺继承了父母的遗志,在神舟号载人飞船工程中开始了她的首次太空之旅,《诗》篇也在小女儿“我也想上天写诗”的内心独白中结束。
除了人物视角的多重转换之外,《我和我的父辈》在主题表达上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视角,一个是以单线故事作为引线的个体视角,一个是对应宏观历史节点的家国视角。这样的创作方式在让作品带有历史全景感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感受到个体与整体的密切关系,使父辈、祖国等词语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由一个个“我”的血肉之躯和精神信仰组合而成的实体。影片中的四个单元分别对应着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当下科技兴国的时代进程。比如在《乘风》一章中,创作者在宏观层面选择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但又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骑兵团在团长马仁兴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英勇无畏的战斗力量,在经历了无数次捍卫民族尊严的战役后,最终以血染大地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微观层面,创作者以父子情为切口,搭建了一条小家与大国的连接纽带。片中父子俩在雨夜里敞开心扉,在昏暗的灯光下,马仁兴卸下严父形象伤感地说出:“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我只怕你不怕死,就算死,也要死在我后头。”这种九死不悔的牺牲精神、舐犊情深的铁汉柔情,铸成了故事壮美而真挚的悲剧感。
三、深远悠长的情感表达
(一)色彩语言的表意功能
在影视作品中,色彩是重要的视觉造型手段,被称为“被赋予生命和灵魂的语言”。色彩的表意功能“不仅是因为它拥有的象征隐喻功能、多维表现功能、形象识别功能和叙事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心灵世界与影片情感化为一体。”[2]可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物情绪的外化反映,在给画面注入情感和灵魂的同时,还能唤起观众不同的情感体验,所以通过色彩的转变来传达作品背后的深层喻指,是创作者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我和我的父辈》中,《诗》和《鸭先知》两个单元就充分运用了色彩的表意功能。比如在《诗》的单元中,父亲牺牲之前一家四口的生活画面,多以黄色、橙色等暖色调营造诗意般的美感。戈壁滩上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实验基地里整齐低矮的黄土房,还有照明设备透出的昏黄色灯光,低强度、暖色调的色彩让画面充满了浓厚的诗意感。尤其在两个孩子熟睡后的夜晚,夫妇二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父亲为孩子的诗篇斟词酌句,母亲坐在旁边静静地缝补衣服,光线的明暗对比让画面具有油画般的质感,使人物身上透射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但是在父亲逝世后,母亲的心绪也随即发生改变,既要收起悲痛继续紧张的燃料研发工作,又要在父与母的两重责任感的驱使下扛起家庭的重担,还要守护孩子的自尊心,向其隐瞒至亲离世的事实。此刻影片开始通过大面积的深色调营造沉重阴郁的氛围,象征死亡的黑与代表忧郁的蓝交织呈现,借此表达人物孤独、悲凉的情感转变。由此可见,色彩以其独特的表现性和寓指性参与作品叙事,具有点睛妙笔的作用。当影片过渡到《鸭先知》单元时,充满怀旧感的复古色调扑面而来,橙黄交织的色彩、对称的构图,同时辅以明快昂扬的背景音乐,使观众迅速沉浸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岁月。可见色彩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作为静态的艺术语言,是影片抒情表意的重要视觉符号。
(二)张弛有度的节奏变化
“电影节奏渗透在表演造型、声音和剪辑中,是电影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3]《乘风》篇便借用节奏来加强影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创作团队按照1∶1的比例挖战壕、搭战场,动用了几百匹战马,再现了骑兵团万马奔腾、冲锋迎敌的磅礴场面。刺刀、枪战、烈马厮杀、战士们擎旗冲锋,同时还有血肉模糊的战马、震天动地的嘶喊,高速镜头下的全景场面与局部特写交错呈现,快节奏的战争场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在此之上,话语、音乐、音响等因素共同参与叙事,在声音的传播性和联觉性的作用下,迸发出强烈的感染力。“节奏不是抓住镜头之间的时间关系,而是每个镜头的时限同镜头引起并满足注意力的动作的巧合,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时间节奏,而是一种注意力的节奏。”[4]所以,影片在快节奏的战争场面中穿插了多组交叉蒙太奇,将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两种情节剪接在一起,通过内容的对照、冲击,含蓄地表达出故事情节的深刻寓意。其中最为动人的是将乘风牺牲与大春子产子的画面交叉剪辑,一面是生命的陨落,一面是新生的开始,肉体的陨灭与重生的希望碰撞出强烈的悲剧感,揭示了薪火相传、代代不息的精神内涵。同样,在《诗》的单元中,创作者在最后也将东方红卫星发射的历史影像与神舟载人飞船的升空画面进行了交叉剪辑,既“画龙点睛”了《我和我的父辈》的终极主题,也寄托了创作团队深远的情感表达。
结语
《我和我的父辈》以时间为序、时代为章,通过四个故事的接力完成了对父辈精神的诠释,并将个体生命价值与民族复兴、时代进程紧紧相连。在对父辈时代的展示中,有热血难凉的戎装奋斗,有细腻诗意的女性叙事,也有浪漫炽热的未来憧憬,同时在视角、色彩、节奏等元素的加持下,达成了故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融合。影片在对生命延续和精神传承的叙述中阐释了“家国融一”的终极主题,父辈们身上不朽的品质,终将成为子辈们前进道路上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