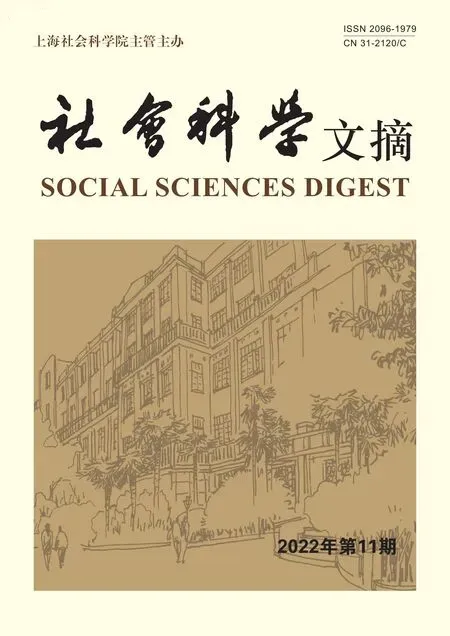社区研究中的田野精神
——以费孝通早期实地研究为例
2022-12-21刘亚秋
文/刘亚秋
费孝通一生行走于田野之中。对于费孝通来说,较为系统的田野调查有三次,均完成于1949年前:即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1936年的江苏开弦弓村调查、1938年的云南禄村农田调查。1949年后,费孝通依然坚持田野调查,尤其是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后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后来将1983—1996年间的田野调查结集成册,名之为《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在80岁高龄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旨趣是:志在富民。这四个字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志在富民”,在今天用社会学的一个术语来解释,就是“保护社会”;而“志在富民”的科学基础便是从实求知,就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科学研究。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开始于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调研。在深入大瑶山之前,费孝通对田野调查实已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他深受吴文藻、史禄国以及英国功能学派的马林诺斯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等思想的影响。可以认为,在进入大瑶山之前他所写成的学术文章,可视之为大瑶山实地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些文章大概完成在1933年4月至1935年8月间。从其最早对人类学理论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学的最初体悟就是认识到“实地研究”的重要性。1933年4月,在介绍人类学的几个派别时,他提到功能学派之实地研究的优势,批评其他学派的不足多是缺乏田野调查导致的,例如“进化学派只注意逻辑不注意事实,所以实地研究风气一开,初民社会实地调查资料日增,他们的结论亦一一的站不住了”。实地研究,可以纠正旧有知识的偏狭,这些偏狭既包括空洞的逻辑推演,也包括头脑中的“无端猜想”。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学术品格的发端。
费孝通这一派社会学人(燕京学派)对实地研究高度重视,这也是后辈学人应继承和弘扬的一种学术研究态度。笔者称其为“田野精神”。那么,费孝通这一时期的“田野精神”包括哪几方面的特点?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怎样的?
“田野精神”的三大特点
(一)发现“活”的社会文化
阐发“活”的社会文化,可以说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主旨。而他对于理论和概念的看法,事实上都体现为一种“功用”态度。他对理论的态度,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将理论作为工具。他指出,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叙述和阐明事实。而科学所使用的概念有两面性,在它做我们认识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知识范围的拓展。概念是人们因生活的需要而造出来的认识客观现象的工具,所以批评一个概念时并不能说它是真是假、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只问这一概念的“用处”有多大。他的这种“功用”态度更多的是受马林诺斯基的影响。
社区研究探索的文化是“活”的。费孝通在1934年明确提出,文化和制度是源自生活的。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就无从谈起,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文化只是他适应处境的方法。处境不同或处境有改变,文化跟着也要有所改变。生活中的文化之所以是“活”的,就在于人有能动性。人是能动的,人为适应环境,可以迁移;为了谋生存,人们生活的办法也一定要和其所处的环境保持一种平衡。
探索“活”的社会文化正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之所在。不过,发现“活”的社会文化,需要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是“客观”和“用”。由于当时的多数工具和方法都是从西方社会理论中借鉴来的,费孝通以工具的态度看待它们,他不仅认为具体的统计分析是社会研究的工具,理论也是社会研究的工具,因为后者在提供洞见的同时,也会成为阻碍。只有真实发生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学应该依赖的根本,它就存在于田野中,费孝通所作的实地研究就是朝着探究活的社会精神而去,他所主张的实地研究就是一种去阅读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的方法,这一点颇值得社区研究者借鉴和效法。
(二)实地研究中的使命感
费孝通实地研究的旨趣是通过社区比较研究来认识中国社会,进而寻求救中国的切实道路。这是费孝通践行的科学研究的使命感,它也是社会研究的价值问题,是任何学术研究都无法规避的又一根本问题。
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就存在于“看不穿”的人类情感和心态中,也就是社会的本质来自一种宗教情感的支撑。如果看穿了一切,社会理想也就不复存在。费孝通认为,人在本能上就可以构筑出一个“看不穿”的物件来,“在一个社会解组过程上,在各个人生活发生艰难时,还是要在原始的生物力中透出求生的积极气息,还是要在已幻灭的憧憬中再寻出一个看不穿的对象来。在生命会灭亡的明白事实中重勾出一个虽死犹生的永存信念来。生命重复获得它的神圣性”。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中蕴含的“使命感”充满信心,他写道,“我们不敢相信中国民族中这种宗教热忱是没有根底的。一切能生存在世界上的民族,在底层里没有不是蕴藏着这一种伟大的生物力”。中国社会也有这种宗教力。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后,费孝通继续进行多地田野考察,他发现中国社会的活力就存在于世代之间,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使命感般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的底座。
对于实地研究者而言,其为了“社会”而研究的使命感就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也是“看不穿”的人之生存状态,或者是即便“看穿了”也依然要坚持的理想主义者状态。
(三)“附身向下”
在大瑶山调查之前,费孝通就写过关于如何对待被研究者的态度的文字,即实地研究的一个要素就是研究者的态度:附身向下、倾听被调查者的观点,如此才能拉近与被调查者之间的距离,才能接近或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一访谈方法可以归为“设身处地”的技巧层面,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以诚相待”。费孝通明确指出,“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坦白和诚实”,他认为,“坦白和诚实能赢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
“以诚相待”就是对被调查对象的尊重,将其作为人一样尊重,因为他们与研究者一样,是有生命、有思想、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以诚相待之后,也会收获被调查者对研究者的感情。这种诚挚的调查态度,使得费孝通对于社会的看法祛除了“我执”,更容易得到对社会的客观认识。
通过大瑶山的实地调研,费孝通还得出了社会研究中一种文化上的设身处地的观点。费孝通指出,尚未研究明了一个文化的结构,而任意批评这个文化的特质是文明还是野蛮,是一件最容易的事。但所作的评价却不足道,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文明、那个野蛮时,都是我们自作聪明而已,结果是“把研究的线索切断,把讨论的门户关闭了”。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费孝通就已走出了文野之别,而建立了一种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费孝通强调,“一个严谨的研究者,假定他是在研究兴趣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在这时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悉欣赏”,就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设身处地”。
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
(一)功能派理论与实地研究间的关系
开展实地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在费孝通看来,尤其是需要一种重经验的理论来指导。相比理论的推演,费孝通更看重社会研究中对事实的叙述和描写。他如此称赞马林诺斯基在《野蛮人之性生活》中的田野记录:“文笔之秀丽动人,娓娓叙述初民之生活,几乎使人忘却所读是一本人类学的专刊。”费孝通对“细节”发出赞叹,就在于通过“细节”,人类学家把文化写“活”了,而功能理论中的“文化”就是活的。关于此,费孝通还深受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派克的影响。派克认为,文化决不单是一堆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也决不单是书本中所描写的习俗和惯例,文化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当它在反映新的生活环境而获得新意义时,它就在不断转变,在生长、在采取新的方式。文化是“活”的,还在于它可传递给后世。
我们回看费孝通在1933年发表的学术文章,可以发现最开始他就较为倾心功能学派。功能学派恰好可以在理论和实地研究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功能学派还意味着一种“整全”的视角,就是所得结论基于对生活全般的考察和研究。如同费孝通提到的,社会学所探究的社会文化应该是“整个性”的,它源自生活的“整个性”。功能学派认为,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是有赖于个性的,同时各部分及部分与整体之间都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存在。“整全”原则被马林诺斯基认为是功能学派方法的主要原则:“在看待野蛮人的性生活问题时,只有将各种关于性的事实加以综合,才能得到这一民族性生活的正确概念;无论从何种角度入手研究,性、家庭、亲属等问题总是表示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
(二)费孝通早期社会观
通过考察费孝通早期的实地研究思想,可以初步总结他的社会观:社会是“超个人”的。费孝通提出,在选择社会的研究对象时,要选择“群”,而不是个人,这便是超个人的社会存在。“所谓习俗、风尚、制度等社会的遗产,都是超个人而先在。而一人的生活中自创的方式和接受群体所给予的形式相较,实是很微少的。”
对“群”的认识有很多方法,费孝通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个人的角度来认识社会,这是他社会观的第一个意涵,这便是费孝通对个人和社会间互构关系的认识。
可以从个人入手研究群体的生活方式变化。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动力是各种不同生活形式的接触;生活形式自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定要靠人口的流动才能有所表达。他甚至认为,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也要依靠这流动来完成,以打破文化的“固定”,令个人的见解从传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费孝通指出,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个人私人的历史,所以我们若要叙述生活方式如何变迁,就不能不从各个人的私人历史入手。在方法上,最好是由经历这一番变迁的人自述其历史。但他所叙说的并不是个人个别私有的,而是和他同在一个社会形式中的人所共有的。也就是通过个体性可以看到社会性、公共性,社会学研究就需要在这一个体性中提升出公共性的议题。
第二,社会不仅是个人和社会的互相建构,还是一个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概言之,社会是一个连续生长和相互融合的机体。在这方面,霍布斯的社会观直接影响了费孝通。霍布斯提出,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社会的和洽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和洽。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在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在至善之境中各人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以谋公共的好。生物演化历程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心”的发展。而一切心理现象的发生都是由于物我的接触,在所谓的“物”中,尤以“他人”最为重要。霍布斯认为,和洽的社会是一种理想,也是人类努力的目标;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发展。
而对于社会发展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从伦理学入手,以阐明至善之境如何逐步实现;二是从历史学入手,看社会实际上如何努力。费孝通认为,这两种研究路径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研究社会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完全在“社会应当如何”,也不完全在“社会的实况如何”。费孝通的社会发展观就带有这样的努力,一方面是看社会的实况如何,另一方面也有社会改良的理想。
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费孝通社会观中的重要维度。他反对行为主义的个人刺激—反应解释模式,认为这是机械的,从而提出用单纯的因果机制难以解释人类复杂行为的观点。费孝通深受派克的影响,派克提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是有抱负的。这一经验主义的认识对于复杂现实极具解释力。也就是说,人类是活在回忆和想象中的。人能回顾和前瞻,所以在人的生活中有一种紧张和犹豫足以破坏已经成立的习惯;在这紧张和犹豫的时间中,活动的方向受当时态度的支配实较已有的习惯为甚。
而个人与身份间的关系,正好像戏子(人)和角色(社会)的关系。任何戏子扮演同一角色时,他们表演着相同的动作,唱着相同的曲子,甚至穿着相同的衣服,画着相同的花脸;但戏子(人)并不是角色(社会)。社会组织变迁(解体)时容易发生人生方面的困惑,费孝通提出,我们只要自问一下:“对于人生,谁能有把握地生活?谁不都是感到空虚、紧张和不安?谁能有把握了解他人?我们天天遇着的不都是使我们不能明了的人(和事)么?”
费孝通所践行的实地研究就是一种“社区研究”,他的早期调查都是深入一个村庄,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做“整全”的社会学研究。它与今天我们国家推进的社区治理实践之间有很大差别,但并非毫无关系。按照费孝通的观点,科学的实地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石。他的大瑶山社区研究是一个典型的实地研究,在这一科学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到具体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也只有在了解了一个社区内部的文化和结构后,所施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才会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重提费孝通的田野精神,还可以为广义上的社会研究提供参考。费孝通的社会形态学式的社区研究与今天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层层剥笋”的社会科学方法有所不同,后者显得更为精细,但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弊端——容易走向碎片化、不容易把握到整体,尽管这也是不能否定的科学精神之一种,但这种方式颇值得反思。今天的社区研究,应该在追求科学精细化的同时不忘“整全”的社会和生活的生态,这样的研究才会行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