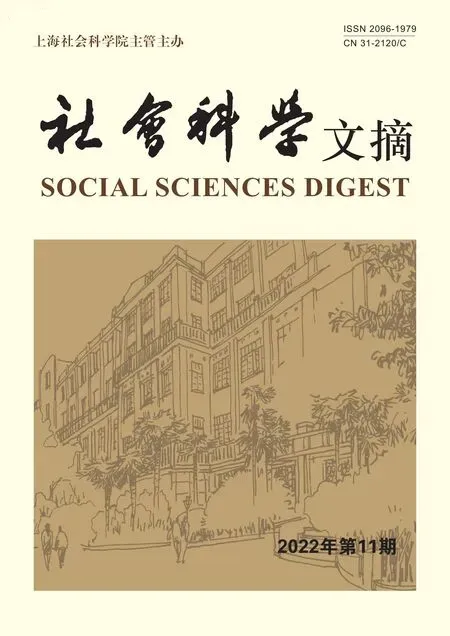汉语言哲学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
2022-12-21刘梁剑
文/刘梁剑
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当代问题
世界风云变幻,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然则,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正孕育其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塑进程。这些构成了当代不容忽视的图景。居今之世,当代中国哲学将以何种情调重新发端,以何种姿态登上历史与世界的舞台?思想离不开语言,理论离不开话语体系。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已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时代大问题。
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需要理解“当代”。“当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标识了一种有别于古代及现代的时代精神气质。创造性地提出一套话语,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即“当代”进行合理论说,在哲学的层面达到对时代的自我理解,这本身构成了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一项首要任务。同时,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将为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和话语创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将进入或者说理应将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生发期”。这一新的文化生发期,既要放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思考,又要认识到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哲学同时肩负着两种看似矛盾的任务: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致力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中国哲学要从气势磅礴的世界历史的展开实践中汲取力量,既发扬传统智慧,又能够会通东西,融入世界哲学的生发历程。
不难看出,对“当代”的理解关联着中国哲学对于自身的反思与检讨,其追问诸多元哲学问题:何为哲学?何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何为?中国哲学如何为?当代中国哲学如何为?如此等等。在当代,中国哲学的中国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何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探索的中国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超越了二级学科定位(作为与外国哲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超越了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作客观对象加以考察的哲学史研究范式,超越了完全依傍西方“哲学”成立自身的做法(中国哲学除了要像西方哲学那样重论理之外,还要“学”以“尽性以至于命”)。
上下五千年,否极泰复来。中国哲学聆听时代声音,在理解当代性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身的使命,扎根生活世界,锤炼中国哲学话语,切实推进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必将开辟出一番有别于古代及现代的“当代”新天地。
从汉语言哲学出发
中国哲学话语创建要提出具有解释力和生发性的标志概念(簇),这便内在地要求汉语言哲学的视域。然则,何为“汉语言哲学”?一言以蔽之,汉语言哲学思考以下根本问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用汉语做哲学,如何从汉语切入,以哲学语法考察为进路开展中国哲学运思,为世界性百家争鸣贡献新的元点与智慧。
“汉语言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何区别?美国学者詹斯在讨论“有没有非洲哲学”的问题时区分了两种“非洲哲学”,其中的“非洲”或作为空间或作为所在(place)。与之相似,“中国哲学”中的“中国”也有空间与所在之异。为了避免“中国”的空间义而突显所在义,我们可以引入“汉语言哲学”这一也许还不尽如人意的提法。“中国哲学”与“汉语言哲学”的辨析有助于阐明空间与所在之异。“汉语言哲学”摆脱了“中国哲学”之“中国”作为空间概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视为一种智性上的地盘。“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法,正是意图用“中国有哲学”来证成中国思想的价值,而“哲学”则是不成问题且用作证据的东西,是不受地域影响的普遍者。在这里,“中国”呈现为外在于哲学的空间。相较之下,汉语言哲学的问题意识则是,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相对于“有没有中国哲学”,这里侧重的是“何种”哲学。哲学不再是先在之物,也不再是与中国无关的普遍者。相反,“中国”以汉语的方式呈现为内在于哲学的地域。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可以看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中国”从标识普遍哲学所处的外在空间转变为标识特定哲学发生其中的地域,而“汉语言”则相应地突显为地域性的基本因素。汉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和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突出汉语表达如何赋予哲学思想以生命力。
中西异质文化的相遇引发人们对他者及自身的文化反思,汉语结构和中国哲学及中国思想的内在关联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在西方,赫尔德(1744—1803)、洪堡特(1767—1833)已对汉语语法与中国思想特质的相干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提出诸多卓见。然则,中国哲学因为是用汉语做出来的而有其独特价值,这是否意味着汉语做出来的哲学是特殊的,而哲学本应该是普遍的?这便涉及“一多”关系这一根本哲学问题,涉及“何为哲学”这样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涉及“哲学”与“philosophy”的中西古今之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跨语际的元哲学考察:阐明“哲学”与“philosophy”的关系、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阐明哲学的实践转向。如果由多元论或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切入,对“一多”问题的讨论将进一步追问:除了共殊(普遍与特殊)、家族相似的理解方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为合理地处理“一多”的方式?“一多”问题同时也是处理不同文明如何共处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我们需要把“哲学”与“philosophy”的中西古今之争放到中西文明交涉的背景中做知识社会学的反思。在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对“汉语言哲学”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一方面,要克服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暴力,让汉语面对哲学问题发声;另一方面,则要确定世界文明背景下应有的哲学姿态,避免对西方哲学的拒斥,避免以汉语自限。
除了“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之外,“汉语言哲学”还涉及西方哲学汉语化问题。“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论争关联着一种担忧,即:汉语能否成为一种哲学语言,汉语能否论说西方哲学。当西方学者(如赫尔德、洪堡特等)把汉语结构特点与汉语思想特质关联起来时,他们似乎否定了汉语可以论说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汉语能否论说西方哲学首先关系到西方哲学的汉语翻译问题:我们能否及如何把西方哲学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近代以来的西学典籍汉译实践似乎已在事实层面证明了,西方哲学能够翻译成汉语。但是,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我们在何种意义可以做到“信”(遑论“达”“雅”)始终是一个问题,这既是一个翻译实践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思想在跨语际、跨文化过程中“转渡”与生成的基本哲学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纳入广义“汉语诠释学”:研究西方哲学的汉语化,即西方哲学在汉语中的翻译、研究、传播与发展。
上文所述的汉语言哲学研究,或者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或者关注西方哲学的汉语化,而西方哲学的汉语化最终将导向汉语哲学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问题。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在哲学创造实践的层面进行汉语言哲学考察。当然,哲学创造之实践既有西方哲学汉语化的脉络,也有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脉络。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古今中西相互激荡的过程中,人们已经用现代汉语创造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哲学,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当代哲学。汉语言哲学亟须对此进行考察,总结哲学话语创建的经验:梳理19世纪中叶以来汉语思想家的运思经验,探寻哲学话语创建机制,揭示翻译与跨语际交流中思想生成、生活世界与经典世界、“译”“述”与“作”“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
汉语言哲学的关切,最终指向汉语在当下的哲学运思,即用汉语做哲学。用汉语做哲学,从运思的语言工具而言,中国哲学话语创建需要“活的语言”。首先,我们应当有效实现中国思想传统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传统思想话语只有成为我们用来说事情、讲道理、想问题的话语,才能够成为生意盎然的活的语言,真正促成中国哲学的原创生发。传统概念需要加以改造才能有效还治当下生活世界。其次,除了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之外,我们还要锤炼活生生的日常语言。日常语言和当下生活世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甚至可以说就是长在一起的。因此,日常语言是可感的,而用可感的日常语言来展开哲学思考便容易贴切、实在。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一项任务,便是从日常语言这一富矿中萃取语汇,进而将其锤炼成具有义理深度与厚度的说理词。
就哲学义理而言,汉语言哲学关注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新形势之下,如何让汉语所做的哲学取得世界范围内被其他哲学系统所理解的形态,进而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较为系统地阐述汉语言哲学对于如何做哲学的方法论主张(且称之为“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跨语际的哲学语法考察”)。进而,循方法而实践,在哲学的实践转向、当代历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性、偶然性、人机之辨、技术时代技术与哲学的互动关系(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技术改变做哲学的方式)等重要问题上,尝试创建兼具世界情怀与中国气象的哲学话语。
不难看出,汉语言哲学涉及理念、方法、实践等不同的层次。“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从汉语言哲学角度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演进,其侧重点是以汉语为切入点做哲学史考察。进而,我们要从哲学史考察转入直接的哲学问题研究。这时,汉语言哲学乃是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实践。更具体地说,就方法论而言,它是以哲学语法考察这一特定方式展开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实践;就内容而言,它是技术时代面向实践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
自西学东渐以来,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创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一直是中国学人内在的冲动;如果进一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以传统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和近代西方为代表的“两希”思想两种异质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大地上激烈碰撞,中国现代哲学家身逢现实遭际上的“乱世”与人类思想交锋的“盛世”,孕育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萌芽,为人类“后经学时代”“新轴心时代”的哲学话语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经验。
中国现代哲学自其开端之处就已然是一种世界哲学,但这种世界哲学在最初更多地呈现为在古今中外之争下的自我重塑,还只是单方面地被预先给予的跨文化情境所支配的地方性、方言性哲学思维,而尚未充分成长为一种对世界有所回报的世界哲学。经过一个近两百年来与世界的不断主动对话,汉语言哲学的世界性视域更加成熟,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世界哲学的形成中。与此同时,随着当代世界文明的加速交流和日益彰显的后人类状况,将人类整体作为思考单元的人类意识日益觉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造世界文明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新使命,汉语言哲学需要更加充分地彰显面向未来世界哲学的生发性意义。
从哲学话语到哲学工夫:穷理尽性至命
上面提到,汉语言哲学需要考察“哲学”与“philosophy”之间的中西古今之争,中国哲学话语创建需要反思“何为中国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中国哲学除了要像西方哲学那样重论理之外,还要“学”以“尽性以至于命”。就此而言,哲学话语创建并非做哲学或哲学实践的全部,而哲学的工夫也不止于论说明理。
哲学的工夫,首先表现在理论的层面。我们说一个人“哲学工夫好”,这首先意味着能把哲学这件事做好,它体现为穷理工夫深密而所穷之理深刻。进而言之,哲学的穷理工夫需要哲学工作范式的转变,从哲学史研究转到面向哲学问题的哲学研究。用“述”和“作”两个词来说,哲学史的研究偏于“述”,哲学的研究偏于“作”,从哲学史研究到哲学研究意味着从“述”到“作”的转变。当然,可能更恰当的提法是“述而作”,毕竟哲学的研究还是离不开哲学史探讨的。
其次,“说”除了强调理本身说得好不好之外,还要强调所说之理有没有具有一种溢出语言文字而进入生活世界以及自然科学、艺术、政治等知识领域的潜能。就后者而言,这意味着哲学可以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它在做好分内之事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其他领域把事情做好。进入生活世界,哲学将涉及个体层面的行动和群体层面的实践。
这样一来,讲哲学工夫,不得不从理论的层面进入实践的层面,即:在实存或哲学境界的层面,在做好哲学这件事的同时成就自己这个“人”。这个“人”已经超越职业意义上的哲学家而到了一般类意义上的“人”,或曰“人之为人”。这时,哲学突显出它的以下面向:一种生命的学问,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修身学。人之为人,涉及对人的意义的追问,需要在人禽之辨、人机之辨、天人之际中,在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中,思考自身的位置。
但是,哲学的实存层面除了为己之外,还指向为人与成物。这样一来,哲学要面对的问题,不仅可以来自哲学学科内部,还可以来自自然科学、艺术、政治等其他知识领域,尤其应该来自生活世界本身,包括政治生活、艺术实践、科学技术实践等。这要求我们对当下的时代问题有所感受,有所经验,进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回应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在当代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