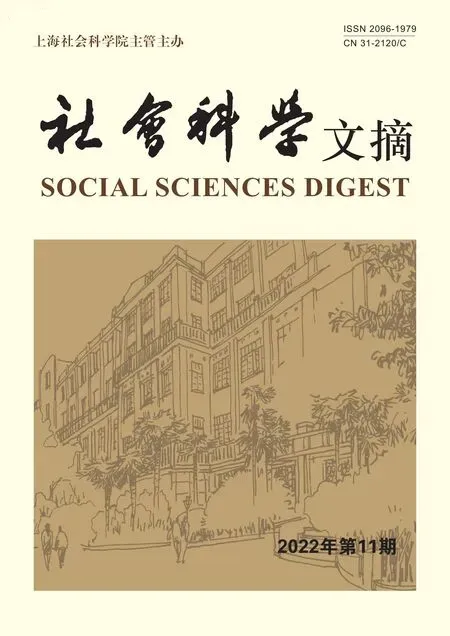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意识与主体性
2022-12-21郭齐勇
文/郭齐勇
在前贤与时贤的基础上,我与同仁合著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近日出版。全书含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少数民族哲学卷、古代科学哲学卷等10卷,逾60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出版的较为完备翔实的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这套书的写作、修订、编校、出版,经历了15年之久。全书以“前后通、上下通、内外通、人我通”作为目标,是否达到了此目标,请读者评说。我想从理论与方法上讨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就教于学界朋友。
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与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怀疑、追索的心理状态。问题意识是推动研究的关键。作为研究者,我们一方面不一定完全了解自己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要力图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不对称,就会导致对研究重心进行客观定位时的诸多困难。
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产生,与时代的刺激、挑战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时代的人,面对自然与人为环境的挑战有不同的应对方式。问题意识的产生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交游有密切的关联。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地域性也与问题意识的产生具有关联。
我们的经典大都是启发式的,往往只提出问题,并不将现成答案和盘托出。《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谈、讨论,开篇即如是三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引而不发,点到为止,或笑而不答,或提供机缘让学生辩难并从相关议题中进行体会。
孔子鼓励学生提问。他激赏当时人与弟子们的提问,把提得好的问题表彰为“大哉问”,如林放对“礼”之本质与本源的提问。孔子没有正面回答此问题,只是提示:执礼宁简毋繁,宁重内容、毋重形式。仁是礼乐背后的精神。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教条、虚伪的仪节、支配性的社会强制,使人不成其为真实的人。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也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体悟:礼乐形式的背后是生命的感通、人的内在的真情实感和道德自觉。“仁道”及其标准并不远离我们,现实的人只要有自觉,只要想去行仁,仁就在这里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两句话表明,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不仅如此,道德还是自觉而且自愿的,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
《老子》更重视的是反向和否定性思维的智慧。他是怎么提出并解决问题的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意识,须从否定入手,一步步减损掉对外物占有的欲望及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与攀援,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中去。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而依事物的自然性去做。
从以上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的提问方式、问题意识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恰恰构成互补的关系,足见中国哲学内部具有叩问、反思、怀疑、批判与检视的兴趣与能力。
人性问题历来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且讨论激烈的话题,古今中外皆然。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孟子提出了关于人性的新看法,即善性良知是天赋予人的,是先天的,是人异于他物之所在,人的这一点“灵明”绝不可抹杀。荀子则指出,在经验的层面上,人性是恶的,人之为善是后天的,应通过教育等来“化性起伪”。孟荀的问题意识,层面不同,一先验一经验,一理想一现实,共同开启了中国人性论争辩的思想闸门。
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们不断地提出、辩论与解决有关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就是问题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即对自己时代精神的呼应,以及解决此时代问题取得的哲学成果。同时,人类的、各族群的哲学思考,又总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展开的,因而有其普遍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在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关切,然而不同的哲学形貌背后都有普遍性问题。
问题意识在哲学史上常常转化为命题、词语、范畴(乃至范畴系统)、思维方式,成为一定的范式。在时代变革时,人们会突破旧范式,采用新范式。历史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概念、命题、范畴,例如先秦的道、气、阴阳、五行、和同;两汉的神形、虚实;儒家的天、仁、诚;道家的无、有;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孔老优劣、自然与名教;道教的性命、内外丹、玄、一、体用、心境;佛教的因果、体相用、止观、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缘起、理事无碍、一即一切、自性是佛、平常即道;理学的太虚、一两、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天理、理气、心性、格物、致知、持敬、居敬穷理、理一分殊、心统性情、道器、理欲、工夫、本体、乾坤并建、两端一致、内圣外王等。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指向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的关系。宋代以后,问题的重心转向了理或心。
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的关系,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的关系,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道)的关系,指向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即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天道与性命、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及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中国人尤重对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的考察,十分关注与古今相联系的诸问题。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的优长体现在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之中。
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
有的学者按照西方哲学思想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和问题,把中国哲学史肢解之后重新组装起来。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统性与主体性。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有人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只承认中国有思想。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史,只有思想史。这种认识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哲学”的定义不同。还有部分的原因,则是缺乏“文化自信”,似乎只有西方才有哲学。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长处与特点。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我们重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前提。
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但绝不是孤绝、封闭的。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台、贤、禅等,这些佛教宗派对东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又继续与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相结合,形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流精神形态——道学(或称理学)。自明中叶以降,中国哲学又走上了与西方文化、宗教、哲学碰撞与交融的道路。
我们分析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特色: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来看,不同时空中国人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确有其不同,而中国哲学的整体特色与这些问题与“问题意识”有关。
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国人依照着它而生活、实践,它不是与人的生活不相干的教条。西方文化与哲学把自然看作外在对象,中国文化与哲学则把自然看作与人融通为一体的存在,表现在《易传》的宇宙论中,即天地人三才统一,这一统一体的内在本质即“生命”。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创立、扩大、融会、潜藏等四个时期,这也是哲学生命成长的过程。
宋元明清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这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质言之,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和中国佛学等哲学形态,只有在中国才可能产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
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还特别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即中国哲学中有的理论、观点、方法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但是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绝非固步自封、狂妄自大,张扬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中国哲学内在的要求是以开放多元来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力。事实上,中国哲学早已走出国门,与外域不同民族的哲学相辅相成,并育而不相害。
《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与撰写主体是当代中国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华古今哲学思潮、流派、人物与典籍,这里包括了各兄弟民族。我们重视少数民族的哲学智慧与哲学成就,研究其特征、渊源与过程,专设“少数民族哲学”卷,这是一个创新。专卷以“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为基本出发点,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以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新传统。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一旦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便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要调动并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以下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我们应以同情的理解,或理解之同情,以钱穆所说“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研究的对象,不能居高临下、简单粗暴地对待哲学史上的思潮、流派、人物与典籍。我们批评、超越传统,但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质疑一定要以同情的了解为前提。有深刻的同情之了解才能做好哲学思想史研究。学术工作者还应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把真善美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史德,以史德统率史才、史学、史识。
第二是打好做学问的基础。应重视训诂、考据,有文字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与辑佚等能力,重视资料文献的鉴别、爬梳与点校的训练。研究中国哲学史,须下功夫研究发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与文献,而且重视对海内外已有学术成果的研读。《中国哲学通史》特别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对新出土的简帛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给予充分重视,各位作者都有个案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哲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做了深入的评析和阐释。
第三是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对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恰当的“度”的把握。没有逻辑就无法整理杂乱无章的纷繁史料,也无法理解复杂的历史现象。当然,没有生动活泼的生活及其资料,哪来的理论与逻辑?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表述并非一定是形式的、逻辑的,在某种程度上,“诗”比“历史”更真实。从问题意识的敏感性和启发性来看,我觉得应当保留对话、故事、语录式、场景式或韵文诗的形式。例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禅宗公案、理学家的语录等,这些对话、偈语生动有趣,意味深长,极富启发性。相形之下,今天我等的所谓哲学论著太干瘪、太枯燥、太无趣了。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希望回到这种诗化哲学的境界中。
第四是重视经典诠释中的追问与创新。本书的撰写重视解释学的方式与追问的方式。我们不应忽视对自己民族及文化传统中丰富的具有特色的解释学思想的分析与提炼,这些思想也可以给西方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解释学的方式是指我们置身历史情境中,同情地理解前人的思想;追问的方式是指我们的价值观念要在其中有所体现,之所以追问,是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有意义。
第五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我们认为要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意识”。应自觉培养“问题意识”,以此启发和引导研究的步步深入。我们设专卷,考察和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或科学的关系,希望开拓出关于知识或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哲学对知识或科学的影响的新的思维意向,以引导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新问题、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