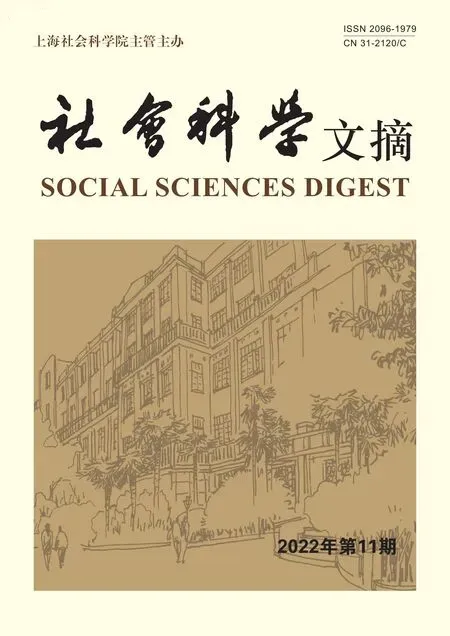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
2022-12-21肖峰
文/肖峰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字技术及其资本化
数字资本主义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衍生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其中的数字技术是基于数字化的电子计算机所控制的技术系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并向数字技术系统的介入,数字技术走向了智能化的新阶段,由智能化数字技术掀起了一场关涉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全面变革。
数字技术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从而数字技术资本化造成的劳动新异化也就有不同的呈现,可以从数字平台技术、数字生产技术、数字传播技术和数字监控技术四种类型数字技术的资本化来分析劳动的新异化。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数字技术依然遵循资本逻辑,资本家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革新不过是为了谋求更多剩余价值、促进资本积累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对劳动的异化,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对劳动的新异化。
数字技术资本化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
1.劳动者及其劳动力成为数字化商品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主要是使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商品化,并使劳动力对象化为“实物形态”的商品,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则使劳动力在消费活动中再度商品化,并使劳动力对象化为可量化的“数字化商品”。马克思曾批评资本主义工厂中使用机器的劳动“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怒斥其“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将工人培植为只有片面技巧的“畸形物”。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的资本化更是将这种畸形升级和扩大化,将原本可供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以外自由支配的身体,在算法的组织和控制下异化为可操纵的外表,将人自身异化为数字化生产活动一环。
2.直接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化
马克思曾经分析了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实体性物质存在的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与现实劳动主体之间存在着异化的关系。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数字技术对劳动主体对象性活动的拓宽和延展,使这种异化关系延伸为非物质化的虚拟劳动对象与虚拟主体之间的异化关系。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各行各业赋能,促使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数据、知识信息等资源作为“数字经济”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直接劳动对象,以其全局性和总体性特征在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和社会财富创造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3.部分劳动资料的智能化
部分劳动资料智能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升级优化和智能改造下,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劳动工具逐步由替代局部人力的“机械动力机器”扩展为具有人的总体性特征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变得更加智能化和信息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智能化控制系统所衍生出的各种智能劳动手段,比机械动力性的劳动手段往往更能体现当下社会生产的决定性特征。
数字技术资本化导致的劳动新异化
1.数字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与“售卖性情感劳动”
平台的运作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具有深层关联,它是资本为实现增殖而不断寻找新的利润获取渠道、新的商品以及新的剥削方式的技术载体和手段,平台所有者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提取实际上是平台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起点。在资本化的数字平台中,平台所有者对平台劳动力的剥削不仅体现在对其生成的数据信息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还体现在对其感觉、情感等感性认知活动的控制和利用之中。
数字平台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由象征和符号所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在数字平台虚拟空间中,“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作为一种新的劳动方式逐渐崛起并风靡社会。霍赫希尔德曾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表述为处于社会中的个体通过调整自身的面部表情,以表演的形式向公众展示经过自我管理的、符合公众期望的情绪这一过程,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出售情绪劳动以获取工资,以此获得交换价值。在数字经济平台盛行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拥有数字身份的个体在数字平台上不仅从事生产数据信息等原料的数字劳动,也从事着“情感劳动”。数字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使个体情感的私人属性被资本家异化为用于售卖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商品,即平台劳动者的情感也被资本化。以风靡全球的网络直播平台为例,直播平台中互动的主播和粉丝在资本家建构的虚拟空间中双双进行着“情感劳动”。一方面,主播通过隐藏自身真实情感,在公众需求和喜好的引导下创造出一个可供展示的外在表情,并以此获得粉丝打赏和平台工资;另一方面,粉丝在消费主播们的情感劳动时,在与主播的互动交流中“自愿”而又“主动”地为平台所有者创造着数据流量。这种将“自身”及自身的劳动力数字化为可计量的虚拟商品而出卖和共享给大众的行为,是一种为了获得金钱而“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行为,无疑体现了数字化时代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人类主体最大程度的异化。它使用户在数字身份中建构的虚拟情感愈加与自身真实的情感相疏离和错位,甚至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将自身情感打造为可出售的商品,通过交换实现对资本的追求,使“售卖性情感劳动”这种新型异化劳动形式逐渐形成。
2.数字生产系统的资本化与“主动性受迫劳动”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生产活动领域中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由智能化数字生产系统逐渐代替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机器生产系统成为最新的固定资本,并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手段促进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还催生出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灵活协作的新运营模式,“智能工厂”中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及全面自动化,使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的支配自身劳动力的主动性,这是社会发展中个人进步的体现。
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异化是由于人们受非自愿的固定化分工的约束而被动与自身的劳动行为相异化,那么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异化则深度演化为人们在非自发的自由活动过程中与自身行为相异化;如果说过去工人受生存需要所迫从事的劳动是强迫性的,那么现在他们在智能化生产系统中从事的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主动性的,为了避免被数字技术所替代而变得不被资本所需要,工人必须“主动积极”地去经受更长工作时间或更大工作难度的“考验”,看似主动积极的背后,其实是避免被抛向失业大军的“受迫”。
劳动的“主动性”还表现在数字化生产系统对劳动者身份的转换,即从直接劳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劳动过程的监督者,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即一定意义上的“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背后仍然包含着多重的受迫性。如在以“工资”为驱动力的报酬机制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主动延长自身工作时间。在物质生产能力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时代,智能化生产系统解放了人的双手,脑力劳动逐渐替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劳动者必须通过高强度的脑力支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竞争力,才不至于在高度“内卷化”的世界中被淘汰。人的生命在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悄然无声地被资本消耗殆尽,在智能化数字生产系统中看似主动的劳动,其背后是“身不由己”的受迫性。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智能科技介导的生产力极大优化了生产系统,使工作环境和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资本家提供的待遇也能使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基本保障。但无论是环境恶劣的工厂还是条件优渥的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在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条件下,它们都是资本剥削的场地。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公开性和隐匿化的区别,但在这些场地所从事的劳动都具有受迫性,由于后者具有“看似主动”的表象,因此称之为“主动性受迫劳动”。
3.数字传播技术的资本化与“消费性免费劳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受众学派”将“受众”定义为在媒体上观看商品广告的用户,并认为这些用户不仅是被媒体公司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还是为媒体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也即是说,互联网媒体用户在观看广告上的时间耗费以及随后购买广告消费品的消费行为中,即受众在文化知识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生产性活动。
可以说,互联网媒体上的观看行为拥有更多自主性,意味着比在工作日中承受更少的异化。但当互联网媒体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被异化为媒体提供者与媒体用户围绕时间展开的动态斗争场所后,劳动时间“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人们所受的剥削将更多更大,从固定工作时日延长到休闲娱乐之暇,从生产活动领域延伸至消费活动领域,固定工作时间被割裂分散为碎片化的片段,固定生产场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则延伸至休闲娱乐场域的消费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合谋”下,人们用于休闲娱乐的消费活动时间间接性地成了不断免费地为资本家提供海量数据等生产原料的剩余劳动时间。获得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平台用户类似于阿尔文·托夫勒口中的“产销者”(prosumers),他们既生产数据,又消费由自身生产的数据所创造出的产品(资本家针对用户数据所推出的广告等)。手机、iPad、电脑等互联网载体成为我们为资本家提供数据原料的劳动工具,沙发、卧室、交通工具甚至是“马路牙子”都成了新的劳动场所。此时,生产性活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生产过程中,一切生活和消费的休闲活动也因数字化而具有了生产性质,此即“生产商品”与“消费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消费性免费劳动”。
4.数字监控技术的资本化与“全景性透明劳动”
如果说数字化传播技术使人的劳动时间资本化,将人的一切时间都变为资本增殖的来源,那么数字化监控技术则使人的活动空间资本化,将人的一切活动空间都置于避免不利于资本增殖的管控之中。在互联网和宽带所及之处,摄像头、传感器等监控设备成指数级增长,这些数字化监控设备捕捉着广大受众在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中产生的一切数据痕迹,监视、调整甚至是操纵着社会的正常运行轨迹,使身处于资本家布控的监控设备中的社会主体如同生活在“圆形监狱”之中。数字技术把人异化为资源的本质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数字资本家通过对用户生产数据的强制掠夺和无偿占有,使用户自身的“劳动成果”异化为资本家用于获利及利用资本和再生资本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社交网络用户自我表达和与他人的网络交往越多,资本家收集到的信息也就准确,对其监控也就越精确,对其剩余价值的盘剥也就越多。资本家就这样用其新发明的生产规训术,为其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谋取高额商业利润,并且通过将整个社会空间置于其数字智能技术设备的监控之下,进一步实现了资本与政治的双重获利。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数字化监控设备将一切可控领域和范围都纳入窥视的界域,使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皆处于全方位的劳动控制模式中,并进一步形成“全景性透明劳动”这一类新型的异化劳动。
数字技术的回归及异化危机的化解
数字技术资本化造成的劳动“新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无法消除,为了克服数字化的奴役劳动,必须质疑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让数字技术回归到“人的工具”的本质,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新手段而不是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新工具。
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应用中,“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数字技术此时被用于劳动者为自己生产和创造财富,这一过程能够使人的本质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和丰富,并且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由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技术资本化导致的“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也被消除,数字技术对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扩大,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将成为巨大优势,为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契机,甚至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必要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创造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从具体技术来看,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还需要实现从数字平台技术到数字生产、传播和监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数字平台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寻获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培育新兴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平台经济”的长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繁荣提供新的支撑;数字生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系统地推动基于智能化生产工具下的“自由劳动解放”,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得到又一次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走向“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提供坚实保证;数字传播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提高公民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科学素养,助力人的精神层面的健康成长,同时还可以强力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舆论场中的话语权,破除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垄断和意识形态霸权,消解资本逻辑支配下利用技术优势制造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和新冲突,扩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力;数字监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手段,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来实施对数字技术的算法审计,杜绝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对算法的植入而导致的种种“算法歧视”“数字陷阱”“网络沉溺”“虚假信息消费诱惑”等现象,使人的数字活动与行为不再沦为资本蚕食的对象,而是回归为丰富生活与健康发展的新手段,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无疑也成为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