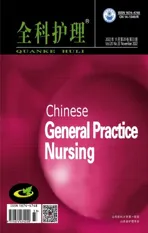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急救体系建设探讨
2022-12-17胡苏珍黄金银
胡苏珍,潘 桃,黄金银,王 华
社会急救是指由非医疗急救人员现场实施的救护病人的活动[1]。社会急救与急救系统院前急救、院内急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急救医疗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低,急救设备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配置不足,社会急救环节处于明显薄弱甚至缺失状态。本文结合目前社会急救体系现状、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有益做法,从完善社会急救体系的必要性、当前社会急救体系存在问题、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急救体系构建方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旨在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急救体系,提高急危重症病人急救成功率提供理论参考。
1 社会急救体系的内涵
社会急救,即公众自救互救,其急救主体是公众,发生场所可包括家庭、社区、校园、商场等居家环境或公共场所,是公众在事发现场自发、志愿的自救互救活动。社会急救体系的功能包括开展广泛的公众急救知识宣传及培训,提供必要的急救物品以及将“第一目击者”、病人、志愿者、急救物品、急救中心等各急救要素有机串联等[2]。
2 进一步完善社会急救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每年心源性心搏骤停者高达55万例,院外心搏骤停者的生存率不到1%,远低于欧美国家的10%~12%[1]。社会急救环节的缺失是导致我国院外心搏骤停病人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心搏骤停发生后的4~6 min内是“救命的黄金时间”,而我国各大城市的急救反应时间大多需10min左右。若缺乏完善的社会急救体系,过度依赖救护车和专业急救人员,未能由高水平的自救互救来填补这10 min的“救护空白时间”,则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降低抢救成功率。为此,急救专家提出了现场救护3个“一”的核心理念,即在突发伤病与事件的“第一现场”,由受过救护训练的“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救护,进而达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的作用[3]。建立完善的社会急救体系,提升公众急救能力和施救意愿,提供相应的急救物品,优化急救流程是落实3个“一”核心理念的关键。
3 当前社会急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水平不高,培训覆盖面仍需进一步扩大 据报道,我国合格的第一目击者不足1%,欧美国家则达到30%以上[3]。国内学者的调查显示,仅有25%的调查对象能说出AED的使用方法,2.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具备开展自救或互救的能力[4],仅有10.31%的大学生知道胸外按压正确部位[5],可见公众的急救知识和技能仍处于较低水平。急救培训覆盖率低是导致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指出,到2025年全国取得应急救护证书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不少于2%。2021年浙江省出台了《关于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5年持证救护员占户籍人口比例8%以上,公安、消防、养老等重点行业领域一线从业人员应急救护持证率不低于50%[6]。由此可见,通过广泛培训进一步提高公众现场急救能力迫在眉睫。
3.2 培训形式仍需进一步优化,培训质量有待提高 当前,公众急救知识普及主要由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美国心脏学会培训中心、医疗机构以及部分社会机构开展,其中,红十字会是各地培训的主力。传统的红十字救护员培训课程需要16学时(通常为2 d)的理论及实训学习,很多机构或人员由于工作等原因难以抽出系统的时间,进而影响其参与积极性。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推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课程,总体培训质量尚未有系统的报道。有学者针对有培训经历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仅有55.0%的受访者愿意为他人实施心肺复苏,是否具备足够的急救知识是其在决定是否施救时的首要考虑因素[7]。可见现有培训仍未使学员完全达到“能够救、愿意救”的目的。急救知识和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遗忘,也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已受训学员若能定期复训,能有效实现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巩固和更新,提升施救意愿;反之,则可造成知识逐渐遗忘,技能逐渐消失,进而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因此,建立完善的复训制度和复训课程,也是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途径。
3.3 公共场所AED配置不足 早期使用AED除颤是抢救心搏骤停病人的关键。每延迟1 min开展除颤,病人的生存率可降低7%~10%。为此,美国心脏学会提出了“公众电除颤计划”(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PAD),即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与大型社区配置AED,以便于在心搏骤停发生时由现场目击者在第一时间实施除颤[8]。据报道,日本AED配置约为每10万人394台,其病人存活率由未实施PAD前的3%提高到实施后的19.4%;瑞典AED覆盖率为每10万人160台,其首都由公众使用AED进行了除颤的院外心搏骤停病人的1个月存活率高达70%[9-10]。深圳市自2017年开始实施PAD计划,其AED配置率居于全国领先水平,目前已安装完成14 158台,每10万人配置AED数量约为80台[11]。2021年初,《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杭州市率先在全国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计划到2022年底AED配置水平提升至每10万人42台[12]。国内AED覆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
3.4 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实施率低,急救成功率亟待提高 研究表明,2017年浙江省公众第一目击者心肺复苏实施率为3.3%,抢救成功率为2.1%[13]。2021年1月—2021年12月浙江省宁波市急救中心的276例心搏骤停案例中,现场心肺复苏抢救成功14例,抢救成功率仅为5.1%,远低于英国和美国的28.3%和33.0%(美国部分城市甚至高达70.0%)[14]。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实施率低是影响抢救成功率的重要因素。除急救能力和急救设备外,信息不对称使得具备急救能力的热心公众无法第一时间获得相应急救需求,也是导致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实施率低的重要原因。借助通信技术组建的急救志愿者平台,可以快速查找并联系意外现场周围的急救志愿者,有助于病人及早得到急救。这一举措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推广,国内也有相关成功运用的报道[15]。
4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急救体系具体构建
社会急救体系是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建议参照发达国家和我国部分城市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不断提高公众急救能力,强化急救物品配备,充分利用高新技术辅助完善,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社会急救体系。
4.1 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深入推进社会急救体系基础建设
4.1.1 政府主导急救培训,提高培训覆盖面 将公众急救培训纳入政府应急队伍体系建设管理。可由红十字会或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公众急救培训工作。明确急救培训的具体实施部门,负责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培训组织与管理等。其他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将急救培训纳入相应人员教育体系,如教育部门负责推动急救培训进入校园,组织教师参与培训,将急救培训内容纳入学生课程;文体旅游部门负责组织相关管理及服务人员参与急救培训;各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相关社工及部分居民参与急救培训。以重点人群为切入点,先行覆盖,继而推广至全人群。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制定相应激励政策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急救培训事业。
4.1.2 加大AED配备力度,优化AED布局 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的要求,以政府出资为主,加大公共场所AED配备,实施公众电除颤计划。明确公众电除颤计划主管部门,统筹AED购置、布点、维护、更新等事宜。制定鼓励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AED配置和捐赠,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机构自主配备AED。在AED数量尚不足的前提下,应分析本地区历年院外心搏骤停大数据,优先在事故高发地点,公共交通、警务执勤车辆等流动交通工具配备AED,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对于农村等偏远地区,还可在基层医疗机构、村镇文体活动中心等场所设置配备AED等急救设备的急救志愿服务车(电动车、自行车等出行方便的交通工具),不断提升AED配置辐射面和利用率。
4.2 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众急救普及体系
4.2.1 建立区域心搏骤停数据库,明确区域内培训重点人群 借鉴心肺复苏Utstein(乌斯坦因)报告模式,构建本区域内的心搏骤停数据库,基于数据分析明确本地区心搏骤停高发人群和区域,以便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培训。
4.2.2 建设形成适用不同人群、教学与评价一体的线上急救培训课程 应根据群体特点和学习需求选用不同的课程内容,可采用“1+X”的模式,即将心肺复苏及基础的止血、包扎技术设为“1”,为必选内容,将常见急症、意外伤害及特殊职业情境所需的救护技能设为“X”,根据人群特点酌情选择。课程还应注重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将评价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最终生成学习报告。学员可凭借学习报告报名参与线下培训和考核,进而获得救护员证书。
4.2.3 打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线上管理平台 该平台应融合急救知识普及、急救培训报名、线上课程学习、线下培训教学管理、救护员证书发放与管理、救护志愿者管理、培训师资管理等功能。
4.2.4 强化培训督导和监管机制 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统筹管理与指导,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检查评估,严把教学质量和考核发证关。
4.2.5 着力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培训覆盖面的扩大必然带来师资的紧缺,师资队伍是培训质量及培训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将参与急救培训纳入医院参与健康中国建设、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的考核指标。在医疗机构组建培训师资团队,设组长或联络员负责本单位师资的选拔推荐、统筹安排等工作,所有师资均由培训实施部门统一管理和调配。将参与培训作为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务人员参与健康教育的评价指标之一,提高其参与积极性。
4.2.6 强化线下急救培训的可及性 在各级医疗机构、医学院校、成人教育机构、社区学校等开设培训基地,基地可在上级部门的统一监管指导下开展急救培训,构建便捷可及的急救网络。灵活培训组班、开班机制,采用送教上门、团体开班、个人合班,开设夜间班、周末班等形式,便于公众参与学习,打造现代化、便捷高效的急救培训形象。
4.3 探索建立联通公众与急救中心的高效社会急救网络
4.3.1 建立急救志愿者网络平台,串联各急救要素 招募急救志愿者,加入网络平台统一管理。意外事故发生时,由急救中心通过平台呼叫邻近志愿者并提供附近急救物品(AED等)信息,由此实现事件目击者、伤病员、急救志愿者、急救物品、急救中心等急救要素的有机串联。
4.3.2 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愿施救”的社会氛围 急救志愿者是社会急救网络最核心的元素。可通过动员医务人员、警务人员、退伍军人、现有志愿服务团体、社区工作人员等群体,先行组建急救志愿者队伍,打造急救志愿者“专属形象”,形成“特色品牌”。再通过推广与宣传,吸引更多人员参与。同时,出台急救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减少急救后顾之忧。此外,还可制定激励政策,对符合条件参与急救培训者给予一定经济奖励或招工政策优惠;对于积极参与现场急救者,加大表彰力度,并在社会信用评分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健康需求贯穿于人的一生,在突发急症或意外事件的情形下,是否够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挽救生命,减轻伤残,是保障“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条件。依托信息技术,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社会急救体系,是推动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