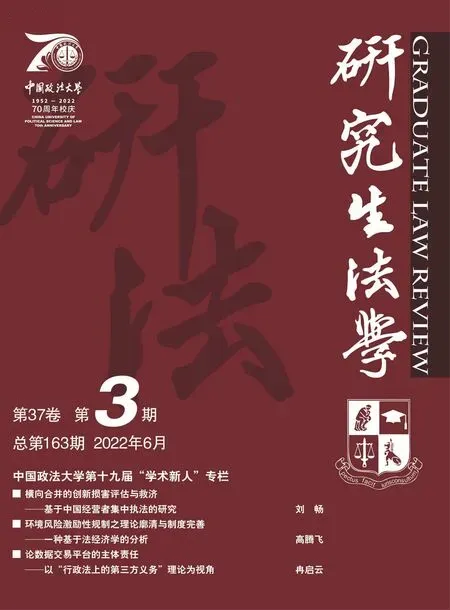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的反思
——从《中美经贸协议》切入
2022-12-16郭沛林
郭沛林
∗ 郭沛林,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下称《中美经贸协议》)对中国提出了“任何地理标志,无论是否根据国际协议或其他方式被授予或承认,都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变成通用名称,并可能因此被撤销”[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1.16条。的要求。一般认为,地理标志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称TRIPS协议)明文规定的知识产权客体,而通用名称则是不受保护的公共资源。[2]参见张今、卢结华:《商标法中地域性名称的司法认定:商标、地理标志、特有名称与通用名称之辨析》,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第98页。若地理标志被认定为通用名称,被撤销似乎是其无法逃避的命运。[3]学者一般认为,地理标志被认定为通用名称的后果是“应当予以撤销”“不宜允许注册”等。参见王洪燕:《从〈中美经贸协议〉看两国法律对地理标志与通用名称的定义及应对建议》,载《中华商标》2020年第4期,第40页。另见唐蕾:《涉及地理标志保护的通用名称判定分析》,载《中华商标》2020年第11期,第64页。这样来看,《中美经贸协议》的要求似乎是合情合理、无可指摘的。
问题未必如此简单。与美国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不同,[4]美国并未制定地理标志专门法,而是将地理标志置于商标法框架下加以保护,see 15 U. S. C. § 1127.我国采取的是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并行的双轨制模式。一个地理标志,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条注册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此即地理标志商标模式;又可以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获得注册并被核准使用于特定产品之上,被核准使用的产品称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受到行政保护,此即地理标志产品模式。二者的基本原理和保护范畴并不相同,其各自肩负独特的制度功能。“通用名称不受保护”是商标法的基本原理,[5]这是学界的共识。参见杜颖:《通用名称的商标权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第77页。另见冯晓青:《商标通用名称化及相关侵权问题研究——以“金丝肉松饼”商标侵权纠纷案为考察对象》,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3期,第76-77页。适用于地理标志商标自是法理使然,无须多言。但是地理标志产品制度并未委身商标法体系,而是自成一体,将“通用名称不受保护”推广至地理标志产品模式似乎缺乏坚实的正当性基础。
同时,在我国现行法中通用名称对此两种模式的影响并不相同。就地理标志商标模式而言,通用名称显然可以作为申请撤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理由。[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3条。但就地理标志产品模式而言,无论是《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还是《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都没有规定地理标志产品的撤销制度。换言之,当下我国并不允许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中美经贸协议》实际上是意图将通用名称引入地理标志产品的撤销制度中,使得地理标志产品可以因为地理标志“变成通用名称”而被撤销。
既然“通用名称不受保护”作为商标法的基本原理,无法直接推广至地理标志产品模式,而《中美经贸协议》恰又提出了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要求,那么就值得对“允许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命题进行反思。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地理标志的两种保护模式及地理标志“通用化”的本质。之后结合两种模式的区别指出“通用名称不受保护”这一原理仅适用于地理标志商标,而并不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最后指出了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危害及通过法律解释解决问题的困难性,得出“不应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应通过立法修正《中美经贸协议》带来的法政策错误”的结论。
二、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及其“通用化”本质
(一)地理标志及其多元保护模式
TRIPS协议规定:“地理标志是指表明一种商品来源于某一成员的领土内、或者该领土内的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志,而且该商品的特定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是由于其地理来源所致。”[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2.1条。地理标志具有保护传统文化、节省消费者搜寻成本、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维持农村文化繁荣与稳定等众多作用。[8]参见王笑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地理标志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一章。See Dev Gangjee, Relocating the Law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4.相较于著作权、专利权,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种类异常多样。在国际上,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商标法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专门法模式[9]法国单独立法,通过受控原产地名称(AOC)制度保护地理标志。Voir Loi no 94-2 du 3 janvier 1994 re lative à la reconnaissance de qualité des produits agricoles et alimentaires.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10]德国将侵害地理标志的行为视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制。Vgl.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 vain 7. Juni 1909 RGBl. S. 499.等。大多数国家并未单纯采用专门法或商标法模式,而是多种方式并用。[11]参见王笑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地理标志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我国即采用了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并行的保护体系,前者类似商标法模式,后者类似专门法模式。这种多元化保护模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淆,使得“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等概念难以区分。因此有必要在进一步研究前明确诸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
按照前述TRIPS协议的规定,“地理标志”这一概念仅仅指代标志本身。可以说,“地理标志”这一概念指的是权利的客体[12]参见冯术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性质、功能与侵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第4页。,而“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是客体的具体保护形式。“地理标志”借由“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等具体制度获得保护。类比而言,就像“实用艺术品”是受保护的客体,而“实用艺术作品(受版权法保护)”或“外观设计专利(受专利法保护)”则是其具体保护形式。
1. 地理标志商标模式
地理标志商标模式是将地理标志注册为法律规定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从而以私权的路径保护地理标志的。其适用商标法的一般原理。
该模式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从权利属性看,地理标志商标模式主要是通过授予商标权这一私权的方式保护地理标志。从保护方式看,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侵权行为,主要通过民事诉讼等私权救济方式保护。这种模式服从商标法的基本原理,主要强调“消费者心目中地理标志和产地的联系”。在侵权判断中,以消费者发生混淆为前提,即必须要求“消费者误认为侵权产品是地理标志所标示的特定产地生产的”。
2. 地理标志产品模式
地理标志产品模式则主要是以特定产品为导向保护地理标志。若某产品“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则可以将这一产品申请为地理标志产品,从而准予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13]参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1条、第5条。地理标志产品与地理标志商标模式以不同的路径并行保护地理标志。二者的关系正如学者指出的,“商标法侧重对就地理标志本身进行保护,而单行法规侧重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从而达到保护地理标志的目的。”[14]王莲峰、黄泽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之争与我国的立法选择》,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48页。
该模式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两部部门规章。从权利属性看,地理标志产品模式并非授予私权,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保护地理标志。从保护方式看,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仿冒行为不通过民事诉讼救济,而是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制止和处罚假冒地理标志的行为和不符合使用条件的使用行为。[15]参见冯术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性质、功能与侵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第4页。这种模式并不考虑消费者的主观认知,而是强调“产品特色和产地风土之间的客观造就关系”。由于其不考虑消费者的主观认知,故其并不要求消费者发生混淆,只需“在未被允许使用的产品上标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就会受到行政处罚。可以说,我国地理标志产品模式极大借鉴了欧盟的“原产地名称”制度,与其具有相同的制度内核。[16]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制度直接来源于原产地名称制度,制度相似性极高,唯我国保护水平低于欧盟。事实上,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与原产地名称制度基本等同。参见马晓莉:《地理标志立法模式之比较分析——兼论我国地理标志的立法模式》,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1期,第53页。
(二)“地理标志通用化”的本质
“地理标志通用化”或“地理标志退化为通用名称”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惯常表达。[17]参见于恩锋:《地理标志的淡化和通用》,载《中华商标》2004年第6期,第48-50页;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知终18号。甚至在中美经贸协议中,也使用了“地理标志……变成通用名称”[1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1.16条。的表述。此类表达显然会导致诸如“是地理标志整体通用化还是局部通用化”“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都通用化了吗”等疑问。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之前,需要明确“地理标志通用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用名称作为一种称谓,其表现形式只能是语词性的,即只能通过文字、词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如“席梦思”“大理石”“阿司匹林”等。故所谓“地理标志的通用化”,只不过是地理标志中文字组成部分的通用化而已。具体而言,若在公众的主观认识中,无法通过文字部分的语词将产品和产品的来源地联系起来,这一语词就退化成了通用名称。[19]有关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的界分标准,参见陈健、郭沛林:《中美经贸协议背景下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界分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22年第1期,第6-8页。其本质是公众主观认识的改变。可见,所谓“地理标志的通用化”并不等于地理标志商标或地理标志产品的通用化。
对地理标志商标而言,其表现形式不仅限于文字,而是可能和图形等因素叠加从而形成组合商标。显然,由于商标的显著性要求整体判断,仅仅语词的通用化并不必然导致地理标志商标丧失显著性从而被撤销。在“库尔勒香梨”案中,法官即认定“库尔勒香梨”这一语词为通用名称,但是没有认定这一语词和孔雀图案组成的证明商标丧失显著性。[20]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云民终398号。但对地理标志产品而言,由于其表现形式仅为“地名+产品名称”的文字,[21]参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2条。故在这一语词变为通用名称后,按照《中美经贸协议》就应当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可见,相较于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更容易受到通用名称的影响。
三、两种保护模式的区别及其与通用化的关系
TRIPS协议规定,如果一个地理标志已经在某成员国演变为通用名称,那么该成员就没有义务对该地理标志提供保护。[22]显然,这并非要求各成员国不保护通用名称,而是将是否保护通用名称的决定权留给了个成员国。参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4.6条。这一规定加之对于“通用名称不受保护”这一原理根深蒂固的认知,或多或少会导致人们产生“无论在何种模式下,对于通用名称都不应当给予地理标志保护”这一错误想法。[23]部分学者在论述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问题时,并未分开讨论通用名称对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的影响,只是泛泛指出“若退化为通用名称,则不能作为地理标志获得保护”。参见唐蕾:《涉及地理标志保护的通用名称判定分析》,载《中华商标》2020年第11期,第64页。显然,这混淆了地理标志商标制度和地理标志产品制度的区别。
本节从关联性范畴、制度设置和认知功能三个方面,指出了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与地理标志商标制度具有的本质区别。也正是这种本质区别,使得发源于商标法的“通用名称不受保护”原理无法当然推广至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中。在地理标志产品的语境中,考虑通用名称的问题并无意义,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不具有合理性。
(一)关联性范畴的区别
地理标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体现产品与产地的关联关系[2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2条。,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分别以不同形式体现这一关系,被称为“主观关联性”和“客观关联性”。地理标志商标由于本质保护的是商誉,实际上体现的是消费者主观认知中产品和特定产地的联系。用关联性理论解释,这一关系是主观关联性的体现,属于主观范畴。地理标志产品体现的则是产品质量与来源地自然或人文因素(Terroir要素,有学者将其译为“风土”[25]我国学者王笑冰认为,terroir就是指产品的质量与地域相伴而生:独特的投入制造了独特的产出,特定产地造就了特定产品,即土地和产品质量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其将terroir译为“风土”。参见王笑冰:《关联性要素与地理标志法的构造》,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85页。)之间的客观造就关系,这种造就关系是一种事实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与公众主观认知无涉。用关联性理论解释,这一关系是客观关联性的体现,属于客观范畴。[26]有关主观关联性与客观关联性的区分,参见王笑冰:《关联性要素与地理标志法的构造》,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82-101页。
如前所述,地理标志的通用化是公众无法将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和产品的来源地联系起来,本质上是公众认知的改变。显然,是“消费者主观认知中产品和特定产地的联系”即主观关联性发生了断裂。就地理标志商标而言,由于主观关联性断裂,地理标志商标无法发挥其作用,自然应该将其撤销。但就地理标志产品而言,由于其体现的是不以公众意志转移的客观关联性,故其并不受主观关联性断裂的影响。质言之,地理标志产品和通用名称一个属于客观范畴,一个属于主观范畴,二者属于不同范畴,当然无法相互影响。无论产品质量与来源地之间是否具有客观造就关系,只要在公众主观认识中,无法将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和产品的来源地联系起来,那么这一标志就一定会丧失主观关联性,从而沦为通用名称。反之,无论在公众认知中地理标志是否沦为通用名称,只要产品质量与来源地风土之间的客观造就关系没有消灭,其客观关联性就仍然存在,保护这一客观造就关系的必要就没有消灭,地理标志产品则当然不应该被撤销。
在诸多强调客观关联性,采取专门法模式的国家的立法中,都体现出了地理标志产品和通用名称分属主客观两个范畴,其间互不影响的理念。《欧盟地理标志条例》中即规定,对于PGI(Protected Geographic Indication,译为“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或者PDO(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译为“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来说,“受到保护的名称不会变成通用名称”。[27]See Article 13 (3) of Regulation 1151/2012. 值得说明的是,PGI和PDO两种制度均属于专门法保护,仅仅是准入门槛有细微的差别。而法国的AOC(Appellation d’ Origine contrôlé,译为“受控制的原产地名称”)制度也与欧盟的制度类似,规定一旦地理标志被注册为AOC,即“不能被视为通用名称”。[28]Voir Code de Consommation, Article L115-5. 值得说明的是,AOC制度属于专门法保护。PGI、PDO、AOC三者尽管命名不同,但是均为典型的地理标志专门法保护制度。法律具有第二性,不能无视第一性的社会现实。[29]参见李琛:《法的第二性原理与知识产权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95页。地理标志的通用化本质上是公众主观认知的变化,而法律无法左右公众的主观认知。无论法律如何规定,都无法决定公众是否将一个语词理解为通用名称。因此,以上立法强调地理标志“不能被视为通用名称”的旨趣实际上在于:一旦地理标志产品获得注册,在专门法体系下获得保护,即不能以通用名称为由将其撤销。此即从侧面体现出地理标志产品和通用名称无法相互影响的原理。
总之,从关联性的角度看,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并不具有合理性。
(二)制度设置的区别
地理标志商标服从商标法的基本原理,通过授予申请人私权的方式保护地理标志背后的商誉,其管理、保护都由私主体自发进行。
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不保护商誉,而是意在保证产品质量和产地风土的客观造就关系,“帮助农产品和食品生产者向购买者和消费者传达其产品和食品的产品特征和耕作属性。”[30]See Article 1 (1) of Regulation 1151/2012.在管理方面,无论是欧盟还是我国,均不采用授予私权的方式,而是由质检机构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保护。[31]See Article 13 (3) of Regulation 1151/2012.《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四章、第五章。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实质上被视为一种“公权”在维护。[32]参见林秀芹、孙智:《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出路》,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52-53页。因此可以说,地理标志产品制度更类似于一种“质量保障制度”,由公权力保证产品来自特定产地,并具有因产地风土而形成的质量。[33]我国现行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要求对于地理标志产品必须制定相应的标准或者规范,并由质检机构进行日常的监督和管理。而从比较法上来说,无论欧盟法还是法国法,都强调以公权力介入监管从而保证产地风土和产品质量的造就关系。参见王笑冰、林秀芹:《中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比较研究——以中欧地理标志合作协定谈判为视角》,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25-132页。王笑冰:《法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4期,第16-21页。《欧盟地理标志条例》甚至直接将地理标志纳入质量体系制度中,并将其视为质量体系标志符号的一个重要类别。[34]See paras. (1), (2) of the explanation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 in the Re gulation 1151/2012.
就地理标志商标而言,由于其私权属性,若沦为通用名称后仍予以商标法的保护,会使得其他地区的生产该类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无法使用该通用名称标识其产品,导致通用名称的垄断,这对于其他地区的生产者、经营者显然是不公平的。[35]参见金海军:《商标与通用名称问题的消费者调查方法——实证与比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第26页。
但就地理标志产品而言,其并非以授予私权的方式排除他人使用,[36]Siehe Simon Holzer Geschützte Ursprungsbezeichnungen (GUB) und geschützte geographishe Angaben (G GA) land wirtschaftlicher Erzeugnise, Bern: Stmpfli Verlag, 2005, S.387.而是通过公权力监控保证产品因产地风土而形成的特定质量。具体而言,是以“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进行质量认证。可见,即使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后,地理标志产品也仅仅排斥其他地区生产者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而并不排斥其对通用名称语词本身的使用,不会产生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者、经营者不公平的后果。类比而言,就像“绿色产品”认证虽然排斥生产过程不环保的生产者使用,但并不会造成任何不公平的后果一样。
实际上,地理标志产品的公权控制属性使得通用名称的判断根本没有必要。法国和南欧国家认为,产地的风土因素不可能被复制,因此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生产出与当地真正相同的产品。[37]参见王笑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在“FETA”案中,欧盟委员会就认为:“因为该类产品地理来源的排他性、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使该产品区别于来自其他任何地方的该类产品。这种情况下,该地理标志在其他商品上的使用会造成对消费者的欺骗,使其对该商品的质量产生误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再判定是否是通用名称。”[38]Joined Cases C-289/96, C-293/96&C-299/96, Kingdom of Denmark, Fed.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Fren ch Republic v. Commission, 1999 E.C.R.I-1557[1998].可见,在地理标志产品模式之下,无论通用与否,只要不是原产地出产的产品,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在这一前提下,地理标志是否沦为通用名称的判断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总之,从制度设置的角度看,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并不具有合理性。
(三)认知功能的区别
地理标志主要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两方面信息:第一,产品的地理来源;第二,产品具有归功于产地的特殊质量、特色或声誉。
地理标志商标的认知功能和普通商标并无二致,因为实际上消费者很难区分普通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39]参见王晓艳:《论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11期,第63页。举例而言,在“沁州黄”案中,被学者们均以“地理标志商标”视角考察的“沁州”“沁州黄”商标实则均为普通商标;在最近的“逍遥镇胡辣汤”事件中,被学者们均以“地理标志商标”视角考察的“逍遥镇”商标实则为普通商标。可见,消费者很难区分普通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一般认为,在上述两方面信息中,地理标志商标仅仅可以提供“商品的地理来源”这一信息,而无法提供“产品具有归功于产地的特殊质量、特色或声誉”的信息。事实上,地理标志商标能否提供“产品的地理来源”信息甚至都是存疑的。[40]这实际上是因为我国在审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时,并不审查“该标记是否被消费者理解为用来指示产品来源地”。这就导致部分包含偏远、不为人知的地名的地理标志在被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后,消费者并不能将其地名部分理解为特定地域,从而无法提供“产品的地理来源”信息。相反,《美国商标审查指南》就要求审查“表明相关消费者认为该标记用来指示产品或服务源自于标记所指示的区域的证据”。See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 1306. 05 (a).比如不为消费者所熟知的、用来指示偏远产地的地理标志商标中的地名部分就很难被认为是指代了某个地区,而更可能被认为是某种臆造性词汇。显然,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此商标提供了“商品的地理来源”信息。举例而言,对世界地理没有精研的人很难将“亚琛烤饼”中的“亚琛”理解为德国城市“Aachen”。[41]“亚琛烤饼”(Aachener Printe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列出并明确要求中国保护的德国地理标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附录六第55项。
可能会产生如下疑问,那地理标志产品就可以完整地传达上述两方面信息,不会产生“无法认识地名”的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地理标志产品的认知方式与地理标志商标大相径庭。地理标志产品不但标注产品名称与产地地名,亦加注了公权认证性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42]或与其本质相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20条、《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15条。前两者可以传达“产品的地理来源”信息,后者作为公权背书,可以传达“产品具有归功于产地的特殊质量、特色或声誉”信息。地理标志产品并不借助“地理显著性”,而仅仅是诚实地描述了产品的产地与名称,并通过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向消费者保证产品质量与产地风土的客观造就关系。其目的仅仅是告知消费者,“这就是你所期望的那个产地产出的传统产品”。[43]See Louis Lorvellec, You've Got to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Jim Chen, 5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5-80(1996).显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在认知上的担保、加持作用,使得地理标志产品可以传递完整的信息。此时,即使消费者并未听说过所涉地名,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也会促使其对其作“地理性理解”,故不会产生“无法认识地名”的问题。[44]在认知心理学上,可以说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给消费者提供了“将地名作地理性理解”的预期和背景。“当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与观察者业已拥有的模式存在足够多的匹配之处时,记忆中的模式就会被唤起并用于填补末观察到的细节进而指导后续的推论。”参见彭学龙:《商标法基本范畴的心理学分析》,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45页。
就地理标志商标而言,若沦为通用名称便显然无法提供“产品的地理来源”这一信息,其认知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自然也就无法受到保护。
但就地理标志产品而言,由于有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保证产品和产地的客观造就关系,通用名称并不会影响地理标志产品的认知功能。无论地理标志是否沦为通用名称,只要消费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地名指代的是某一地域”且“产品名称指代的是某一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就一定可以向消费者保证“产品一定来源于产地”。可以说,来源关系的主观认知被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客观关联性保证功能“锁死”了。这样一来,无论地理标志是否沦为通用名称,均不影响地理标志产品的认知效果。
总之,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看,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并不具有合理性。
四、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危害及解决路径
(一)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危害
作为新世界国家的美国采取集约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保护地理标志的传统,甚至认为地理标志是其扩大市场准入的“拖油瓶”。[45]正如Jim·Chen教授所言,“美国有多么不尊重地理标志,即使是对美国法律最粗浅的调查也可以看出”。See Jim Chen, A Sober Second Look at Appellations of Origin: H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rash France's Wine and Cheese Party, 5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9-64(1996).美国希望通过《中美经贸协议》“解决不适当地‘过度保护’地理标志,从而将美国农业和食品生产商拒之门外的可能性”[46]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ct Sheet. 2020:3.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phase%20one%20agreement/Phase_One_Agreement-IP_Fact_Sheet.pdf.,要求中国降低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就是其要求之一。
前面已经指出,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不合法理,没有必要。实际上,其还会降低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水平,造成我国地理标志资源的流失。整体来说,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具有负面影响。
1. 降低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水平
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现行法的关切完全集中于产品和产地的客观造就关系,并不考虑公众主观认知。在申请阶段,需要审查产品的特点和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客观造就关系,并不审查其是否为通用名称。[47]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审查审理指南(2021)》,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23/5652697/files/e2f755e4e49940239444689f6bc8dfd0.pdf.同时,现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也未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原因。这并非立法疏漏,事实上,这恰是在地理标志产品的审查和管理中坚持客观关联性原则的体现。
若按照《中美经贸协议》的规定,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原因,则会使得地理标志产品模式的保护稳定性下降,水平降低,无法发挥充分保护产品和产地之间客观造就关系的作用。因为一般而言,产品和产地之间的客观造就关系是很难消灭的,这一特点造就了地理标志产品模式的稳定性。地理标志产品一经注册,便很难被撤销,可以获得长久、稳定的保护。这也解释了为何地理标志产品模式被认为是“保护水平更高”的模式。[48]参见王莲峰、黄泽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之争与我国的立法选择》,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47页。然而公众认知却是主观且易变化的,公众认知中产品和产地的主观联系很容易断裂,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的事情时常发生。[49]See Louis Lorvellec, You've Got to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Jim Chen, 5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5-80(1996).事实上,有些时候越是成功的、销售广泛的地理标志越容易沦为通用名称,因为地理标志越成功就越可能吸引仿冒者,难以抵御侵权带来的通用化。就像Jim·Chen教授指出的,“在美国,最著名的地理标志最有可能变为通用名称。”[50]See Jim Chen, A Sober Second Look at Appellations of Origin: H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rash Fran ce's Wine and Cheese Party, 5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9-64(1996).Blakeney教授也指出,“著名地理标志将不可避免地滑向通用名称的深渊,最终丧失商标保护的资格。”[51]See Michael Blakeney, Proposa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4 The Jo 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629-652(2005).显然,若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原因,则会使得地理标志产品极易因为公众认知的改变而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地理标志产品所应当具有的稳定的、高水平的保护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
2. 造成地理标志资源的流失
如前所述,即使地理标志因为沦为通用名称从而无法受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保护,若此时产品和产地仍然具有客观造就关系,其仍然可以获得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换言之,此种情况下地理标志资源并未完全流失,其客观关联关系仍然可以受到保护。特定产地的生产者依然可以在不妨害其他生产者使用通用名称的同时,通过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保证、标识其产品的特殊质量,从而获得市场优势地位。
但若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原因,则会使得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之后,在商标模式和地理标志产品模式下同时终局性地丧失保护。此时会使得尽管产品依然具有由来源地风土造就的独特质量、特征,但其无法受到保护,特定产地的生产者亦无法以其获得市场优势。这实际上就产生了地理标志资源的流失。同时,因为地理标志产品被申请撤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于其制定的质量标准自会失去适用的空间。[52]参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17条。没有了标准的规制,长期来看还会产生产品质量降低,丧失特色,最终“泯然众人”的不利后果。
(二)我国对《中美经贸协议》的回应
《中美经贸协议》的签订推动了我国一大批法律、法规的出台与修订。为了满足《中美经贸协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通用名称判定指南(征求意见稿)》,在明确规定“本指南适用于地理标志保护、行政裁决中通用名称的判定”的适用前提下,规定了“在我国已获保护的地理标志演变为通用名称的,可依照有关程序撤销”。同机关发布的《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在第7条和第23条中,规定了以通用名称为由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具体程序。[53]《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第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给予地理标志保护……(二)产品名称仅为产品的通用名称的……;第23条: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认定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本规定第七条情形之一的,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撤销地理标志,提交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不难看出,我国当下的回应基本是将《中美经贸协议》中的要求完全照搬,可以说完全没有解决《中美经贸协议》导致的问题。无论是《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通用名称判定指南(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界定的适用前提,还是《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具体程序,都明确且直白地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原因引入了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中,没有对其风险从任何方面加以规避。如此一来,前文所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水平降低、地理标志资源流失的恶果便都会显露无遗。
所幸与同样源自《中美经贸协议》,却木已成舟、饱受诟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不同,[54]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为了满足《中美经贸协议》的要求,基本上原文引入了《中美经贸协议》的第1.5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32条。该条后因证明责任分配不明、证明标准难以确定而饱受学界诟病,学者多认为其不利于我国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典型意见参见崔国斌:《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32页。《中美经贸协议》提出的“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之要求尚且停留在上述两部规章的征求意见阶段,并未被正式立法所固化。[55]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0年10月24日,就《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通用名称判定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0年5月9日。到目前为止,这两部部门规章尚未正式通过。尽管在程序层面仍有补救空间,但若不尽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及时纠偏,我国为履行《中美经贸协议》确定的义务而发布上述规章(或以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规则)恐怕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三)通过法律解释解决问题的困难
允许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是《中美经贸协议》的有意要求。与其说其为体现“法律体系上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的法律漏洞,[56]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不如说其为法政策错误。法政策错误一般而言无法通过法律解释解决,而只能诉诸立法。[5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2页。我国部分学者已经尝试通过重新理解通用名称判定的标准、引入客观关联性等解释性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1. “引入客观关联性”的解决方式
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引入客观关联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其主张在《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通用名称判定指南(征求意见稿)》确定的通用名称认定标准中引入“关联性”(实际上就是客观关联性)要素,认为: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则地理标志则不应当被认定为通用名称。[58]参见宋昕哲:《地理标志保护中通用名称认定的独立标准》,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7期,第70页。
这一模式意图通过在通用名称的判断中引入难以磨灭的客观关联性要素,降低地理标志被认定为通用名称的可能性,进而解决地理标志产品易于因通用名称被撤销的问题。本文认为,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2. 引入客观关联性导致的问题
首先,“引入客观关联性”本身可操作性即存疑。要判断客观关联性是否存在,至少要确定地理标志可能覆盖的生产者,进而判断这些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是否丧失客观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是两套性质不同的并行制度,这就导致其覆盖的生产者范围可能会有出入。这种情况下,生产者范围是很难确定的。同时,地理标志商标无需采用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而仅需采用“有地理含义的名称”(如“鲁锦”),这更是使得生产者范围的确定难上加难。
其次,对地理标志产品,引入客观关联性判断会导致体系上的混乱。与前述学者持相同意见者援引“第戎芥末”[59]第戎芥末原指产于法国第戎的芥末,旧时的第戎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适合芥末的生长,使得第戎的芥菜籽味道辛辣浓郁。之后当地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而第戎芥末的原材料开始来源于本地之外的地区,最终被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原料所取代。由于产业结构导致的生产环境的变化,以及芥末酱产业的不断发展,第戎芥末逐渐失去了产品与产地之间的质量联系。最终,第戎芥末演变成为了通用名称。参见法国旅游发展署:《为什么“第戎芥末酱”不能叫“勃艮第芥末酱”?》,载搜狐网2016年12月6日,https://www.sohu.com/a/120805093_171728。的例子,认为若客观关联性断裂,主观关联性也会受到影响,故可以将客观关联性判断引入通用名称判断的考量因素。[60]参见张晓晴:《地理标志通用名称的认定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6页。在“第戎芥末”案中,固然这一名称最后演变为了通用名称,最后也被撤销保护,但是实际上,其被撤销并非是因为其变成了通用名称,而是因为其丧失了客观关联性。上述观点实际上还是没有认识到通用名称和客观关联性分属主客观两个范畴,弄混了因果关系。从本例中不难看出,若客观关联性丧失,自然可以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但此和通用名称并无关系。[61]参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10条、第23条。换言之,允许以“掺入客观关联性的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只不过是在本来就可以进行的“因客观关联性丧失而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之上加了一个不稳定的“通用名称”变量而已。对地理标志产品而言,此举不仅不会起到实质性作用,反而会徒增体系的混乱。
再次,对地理标志商标,引入客观关联性判断会导致不合理的过度保护。如前所述,地理标志通用化实际上是语词的通用化,这导致了通用名称判定的一体性。并不存在“在地理标志商标语境下通用化而在地理标志产品语境下未通用化”或“在地理标志产品语境下通用化而在地理标志商标语境下未通用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若要在通用名称判断中引入客观关联性,就无法区分判断情景,只能在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两个制度中一并引入。[62]实际上该学者在论述中,也并没有区分地理标志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语境。参见宋昕哲:《地理标志保护中通用名称认定的独立标准》,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7期,第69-70页。然而,由于产品和产地的客观造就关系很难会发生断裂,客观关联性是极为牢固的。若将客观关联性一并引入地理标志商标制度的通用名称的判断中,会导致尽管部分地理标志已经丧失标示地理来源功能,但是因为其客观关联性仍然存在,导致地理标志商标无法被撤销的情况。如前所述,若地理标志变成通用名称之后还给予其商标保护,会导致其他地区的生产者无法使用这一通用名称,产生通用名称语汇的垄断,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者并不公平。这显然是保护过度了。
最后,引入客观关联性判断有违反《中美经贸协议》的风险。《中美经贸协议》不但要求将通用名称作为撤销地理标志的原因,同时要求地理标志“可能因此被撤销”,换言之,是要求被撤销的切实可操作性。若引入客观关联性判断,因为客观关联性难以磨灭的特性,地理标志实际上是难以被认定为通用名称的,故而很难“因此被撤销”。这显然会产生违反《中美经贸协议》的风险。
总而言之,地理标志产品与通用名称判断间鸿沟之广之深,难以被法律解释轻易填平。强行以解释的手法在通用名称判断中引入客观关联性要素,反而会产生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混乱、地理标志商标的过度保护、违反《中美经贸协议》等问题。
(四)纠偏之道:诉诸立法,从根源消除不利影响
一如前述,若选择接纳《中美经贸协议》1.16条,并以解释性的方法加以缓和,不但可行性存疑,还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故本文的观点十分简单:《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是典型的法政策错误,无法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仅可以诉诸立法。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其不良影响,就需要直接对《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和相关条款作删除处理。在国际法层面,《中美经贸协议》的第8.2条预留了双方合意修订协议的空间,美国亦有积极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意向。[63]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1年提交给国会的《2021年就中国WTO遵守情况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希望在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中处理的多项问题,可以推断,美国亦有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意向。Se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21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2021:20-64.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2021USTR%20ReportCongressChinaWTO.pdf.无论是在现有《中美经贸协议》中作出修改,删除第1.16条的错误内容,还是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另立协议进行纠偏,均为可取的选择。在国内法层面,本文认为所有《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影响下的条款——无论是《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通用名称判定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第6条,还是《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7条第2项——在正式发布时亦均应作删除处理。
相较于较为缓和的解释性方法,直接对条款作删除处理的立法性方法难免有过于激进之嫌,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站在我国的角度,本文已经充分论证“允许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有害无利,应予纠正。上述两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亦属我国国内立法,修改上并不存在困难。唯需注意的是,问题根源《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的修改需要中美双方同意,若对“允许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之纠偏会过分损害美方利益、阻碍美方欲求的市场准入,想必美方亦不会同意对《中美经贸协议》进行修改或在第二阶段谈判中作出让步,此时立法性方法的可行性即会受到质疑。
事实上,地理标志保护对市场准入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而是要视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而定。以欧盟为例,《欧盟地理标志条例》确定了地理标志保护的极高水平,专门法体系下注册后的地理标志可以排除对地理标志语词、标志本身的任何使用、模仿和淡化。即使原产地外的商品明确标明其真正产地,并采用“……类”“……风格”等方式说明,亦不可使用地理标志的语词。[64]See Article 13 (1) of Regulation 1151/2012.可见,在欧盟体系下若给沦为通用名称的地理标志以专门法保护,显然会造成语词的垄断,影响他国产品的市场准入。相较而言,我国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仅仅排除来源地外生产的产品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并不排除对地理标志语词本身的使用,更谈不上对模仿、淡化行为的排除。[65]《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21条:各地质检机构依法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保护。对于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的;或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可监督、举报。可见,在我国无论地理标志是否沦为通用名称,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均不会对他国的产品准入产生影响。换言之,在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水平之下,即使对沦为通用名称的地理标志施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亦不会损害美国的市场准入。明确这一点后,就可得出以立法方式纠正“允许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法政策错误并不会导致美方利益过分受损,应当不会遭到太大诘难的结论。删除《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及国内立法的相关条款的解决方式并不存在可行性上的问题。
结 语
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保护地理标志的必要性十分明显。《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要求“健全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互协调的统一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在《中美经贸协议》中规定并被《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等文件落实的“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制度,无疑会成为我国健全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掣肘。为我国地理标志产业的长远发展考虑,立法者有必要正视地理标志商标模式和地理标志产品模式的本质差别,以立法方式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对《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及其不良影响进行纠偏,努力改变“以通用名称撤销地理标志产品”的模式。
通用名称问题本质上是国家利益的博弈。[66]See Tim Josling, The War on Terroi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a Transatlantic Trade Conflict, 57 Jo 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 p.339.以欧盟为代表的旧世界国家地理标志资源丰富,地理标志保护水平较高,因此成为反对地理标志通用化的主要力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国家农业集约化、机械化发展,地理标志资源有限,因此更加主张以通用名称降低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寻求更广泛的市场准入。[67]参见王笑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新世界国家与旧世界国家的“战场”不可避免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68]See WANG Xiaoyan & SONG Xinzhe, Terroir and Trade War: Reforming China’s Legislation on Gene ric Ter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U and US, 5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66(2022).《中美经贸协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的签订即为明证。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面对新世界国家与商标法体系、旧世界国家与专门法体系的“双面夹击”,同时自身亦少有悠久的地理标志保护传统与成熟的地理标志立法范式,因此面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时常常忽视本国现状与国际差别,对双边、多边协议全盘原样继受,这显然带来了诸多问题。[69]已经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对《中美经贸协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的混合继受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调和。See WANG Xiaoyan & SONG Xinzhe, Terroir and Trade War: Reforming China’s Legislation on Generic Ter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U and US, 56 Journal of World Tra de, 165(2022).《中美经贸协议》第1.16条及我国对其原样继受带来的问题提醒我们,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在地理标志国际条约的订立、加入还是接纳、继受过程中,都要充分考虑其与本国产业现状与法律体系的契合性。以无条件继受和原样引入的粗放做法径取他山之石,恐怕不但不能攻玉,还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