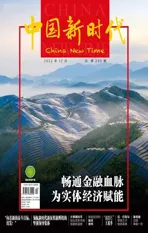你有多久没写信了?
2022-12-15苏楠
|文·苏楠
见字如面、见信如晤,你有多久没写信了?
鸿雁传情,云中寄锦书,这是最古老的交流方式。
往日,每逢年节总忘不了给远朋近亲写上几句话,以书信或贺卡寄托思念,送去祝福,同时也期盼着收获几多温馨的寄语。近些年,书信、贺卡等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替代它们的是短信、电子邮件和微信,很多还是千篇一律的格式化之作。不知不觉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快餐化、从众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少了一点曾经的那种“人情味”。
从前车马慢,书信远,鸿雁尺素寄深情。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书信一直是连接彼此、表达情感的最美形式之一;现如今,通信科技信息发达,沟通不再是障碍,写信、收信、读信这种最朴素的情感纽带和交流形式,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见字如面、见信如晤,你有多久没写信了?

用书信打开历史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在中国古代又称为尺素、尺牍、尺翰、书牍、双鲤、鸿雁、函、札、笺,由此又衍生出玉函、瑶函、书札、手札、彩笺等等。
书信在我国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书”和“信”是有区别的。“书”指信件,是最古老的称谓,从春秋一直沿用到今天。“信”,则指送信的人,而并非信件信函的意思。
在我国,书信起源于商代。殷墟出土的第513 片甲骨,就是一封由殷的边境传至京都的“边报”。考古学家吴汝浩和潘悠两位先生在考证后断言,这是“侯伯和大将军报告方国入侵的”。可见,从殷商时代起,我国就开始以文字的形式来传递军事信息。
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先秦两汉人写信,形式比较随便,且多为官方的政务公文传递,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写道:“凡书于牍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没有个人情怀的吐诉,只是些“陈政务以进君主”的陈词滥调。
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就是各类书信的格式,以供他人写信时套用。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月仪》。
书信在明代达到了鼎盛。明代进入封建社会晚期,思想文化日趋活跃,社会各阶层交流广泛而频繁,遂产生了大量的信函书牍,这些信函书牍,既有关照时局政务、针砭世相百态的淋漓之笔,又有言说文化、论说艺事、状摹自然、抒发心绪的性灵之作,所触及的对象极为宏富,所涉猎的内容非常广博,特别是文学家兼史学家王世贞、戏曲家兼书画家屠隆、散文家归有光、史学家兼心学家李贽、诗人兼散文家袁宏道、文学家兼书画家陈继儒、书画家兼文学家徐渭、文学家兼戏曲家汤显祖等人,都是文风殊绝、各擅其长的尺牍大家。
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一些艺术家和政治家力倡家训家风,家书文化日渐兴盛起来,流传至今且影响甚巨的当属《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等,在这些家书中,表达的家训家诫已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引发其他社会成员的共鸣与思考,并从中受益。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书信出现,进一步促进了书信大众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近代中国书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发展历程。随着有线电话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书信这种曾经异地沟通的唯一方式逐渐被冷落。
在交通不发达、通信不方便的时期,无数的思念、关心和嘱咐都诉诸笔端,纸短情长,缱绻情思,遥深寄托。一封封书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收信人手中,被拆封、阅读和珍藏。一封书信,一段历史,书信背后,沧海桑田,风云舒卷,离合悲欢,上演了多少动人的故事,蕴含了多少历史的信息。通过书信上的文字,我们能够走近古人,而他们的声音穿越了时光,仿佛就在我们耳边,他们的牵挂也与我们无异。
用书信传递文化
近两年,电视、互联网上各种书信诵读类专题节目像一股清流直指人心、温暖人心。没有华丽的布景、吸睛的互动,一人一舞台,观众静坐聆听朗读书信,深深感悟沉醉其中,这就是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带给观众的视听感受。
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见字如面》,首季就出人意料地火爆网络。以书信为主角,把一封封与现代人已渐行渐远的书信,化作声音再现与背景解读,让传统书信重回人们的视野,燃起人们对历史的重温和对未来的寄托。之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信·中国》、北京卫视播出的《念念不忘》等,都是借助珍贵书信进入时空隧道,使观众透过信件主人的视角,感受信中鲜活的时代场景、人情世故、社会风情,呈现不同时代的悲欢离合,引导观众不忘历史、温故知新。
书信类节目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叠后产生的聚光。既有节目制作者为了确保内容品质在主题设定、场景搭建层面的用心与匠心,也离不开明星和嘉宾的演绎及其光环效应;既有对观众日益提高的文化审美的肯定与满足,也有融媒体时代对于碎片化信息的深度整合。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书信作为信息或精神载体,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文化意义。
书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作为最主要的人际交流方式和载体,千百年来已成为家人、亲友之间相互传递情感信息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汉代之后,在边疆布防的军士常年无法回家,书信承担着重要的情感沟通作用。
《见字如面》第一期书信朗读的内容,选择了2000 多年前秦军将士黑夫写给家中兄长的木牍家书。将这封家书安排在《见字如面》第一期播出,代表了传统家书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远的历史寓意。这封信的朗读者是林更新,在他的朗读中,我们仿佛穿越了时光长河,来到2000 多年前的秦国,在战事间隙,黑夫提笔在木条上向家中大哥描述战事,同时袒露出对家中亲人的牵挂,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这封家书言辞质朴感人,虽然历经2000 多年,所有的一切都已化为尘埃,但历史的记忆在竹简书信中得以保存,使这段久远的历史在书信阅读中鲜活重现,战士心中对亲人的牵挂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衰减,初心依旧,这份温暖与关爱令人感动。
书信记载着个人成长情感历程、家庭的悲欢离合,从中折射出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态。从微观角度来看,书信记录了个人生活,是展现个人思想发展的原始记录;从宏观角度来看,书信蕴含着人伦亲情和道德。
在中国文化中,家书是非常重要的书信形式。长辈通过一封封家书,把人生体验、道德修养传授给后代,更类似于论述家庭教育、家庭规范的家训。而一些优秀的家书,本身就饱含了人生的全面经验。比如曾国藩在其1500 多封家书中,既有过日子的窍门,更有治国理念,是他人生追求、政治理念、军事战略及行为处事的完整体现;《傅雷家书》则更接近于一部文学作品,完整展现了新时代人们对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注重与追求。
不仅如此,书信还是书法、文学、艺术的综合文化载体,具有超越信息传递的种种文化功能。很多书信不仅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文献价值、手迹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比如中国现存最早的传世墨迹作品《平复帖》,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的尺牍,以及苏轼的《致运句太傅尺牍》等,都是中国古代书信留下来的名品。孙过庭在《书谱》中有言:“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书信中的书法,一般收信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保留书信。
传统书信记载了历史,也为历史所记忆。如《诫子书》《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板桥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内容涉及文史哲各个方面,是国学的重要体现。
随着书信本身的发展,除了寄托思念的家书之外,也涌现了许多文人赠答、互诉理想的书信。为了满足文人趣味,这些书信所使用的纸张和信封种类也大大丰富起来,比如之前使用的是动物形状(鱼、雁)的木盒充当信封,魏晋以后开始使用纸质信封。信纸也称笺纸,形式就更多样了,晚明时还有《十竹斋笺谱》这样记录笺纸种类的作品,许多笺纸上印制着精美的图案,大多以山水花鸟为主,即使是在室内读一封信,也能感受天地万物环绕左右。
在如今这个快速通信的时代,人们只需敲打几下键盘,便可在霎时间把信息传到任何地方,古人梦寐以求的“天涯若比邻”从此成为现实,尽管现代通信网的高速传送信息功能极大地挤压了传统书信的生存空间,但它根本无法包容传统书信的丰富内涵,展现不了那植根于书信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
用书信重拾慢生活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短信、微信等信息媒体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信息传递快捷、高效的需求,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天涯若比邻”。这是人类信息传播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电子信函取代大部分书信实体是历史的必然。

但也许是由于过于快速和便捷,人们对于信息的内涵反而忽略了,对于传递信息的技巧反而更随意了,远远不如古人看到手书“见字如面”时,那么郑重其事,那么认真细致。在互联网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传统书信所承载的思想力量悠长韵味正在消失。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只看到书信的信息传递功能,却很少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看来,“书信文化在没落,但不会消亡……因为它能激发起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
其实,在信息时代,书信最重要的作用不再是传递消息,而是情感的承载与文化的传承。曾经“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书信的意义没有衰减。纸张与笔迹将时光定格,成为独家记忆;情感经岁月洗礼,得到更好的升华,历久弥新。
平时人们习惯了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当你铺开纸,拿起笔,静静地伏案写家书时,亲人的音容笑貌和平淡的往事总会历历在目,不断激荡着自己的内心。
可以设想一下,每值年节,在贺年的短信、微信如潮涌来的时候,你是否也期待着收到一两封夹带着墨香,由寄件人亲笔写来的贺信,或若干枚由寄件人精心制作的贺卡呢?这时,你定不会去计较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多久,而更看重蕴含在其中的深情。
基于本身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和文化内涵,书信不应消亡在新时代的洪流中,书信文化也不应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老去,我们应该欣赏与传承这份积淀千年的文化。所以不妨重新拿起手中的笔,为远方的亲人和朋友写封书信,叙些人间冷暖,道些此处情长。那最本色的文字,或许会给思念的人带去惊喜,让他从字里行间回忆起往昔,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