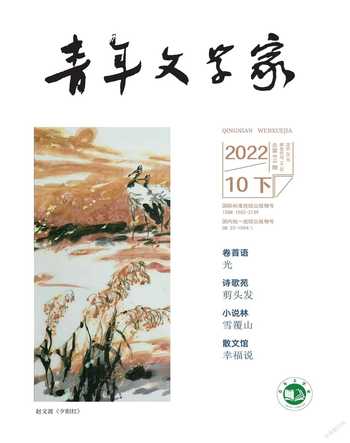论叙事交流中作者的编码过程
2022-12-14梁鑫顾恬瑞
梁鑫 顾恬瑞


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中首次提出了叙事交流模式,指出了叙事交流中的六个主體,其中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的交流是文本外的交流,而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属于文本内的交流。西摩查特曼将研究重心放在文本内的交流,并指出在叙事交流中被交流的是故事,而故事是通过话语来交流的。
但通过考察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发现,叙事交流并不只在文本内发生,它在作者创作伊始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本文将试从作者的创作过程作为切入点,结合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美学来重新探讨该叙事交流模式,并重新阐释该模式中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间的互动关系,以此完善叙事交流理论体系。
一、故事层的交流现象—自我交流
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审美关系出发来探讨,作者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小说文本是作者基于审美体验创造出来的,是在作者与审美对象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而审美关系不是单方面一方决定另一方,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流关系。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总是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参与者,他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并且两者各自独立。由此,巴赫金提出了审美活动中的超视说和外位说。“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者,需要他者的观照,记忆与集中整合的功能性。”(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种审美活动的外位性催生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即审美活动就是主体对一个外位于自身的他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活动。巴赫金将审美的对话原则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提出了复调理论。他认为人与人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充满了对话性,人的意识、思想无不带有这种相关而又独立的特征。
笔者认为,这种对话交流的原则可以适用于小说作者的创作过程之中,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从对话原则来看,文本中的一些基础核心成分是预先就存在的而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这些被埋没在文本之中的成分笔者称之为文本的初始成分,是这些文本的初始成分召唤了作者,使作者对这些文本的初始成分进行创作加工从而创造出文本来。而这个加工和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话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这些文本的初始成分等同于作者创作过程中某些一闪而过的灵感,这些成分最先成了作者的审美对象,作者将其观照成为审美对象的那一刻,创作才算真正开始,这些初始成分可以是某个人物形象的片段或者某一段故事情节,这些零星片段唤起了作者的创作兴趣,将作者召唤出来。而作者对这些初始成分进行观照,和这些外位于自身的成分进行对话和交流,通过调动自身各种心理机制对这些成分进行加工,如想象、体验和反思。
另外,作者的加工和创作都必须基于这外位于自身的成分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如巴赫金所说,“作者要受到被选者内在逻辑的制约,自我意识的逻辑只允许自己特定的各种揭示和描写的艺术手法,只有提问与激发而不是把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形象强加于它,才能揭示它”(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创作过程中的交流实际上是为了激发审美对象,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运用想象等诸多心理机制激发被作者观照的初始成分,让这些初始成分涌现出自身的规律性。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的交流,这些初始成分虽然外位于自身,但它们依旧是作者自我创造出来的。“如歌德曾谈过他的创作经验,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极喜欢在内心中交流的作家,有时候即使是个人独自思索也要化作交谈的对话。就是在脑海中把所认识的某个人邀请来然后跟他交换关于自己刚刚想起来的问题和意见。”(谭君强《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从歌德的创作经验来看,其实作者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自我交流的过程,那些被他邀请进入脑海中的人物都是他依据现实经验创造出来的。但这些人物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和逻辑,歌德对这些人物提问和激发实际上是自我的交流,也是一种审美体验。
综上所述,叙事交流显然已经不仅仅存在西摩查特曼所说的话语层的叙事交流,叙事交流已经融进了故事层面,即便是故事层面也有着充分的交流,而不是西摩查特曼所描述的交流只存在于话语层中。西摩查特曼将叙事文本的故事层分为事件和实存,而作为实存的人物并不产生交流效应。但是,在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彼此之间的交流。同时,人物因为具有自身的意识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人物声音是直接向读者呈现的。所以,在文本中交流是无处不在的,并不受到“故事-话语”二分法所局限。另外,主题也可以成为文本的初始成分进入作者的创作过程中和作者进行交流。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主题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这种探询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主题词进行审视。如重和轻,灵魂和身体。”(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提到他首先想象这些关键词的具体体验,但这种体验是放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并结合具体的情境中进行考察的,例如他在书中提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女主人对眩晕的定义,是他从女主角的立场和位置出发,思考她的态度和看待事物的方式。这种探询式、假设式的创作其实就是作者在和他观照的对象进行交流和对话。
巴赫金、歌德和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创作体验都是一种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故事层面中,和这种交流相对应的是作者创作中的虚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建构出文本的故事层,如故事中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的情节和主题等,若以西摩查特曼所划分的叙事层面来看,故事层中的事件和实存都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被完成。作者创作中的虚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交流的过程,在文本中体现为故事层。在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模式中,隐含作者是处在话语层的,但笔者认为,隐含作者同样存在于故事层,隐含作者在作者进行自我交流的过程中就已经在不断显现了。这个隐含作者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故事层的思想主题,在作者的虚构过程中作者的创作意图逐渐形成。
二、话语层的交流—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
作者在虚构过程中完成了隐含作者的构建,心中已经有了完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但这一切都还只是作者的“胸中之竹”,而如何将心中的审美意象表达出来则涉及作者创作叙事文本的表达过程。这个过程作者不再是进行自我的交流,而是建立起了一个表达对象,即故事的接受者,这个受话者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隐含读者,首先隐含读者同样是一个外位于作者自我的存在,因为只有外位于自身才能与之产生交流关系。关于隐含读者最早是由接受美学中的伊瑟尔提出来的。他认为隐含读者是作者理想的听者,是隐含作者自言自语的聆听者。申丹曾这样描述隐含读者,“所谓隐含读者就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读者,是文本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一致,完全能理解作品的理想化的阅读位置”(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笔者认为,申丹对隐含读者的定义具有片面性,她将隐含读者完全归入文本之中,认为是文本预设出来的,同时申丹的隐含读者是和隐含作者是完全一致的。而笔者认为,隐含读者不仅仅应该放在文本之中考察,同时也应该放在作者的表达过程中考察。而且,隐含读者并非和隐含作者完全一致的,如果完全一致那么没必要区分出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首先隐含读者必须外位于隐含作者,只有这样隐含作者才能和隐含读者产生交流。
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发生在作者的表达过程之中。首先笔者回到隐含读者最初的定义上来,接受美学承认隐含读者是作者理想中的读者,但接受美学也指出了隐含读者是艺术家凭借经验或者爱好,进行构想和预先设定的某种品格。从这个定义出发,隐含读者成了一个具有人格化的存在,而且是外在于隐含作者的存在,隐含作者要想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隐含读者就必须理解隐含读者,只有对外位于自身的隐含读者有所理解才能确保自己表达出来的声音被隐含读者理解到。例如,作者在想表达眼前这片蔚蓝天空的蓝时,他可以直接用一个概念“蓝”来表述出来,但当他这样表述“天空像大海一样蓝”时作者其实就建立起了一个隐藏的对话者,这个对话者就是隐含读者,这个隐含读者必须具备某些人格或者经验,如它必须了解大海是什么样子才能理解作者的这个表述。所以,作者在作出这样表述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隐含读者。这个隐含读者首先是外位于自己的,即它并不知道作者看到的天空是如何的蓝,如果隐含读者知道,那么作者也没必要作出解释,只有基于隐含读者外位于自己的这个情况,作者才能做下一步的工作,即预设了隐含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具有某种人格特性或者某种经验。而这个作者预设出来的隐含读者决定了作者在文本中的表述,也决定了作者在表达过程中的交流。
作者的表达过程就是预设一个又一个隐含读者并与它们进行交流,最后这些预设出来的隐含讀者整合起来成为文本一个统一的隐含读者形象,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隐含读者决定了文本表述的表达形式,而表述的意图则是由隐含作者所决定。由此可得,文本中一切修辞手段如隐喻、反讽、夸张等都是作者在表达过程中的策略,这些表达形式都是由作者预设的隐含读者所决定的,读者可以通过一个隐喻或者一个反讽来推测出作者预设的隐含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也能通过故事的叙述者或者视角来推测出作者在表达过程中预设的隐含读者是怎样的存在,比如书信体的第一人称小说就是作者在表达过程中预设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亲密朋友。隐含读者决定了作者在表达过程中所使用的叙述手法和修辞手法,决定了作者采用哪一种视角、哪一种修辞。同时,隐含读者也是对应隐含作者而存在的。隐含读者作为讲述故事的对象,它直接面对的是作者的意图也就是隐含作者。文本中的一个表述由它的表述形式和表达意图共同构成,隐含作者就是一个表述的表达意图。所以,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
因为隐含读者所关涉的是如何表达的问题,所以它主要是存在文本中的话语层。作者在表达过程中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或者叙述手段试图让隐含读者认同作者的创作意图即隐含作者,这种创作意图在文本中体现为作品的思想规范,而该思想规范存在故事层上。由此可以看到,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在作者与文本的交流中的位置,隐含作者主要存在作者的虚构过程即自我交流的过程,而隐含读者主要存在作者的表达过程,这个过程是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交流过程。这两个交流过程体现在文本中时分别是文本的故事层和话语层。作者的自我交流在故事层中完成,在自我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隐含作者,而在作者的表达过程中,作者预设了一个更外位于自身的隐含读者并使之与隐含作者进行交流,两者的交流体现在话语层中,两者交流的结果是文本的具体表述。也正是如此,文本中的每一个表述必然指涉着一个隐含读者,同时也包含了一个隐含作者。故事层的隐含作者和话语层的隐含读者在文本中重叠起来。故事层与话语层在文本中也是一种重叠状态。
综上所述,笔者将作者和文本之间交流关系划分为作者的虚构过程和表达过程,前者是作者自我的对话交流,后者是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修辞交流,两者在文本中分别体现为故事层和话语层。同时,笔者认为隐含作者既存在于话语层又存在于文本的故事层。以上是从作者和文本的交流出发作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