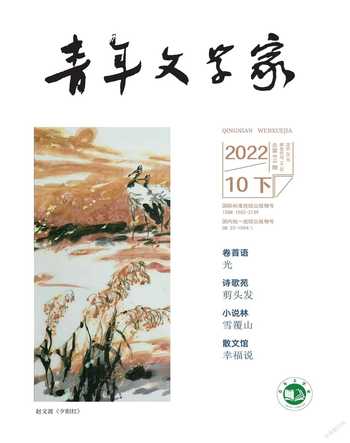从“美刺”角度看《寒食》之主题
2022-12-14高雷
高雷
一、《寒食》主题研究之梳理
唐代诗人韩翃所作《寒食》一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此诗因“与此韩翃”四字而被广为传颂。在对韩翃诗作的众多研究中,该诗高居榜首,其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以该诗为例,进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第二,对该诗的主题研究。对该诗的主题研究历来众说纷纭,颇有争议。
(一)讽刺说
学界的大部分人认为此诗为一首讽刺诗,只是对具体的“五侯”存有分歧。例如,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认为“五侯”指的是外戚杨国忠兄妹:“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杨氏擅宠,国忠、铦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能之比,故借汉王氏五侯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馀锡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今人李建华在《韩翃〈寒食〉诗新解》中认为“五侯”指藩镇称王之人:“唐德宗继位初,河北、淮西等藩镇发动叛乱,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李希烈等相继称王,史称‘五王二帝之乱……建中四年,德宗被困奉天,差点破家灭国……德宗猜忌、痛恨藩镇……却又不得不姑息他们,给予其优厚待遇及特权。”
韩翃所讽正是德宗所恨,此诗正好说了德宗想说又不好明说的心事。这一看法,更符合德宗看了此诗而赐予他“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显职的历史事实。
但是,上述对“五侯”的观点都是基于一个前提:该诗的大致写作时间。而实际上,在现存史实资料中,我们并不能知晓其具体创作时间。因此,有持中的观点认为“五侯”为不可考的,因写作年代不同,作品所讽刺对象亦会有差异。例如,沈祖棻认为《寒食》“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不可考。如果是天宝年间的作品,则应是讽刺杨国忠兄妹的,如果是安史之乱以后所写,则很可能诗讽刺深刻而表现含蓄”。所以,笔者认为此诗是一首讽刺诗其理由依旧不甚充分。
(二)颂诗说
罗时进在《〈寒食即事〉诗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中认为:“韩翃《寒食即事》是一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皇权声威,呈现着生动的中和气象的风俗诗,作者道德创作意图显然并在‘托讽。时人对这首诗的欣赏既反映了中唐文人士大夫中和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其以中和为出发点的审美情趣。”此种看法乃是从此诗中所涉及的民俗风情入手,罗时进认为此诗具有丰富的文化韵味所选取之景亦充满华美与热闹,因而此诗所呈现的是一幅具有中和气象的盛世之景。
(三)諷谏说
李定光在《韩翃〈寒食〉诗正解》一文中提出了“讽谏说”:“全诗的妙处在于,作者着眼于皇宫,客观地描绘出两幅皇家独特地寒食图:白天清丽的飞絮图、傍晚祥瑞的轻烟图。第一幅画象征皇恩浩荡,无处不在;第二幅画象征皇权的祥瑞与特权的荣耀,并暗示五侯家近水楼台,得沐皇恩最多……在歌颂的背后也蕴含善意得讽谏而不是讽刺,提醒皇上注意皇恩的普惠,这种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也是皇帝乐于接受的。”这种说法把诗歌的景与事融为一体亦不忘文人风旨。
这就是对于该诗的主要三种主题认识的简单梳理。在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除“颂诗说”以外,大多数学者是集中在对“五侯”的理解上来理解此诗,即认为此诗是一首讽刺诗。但是,若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理解,对德宗因此诗而嘉封韩翃是有一点儿说不过去的,而若为单纯的颂诗,也颇为牵强。其实,不加深入考察便可知此种学说是颇为牵强,作者生于719年,而开元盛世则是712年至741年,在唐玄宗的治理下可谓把大唐盛世推向了鼎盛,成长于盛世的诗人则能敏锐地感觉到自安史之乱后大唐的衰落。在笔者看来,此诗歌颂中唐气象不假,其中有蕴含讽谏也是真,此诗的讽谏可以说得上是“怨而不怒”的美刺。因此,诗写作时间不详,假定写作时间为唐德宗时期以便作解。
二、“传蜡烛”中所体现的“正名”
“名”“实”关系从先秦直至当今,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现今还在讲做事要“名正言顺”。“名”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句话揭示了孔子对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孔子看来每个名都有它的意义,代表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名的意义,就是周礼所规定的那些条条框框。照他看来,应该用这些条条框框来纠正当时不合乎这些条条框框的事。这就叫正名。《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事实上为君的人的行为要合乎“君”这个名,为人臣子的人的行为要符合“臣”这个名,而为人父、为人子的人的行为也都要符合“父”“子”的名。
《寒食》一诗中主要写的是“传蜡烛”一事。传蜡烛实际上是寒食节的习俗之一,即“赐新火”。“赐新火”与“禁火”“取火”是寒食节的主要习俗。据唐人韩鄂在《岁华记丽》中记载:“禁火之辰,游春之月,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当三月之初,禁其烟,周之旧制。”可见这个“禁火”习俗来源于周礼,是属于“礼”之范围。
孔子称“天下无道”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论述了天下有道与无道的区别,有道之天下礼乐、出兵征战都由天子作决定,而无道之天下则与此相反,且无道之天下是不能长久的,数年便会被推翻。可见,天下有无“道”的依据是根据有无按照“礼乐”所规定行事的。
《尹文子·大道上》中提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那么,名对于形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名为何如此重要。尹文同样也作出了解释:“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名与形之关系在此处被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在古代非常强调形名相应的,所谓名正言顺也正是此意。在《寒食》中则体现出了“事以检名”的思想,亦是间接证明了德宗时期朝堂是有“礼”的,而不是一个朝政混乱、君臣不分的时代。
“事以检名”主要就体现在“传蜡烛”即“赐新火”的习俗上。和为“礼”,简单地说,就是维护秩序的一套统治规则,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这种礼则表现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这种等级制度也是人之不对等的表现。《寒食》一诗中提到的寒食习俗,尤其是“赐新火”就是礼的表现。关于“赐”字,后世儒学亦对其“正名”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第一种,形名解。“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所写之事是寒食节传统习俗“禁火”“取火”和“赐新火”,而主要集中在对“赐新火”的描绘。“赐”字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一种由上至下的给予,其中隐含的是施予者和被施者之间的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在古代,君王给予臣民东西称之为“赏赐”,就连死亦叫“赐死”。而在寒食节“赐新火”一事,也正是对这种封建文化的“礼”的一种反映。《说文》:“赐,予也。”上给下谓赐。《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这无不体现出施予者和被施者之间的不对等的关系。这种不对等亦是君臣关系的体现。这就不是在讽刺“五侯”乱朝纲,而是对君主的“正名”,亦即朝政依旧君是君,臣是臣。
再看作者所写蜡烛之景,“轻烟”二字至少能看出此火并不十分旺盛。王濯在《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中云:“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转影连金屋,分辉丽锦茵。焰迎红蕊发,烟染绿条春。助律和风早,添炉暖氣新。谁怜一寒士,犹望照东邻。”全诗六十字,称“新火”为“华光”如“星流”,这显然是《寒食》中的“轻烟”所不可比拟的壮丽之景。并非韩翃所见之“赐新火”场面不如王濯所见,实乃其故意为之。在世人眼中,都云皇帝因专宠“五侯”(不明具体所指)而“赐新火”,但实际上“赐新火”于百官乃是中唐习俗,皇帝并非昏庸专宠而只是按照“礼”之规定赏赐百官罢了,“轻烟”二字便可看出,若是作者意在写专宠,那么“轻烟”二字所体现之“宠”又实在太薄。
三、景物描写所体现的“正名”
诗歌上面作者对寒食节亦即暮春之景的描绘颇具特色。暮春是百花凋谢之时,“春城无处不飞花”中的一个“飞”字把本应是伤感的白花凋谢之景,但作者写得甚是热闹,“无处”在空间上更是延伸了这种热闹之感。
唐德宗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至“中兴”,《旧唐书》载唐德宗自言:“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对“小康”的肯定便体现在诗中第一句所写之景当中。陈寅恪在《陈寅恪文集之六: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
第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中的“春城”暗指经过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唐王朝,“飞花”之热闹指的是唐德宗的“小康”之治。第二句“寒食东风御柳斜”则是通过景物描写对“君”之正名。“御”字在很多诗解中作名词解释,指皇宫。但在这里也可作动词解释,“御”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像持策于道中,会驾驭之意。“御”在典籍中多指驾驭车马,引申指驾驭车马的人。“御”也泛指驾驭一切。此外,由本义还引申为治理、统治之义,因帝王是离不开车马的领导者,所以扩充意义至与帝有关的事务。因此,“御”字作动词来解的话,那“寒食东风御柳斜”便有了全新的理解。“东风”在这里指君王,“柳”便是臣子。君对臣的领导统治便是“御”,这实际上也是对君王的“名实”的肯定,“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最大的体现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但只此一字“御”便体现出了“君君”“臣臣”的关系,从而明确了君臣有别,肯定了唐德宗的“君”是名实相符的。
四、“美刺”之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诗中的景物描写还是“赐新火”的叙述,我们都可以看出诗人“正名”的思想,即“君君”“臣臣”。但是若只限于此,此诗则是一首阿谀之作,实在难看出“文人风旨”。从先秦各家就看到了诗的社会作用,孔子更是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这里“怨”被孔安国解释为“怨刺上政”,可见,诗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刺”。但是,儒家又是讲求温柔敦厚、中和的,故即便是“刺”也是“怨而不怒”。到了汉代,汉儒更是把“刺”发展成了“美刺”,《毛诗序》在解说“六义”的时候提出了“美刺”的概念:“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颂,是比拟和赞美盛大之德的容貌,以人间万物群生的各得其所来虔敬地告诉神明。韩翃在诗中主要是通过“赐新火”以及通过一系列景物描写来突出圣德。《毛诗序》中又继续解释何为“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国君用风诗教化民众,民众用风诗谏劝国君,用富于文采的诗隐约地劝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应引起足够的警惕,这就是“刺”。“美刺”实际上就是一种委婉的劝谏,让“上”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是一种劝谏的艺术。
在《寒食》一诗中,“刺”的部分主要就体现在“斜”字上。如前文所述,我们把“御”作动词解,这样“御”便是君王对臣下的统治,“东风”即指君王,而“柳”就是臣子,“柳”的特征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斜”字便刻画得淋漓尽致,“斜”即“不正”,“不正”则“不合礼”。若是这样去看“寒食东风御柳斜”,就是君王的御臣之道使得臣子有些“不正”,也就是恃宠而骄。但在这里对宠信臣子所带来的后果是建立在对朝政依旧是“君君”“臣臣”的肯定之上的。
此诗作为一篇“美刺”之作,在对君王的圣德作出称颂之时亦不忘在其中隐晦地加入委婉的劝谏,故韩翃方能因此诗而被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