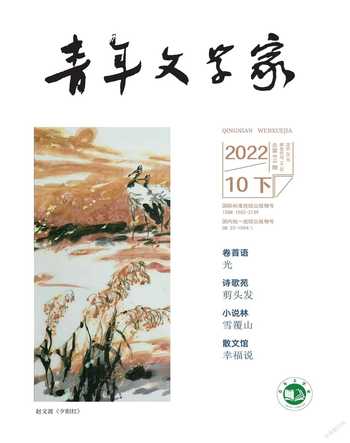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叙事特征
2022-12-14段海艳
段海艳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因对叙事形式的专注而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英美文学史上“礁石般鼎立的文学大师”。福克纳的小说具有显著的意识流特征,他的作品因复杂的结构形式和多重叙事视角的叠加而犹如一个景致丰富的“万花筒”,具有超凡脱俗的叙事魅力。
一、多元复杂的结构形式
威廉·福克納对小说技法的革新决定了其拒绝以传统叙事平铺直叙的方式结构小说,他对小说外部形式的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其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上。他着意在不同的篇目中实践不同的小说结构形式,使其小说结构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叙事特征。
弗兰克的空间叙事理论揭示了具有不同面的小说情节可以“并置性”地放置在文本中,只要它们统摄在共同的主题下,便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福克纳在《喧哗与躁动》中便进行了这种空间形式的叙事实验,使小说呈现出了橘瓣式的叙事结构。小说以不同的叙事主体为依据,分为四个叙事单元,讲述了不同叙事者的生活经验及其带来的心理体验,然而他们看似迥异的讲述都共同指向了康普生家族的发展历史,因涉及公共的话题而有了统一的叙事指向。第一部分班吉的叙述是极为模糊的,完全以其意识流动为导向引领读者了解这个家族的历史。通过班吉的讲述,我们得以知晓康普生家族衰落的现状以及凯蒂的离去,并对其原因产生好奇。第二部分昆丁的叙述为我们揭开了康普生家族没落的原因,不仅袒露了家族内部的各种分歧,还提示了外部社会环境的移置。读者也能够从其对凯蒂的追忆中逐渐拼凑出凯蒂远走的动因,在满足了对家族往事的探秘心理后,产生对康普生家族未来的好奇。于是,在第三部分福克纳以杰生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其振兴康普生家族的经历,以及家族下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以接续性的叙述使家族故事具有完整的发展脉络。第四部分的叙事者迪尔西则从“旁观者”更为全知、客观的角度讲述了康普生家族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前几部分叙事情节的补充。四个叙事单元各自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任何叙事单元都是不完整的,然而它们统摄在共同的主题下,呈现出“发散且集中”的结构特征,恰如一个完整橘子的各个橘瓣,只有拼凑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叙事内容。这种结构上“发散且集中”的特征使小说充满了悬念,令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不断试图拼凑出缺失的情节,从而产生了高度的阅读期待。
而在《野棕榈》中,福克纳则形构了对位式的小说结构,让小说的各个章节发生的背景在“野棕榈”和“老人河”之间交叉着置换,形成了复调的结构特征。两个交织并行的故事在初看时并无联系,却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使读者觉察其主题层面的对比意义,引发读者深刻的反思。“野棕榈”讲述了夏洛特与维尔伯恩充满原始激情的爱情故事,他们忘情地追逐着理想化的爱情,不想以平淡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在短暂的激情退去后,他们却因未能履行应尽的责任而感到羞愧,维尔伯恩更因此失去了成为医生的机遇。与之相对的,“老人河”看似讲述了与“野棕榈”毫不相关的故事,却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理性精神的可贵。高个子的囚犯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时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拯救了怀孕女子的生命,并在严苛的条件下协助其顺利生产。在默默地完成全部善举后,高个子没有选择就此逃亡自由的世界,而是返归监狱。他以可贵的理性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以对责任的承担洗去了曾经的污点,呈现出了人格的高贵。两个故事形成了有意味的对位式结构,激情与理性、失序与正序、渎职与负责,接受者对于“理智与激情的冲突”这个命题的思索只有在对比阅读中才能更加深刻。此外,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则创造性地采用了倒置的“U”型结构展开小说叙事,以倒“U”型的曲线反映了主人公萨德本起伏跌宕的生命轨迹,使小说的结构形式与人物的命运达成完美的和谐;《八月之光》则采取了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在莉娜寻找卢卡斯的主线故事之中嵌套了花样繁多的辅线故事,使女主人公单调的寻找之旅变得丰富复杂,让小说成为展览世相、观照众生的舞台,同时也使得叙事的节奏由平铺直叙变得波澜丛生。
叙事结构的复杂令福克纳的叙事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使读者能够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获得内容之外的形式美感。同时,其小说的结构与主题之间存在内部的呼应,达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之境。
二、动态流动的心理时间
威廉·福克纳对内在心理的关注使其小说具有显著的意识流特质,人的意识流动与客观的现实时间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他认为客观物理时间的线性发展决定了时间具有当下性,而人的意识与心理却可以将过去、当下和未来统摄在同一时空中,人的时间感知取决于主体的心理体验,因而人的心理时间较之于客观的物理时间更加具有权威性。这种独特的时间观让福克纳小说中的叙事时间经常处于“失序”的状态,情节自然发展的时间状态,也即“故事时间”经常为叙事文本的时间状态,也即“叙事时间”打乱,使读者必须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不断依靠自己的判断重新整理、建立情节的发展秩序,从而获得延宕性的审美体验。
福克纳小说的叙事时间常呈现出随着主体内在心理与思维的转变而流动的特质,如《押沙龙!押沙龙!》中叙事时间的流动便呈现出显著的心理特质:“一位先生注视着舞池中舞动着的舞者,她的裙摆带起一个利落的旋转,如水的发丝弧形地倾泻在半空,于是三年前的夜晚摇曳着浮动在眼前。”叙事时间的切换完全不合乎物理时间的逻辑,仅仅依凭主人公心理的转换而由当下的叙事时间流转到过去的叙事时间,小说的叙事场景也随之而立即切换。这种变动不居的叙事时间呈现出强烈的意识流特征,往往通过感觉器官为中间媒介加以实现。而在《喧哗与躁动》中,这种心理化的叙事时间被表述得更为具象,在以班吉为主体的讲述中,叙事时间变得极为模糊,极具流动性的特征,他完全是依凭自己感官体验与情绪流动进行叙事。在接触到外部潮湿的空气后,他脑海中时而浮现出康普生家的老宅“外墙上湿漉的苔藓与室内稀薄的光线”,宅邸的年久失修揭示出康普生家族没落的处境。他时而又怀念起凯蒂身上“清新的树木的气味”,并因为无法嗅闻到这种气味而滚地哭叫,味道的消散暗示着凯蒂已经离开家族远去的现状。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完全没有遵循客观的时间秩序,而是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反复跳荡,在有限的时空中串联起了丰富的叙事内容,显示出心理化的叙事时间具有的叙事潜能。
同时,现代先锋性的叙事技法使福克纳小说中对叙事时间的表述充满了象征性,“钟表”无疑是福克纳小说中重要的时间象喻。它与现实的物理时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可以被视为传统的线性发展时间的象征。例如,《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中,南方贵族小姐艾米丽身上总是携带着一只“精巧的金色怀表”,钟表古旧精致的外部造型象征着艾米丽没落的南方贵族小姐的身份,表征着南方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而逐渐远去了。且艾米丽经常忽视钟表的存在,任由其“落入衣服的褶皱间”而不去理会。主人公对钟表的忽视象征着其对客观自然时间的隐性拒斥,艾米丽不愿认同南方社会的经济结构业已发生内部的质变,她的思想深处盘桓着对过去的深刻眷恋,因而只能以搁置钟表的形式拒绝进入现在的时空。这种时间的象征意义也揭示了福克纳对心理时间的认同,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识调节自身对时间的体验,从而挣脱时间线性发展的规律的束缚抵达自由的境地。而《喧哗与躁动》中的“钟表”也同样具有深刻的时间象征意义,主人公昆丁打碎了那只“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由父亲传下来的手表”,将“两只指针从表盘上拔下来”。然而,被损坏的钟表依旧没有停止运转,“清脆而急促的嘀嗒声”依旧从钟表的内部传来。昆丁打碎钟表的行为象征着其希望阻断物理时间流逝的心理意向,康普生家族的荣誉在日渐稀薄,而身为长子的昆丁却无力带领家族恢复往日的辉煌,只能借由打断钟表的时间指向的方式希冀延缓这个过程。但钟表依旧嘀嗒作响,揭示着昆丁在心理层面对时间的意识仍旧清晰,他内在心理时间的流动并不因失去了对物理时间的有效认知而停止,随之也就无法释怀自己内心因责任感而带来的紧张。
叙事时间的流动使福克纳的小说颠覆了传统线性时间的发展秩序,呈现出一种新的时间哲学。心理化的叙事时间带给了小说叙事以极大的自由,使小说突破了文本篇幅的限制,可以包涵丰富的叙事内容。
三、多重变幻的叙事视角
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叙事视角呈现出多重变幻的特质,他的小说往往不会从单一的角度进行故事的讲述,而是通过变幻的叙事视角敞开情节的丰富可能,以叙事视角的变幻制造多样的叙事效果。同时,福克纳常常在小说中引入特殊叙事主体的视角,以偏离常规的叙事视角制造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福克纳认为“现实具有驳杂的细节,因而从不同的角度觀瞻会呈现多义性的效果”(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因而他的小说常常采取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对现实本相加以表述。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在讲述萨德本的人生轨迹时采取了四重叙事视角叠加的叙事策略,令身份各异、立场不同的叙述者共同还原主人公萨德本的形象。罗莎小姐视角下的萨德本无疑是个“脾性暴躁且自私自利”的“外来者”,萨德本与自己的姐姐埃伦成婚却并未带给姐姐幸福,她认为萨德本只是因为想要融入小镇才缔结了这桩婚事。康普生先生视角下的萨德本却是个“理想化的进取者”形象,他赤手空拳地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辟了“百里地”的庄园,亲自和工人们一起投入劳动且从不轻易斥责他们。他机警而冷静地化解了小镇人对他的各种刁难,最终成功地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落地生根。昆丁视角下的萨德本最为复杂,因叙述者本人对南方传统“爱恨交织”的特殊情结,因而昆丁视角下的萨德本既是“父辈辉煌历史的象征”,又是缺少道德规制的“不择手段的开拓者”,具有双重的面向。而施礼夫视角下的叙事则更加具有不可靠性,因为他全然是通过他人的话语来对萨德本的形象进行推测的,其间还夹杂着他自己的虚构与再创作,这种间接性的想象建构根本无法还原人物萨德本的真实面目。叙事者通过多重视角形塑萨德本的人物形象,然而读者发现多重叙事视角并未让萨德本的形象变得清晰,反而因叙事者各自立场的矛盾而变得驳杂难辨。多重变幻的叙事视角使萨德本变成了“迷宫式”的人物,因其形象的多义性而富有艺术的魅力。
与此同时,福克纳的小说常出现特殊的叙事视角,如儿童的叙事视角等。特殊的叙事视角往往能够看到与常人不同的风景,儿童角度的叙事同成人的隐含视角构成了小说中的“复调”,在互照间带来陌生化的惊异性审美体验。例如,《清晨的追逐》中,福克纳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次清晨的猎鹿之旅,以儿童为主体的视角带有不谙世事的天真,当他们观照自然生命时总能觉察其中的诗意:“河边潮湿的雾气像棉花般柔软,堆叠在幽深的水面上,安静地好像温馨的睡床……森林在等待着太阳的出现,使它们在金色的光晕中沐浴,驱散夜晚的惺忪。”自然景物在儿童的视角下被赋予了拟人化的特质,具有成人视角下不曾得见的勃勃生机,两种视角的对照令读者获得了更细腻的感受。而当那头雄壮的公鹿出现时,猎手欧内斯特先生视角下的鹿是“寻觅已久的大家伙”,而儿童视角下的鹿则“顶着巨大的,如树杈般的棕色鹿角,阳光将它镀成了金红色,我们的喧扰弄惊了它”。成人视角下的公鹿是等待狩猎的猎物,而儿童视角下的鹿却是森林中的自然生灵,它那雄伟的外表象征着自然造化的神奇,金红色的公鹿无疑具有某种自然的灵性或神性,而只有儿童的视角才能与自然建立如此亲近的关系。
叙事视角的多重变幻使福克纳的小说突破了单一性的叙事效果,带给读者层次丰富的阅读体验。视角的切换与比照使小说叙事更具有开放性,也揭示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
福克纳在小说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令其小说具有浓厚的个人化特质,多变的结构形式和变幻的叙事视角呈现出了现代文学的先锋特质,其心理化的叙事时间更带有意识流小说的突出特征,折射出作家独特的时间哲学与对人的认知的思索。我们可以说,福克纳的小说的表现形式与思想主题达成了有机统一,在手法与内容的契合间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