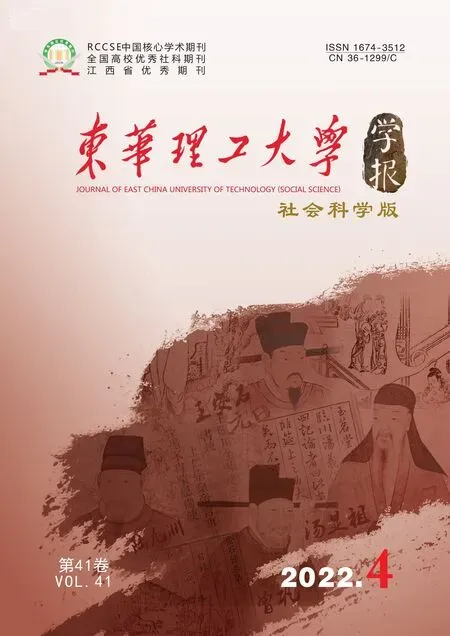新发现李健吾集外作品四篇
2022-12-13武斌斌
武斌斌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在为十一卷本《李健吾文集》撰写的编后记《父亲的才分与勤奋》中,李健吾的五位子女总结道:“尽管我们收集和选录了大量文稿,特别是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由原来的十卷扩展为十一卷,并在最后时刻因为每卷有些增补稿而改变了版面,从而给出版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我们还是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全部收录,《李健吾文集》并不是《全集》。”[1]356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一个不断发掘、不断完善的过程,即便有多方配合,也绝非一蹴而就。
1 抗日宣传剧:《从军去》
李健吾的一生与戏剧有着不解之缘。他15岁时第一次登台演出,17岁创作了第一个独幕剧《出门之前》,一直到74岁,仍笔耕不辍,创作了反映时代生活的剧本《分房子》,但他的一生究竟写了多少剧本,“他说他没有统计过,也记不清了”[2]520。对此,《李健吾文集·戏剧卷》的主编曾不无遗憾地表示道:《李健吾文集》目前收录剧作42种,但也“并非全部”“我们在两年多的搜寻过程里,发现过另一些剧本的线索,但是找不到本子。比如四十年代健吾先生改编了《啼笑因缘》和《满江红》,而且都演出过,只是剧本没有留存下来;报上披露过健吾先生写了独幕剧《中·发·白》的消息,我们也曾东查西找,但是杳如黄鹤。另外,二十年代写的剧本,是不是还有未被发现的?也有可能”[2]520。《啼笑因缘》《满江红》笔者也未曾找到,但在翻阅民国报刊的过程中,笔者新发现了李健吾1941年发表的一出独幕剧《从军去》,或可稍微弥补编者的遗珠之憾,披露如下:
从军去
李健吾
父
子
子之未婚妻
女
众男学友(戎装自外边呼唱而上)
众 (呼唱)救我祖国!救我祖国!赴汤蹈火救祖国!
父 好!好!你们这些孩子们的精神真好!
男甲 老伯,我们来辞行了。
父 你们都决心从军吗?
众 (呼唱)海可枯,石可烂,此志不可移!
父 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动过。我简直在梦里。干吧!孩子们!我快要流出眼泪来了。
次子 (向父)我随他们一同走了,爹爹!
父 走罢!走罢!忘掉我,忘掉你的爱人,忘掉你的家!
次子 谢谢爹爹一生的教养。
父 (握其手)我还要感谢你呢,好孩子!你洗雪了我一生,我一家的耻辱!(向众)你们真已视死如归,心上没有一点懊悔的意思吗?
男甲 我们有什么要懊悔的呢?平日慵懒安逸惯了,现在正是我们唯一自赎的机会了!
父 你们都是年轻人,没有尝过战场上的风味。
男乙 噢,我们想过了。老伯不用愁我们没有经验。老伯见过学生吗?第一天到校,又得意,又畏怯,又谨慎,好比新兵第一次听了大炮响,禁不住要打一个寒颤。
女 不用说了,说下去,使人丧气。
男乙 经验是从打寒颤里得来的。如果第一天我们发抖,第二天我们就会让敌人发抖的。我们扑上去,和一群小老虎一样。(向众)不是吗?
余众 真的和一群小老虎一样。
男乙 我爱听这几句话!女同志,唱!喝!和哑叭一样,你们临别不赠两句话吗?
未婚妻 希望我们再见!
男丙 一定再见的!你不来充当看护吗?
未婚妻 我很有这意思。
男丙 好拉,不愁没有见面的机会。
女 我想送你们一样东西,你们猜是什么?
男丁 是什么?不是吃的东西?
女 是一朵蔷薇!等一等,我给你们取来。(女向内驰下)
父 你们没有人预备做战场的日记吗?那是我最喜欢读的。看看你们的日记,仿佛和你们一同在战场上。
男丙 老伯这是我的事情。
男乙 没有一个字会让老伯红脸的,并且还有一种稀有的愉快:那里面常常会发现几首很好的诗呢。
男丙 我发誓不写诗了。
女 (自内持花驰上)看,看!这是我特自采来的蔷薇!秋天有这样妍丽的蔷薇,不很难得吗!(向子)哥哥,我先献给你一朵,是妹妹的,你不欢迎吗?
子 谢谢,这朵花,我当永久保存起来。
男甲 这是战地最好的纪念!
女 是吗?谢谢你的称颂。
男乙 花真红的可爱!如果枯了,只有血浇得活来!
女 真的?
男乙 不是敌人的血,就是我们的血!
女 你那么看重它吗?谢谢你!
男 来!来!唱我们的歌,唱我们的出征歌!
子 我们该走了!
男甲 唱完了走了!走,走!
众 (唱歌)
今日何日?
强敌寇疆。
嗟我祖国,
呼吸存亡!
奋起奋起!
同上战场。
不怕蹈火,
不怕赴汤!
救我祖国!
救我国光!
《从军去》发表于《兵役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此刊物创刊于1939年4月,是军事类刊物。程泽润写的发刊词里指出此刊的创刊宗旨为:“检讨与策进自身的工作,阐发兵役的理论,普遍宣传兵役法令,沟通各方面对役政的意见及唤起民众踊跃服役。”[3]该刊主要设置有“特载”“论著”“法规”“奖惩”“消息”“资料”“会议记录”等栏目。除此之外,该刊还专辟“文艺”与“杂俎”栏进行与如上栏目相匹配的兵役文化宣传,诸多著名作家如谢冰莹等都在此刊上面有过文章发表。李健吾的《从军去》剧情十分简单——主要描写了一个老父亲送别年轻孩子们奔赴战场的故事。在简短的剧情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慈父和一个多情女子的形象,使该剧生动、活泼。少年儿郎们即将奔赴战场,老父担心这些孩子们“没有尝过战场上的风味”,而年轻女子则难忍离别之痛,不忍卒听“使人丧气”的话。剧情在情绪的波折中推进,为了民族国家大义,老父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私爱、忧心,鼓励道:“忘掉我,忘掉你的爱人,忘掉你的家!”,而年轻女子则送上了一朵蔷薇花以表激励。如此,全剧在年轻男儿们发誓用血(敌人的或自己的)浇灌蔷薇花的高潮中结束:“花真红的可爱!如果枯了,只有血浇得活来!”整体看来,该剧情节紧凑有致而又跌宕起伏,不失为一出新颖别致的宣传剧。司马长风在研究李健吾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时曾指出:“他不但勤于写作,艰苦支撑着上海剧院的发展;并且致力选择了具有抗敌意识的题材,在不损艺术素质的情形下,对民族抗战略尽微力,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上虽然不必过于重视,但可见出他的人格。”[4]266此话虽是针对李氏几年后的创作而言,但在此佚文中也可看出其爱国主义的深切表现。
2 戏剧评论:《艺术成长在委曲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上海,上海沦陷,李健吾困顿失业。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沦陷区的上海戏剧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包括黄金荣之孙黄伟在内的诸多名人纷纷拉拢上海话剧界人士组建剧团,演出牟利。对此,一方面是迫于生计,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在抗战期间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李健吾终于“跳出了象牙之塔,扔掉了清高,摔开了诱惑,从此以戏为生,成了士大夫所不齿的戏子”[5]216。此一期间,李健吾虽有过登台表演的经历,但多属客串,故上文应为戏言。此间,他真正倾心付出的,是为多所剧院改编了诸多剧目,如《花信风》《喜相逢》《风流债》《金小玉》《好事近》等。这些剧作在上海的演出,一方面为李健吾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被称为“沦陷区剧坛的巨人”[4]266),另一方面却也让剧作家本人颇感不安。论其缘由,如作家自述:“人属于一种有遗憾的动物,喜欢做的不一定能够做,时间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尤其是,说也可怜,机会不允许。通过允许的往往多是不最喜欢的工作,悲哀就在这里。拿我自己来说,悲哀给我力量,悲观主义让我积极。我要写的戏永远没有写,我要改编的戏永远没有改编。我敬爱的作家,我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去,自来没有掏出半根木桃酬谢。而酬谢的倒多是未尝谋面的人情和世故。”[6]273换而言之,在李健吾看来,他自觉此一时期翻译、改编的作品都不是自己的心中所想、心中所愿,在现实生活里,他不得不拿萨尔度这样的徒以技巧和舞台经验取胜的夸饰之徒来博取观众的眼球,但在内心里,他又认为只有莫里哀那样的剧作大师才配得上自己的倾心付出,于此,作家内心百般纠结。笔者翻阅民国时期刊物,新发现一篇李健吾评论《喜相逢》的文章——《艺术成长在委曲中》,认真读来,多有如上的心态记录,现披露如下:
艺术成长在委曲中(1)本文发表于1943年6月3日《海报》第4版。
李健吾
“上联”现在上演的《喜相逢》,和原作的面目大有出入。假如有人叫我担负这个剧本的全责,惭愧之至,我实在没有心情承受。有谁能够吗?问问做母亲的人们,她们能够接受任何人的建议,重新改换一下儿女的体气吗?儿女永远是自己的好,我相信这句话,但是艺术作品不就是儿女。用儿女来比喻自己的制作也许是浪漫作家的感情话,我这个被人誉做“浪漫派”而又“为艺术而艺术”的小子,却自来不便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我不能够用一句话说明创作的过程不就是宿命论的生儿育女,同样我也不能够用一句话说明我对于这个剧本的责任。
一个剧本如果需要修改,我是非常乐意于修改的。年龄越增加,我越感觉自己和自己的制作一无是处。因而也就越发不敢冒昧从事。可是等我完全脱稿之后,在永远等待指正之余,我也永远给自己保留一个最后的壁垒,我不能够丢掉我全部的概念另来一个概念,因为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概念,假如有第二个概念可以替代,那它就不复是它了。一个生命只有一个生命,略加删削,就不复是生命了。艺术的完整就建立在它的生理的匀适,可多可少,便有些近于儿戏。
我是在说《喜相逢》,不料跑了一个迂阔的圈子。其实理论仅归理论,事实上,我是接受了这个痛心的责任。《喜相逢》和我早年的《这不过是春天》相仿,比较起来,更其多了冲突和不幸。调子是单纯的。然而舞台的成分却是浓厚了许多。现在么,真可怜了,除去了“浪漫的”热情故事之外,真是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我的了。当然,语言还是我的。我能够欺瞒谁吗?听听看,它是多富于“哲理的”“文艺的”气息呀!
现在,这成了什么东西?我倒很想高攀莘农先生,把它东施效颦称作什么“惊奇剧”。或者索性尊重导演仞之先生的意见,把它排成“侦探戏”吧。仞之先生现在又不预备把它排成“侦探戏”了。我晓得他和我一样痛苦,因为种种关系,不得不时时刻刻改变他的观点。我们是一对可怜虫。有什么办法?艺术在委曲之中逐渐成长。所谓委曲,是一切;所谓一切,用一个时髦词儿罢,就算是耳目的濡染。
有谁知道此中甘苦吗?我不会讲给任何人听的。□(2)“□”为无法辨认的字,疑为“讲”。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点子委屈也值得人洒一掬同情之泪吗?戏是要上的,幕是要揭的,但是最重的戏却在舞台以外,眼睛不敢看,心灵不敢接触的角落。《喜相逢》是一出悲剧,因为他上演的命运是悲剧的(图:喜相逢演员沙莉)。
由上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其时,李健吾对此类剧作的改编十分不满,这除去自身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客观存在的原因——市场商业化的冲击。如《喜相逢》,就创作初衷而言,作者原本想要展现的是一出极具“哲理的”“文艺的”气息的文艺创作,但沦陷区的观众,生命无着,享乐盛行,显然对此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所喜欢的是“传奇剧”或“侦探戏”,与作家的创作宗旨相差甚远(3)李健吾在之后的其他评论文章中,也对此问题有过进一步的阐述,如在《上海屋檐下》一文中,他曾说道:“我们毋庸讳言,一种恶劣的倾向直到如今还在戏剧文学方面盛行。某些人士从未纳心戏剧,从未涉足舞台,从未深尝人生,由于聪明,由于上演税与版税的双重利润,由于可以直接博取无识的观众……我们不用妄想从里面寻找人生、理想、一切感动人类的优越之感。他们一向不理睬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生如何决定一切,而一切又如何渗透作者的心灵,浑然成长。正是这样一批买空卖空的剧作家,率同他们的喽啰和观众,依仗周密布置的茶酒联络,暂时攘去了浩大的声势与营业。悲剧成了情节戏,一切成了服装戏。”参见李健吾.上海屋檐下[M]//李维永,李健吾文集:第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241。,这便有了如上的一篇怨怼之辞。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李健吾虽然有崇高的启蒙理想,但面对现实境遇,他最终只能无奈地承认此类改编戏终究还是要上,“但是最重的戏却在舞台以外,眼睛不敢看,心灵不敢接触的角落”,这真是一种况世的无奈。对此,他所能做的,或许唯有多次强调:“所以,让我不妨再重复一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小民,诚不足道也矣!”[5]216
3 艺术评论:《喜剧的大无畏精神》
除是优秀的戏剧家、文学评论家外,李健吾还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他倾注心血最多者当属莫里哀。早在1940年代,李健吾就翻译了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党·璜》《吝啬鬼》《向贵人看齐》等多部独幕剧与多幕剧。1981年,在生命的晚期,李健吾仍孜孜不倦,坚持翻译完了《莫里哀喜剧》(四卷本)。此事完成,他倍感欣慰,“了却这桩心愿,心情的愉快是可以想见的”[7]389。如若说1940年代改编萨尔度的剧作让他感觉如鲠在喉的话,那翻译莫里哀的喜剧对他来说则是甘之如饴。1946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结集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集》。李健吾不仅为这部剧集写了“总序”,还为其中的七篇剧作(《可笑的女才子》《党·璜》《屈打成医》《乔治·党丹》《吝啬鬼》《德·浦叟雅客先生》《向贵人看齐》《没病找病》)写了“分序”进行详细介绍,由此可看出其对莫里哀的由衷喜欢。据笔者考证,李健吾最早明确表示他对莫里哀喜剧的喜欢与认同当是1946年在《昌言》杂志发表上的一篇艺术评论——《喜剧的大无畏精神》,抄录原文如下:
喜剧的大无畏精神(4)本文发表于《昌言》杂志1946年6月号。张新赞在《在艺术化与现实化之间——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一书中曾提到过此文,但一则是节录,再则他所指出的发表时间有误(李文指出该篇载《昌言》1949年第6期),故本文重新披露了全文。
李健吾
一个有良心的喜剧作家似乎生下来就不是为现时活着的。他或许不曾意识到使命的重要,但是他投下去的无形的炸弹轰然作响,若干世纪后,震颤的余波继续还在荡动,同时他的富有爆炸性的激烈的言辞,从已经化为灰尘的束缚人性的传统解放出来,在他不朽的精神后面,形成圣者的光晕。人是朝着未来和理想走的,但是喜剧作家的道路最切实,也最直率,因为他的最大的根据是现实,永远是现实,同时他走路的方式最轻快,也最利落,充满人类的智慧,仿佛保姆哄着一群顽皮的孩子喜笑,就在喜笑之中解除他们的自负和愚昧,在最明显也最有意味的比照之下看出制度的腐朽和人性的狭隘所在。单从这一点来看,假如一切文艺基于理想的生命,站在前进的方向,喜剧由于本质和方法,显然属于激烈的革命,仅仅比实际的行动温和一点罢了。
此其所以正人君子特别鞭斥喜剧,因为喜剧仿佛一只困兽,企图突围而出,在风习和法令之外追寻一种更大的自由。它是一把晶明的匕首,摆在桌子上面和不合理的人事,尤其是人性,挑战。最勇敢的由人事着手,最深宏的由人性着手,一个走着笑骂的路,一个走着分解的路,一个辛辣而味道不永,一个蕴藉而情趣长在。人事最容易惹来祸患,也最容易崩溃,完全属于时间。但是无论所攻击的是特殊现象或者普遍现象,喜剧作家之易于成为危险分子,却是自戏剧有史以来的事实。
莫里哀把最高的喜剧的成就留给我们,同时也把最艰苦的斗争的实例留给后人。他不及后辈包马丽(Beaumarchais)那样尖锐,那样调皮;包马丽的词句是火药,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紧紧跟着就来;贵族社会的罪恶随着年月加重。花结了果子,果子似的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但是花似的路易十四呈有盛开的表面的绚烂。时代限制了莫里哀,政治的感觉不像包马丽那样敏感,不过,虽说邀得路易十四的知遇和恩倖,莫里哀从来没有放弃他对于时代的鞭策。几乎每一出戏为他招致一场是非,而每一场是非为他带来斗争的兴奋。和他作对的不是一个人,一个沙龙,一个制度,而是所有制度,所有沙龙和所有在这里面长大的人。直到十八世纪,他死了将近一百年了,还有学者文人如卢骚(Rousseau)达朗拜(Dalembert)拿他当作恶例来坐实喜剧伤风败俗。假如不是路易十四说情,死了的可怜虫就连一个坟穴也不要梦想得到。大主教把他看作罪恶的化身,不许他在白天入土。然而莫里哀,这个不做阔少爷要做戏子的流浪人,身子一直生病,好像有千万年好活,偏偏找气给自己受。
莫里哀的前辈剧作家高奈叶(Corneille),在他的《撒谎人》里面,利用父子争吵,提到一个基本做人的问题:维持身份的是道德不是门第。“世袭”的荣誉要以道德存在,以罪恶丧失。这是一六四三年的事。二十二年以后,同样境界到了莫里哀的笔底下,简短的诗句舒展成为详尽的散文,反复的质问藏有深厚的不平:
“——你这样不配你的家世,真就脸也不红?告诉我呀,你有什么权利引以为荣?你干了些什么来充官宦子弟?你以为顶了名姓,有了家徽就算数?你以为我们出自贵人的血统,然而在罪恶之中过活倒是一种光荣?不,不,没有道德,门第也就不在。……你要知道,一个不学好的官宦子弟是天地间之间的一个怪物,只有道德才是贵族的头衔;我看重的不是签的名字,是做的事;我看重一个下流人的规矩儿子,远过于你这样生活的一位太子殿下。”
现代人或许还嫌莫里哀太温和,那是忘记了他的环境和时代。十七世纪难得有第二个作家斗胆申斥嚣张的贵族子弟。他拿他仅有的武器来攻击他所能看到的不合理的人情制度,也是他最好的武器,那驰驱战场的喜剧。读惯了歌颂文字,如今就是温习一番活在路易十四的余荫之中的莫里哀,我们的耳目也是如出新浴,特别清新。
这种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是喜剧作家最高的表征,他的智慧永远和这种精神密切合作,他不个别攻讦,然而正因为倒在他的言词之下的是制度,是风俗,是一般,他以千钧之力来克服。莫里哀就这样活生生送了他的性命。他的艺术永远是人类的一个崇高的榜样。
三十五年五月
“昌言”顾名思义,取其“畅所欲言”义。此刊创刊日期——1946年5月4日,显然有“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前行”的意思。刊物主编马叙伦在《昌言发刊词》中曾指出:“自然,我们决不用主观来说话,也决不用偏见来说话。我们说的是我们良心上要说的话,也是无党无派的老百姓要说的话,所以在我们毫无顾忌,替人家不做隐瞒,真是‘直言不讳’,‘昌言无忌’,所以我们叫这个刊物做《昌言》。”(5)本文发表于《昌言》1946年5月创刊号。这与李健吾此篇评论文章的创作宗旨不谋而合。
在上文中,李健吾继续延续其跳踉、洒脱的文风,综合概述了喜剧的本质和方法,指出喜剧“显然属于激烈的革命,仅仅比实际的行动温和一点罢了”。他以莫里哀喜剧为个案指出喜剧的重要价值:“喜剧仿佛一只困兽,企图突围而出,在风习和法令之外追寻一种更大的自由。”作者对比了莫里哀与包马丽(今译作“博马舍”)的创作,认为莫里哀的确没有包马丽对于政治的感觉那么敏感。他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剖析,明辨莫氏喜剧的精神价值与意义,指出:“他不个别攻讦,然而正因为倒在他的言词之下的是制度,是风俗,是一般,他以千钧之力来克服。”李健吾对莫里哀的喜爱是由衷的,对他的同情是深切的,对他的认知也是深度共鸣的。同是知识分子,同为革新人类精神、社会习俗、国家自由而奋斗,翻译莫里哀对于李健吾来说,是身处沦陷区精神生活的一种莫大慰藉。有论者说:“除了爱国抗日之外,健吾先生把清除中国大地上的封建糟粕置于他视野内的重要位置上。或者说,正是这两点:反帝反封建的主旨,使健吾先生置于进步作家的行列里。”[2]526此乃知人之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健吾承续了他先前对莫里哀的喜爱,不仅在生命的晚期彻底翻译完了《莫里哀喜剧全集》,还写有《〈莫里哀戏剧集〉序》《莫里哀的戏剧》《〈伪君子〉——莫里哀的戏中演的最多的一出》《法国大喜剧家莫里哀》《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关于莫里哀的戏剧艺术》《试谈导演莫里哀的喜剧》《〈莫里哀喜剧〉序》等多篇序中对莫里哀的创作进行了深度的推广与介绍,其艺术见解与思想观点都可在上述文中找到。
4 自传散文:《感谢母校》
1925年9月,李健吾考上了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自此成了一个真正的“清华人”。查阅《李健吾年谱》可发现,清华师友、同学在李健吾一生的诸多活动中都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此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是“清华同学会”。《李健吾年谱》记载:1933年10月31日,李健吾与尤淑芬的婚礼,由“清华同学会包干承办”[8]57……1948年8月,恩师朱自清先生病逝,上海文协总会与清华同学会共同出面为朱自清举办了追悼会[8]144,这样的例证在李健吾的一生中不胜其数。1948年12月,恰逢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上海清华同学会推出了校庆纪念特刊,其中“专载”栏着重推出了两方面的文章:一者是邀集校友写作的庆贺文章,如《母校教育的伟大》《三时期周校庆感赋》《我憧憬着清华园的钟声》等;再者为纪念母校受难的专篇文章,如《南行纪略》《忘不了的联大》《昆明的灵生活》等。李健吾也在受邀之类,论文章属性当属第一类,但在行文中,他以真切的话语、忠实的笔触记载了他自身求学清华时期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发布如下:
感谢母校[9]
李健吾
前年在一个为清寒学生募集学费的集会里,我有机会参加一个节目。我同情他们,因为我想到我自己。记得我进清华大学的头一年,家里每月只有二十元收入,我十三岁失了父亲,和母亲姊姊一直守在会馆里面苦苦过活。我从中学二年级起,就卖文为活,经常则靠父执捐助的两千元利息来维持。清华据说是一所贵族学校,但是想不到做学生的开销非常小,我一直读到毕业。上了半年,寒假到了,开学前必须筹到四十元,才够对付学杂费和膳费书费。我决定到天津去看一位父执,请他帮我一笔款子。
那位父执是续西峰。他给了我五十元,我很感激他。但是回来坐火车,风沙太大,车厢里又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车门外边,挨过了四小时的风寒。紧接着学校开学了,我回到清华园把费用全缴清。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埋伏下的病根爆发了,我有了高热,同学把我送到学校医院医治。那时医生是拉佛尔斯,一个有趣的老头子,手永远在抖擞,劝人信基督教,待人很和气。我躺了很久,记得“三八”学潮那天,我还没有起床。早晨看我病的汪振儒,下午自己受了枪伤,进了协和。拉佛尔斯起先找不出我的病原,过了许久,决定我左肋有了毒水,要我到协和去抽掉,我顺道还去看了老汪一趟。水抽了,过了一年,我的右肋又有了毒水,结果肺量压小了,肺也受了伤,有了一点点结核。这一下子我就养了好几年,但是我并没有辍学,仍然按班就步的读完了学分。临毕业的时候,身体逐渐复元,居然好下来了。
我那时候可以当得起“贫病”二字,文章也就卖得更勤了,好些小说,短篇小篇都是那时写的。我必须感谢清华母校,鱼肝油白送我吃,药钱没有向我要过,隔些日子还给我鸡吃,每天上午十点钟,我还得到先生的同意,在体育馆后边假山上晒太阳。这不是学校,这是理想的肺病疗养院。因为还有课上,还有书读,绝不寂寥。清华是贵族的,那是说学校。学生并不都是阔人家子弟,然而最沾光的都是我们那些穷学生。假如中国学校都像清华那样“贵族”也就好了,按说也是应该的。
现在就是清华也穷了,听说我的几位老师也都瘦病不堪,没法子过活。至于做学生的,天晓得成了什么样的叫花子,我也就不敢想象了。可是当着那群清寒学生,个个面黄肌瘦,我没有朗诵,眼泪先就落下来了。他们如今是真生不起肺病了。
此文虽是庆贺文,但并没有虚张声势的痕迹,而是以具体的例证、质朴的笔墨记录了李健吾求学清华时期的艰难经历——家贫、重病、孤苦但终究得到了母校的悉心帮助等。这段经历在韩石山先生所写的《李健吾传·清华时期》一章中有所记录:“续西峰是过惯了夜生活的,夜很深了还躺在烟盘子旁边,和两三位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偶尔转过身子问他一句。一整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早赶八点钟火车回来,车厢里挤满了人,只好冒着大风站在车厢外头的过道上,身上穿得挺薄,一站就站了三个钟头。回到家里跟母亲交代一声,当天赶到学校,第二天缴清费用,第三天就躺下起不来了。在医院一住就住了两个月。体温始终不退,最后检查出来,左胁有了肋膜炎。这回治好了,但是隔不到几个月,帮小学时一位同学家里办丧事,一劳碌,右胁又有了肋膜炎。同时又引发了肺病。”[7]48-49对照上文,即可发现,韩著中所记载的某些经历如李健吾此次发病的时间(一星期后)、右胁有毒水的时间(一年后)以及四小时的风寒(而非三小时的大风)等细节与李健吾的自述均有所出入。作家为传主写传难免有虚构成分,但既然有传主自述还是应以传主自述为准。就此而言,上文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
5 余论
史料的整理与发掘为作家的“生存与思想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10]。李健吾“从剧作、小说、散文,甚至诗歌、翻译、中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确实是一位成就杰出的学者和多面手”[1]375,我们不应让其功绩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而应努力让它们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学界对李健吾的小说、剧作、翻译以及文学评论的风格投注了较多的目光,但对李健吾生平资料的整理、收集,李健吾笔名的考证以及对他戏剧评论的关注度尚有欠缺,不无研究之憾。笔者钩沉、整理以上集外文,抛砖引玉,以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