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不可言说之秘
——评《神唇之笛》
2022-12-11梁业涛
文|梁业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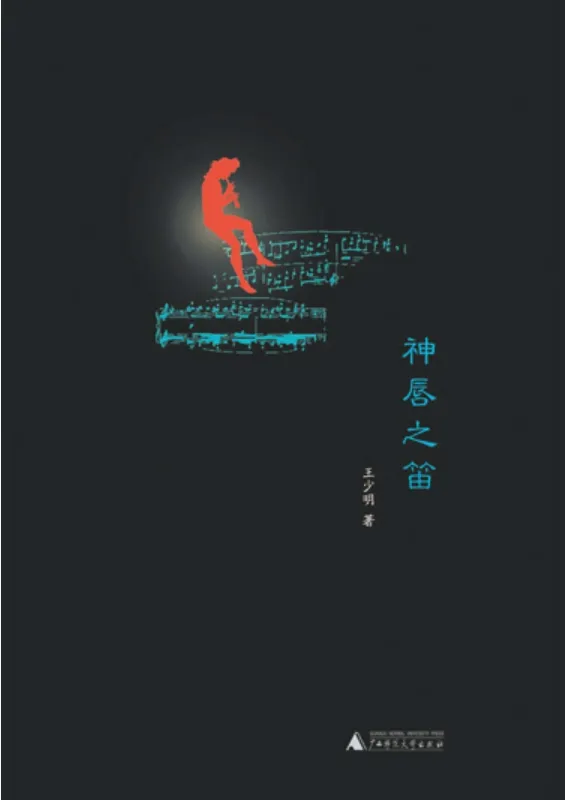
《神唇之笛》
音乐,在语言学意义上,其自身的形态结构是可说的,但从哲学本体的角度,又是不可说的,凭人作千般努力亦往往难捉它一瞬的风采。我想王少明教授的《神唇之笛》正是从后者的意义上探勘那不可言说之处。《神唇之笛》是一本音乐哲理散文集,全书共22篇散文,每一篇都似一面晶莹剔透的镜子,反射出音乐隐含的神之光。其中角度亦迥异,有的从灵修出发,有的从哲学出发,更有的从死亡出发,正是通过这层层的影射,我们亦似乎明悟到那不可言说处。
以我看来,全书的命脉应在它的题目“神唇之笛”,书中每一篇散文的运思起伏都离不开这四个大字。因为正是站在“神唇之笛”这个角度观音乐的创作、听音乐的表现,才有了这种种的神思。就书而言,“神唇之笛”指的应该是音乐家及其作品,准确来说,是音乐家应该有的状态——即作为神唇边的笛子,所以笛子散播出的亦应该是神的福音。这里的神当然不是基督教意义的上帝,也不是中国式的漫天诸神,而是一种对形而上的存在的信仰。正如王教授在书中所提到的:“这种神既是超越个体、族类,也是超越肉体、物质的。最高层次的艺术式音乐是要表达这种具有超越一切,定于一尊指令的‘天道天命’,并引导人们作此追求。”所以音乐家创作时应具有一种“超功利性”,一种“超目的性”,让存在去“做主”,而音乐作为“福音”应摆脱“工具性”,还原成生命的声音。这是针对立足于现今音乐界的两种“异化”而言的:第一种异化是人的异化,第二种是音乐的异化。前者主要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创作者被娑婆世界的幻象蒙蔽,为争那一亩三分地而丧失自我,更丧失作为“笛”的责任,只能产出一些无个性的、平面化的音乐。欣赏者也仅局限于“感官的快适”,慢慢地变得麻木,即便是心灵的音乐亦难唤起他心中的一潭死水。这样一来,音乐就被异化了,本应该满足生命的,降低为满足生存的需要,本应该是异质的艺术,变成同质的技术,音乐异化成工具。可以说“神唇之笛”是在勘破那不可言说处时必然显现的,因为这正是音乐的根,也应该是人的根。所以每每阅读书中的散文,总会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形而上存在的祈向所迸发出的“神圣感”,这种“力量”亦应来自对音乐本质的敬畏感。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视野的宽广,这首先体现在关注面之广上。正如笔者前面所言:王教授的22篇散文,正是22面镜子,从各方面透出音乐之光,其中包括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生命、音乐与爱、音乐与诗性、音乐与艺术、音乐与尼采、音乐的教育等不一而足,亦不必按理论逻辑细细划分,更多应是王教授多年涉猎后的随性之作。视野广阔还应包含理论视野的广阔。在文中充满各式各样的理论,也有着“不分东西”的引用,只要适时适地,无不可用。就哲学而言:有引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柏拉图“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实体论”、尼采的“强力意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等。在美学上也有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美学、康德对判断力的批判等。总之这些理论就如一个个“放大镜”,让我们窥见音乐之微。但王教授绝不仅仅囿于西方二元逻辑理论的“正方法”,应该说他是用东方的“负方法”统筹这些“正方法”的。所以文中更多的不是这些观音乐之微的理论体系,而更多是把握音乐整体的各种感悟,通过这些感悟,音乐成为一个超越的整体。
第二个特点是洞见深刻。我想这些深刻的洞察是源于对上述各种理论的整合及感悟的。在这里笔者稍摘一段供各位体味。在《喜鹊与乌鸦——民族音乐及中西音乐比较》一篇中提到:
我曾经把西方文化比作乌鸦文化,即报忧多于报喜;把中国文化比作喜鹊文化,即报喜多于报忧。乌鸦文化是一种悲剧文化,这种悲剧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它预设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它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既然有罪就应该受罪就应该接受惩罚。二是人生来就是要死,每个人必须面对必死这个前提。生也好,死也罢,整个过程充满着无常式各种可能的痛苦和恐惧。所以人生来就是一场悲剧。西方文化中,无论是神话、戏剧、音乐,还是小说、诗歌舞蹈大都以悲剧为结局。喜鹊文化是一种喜剧文化,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大都是以大团圆结局的。
这是从本质上剖析中西文化,可谓一针见血。西方的悲剧精神一直贯穿于它的文化当中,但与其说悲剧是为引起人的恐惧,毋宁说是要净化情感,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言:通过强烈的情感宣泄而达到平衡。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中庸”与克制,即便是强烈的悲剧亦不使其丧失美好的追求与憧憬,致使每个悲剧故事迎来的必是大团圆的结局。正是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两部同样伟大的爱情悲剧不同的祈向——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以死殉情,只能期待下世再遇,遗憾千古;而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死后却化为仙蝶,传为千古佳话。以此为基础,作者又将笔触转向音乐,得出中西音乐的差异在于“中国传统乐器是一种生命的构造,是心灵的投影;西方的乐器是一种理性的构造,是大脑的投射”。这些正是“一种文化积淀或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中庸”和“克制”,导致我们更习惯于一种顺其自然的,亲和圆润的,更多是心灵作用的艺术方式;而西方文化强调在“日神的理性与酒神的沉醉”碰撞下的悲剧精神,由此应习惯一种二元冲突强烈、个性表现强烈的“大脑”、理性构造的艺术方式。这些对艺术的洞见也直接戳中了中西艺术的本质,或许正因站在哲学王国上,才有如此深度的体会。除这篇外,其他的文章也或有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深思熟虑处,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神唇之笛》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度解读的书,如能“吃透”,想必裨益不少。当然作为一本音乐性的随笔来说,确是稍欠一些站在具体作品上的体会与感悟,如能加上对具体音乐作品的赏析,想必能使全书更添色彩。但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站在音乐王国以外,静观音乐。我想王教授正是处于这个位置的。在这本散文集中虽没提到音乐之“用”,但全书关涉的却是音乐之“体”,关注的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工具之用”,而是他说的“无用之用”。正是这种无用之用,引领我们解开音乐的奥秘,勘破那不可言说之处。诚如罗小平教授在序中提到的:阅读此书你虽不能获得物欲的满足,但可以得到精神的财富、灵魂的救赎、爱乐的幸福和生命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