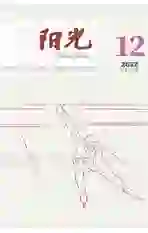出乡
2022-12-08赵旭东
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闫耿是不会去西乡打工的,虽然他现在只不过是个规模不大的旅游村农家餐馆的老板兼厨子。
得到封村的消息时,闫耿和父亲正在准备过年时游客的食材,大棚里西红柿、黄瓜、茄子、北瓜、豆角长势喜人,这是今冬的第三茬菜。闫耿父亲说:“来村儿过大年的游客比往年只多不少,咱家的大棚恐怕是供不起了。”说这话时,闫耿父亲语气里藏满了喜悦。
闫耿母亲气喘吁吁地跑来,带来了封村的消息,闫耿急忙蹿出大棚,大喇叭里村长的吼叫声夹着寒气当头劈来,闫耿心里“咯噔”一下儿:“完了!”闫耿父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压断了一棵坠着青果的西红柿秧。
这个年真是难忘又难过,一家老小窝在家里一个多月了,闫耿母亲一边拒绝别人送来的东西,一边把宰了的鸡鸭鱼和下架的蔬菜往外送。
爆汁儿的蔬菜、瓜果在闫耿一家的手里越拣越蔫,越择越少。闫耿眼睁睁看着那些变质的食材被丢弃,心里刀绞一样。
“狗东西!啥时候是个头儿?”
闫耿父亲望向窗外,语气里团着浓浓的愁,他把所有不好的事务都称作“狗东西”。
闫耿父亲又说:“再这样下去,就要‘吃棺材了!”
在东乡,“吃棺材”是句重话,是“吃老本儿”意思,东乡人奉行着很严苛的消费规则:花小不花大,花零不花整,能不花决不花。不为别的——穷怕了!有时候,宁愿撇下脸子跟人张口借,也不轻意动自己的大钱或整钱。其实就想凑个整儿,变着法儿逼自己少花钱,虽说这几年家家手里有了些闲钱,可节俭的本性仍然緊扯着大家动存款的念头。
闫耿的村子在太行山下一隅角,前后左右被山围裹得井筒一样。三十年前,外面的风吹不进来,挑着扁担卖粮食卖山货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出山三十里,回来三十里,都是一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闫耿想,他得出门了,其实这也是父亲的暗示,再待下去,人废了不说,只出不进,不合规矩。闫耿给在西乡的同乡打了电话,回应说:“西乡的厂子正在招人。”闫耿便动身往西乡去。
去西乡,是东乡人的向往,或者说是梦想。一条幽深的峡谷将两个县划得清清楚楚。峡谷以东为东乡,穷且山,资源匮乏;峡谷以西为西乡,富而平,矿产丰富,自古就有“穷东富西”的说法。老天爷真是偏心!
西乡厂矿林立,不但待遇丰厚,环境也舒适,随处都有招聘的岗位,不愁找不到工作,是打工者的天堂,回乡之前,闫耿和妻子就在西乡打工。
那些年,上了年纪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留守在家,家是最大的牵挂。有一年,老父亲突发急病,乡亲们抬着担架连夜将他送至医院,闫耿夫妻拼了命往家赶,病床上,父亲一脸憔悴,见到闫耿回来,满心的自责,痛骂自己身体不争气。隔壁的床上,躺着发烧的儿子,母亲左右侍奉,没了人样,闫耿愧疚不已,感觉心都被剜空了。醒来的儿子发现爸妈都在,高兴得像得了宝贝。后来,闫耿问儿子最想做的事儿,儿子回答:“希望能和爷爷一起生病!”
临行前,闫耿去跟凤奶奶道别,这是母亲特地嘱咐的,其实即便母亲不说,闫耿也会去。绕过“眼泪”东岸,穿过广场,就到了凤奶奶家,凤奶奶坐在院子里的老榆木凳上打盹儿,安详得像来村里采风的画家们画板上的油画。
闫耿一到,“油画”醒了,一笑,露出仅有的一颗上牙。闫耿给凤奶奶磕头。凤奶奶问:“耿娃儿,你也要出门?”闫耿说是。凤奶奶说:“去吧,不怕!去歇歇吧,让山也歇歇,鸟也歇歇。”闫耿说好。
告别了凤奶奶,闫耿向村口的公交站台走去。
也许是习惯了人来人往的日子,闫耿对于这静悄悄的山路反而不适应起来,这样的静谧还停留在遥远的记忆里。
站台被茴香田簇拥着,这是村子里最大的一片平地,夏天时,茴香开满黄色伞状的小花,密密麻麻,像绽放的礼花,香飘十里,引得游人顿足观赏。再过几天,就是种茴香的节令了,东乡人管它叫“茴香会”,也是开春的庙会,在外漂泊的人,每年“茴香会”这一天都会赶回来,撒上一把茴香种子,期盼开年的丰收。一连几天,会有各式各样的社火表演:扛桩、高跷、威风锣鼓、神旗、銮驾,热闹得如同过年。闫耿想,今年的“茴香会”会不会像往年一样热闹?
老村长戴着口罩,孤身一人把在村口,沧桑得像村里的老槐树,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消毒药品和体温计,旁边是几筐菜果,这是村里人送来的,谁家有需要,都可以拿一些。
跟闫耿父亲年纪相仿的老村长,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是个憨实不善言辞的长辈,见闫耿到来,急忙起身,踉跄了一下儿,险些摔倒,闫耿赶紧上前搀扶,老村长眼里布满血丝,声音沙哑。“耿娃子……”
老村长指指山外,闫耿点点头,再无言语。最大的心酸就是相顾无言吧。
老村长抽出被冻得紫红结满老茧的手,向闫耿伸出三个指头,再回望时,四目含泪。闫耿明白老村长的意思,这是他今天送走的第三批外出打工的村民。
和老村长道别后,闫耿提着行李上了公交车,把家乡扔在了身后。
公交车喘着粗气呼啸在忠爷爷开凿的路上,盘旋向上,这条路一边靠山,一边临崖,山有几十丈高,崖有几十丈深,疫情之前,这条路每天接待成百上千的游客,观光大巴、私家车、骑行者、徒步者将这条山路塞得满满的,大家不紧不慢地驱着车,让眼睛尽赏沿途的景致。
公交车逐圈儿爬高,“眼泪”的全貌便显现出来。“眼泪”呈现出让人心疼的碧蓝色,它是山泉聚成的一片湖,是巍峨磅礴的太行山少有的一丝温情。至于为什么叫“眼泪”,没有人说得清楚。闫耿想到上学的时候,凤奶奶讲课时说过:“别看你们忠爷爷五大三粗,其实以前也是个爱掉眼泪的家伙。”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凤奶奶还说,“老天爷是公平的,咱们吃的苦不会白吃,咱们流的泪不会白流,老天爷都给攒着呢,迟早有一天会还回来的,或许还能加点儿利息。”
凤奶奶的话没错,先辈们吃的苦流的泪在三年前开始有了回报,乡村旅游兴起后,闫耿丝毫没有犹豫,带着妻子回了乡,贷款办起了农家餐馆,再后来,更多的年轻人如同疲倦的鸟儿一般,扑棱着翅膀披星戴月归了巢,这些归来的鸟儿有的衔来了橄榄枝,有的叼回了如意草,他们已经不再是只能靠土地生存的东乡人了。农家乐、旅社、写生馆、有机大棚、鱼塘、畜牧厂、游乐园在一夜春风间遍地开花,这里成了小有名气的旅游村。
再往前,就是远近闻名的“挂壁公路”。一条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的通往山外唯一的路,如勒在山涧上的一条腰带,是山和平地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疫情以前,成群结队的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惊叹于太行山的雄伟壮阔,也感叹于修路人的胆识与壮举,网上有好多写它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每每听到别人谈及家乡的“挂壁公路”,闫耿心里倍感自豪。
“挂壁公路”起头是山神庙。在闫耿看来,大山里哪有神?征服大山的人才是神,忠爷爷就是神。忠爷爷是凤奶奶的男人,当年,他带头捐出自己的棺材板,领着村民一凿头一凿头、一铁锤一铁锤啃出了这条路,路修到一半儿,忠爷爷就心脏病发作死了。老人们说,忠爷爷是累死的。办完忠爷爷的丧事,凤奶奶说:“哭都哭了,该干嘛就干嘛吧。”半年后,凤奶奶的儿子掉下悬崖摔死了,大家以为凤奶奶要挺不住了,凤奶奶又说:“哭都哭了,该干嘛还干嘛吧。”从那以后,孤寡的凤奶奶成了全村人的奶奶。每年学校开学,凤奶奶都会给娃娃们讲很多故事,逃荒的故事、修路的故事,村子里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在外乡人看来,这条路就叫“挂壁公路”,其实它是有名字的,忠爷爷说过,咱们修路不光是为了出山,也是方便咱们回乡啊。于是,这条路就叫“回乡路”。
刚刚兴起三年的乡村旅游,还是个脚跟不稳的孩童,一心想快快长大,不料却被疫情抽掉了骨头,软泥一样瘫痪了。
公交车缓缓通过“挂壁公路”,崖壁上凿子的印记历历在目,闫耿仿佛还能听到回荡在这里的凿石声、呼喊的号子声和开山的土炮声。
“挂壁公路”像一只淘气的松鼠,在山腰间钻来钻去,进进出出,时隐时现,忽明忽暗。路到尽头,出得洞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了山。
山外的天空格外清爽,大地被风儿温暖的舌头舔过,一切正在醒来,小草稚嫩的身体挣脱了泥土的束缚,冒出头,看到了整个世界,真正立于天地之间,小麦正在返青,枯黄中涌动着隐隐的绿。
“挂壁公路”出口不远处的坡顶有个长满荒草的土包包,忠爷爷就睡在那里,时时刻刻守着他的路,守着他的家乡。闫耿在心里祈祷:“忠爷爷保佑,让疫情早点儿过去吧!”
赵旭东:山西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漳村煤矿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