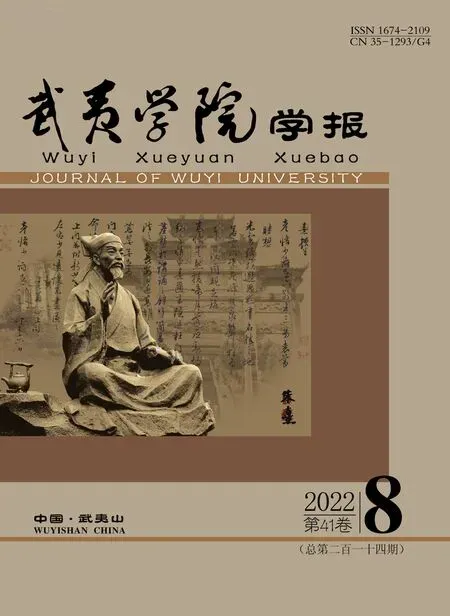浅析朱熹“为己之学”的课程思想
2022-12-07陈云
陈 云
(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0)
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他的著作 《中国人的精神》中曾提出:“中国文明的精神,不以暴制暴,而是诉诸义礼。诉诸义礼,就是指践行正义,恭敬有礼,修养良好。这是中华文明的秘密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1]辜鸿铭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的看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对人的培养目标上的反映,它支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日常生活。正如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修养,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不是为了装饰给他人看,作为显摆自己的资本。这种“学以为己”的学习目标不仅在于个人所获得的知识,更在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个人心灵的陶冶,是心灵和理智完美结合的产物。这种“为己之学”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想”“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2]。宋代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教育思想,他认为学习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自我德性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为己之学”的课程理论,并践行在自己的教学上。
一、朱熹“为己之学”课程思想的渊源
朱子理学在宋以后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主流,他的思想也被称为“新儒学”。在他早年时期酷爱佛老学说,虽然在师从李侗之后,他开始批判和反对佛老学说,专注儒家学说,但是在他的理学理论体系中依然浸润着佛、道的观点。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在儒佛道三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也成为他课程理论思想的渊源。
(一)儒家思想的继承
对于“学”,孔子认为“学”是引领个体走向君子之道,促进个体“成己成人”修身之路。在对弟子的教导中,孔子推行“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的育人观[3],比起外在功名利禄,孔子更注重学生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进一步论证孔子“治学以修身”的育人目标:“观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独称颜渊,且以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其证一也。孔子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其答子张学干禄,则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为学,其证二也。大学之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证三也。”[3]可见孔子推行的学是修身之学,比起外在的浮华名利,孔子更重视主体自我德行的修养,正所谓其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而孟子在对“学”的这个命题上,他主张“自得”之学,在《孟子·离娄下》中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虽然孟子没有明确表示学习能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但是他强调学习是为了使自己有所收获,学习的价值在于个人的自我满足。荀子更是总结了二者的看法,在《劝学》中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通过“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两者之间对比,强调“学”的内在价值核心——自我人格的完善。“学以为己”的观点体现在儒学大师的真知灼见中,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更是十分推崇“为己之学”的教学理想,认为“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4]朱熹这种注重修养,求得道德学问的治学目标成为其课程思想的内核,更重构了儒学的人文信仰。
(二)佛、道思想的兼容
朱熹在专注于儒家之学前,曾流连于各种思想之间,尤其是对佛、道学说的学习,无论是从师承渊源还是家学传承,朱熹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朱熹早年泛滥百家,出入佛老,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5]更是在《上孝宗封事》中明确表示自己“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6]从朱熹的早年学习经历来看,对佛、老学说可谓“求之亦切至矣。”“为己之学”作为朱熹课程思想的精神内核,反映了朱熹对学子学习之道的价值选择。在朱熹与朋友的论学书札中就曾提及“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7]又云:“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7]朱熹在探索“为己之学”的途径时,却“不得其要”“未得其处”,在其“出入释老者十余年”后,朱熹以“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为宗旨的办学根本作为“为己之学”的门径。“不远复”即通过反观自省自身的言行以达到个体修身的目的,朱熹用“主静观复,修厥身兮”概括其核心内涵。在朱熹看来,“不远复”与道家的“主静观复”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朱熹将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主静观复的修身功夫与儒家“克己复礼”的修身途径统一起来以此进入“为己之学”的门户[8]。朱熹认为“为己之学”的精髓就是通过学习达到“明人伦”的目的,也就是“向天理”的回归。而学者如何达到天理的回归呢?朱熹认为“须是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9],而“尽人欲”的道德要求与佛教的“禁欲”思想息息相关。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新旧“中和之悟”,亦是吸收佛禅“明心见性”而达致的,而“中和之悟”的本质内涵即个体心性涵养和道德履践的统一,而这一内涵也成为朱熹“为学”的重要培养路径。除此之外,作为实现朱熹对学子理想人格培养的实践基地——书院也体现了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书院的设立就是基于朱熹对于佛教僧院的理解,佛家的戒律也影响着朱熹对于书院学规的设置,以及自由会讲的讲学方式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二、朱熹“为己之学”课程思想的内涵
朱熹将自己的理学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课程理论中,在《朱子全书》中提到:“小立课程,大作功夫。”[9]这句话里就蕴含了朱熹对于课程的见解。“课程”是指课业的发展,也是指个人学识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要为课程设置目标,并且下功夫去实现。朱熹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通过学为自己的学习动机以达到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为己之学”的课程理论。
(一)课程目标
科举从隋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宋代逐步完备,科举的影响也在社会上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不良学风。对于读书和科举的关系,朱熹认为“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5]朱熹以“三七分”的比例来协调科举与读书之间的相互冲突,也从侧面反映他十分不满当时科举制的科目设置、考试内容以及学子们将其作为追逐名利的工具,正如其所云“学者之病在于为人,而不为己。”[7]他反对当时社会上学子们形成的“以科举为为亲,而不为为己之学”的读书观[5],认为学子们的学习是为了主体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追求功名利禄,而应该是对主体自我的肯定,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朱熹十分推崇“成己成物”的治学逻辑理路,以达成“仁知统一”的教育标准,这也符合儒家一直对于培养目标的要求,正如他曾告诫学生所说的:“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正当学问“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而是从个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成己”境界推至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物”境界[6],而这一学问价值追求也成为朱熹课程思想的目标。
(二)课程类型
朱熹根据个体发展的阶段,将学校教育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学事”型的小学阶段及“明理”型的大学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为学生安排不同的课程内容,也体现了他“为己之学”的治学价值取向。朱熹认为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小学的教育任务是“圣贤坯璞”,是打基础的阶段,必须抓紧抓好。课程内容安排上应该是以“学其事”为主,他要求儿童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必须进入小学学习,正如其云:“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4]通过这些简单的知识学习和儿童具体行为训练着手,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小学》开篇中朱熹也提到:“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10]通过日常行为习惯的培养,使学生懂得基本良好的道德规范,儿童通过“学其事”来为成为“圣贤”做准备。朱熹认为十五岁以后学生则进入大学阶段,大学的学习是在小学阶段上的进一步深造,在教育内容上要“明其理”,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培养其成为“圣贤”。他说到:“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4]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学生能够达到“明理”,从而达到儒家所要求的目的“止于至善”。“正心修己”立足于主体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在此基础上达到“治人之道”,以此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培养目标。朱熹明确大学课程的学习不是将“声名利禄为归极”作为人的目的之源,而是通过“明理”的学习完善个体的人格,达到“圣贤”的目标,然后推己及人,实现“内圣而外王”质的飞跃。
(三)课程教材
朱熹在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对教材的编写,他根据人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将教育分成两个阶段,而在这两个阶段他也提出使用不同的教材来促进学生的发展。朱熹认为小学阶段的儿童处于“智识未开”的状态,所以他编写的启蒙教材是符合这一阶段儿童智力特征并能让儿童体会儒家伦理道德的读物。其所编写的《小学》一书分为内外篇,道德教诲是这部书的主要关注并充斥在这本书前后,内篇有四个纲目分别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则是古代圣贤的嘉言、嘉行。目的则是为了儿童“明伦”,即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有序、朋友之信,也就是他在《小学》开篇提的“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教导儿童以“明伦”来立心也即为“为己之学”立志。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童蒙须知》来规定儿童的行为习惯和礼仪规范,比如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等作出了具体规范,以便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学习习惯。朱熹编写的启蒙教材反映了朱熹“为己之学”的精神,这些内容不仅是为了儿童的识字学习,更是为了儿童提高自我修养,涵养德性,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朱熹为大学阶段的学子重新编著了《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和各级各类学校必读的教材,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长达数百年,颠覆了宋以前以经学为主的科举教材选择。正如杜成宪教授所说:“《四书》 的出现成为中国传统学校课程发展到宋代的又一重大变革事件”[11]。朱熹编著《四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修身成己”的治学精神,他在《朱子语类》中曾论述过读《四书》的必要性,“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果然下功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切。”[5]其次,他根据《四书》的特点定下了修读《四书》的顺序,“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5]在朱熹看来,《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论语》是修身之根本,“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孟子》则“教人多言理义大体”,《中庸》则讲解儒学之根本做人之道。这种阶梯式的教材安排次序步步推进教学内容的深入,循序渐进地促使个体“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抉择而修持耳”[7]。《四书》强调以完整而且道德的态度追求知识,深深影响了中国儒家学者乃至其他宗教的学者对学习目的所抱持的看法[2]。朱熹将《四书》作为大学阶段所必须要读的教材,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他“为己之学”的治学追求。
三、朱熹“为己之学”课程实践基地——白鹿洞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私学的代表,其发展进入黄金期则缘于南宋理学大师为弘“己道”而纷纷以立书院作为自己讲学的主阵地。朱熹作为书院发展的中坚力量,主持修建、讲学于多家书院,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白鹿洞书院。朱熹将白鹿洞书院作为实现自己教学理想的机构,将“为己之学”的课程理念贯穿于白鹿洞书院教学实践中,开创了“为己之学”的书院精神,并成为后世书院坚持和传承的纲领要求与核心精神。
(一)为己之学的理想机构
宋朝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使官学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随着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学子们求学的目的逐渐功利化,官学教育成为了学子们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针对学子们汲汲于名利的社会学习风气,朱熹通过修建白鹿洞书院来弘扬“己道”,以此扭转当时“钓声名取利禄”的士风。在他为书院修订学规时对自己的办学做了一番解释:“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7]朱熹明确地批评了当时社会“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规劝学子们“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强烈反对学子们“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的学习价值取向。同时这一院规再次重申了书院“为己之学”的精神,提出书院应将“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作为治学的核心,恢复儒家道统的根本旨趣“明德修身”。朱熹认为当时的官学教育是为了科举服务,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指出“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不暇深究义理”[7],这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为己之学”的精神。“中国书院教育的理想是‘为己之学’或‘自得’,书院成为维护‘为己之学’的理想机构,正也是朱熹提倡‘为己之学’的同时。”[2]白鹿洞书院的重修正是朱熹“为己之学”理念的体现,他主张书院应该成为个人“明义理修其身”的机构,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场所。
(二)修己安人的课程标准
为了使学生能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朱熹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课程的标准,这一揭示针对修身、做人、治学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阐述。其一,学子如何“自修身”?朱熹认为当时社会中学子“诵数虽博,文词虽工”,但“只以重为此心之害”,因此他提出三要作为修己的标准,贯穿学问始终,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7],以此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之本,重诉儒家对人自身内在价值的呼唤。其二,朱熹明确了教育的目的——明人伦,他提出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作为“五教之目”,这一纲目要求个体从关注自身修养的“内化”而推至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外修”,由内而外,在完善个体自我德行的同时践行个人社会责任,达成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其三,关于治学,朱熹提出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治学顺序以“穷理修身”,强调学问思辨行的为学顺序,促进治学与修身的统一,为学子的“穷理修身”指明发展途径和具体的学习路线。朱熹将修己安人的课程标准作为明理修身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将治学态度和道德要求结合起来,规范学子们的道德行为,从而使学子们达到“圣贤”的标准。
(三)知先行后的求学原则
在儒家思想体系上,知行问题主要是道德知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在朱熹的思想中知行问题主要是指致知与力行的关系[12]。他在《语类》中曾论述过知行问题:“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5]在朱熹看来知先行后是指伦理学上的致知与力行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先要了解道德知识才能履行道德行为。所以朱熹在治学顺序上,他强调学思问的同时也强调力行,在致知之后力行,由内到外,最终达到“学为圣贤”的标准。“圣人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7]朱熹认为书院的教育在教会人“义理”之后需要将其履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内向外地履行道德认知,一方面将义理诉诸在日常生活中,达成情感与理性的融合;另一方面避免了义理成为空空之谈,将为学与做人融为一体,促进自我德行完善。“学以为己一定是身体力行的,即必须把学到的东西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举止中,而不能仅仅是作为显摆自己或者换取名利的资本。”[13]“致知”并不是学习的终点,最终还需落实到力行中,追求个人修养的完善并履行在生活实践上应该成为学子的求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