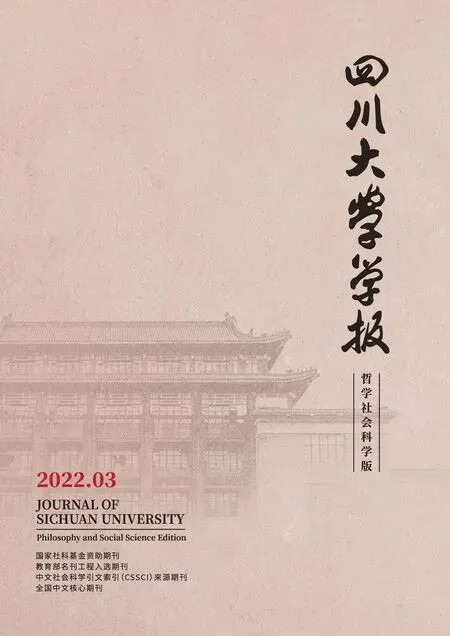何以批判?
——对这个问题的康德式回答
2022-12-06丁三东
丁三东
批判是当代哲学的常见词,被冠以“批判”之名的哲学作品数不胜数,批判一词就仿佛是个自明的概念。
初看起来,哲学中常见的批判与日常生活中的批评明显并不等同。老师批评学生作业马虎,妻子批评丈夫游手好闲,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乱丢垃圾,把这些句子里的批评换成批判,似乎就言重了。因为,哲学的批判针对的基本是群体的普遍现象和个体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所谓对事、对理不对人。直接针对个体的批判往往意味着一种不正常的权力滥用。不过,两者却有一点是类似的,即都表达了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否则,就不是批判或批评,而是赞颂了。
然而,“否定性评价”是批判的唯一含义么?我们又凭什么否定一类现象或某种思想观念?换言之,我们何以批判?我在这里用“何以”表示的意思是,我们凭什么可以进行批判?我们批判行动的根据是什么?用英语表述就是,On What Bases Could A Critique Be Made?
我在这里尝试一般地讨论批判的根据,基本不涉及对特定思想观念的辨析,并且,我将借助康德的思想资源来讨论。不过在讨论康德之前,有必要先讨论福柯对康德的一个批评,因为它直接构成了我们肯定性地运用康德批判构想的“绊脚石”。
一、福柯对康德的批评
福柯于1978年5月在法国哲学学会做了一场题为《什么是批判?》的讲演。他注意到,西方现代早期(约15-16世纪)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出现了一个普遍的趋势——尽管它实际上分散地出现在各个领域——它涉及“某种思维、言说和行动的方式,某种与实存的东西、与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与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的关系,还有某种与社会、与文化、与他人的关系”,他把所有这些统称为“批判的态度”。(1)Michael Foucault,“What Is Critique?,”trans.by Kevin Paul Geiman,in James Schmidt,ed., What Is Enlightenment? :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 Century Ques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382.福柯把它定性为现代早期人们对源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治理(governmentalization)的抵制。曾经,根据基督教的基本构想,人的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得到救赎,他的整个生活世界都围绕此目的展开,因而他的生活全面地受到牧领的治理。但到了现代早期,人们“不愿被治理”,转而对传统生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为了把这个一般性的模糊描述具体化,福柯提出了观察批判态度的三个历史锚定点(historical anchoring points):第一个锚定点是宗教领域的批判态度,人们拒绝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主导权,发展出与《圣经》的另一种关系;第二个锚定点是法律领域的批判态度,人们否定传统法律的公正性,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然权利理论;第三个锚定点是面对所谓权威真理时的批判态度,人们不再简单地接受权威的说法,发展出了现代科学。“《圣经》,权利,科学;著述,自然,与自己的关系;教权,法律,独断的权威”,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现象中,福柯识别出了一种统一性的批判态度,它构成了权力、真理和主体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网。进而,福柯总结说,“批判就是这样一个运动,通过该运动,主体赋予它自己以权利,去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去质疑权力的真理话语。批判是自愿的不臣服的艺术(the art of voluntary inservitude),是反思性的不顺从的艺术(the art of reflective indocility)”。(2)Foucault,“What Is Critique?,”pp.385-386.
在我看来,福柯对现代早期批判态度的观察是敏锐的,我们还可以把他提出的这三个锚定点更明确地指向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3)“事件化”(eventualization)也是福柯在该演讲中着重强调的分析方法。第一个锚定点指向的是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反对传统的天主教组织,不认可教士对教义解释的主导权,而是强调人作为主体直面《圣经》和信仰本身的能力,由此塑造了现代形态的信仰。第二个锚定点指向的是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现代早期自然权利理论思潮,它否定基于神权的君权和法律规定,通过区分法律(lex)和权利(jus),从而把自然法(lex naturalis)阐发为自然权利(jus naturale),并把后者归结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权利的自由,由此塑造了现代形态的政治和法律。第三个锚定点指向的是以伽利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研究,它不再简单地接受传统的权威说法(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宇宙模型),而是通过提倡对权威的普遍怀疑,运用逻辑推理和实验检测来探求真理,由此塑造了现代形态的科学认知。实际上,按照福柯的提示,我们还可以在其他诸多领域发现这种对原有传统的批判态度,例如艺术领域著名的古今之争。(4)关于“古今之争”中的批判性问题,参见张颖:《古今之争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美育学刊》2017年第1期。
福柯上述思考最重要的特点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特别是从权力分析的角度来定义批判,这也是福柯学术研究的通常角度。无疑,福柯的这个思考角度有它的限度,因为权力分析终究不是唯一的角度,在有些领域——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它甚至很难说是优先的角度。(5)这也是为什么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尽管对科学哲学形成了重要补充,但它对科学的解释总有隔靴搔痒之嫌的原因。特别是当它把科学发现的事情激进地还原为科学家之间的权力争斗之时,它无视和消解了科学知识内在的逻辑和客观性标准。但福柯的权力分析角度又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政治权力是对人的生活世界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在有些时候有些人类群体中,没有这个“之一”),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往往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而如果我们接受源自赫尔德、或许通过黑格尔才更为人熟知的“时代精神”构想,(6)我对这种简单的总体概括思维持谨慎态度,因为它往往忽略了真实历史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以及发展非共时性。则福柯对现代早期“批判的态度”的描绘的确是抓住了现代思想的基本情态(mood)。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的著名段落中对此也有生动的描绘。(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页。在此我们可以注意黑格尔使用的一系列动词,例如“决裂”“葬入”“拆除”。
而任何对现代“批判的态度”的谈论都绝不可能不谈到明确提出了“批判哲学”的康德。所以,毫不令人惊讶地,福柯在这篇讲演中对康德谈了很多。他赞誉康德的批判哲学是“高尚的事业”(the lofty Kantian enterprise),并认为他自己在此演讲中对批判的定义与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的定义没有什么区别。他突出了康德启蒙定义中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来的“决心和勇气”。他也注意到了康德的启蒙思想与其批判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福柯的理解是:“对于康德来说,与启蒙相关联的批判会是对知识来说的东西:……总而言之,批判会说,我们的自由并不取决于我们怀着或多或少的勇气所做的事情,而是取决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及其限度所具有的想法,因而,正是在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知识的时候,我们将能够发现自主原则,我们将不会再听到‘服从’;或者更确切地说,‘服从’将建基于自主本身之上。”(8)Foucault,“What Is Critique?,”p.387.
但正是在这里,福柯对康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康德把批判的首要任务确定为对知识的理解,实际上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批判的窄化;(2)康德的启蒙主张与其批判事业之间存在着某种“下降”或“后退”,因为,批判哲学对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制,完全可能与启蒙本来要反抗的他律治理同构共谋:在理性能力的范围内可以自律,但超出此范围,就得要接受某种治理。因而,如果说启蒙要求的是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则批判实质上所做的乃是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9)福柯的原话是,“批判的根本功能将会是在我们可以简称为‘真理的政治’的游戏中的去主体化”(Foucault,“What Is Critique?,”p.386)。在此,福柯是从其政治效应的角度来看待康德为知识划界的做法的。简言之,福柯实质上认为,康德的启蒙分析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批判计划则是可疑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于是,福柯要接续康德的启蒙主张,改造康德的批判概念,明确批判的“反抗治理”这一含义。这一思路在福柯1984年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得以延展。该文接续康德的启蒙旗帜,把康德“以必然性界限形式展开的”知识批判转化为以某种可能性逾越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
从康德哲学阐释的角度看,福柯对康德的批判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两组问题:(1)由于福柯写下了《什么是批判?》和《什么是启蒙?》两篇作品,而康德明确写就的只有《什么是启蒙?》一篇作品,这就给人一个错觉,康德对什么是批判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提法。因此,需要探究的第一组问题就是,在康德的构想中,究竟什么是批判?康德是否真如福柯所言,把批判窄化成了对知识的形而上学分析?(2)福柯指责康德的批判构想的实质是去主体化的新型他律治理模式。因此,需要探究的第二组问题就是,康德的批判构想是否真是去主体化的?它是否真会支持他律的治理模式?进而,我们能否从康德哲学出发阐释出一种对何以批判的回答?
二、康德所论“批判”的两层含义
康德有没有对批判作出明确的定义?一位只了解福柯作品的人很可能会以为康德没有。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对此有意无意地含糊其辞可能也会加深这个错觉。(10)福柯的相关表述是,“无论如何,相对于这一启蒙,康德会如何定义批判?或者,无论如何——我不宣称要把握康德在哲学上严格的批判计划是什么(在诸位哲学家听众面前,我可不打算做这个事,因为我自己不是个哲学家,我勉强只算是批判的学者)—— 一个人如何能够在与该启蒙的关联中安置批判”?Foucault,“What Is Critique?,”p.387.然而,任何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的人都会知道,康德明确界定过批判。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的一个脚注中,康德观察到他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1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这正是福柯同样观察到的现代早期的“批判的态度”。在这个脚注以及它对应的正文段落中,康德也提到了福柯讨论批判态度时的三个锚定点,即宗教、政治权力和传统权威理论,它们都受到了人们以理性为旗帜的怀疑和批判。这里的“批判”体现为理性“自由而公开的检验”。这也是康德后来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倡的“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12)康德:《康德文集》第八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这个脚注里批判的含义与福柯所言的“自愿的不臣服”和“反思性的不顺从”是一致的。实际上,福柯在其研究生涯中,一方面对压迫性的权力进行了各种理论批判;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各种公开访谈和辩论,这些都是启蒙运动中典型的批判行动在当代的接续。
康德并不否定他的同代人以及后来福柯所主张的那种批判,他只是把批判推进了一个层次。如果说在康德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凭借理性进行着批判的活动,那么理性本身又凭什么进行这样的活动?康德写道,这个时代对理性本身发出了“吁求,要求它重新接过它的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那件任务,即自我认识的任务,并委任一个法庭,这个法庭能够受理理性的合法性保障的请求,……这个法庭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理性的批判”。该“纯粹理性的批判”的任务是,要确认理性有权进行批判。因而,康德紧接着说明了这种更深层次批判的含义,“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4页。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句话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但它提到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显然不只涉及理性的认知能力,不只涉及知识,它还涉及理性的其他能力,包括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讨论的理性的实践能力以及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讨论的情感感受能力,它们共同构成了康德的“批判哲学”。而在康德哲学著名的自我概括中,“我能够知道什么”也只是他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此而言,福柯指责康德把“批判”的含义窄化为仅仅针对知识,这是不成立的。
“批判”(Kritik)从词源上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的kritikós一词,其含义为“分辨要素,作出判断”。不过,18世纪早期的人们把这个词作了一种新的使用,它最初出现在文艺领域,指对文学艺术作品作出褒贬评价,后来这种批判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领域。这两种含义的分别在德语里不太明显,而在英语里有时候会专门用不同于critique的criticism表示后一种含义。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所主张的,以及他所肯定、康德本人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主张的批判乃是后一种类型的批判。而康德的“批判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则更近于批判一词的古典含义。简言之,在康德这里,批判有两层含义:前一个层次的批判——康德同代人的批判——指向的是理性运用于其上的各种事物;后一个层次的批判——康德自己独特的批判——指向的则是理性本身。除了对象上的分别之外,两个层次批判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前一个层次的批判主要是对各种对象的怀疑性审视和否定;后一个层次的批判则主要是一种对理性诸能力本身的辨析和厘定。并且,在康德的构想中,后一个层次的批判是前一个层次的批判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在厘清了理性诸能力的要素、来源和合法性界限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根据地审视我们的认知、信仰、道德和政治实践,批判各种谬误的见解、盲目的信仰、不道德的行动以及侵犯权利的政治举措。
批判在康德哲学中有两层含义,这应该说是康德哲学的常识,我把它们分别称为理性的对象性批判和理性的自我批判。这也是我们常作的两种批判,批判不只指向我们之外的各种现象和观念,它还指向我们自己的行动和自己持有的观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何以能够进行对象性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两种批判的根据何在?我先来考察第一种批判,这是人们最常作的批判类型。
三、理性的规范性作为对象性批判的根据
观察一个对象性批判行动,它的结构很清楚也很简单:
批判标准
批判者…………………………被批判者
这里的关键在于批判标准。尽管批判者无须清楚地意识或领会他的批判标准是什么——例如,尽管一个人不一定说得清什么是好的,但他还是可以说“这个不是好的”——但倘若缺乏这个至少是悬拟的要素,就不是批判行动,而是开放式的探究行动了。
不过,这种批判立刻就面临一个困境:批判总是某个人作出的行动,因此,批判标准首先总是呈现为批判者的主观东西。然而,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当不同的人持有的批判标准不一时,他们对同一种现象或思想观念的评价也会不一,此时批判行动本身就成了陷入争议的事情。因而,批判所依据的标准不能仅仅基于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应当是他人也能认可的客观东西。
对于客观性问题,康德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处理路径,这就是他的先验思路。我把它勾勒如下:
(1)在康德看来,对人来说的客观东西绝不系于所谓事物自身的状况。因为,人只能以特定的方式去感受事物,以特定的概念框架去思维事物,在我们和事物之间总是有中介/居间者的。换言之,人不拥有直接通达事物自身的道路。——客观性≠事物自身性。
(2)客观的东西当然也不系于个人的特殊想法。各个人的经验际遇千差万别,由此导致的思想观念也各不相同,它们是纯然主观的东西,和客观性正相反对。——客观性≠经验主观性。
(3)尽管各个人在经验际遇上千差万别,但康德主张,所有人都共有一些基本的心智构造和能力,他称之为“先验的”或“纯粹的”,意为不是来源于经验的,而是逻辑上先于经验、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当然,“人同此心”在康德这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宣称”(a simple claim),而是一个“得到了演证的理论”(a demonstrated theory)。这个演证从一系列观察出发,康德发现,存在普遍的知识,存在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具备的道德理解,存在所有人都共有的审美感受。何以可能有这些状况?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在此只能设想,所有人在认知、实践、感受的时候都有着一系列先验的心智能力作为认知经验、实践经验以及审美经验的必要前提条件。先确定有B,然后确定只有在有A的条件下才有B,从而确定有A,这是康德哲学中先验论证的基本模式,其结论是:人的心智不纯然是经验的产物,它至少有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共同的先验要素成分,正是后者才使得人不同于其他的存在者,才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康德把它们泛称为理性。
(4)进一步地,在康德的构想中,理性绝不只是进行情境比较的推理计算能力,它根本上乃是一种本源性地产生纯粹概念和原则的能力,这些概念和原则作为最底层的形式框架规定和指引着人的认知、实践和感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讲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己的实践立法。也正由于人是这个意义上的有理性者,人才成其为支撑着“对象”(Objekt)的“主体”(Subjekt)。——客观性=先验主体性。
按照以上康德的先验思路,对象性批判的根据在于,批判所依据的标准最终根源于理性所产生的概念和原则,它们具有一种特别的规范性。按照拉尔夫·威基伍德的主张,(14)Ralph Wedgwood,“The Unity of Normativity,”in Daniel Star,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asons and Normativ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1-25.规范性是某些概念的一种特性。他通过对一系列相关语言现象的分析指出,这类概念的规范性考虑到了一切事情的实践规范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在有些情况下的“应当”,而是在一切情况下的“都应当”;此外,这类概念也是指引着我们进行实践推理,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最终理由辩护的概念。在康德这里,理性所产生的概念和原则构成了人的认知和行动的先验条件,人的一切认知对象和实践行动只有在它们之下才得以可能,因而它们对前者也构成了最终的理由辩护,就此而言,它们正是威基伍德所论标准的规范性概念。
科尔斯嘉德早就充分注意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规范性特征。她把规范性视为道德概念对人的实际行动的要求,道德概念对人的道德实践和心理具有一种约束力。它们不同于对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心理的充足原因解释,而是对之的充足理由辩护。这种辩护是从行动者的第一人称立场作出的;它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它直接成为行动者如此行动的理由;它最终会关涉行动者的自我认识,“我是谁?”科尔斯嘉德讨论了关于规范性的四种构想,包括唯意志论、实在论、“反思认可”以及自律主张。她认为,反思是人类的本性,人能够把自己的知觉、欲望等东西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加以审思,基于某些理由而接纳或拒斥它们。这在规范性现象上的体现就是,如果我们在反思了一种道德理念之后,依然愿意认可它的要求,则它就是规范性的。在康德的自律构想中,人对自己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身份定位使得人的理性所产生的概念和原则成为人的种种行动的最终规范根据,为它们提供最终的理由辩护。科尔斯嘉德把康德的道德规范性构想最终确立于康德的人性构想:“人是需要对她自己的身份具有一种实践构想的动物,关于她是谁的这一构想对她而言是规范性的。”(15)Christine M. Korsgaard,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23.汉译参见科尔斯嘉德:《规范性的来源》,杨顺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如康斯坦丁·波洛克所论,尽管康德本人从未使用过“规范性”(Normativität)这个术语,但康德批判哲学所论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本源的规范性理论。在认知的语境中,先天综合判断构成了数学和经验认知的根本规范。在道德的语境中,它们决定了我们行动准则的有效性。而在审美的语境中,它们则决定了我们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有效性。“把这些不同的语境统一起来,正是先天综合判断阐明了我们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判断的有效性,并在这个意义上为‘理由空间’提供了框架”。在波洛克看来,规范性特征不同于建构性特征。“它们(先天综合原理)对有些类型的判断来说是建构性的,对运用其认知能力——理性、知性和判断力——作出那些判断的有限推理者来说是规范性的。……这些原理是建构性的,因为,若不服从原则,就不会有那种给定类型的判断,但它们也是规范性的,因为,我们可以作出不能算是那种特定类型的判断,但这些判断依然是某种类型的判断。因此,我们依然在做着形成判断的活动,我们只不过错误地做出了判断”。(16)Konstantin Pollok,Kant's Theory of Norm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p.3,10.
的确,在康德的构想中,理性产生的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建构性的功能,二是范导性的功能。前者规定了事物的所是,后者规定了事物的应是。从这个思想出发,我们也可以把对象性批判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批判所依据的标准刻画了人、事的所是或本真状态,被批判者偏离了它,不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非,因而受到批判。第二种类型是,批判所依据的标准刻画了人、事的理想应是,被批判者尚未达乎该理想情形,尚在趋向理想的途中,因而受到批判。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例子,从许多学者看重的康德定言命令“目的表达式”中引申出这种类型的批判:如果一种社会现象或思想观念不把人当人,不尊重并维护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所是以及人由此而具有的人格和尊严,则这种行动就要受到批判。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例子,尽管人的非社会性的欲望和利益追求在社会中的对立促成了合乎法则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促成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在普遍历史理念的视角下,它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终究要走向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以至最终建立起一种完善的全人类公民宪政。(17)参见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38页。
小结一下,对于对象性批判,康德启示我们的是:一个人所作出的对象性批判若要客观合理,他就得超越个人的主观偏好,他的批判标准得是最终源于理性的普遍概念和原则。这些概念和原则刻画了人、事的本真所是或理想应是,对于实存的人、事状态具有规范性的力量,对它们是其所非或未臻理想的状态作出了批判。
可是这样一来,批判者的批判眼光就需要不只指向对象,更要指向自己。如康德所言,理性不只要批判宗教、权力、权威等各种对象,更要批判理性本身,厘清理性的权利及其限度。在此,自我批判为对象性批判奠基,而且,唯有通过自我批判,批判者才能得以完成从经验个体到理性个体的转变,他的对象性批判之标准的客观性才能得以被确认。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自我批判何以可能?
四、理性的反思性作为自我批判的根据
自我批判是件困难的事情。一个人根据什么才能进行自我批判?
表面上看,自我批判和对象性批判似乎区别不大,在对象性批判中受到审视的是别人体现的现象或持有的思想观念,现在受到审视的只不过是换成了自己体现的现象或持有的思想观念。然而,最小的缝隙也是最难越过的,这里的困难在于,一旦某个东西被一个人所体现或持有,就会被打上“我的”这个烙印,会受到种种情感机制的“加持”,很容易自我肯定,自我强化,陷入“我执”。如何打破这种“固执己见”的机制?这是自我批判需要应对的艰巨挑战。
前文提到科尔斯嘉德对康德道德哲学的阐释,她强调了反思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性。“根据康德的观点,当每个行动的冲动向我们展示它自身时,我们应该使它服从反思的检验,看看它是否真地是行动的一个理由。既然理由据信是内在地规范性的,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个动机,通过确定我们是否愿意它成为对我们来说的法则,来看看它是否是个理由。我们的检验方式是问,行动的准则能否被意愿为一个法则”。“每个冲动在把自己提供给意志的时候,都必须通过一种规范性检验,然后我们才能把它采纳为行动的一个理由。……这种检验是一种反思认可的检验”。(18)Korsgaard,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pp.89,123.汉译参见科尔斯嘉德:《规范性的来源》,第101-102、141页。科尔斯嘉德这里阐发的乃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定言命令第一个表达式的意蕴。批判者总会持有某种批判标准,它最初呈现为批判者的主观准则,但批判者要对它作出有关其合理性的反思确认,然后才能将之采纳为自己行动的法则。科尔斯嘉德所释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人有意识地与自己拉开距离,仿佛灵魂出窍,旁观审视自己行动准则的合理性。
不过,康德对反思的构想实际上比科尔斯嘉德阐释的更加复杂。乍一看,反思呈现为经验自我返回自己的纯粹理性状态,依据后者来审视前者。它在自我的经验中体现为良知这个“内在审判的意识”——它是人的本质之一,是人的“本源的、理智的和道德的禀赋”,“在它面前,人的思想彼此起诉或者辩护”。但这种道德的反思绝不是反身而诚,回复本心这么简单。康德指出,表面上看,“良知的事是一个人与他自己的事”,然而,“把被其良知控告的人设想为与审判者是同一个人格,这是一种荒唐的表象法庭的方式;因为这样一来,控告方在任何时候都会败诉”。对于败诉的原因,我们可以援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所论人的自欺或自我美化、自我崇高化的自然倾向:“我们根本不能有把握地断定,确实完全没有任何隐秘的自爱冲动,藏在那个理念的单纯假象之下,作为意志真正的规定性的原因;为此我们倒是乐于用表面上适合我们的更高贵的动因来迎合自己,但事实上,即使进行最严格的审查,我们也绝不可能完全走进背后隐藏的动机。”(1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康德深刻地意识到,人的心灵深处乃是一个“深渊”(Abgrund),而不是一个最坚实的根据,而自我认识的历程乃是一场“地狱之行”(Höllenfahrt),而绝非明心见性之旅。(20)以上关于良知的讨论,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48-452页。
为了走出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这个困局,康德提出,良知在进行审判时要“设想一个(与一般的人,亦即)与自己不同的他者来作为他的行动的审判者……这个他者可以是一个现实的人格,或者是理性为自己造就的一个纯然理想的人格”。(2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49页。
在第二条出路上,理想的人格须要是一个“知人心者(Herzenskündiger)”,还须是一个做出某种审判,就确保相应的效应现实地发生的存在者。这样一个存在者只可能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洞察人的肺腑,才能在对个人作出判决之后保证人能够做就实际地做到。然而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康德哲学中的存在及其地位是非常暧昧不定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上帝从来不是人的行动准则的最高审视者和最终根据。相反,“对于作为至善的上帝,我们从何处得到他的概念呢?只能出于那个由理性先天地对道德完善性所拟定的、并与一个自由意志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结着的理念”。(2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35页。上帝的实在性乃系于自由的实在性。
因此,康德实际走上的乃是第一条出路,即诉诸一个现实的他者。这也正是定言命令第一个表达式中提出的可普遍化检验机制的做法:把“我持有的准则是一个客观的法则么?”转化为“当别人也这么做或这么对我做的时候,我是否愿意?”这个问题。在此,他人成为自我的反思镜子,自我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来鉴定自己行动准则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人的引入对自我反思的意义在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讨论普通人类知性思维三准则的第二个准则——“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时得到了更清晰的揭示:“这种思维方式不论人的自然天赋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多么的小,却表明一个人具有扩展的思维方式,如果他能够把如此之多的其他人都如同被封闭于其中的那些主观个人的判断条件都置之度外,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这个立场他只有通过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才能加以规定)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的话。”(23)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康德自我批判构想中的这一他人因素得到了阿伦特的充分关注。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揭示:(对康德来说)“理性不是用来‘孤立它自己的,而是用来与他人一起进入共同体的’。”阿伦特基于康德的思想,主张一种特别的批判性思维。虽然她强调,这种思维只有在与他人思维的接触过程中才能学到,但她写道,“批判性思维尽管依然是一项孤独的事情,但它并不把自己与‘每个其他人’割裂开来。无疑,它依然是在孤独中发生的事情,但它通过想象力而使他人在场,从而,它就进入了一个潜在地公共的、对各方开放的一个空间”。然而,由于阿伦特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一种孤独的行动,他人只是通过我的想象力才得以在场,因此我认为,她并没有把康德自我批判构想中的他人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她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模型本质上还是一种古典式的自我沉思模式。尽管她指出,“批判性思维的诀窍不在于一种极大扩展的共情(empathy),通过它一个人能够知道每个其他人内心实际的感受”。(24)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40,43.但想象力终究是有限度的,再强大的对他人内心的想象能力都比不上与他人现实的交流。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前文所引康德描述第一条道路时所说的“现实的人格”。
韦尔默同样注意到了康德所说的普通人类知性思维三准则中的第二条准则。他指出,在康德那里有着一种很强的先验唯我论色彩,“从概念上说,康德的先验主体是按照单称的模式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康德来说,我们的理论或道德判断的主体间有效性是由形式条件来广泛地保证的,这种形式条件要么是无须参照主体的本质上的多元性就能得到解释的,要么就把其他主体只是当作同一个本体自我的另一种体现。但如果是那样,从每个别人的立场上思维就等于是从一个纯粹主体的立场上思维,这种主体已经消除了一切属于经验的也就是肉体化的存在物的主体特质(情感、激情、生物学的和历史的限制,等等)。纯粹的主体就是先验的或本体的自我”。因此,韦尔默借助当代语言哲学思想,把康德的第二条准则做了语言维度的创造性阐释:“‘从每个别人的立场上思维’……意味着以一种使得我们思考和判断的东西能够被每个别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判断;而这又转而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压制或无视他人针对我们的真理要求提出的重要论证。”但韦尔默认为,康德的先验唯我论妨碍他看清问题的实质,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的立场,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忽视任何有效的论证或异议。因此,韦尔默提出了一种非康德式的转折。他主张,要想真正达成主体间性,就必须“通过发现现实的他人必定会说些什么。如果(像我前面已经论证过的那样)我们的语言资质是一种集体的资质,那么对于我们是否忽视了任何可能的异议的惟一可能的检验标准就是一种现实的检验标准”。(25)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98-99、121、122页。
考虑到康德已经提醒我们,从每个别人的立场上思维中的别人须是“现实的人格”,韦尔默的转折根本上很难说是一种非康德式的转折。不过,我承认,在康德那里,主体间性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康德式的纯粹自我本质上依然是单称的自我;康德哲学中蕴含的主体间性思维只有到了费希特、黑格尔,特别是哈贝马斯、韦尔默等人那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回到本文的话题,小结一下,对于自我批判,康德已经启示我们:自我批判绝不是通过在自己这里打转转达成的,而是通过进入与他人的共在中而达成的。人的自我批判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论理对话,交换理由,对批判的标准进行自我申辩和相互辩难。
五、何以批判?——简短的康德式回答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批判何以可能?基于康德的启示,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一种普遍现象或思想观念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乃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概念构想,它刻画了人的生活的本真所是或理想应是,对实存的生活具有一种规范性。而什么样的理念或理想才是合理的?这需要通过自我和他人共同进行现实的理性论理才能得到确认。无论如何,它绝不是通过一个人独自沉思或心证,抑或一群人独断地宣称或简单地相互肯定就可以达到的东西。
对于康德的上述启示,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尽管在康德看来,理性的功能有建构性的和范导性的两种,但他实际上似乎更加看重后者。倘若理性发挥的是建构性的功能,那就意味着,理性构想的理念和原则至少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得以实现,进入真实的历史生活。可这样一来,理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将是,给出一条通达这个未来的现实道路。然而,对康德来说,实践理性的语言标记号仅仅是“应当”,而对这条道路的合理构想能力也只属于反思判断力。因此,在康德那里,理性的概念和原则在面对实存生活时更多地发挥的是一种范导性的功能,批判的事情更多地是一种防御性的现实纠偏:一种现实的状况违背了“应当之是”,因而我们批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