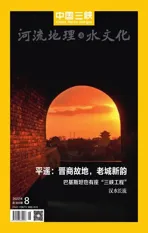汉水长流
2022-11-30艾子编辑王芳丽
文 | 艾子 编辑 | 王芳丽

湖北襄阳,雨后汉江上空现瑰丽晚霞。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沮水河畔傍晚时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初遇汉水
我的家乡在荆山深处,那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沮水。它发源于神农架脚下一个叫马坡的地方,水质清冽如玉,甘甜可口,声名远扬,古老的典籍上都有它的芳名。《山海经》卷三十二“沮水”条上写着: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景山……景山,即荆山首也。
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常唱一首童谣:
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下汉口。
开后门,摘石榴,石榴里头一包油。
为什么是“下汉口”,而不是到它离得更近的、顶头的管辖城市——襄阳?大人们说,汉口是省会哩,那样大的码头。不过粗通文墨后,我却琢磨出童谣里另一层隐秘的含义:沮水,与襄阳城区及流经襄阳的汉水并没什么联系。它在流经保康、南漳、远安、当阳四个县后,直接汇入了长江。
在沮水边生活了三十年后,我和家人来到襄阳生活。第一次站在汉江大桥上,打量汉水这条当地人口中的“大河”时,我激动得险些晕了过去。那是一个下午,夕阳即将跌进山的后面,最后一缕余晖照耀着大地,河里金黄一片,像是从上游流来的满满一河金子,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同时伴随着金属相击的声音。这是一条数倍宽于沮水的大河啊,足有五六里宽!恍惚间,我仿佛看到,这河转眼幻化成了一个身披金甲、平躺着的巨人,是逐日的夸父力竭后訇然倒下了吗?水声仿佛是他急促的呼吸!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和壮观一下子袭击了我,我浑身颤栗,心醉神迷,突然有了与它亲近的念头。
在以后的很多天里,我的脑海里一直是汉江那天的样子。我暗忖自己是否过于大惊小怪?只不过一条宽一点儿的河流,日落其上,满河碎金而已。但随着对它认识的加深,我倒庆幸自己曾被它震惊!这条获得过广博美名的河流,实在不止征服了我一人。《诗经》夸它:“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为它立传:“墦冢导漾,东流为汉。”在诗仙李白眼里,它好比珍贵的美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当代作家们把它比作“东方的莱茵河”“秦巴山地上的一条绿丝带”。
其实所有的大河都受到过人们的颂扬。水惠泽万物,人们逐水而居,枕河而眠,就是对它的热爱、追随和膜拜。只不过脚力有限,每个人只能走近与他生命有关的河流,并予以关注。
被它的声名吸引,在初遇汉水的整个初冬,便一次次地在它身边流连。通常是在午饭后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工作的地方离河边不远,那里有市县两级政府的航运管理局。正是在这附近,西行了1000 公里的汉水,接纳了从东北方向来的唐白河,然后折身向南奔流。这个季节,正是枯水期,大河已失去了盛夏的丰满,有些消瘦,露出一些河床。不过此时它与人的关系倒更密切了。人们从码头的石阶下到水边,爱垂钓的男人忙着钓鱼,小孩子忙着玩耍,捡石子儿……正午的阳光下,河面看起来像涂了一层釉,点缀着无数个金色和蓝色的斑点。这些斑点闪闪烁烁,不断变幻,又随着光线的强弱时隐时现,就像一个个谜语。说来也怪!在桥上看起来十分清澈的河水,走近了,却只能看清水面,至于水下,则昏暗到浓稠。但这种昏暗,让人觉得河流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仿佛在水面下藏匿着什么东西。

古城襄阳风光旖旎,南城北市,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是什么东西呢?水哗啦哗啦不应答。它才从峡谷对峙的上游奔涌而来,好不容易摆脱了两岸山峰的束缚,正活络着筋骨,惬意地往两岸铺排身子呢。哗啦哗啦,它悄悄使着劲儿,猛地朝我偷袭过来。霎时,脚下的沙滩上已漫上了水,鞋子也打湿了一半。我本能地后退了两步,再打量,它已款款地撤回了身子,撒着欢儿地向下游奔去了。
汉中汉源
汉水的源头在汉中。
在汉中,人们最引以为傲的名人是刘邦。城市最中心的地方——汉台区东大街26 号,汉中博物馆所在地,过去是刘邦做汉王时的王府。围绕着刘邦,还有一系列相关的景点:拜韩信为大将的“拜将坛”、张良隐居过的张良庙、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寒溪夜涨”……汉中人无不自豪地告诉世界:正是有了刘邦,才有了汉族、汉朝、汉字、汉服、汉文化……
如此想来,汉中不该叫汉中,该叫“汉源”——汉民族文化的源头!但2000 多年了,它一直守着“中”字,倒把“源”留给了一个小山村。
在离汉中市一百公里外的宁强县石钟沟,有条长约20 华里的溪流。它下游名赵家河,上游叫朱家河。这是条深沟,两岸青山对峙,树木掩映,野花吐艳,鸟语啁啾,清澈的泉水就在其间奔腾,溅珠喷雪,声若琴筑。沟尽头,一道瀑布飞流直下,旁边的崖壁上,镌刻着“汉江源”三个朱红大字。这是通过现代科技确定的汉水源头。因为守着汉水的源头,赵家河、朱家河所在的村——这块方圆公里的地儿,当然改名“汉源村”了。

湖北襄阳,“汉江洲岛”鱼梁洲成为市民戏水消暑好去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汉水就从这里出发,穿峡谷,过平川,沿途不忘接纳无数溪流,在1577 公里外奔腾入江。入江的那个地方,就是童谣里的汉口。
刘邦从汉中出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着义帝发丧的名义,派人联络诸侯讨伐项羽,逼得项羽垓下自刎。英雄霸王的一生落下帷幕!刘邦在长安建立大汉王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汉水承载了一个帝国的萌芽?
也许汉水感受到了刘邦的至诚,它源源不断地给汉朝提供着滋养。200 年后,在汉水中游,刘邦的后裔刘秀不满刘家江山被外戚把持,带着一批亲信起兵,夺回了祖宗的江山,延续着大汉国祚。又200 年,东汉风雨飘摇,刘邦的另一个已沦为靠卖草鞋为生的后代刘备却怀揣着复国的梦想。但他无权无兵无地,常年跟随的,只有两个异姓结拜兄弟。这般惨景,何年才能圆梦?又是汉水怜悯,将卧龙孔明赐给他,促成了三国鼎立。
汉水一泻三千里,除了汉朝和刘氏子弟外,还有几次机会与宽广的历史交汇。如南宋末年发生在汉水中游的那场著名的保卫战。方圆不到三平方公里的襄阳城,在吕文焕的指挥下,依靠汉水天堑、宽阔的护城河和坚固的城墙,拒元军长达六年之久。金庸曾以此为背景,写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郭靖、黄蓉夫妻曾与吕文焕一起,坚守襄阳城。金庸先生一生,并未到过襄阳,他是在史书中触摸并熟悉襄阳。那些简单的字里行间,藏着战火的浓烟、两军的对峙、匐地的士兵以及嗒嗒的马蹄声……它们搅成一团,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

陕西安康:凤堰古梯春色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汉水移民
从上游到下游,河流不仅流过空间,也流过时间。自有国家开始,无数人便因为战争,抛却故土,来到汉水沿线。
刘表驻荆州时,因为治理有方,荆州成了战火中的一片绿洲。北方人纷纷南下投奔,包括綦母闿、宋忠这样的学术大咖,王粲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包括诸葛亮这样的明日之星。至于普通百姓,则多达数万。
东晋末年,战火被氐人苻坚点燃。人们纷纷逃难。为安置流民,小皇帝司马曜于太元十四年(389)以襄阳为中心,划宜城、枣阳等地,侨置雍州。一批批关中人、河东人、蓝田人,拖家带口,翻秦岭,过武关,走商洛,来到汉水边的襄阳、邓州一带繁衍生息。今天,在襄阳市宜城县几个乡镇里,把“树”(shu)”说成“付(fu)、水(shui)说成匪(fei),和西安城的一些老人如出一辙。
将雍州之名从关中带到襄阳,并非东晋首创。更早的时候,楚国人已把沮水、重阳等名字从故土带到荆山深处。《水经注》卷二十七记载:“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口,沔水一名沮水。”楚国人曾在荆山深处的沮漳河一带生活,沮河之名,便是他们漂移了故乡河流的名字。
作为一个南北交融之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汉水沿岸,特别是中上游,永远不缺各地涌来的流民。明朝中叶,频繁的天灾,沉重的苛捐,使得河南、陕西等地的百姓沿汉水一带逃难,进入之前被禁封的秦巴老林。
移民们纷至沓来自有缘由。一是沿汉水山区特产丰富,盛产各种中药材,也是山兽野禽栖息的良好场所,锦鸡、果子狸、野猪、兔、鹿、獐等动物出没其间,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这里幅员辽阔,跨连数省,行政管理上鞭长莫及,人口在此地难以稽查,可以不必附籍,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南方人来了有水田耕种,北方人来了有旱地劳动,所以南北流民纷纷冒险涌入。
明成化二年(1466),二品官员王恕向朝廷打报告:“荆襄一带,山林深险,土地肥饶,刀耕火种,易于收获,各处流民、僧道人等,逞逞逃移其中,用强结庵立产。”巡抚荆襄的官员杨竣也上折子,称:“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清朝三百年,照旧有大批的移民进入汉水的中上游。相传吴氏在清中叶来到汉阴,他们带来了南方地区的水稻种子和耕作技术,于是在原本杂草丛生的大山小岭上,造就了美如画卷的凤堰古梯田。梯田绵延数十公里,又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大的如曲池,小的似新月,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每到盛夏,引得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拍摄。
鄂东人、江淮人、江西人、关中人、四川人、湖南人,包括福建、广东的客家人,因为各种原因,一批批沿着汉水,走进秦巴深山,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今天,仅在安康境内,就有江淮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湘语等各种声腔,形成了湘方言岛城、江淮方言岛、赣方言岛……他们喝着汉江的水,说着祖先的话,唱着远方的歌。
在安康旬阳县的蜀河古镇上,有位远近皆知的“麻城婆”。她瘪着没牙的嘴,为我唱起她童年爱唱的儿歌:
月亮长恶(眉)毛,叫我乞(吃)红桃。
红桃冇(没)开花,叫我乞(吃)热粑。
热粑冇(没)敞气,叫我去看戏。
看戏冇(没)靠(敲)锣,
叫我接嘎婆(外婆)。
嘎婆(外婆)冇(没)穿孩(鞋),
叫我用轿抬。
我听了,全身有如触电。从我打小,就将外公称“嘎爷”,外婆称“嘎嘎”或“嘎奶奶”的。这种叫法,在荆山深处并不多见。我在长大读了几年书后,觉得“嘎嘎”这个叫法实在太土,就随了大流,把外婆改称“婆婆”,转眼已快三十年。现在猛然从一个异乡人口中听到如此熟悉的称呼,怎能不生出感慨?
迁徙的地名
在我早先幼稚的想象中,汉水仿佛一条流着蜜的河流,在漫长的时间里,引得无数人前来。了解深了,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有无数人前来,也有无数人离开。抛开战争的影响,汉水本身并不是一条温驯的河流。很多时候,它几乎就是一个性情暴躁的角色。据资料显示,仅1822~1949 年的128 年间,汉江就有65 年冲垮干堤或主要支堤,导致大片良田遭淹没,村庄被冲毁,人民无家可归,只好四处逃生。那幅惨景,记在讨饭的渔鼓词里:
汉江发水浪滔天,十年就有九年淹。
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去上捐。
家破人亡骨肉散,背起包袱走天边。
我们祖先抵御灾难的能力那么脆弱。不管是大汉,还是盛唐,抑或宋元明清。每遇天灾,人们便拖家带口,四处乞讨。他们破衣烂衫,瘦骨嶙峋,面如菜色,走着走着就倒毙在地……这时候,常年供奉的各路大神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灾难与赈灾相伴而来。小到搭粥棚施粥,大到减免一地赋税、下拨救济款、治水、筑堤……只是某些做法荒谬到可笑。拿襄阳来说,襄、樊二城一水之隔,早已形成南城北市的“双子城”格局,偏偏襄城的大堤修建中央财政全额支付,樊城筑堤却分文没有,全靠官员自己想办法。究其背后的原因,乃因襄城这边是城,是朝廷基层政权所在地;而樊城是市——市井嘛,多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朝廷哪里顾得上!
汉水下游,流经的第一个县叫钟祥。这个县因为明朝的嘉靖皇帝在这里出生、长大,又建有他老爹的显陵而小有名气。
钟祥的汉水左岸,有个地方叫大柴湖。20世纪60 年代,为支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建设,近五万河南省淅川县人背井离乡,分批整建制,乘汉水而下,在岸边的大同码头上岸,到达指定的搬迁区——大柴湖。移民到达这里,带来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同时,还带来了故乡的地名:李官桥、鱼池、宋湾、罗城、武州……这些祖辈们起下的名字,藏着祖先回家的路径,寄托着世世代代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岂能不随着后代的脚步迁移?上游的地名因汉水的流淌再次向下漂移。

汉江钟祥段 摄影/陆秀梅/图虫创意

世界文化遗产钟祥明显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移民第一大镇”大柴湖参观,短短50 年,当年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已被改造得现代、整洁又富裕。但人们乡音未改,风俗依旧,说河南话,唱河南戏,吃捞面条,喝胡辣汤或苞谷糁,连婚丧嫁娶都与河南淅川一样,被称为“湖北的小河南”。带我参观的是个90 后女孩儿,也是淅川的第三代移民。她说:“我户籍是湖北的,人却像是河南的。不知我到底算哪儿的……”
与大柴湖隔汉水相望,是一个叫掇刀的地方。它因三国时关羽在此掇刀而得名,现在是荆门市的一个区。虽然离襄阳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并未到过那里。但在梦中,却无数次梦到过它!
我与它的联系仍然来自荆山。在故乡那块家族墓园里,有方青石墓碑,属于我长眠地下的祖父的祖父,也是我们这支血脉的“进山祖”。虽然石碑上的字多有漶漫,但仍勉强识得,有这样两处关键的信息:“祖居掇刀。后迁至漳西。”
“漳”指南漳县,因有漳水而命名。漳西泛指南漳县的西部,正包括我老家那个沮水边上的小山村。掇刀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其富庶繁华,不知比荆山深处要好多少倍。无法得知先辈为何选择这种迁移,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祖先确实把自己,也把后代从汉水带到了长江。而我,又迈着细细的脚杆,重新回到汉水边。
天色将晚,太阳慢慢滑下地平线,河面上开始升腾起一层薄雾,先前还清澈的汉水再一次变得昏暗,让人感到诡黠和神秘。注视着这条我长久亲近的河流,联想它身上近些年发生的大事——上游的“引汉济渭”、中游的“南水北调”、下游的“引江济汉”,我似乎窥到了它隐藏的秘密:陆地把宝贝深埋在肚子里,渴望人们发现,再为它们编年、立传,河流却对此不屑一顾。汉水和它的千万条支脉汇编的历史,迅疾而流畅,充满了迁徙的脚步,包括人类、生物,现在又加上了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