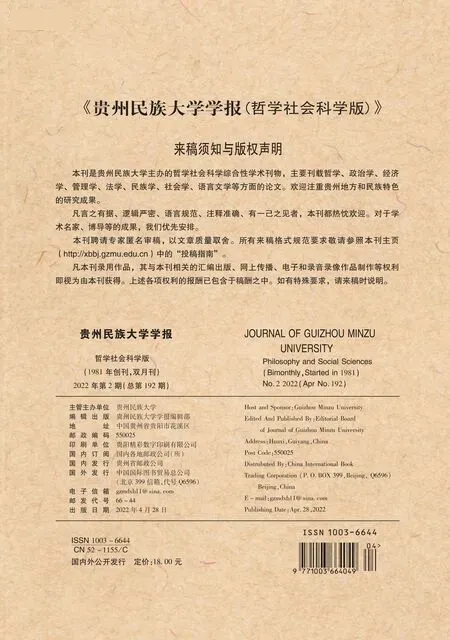从生活化到景观化: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实践路径分析
——基于婺源篁岭“晒秋”农俗的个案研究
2022-11-28刘爱华,邓冰清
刘 爱 华,邓 冰 清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乡愁安放的精神栖居之地,是村落民俗依存的重要场所,是村民居息的生活空间,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村落民俗也备受青睐,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本身就是民俗,而不只是在利用民俗”(1)刘铁梁:《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村落民俗作为旅游的资源或对象,蕴含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气息,在旅游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在旅游凝视的推动下,村落民俗的生活化逐渐“蜕化”为景观化,在保护村落民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文化内涵。“本真性”是一个建构概念,在乡村旅游实践中,景观化的村落民俗,丰富和拓展了原有文化内涵,扩充了其展示价值,激活了传统村落的生命力,不失为一种探索路径。
一、生活化:篁岭“晒秋”农俗的“原生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广阔的乡村和人口数量巨大的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以往的城镇化,一味追求粗放的城镇化率,重视农民进城上楼,未关注可能导致城乡分割的问题。一方面造就了大批“候鸟式”农民工,他们想融入城市,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刚性的科层制度、疏远冷漠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徘徊于城市的边缘,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即便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但依然感觉是都市的过客,没有归宿感,对故乡亲人的依恋愈加强烈”(2)刘爱华:《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城愁”与“乡愁”交织,同时,城市也由此产生了交通状况恶化、资源供应紧张、发展成本增加等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业产业人才流失、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农村整体布局严重破坏以及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等”(3)范东君:《农村空心化挑战及其化解之道》,《光明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3版。,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产业空心化、服务空心化、人力空心化及文化空心化等一连串负面连锁反应。当然,城乡分割加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广大乡村的破败,传统村落的消亡。据《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呈严重下降趋势:行政村自1986年至2011年,数量减少258 020个,平均每年减少10 321个;自然村自1990年至2013年,数量减少1 123 200个,平均每年减少48 835个。”(4)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传统村落是村民居息的生活空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精神场所,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凝聚、交融的物质载体。奇花异树、街道巷陌、亭台楼阁、戏台老井、庙会集市、民俗器物、传说故事、俗谚俚语、乡风习俗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构成了一个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文化形态,再加上生活其中的有创造力的村民,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村落民俗依托物质形态而存在,没有古街巷陌、亭台楼阁、民俗器物等物质文化遗产,村落民俗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失去了村落民俗,传统村落也失去了生气,缺乏生命力。
篁岭,位于婺源东北部,江西、安徽和浙江交界处,悬挂于石耳山脉。篁岭,古称篁里,山岭生长有方竹、水竹、苦竹、斑竹、紫竹、观音竹等,修篁遍岭,故又称为篁岭。清道光版《婺源县志·山川》载:“篁岭,县东九十里,高百仞,其地多竹,大者径尺,故名。曹氏世居。”(5)黄应昀、朱元理纂修:《婺源县志》,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篁岭,面积为7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徽式传统村落,为曹氏祖居地。明代宣德年间曹文侃由婺源上晓鳙迁至篁岭,是为始祖,村落至今已经580多年,人口繁衍近800人。
因篁岭地处赣、皖、浙结合部的边缘山岭地带,交通不便利,信息相对闭塞,近百年来既避过了无数兵燹战祸,也相应绕过了几次经济发展大潮,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也相对落后于周边地区。这种独特的村落地理地貌,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也客观上保留了大量徽式古宅、独特的民俗文化。在当代世界呼唤绿色生态环境、倡导绿水青山之际,篁岭以其具有层次感的山居村落、广阔的梯田景观、宝贵的水口林资源及独特的“晒秋”农俗,惊艳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晒秋”农俗源自篁岭所处的山区地形地貌,因“地无三尺平”,篁岭村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山区独有的一种晾晒农作物的农俗。“民俗是一种感性(为主)的生存活动,是普通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6)赵德利:《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页。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传承的生活文化。可以说,“晒秋”农俗是篁岭村民完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活哲学,是生活经验的沉淀与升华,他们限于山区的逼仄,就向天空“借”空间,在房屋的一楼楼顶眺窗上支出一排杉木,朝外一端顺着屋脊稍微往下倾斜,屋檐上树几个混泥土的砖墩,上面置一长铁管与杉木垂直,以承托晾晒农作物的重力。在杉木上面摆满晾晒朝天椒、篁菊、玉米、稻谷、芸豆等农作物的晒匾。因在相对陡峭狭窄的山岭间,大量徽式老宅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向上生长”,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色彩艳丽的农作物、斑驳的徽式老宅,在蓝天白云下很是壮观,蕴含丰收寓意,展示了一派素朴、饱满、艳丽、壮观的农村丰收景象。
篁岭“晒秋”(7)晒秋,有不同称呼,篁岭村汪志源老师说当地俗称晒桹、晒谷桹;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篁岭景区董事长吴向阳说当地叫秋晒。并非篁岭独有,在婺源其他地区及江南一些山区也有类似景象,如重庆市梁平区,广东省惠州市,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安徽省歙县石潭村、阳产村及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等,但规模度、集中度、落差度、美感度远不及篁岭。当然,篁岭“晒秋”农俗在开发前并没有什么名气,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姑”,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靓丽”。“晒秋”农俗产生是客观生活条件、生活环境造就的,村民生活在山岭间,缺乏平坦的晾晒农作物的地方,故而篁岭先民在结合村落布局、房屋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创造,在老宅二楼眺窗上设计出一个节省空间的“晒台”。这与其他地方直接在屋顶或地面上“晒秋”相比,更具生活性、观赏性和艺术性。当然,篁岭过去的“晒秋”并没有什么讲究,各种农作物甚至衣物都可以晾晒。也就是说,在开发前,篁岭“晒秋”农俗是村民的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智慧,富有生活气息,更具生活化,更富“原生态”。
从学理上来说,这种“原汁原味”的篁岭“晒秋”农俗,或者说生活化的村落民俗才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因为它体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原生境人”(8)“原生境人”,是指产生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民族或自然社区中的民众,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地、发祥地民众。参见赵纲:《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法律地位的价值分析》,《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与民俗器物、民俗文化水乳交融,展示了一种想象中的生活真实,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展示性、表演性。“在民俗文化回归乡土时,一方面对游客展演的民俗要真实,舞台化的过程中保持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居民真实的生活场景是最好的展演方式,因此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要保留。”(9)张颖:《后现代视角下民族旅游发展的困境与反思——以云南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例》,《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民俗旅游发展应有所限制,避免功利化,突出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生活化是村民生活的真实表现,也是村落民俗传承的基本要求,村落民俗的产生源自“原生境人”在传统村落这个独特空间生产、生活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生活形态,其传承也要求限定在村落群体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里,通过反复性的叙事,内化为村落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这种传承无需专业性知识,只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无需特别设计,只是其循规蹈矩的生活表达。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的快速消亡让这个理想更为遥远。乡村旅游成为传统村落、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如果仅仅致力于保护其“原生态”,僵化追求其“本真性”,致力于恢复村落民俗“原貌”,其日常生活的琐碎化、庸常化、单调化,其脱离现实生活的风化的“古朴性”,早已失去了生命力,往往很难吸引游客,让游客发现其亮点和独特性,其资源价值就难以发挥,乡村旅游也就失去了其独特魅力和吸引力,而村落民俗也同样无法挣脱被抛弃、被冷落,乃至走向消亡的命运,更别提其人文价值展示、深厚内涵挖掘。因此,在城镇化语境下,可以说生活化是村落民俗传承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最高要求,一种理想化想象。
二、景观化:篁岭“晒秋”农俗的重构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村落民俗生活化很难实现,而景观化,则成为村落民俗保护或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景观化,在消减村落民俗生活化内涵的同时,也更好表达了其生活属性,丰富了其呈现形态,因而也成为旅游景区模式化的“理想化”的景观生产方式。“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10)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景观作为物化了的世界观,在现实世界具有重要地位,景观化也就成为旅游景区甚至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篁岭“晒秋”农俗经过精心提炼及系列打造活动,其知名度、美誉度迅速提升,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成为“最美中国符号”。
篁岭村悬挂山崖间,最高点海拔485.9米,房屋建筑沿山岭凿岩而建,一栋栋徽式老宅镶嵌在崇山峻岭间,上下落差达近百米,富有层次感。且篁岭村民一直延续自古以来的“晒秋”农俗,具有很好的展示性,这为“晒秋”农俗、“晒秋节”打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篁岭村在开发前,却是一个“半空心村”,存在用水紧缺、交通不便、地质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在现代化语境下,城镇化快速推进,其居住价值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村民因此陆陆续续迁出了大半,村落日益空心化。为了保护这个古村落,2009年江湾镇人民政府、栗木坑村委会引入社会资本——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1)简称公司,下同。,参与篁岭古村的旅游开发。公司通过产权置换、土地流转等措施获取土地经营使用权,采取“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老建筑寄养”“村民返迁”等方式加强对篁岭古村的建设,并挖掘出在婺源地区独一无二的“晒秋”习俗,提炼“晒秋人家”概念,打造“晒秋节”品牌,经过一系列建构性行为,推动了篁岭古村的景观化,也促使其发生“蝶变”,从而“起死回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功打造了篁岭景区这个江西乡村旅游的经典样本。
“文化本质上是原生性与建构性的存在。原生性文化的挖掘与运用符合国家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要求,而建构性的文化则符合当代资源以资本实现耦合的市场性要求,文化建构与展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原生性文化与建构性文化的融合与贯通,使文旅融合发展既体现经济性,又显示其文化价值的张力。”(12)柏友恒、杨昌儒:《存在与发展:乡村振兴的优秀乡村文化符号及其价值空间逻辑研究——基于贵州乡村旅游资源的调查思考》,《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篁岭古村“晒秋”节庆品牌的打造也体现了原生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晒秋”农俗的挖掘是原生性的,而“晒秋”景观的生产是建构性的。通过原生性和建构性的共同作用,篁岭景区迅猛发展,蜚声海内外,获得众多很有分量的奖励和荣誉。2014年篁岭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收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最美中国符号”的美誉,2015年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016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胜地,2017年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超级IP村,2017年、2019年两度荣获亚洲旅游“红珊瑚”奖——最佳旅游小镇,2020年荣获携程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峰会“景区复兴贡献奖”等,还被网友赞誉为“世界最美村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
篁岭“晒秋”场景的集中、奇特、恢宏及其山居村落的高低错落、富有层次感,在婺源地区是比较独特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向阳在篁岭村考察时为这一素朴而壮观的丰收图景所吸引,“老百姓要解决晾晒农作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后来挖掘的‘晒秋’的概念,老百姓晾晒农作物,在自家屋顶上搭晒台,房前屋后挂晒、晾晒农作物的这种习俗,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摄影家、画家就已经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篁岭晾晒农作物的这种习俗,在婺源是比较独特的,既是一个农俗景观,也是一个人文景观,是可挖掘的、可提炼打造的一个亮点、一个特色”。(13)访谈对象:吴向阳;访谈人:刘爱华;访谈时间:2019年7月24日;访谈地点:篁岭天街邂逅你音乐吧。社会资本介入后,篁岭景区围绕“晒秋”进行了一系列重构活动:一是修复、搬迁徽式老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老宅120多栋,并异地搬迁来30多栋徽式古建筑,其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婺源三雕”技艺得到较好呈现,尤其是怡心楼,采用了“寄养模式”(14)“寄养模式”,是指“怡心堂”的保护模式。2014年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许村镇政府达成协议,由公司全额出资,将“怡心堂”整体搬迁至篁岭修缮保护,所有权仍归许村镇政府,公司则拥有经营使用权。“怡心堂”搬迁至篁岭后,名字改为“怡心楼”。,使徽式老宅得到保护,且更为恢宏、集中,俨然成为一个徽派古建筑博物馆。老宅古建筑的修复、迁入,使“晒秋”场所更为壮观、集中、唯美,“晒秋”农俗景观更为震撼、绚丽。二是规划村落整体布局。篁岭古村在开发前,街道布局凌乱,道路狭窄。在旅游凝视下,篁岭景区对街道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其设计为“三桥六井(塘)九巷与天街”的架构,即“三桥”为步蟾桥、安泰桥和通福桥,“六井(塘)”为五色鱼塘、方塘、尚源井、忠延井、霞披井和廉井,“九巷”为大丰巷(长120m)、担水巷(长178m)、添丁巷(长93m)、厅屋巷(长140m)、团箕巷(长40m)、五桂巷(长147m)、犁尖巷(长157m)、月光巷(长169m)和方竹巷(长128m)。村落架构以天街(长388m)为主轴,纵横交织、曲折蜿蜒,富有田园气息,使村落面貌发生“蝶变”。同时,引入茶坊、酒肆、篾铺、伞店、砚庄、邮驿等传统业态,使其与晒秋景观更为协调。三是加强“晒秋”农俗的设计。在景区开发前,村民对“晒秋”对象并没有特定要求,想晒什么就晒什么,景区开发后,“晒秋”成为一个专门化工作,有负责“晒秋”设计的管理人员、有具体操作“晒秋”的晒秋大妈,晒什么、什么时候晒都有讲究。“晒秋”所用原材料,有时也要向周边村民购买。而且,篁岭景区发展出四季“晒秋”理念,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等,一年四季延绵有序,“晒秋”成为一个丰收符号和文化景观,而不仅仅是一个农俗活动。四是打造“晒秋节”启动仪式。为更好打造“晒秋节”,篁岭景区对每年六月六的中国传统“洗晒节”进行重构,作为“晒秋节”的渊源,并将时间移置于立秋日。每年“晒秋节”,篁岭景区都会举办启动仪式,如2021年8月7日立秋时,篁岭景区在婺源民俗文化展览馆外广场启动了篁岭晒秋嘉年华暨第七届中国(篁岭)晒秋文化季开幕式。开幕式以“乡土、乡愁、乡趣”为内涵,围绕“庆丰收、晒青春、晒回忆、晒美好”为主题,活动分为五个篇章。第一篇章“万物皆可晒”,通过观看行进式晒秋快闪队伍、村长主题演讲、颁奖仪式、篁岭晒秋舞、蔬菜时装秀、青春活力热舞等活动突出嘉年华主题。第二篇章“瓜果创意晒”,通过“秀”晒秋大妈的“才艺”,打造创意晒秋场景,同时游客也可以在晒秋体验区进行晒秋,晒出自己想晒的图案或祝福语,展现果蔬创意晒的成果。第三篇章“青春活力晒”,通过设计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方式让游客参与推独轮车、吃西瓜、剥玉米、套南瓜等活动,展现乡村生活多彩性。第四篇“哇晒丰收宴”,通过长桌宴的方式,用晒盘盛放做好的花生、玉米、南瓜、芋头等晒秋农产品款待游客,营造乡村宴饮的乡土性。第五篇“山村奇妙夜”,通过灯彩秀,让游客感受流光森林和古村夜景。同时在众屋广场还有乡村迪斯科、复古老歌会、时光老电影、主题果酒趴等精彩活动,烘托乡村“夜生活”的精彩。五是注重“晒秋”节庆品牌的营销。结合创意“晒秋”图案设计,景区很注重热点营销、事件营销、借势营销等营销策略。如2014年国庆节前,景区抓住国庆主题,推出了晒秋大妈用朝天椒、篁菊、稻谷、白豆等,“晒”出长5.76米、宽3.84米的一面“国旗”。此次热点营销篁岭赚足了人气,国内外主流媒体纷纷转载,占据头版头条一周多,篁岭“晒秋”不胫而走,名声大噪。此外用农作物“晒”出的建军90周年纪念创意图案、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图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案、北京大学江西校友会庆祝北大120周年图案、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图案、庆祝“全面小康”图案、庆祝“建党百年”图案等所采用的热点营销策略,以及篁岭景区喊话成龙捐古建事件、篁岭景区“最美老板娘”事件等事件营销策略,极大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
“晒秋”农俗的提炼与营销,使村民原有生活方式逐渐演变为景观的一部分,一种生活化的行为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程序化、组织化行为,其文化功利效应凸显而本体性效应削弱。“对当代旅游业来说,任何景观都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被‘发明’的符号,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旅游需要。”(15)周宪:《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在旅游凝视下,为了增加旅游景区的吸睛指数,景观生产作用下的景观化现象在当前我国旅游景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城镇化语境下,经济发展依然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村落民俗保护也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景观化成为村落民俗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传统村落空心化、村落民俗急剧消亡的背景下,景观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行将消逝的村落民俗进行提炼、整合、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其一部分内涵,至少保存了其有效形式,在与消亡赛跑的抢救活动中,其意义仍是巨大的。过去“晒秋”农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是深藏山中即将伴随村落衰败而消亡的一种民俗文化,经过篁岭景区的抢救、挖掘、打造,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旅游景观,成为旅游业的一朵奇葩、中国乡村旅游的一个样本。因此,屏蔽其生存语境,苛求其“晒秋”农俗的生活属性,显然是过于理想化。正如一位负责“晒秋”工作的管理人员所说,没有旅游,篁岭古村或许已不复存在,更别提“晒秋”文化的传承了。(16)赵征南:《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叫晒秋,真的好美!》,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809/23/214247.html。这句话说出了村落民俗保护或乡村旅游的症结所在,通过旅游、景观化的行为,传统村落或村落民俗得以延续,尽管其展示价值远远大于生活价值,但它至少保留了另一种形式的村落民俗,至少可以让子孙后代有迹可循。
当然,景观化作为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实践路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鲜明,具有突出的功利价值,其负面效应也不少。景观化压缩了生活内涵,放大了表演色彩,村落民俗不再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种被设计的镜像化的手段,是被剪辑、被编辑、被展示的生活文本,如同室内的精美盆景,虽然枝繁叶茂,但离不开人的精心“伺候”,缺少了泥土气息,缺少了自我色彩和个性,也缺少了生命成长内在的奥秘。“‘被制造’的旅游景观常常因对当地人缺乏意义和价值而难以被认同或不被认同,在这一点上旅游景观很难与日常环境景观相匹敌,因为后者凝聚了栖居者的安全、依恋、怀旧等稳定的情感因素,是难以言喻的‘生活之爱’。”(17)赵红梅、李庆雷:《旅游情境下的景观“制造”与地方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被制造的旅游景观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是“他者”设计的一种符号,游客的旅游体验客观上不是接近而是更加远离生活真实。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景观化是否是村落民俗传承的唯一路径?在生活化与景观化之间是否有协调的空间?景观化中能否安放乡愁,融入更多的生活内容、生活絮片、生活气息?
三、关键点:如何看待“本真性”
村落民俗的景观化,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实践保护或传承方式,这涉及到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问题。“本真性”问题一直就是民俗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往往和“伪民俗”问题交缠在一起。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认为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麦克菲森(James Mac Phearson)出版的《莪相诗集》、德国格林兄弟(Die Gebrüder Grimm)1812—1815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和1835年出版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等伟大民间文学作品其实也是“伪民俗”,但也强调民俗学者不应先入为主排斥加以抵制,而应先接受这样的事实,并采用民俗学方法去研究它。(18)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伪民俗的制造》,周惠英译,《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那么,什么是“本真性”?美国民俗学会前主席艾伟(Bill Ivey)认为:“‘本真性’表示事物、人物以及活动具有真实、诚实、原始、未经污染以及热情的属性。”(19)艾伟(Bill Ivey):《美国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本真性”问题》,王文婷译,《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就美国民俗学来说,本真性问题尽管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这一概念的建构更为精致而复杂,至今仍被一些学者僵化地使用。
本真性话语是和民俗学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尚古主义等紧密相连的,“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异化的反思和反抗,这构成了学者的民俗研究和大众的民俗主义的共同根源”。(20)胥志强:《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根源、局限及超越》,《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从国内民俗学界来看,对“本真性”话题也一直争论不休,但纵观相关争论,其焦点略有不同,或者说其争论并未构成真正的对话,“本真性”保护论者针对的是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稳定性的一面,而反对论者则强调其活态性的一面。刘魁立早在2004年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一文中,就提出“本真性”话题,认为“一个事物的本真性既不可能脱离开特定的时空而抽象地存在;同时,也不能脱离开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来认识”(21)刘魁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并批评了不少民俗旅游过程中的“作秀”,导致民俗文化商品化、对象化、舞台化、碎片化的极端现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本真性”作了一个界定,“我这里所说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22)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认为本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灵魂,否则意味着它生命的消逝。他不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性,而是要求这种变异应在一定的限度内,要遵循其演变规律,不发生本质的改变。韩成艳对刘魁立的观点比较赞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落地,本真性理念就发挥着基本理论的作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失成败的参考标准。但她将“原生态”和“本真性”看成是一对姊妹概念,这种认识显然有失偏颇。(23)韩成艳:《从学术上拯救“原生态”和“本真性”概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陈金文也坚持“本真性”论调,认为要不要保持其本真性是事关“非遗”保护质量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排除了“本真性”原则,但他仍详细辨析,坚持认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强调保持本真性还是有道理的。(24)陈金文:《“非遗”本真性问题再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与上述论者观点不同,刘晓春则不认同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本真性”,并对此问题撰写了多篇文章。他认为民俗文化是活态的,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具有公共意义,地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等从各自利益出发,往往极力强化其真实的、本原的文化元素,并经过一系列符号化过程,逐渐使之定型、固化,从而建构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以梅州客家山歌为例,认为它是发展变迁的,很难用某个特定时空中的表演形态、口传形态、工艺品的形制、制作工艺等作为真实的版本或者本真的样貌。(25)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文中,刘晓春认为当前的非遗保护存在着保护者“原生态”想象和“非遗”传承的“活态”之间的矛盾,也充满着悖论,往往是“局外人”而不是“局内人”提出保护措施,“局外人”“局内人”各自对立,缺乏对话交流,“‘非遗’本来是‘活态’的,不断随时间、地点、情境发生变化,如果以某种看似科学的、客观的、‘本真性’的标准予以固化,则将扼杀‘非遗’的生命力,在本质上违反文化多样性的本意”(26)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并认为中国非遗保护的“本真性”概念是世界遗产的“原真性”概念挪用。同样关注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性的一面,徐赣丽以民俗旅游为例,认为民俗旅游满足了游客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游客关注的是民俗旅游产品质量带来的旅游体验,并不关注民俗是否是真实的,她对这种民俗文化传承持肯定态度,认为“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并没有丧失殆尽,而是被融进当地现代新传统中,并且新的地方(民族)文化被创造出来”。(27)徐赣丽:《民俗旅游与“传统的发明”——桂林龙脊景区的个案》,《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
总的来说,民俗学界对“本真性”问题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只是认识问题的视角有差异,保护论者关注的是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稳定性的一面,以确定保护的对象,即保护什么,而反对论者则关注的是其动态性的一面,即如何保护。也就是说,前者保护的是其不变的元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其可变的元素。其实,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存在变与不变的一面,变与不变只是其不同的“脸谱”,两者也是统一的,变化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只强调某一个面而忽略另一个面都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
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有时过于琐细化、庸常化、平淡化,往往让人难以接近、亲近,其保护或传承也往往因其失去时代气息而困难重重。篁岭“晒秋”农俗,作为篁岭村民的生活创造,生活化是其基本质素,其“本真性”应体现在其生活性展现上,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的民俗,在现实生活中,“晒秋”农俗仅仅是一种日常晾晒农作物的活动,缺少相机的“过滤”效果,其行为、场景并没有什么精彩或出彩的地方,也没有今天经过创意设计“特效处理”后的独特魅力。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晒秋”农俗作为地区文化一个亮点被挖掘出来,“晒秋”不再是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景区的一道风景,成为被设计、被展示、被欣赏的一个道具,也就是说其生活属性逐渐丧失,商业属性日益加强,即生活化让渡为景观化,这显然不是理想的保护目标。但我们也应尊重现实,由于用水紧缺、交通不便及地质灾害等因素,篁岭古村早已半空心化,早在古村开发前,村民已经陆续搬迁,在2002年前自动搬出30多户,2002年由于地质灾害影响政府又组织搬迁了50多户,到开发前篁岭古村已经有一大半的村民搬至山下居住。如果不进行开发,消失的不仅是篁岭这个古村落,“晒秋”农俗也将随之深埋,更别提发掘今天篁岭色彩绚烂的“晒秋”美景。立足于传统理想化理念,来审视景观化的村落民俗“本真性”,显然是苛刻的,因为“本真性”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具有多义性和不易把握的本质”(28)瑞吉娜·本迪克丝:《本真性(Authenticity)》,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村落民俗的景观化尽管不是理想的保护或传承措施,但至少可以让传统村落得以保存、村落民俗得以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景观化的村落民俗,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拓展和扩充了其展示价值,也有助于生活化的村落民俗的传承和传播,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是统一的,因此,可以说也是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实践路径,一种需要继续深化探讨的路径。
景观化,作为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实践路径,可以继续探讨的地方在于去语境化、商业化等问题,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共性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第九条指出,社区、群体等保护主体“对可能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或实践该遗产的社区的任何行动的直接和间接、短期和长期、潜在和明显的影响都应仔细评估”(2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巴莫曲布嫫,张玲译,《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其中提到了要评估非遗的存续力及行动带来的各种影响,也就是说非遗保护不能仅仅注重其活态性,可以任意开发、利用,其“本真性”尽管不作为其核心原则,但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抛弃;第十条指出,“社区、群体和个人在确定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威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并决定怎样防止和减缓这样的威胁时应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明确提出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威胁。根据这两条,景观化在保护村落民俗形式的同时,拓展和扩充了其展示价值,这是其重大意义,但也存在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笔者列举两个成功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周星运用“旅游场景”的视角分析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上郎德寨,这种村民生活于其中的“村寨博物馆”的开发促进了村民生活、市场行为及心理的变化和调适,也就是说这种旅游场景实质是异文化相互接触、相互涵化的过程。旅游发展也伴随着苗寨传统生活节奏的紊乱、传统文化的变迁。这种通过展示和表演来吸引游客的行为,也蕴含了村民自身的主观建构和自我期许。(30)周星:《旅游场景与民俗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尽管苗寨采用的“村规民约”对村民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但在商业利益面前,其成效也是有限的。而且村民习惯了每天穿戴节日盛装的接待旅游团的流程,其日常生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民俗文化的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自然难以避免。郑文换提供的国外案例具有借鉴意义。韩国河回村为解决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无序的商业化现象,河回村保存会通过努力,在村外1.2公里处建设了一个商业区域,推动了居住区与商业区的分离,解决了商业化无序的问题。(31)郑文换:《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化旅游开发的乡村振兴之路:以韩国河回村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笔者虽然没有去过韩国河回村,无法现场感受其村落民俗,但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解决方案自然会有助于缓解文化旅游带来的商业化问题,但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居住—商业分区,即景区—商业区的分离无疑会带来收入的减少,其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同时,“旅游凝视”对村民生活、自我认同的解构,也必然导致村落民俗的去语境化、去主体化等问题。因此,景观化是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或实践路径,我们应从活态性的角度看待其“本真性”问题,当然,其存在的问题仍需深思和进一步探讨。
四、小结
为促进城乡交融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了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宏伟蓝图。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它客观要求传统村落的复兴。传统村落的复兴自然离不开村落民俗的保护与传承。村落民俗则是传统村落的生活面相和灵魂归宿,失去了村落民俗,传统村落也失去了生命力。从理念上来讲,村落民俗保护应“见人见物见生活”,关注其“本真性”,保护其文化生态,保护其生活属性。也就是说,生活化是村落民俗保护的基本要求。篁岭“晒秋”农俗原本就是村民的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适应环境而变通或创造的一种生活化行为,并不具有观赏性,对其进行保护则意味着保护其“晒秋”活动的“原生态”。但是,随着城镇化发展,篁岭古村因交通、用水及地质灾害等问题,生活并不便利,许多村民搬迁而去,其村落早已半空心化。也就是说,篁岭古村也面临着衰败或消亡的危险,“晒秋”农俗的消亡也只是早晚的事情。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篁岭古村得到了开发,徽式古宅得以修复,“晒秋”农俗得以挖掘和提炼,成为篁岭景区独特的亮点和风景。当然,此时的“晒秋”农俗成为被设计、被展示、被欣赏的景观的一部分,景观化代替了生活化。景观化作为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路径,虽消减了村落民俗的文化内涵,但也丰富和拓展了原有文化内涵,扩充了其展示价值,传承和传播了村落民俗,激活了传统村落的生命力。因此,不能仅仅拘泥于生活性,僵化理解村落民俗的“本真性”,在现阶段,景观化无疑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实践路径,尽管它不是一种理想路径,它还存在去语境化、商品化及歪曲等世界性难题,如何更好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讨、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