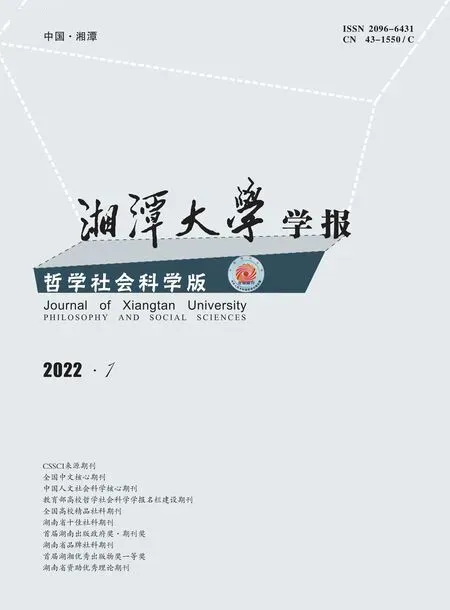《庄子·大宗师》篇名辨正*
2022-11-28邓辉,周蓉
邓 辉,周 蓉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学界对于《庄子·大宗师》篇名怎么句读,历来有所分歧。不可思议的是,在不同的句读之下又都能归结到一点:庄子以道为师或是师法大宗。方家异路同归,臆测疏解而强合庄意,缺乏对“大宗师”进行宏观的审视与语义的考察。为了更好地理解庄子思想,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大宗师》篇名进行辨正。
一、前贤对“大宗师”的解析
关于“大宗师”之断句与解释,历史上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大-宗师”,其二是“大-宗-师”,其三是“大宗-师”。
1.大-宗师
解为“大-宗师”,把“宗师”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此解虽是少数,但也有这么几位代表人物:明代中期李光缙曰:“宗师,学者所尊主之称。冠之以大,犹言众父父也,释氏言最无上乘是也。”[1]795明末觉浪道盛曰:“知天知人者,乃天人师也。知天知人,岂天人之所能哉?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于此知得,岂特为天人之宗师?”[1]796余兆清曰:“宗师,学者所主而尊之之称,冠之以大,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797李光缙、余兆清认为“大-宗师”是学者所尊崇之术的最高名称。觉浪道盛则认为,知天知人,则可为天为人之“宗师”,如果能够“非天非人”“能天能人”,就不仅仅是天人之宗师了。总体看来,李光缙、余兆清、觉浪道盛三人把“宗师”当作一个名词。但“宗师”连用,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大宗师》虽然“宗师”连用,但不一定句读为“宗师”,后文将论述)出现在《汉书·平帝纪》: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2]250-251
如上所示,刘邦以及刘邦之兄吴顷王刘喜、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等,其宗室子孙,经过数代繁衍,至平帝时已有十万余人。由于教导训诫不力,有的触犯刑法,因此,各郡国置“宗师”一职,选有德有义者任之,主要负责对宗室子孙进行教导与监察,如有不服从教导或未尽职责的宗室子孙,宗师可通过书信,告知宗伯。由此可见,“宗师”是一个职业的名称,始于汉平帝时,“宗师”俸禄二千石即每月一百二十斛,低于宗伯(宗正)“中二千石”即每月一百八十斛[3]984,各郡国“宗师”均可将所监察情报向宗伯汇报。此“宗师”是刘邦及其兄弟宗室子孙教导之师。此外,“宗师”连用亦见于《汉书·艺文志》中:“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颜师古注曰:“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为明法,又师尊仲尼之道。”[4]117虽然《艺文志》中的“宗师”连用,但“宗”与“师”都具有独立的含义,“宗”表遵从、遵守;“师”表师法。“宗师仲尼”即遵从师法仲尼之道。
“宗师”作为名词,并表达为一个完整概念的第一次出现以及运用,限定了我们对“大宗师”的断句与理解,如果内篇篇名出于西汉时期或者西汉之前(后文将推断内篇篇名产生的时间段),那么这里的“大宗师”就不能断为“大-宗师”。
2.大-宗-师
断为“大-宗-师”是指将“宗”与“师”独立出来,分开解释。有如下学者:郭象曰:“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5]229郭象之解有个重要的倾向,规避了“道”,以无心为所师的对象。郭象的宗是动词尊崇,师是师法。王先谦曰:“本篇(《大宗师》)云:‘人犹效之。’效之言师也。又云:‘吾师乎!吾师乎!’以道为师也。宗者,主也。”[6]55王先谦训宗为主,这个“主”是名词“主宰”,王先谦十分谨慎,并未明言“大宗即道”。
陈鼓应先生认为,“‘大宗师’——即宗大道为师”[7]184。陈鼓应虽然没有具体给出各字的解释,但是根据他的翻译,这里的“宗”为动词“尊崇”,“师”为名词老师、师父或学习的对象。方勇先生指出:“大宗师,即以道为宗为师,庄子认为,大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是产生宇宙的绝对本原,是天地之间的最高主宰,万物万众都必须绝对地以它为宗,以它为师。”[1]805方勇的“以道为宗为师”是在郭象的基础上,将“无心”换成了“道”,并吸收了王先谦“以道为师”的观点,从而综合起来:“以道为宗为师。”方勇将宗作为名词,师也是名词。断为“大-宗-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往句子里添词”。无论是郭象的“无心”,还是王先谦、陈鼓应、方勇的“道”,都是“大宗师”未曾直接表达的或不曾包括的,故诸家之解亦是以己之意进行的疏解。
3.大宗-师
以“大宗-师”为断句的有王船山,船山吸收郭象无心之说,结合庄子对成心的批判,提出:
凡立言者,皆立宗以为师,而所师者其成心,则一乡一国之知而已,抑不然,而若鲲鹏之知大,蜩鸴之知小而已。通死生为一贯,而入于“寥天一”,则“倏、忽”之明昧,皆不出其宗,是通天人之大宗也。夫人之所知,形名象数,是非彼此,吉凶得失,至于死而极。悦生恶死之情忘,则无不可忘,无不可通,而其大莫圉。真人真知,一知之所知,休于天均,而且无全人。以阕虚生白者,所师者此也,故唯忘生死而无能出乎宗;此七篇之大指,归于一宗者也。[8]130
船山认为,立宗为师,既已成心,所得不过是小知。若有“通死生为一贯,而入于‘寥天一’”者,也就是“通天人之大宗”。何谓“寥天”与“大宗”?“寥天者,无生也,无死也;哀乐现其骇形,如浮云丽空而无益损于空,夫乃无撄不宁,而生死一,是之谓大宗。”[8]142船山认为在“寥天”的世界里,无生无死、“不死不生”“忘生死”,实则是“未始”,人能“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安排去化,才能“与寥天为一”[8]141。“大宗”为何?根据船山“夫乃无撄不宁,而生死一,是之谓大宗”[8]142,以及“所谓吾师者,合天人、生死而一之大宗也”[8]142的表述,我们可以知晓,船山的“大宗”即为“寥天”,二者都在于“死生为一”。船山对“大宗”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以阕虚生白者,所师者此也,故唯忘生死而无能出乎宗”,船山在此引用了《人间世》中“坐驰”的概念,“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5]155。由此可知,船山对“大宗师”篇名的解释即为:师大宗,与寥天为一。而通大宗的关键一环是生死为一。船山敏锐地把握住了一点:既然已经立宗了,何以不会是师法成心?船山提出师法“阕虚生白”。因此,船山之“大宗师”看似师法大宗,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师法无宗。这也是郭象的观点:“游于不为而师于无师也”[5]288。船山之解与庄子本人之意高度吻合,但也存在一个疑点需要追问:“大宗师”是庄子本人自拟的篇名吗?如果不是,那就必须得重新审视“大宗师”的含义以及命名者的用意。此外,林希逸、朱得之、沈一贯、陈治安、吴默、高秋月等前贤皆作:“大宗师者,道也。”[1]794-799以上诸家没有考虑的一点就是,“道”莫名其妙就从“大宗师”这个篇名中跑出来了,没有思考这个“道”到底该从“大”、从“宗”、从“师”、从“大宗”还是从“宗师”解出来。如果都不是,那“道”在这里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解出来的吗?张士保曰:“宗亦主,义为天地造化之根元,故曰‘大宗’,即所谓‘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本无可名,强名曰‘道’。”[1]803以“大宗”寓“道”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庄子之意?比如说,刘武就认为庄子“谓天为宗,而谓道为大宗”:“所谓大宗者,道也;所谓大宗师者,以道为师也。”[9]144刘武用外杂篇中庄子后学的概念解释内篇的概念,并以此代替庄子思想,方法上有可取之处,但在具体内容上还是要慎重,因为内篇没有“大宗”一词(除了篇名《大宗师》之外),怎么能认为庄子“谓道为大宗”?
无论如何句读,或者采取哪种方法进行诠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对内篇篇名进行一个宏观的审视,对“大宗师”进行语义与哲理上的辨析。
二、从整体视域审查《庄子》内篇篇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司马迁所见的《庄子》尚有“十余万言”,而现在的通行本,也就是郭象本,约八万字。《经典释文·序录》云:“然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5]5从这一段文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其一,“后人增足”,即后人对《庄子》一书进行了文本添加,并且添加的文本所反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离庄子之意甚远;其二,这个“后人”到底是庄子后学还是秦汉以来的后人,难以确定;其三,郭象指出,《庄子》文本中存在一些“妄窜奇说”,即与庄子思想特别不相符合的奇说杂篇。值得强调的是,这段有关郭象的引文并不能证明郭象芟剪了《庄子》诸篇。但可以确定的是,郭象之时,《庄子》一书杂乱缤纷,版本各异。
1.《庄子》内外杂篇的命名方式
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序》中有言:“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于题下即注解之,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之类是也。”[5]7成玄英试图解释内外篇篇名命名理由,认为内篇单独取篇名的原因是“内篇理深”。这个解释确实难以服众,因为内篇并不都是“理深”,比如说《人间世》《养生主》《应帝王》。针对《人间世》,冯友兰就曾指出:“我认为庄之所以为庄者,突出地表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之中。这两篇恰好也都在郭象本的内篇之内。但是我认为郭象本内篇中的有些篇,例如《人间世》,就不代表庄之所以为庄者。《人间世》所讲的‘心斋’和《大宗师》所讲的‘坐忘’就不同。‘坐忘’是代表庄之所以为庄者,‘心斋’就不然。”[10]348笔者认为,《人间世》有以不材为材,无用为用,求生全身之意,与逍遥物化之旨不合。且有戒慎恐惧,斋心正身之规,颇类儒家遵守操持之法,与庄生风度不类;立意趣取,不似庄生,至少不能代表成熟期的庄子思想。相反,外杂篇有很多作品就未必“理不深”。船山就认为《天地》篇“有与《应帝王》相发明者,于外篇中,斯为邃矣”[8]175;认为《达生》篇“于外篇中尤为深至,其于内篇《养生主》,《大宗师》之说,独得其要归”[8]228;至于《天下》篇,船山则认为“或疑此篇非庄子之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8]351。由此可见成玄英以理之深浅来断内外之分是难以成立的。此外,成玄英之语“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也不是非常严密,比如说《庚桑楚》首句为“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选的就是篇首第一句句尾数字。
成玄英之所以刻意解释内外杂篇之篇名,是因为一部书中诸篇命名方式不一致,故而有疑惑。张恒寿也认为,内篇离奇的篇名值得怀疑。首先,篇名三个字“是先秦篇名少有的形式”,其次,篇名与内容联系不紧密[11]27—29。笔者以为,《庄子》外杂篇的命名方式与《论语》《孟子》《楚辞》的命名方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因篇首句子(第一句或第二句)情况选取有比较完整意思的词语,以及遵循“虚词不入篇名”和“作者本人的姓名不入篇名”的原则。篇名尽量避免选用虚词(除了《论语》中的《学而》《雍也》《述而》运用了虚词之外,其他作品一般遵循虚词不入篇名),比如说,《天运》篇首句是“天其运”,编辑者刻意去掉了虚词“其”。刘笑敢也认为,“外杂篇是以取篇首二三字为命题原则的……其意义都比较完整,不包含虚词”[12]49。“作者本人的姓名不入篇名”也有例可证,比如说《论语》中,有的篇章首句就是“孔子谓”或者“子曰”,但不命名为《孔子》《子曰》。在这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笔者将《庄子》外杂篇的命名方式概括为三种方式:(1)连续性选词,在篇首第一二句中进行选词,位置可靠前或靠后。靠前选词比如说《田子方》首句为“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靠后选词比如说《庚桑楚》首句为“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连续性选词是《论语》《孟子》《楚辞》《庄子》外杂篇等文献的基本命名方式。(2)跳动性选词,从首句或者首段中,跳动性地选取两个字组成一个具有比较完整意思的名词。比如《山木》篇,即从首句“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中跳动性选“山木”两字。(3)拟词,根据文意或者首段段意,从中拟定篇名。《让王》篇首句为“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编辑者没有用“让许由”或“让天下”,而是拟“让王”一词进行代替;又比如《说剑》篇首段有云:“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这里既可以看作是跳动性选词,又可以看作是根据段意进行的拟词。从篇名字数来看,连续性选词、跳动性选词以及拟词,一般是两个字,除非遇到不可分割的人物名称迫不得已才使用三个字。但《庄子》内篇篇名均为三字,从这一点来看,《庄子》内篇的命名时间应该与外杂篇以及《论语》《孟子》《楚辞》等文献中篇名的命名时间不同。
2.历史上诸家对内七篇命名者的猜测
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指出:“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13]348苏轼对分篇与命名进行了断定: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为。分篇起于何时?张恒寿总结了几种不同观点,一是傅斯年的内外之分起于郭象说,二是郎擎宵的内外之分起于梁朝周宏正说。三是唐兰的内外之分起于刘向说。张恒寿最后指出,在刘向之前,已经有内外之分,“淮南王刘安是整理编纂《庄子》书的开始者”[11]21-22。张恒寿的观点影响较大,任继愈就认为,(《庄子》)“篇分内外,既始于汉代,《庄子》内篇应当是汉代编辑的结果”[14]58。邓联合认为,“这七个题目叠合在一起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内蕴却在总体上主要具有黄老学的特征”,通过文本所反映的思想以及比对《淮南子》,邓联合认为内七篇的篇名可能是刘安及其门人所作[15]58。王攸欣“综合各种留存史料及张恒寿、崔大华等论述”,结合《淮南子》《新序》的思想和风格,“确定内篇篇名非庄子本人所命,很可能系淮南王刘安所定”[16]64。
自成玄英以来,《庄子》内篇篇名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与猜测,无数学者试图以此为线索,解出内篇篇名出现的大致时间。除了以上著名学者从比较《淮南子》与《庄子》的思想、风格这一方法进行推断之外,近来年轻学者的研究亦值得注意。四川师范大学的张程在他的硕士论文《〈庄子〉内篇成书问题三题补证》中对先秦以及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文献的篇名进行了分析,统计表明,先秦著作的篇名主要以“二言”为主;而“三言”篇名则在战国晚期及两汉时期的著作中才广泛出现。令人惊喜的是,张程继续对“三言句式”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及至战国晚期,独立的三言句才被有意识地集中使用”,“及至汉乐府诗,三言更是被普遍地使用,三言句走向兴盛。”[17]33-34张程对“三言篇名”以及“三言句式”的考证,间接佐证了推断,《庄子》内篇的命名时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这一时间段内。
笔者以为,《庄子》内篇的篇名不是庄子本人自命的篇名,而是西汉“编辑者”定的篇名。这个“编辑者”到底是不是刘安及其门人,虽然拿不出铁证,但根据张恒寿、王攸欣、邓联合的观点,很有可能就是刘安及其门人。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已经确定《庄子》内篇篇名的命名方式独立于外杂篇之外,亦独立于庄子同时代典籍通行的“连续性选词”“跳动性选词”与“拟词”方式之外。而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参考《孟子》以及《楚辞》中屈原的作品,我们发现典籍大都是以两个字命名,而用三字命名(这里要排除不可分割的人物名字的三个字)发生于战国晚期,盛行于秦汉,由此将《庄子》内篇篇名的命名时间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这一观点是合乎历史状况的。那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间之内,“大宗师”如何句读与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对“大宗师”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语义考察。
三、“大宗师”本义及其演变
1.甲骨卜辞中表集合宗庙的大宗
许慎《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宗是祭祀先王的场所。甲骨卜辞中有大宗、中宗、小宗、新宗、旧宗、亚宗、北宗、西宗等词语。需要特别注意,甲骨卜辞中之大宗、小宗不能从周代宗法中的直系与旁系意义上来理解。晁福林先生就指出,殷代并没有直系与旁系的严格区别,“在殷商史的研究中不应当把殷人所没有的‘直系’‘旁系’的概念强加给他们,更不必把这概念引入‘示’和‘宗’问题的探讨”[19]158—159。晁福林进一步分析了大宗与小宗的区别:“过去以为卜辞里的‘大宗’、‘小宗’是宗庙建筑,‘中宗’ 是先王称谓。现在看来,并非绝对如此。应当说,大宗、中宗、小宗既是宗庙建筑,又是先王称谓。它们之间的区分标准应当和大示、中示、小示一样,以时代先后划分,而不在于所谓的‘直系’与‘旁系’的区别。”[19]164陈梦家认为,大宗小宗是祭祀先王之“集合的宗庙”[18]1988。综上可知,卜辞中的“大宗”既可表祭祀先王的集合宗庙,又可表集合先王的称谓。但在二者之间,常用的是“集合宗庙”这一含义。
2.周代宗法制中的大宗
周革殷命,历史巨变,“大宗”一词从殷商时期的集合宗庙与集合先王的称谓这双重含义演变为“宗族”中某一部分人的称谓。殷之“大宗”可指先王人群,是逝去之人;至周则不仅可指逝去的人群,还可以指活人,即“大宗”一族。由此可见“大宗”一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外延也扩大。《诗经·板》云:“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郑玄注:“大宗,王之同姓之嫡子也”[20]933,也就是周天子同姓的宗族叔伯兄弟等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公辅政,以周天子之名,封“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为诸侯,纠合兄弟宗族,捍御外侮,“以亲屏周”。
《逸周书》云:“选同氏姓,位之宗子”,“维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维周之始并(屏)”。所谓“选同氏姓”而“旁建宗子”,即指周天子分封同姓叔伯兄弟为诸侯,为周屏障之事。《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故而可知,“大宗”与“宗子”,作为周室王邦的藩篱屏障,绝不是指周天子本人,而是周天子的叔伯或兄弟等诸侯。金景芳亦认为:“大宗、宗子所说的都是同姓诸侯。”[21]207此外,马瑞辰指出,“《传》以大宗为王者,失之”[20]933。“宗子”特别强调同姓诸侯,而不是像周封纣王之子武庚等这类异姓诸侯。
“西周时期的宗族与夏商时代的氏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尊祖敬宗,而在于宗族严格区分嫡庶,并且由此出发而形成了严密的大宗与小宗的体系。”[22]213“大宗”除了指代周天子同姓诸侯之外,在周代宗法制度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即相对于小宗的“尊统”地位。《仪礼》云:“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说的就是大宗相较于小宗,处于尊统的地位。《白虎通义·宗族》云:“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由此可知,大宗统率群宗,是宗人之主与尊。毛传在解释《诗经·板》时云:“王者,天下之大宗。”[20]933我们知道“同姓从宗”,而天下姓氏各异,种族多类,因此,这个大宗已经不是宗法意义上的宗,而是天下人对君王的“尊崇”与依归。正如金景芳所说,“有宗法上的大宗,也有政权上的大宗”[21]208。毛传说的“大宗”已经是纯粹的政治领域的对天子尊崇的“大宗”,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23]461。
“君统的主体是诸侯,而宗统的主体是大夫士,君统与宗统分别针对‘国’(政治)与‘家’(宗法)的构造。”[24]39无论是政治层面的“君统”还是宗法制度里的“宗统”,“大宗”都透露出一种不可僭越,不容质疑的尊严与威势,“嫡子庶子只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礼记·内则》),庶不夺嫡,孽不夺宗,不可以支、别等“小宗”侵夺大宗,强调大宗相对于小宗具有尊卑分明,嫡庶有别,礼法合一的尊统地位。
“大宗”还是一个职业。国家设立大宗一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周礼·春官宗伯》)因此,掌管这个职位的人也称为大宗伯。
3. 老子始源之宗与庄子物化之宗
“宗”在“祖宗”这一义项下引申出始源、本源含义。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王弼注曰:“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其量。万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25]11王弼训“宗”为“主”,认为道为万物之主。河上公则解为:“道渊深不可知,似为万物之宗祖”[26]14,一个是宗主,一个是宗祖。陈鼓应两个解释都采用,“万物的宗主”“万物的根源”[27]73。通过我们的考察,宗有“本源,尊主”的含义。但根据老子“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以及“万物归焉,而不为主”的论述,笔者以为这里的“宗”不宜解为“主”,当从河上公“宗祖”义,解为“始源、本源”。“宗”说的是万物与道之间的关系,物所由,物所出,物所归:万物由之而出,故道为物宗。
《管子·轻重己》云:“宗者,族之始也。”即追本溯源,尊祖敬宗,明族人之所始。又有《淮南子·原道训》云:“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高诱注:“无形生有形,故为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为声大宗。祖、宗皆本也。”[28]11高诱之“本”强调的不是主干枝叶的本末之分,而是指出宗祖与派生的本源生起,表明无形、无音与大祖、大宗之间的所出与所由关系。
庄子在理解道与万物的关系时,使用了老子“道为物宗”层面“始源”的“宗”。(“宗”在《庄子》内篇中出现三次,《齐物论》中的“宗”是国名,不作探讨,因此主要分析其他两处)《应帝王》篇云:“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未出宗者,未有始也;“未始出吾宗”即未始有我,未始有物,未始有畛。“委蛇”“弟靡”“波流”等说的都是壶子无有一实,不形一状。壶子虚己应物,与物同伦,季咸惊怖而逃。此时之壶子已经达到了“与道徘徊”的境界,沦闷混冥,不表现为具体的形状与属性,不具体为一事一物,即游于“物之初”。
《德充符》云:“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守其宗”是心“守其宗”,是仲尼对前文常季所问“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的回答。此外,《天道》篇有云:“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文子·守朴》有云:“审于无假,不与物迁,见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专于内,通达祸福于一。”《天道》与《守朴》两处文似意类,紧扣于心,可知“守”是说心之守。兀者王骀面对死生之化,天地之变,心有所守,不与物迁。与之相反的是“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心守其宗,宗为何?《德充符》原文进步一解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死生一府,万化一气,此即我之宗、彼之宗、物之宗。由此可知,“物化为一”就是心所守之“宗”,此“宗”即恒在常存。成玄英即有云:“达于分命,冥于外物。唯命唯物,与化俱行,动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5]196因此,“守其宗”当理解为知识层面的心知物化一通。万物同宗,一化万异,人面对“物化”时听物之化而不与物遗,齐同死生而知通为一。
《庄子》内篇两处之“宗”是有差别的,“守其宗”乃是心有所守,知物化归宗;而“未始出宗”即未始有物或未出其宗,说的是物之未始。前者已出宗而欲返,后者未始而不离宗。
4. 黄老道家治理之道的大宗
将“大宗”作为“道”的代称是庄子后学黄老一派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庄子后学中不同派别强调的“道”已经不是庄子本人之道。《庄子》内篇无“大宗”(除了《大宗师》篇名之外)一词,“大宗”出现于《庄子·天道》篇:
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5]463-467
我们知道,《天道》篇是一篇具有浓郁黄老道家思想特色的作品,船山就指出《天道》篇“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8]188。刘笑敢也认为,“作为黄老之学的资料,《天道》诸篇或许比《经法》等帛书更有代表性”[12]304。这就为解“大本大宗”进行了基本立场的定性。“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郭象注曰:“天地以无为为德,故明其宗本,则与天地无逆也。”[5]466郭象点明了天地的宗本是“无为”,因此,“大本大宗”说的并不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是强调“天地之德”的王道。王道效法天地,朴素无为,齑万物、泽万世,不为仁戾。由此可知,“大本”是指治国之根本,“大宗”是指治理之术的源头,也是治道的根本。
《天道》篇云:“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宗、主、常,说的是依归、尊主、遵循。(《吕氏春秋》就明确提出:“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天道》篇进一步对“大本”进行解释:“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这种君臣上下、主次本末的关系,使得“大本大宗”展露出强烈对比意味,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再次表明“大本大宗”所指代的“道”是“治之道”。在这个基础上,《淮南子·主术训》云:“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无为是治道的本宗与根本,能“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淮南子·主术训》);这种抓根本,抓关键的治国之术,“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淮南子·精神训》)。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中的“宗”强调一种对比关系中的关键性地位,这种对比是基于本末、主次、要详的考量之后才凸显出来的。
此外,“大宗”在《淮南子》中,除了治道之本的含义外,还指“事物的本原”。《淮南子·俶真训》云:“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又《淮南子·要略》有云:“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两处之“大宗”都是在“至德之世”语境下的“大宗”。从“鸿蒙”“无畛”,有“知而无所用”;衰变至伏羲氏之世,人离童蒙而“知始”,“吟德怀和”;再降至神农、黄帝之世,万民买名誉而性命失,以巧故为刀而“剖判大宗”。故而“大宗”是指心知之纯朴,性命之初始,德性之“本原”。总体看来,《淮南子》的“大宗”呈现出来一种强烈的道德指向与政治预设,“大宗”为“本原”,喻指大道自然与治道无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概述出“宗”“大宗”本义与演变:宗是指宗庙;“大宗”是先王集合称谓与集合宗庙,由此引出宗祖,始源,而后引出老子的本源;“本源”又抽象化为“本原”,并以此作为道的代称,由此引申出主宰的“主”,在《淮南子》中有集中展现。与此同时,“本原”之宗又引发出“经、恒、常”之义,发生时间在老子与庄子之间。周代在“先王称谓”的基础上,将“大宗”转为与小宗相对的大宗一族,表活的人群;并由此产生了“大宗伯”。在与小宗的对照中,大宗产生了尊、主、本之义;同时,在“大宗”这一名词下出现了动词的归宗,遵从。“大宗”主次分明,上下尊卑的意蕴又被黄老道家吸收,引出“大本大宗”,指代治道之本,为政之根。
“大宗师”的训诂为我们解开《大宗师》篇名提供了可靠的语义基础与哲学分析背景。如果将《庄子》内篇篇名的出现时间定为“战国晚期与西汉之间”或者直接遵从张恒寿的观点,为刘安及其门人所拟,那么《大宗师》篇名的编辑者原意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思想倾向与意图?
四、《大宗师》编辑者之本意与庄子思想的对照考量
上文《天道》篇“大本大宗”一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大宗师》篇名三个字的来源。《天道》篇的作者论述完“大本大宗”之后,紧接着就引用了内篇《大宗师》的话:“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这段话在《大宗师》中是有不同语境的。在《大宗师》中,意而子见许由,意图“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许由认为意而子已经受到了尧之仁义所造就的黥劓之刑,不能游了。意而子辩解,“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许由才不得已言之“大略”:“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不为戾”“不为仁”“不为寿”“不为巧”,庄子的本意是消解掉仁义故巧,进而外物外生外天下,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但《天道》篇却故意去掉《大宗师》原文后面的“此所游已!”换成“此之谓天乐”,利用庄子语言的开放性所造就的空间,改用了庄子原意,将庄子本要去掉的东西(仁义是非、治理天下之术等)都捡了起来,并作为“帝王天子之德”,从而顺利地引入南面为君而王天下、畜天下之道。
编辑者所取“大宗师”三字用意是点明庄子之学的依归:庄子师大宗,法大宗。这个“大宗”具体是什么,编辑者并未表明。但编辑者把握住了庄子本人并未特别强调“道”这一特点,在此亦不直言“师道”“法道”,而是提取了“宗”这个概念,并以大宗暗喻道。编辑者是从什么层面使用的“大宗”,到底是出于宗法制度上的“尊统”意义,还是从黄老道家角度的“根本”,还是二者都有?笔者以为,最主要的还是在“大本大宗”之“主干”“关键”“主要”“根本”这一意义上使用“大宗”。
编辑者的意思无外乎说的是庄子之学以道为本原、以大宗为关键,强调的是师法“大本大宗”,此正是《人间世》中颜回的“与古为徒”“与天为徒”的思想。仲尼指出:“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仲尼认为,无论是“与天”“与人”或“与古”为徒,不过是“师一己之成心”罢了。最后仲尼提出了虚以待物,虚以斋心之说,“虚室生白”,以虚应万变千化。《天下》篇也对这个层面的思想认识进行了定位,无论是“以天为宗”还是“以道为师”,或者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们的境界与宋荣子差不多,“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天下》篇认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而“以天为宗”,“谓之圣人”。并特意分析了“圣人”的代表:“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之“未尝先人”,老聃之“以深为根”,二者本末精粗的主张和取舍扬弃的是非分畛依然“未至于极”。
从品评百家各自的立场这种外部视角来看“大宗师”,把“大宗师”理解为庄子以道为本原,是为主干大明;而天下诸家所学皆为枝末一曲之明,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己立“大宗”为尊为师,与儒墨各家彪炳自鸣己为“大宗”又有何异?难道庄子要抑人扬己,与百家相刃,与诸子相靡?或是自立一宗,以统百家,成万世之宗主?那岂不是又陷入“小大之辩”中去了!此外,“大本大宗”就是“天地之大全”?事实上,无论是人籁、地籁还是天籁,大知小知大年小年,朝三或者暮四,庄子早就指明“道通为一”“复通为一”“知通为一”。
从庄子思想内部审查“大宗师”,标榜“大宗”,以“大宗”为师,这种理解会让人以为只有“大宗”才可师,而其他小枝末节则不足观矣。难道只有师法大宗才能入道?在高低之间,未必就要师高尊主,庸常卑贱也可师,即所谓“道在屎尿”。《秋水》篇即有云:“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秋水》篇认为,并不是师法“是”就可以无“非”,师法治道就天下无祸乱。一旦有目标鲜明的师法对象,必定会有所忽略而陷入“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人间世》)的境地。船山亦有云:“师心不如师古,师古不如师天,师天不如师物……卫君之暴,楚齐之交,蒯聩之逆,皆师也,而天下何不可师者哉?”[8]50船山抓住了庄子之学的要害,利用以物为师,引向无不可师。
此外,言“大宗师”已有所立,立宗为师,心有所系。船山即指出:“标道之名为己所见之道,则有我矣;立道之实以异于儒墨之道,则有耦矣。”[8]96庄子不能立本言宗,立则有耦,有耦则何以破小大?成玄英就指出:“夫昭氏鼓琴,虽云巧妙,而鼓商则丧角,挥宫则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则五音自全。”[5]81-82昭氏鼓琴的例子极为清晰地说明了庄子的立场与处境,“鼓商则丧角,挥宫则失徵”;同样,如果庄子以大宗为师则有所立,立则有所是,是则生非矣。
结论
从老子到庄子,面对的同一问题是“道不可言”,给人造就的处境是“道不可思议”。在这种语境之下,我们再来审查《大宗师》篇名以及品评历史上诸家对篇名“以道为师”的理解,就会发现,既然道不可见、闻、言,亦“可传而不可授”,那么,我们还能说“师法大宗”或“以道为师”吗?
《大宗师》中,南伯子葵曾问女偊,“道可得学邪?”女偊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从这里,我们至少可知南伯子葵是不能“学道”,但是否天下人都不可以“学道”,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应帝王》中,阳子居见老聃,问:“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回复:“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有人“学道不倦”,老聃认为这不过是,为技所累,为能所苦,追求“圣人”境界的“劳形怵心”。如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庄子对天下大部分“学道”者的态度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是此处的“圣人”相对于“明王”而言,如同《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列子相对于“至人”“神人”“圣人”(不同于《应帝王》的“圣人”)而言。
庄子的“道不可学”(针对的是大部分人)以及“道不可师”的晦涩态度,在庄子后学述庄派的论述中亦可见。《知北游》中的“知”欲“知道、安道、得道”,三问而未得,表明“知”在“道”面前的茫然无措。《秋水》篇亦指出,“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人之知、求、思、辩所得之道,不过是一曲之明罢了,是亦表明“道不可致”。在道面前,人发现人之为人不复存在,反而陷入了茫然、恍然、忘然、窅然的空虚之境与“无何有之乡”;初遇此境,人显得有些慌乱与彷徨,故而《田子方》中的魏文侯云:“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
尽管庄子暗示了对“学道”的“否定”态度,但“大宗师”按照编辑者的原意,当读为“大宗-师”。师作为动词:师法;大宗作为名词:大本,同时暗喻作为事物本原的“道”;“大宗-师”理解为庄子师大宗、法大宗。而按照庄子的思想来考察,这个篇名是与庄子本人思想相悖的。因为,一旦凸显“大宗”之尊崇、本原的地位,就会与“置其滑涽,以隶相尊”的思想矛盾;而一旦理解为“以道为师”,则将“大道”降格,落于有迹之弊,并使人以为大道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天下》篇的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庄子之学“芴漠”“变化”,“莫足以归”的思想特征,用负的方式去讲或者解释,才能避免有所相悖的局面。如此看来,郭象的“无心为师”、船山的物物可师而无不可师正得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