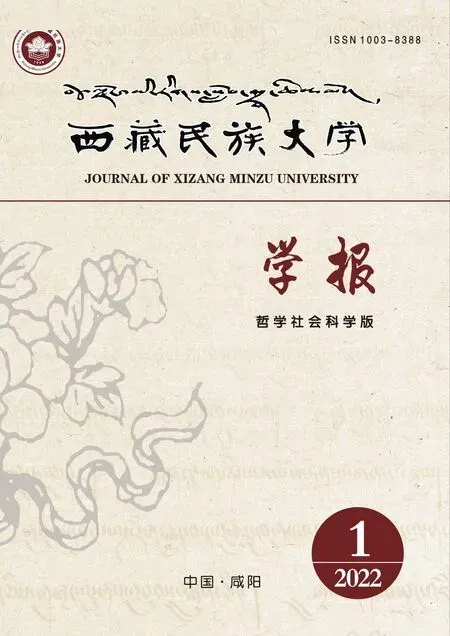《卫藏通志》所见西藏环境史及环境史资料
2022-11-27韩强强
韩强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与内地诸省相比,西藏地区的地方志为数不多,官修方志就更屈指可数。《卫藏通志》是清代西藏唯一的一部官方修纂的地方总志,约成书于嘉庆二年(1797),主要取材于西藏地方旧志、《卫藏图识》、史鉴类函、各项档案及汉译藏文典籍,是反映嘉庆二年之前西藏各历史事项的重要地方文献。[1]目前学界对《卫藏通志》的研究多集中于该书的作者考辨、编纂过程与流转传播等历史文献问题上,对该志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尤其是环境史史料价值则未曾过多发覆。[2]
环境史是21 世纪的“显学”,西藏是民族边疆地区,相较于内地,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可谓相形见绌。就像有学者所言,“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学界研究的视野及思路多集中于中原地区,对不断内地化的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环境史,被大部分主流学者在有意无意中漠视了”。[3]面对此情此景,诸多学者呼唤推进中国边疆环境史的研究,认为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乃是“尽可能地充分搜集整理和挖掘相关资料,抢占创建主题数据库之先机”,此种呼吁充分重视了边疆环境史研究中的史料建设任务。[4]但正如有学者所思考的,环境史研究“应从呼唤环境史重要,到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要”。[5]换句话说,应从呼唤环境史史料建设重要,到以具体案例来体现其重要。因此,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环境史的重视必须体现到实践上,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环境史的研究应自环境史资料的挖掘起始。①
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但关于环境史史料体系的构建尚属起步,仍需加强以为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入架桥铺路。在此背景下,无论在中国环境史的版图上,还是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建设的计划中,西藏地区都是最重要的边疆,西藏环境史的研究实践无疑对中国环境史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王利华所论“自然环境的历史面貌”“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生命护卫系统的历史”“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与“生态-社会组织的历史”这五个环境史研究的层面入手,[6]以《卫藏通志》为切入点,窥探该志反映出的西藏环境史,并揭示其中蕴涵的环境史史料价值。一孔之见恐有失偏颇,尚祈专家学者以教正焉!
一、对自然环境基本状况的记录
在所有对环境史研究内容所作的界定之中,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对自然环境的面貌及其变迁的论述应是环境史研究的当然内容。但同时不得不重申的是,在环境史之名远未舶入中国之前,历史自然地理等学科就已经十分关注自然环境变迁史的研究了。因此,环境的历史,也即自然环境变迁史,不是环境史唯一的、特有的研究内容,但是是环境史研究不能缺失的组成部分。
山岳与川流是一个地区具有标志性的地理事物,而每一部地方志几乎都会列“山川”之内容,这部分内容集中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卫藏通志》“山川”部分记诸山之名称、方位、形状、广袤及气候、植被、动物等环境状况,如“布达拉山,前藏地方,四面皆崇山峻岭,不生草木……其中原隰平衍,南北约六七十里,东西约二百余里”;又如“锅噶拉山,前藏南行二日,桑叶地方,山高积雪不消,中多瘴气”;再如“角子拉山,前藏东北,上建呼正寺……路径曲折,鸟兽寂然”;又如“克哩野拉山,前藏北途长,淤沙积雪,烟瘴逼人,自羊八井入草地,至巴彦图河皆大山难逾”;再如类乌齐之瓦合大山“在类乌齐西南,山大而峻,路险难行,四山相接,绵亘一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7]记诸水之源头、流向及水系,如记藏布江之源头、流经之地与入藏布江之冈布藏布河与朋楚藏布河之流向,记大金沙江即雅鲁藏布江的源头、流向与沿途诸汇入之河流;除条状河流之外还记水域,如记腾格尔池,言其“池广六百余里,周千里……其东有三水流入……西有二水流入……合西来数池水,东流入池”。[7]如此详细的关于山川水流等自然环境的记载,为我们了解彼时当地自然环境状况,尤其是为了解气温变化、植被面貌、动物栖息、水系盈缩等环境要素的历史面貌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是复原历史上西藏环境变迁的很好参照物,也是辨察藏地古今地理景观之差异的很好视窗。
除了“山川”部分专记自然地理事项外,在载述驿路的“程站”部分,方志编纂者亦将沿途气候、地势、积雪、密林、水草等自然环境状况纳入其中,有关信息相当丰富多样且细致入微。例如,打箭炉“天时多寒少暑”,从打箭炉至折多,“平坡逶迤四十里至折多,山麓有塘铺、有旅舍,崇冈在望,峗嵲逼人,药瘴气候异常,令人气喘,自此一揽山川至胜,蛮荒冰雪中使人心慑”;又如,东俄洛至高日寺尖卧龙石,“东俄洛南行过大雪山二座,深林密箐,矗如玉立,人迹罕至,逢三十里至高日寺,循海子而南三十里,穿大松林下山,十五里至卧龙石有旅店、有塘铺”;再如,驻藏大臣松筠乾隆六十年(1795)巡边时所记,“前藏至纳克产计二十四站,沿途俱有瘴气。又自纳克产分小卡四处……一曰拉克察,距特布托罗海七日,约程三百余里,其地草微无柴,有瘴;一曰库克擦,距纳克产十三日,约程五百余里,有烧柴,水草俱微,有瘴;一曰札克钦,距库克擦八日,约程四百余里,其地柴草俱无”“自们都至此(楚木拉)有水草,无柴,烧粪,有瘴”“自绰诺果尔至此(布哈赛勒),俱有水草,无柴,烧粪,有烟瘴”[8],对于所经之地详细的自然环境状况的描写,总是服务于旅人的,尤其提醒有无瘴气,但是对气候或者多寒少暖、地势或者崎岖平坦、植被或者林密草少的记载都或多或少无意间为我们了解西藏的自然环境状况提供了可资依凭的材料,而跨时间的同类材料的比对,无疑对我们认识西藏地区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变迁提供了可能。比如,如果我们将瘴气之地进行重点观察,会发现昔日瘴气弥漫之地今日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许瘴气之地有所减少,而这所指示的无疑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二、生命支持与护卫系统的历史
环境史的“环境”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环境,但我们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择取较为中立的“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王利华认为“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以人的生命(肉体组织)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前提来建构其唯物史观的,这应当作为中国环境史学建构的逻辑起点”“环境史学应当以‘生命’作为第一个关键词,把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把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作为思想起点,从而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9]基于此种认识,则以物质能量支撑为核心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以健康安全防卫为核心的生命护卫系统就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环境史研究者必需花费较大精力所致力的研究内容。
生命支持系统是指,“从维系人类社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食物和能源)出发,考察人们如何为了谋取生活资料不断与自然交往,不同历史时代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文明具有怎样的食物及其他物质能量基础”。[6]《卫藏通志》与其他地方志相较,其首先在体例上就已经缺失了很多内容,比如与生命支持系统特别相关的“田赋”“物产”“风俗”等内容或是简略、或是缺失。不过通检整部方志后,还是有关于物质能量支撑的蛛丝马迹。例如,在关于驿路历程的叙述中,从折多至提茹尖阿娘坝一段,“阿娘坝土产饶多,地方俨有富庶之象”;又如,从小巴冲至巴塘一段,巴塘“其地沃野千里,水泉环绕,日丽风和”,巴塘“土地饶美,天气暄妍,俨然内地也”;再如,从洛隆宗至曲齿尖硕般多一段,硕般多“居人稠密,物产亦饶”。[8]在“程站”部分所附的驻藏大臣松筠乾隆六十年(1795)巡边记亦记有不少类似内容,比如香郎“有人户,系土墙版棚碉房,有柴草,水田出稻谷,竹木与中华同”“西木多、札什曲宗夏日稍凉,故至此避暑,其方产稻谷麦豆黍稷各种,瓜果蔬菜、鹅鸭鸡猪等物仿于中国”;又记“自藏至青海西宁,具有蒙古番子七十九族住牧,其生计种田牧畜打牲各不等”“自打箭炉草地至察木多,路遥平坦,草广柴微,此一带番民多住黑帐房,以牧畜为主,有烟瘴”。[8]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蕃衍的牲畜是西藏地区人们主要的生计来源,土地出产稻麦、粟稷等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等辅食作物,地带性的草原植被又为牧养牲畜以供给肉奶等食物提供了便利,而回答一方水土是如何养育一方百姓的问题正是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生命护卫系统是说,“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考察历史上的疾病、灾害乃至战争的生态环境根源,考察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人类如何应对来自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的、人为的或人与自然交相作用所造成的灾祸”。[6]具体而言,人们常常需要为应对致病微生物而祛病愈疾、为应对寒冷酷暑而防寒降暑、为应对动物袭击与同类杀掠而驱兽御敌、为应对自然灾害的侵害而救灾减害。《卫藏通志》中的内容并不能涵盖理想状态中生命护卫系统概念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因为除了与生命护卫系统特别相关的“风俗”付诸阙如之外,“城墙”“灾异”“碑记”等内容也不见诸载录。但通检通志仍能发现人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护卫生命的蛛丝马迹,关于“避暑”的记载是驻藏大臣松筠的巡边记中提供的,其言“西木多、札什曲宗夏日稍凉,故至此避暑”。[8]关于“防寒”的记载比较间接,主要是对房屋样式的记载,驿路中山湾至常多尖宁多一段,宁多“居人以树皮为屋,仅数间”;协噶尔至咱果尔尖眉木一段,眉木“有碉房人户”;白孜至达楮尖撒喜一段,撒喜乃“黑帐房”。[8]房屋的作用除了防寒保暖避暑之外,还有抵御猛兽或敌人的侵袭的作用。但是,主要起抵御敌人作用的还是城堡,在西藏虽不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城墙,但一些城市还是设置了城墙用以自卫,如从包墩至猛布尖察木多段上的察木多“有土城,居民二百余户”;罗罗塘至协噶尔段上的协噶尔“有喇嘛寺,营官寨”;撒喜至宗喀段上的宗喀“有石堡”。[8]当然,与城堡等相匹配的军事戍守等防御敌人侵入的设置亦是生命护卫系统的研究内容。
除避暑、房屋、城墙等生命防卫的事项外,《卫藏通志》中还记有关于应对致病微生物导致的“痘疹”的记载。“为译知捐济事,照得西藏风俗,凡遇番众染患痘疹,皆逐赴山溪躲避。而被逐之人,家道可度者,日食饱暖,尚可将息望其全;可若贫苦之家,一经被逐,口食不资,露处山溪,父子兄弟夫妇至亲两不相顾,任其冻馁,无人照管,因至多有病毙者。本部堂下车以来,闻其情状,甚属不忍,当即于山僻找一空寨,捐廉购办酥油、糌粑、茶叶、柴薪,专派弁兵及已出痘之番民,早晚散给,以资养赡,半载以来,该出痘贫民等有口食痊愈者已有数百余人,想达赖喇嘛乃出家之人,以慈悲为念,积善为本,岂忍无辜番民因病受饥、束手待毙,及各大喇嘛番官等具有人心亦不忍自伤同类,相应咨移达赖喇嘛班禅烦为查照,嗣后凡遇痘疹被逐之人,必须首领倡率,捐给酥油、糌粑、茶叶、柴薪,派人前赴避痘之处,早晚照管给散,俾有口食,以免冻馁之虞,则活人性命功德无量矣,仍将如何办理缘由见覆,须至译咨者,右译咨达赖喇嘛班禅,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工部尚书和行”。[10]在应对自然界中的致病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时,西藏地区的应对措施与驻藏大臣等所认知的应对措施有所出入,这是知识、技术、策略上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面对侵害人体健康的疾病时的护卫手段,其目的都是减少伤亡。这则史料也充分地证明了,边境与内地逐渐增多的交通往来,使得内地相对完备的护卫生命的知识、技术、策略等得以传入西藏,从而改变染病者的生命体验、生命历程,体现了驻藏大臣与当地人迥异的生命关怀态度,而生命关怀无疑是环境史应当重点强调的。
三、生态认知、生态-社会组织的历史
物质能量的获取与身体健康的保证无疑是最为基本的,但环境史研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生命支撑系统、生命护卫系统的考察上。在保证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吃饱穿暖、身体健康、性命保全的前提下,人们的思想观念、群体组织、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都或多或少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关联,这些关联最终也都是为人们更好地生存服务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观察《卫藏通志》中有关生态认知系统和生态-社会组织的内容。
生态认知系统是指“人类对周遭世界各种自然事物和生态现象的感知和认知方式,以及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观念、信仰、意象乃至情感等”。中国内地汉文化传统的生态认知方式大概可划分为实用理性认知、神话宗教认知、道德伦理认知和诗性审美认知四个界限较为明晰的方面。[11]《卫藏通志》的撰述者是驻藏大臣,尽管参照了一些汉译藏文典籍,但其中能发现的关于生态认知的内容并非是藏族人本身的认知。可幸的是驻藏大臣所使用的一些山名应该是地方传统称谓,这反映的才是人们对于自然物外观的认知,如在巴贡至窟笼山尖包墩一段中有座山名“窟笼山”,此山得名于其外观,所谓“山多石穴,大者如堂、如皇,小者如钟、如盎、如钹、如铃”,对其形状的比喻恐怕是当地先民对自然景观的初步认知。[8]除了这个别之处外,《卫藏通志》中更多对于自然环境的直白认知是来自驻藏大臣的,如驻藏大臣松筠乾隆六十年(1795)巡边记记载,“前藏至纳克产计二十四站,沿途俱有瘴气。又自纳克产分小卡四处,一曰特布驼罗海,距纳克产十四日,约程五百余里,其地甚冷,瘴气甚盛;一曰拉克察,距特布托罗海七日,约程三百余里,其地草微无柴,有瘴;一曰库克擦,距纳克产十三日,约程五百余里,有烧柴,水草俱微,有瘴;一曰札克钦,距库克擦八日,约程四百余里,其地柴草俱无”。[8]对于所经途中的自然物的描写,是最基本的生态认知的范畴。如果更深一步,就会跨越到“诗性审美”的阶段,如从乍丫至雨撒尖昂地一段,“至雨撒,有人户,柴草复西行,过大雪山,路甚陡险,积雪如银”;从小巴冲至巴塘一段,巴塘“其地沃野千里,水泉环绕,日丽风和”,巴塘“土地饶美,天气暄妍,俨然内地也”。[8]“积雪如银”“水泉环绕”“日丽风和”“天气暄妍”体现的是编修方志者对自然景观的审美认知,否则不需要用如此优美的形容之语,而“沃野千里”“土地饶美”虽不是对纯自然风光的描写,但确实是对“人工自然”之田园风光的由衷赞美。藏地旅程可能要面对瘴气与严寒,但深受“诗性审美”认知方式浸染的驻藏大臣笔下的自然也有沁人心脾、摄人心魂的美感。纵然从《卫藏通志》中难以发掘出更多关于当地人生态认知的内容,但依然显示出方志对于理解生态认知系统历史的重要史料价值。
生态-社会组织包括互相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如何通过一定的观念、知识、制度和技术,将各种生态资源组织起来,构成自身生存条件的一部分”;二是“人类在适应环境,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又是如何组织自己的群体,形成了怎样的体制和规范”。[6]在查阅了《卫藏通志》之后,我们认为交通道路、疆域划定乃是属于“生态-社会组织”系统要考察的内容。
交通道路是人们创造出来以保证支持生命、护卫生命的物质及精神等与生命生存、延续有关的一切资源的寻找、获取与积累的活动能够达成与实现的客观存在物,位于川藏间交通要道的“泸定桥”就是这样的交通道路。《卫藏通志》卷首一卷为御制诗文,载录了康熙帝所撰《泸定桥碑记》,记康熙四十年(1701)之前未修桥之时,“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泸河旧渡口)焉”“入(打箭)炉必经泸水,向无桥梁。巡抚能泰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偕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址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锁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诏从所请”“桥成,凡命使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仍申命设兵戍守……继自今岁时缮修,协力维护,皆官斯土者责也。尚永保勿坏,以为斯民无穷之利”。[12]泸定河为川藏交界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设置了障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叶等物质能量的流动、阻碍了很多自然知识的邮传,本质上是为人们组织各种生态资源以供生命所需设置了障碍,而悬索的设置以及清康熙时期桥梁的建设无疑是人们利用知识、技术来构成自身生存条件的实践活动,在桥梁建成之后的设兵戍守、岁时缮修、协力维护、官员专责等制度设计,正是在人们利用桥梁组织生态资源过程中形成的,并反过来为永保桥梁这一生存条件不遭受损坏提供保障。总之,包括桥梁在内的道路系统的建设与维护为人们组织物质的、知识的生态资源提供了条件,是人与自然关系互动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内容,而这与以往的交通史研究的视角全然有别。
划定疆界本质上是确定领土的行为,领土是不同社会群体履行领土性的结果,而领土性又是通过边界划分确定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空间组织,领土性一词来源于关于动物行为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把领土需要视为一种普遍的动机或本能。[13](P720)换句话说,人类所谓的领土本质上与生物学上之领地或领域概念略同,生物学意义上的领地或领域是指个体、家庭或种群为获得食物、配偶等生存资源以保证生生不息而占有并保卫的地理空间。人类的疆域界定与动物的领地意识本质上并无不同,是人们为组织生态资源而产生的,与生态-社会组织的内涵相符合,是人们生态-社会组织的有机构成部分。像所有的地方志一样,《卫藏通志》亦专门设置了不可或缺的“疆域”部分,这部分一般界定了某行政辖区的四至八到,限定了域内人民的基本活动范围。虽然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组织生存资源的目的,但其隐含的确实是,疆域界定与守卫是人类为了避免竞争造成的生命消耗与生存竞争而设置的制度。除此之外,“疆域”部分后续关于疆域问题的官方动向,实际上是生态-社会组织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化冲突为讲和以高效利用资源保卫生命的生存策略。人类为获得生态资源以供生存而构建的生态-社会组织当不止交通道路与划疆定界二端,例如至少还有为物质交换所建立的市集等贸易网络体系、为获取更多的农田产物而建立的土地制度体系等,对这些内容的环境史视角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发掘。
结 语
《卫藏通志》作为清代第一部官修地方总志,从体例之设置与内容之择取上与内地诸地方志尤其各省通志差别甚大,常常有些名目或付诸阙如或极为简略,但大体不影响一窥西藏环境史的面貌与西藏方志所具有的环境史史料价值。本来,由于古代并未有环境科学的学科或图书分类法,也就并无专门的环境史史料文献,众多环境史所能依据的史料均分散在众多类型、卷帙浩繁的文献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地方志乃是较为系统的地方环境史史料的出处。以《卫藏通志》为观察对象,我们发现,环境史要讨论的自然环境变迁问题、生命支持与护卫问题、生态认知与生态-社会组织问题都能从中发现或多或少可依凭的资料。换句话说,地方志乃是环境史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来源,尤其对地方文献总量偏少的民族边疆地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西藏环境史史料体系的构建不妨先自地方志始。
不过,不得不强调的是,利用单一文献进行区域环境史观察是有危险的。西藏虽属于边疆地区,但存世的汉文方志等地方文献也不止《卫藏通志》,所以必须同时重视多种文献的综合利用,这样才能对西藏环境史的把握更为全面。同时,在对《卫藏通志》中关于生态认知系统内容记载的观察中,我们并未看到更多的以藏人为认知者的认知内容。因此,尤其是当我们要探讨西藏地区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时,必须主要借助藏文的文献资料或者西藏口述资料,与已知的汉文文献对生态认知历史记载作比较,如此方能达到更客观、更真实、更全面的中国环境史书写目的。总而言之,西藏环境史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西藏环境史资料体系的构建尚未完全展开,但西藏环境史的书写与建设对中国环境史的书写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期待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有朝一日西藏环境史研究能够大放异彩。
[注 释]
①西藏环境史研究及环境史资料的发掘,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更高。吾斯漫江·亚库甫所撰《波斯文历史著作〈拉失德史〉所见关于西藏的记载》(载《西藏研究》2013 年第1期)虽未以“环境史记载”为题目或主攻方向,但在文中指出了《拉失德史》中有关西藏地理、自然资源、环境疾病等的记载,这对西藏环境史资料体系的构建具有添砖加瓦之作用。但是这样的工作仍嫌不够,还有待学界同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