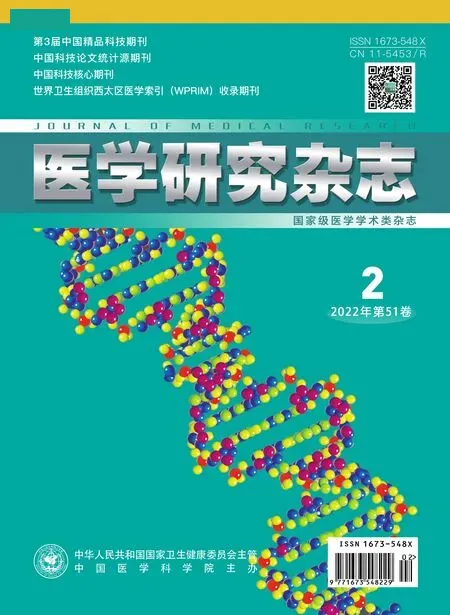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紊乱与肝脾不和之肠易激综合征的关联性分析
2022-11-26旺建伟王一鸣赵清玉赵文静隋方宇关子赫
旺建伟 王一鸣 赵清玉 赵文静 隋方宇 关子赫 张 淼
现今,很多研究者认为肠道微生态学中许多机制和观念与中医学理论体系密切相关,阐明肠道微生态与中医理论的相关本质对于研究中医药和肠道微生态的相互作用以及从中医角度治疗微生态失调等相关疾病意义重大[1,2]。且中药作用机制可直接通过调控肠道微生态与影响宿主共代谢物质而实现。因此,肠道微生态成为中医药研究的热点与切入点。近年来,肠道微生态紊乱在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病程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引起关注。IBS是目前公认的与肠道微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疾病之一,二者互为因果关系,肠道微生态失衡可引起/加重IBS患者病症。IBS机制复杂,涉及肠道动力异常、内脏敏感度、肠道免疫功能紊乱、肠道菌群失衡、肠道屏障功能异常、精神心理疾病诱发等多重因素,且多重因素间有着共同、交叉、互为影响的作用。中医学认为肝旺脾虚是IBS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在其病机演变中居重要地位。可见,中医学肝失疏泄、横逆犯脾、脾气渐虚、肝脾不和的病机观点与肠道微生态变化有关,两者间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客观的、量化的物质基础。
一、肠道微生态的概述
肠道可以看作是一个丰富的、能够自行调整的微生态,其中肠道菌群处于核心地位直接影响肠道微生态,肠道屏障及菌群代谢产物通过与菌群、机体作用间接影响肠道微生态系统。肠道菌群的平衡保证着机体营养物质供给维持,使肠道屏障发挥正常生理功能,肠道屏障为肠道菌群提供繁殖环境,保护原生菌群结构稳定。二者彼此作用,共维持肠道微生态健康。
1.促消化和营养吸收:肠道作为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基础功能是吸收营养与消化,肠道菌群也参与其中。双歧杆菌在肠道中合成人体必须营养物质,并且与其他菌群作用释放信号分子推进胃肠动力以及提高肠道免疫而抗感染[3]。肠道菌群的代谢过程中可分泌大量活性酶使消化液难以分解的膳食残留物进一步分解,并释放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SCFAs丁酸作为原材料参加肠道细胞能量代谢,与肠上皮细胞作用为肠道菌群的生长繁殖提供营养[4]。
2.调节免疫功能:肠道菌群与人体免疫之间有着复杂关联,人体约70%免疫球蛋白分泌在肠道内完成。菌群调控免疫水平,同时肠道免疫也决定菌群结构[5]。肠道有益菌诱导肠道黏膜免疫细胞识别并减少炎性反应,肠道内致病菌诱导下的炎性反应,使其他菌群不被免疫细胞所杀灭[6]。菌群与肠黏膜、肠上皮细胞及涵盖在内的菌群代谢产物构成多重御防体制[7]。优势菌群代谢产物SCFAs是肠道免疫调控的关键介质,SCFAs乙酸减轻葡聚糖硫酸钠诱导性结肠炎和关节炎,SCFAs丙酸和SCFAs丁酸对树突细胞免疫应答有抑制作用,降低炎性细胞基因转录和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8~10]。
3.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影响或参与神经系统功能。肠道菌群通过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与迷走神经连结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功能。菌群代谢产物诱导神经递质释放,影响肠内分泌细胞分泌并将信号分子通过外周血液循环传导至CNS[11]。肠道菌群代谢过程代谢产物SCFAs、间接产物神经递质与细胞因子如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多巴胺、γ-氨基丁酸(GABA)等不仅作用于迷走神经与ENS向CNS传递信号,还能进入循环系统作用于下丘脑及相关区域调控内分泌而影响CNS[12]。肠道菌群与免疫细胞作用,促进细胞因子与组胺等免疫活性物质释放而调节中枢神经功能。脑部室周器和脉络丛细胞中也有相关免疫受体的表达,能够应答细菌代谢产生的内毒素[13]。
4.构建肠道生物屏障:肠道菌群占据肠道表面,在物理空间形成一层“菌膜屏障”阻止了病原体与其他有害物质与肠上皮细胞直接接触。优势菌群因其庞大的数量在肠道微生态中有着强竞争力而占据肠道营养优先级。菌群代谢产物间接抑制致病菌群,释放免疫诱导因子(防御素、细菌毒素、抗菌肽、H2O2等),维护肠道微生态稳定。SCFAs控制致病菌生存环境,对肠道屏障具有维护和加固作用[14]。
二、肠道微生态与IBS
1.菌群失调:IBS患者基本存在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患有IBS肠道内双歧杆菌、乳杆菌数量减少使肠道定植抗性减弱[15]。SCFAs调节肠道pH值使其维持在弱酸性水平利于有益菌群的生存并控制外来致病菌群的增长[16]。肠道菌群与肠道屏障的修复更新有直接联系。肠道有益菌分泌SCFAs诱导分泌黏蛋白,与肠黏膜屏障修复物质——白介素(interleukin,IL)-18分泌有关,参与肠道免疫环节降低炎症物质表达水平[17,18]。此外,SCFAs 作为介质还可调控5-HT肠内浓度,从而间接影响着肠道动力、免疫系统、血管收缩等多项功能。IBS治疗针对肠道菌群紊乱采用抗生素及益生菌制剂疗法发挥一定效果。如抗生素利福昔明调整肠道菌群降低内脏感觉阈值使IBS得到缓解[19]。益生菌联合制剂通过改善菌群结构、减轻黏膜层炎性反应、修复肠道屏障增加定植抗性使肠生态回到平衡[20]。
2.神经免疫调节网络异常:IBS的发生、发展过程与机体神经免疫调节网络密切相关。菌群代谢产物通过ENS传递信号与CNS连接。肠神经系统涵括食道到肛门消化道内壁,大约有上万神经节和四亿神经元调控消化道平滑肌运动、消化液分泌、局部血管血流量等功能。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沟通使脑部与肠道功能关联,沿着脑-肠轴进行下-上调节或是上-下调节[21]。脑肠轴神经递质5-HT是调节网络中关键物质。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异常使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打破固有平衡状态,改变机体神经功能、免疫调节和内分泌水平。
肠道微生物群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活跃性而调节压力应答阈值[22]。通过调节下丘脑皮质酮释放因子及脑皮质与海马体中脑源性神经营养物质、2A亚型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5-HT受体表达水平调节HPA轴活动[23]。HPA轴在体液代谢、免疫调节、内分泌调节过程中释放相关物质如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儿茶酚胺等对于肠道微生态产生影响。有研究指出,应激情绪诱导的HPA轴影响肠道屏障通透性和诱导肠道免疫失调引发肠道微生态失衡[24]。菌群代谢产物进入循环系统通过HPA轴影响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CRF)合成,是导致内脏过敏症状以及肠道动力异常的因素之一。CRF与5-HT分泌有关[25]。
人体内95%的5-HT由肠嗜铬细胞分泌,是脑-肠轴关键信号物质,在调控神经内分泌与肠道功能间发挥重要作用。5-HT释放转运因子(serotonin transporter,SERT)失调使肠道动力系统紊乱和诱导IBS内脏过敏。肠道黏膜细胞和迷走神经末梢相连,接受肥大细胞发出的免疫因子(组胺、蛋白酶、5-HT、CRF)、巨噬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做出应答影响着内脏感觉[26]。IBS发展的前期环节中肠道屏障损伤以及肠道菌群失调触发免疫,肠道免疫细胞激活向迷走神经输放信号物质,降低感觉阈值而引起内脏敏感。前期研究中发现,IBS内脏过敏大鼠血清5-HT浓度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给药后内脏敏感度下调,5-HT水平下降,认为IBS内脏高敏性与5-HT的过度表达有关[27]。疏肝健脾方通过影响结肠黏膜5-HT表达和再摄取因子介导的相关离子转运而改变结肠分泌,影响5-HT及相关受体释放、降低结肠中肥大细胞的表达是给药后降低了大鼠内脏敏感的原因[28]。
IBS症状中出现情感调节功能障碍与5-HT水平异常和肠道低水平促炎反应有关。脑组织中的5-HT以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中枢情感区域影响情绪。肠道免疫激活产生IL-10、IL-1β、TNF-α、IFN-γ、IL-6等炎性物质影响5-HT合成。此外,这些炎性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可透过血-脑脊液屏障转运影响脑功能。益生菌制剂改善免疫水平和降低肠道免疫促炎物质——IFN-γ、TNF-α、IL-6、5-HIAA的表达而调高5-HT水平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三、肠道微生态失衡与肝脾不和的关联
历代医家多认为肝脾不和是肝脾之间相克乘侮不良关系。肝旺而导致肝气乘脾,脾虚而肝气克制太过,抑或是肝旺与脾虚并重,都可认为属于肝脾不和范畴。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主运化。脾胃运化功能正常,脾才能散精,机体才能吸收精微物质而发挥正常生理功能。故此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肝主疏泄,对于气机的调畅起着重要的作用,能促进脾气上升,脾升则健运,协助胃浊下降,所以肝的疏泄功能对促进脾胃受纳运化功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唐容川所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血证论·脏腑病机论》)。肝脾不和,则疏泄失常,脾有失运化。研究表明,肠道菌群是肠道吸收营养与消化功能中重要物质基础,参与机体营养物质吸收,肠道菌群失调可导致消化吸收障碍。
脾胃具有抵御邪气侵入机体的作用,《灵枢·五瘾津别论》云:“脾为之卫”, 由于饮食不当或其他因素如情志不遂,致邪气侵入,若邪气偏胜,正不胜邪,则病邪侵入机体引发疾病。肠道菌群的结构、代谢与机体有着深远的影响。肠道屏障具有隔绝病原体以及调节肠道免疫的功能。不良饮食、情绪可致肠道屏障受损、菌群失衡,即“正气不足而邪气侵入”,是引发多种肠道疾病甚至代谢异常的根源。
脾在志为思,“思出于心,而脾应之”。思虑过度,所思不遂,“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有碍于脾之运化。故思虑过度,常致不思饮食,脘腹胀闷等症。肝在志为怒,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气机调畅,气血和调,则心情舒畅。肝失疏泄,或肝郁气滞,或升泄太过,均可致情志异常。肝脾不和可致情志失畅。脾胃疾病症状中常出现焦虑、抑郁等情志不良症状,焦虑、抑郁症患者亦常出现肠道菌群失调症状,说明人体情志变化与肠道菌群有关。内分泌功能与情志变化均由脑部神经系统调控,肠道微生态的失衡与肝脾不和的关联亦可以看作是肠道菌群与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相互作用。CNS通过转导神经递质向ENS输送信号或影响内分泌的途径影响着肠道菌群。菌群代谢产物通过诱导神经递质释放、激活免疫、改变肠道分泌等途径影响神经系统功能。菌群代谢产物通过肠黏膜上皮细胞作用,肠神经受体信号转导等路径,使肠道菌群与脑肠轴实现交流。脑部神经免疫网络决定情志与机体各个器官的代谢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调导致神经免疫网络调节异常,从而在疾病中表现出肠道功能紊乱与代谢、情志失调的双重症状。
由此可见,中医脾胃主受纳运化,肝主疏泄调情志,与肠道微生态的功能均有直接关联性,肠道微生态学当中许多机制和观念与脾肝理论体系密切相关,二者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相关性。阐明肠道微生态与肝脾的相关性既有助于研究IBS与肠道微生态变化关联,又能从中医角度分析及治疗IBS微生态失调。
四、总结与展望
IBS是一种表现为肠道功能异常,涉及内脏感觉、情志不良的社会心理疾病,病因病机复杂多因,非单一角度而能论证其机制。中医的整体辨证分析研究IBS具有全面、客观特点,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对于胃肠道运动功能、肠道免疫、内脏感觉、精神状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与中医整体辨证观有异曲同工之处。故此,以肠道微生态变化为切入点,结合中医学与肠道微生态学,通过客观的、微观的、动态的微生物学基础分析、阐明中医证候,为中医辨证提供客观化、规范化的依据。亦为复方中药与肠道微生态及其与宿主共代谢物相互作用的研究则提供作用实质内涵分析基础,为中医药理论与肠道微生态学相关研究提供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