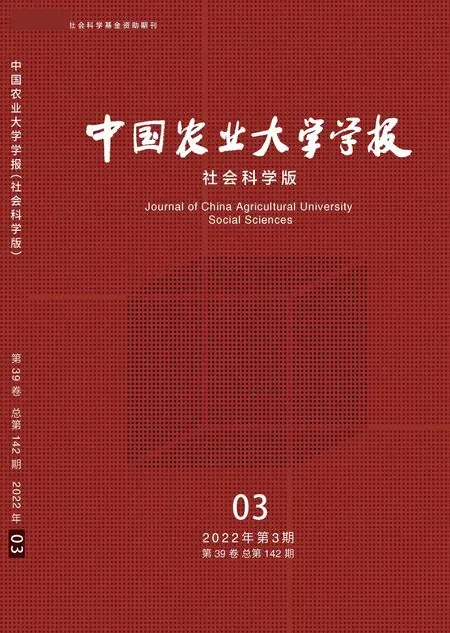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与伦理实践
2022-11-26胡梦茵
胡梦茵
确立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在实践层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语境之下,农业文化遗产的识别与界定工作都已经形成了规范而有效的标准。但农业文化遗产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之中继续留存,即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依然是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简要回顾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议题的相关讨论,并试图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以及伦理研究的观点,厘清农业文化遗产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的伦理关系与多元的伦理主体。通过ANT理论视角的拓展,我们将伦理行动的主体由人推及非人的生物、技术以及市场、制度、政府等等,从而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伦理关系网络得以以一种整合的、全面的视角呈现出来。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否成为其中伦理关系的基础,又会怎样影响现实中的行动?厘清这些问题可以为透视当下农业文化遗产的存在状态与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危机与保护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界定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闵庆文,2007);同时指出“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人类面临的食品安全与贫困缓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补偿、文化多样性保护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孙庆忠,关瑶,2012)。
在FAO的定义当中,农业文化遗产首先被指明为“土地利用系统”与“农业景观”两类。“土地利用系统”涉及农业技术(地方性知识)、物质工具(物质性)、系统中农业活动的实践者(能动性)和土地(客体化的生存世界/行动对象)。“农业景观”则涉及经济系统(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交易)、政治系统(土地产权管理、税收以及村落政治结构)和具象化了的物质空间(空间结构/宇宙论)。这些议题都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地区可持续发展”。从这三者之中,我们又可以抽象出更基础的价值维度,比如,人-生物/环境的权力关系维度与社会进步主义的维度。在人与生物/环境的权力关系维度中,人类行动者处于被约束或者控制的一方,生物上的多样性指的是当地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原本存在的“非人类居民”,而非人类后天设计或有意引进的物种。虽然在实践中,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一直包含着持续的物种的挪移、利用、共生以及驯化。但在“生物多样性”的诉求中似乎更强调“本土”和“原生”的特性,即在“土著政治”领域更常见的那些诉求。同样,除了本土居民与外来居民这一对权力关系外,还存在着现代(性)与地方(传统)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除了隐喻土著政治抗争的合法性之外,还代表着明确反对现代农业扩张、反对现代动物园式改造工程等等的价值取向。而“地区可持续发展”也不仅仅是约束人类对自然环境粗暴无度的索取,还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平均或协同发展的意涵。地区内部各个地方、社会内部各个方面或系统、社会之中各个阶层或人群以及整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都是一种平权且联盟的关系。这种价值取向显然可以成为社会进步主义的限定语或注脚。“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有明确的社会进步主义价值标准——“发展”一词是正向的指向。关于权力关系的讨论限定了发展的唯一路径,也否认了其他途径达到发展的正当性或价值性。“经济”与“文化”这两个要素的选取显然是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话语预设的产物。但这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语境无论是在现实维度还是在理论维度都是“农业文化遗产”不可忽视的前提。
这些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及其所承载的价值取向,都被认为应当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并且需要具有独特性。这个定义同时也是选定标准,暗示了另外一些互相匹配的价值要素。比如,虽然默认现代和资本主义的语境的存在,但仍特意强调“农业文化遗产”似乎应该处在“农村”。这背后隐含着的“农村-城市”的二元区分,也带着前文所述的代表着现代与传统相抗衡的土著政治的影子。同样,对于长时段的限定不仅贴合“遗产”这一术语本身,还为延续的时间赋予了一种价值量,即其价值依附于时间单位,并且可以计算和积累。尽管这样的表述有功利主义认识论的嫌疑,但是在广义的“遗产”概念中,由此带来的“越古老越有价值”的认识依然是一个有效的价值要素。同样,“协同进化”暗示了一种平权主义的倾向与色彩,而“动态适应”则试图将“变化”这个不带色彩的中性的过程描述为一种科学主义之下的价值要素。无论是“进化”“演化”,还是“适应”,这些生物学的词语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下往往会带上科学主义的色彩,词语本身就会被赋予极大的价值量,即“变=兼容=好”,或是“不变=不兼容/孤立=不好”。
由此,从FAO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概念背后一些重要的价值标准。在罗宾斯的价值领域(Value Sphere/Domain)理论中,文化是由诸多价值领域组成的一个阶序(hierarchies)。价值领域又是围绕某一核心价值(paramount value)而组成的行为阶序。不同的价值领域各不相容,并且组成了一种价值的层级关系(Robbins,2012:117-132)。简言之,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某一特定的价值领域,都是由一组核心价值以及其下一些相容或不相容的外围价值组成的金字塔层级。如果将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以及相应的实践行为都看作是一个“农业文化遗产价值领域”,那么重要的工作便是确定其核心价值和具体的外围价值。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化遗产价值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两个连贯的价值表述是平权主义与进步主义。围绕这两个核心,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土著政治权力、科学主义、历史尺度与变动偏好等组建起了外侧的阶序。同时,食品安全与贫困缓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补偿、文化多样性保护这五个意义取向也可以对应到这一以“平权-进步主义”为核心的价值领域中来。
在厘清了“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和实践的价值领域之后,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相关问题也就可以得到梳理。首先,已有研究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保护工作存在主体缺失、保护对象不明等问题(李明,王思明,2012);农业文化遗产地确立之后的保护又被一般性地理解为用经济发展来替代保护区式的工作,因此讨论集中在如何开发和利用农遗资源,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常见的措施是生态农业发展(李文华等,2012)、生态旅游开发(常旭等,2008);保护工作依赖于外部政策的规范与社会多方共同参与(赵立军等,2012);等等。其次,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讨论焦点还集中在保护工作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内容。从上文对核心定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因此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和理解也常常因地而异。总体而言,地方性知识(技术)、物质工具、生产组织模式以及空间结构是比较一般性的保护对象。而由于这些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同,涉及的保护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加大了某些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最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背景、人口从乡村地区的迁离成为许多地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突出困难。与此同时,现代农业扩张的威胁一直存在,在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两种农业实践之间,农民往往无法基于长远视角做出正确的选择。总而言之,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一直是危机与成就并存。因此,多方共同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就在于激发各成员主体的主观性,形成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动机只有符合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核心价值,才能真正推进保护和传承工作的进步。
二、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
价值构成了一般行动背后的伦理维度。因此,在厘清FAO规划和设定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农业文化遗产中存在且支配着行动的伦理关系。在此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扩大伦理主体的范围。这符合“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界定:农业描绘了人与非人世界的互动,文化则包含了人的一切社群活动,而遗产则将不同代际的人群联系起来。因此,对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伦理主体的分析,必然是一种多元中心主义的、历史的视角,这种多元中心主义正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带来的可能尝试。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一种研究利益参与者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影响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人类主体(actor)与非人类主体(actant)进行对等性观察,探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异质性网络以及其中关键的转译过程。这一理论意在消除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分的研究范式。同时,非人的主体既能包含人类世界的“被动作用物”,也能涵盖宏观性的制度、结构、技术等,因此也打破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界限,有助于还原真实世界当中事件的发生逻辑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行动者网络理论拓展的主体并非只是将“能动性”(agency)的概念予以泛化,而是想要避免对人作为唯一且绝对的主体的预设。同样在伦理主体的拓展之中,非人主体的讨论也无意追究其是否有道德可能、自由意志的可能以及绝对的目的性的可能。市场、地方组织和技术等各自在强烈的价值取向的驱动之下而具有了伦理的可能。同时,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也迫使其他主体配合自身的运作过程使其有了成为主体的可能。因此市场创造新的需求而使得地方配合、特定的作物品种要求特定的饲养/种植方式和农药化肥的使用需求等等,都可以视为多方伦理主体互动的可能。这种互动最终会在社会场景之中以道德化的表述方式展现出来,但事实上多个主体之间,各自的运作轨迹也会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发生变化或者偏离。
土地、作物等生态系统中的他者存在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被动的客体。但一方面,正是它们形塑了地方生计系统的可能模式,从而最直接地决定了该地农业文化遗产的形貌;另一方面,农业耕种方式与地方社会的组织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贯性,作物也因而影响了地方社会结构的可能形态。更多研究表明,农业劳动体验、农民代际间的地方知识传承、历史的情感性的亲密感的建构以及相关农业神灵与农业节庆的内涵等,都极大地被作物本身的生长需求及其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的关系所形塑(施宾格,2020;金茨堡,2021)。因此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脱离实际的人的运作模式,而是讨论一群人的农业体验和生存体验。因此,形塑这一体验的其他参与者在此种意义上对人负有一种伦理的责任,彼此诉求、彼此满足、彼此回馈。
当然,农业从事者与生产者依然是农业文化遗产中最直观也最主要的伦理主体,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的稻农,澜沧江下游古茶树群遗产系统中的采茶农和炒茶工等。他们的几乎所有行动都可以被视作伦理性的,也就意味着可以赋予一定的道德衡量。因此他们的伦理主体身份不仅仅局限在农业文化遗产之内,而且还作为在外部市场、地方社会等场景之下的“道德的人”。在这里可以稍微区分一下伦理的个体与道德的个体。在本文的处理当中,伦理关系意味着参与的双方互为主体而不是单方向的施为。同时彼此的义务激发了主体的行动,因此伦理关系也被视作行动背后的动机或者缘由。而道德性在本文中更多会被视作一种社会场景之下的表述,特别是主体对自身的善恶的(合理性的)强调和辩护,对场景之中存在的其他事物的一种善恶分类(classification)或是叙事(narratives)(Zigon,2012:204-220)。因此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多重的伦理关系或者多元伦理主体可能从未进入道德表述中,但依然强有力地引起了行动的发生。
农业从事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各种道德表述之中。一种常见的表述是关于他们在两种农业模式之下的模棱两可的位置。处于工业、农业的背景之下,他们的劳作方式似乎守旧且低效。他们接受工业、农业的行为也被视为不道德或者破坏性的,比如农药与化肥以及渔业畜牧业中用到的药物。在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当地农科站推广的“由传统的、粗放的低产模式向沟坑结合、高埂深沟等高产养殖转变,由鱼的自然生长向投喂饲料、鱼体消毒和鱼病防治发展”(朱洪启,2007)被认为破坏了原有的共生体系,从而将稻鱼共生系统逐渐导向了塘鱼养殖。另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指出,这些农业生产者离开了农业生产,转而外出打工或者投入旅游业的工作之中。这其中关于“逐利”诉求的部分构成了表述的核心,如“注重其经济效益的评估,忽视或没有充分认识到其独特的生态效应与文化效应,对其文化遗产价值更是认识不足;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注重有形价值而忽视无形价值等”(郭胜晖,司徒尚纪,2010)。
这些道德表述似乎都和“进步主义”的生产思维有相关性。工业农业在效率和产量上是一种进步,经济利益直至地方社会的发展也是进步的一种体现。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产方式似乎站在进步的对立面。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正是进步主义,但是是一种平权主义加持之下或者结合之后的进步主义。因此,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生活生产方式不在于留存一种“前现代的博物馆/遗址公园”,而在于对抗工业化与现代社会的冲击,使得地方文化,尤其是农业社会标志之下的文化空间得以存在下去。这种进步主义一方面是指农业文化遗产成功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人可以使用的物质能量,成功地组织起社会生活以及形成可传递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也是指成功对抗工业化农业的齐一的暴政,保证一种地方社会生产上的多元可能。此时,小规模社会中人们的文化习俗得到尊重,而物质性的农业生产系统之外的农业记忆与情感也得到同等的珍视。因此,农业生产主体的伦理关系不能仅仅建立在一种工业进步主义的价值之上,而是“平权-进步”这一核心价值。
地方政府与政策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存续过程中往往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更是如此。将地方政府与政策规范视作伦理主体,也正是因为在其内在的治理逻辑之下,相应的价值取向会极大地对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其他主体产生驱动力量或是阻断力量。无论是土地的开发使用,还是新品种新技术的引入,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主导。同时市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入当地社会也是在一定的政策规范之下完成的。通常情况下,政府和政策的伦理职责在于完善监管和满足自身的治理需求。但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地方政府和政策的伦理职责还在于能够将“平权主义”的价值推行下去。这种平权在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以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人地共存智慧作为地方生态伦理的基础,放弃将自然视为被动客体的掠夺式的视角。同时这种平权在社会内部表现为一种资源使用以及利益分配过程上的公平,限制某一单一方面的垄断性的利益诉求。并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对于工业化农业无限扩张的抵抗,同时平衡经济利益诉求与精神文化诉求。
厘清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后,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其中的价值流动的领域,即伦理主体共同参与的伦理关系类型。农业文化遗产中,当各类型的伦理关系都以“平权-进步主义”作为其基础时,那么行动中的张力就会大大减轻。因此,梳理农业文化遗产中存在的伦理关系类型,以及它们与核心价值相匹配的可能,可以更好地展现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和路径。
三、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重伦理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中存在四种基本的伦理关系类型。在农业伦理学中有生命的动植物构成了农业伦理的对象(阎莉,高航,2021),借由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将“有生命的伦理对象”发展为非生命的伦理主体,并且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关系组合。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不同的价值成为主导,而“平权-进步主义”正是统领这些价值的核心。
(一)人-作物伦理关系
人与作物形成伦理关系是农业文化遗产这一网络之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类型之一。Archambault(2016)对莫桑比克城市花园中园丁与植物之间的情动关系(Affective relation)的研究写到,园丁把植物挖出来并在根部套上塑料袋,这个做法会造成厌氧植物的死亡,这时园丁就会面临失职的指控,尤其是情动性的他辜负了对植物本身的照顾义务。同样,贝斯基也写到了大吉岭茶园的女工在修剪茶树时“照顾茶树”的心态(贝斯基,2019:91-96)。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实践是场景中最主要的部分,而这些实践中人与作物之间会形成一种照顾关系。顺应这种照顾责任,作物也同样负有回报生产者的义务。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伦理关系不可以被简单地理解成对人类照顾孩子的某种比喻。因为人与作物缔结的伦理关系还可以从作物身上衍生出去,形成一种伦理关系的拓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回报的义务是否还存在,照顾的责任依然落在生产者这一主体身上。在农药使用的问题上,将农药过量或不合格的农产品销售出去,这便是同莫桑比克的园丁一样,辜负了照顾(农产品的接受者)的义务。显然在人与作物的伦理关系没有缔结或者较弱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责任的延伸也很难实现。
这种人与作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莫斯(2016:24-27)在《礼物》中关于互惠关系的描述:给予-接受-回报的义务。那么照顾的部分包含的工作便是一种礼物性的给予——松土、施肥、捉虫,满足作物的要求。而同样,作物的回报也以丰盛的食物或者转换而成的经济收益馈赠给生产者。这一回报过程宛若夸富宴上慷慨的饱腹款待确实对应了礼物所描述的场景。当然,若收成不佳或家畜夭折,等待回礼的希望落空,礼物蕴含的关系和义务也将破裂。顺着莫斯的思路,人与作物之间的礼物交换应当也遵循“总体社会呈现”(total presentation)的性质,因而网络当中其他的联合关系——当地社会的总体呈现也可以由人与作物间的伦理关系与义务得见。
在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中,稻田之内养鱼,鱼在人与稻作之间扮演了具有多重身份的中介。鱼通过进食杂草、吞食害虫、为稻苗疏松土壤保证供氧以及通过鱼粪为稻苗施肥(孙业红,2011),在人与作物之间扮演了合作生产者的角色。同时,鱼又是当地的农业系统的产出物之一,也就是作物这一主体。从实际中当地人对鱼文化的推崇,以及将鱼制品作为当地特色的美食,可以看出当地文化对于鱼在其生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的认知。因此,当地的人与作物的伦理关系,不仅仅在于人和稻之间,更集中地体现在人与田鱼之间。田鱼对稻作的“照料”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回馈”。
因此,当现代农业技术进入当地之后,鱼的产量逐渐成了该地生产系统产出的核心。但高效的“塘鱼养殖”并非被视作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青田的人与田鱼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人“照顾”鱼。优化的养鱼技术在这一体系中非但没有促进人-鱼-稻的关系的加强,反而使得原有的体系退化了。其原因在于,强化人对鱼的“照护”时,剥夺或者破坏了原先鱼-稻关系当中鱼作为生产者的行动力。因此,在青田稻鱼共生体系中,核心在于“共生”,即人这一生产者需要维护和平衡体系中存在的多重生产者-作物的关系。这种维护得以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鱼”这一主体身份的保持。因而,人将“鱼”视为平等的另一合作“生产者”,恰恰也与农业文化遗产所强调的“平权主义”这一核心价值相符合。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进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其内部核心的人-鱼-稻复合伦理关系正是立足于人与田鱼这一物种之间的平等的主体身份。
(二)人-土地伦理关系
在农业文化遗产之中,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是实现保护目标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人如何对待土地,土地如何回应人类活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便是协调这两种进程。同作物一样,照顾责任依然在人-地伦理关系中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两种主体之间,照顾的责任有时是双向的:土地给予人(作物)饱腹或得利;人给予土地以保护(既有的形态)。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为人为造成的土地空间,如哈尼梯田或者坎儿井的水利灌溉系统。因此,两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在生产者转译之后形成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有着强烈的保持性倾向:人应当让土地(环境)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某一样态;土地也应当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人(群)的存在。正是顺着这种保存的思路,人-地伦理关系可以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纵深推广。
在空间维度上,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一样,随着土地的延伸,这样一种照顾责任也随之延伸出去,从地方到地区,最终到达全球这一层级。现代农业中对土地污染以及水源、空气污染等的担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全球性的连带伦理责任:农业生产不仅仅要照顾好某一地区的土地状况,对进入到全球性流动的其他系统都需要履行照顾的职责。因为土地、水源等的全球性特性,对其他地方造成伤害一样被视为失职的行为。在时间维度上,人-地伦理关系延续到人类社会的代际之间,即对子孙后代依然负有照顾职责,这也是保持土地既有状态的初衷。而同样土地回馈的照顾之责也可放置在几代之后。
在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中,对农田的开辟本就是针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条件而进行的因地制宜的发挥和创造。而鱼入稻田本就是因引溪水灌溉稻田而顺势发生的情况。因此,稻鱼共生的农业体系,其基础依然是传统的水田灌溉系统。当农民开始用水泥浇筑田埂时,很显然土地无法再恢复原样。而人工投喂饲料以及鱼药的操作也使得稻田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种趋向很显然有违“保持性”的特征,也因此被视作生产系统逐渐退化的例证。
在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中,常见的争论点在于人对客体的土地施为的限度。在青田的例子中,人对土地改造的程度需要框定何种边界便是其关键所在。无法复原性的改造显然背离了“保护”的诉求,其原因在于,土地得以再生产或者不断演进(进步)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特质。水泥的混入很显然是对这一特性的一种彻底摧毁。同样,投入异质性的鱼饲料以及药品,对当地的水源和土壤来说都是一种损毁性的改变。当土地原有的这一特质被剥夺之后,其承载“进步”的能力也将消失。因此,这种重新浇筑田埂的工作不单纯是鱼塘养殖系统代替水利灌溉系统的过程,还隐含着对土地本身所蕴含的再生产能力的否定。而这一点,正是人与土地伦理关系断裂的本质原因。
(三)生产-市场伦理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商业转化一直被认为是有效且正向的发展措施。其中,如何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生产者公平地参与利益分配一直是各方关心的重点。这便涉及生产者和市场这两类主体之间形成的伦理关系。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责任和义务的指向是公平原则与正义原则。公平原则是指生产者输送进入市场以及市场回报给生产者的利益应该遵循经济交易中一般性的公平尺度。正义原则则是指市场对包括生产者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发过程需要有正义性的前提。两种原则被违背或者未被履行的情况即被视为伦理责任的失职。
同时,生产-市场间的伦理关系有着很强的资本主义语境,也必然会与前文论述的人-作物关系与人-地关系产生转译的情况。其中,公平原则保证了生产者作为主体的完整性,而正义原则则减少了社会伤害的可能。由于市场是一个跨地域的主体,因此,生产-市场伦理关系也超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的范畴,生产者与市场终端网络中的主体形成新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这样,消费者在完成农产品的最终交易流程时,也实现了对生产者的回报。回到莫斯的研究中,也就是礼物所代表的这样一种超远距离超长间隔之后的回报行为。但同样,这种回报所带来的伦理性效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生产-市场的伦理关系能够真正实现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最大效率回报,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网络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
(四)国家-地方伦理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中最后一重伦理关系是国家/政府与地方性权力结构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地方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费孝通,吴晗,1988)。这背后涉及的不仅仅是权力关系博弈的问题,还有政治道德的层面。因此,传统乡村社会语境之中的国家/政府是一种充分道德化了的形象,地方乡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也具有高度的道德性。而在当下社会,“绅权”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型权威已经基本解体,但模糊松散的地方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并且通过其中的精英村民代表在与国家/政府的接触中不断增加自身的道德性。国家/政府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原本就是道德主体。因此,两者的伦理关系是合作或互补的。国家-地方伦理关系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中其他几重伦理关系的背景和前提。在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中,平权主义带有明显的地方主权,即土著政治的色彩。而进步主义在我国语境之下依然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两者结合互为前提的“平权-进步主义”是政府对地方社会的伦理义务的基础。同时,合作互补型的国家-地方伦理关系也对其他三种伦理关系形成了监督和约束。
四、结束语
前文对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四种伦理类型的分析并未涉及时间的维度。在其名称之中,“遗产”本就蕴含了明确的历史传承的特性,同时进步主义本身也蕴含着一种向前流动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但是,在许多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时的变化以及能量的时空流转当中的循环性。这种循环性同时被代际之间的传递承载下来,因此必须在线性的向前的时间流淌中看到一种循环的特质。基于这种特质,农业神话以及农历节庆仪式都是以年度循环的方式存在于当地社会之中,比如哈尼梯田的寨神林祭祀(李晋,燕海鸣,2021)。循环性同时也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之中理解伦理关系的流动方向以及伦理义务的传递可能的重要提示。随着这种循环性从时间层面拓展到时间-空间层面,伦理流动的可能方向也会进一步扩展。
伦理关系的流动与伦理义务的转移是讨论农业文化遗产伦理维度必要的部分,而循环性似乎可以作为一把合适的钥匙。但本文的主旨在于梳理参与伦理关系实践的主体及其实践的特定伦理关系类型。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发掘,并且借由行动者网络理论达成对伦理主体的扩大,本文认为在农业劳动、食品生产、市场贸易以及行政管理中的多元伦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中有效嵌入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可能路径。